真实是摄影的金科玉律
《中国摄影》记者:您的作品大致有几个部分,拍了一辈子的“黄河人”,“上世纪80年代北京”,“改革开放初期的珠三角”,还有早期在“文革”期间拍摄的很多作品,基本上是这么四大块。近些年,您宝刀不老,依旧以极大地热情把创作投入到生活当中,贴近百姓,了解百姓,扎根百姓。纵观您的作品,不管是什么主题,也不论哪个时期,四五十年的拍摄都是跟着社会进程的脚步,所表现的也几乎都是平民百姓最鲜活的生活和他们内心的最真实感受。经过几十年的拍摄,您认为摄影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朱宪民: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做摄影研究,也有几十年的摄影实践,我认为摄影这门艺术本身它存在价值,它最重要的价值,是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所独有的功能,那就是真实,其他的艺术门类都不具备如此真实。
记者:没错,电影、音乐、绘画、文学。
朱宪民:戏曲、美术、电影,它都不存在像摄影这样的真实。所以说摄影要遵循着真实艺术的价值,我一直把握真实,时代的真实,照片的真实。我也不反对年轻人尝试新的东西,因为要百花齐放,不能光强调纪实,商业摄影、创意摄影、风光摄影,它都是很好。但是不管是风光、纪实等等,都不能抛开真实去谈摄影,这是我们要共同遵循的观点,因为摄影离开了真实,离开了摄影本身存在的价值,摄影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您的很多经典作品都是用胶片拍摄的,有不少人认为,不用胶片出不来那种味道。数码逐渐替代胶片已经很多年了,最初有些人很抵触,最后也放弃了胶片,当然目前还有很少的人使用膠片,您必然也是要改成数码相机,还偶尔继续使用胶片吗?
朱宪民:我已经完全不用胶片了。我是这样感觉,因为摄影本身存在着一种科学表现,用科学的手段来表现影像的。所以说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数码技术,我认为完全能完成摄影本身所要求的技术指标。所以没有必要去一味地追求胶片。但是有些人喜欢用胶片的那种过程去玩摄影,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持反对、赞成、不赞成的观点。
记者:反正您觉得现在的数码相机完全够用,所谓“大片”与此无关,人家愿意玩胶片就玩胶片,是个人的事。
朱宪民:对,这就是时代。像三四十年前,满街都是柯达、富士冲洗店,现在到美国、到法国你找一个冲胶卷的地方都很难了,买胶卷都很困难了。这个时代一定要相信科学,现在宇宙飞船上用的都是数码,从清晰度、层次等方面看,也就是说你想追求的效果其实数码、电脑今天都能完善地解决了。但是胶片摄影作为一种爱好、一种享受过程也不能反对。
记者:您一向强调真实,认为这是摄影的金科玉律,必须得真实,不然摄影就失去了很多意义。
朱宪民:对,我坚信摄影生命在于真实。
记者:数码在后期制作时可以很好很方便地改变画面。
朱宪民:PS。
记者:您对PS怎么看,光影、色调的调整相当于过去的暗房?
朱宪民:电子暗房。
记者:这个您不反对吧?
朱宪民:不反对。
记者:曝光不理想、局部的光影不太舒服之类,还是可以调整的。
朱宪民:当年用胶片放大照片,也有一号纸、三号纸,我认为不改变影像就行。所以说电子暗房给摄影家带来更多方便,更加简洁的去完成自己的影像。
记者:而且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
朱宪民:摄影有几个方面,记录这个时代有自己的影像,真实的记录生命的阶段,通过照相机来记录这个时代。有的人想达到自我艺术的一种表现,包括风景、创意摄影达到个人艺术的一种手段。现在全民摄影,有很多人并不是为了创作,它只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把这个东西过于强调,艺术上没有对和错的问题,什么叫艺术?艺术就是创新,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才叫艺术,和别人不一样有没有道理,别人喜欢不喜欢,这是作品的差别。现在纪实摄影在咱们摄影界也有很多的流派、追求。纪实摄影绝不是记录,简单地把它拍下来了、照下来了,今天这个时代不需要这种简单的记录,拍摄的手段太多了。怎么能表现社会时代的特点,要用自己的思维。
记者:就是把自己对社会的判断参与到其中,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记录。
朱宪民:对,千万不能仅仅是简单随意的记录,要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对社会的认识,对影像结构的处理,变成自己的一种表达。
记者:没错,摄影基本上是两件事,一个是记录,一个是表达。
朱宪民: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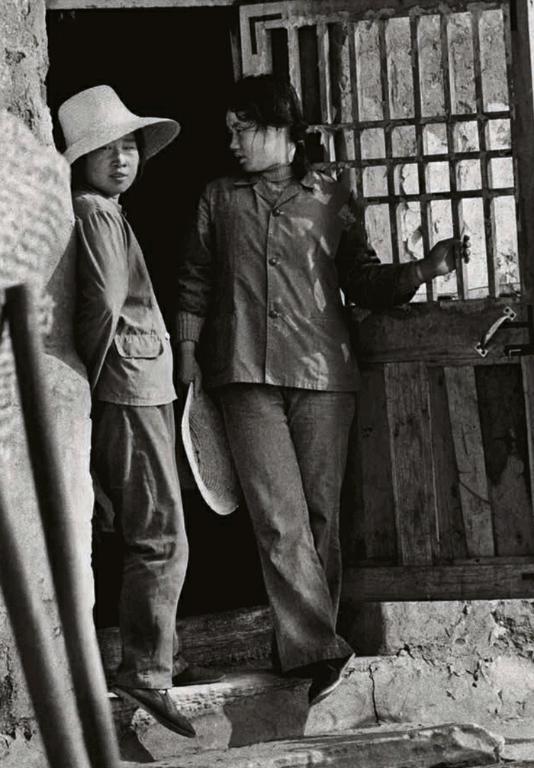
记者:所以您刚才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要不然怎么能叫摄影艺术家呢,否则就成机器了。
朱宪民:那就成监控了,监控录像了。
记者:所以既要有真实记录,也要有个人的表达,个人对世界、对生命、对社会的看法。
朱宪民:对。
记者:我个人觉得,其实摄影改变了您的人生,从年轻的时候,最初到电影厂参加美术培训班,开始接触艺术,后来去画报社当摄影记者,然后再来北京到《中国摄影》做编辑,又去艺术研究院创办摄影杂志和摄影研究。可以说,摄影完全改变了您的生活,这个生活可能是世俗层面的,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改变,但可能对您整个人的状态、思维方式,包括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目的可能都有很多影响。
朱宪民:因为尤其是我从事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必须有一个判断社会、判断人与人的关系,它需要有一个浓郁的社会知识的积淀。你刚才讲改变一个人、塑造一个人,尤其是纪实摄影,牵涉社会与人,所以这个过程使自己更加准确地判断社会、判断自己的道路。摄影是能改变人生的一种生活道路,对社会、对事业改变很重要的。
记者:您已退休多年,但好像还是非常忙,到处跑。有空闲时您还拍吗?
朱宪民:一直拍。
记者:就是说,不论到哪去在干什么,总是惦记着拍照这事儿。
朱宪民:是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社会的东西。比如说尤其是我们赶上这个时代了。我说从三中全会一直到今天,三中全会以前包括“文革”以后,就是说三中全会咱们画一条线,之前我一直关注农村、农民,那时候的农民,不客气来讲还是真正的黄河百姓,还在一个农耕时代,生产工具没变,几千年都没变,生活方式、居住条件等等。
记者:思维方式都没变。
朱宪民:对,完全是几千年、几百年延续下来的。四十多年前我刚踏入中原大地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基本上还是百年千年都没变。他们那种服饰也好,他们的生活用具、农具全都是几百年、几千年没变。我们正好赶上伟大中国历史的一个变革时期,包括深圳从茅草房到坐电梯上去,渔村草房一下子变成电梯大厦这样一个变革。我最后拍了一个农民形象,记录了中国农民最后的形象,现在没有农民形象了。现在到黄河边上去看,那里的人和咱们是一样的,穿戴是一样的,交通工具都一样的。到村里看,好几辆小轿车,家里都安空调了。现在家家都有煤气,那时候还烧柴呢。从烧柴到天然气,这是个国际化的过程,起码天然气国际化了。刚踏入中原的时候一个村一两辆自行车,基本上家家户户没有自行车。卫生所的,当教员的,在公社工作的有一辆自行车。
记者:还是公家的车。
朱宪民:今天连自行车都没有了,全部电动三轮车、摩托车、小轿车,要说现在每家有一辆轿车有点不实际了,现在如果拍新农村,家家轿车又不真实了,现在要拍农村,拍黄河百姓那就是摩托车,就是电动三轮车,这就是社会的真实。黄河边上的老百姓谁也没有想到,能有今天这种农村的变革,想都不敢想。
记者:确实赶上了好时候,这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变革最大的一个阶段。
朱宪民:伟大的变革时代。
记者:记得您说过,小时候从黄河边的家乡去东北讨生活,到了东北,别人给个苹果,您居然没见过。
朱宪民:我都没听说过世上还有苹果,书本上没有见过这两个字,也不知道香蕉。
记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在离家十几年后再回到家乡,却发现似乎一切几乎没有改变,您作为摄影家自然会用照片去关注这一切。从您的作品上看,近些年的变化非常大。
朱宪民:天翻地覆了,农村的超市跟城里完全一样。
记者:如果社会没有大的改变,纪实摄影家的日子就不好过,前几天在798举办阿龙·瑞宁格一个关于体育的个人展览,他曾经是美国很牛的一位纪实摄影师,是不是美国的好多社会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以没得拍了,才用艺术的手法去拍体育了?那么,现在的中国,咱们不说有多少社会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变革之中,所以纪实摄影师大行其道,这是最好的时代。
朱宪民:不完全是,在这30年你如果没有拍到中国的变革,你说你是纪实摄影家就有点失职了。中国历史上哪有这么一个,从农耕到今天这样的变化。我们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没有把它真实地用图片反映出来,怎么能是个好的纪实摄影家呢。虽然能赶上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是人民的幸运,也是纪实摄影者的幸运和机会,但是怎样和这个时代同步,怎样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怎样与广大百姓共同为国家的进步出力,怎样把在变革时代的百姓生活真实地记录下来,给历史留下重要的影像档案,这才是我们份内最最重要的事情。
从1980年代中国的变革一开始到今天,说老实话纪实摄影还有很多要拍的东西,比如,当前农民工的问题、城乡接合部的问题,体制和改革中间的诸多问题等等。艺术家和摄影家是通过了解社会,去看问题、发现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使它成为促进文明的工具,我们怎么把握好纪实摄影,为这个时代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刚才我讲纪实摄影的记录问题,很少人去研究琢磨纪实摄影画面的冲击力、画面的平和、画面的结构,包括纪实摄影悬挂性走入家庭、走入会议室的问题,走向博物馆的问题,最终你的纪实摄影的影像能不能走向博物馆,能不能给后人留点有价值有意义的照片,这是我们纪实摄影研究的很大一个课题。一代一代的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你一辈子搞摄影,你给这个社会给人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影像,是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东西。
现在我对纪实摄影一方面拍一些社会上的人,关注人、尤其是农民,城乡接合部的农民、农民工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因为人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你的作品叫人看的问题,不要太痛苦的一面。包括现在人们的观念都在变,人们的回忆总是美好的,回忆总是美好的,不要痛苦的回忆。有说痛苦的回忆往往会折寿影响自己的生命,所以我现在在很多方面就在尽量地拍一些,地狱什么的增加一些美感,增加一些观赏性。
记者:您认为纪实摄影最首要的是什么,怎样能成为一个好的纪实摄影者?
朱宪民:一句话,接地气。到百姓中去,了解人们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地拍摄,一定能拍出有意义的好照片。
记者:您说得没错,国外有一个艺术家说,他说世界上所有的艺术,所谓能成为经典的、长期能够留存的东西、让人叫好的东西,不管它表现是什么,但最终一定是美好的积极向上的,哪怕表现痛苦,也不是讓你跟着一块哭、一块失望、一块去堕落,一定是积极向上的。
朱宪民:布勒松《我给爸爸买啤酒》,全世界都能记住一个画面,一个快乐的少年给爸爸买啤酒,非常美好。所以说我们到了今天要与时俱进,今天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叫人们回忆更美好的一些东西,不要太痛苦。并不是说我们到处莺歌燕舞,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老百姓还是比较安居乐业,前30年、40年能有饭吃大伙都很乐,何况现在都有现代交通工具了。
记者:有人强调纪实摄影的画面要讲究冲击力,特别是一些刚入道的年轻人,想方设法弄出一个特强烈的画面。但是我看您从最初,“文革”期间那会儿的摆拍就不说了,当时是为了宣传的目的。从80年代至今,其实您的画面一直是比较平和的。
朱宪民:对。
记者:而且这种平和的纪实摄影的表现好像几十年没变,很难找一到一张张牙舞爪或者怎么样的。
朱宪民:冲击力就是让人有一种思考,冲击他的内心,平和的画面也具有一种很强的长久冲击。
记者:你是想冲击一秒,还是冲击十年。视觉冲击力或许是刹那的,默默的心灵冲击,应该更有力量。这跟观赏者也有关系,如果按相对浅薄视觉经验来判断,可能多被那种表面的东西影响,那种瞬间的冲击之后,就没什么东西了。
朱宪民:就是说少追求一些花哨的东西。有很多照片总能看到摄影者的影子,要让人看不出也感觉不到摄影者的影子。这种影子“文革”时的照片就特别重,就是摄影者在那摆的。但是对“文革”的照片,今天来讲是另一种真实,那时候必须那样做,如果不那样做就不真实了,“文革”要不摆拍就真不真实了。哪有几个摄影家能像安东尼奥尼那那样,那是另一种真实。
记者:没错。就是您拿着相机带着大家去张望。
朱宪民:对,里面别有摄影家本身的影子。
记者:别一会儿仰角、一会儿俯拍地找什么独特的角度。
朱宪民:对,越平和它越可能打动你。摄影者的介入元素越多,人们越有一种逆反,影响真实,影响冲击力。
记者:您有一张80年代在沙头角拍摄的几个女青年烫着飞机头,有时在讲座中,介绍您的作品,放映到这张大家都会心的笑。照片中的几个人当时很时髦,现在来看土得好笑。但这张照片背景不知道是一个船帆还是两个铁棍,有些乱,和主题也并不相关,反正不是那么完美,但它真的很真实。您不是刻意地去经营这个画面,而是到生活中去找这个东西。
现在这么多人拍纪实,都是拍摄最黑暗、最丑陋的,但您并不是这样,您不回避社会问题,比如贫穷落后,但没有把那些极端的、非典型性东西有意识地捡出来,来显示自己的深刻。我觉得可能还是与拍摄者的目的密切相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冲击力,就是为了恶狠狠、血淋淋?似乎纪实摄影师为了照片的冲击力去揭露问题,拍得越耸人听闻越好。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就有问题,这种哗众取宠的照片或能得到某些利用,但他的目的是不好的。您可能表现农村的贫困落后,但是是希望它好,不是看笑话,不是悲观失望,不是泼冷水,更不是居高临下,而是感同身受。
朱宪民:我同意。另外,纪实摄影不是新闻摄影,新闻摄影是今天拍今天看,纪实摄影是今天拍明天看的。
记者:说得非常好。
朱宪民:所以说国家博物馆不可能收藏新闻照片,为什么?一个新闻照片说哪着火了、哪火车出轨了,博物馆留这个没有用。它需要大的社会的演变、变革、变化过程的一个记录,它不是说某一个特殊的案例来代替这个社会的主流。所以说世界上的各大博物馆不可能收藏各地着火了、火车出轨了。所以说纪实摄影它的意义就是反映社会变革的旅程。
记者:有一个美国摄影师,他说纪实摄影师是干嘛的?他说假如明天我们有机会去火星,火星人不知道地球是什么情况的,如果只允许带20张照片,用照片告诉火星人,地球和上面的这群人是怎样的情况,你所要带的这20张照片,就是你应该拍摄的。咱们不说这么大,起码是中国以外的人,包括身处中国的人,这些年几十年发生了什么,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您照片具有这个意义。
朱宪民:对。
记者:您的作品几乎没有空镜头,画面里永远有人,如果说到一个风景极好的地方,那种自然风光很美妙,您拍不拍?
朱宪民:其实我也啥都拍,但是没有更多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风光摄影又一个领域,也是很难的,等光线、等太阳,虽然有时候我也拍,但是说老实话,拍得可能不如那些风光摄影家。我还是把大部分的精力专注百姓生活的一种变革,中国需要摄影家动点脑筋去观察这个社会,去观察它的细节。包括拍城市也一样,我拍了不少的城市,包括深圳、北京、上海,历史的遗留建筑、风情,时代的变革中的人们。像美国、法国很难有这种东西了。
记者:是啊,那里一百年不变,起码从表象上看。
朱宪民:中国复杂的社会现象,城镇化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污染问题等等,这些值得摄影家去观察去表现。现在有很多搞纪实摄影的人,觉得现在没啥可拍的了,其实是缺乏思考。
记者:您曾经说,拍摄农民工,不仅是拍摄农民工进城,还可以反映农二代,这些农民工到了城市以后,他们的第二代与社会的不融洽,还有自己身份认同等好多问题。
朱宪民:所以说大量农民涌向城市,留下了空村,他有他的后代,他有他的生活,而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都有不少问题,而且这个群体是很大的。
记者:没错,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好多问题。
朱憲民:我到东北去,看到东三省的人口外流严重,这些问题需要摄影家用什么样的思维去表现,这个历史阶段,我们把社会这个阶段人的生活状态,存在的一些问题,怎么能巧妙地利用影像把它表现出来,这需要思考,需要动脑筋。我们常流于形式,拍个火车站的人流什么的,都是形式表现。
记者:您的拍摄始终关注百姓,去拍摄怎样的百姓,又怎么去拍。
朱宪民:我更关注最底层的农民。前几天我又到了黄河边上,农民现在吃的、住的、生活状态、生活状况天翻地覆了,包括精神面貌,作为摄影家你怎么去真实的去表现。我一直说, 85%人们的生活状态才是真实的,你不能说个别的,个别的穷呀、富呀,你到美国也有乞丐,也有流浪汉的。所以你不能把个例拿到社会层面去看这个问题,你要去看85%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
记者:您还有一个弟弟在老家。
朱宪民:两个弟弟在老家。
记者:但是您从来没有拍过他们。
朱宪民:要关注大众,家人太小众了,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弟弟妹妹几乎都没拍过。
记者:个人亲情的拍摄那是另外一回事。
刚才说到您也偶尔拍摄风光,我记得,30多年前《中国摄影家》杂志创刊号的封底,是您拍摄的一张偏重艺术表现的作品,是在俄罗斯拍的一个裸体女青年,前面蒙着一块纱,朦朦胧胧很艺术。好多人大惊失色,说这是朱宪民的作品吗?对这种所谓纯粹的艺术表现类作品,您是什么态度。
朱宪民:我不拒绝任何形式的摄影作品,我也有过很多尝试,虽然纯粹的艺术摄影有时并没有像纪实摄影那样真实的要求,但也有言之有物,要真诚,不能跟风赶时髦,拍那些无病呻吟,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东西。
记者:今年是《中国摄影》创刊60年,您是《中国摄影》的老编辑老前辈,给杂志说点什么。
朱宪民:一晃60年,《中国摄影》60年,我在《中国摄影》干了10年。最近的变化很大,已经是网络时代了,纸媒衰弱了。我觉得《中国摄影》是一个旗帜性的,它是引导性的,一个中国最高的,最权威性的摄影媒体。泱泱大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摄影队伍,是摄影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中国摄影》对于摄影家的一种象征,这样就需要我们编辑坐下来,与时俱进地好好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方向问题。
我想《中国摄影》应该有典藏性,让人觉得这本杂志我要收藏,我珍藏起来。所以从内容来说应该是研究更多的表现更多国内外成功的一些摄影家,成功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市场定位决定杂志的命运,也决定杂志的未来。你一定不能抛开网络时代,也不能一味地去追求一种新摄影,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东西是不是方向?还是在探索。我不是说批评哪个人,而是批评这种理念、这种观念;不是批评哪一张作品,哪一种理念。包括对“当代”也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拍的都是“当代”、“现代”,谁不是“当代”,活着就是“当代”。所以说“新潮”这个还比较确切,新潮、新理念、新观念,它是不是一个主流?美国、法国是不是主流?
如果说我们一味引导一些新潮,这个东西把摄影走向不正规,现在有很多新的理念:我作品还需要你理解吗?我拍的东西我自己看,我要表现我的思想,我需要叫你懂吗?摄影还需要有思想吗?很多探索的理念,其实他太自我了。你想的就是世界的?那太错了。我经常这样讲,有很多的错误理念,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话不负责任,民族的怎么就是世界的?优秀的民族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不是说一味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你在紐约广场跳大秧歌去那是民族的?踩高跷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接受不接受你?你到美国去说相声,去演小品他不接受,优秀的才是世界的。这个东西现在是网络时代,国际化的时代,你的作品怎么能够国际化?怎么能走向国际化?这是我们摄影人研究的一个课题。
有60年历史的《中国摄影》,绝不能办成一个中国的摄影,要办成一个世界的摄影。比方说我们表现的是中国题材为主,但是这本杂志要国际发行,发行到世界,今天这个时代不能光局限到区域性的中国。
记者:《法国摄影》《德国摄影》做的就不仅仅是法国的、德国的摄影。
朱宪民:这个观念我特别的赞成,打破中国区域性,我们的杂志怎么能在美国发行?怎么能在法国发行?这个是我们目前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要有国际化的思维、想象和能力。
中国这么多好的作品,中国摄影水平可不差,它是一个窗口,我们要开放一点,什么Photo法国、巴黎、洛杉矶,这样的摄影活动都参加,带着《中国摄影》,带着中国的摄影作品。
你还保留那种旧的理念,作为一本杂志那是开玩笑。要生存,你不变生存不了,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生存不了。
记者:和您聊得很开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