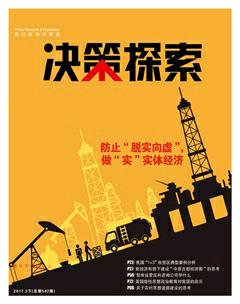文化“路向”与写作“心向”的纠缠
李喜民
在当代中国文坛,孙方友、墨白(孙郁)兄弟是一对引人瞩目的文学星座。但是,二人的写作叙事,虽然都植根于那个“陈州”、那个“小镇”(即孙方友、墨白小说中常出现的“颍河镇”)的文化生态中,但是作者的寫作“心向”却迥然不同,这里所言的“心向”是借用心理学概念,代指孙方友、墨白兄弟二人文学创作中不同的心灵图景和叙事路径的抉择,本文以此来解读文化生态与写作“心向”的内在关系,剖析文化群落与文学丛林互生共存的思想内涵。
一、文化群落与文学部落的版图切割
文学总是植根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不同的文化群落会产生血脉相连的文化部落。从古代楚文化与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中原文化与《诗经》一路走下来的文化与文学族群一直到当代绵延不绝,如湘西文化与沈从文、黄永玉,商州文化与贾平凹,中原文化与李佩甫、刘震云等,但这只是一种粗浅的划分,实际上,相同的文化群落所孕育诞生的文学部落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晰的对等关系,也不存在边界分明的写作领地划分,而是不同的写作个体不断地进行着文学版图的切割,以此来捍卫自己不同的文化个性与文学立场,在同类中成为异类,在独特中追寻着文学的丰富。孙方友、墨白兄弟从小都生活在由人文始祖文化、陈州楚文化、淮河文化、中原文化等各种大小文化形态胶着在一起的文化群落中,他们都沐浴在这样草长莺飞的文化群落中,由于两人先天秉性气质、后天成长环境的不同,兄长孙方友性格宽厚内敛,深受古陈州乡风水韵的民间民俗文化的浸润,所以他扎根沃土,为乡民立传,为乡俗增彩,为乡情增重,为乡史增色,充满浓烈扑鼻的土气。《陈州笔记》与《小镇人物》穿越于历史的陈州与当下的淮阳之中,以足够的写作韧性与执着,以饱满的写作热情与感情,建构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专属于中国文学做派的新笔记体小说重镇,属于地域文化的虔诚守护者与打捞者。弟弟墨白性格开朗活泼,几年的流浪经历让他不断参悟社会人生的底色,系统专业的学历教育又让他在乡土气息中夹杂了几分书生意气,所以他在故土中寻找思想迸发的突破口,在跳出农门走向都市的苦苦挣脱中,他在故乡的边缘地带寻找精神叛逆的逃脱口,其作品充满了怪诞神秘的洋气和现代化的市井之气,属于地域文化的审视者与开拓者。他们在相同的文化群落中寻找到了自己的文化种群,一个是民间历史文化种群,一个是当下大众文化、政治文化种群,可以说,他们殊途同归地从不同的文学向度建构着自己的文学部落,一个是向后转的真诚回望与守望,一个是向前走的真挚打探与前瞻。写作就是文化版图的不同切割。在切割中,孙氏兄弟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地与根据地,也完成了精神层面的对故乡文化群落的归依。
阅读孙氏兄弟不同的小说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生命感觉。孙方友的小说属于笔记体小说,正如鲁迅所言该文体属于“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孙方友向陈州历史与当下文化深处挖掘,咫尺篇幅,情节跌宕,追求所谓“翻三番”的艺术构思,很明显其小说的趣味是指向民间大众的,是草根文化与市井文化的杂糅,小说的文化根系是向下伸展的,小说矿藏的矿脉是沿着陈州过去与未来的时间序列不断拓展,人物身份界定在“小”上,细节界定在“微”上,艺术界定在“奇”上,这是典型的民间乡土叙事情怀。读孙方友的小说,就像瓜田李下老农的闲聊,就如冬日暖阳中几位积古老人谈天说地,轻松随意,韵味悠长,这也暗合了松散零碎的民间文化语境,适应了万物并生而不悖的文化生态。而属于先锋作家的墨白,小说的先锋意识很浓,如果说,单就小说创作中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两大维度而言,孙方友更注重“写什么”,墨白更注重“怎么写”,因为在墨白看来,小说注重的是叙事艺术,小说不是对生活的还原,而是对生活中的人们内在精神心灵世界的反映。他认为小说世界描画的是“梦境、幻想与记忆”,是“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是“欲望与恐惧”,是“梦游症患者”,小说虽然也写“小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在挣脱这种“小”中走向域外之大。孙方友小说中那种人物生存的自足感弱化,代之而来的是人物生存的焦虑与恐惧,是生活热情的下降。就如海拔很高的山脉,作为基座的民间文化,反映在叙事文学中的景观是热带、亚热带风光,而墨白的小说却是北寒带的区域地貌,笔力偏重,感觉阴冷,人物形象模糊,人物关系暧昧,这是因为墨白站在时代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边界地带,小说叙事的伦理秩序被颠覆,唯一能够把握的是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与经济文化语境叠加后对心灵情感的漠视与摧残,所以作为时代症候表征之一的先锋派艺术本身就是“冷”的艺术,以此来抗拒外在的喧嚣与燥热。就如当代全球气候变暖而人心变冷变硬、鸡鸭鱼猪要增肥而人类却不断减肥一样,“道者反之动”,在冷暖肥瘦中寻求着与世界的平衡。我们在孙氏兄弟二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相同的人物角色,却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化温度。同样写医生,孙方友笔下的“乡医刘山”与墨白小说《局部麻醉》中的“白帆”,前者人物形象明朗清晰,侠肝义胆,后者人物形象暗淡无力,他在强大的生活潮流中晕头转向,妻子与屠夫的通奸、为院长开脑颅、为院长母亲接生,高明的医术却在巨大混乱的生活场流中变得无足轻重,变成了小说叙事的反讽。小说《兵痞》中的张二豹与墨白小说《光荣院》的“老金”都是退伍老兵,张二豹因为会骑马打枪退伍后遭人们对其勤务兵角色的怀疑,但是他却活得依然坦坦荡荡。而“老金”却在磨鱼钩的无聊行为中打发着光阴,他视为无价之宝的军功章,在收破烂的老头看来,“废铁片,不值几毛钱”,甚至小说题目“光荣院”本身都是具有反讽意义的文化符号,“老金”光荣的身份与他那无聊的退伍生活构成了落差极大的反讽。孙方友的小说创作还是站在民间温和的立场,积极肯定了芸芸众生的价值存在。墨白小说却是无比鲜明地解构与批判,这些人物虽然都是置身于颍河镇的文化群落中,可是孙氏兄弟却因为依据不同文学语境,描摹出了不同的文学图景。孙方友的小说创作价值体现在为历史提供更丰富的细节真实,而墨白小说的价值却是为小说叙事提供更广大的心灵空间,提供了情感心灵最隐秘的真实。
二、文化生态与文学心态的情感交错
在当前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比较孙氏兄弟的文学创作心态,也会发现他们虽然以故乡颍河镇为创作根据地,但是二者的写作姿態却迥然不同。打个比喻,如果说孙方友的文学创作好比是在颍河镇里采风,在颍河里淘金,他的视角是社会文化的视角,而墨白好比是在颍河镇里探案,在颍河里荡舟,视角是精神与心灵的视角。在孙方友的文学图景中,颍河镇中人人都有不平凡的传奇经历,都有可圈可点的生命故事,自己只是为他们树碑立传的代言人,只是历史与现实的记录员,所以,他的创作心态是平和、包容、欣赏的心态,这源于他本是布衣出身,这些人物在他看来都书写了自己生命的传奇。虽然在《小镇人物》里有批判,但也是以淡淡“思无邪”的笔触,以委婉的语调旁敲侧击,便荡开一笔,径直转入故事的叙述,没有金刚怒目式的肝火气与怨怒色,而是经历人世沧桑后的从容淡定,小说叙述的格调是中和温婉的。我们透过这些凡夫俗子看到了平淡生活场景中,依然不乏生命的传奇,原来传奇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具有的生命基因,是芸芸众生存活于世的资本。统观墨白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作家的创作心态如颍河水般充满宣泄的湍流与浪花,他从那个封闭的底层走出到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流浪的经历中做过装卸工、搬运工、漆匠等,他真真实实地体味了更多的屈辱与无奈。如果说大哥孙方友小说中躲避隐藏了自我,建构别人的传奇是小说家的本分,对于墨白,他不可能像大哥那样把创作情感与自我情感隔离开来,而是把二者融入到一起,他的系列小说都是在这种愤激甚至是控诉般的文字中表达着自己对社会的价值判断,在诗意般的文字中,甚至会借主人公身份大爆粗口。这是墨白小说中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真实的统一,也有人认为这是墨白小说的硬伤。笔者认为,这是墨白在处理个人心态与文学心态二者关系时出现的败笔。我们不妨以他的几部中长篇小说为例,在《错误之境》中谭渔的一段心理剖白:“那个给我面子的小子肯定同我在一个酒桌上喝过酒,我记得当时就一口一个大哥地叫,我知道他当时想弄我的皮子给他的小姨子做皮衣呢,妈那个X,现在装着不认识他爷了!”接着小说中出现了“我日你奶奶”“我日你那先人”等词语,在《裸奔的年代》《进入城市》《父亲的黄昏》等小说中,这种粗口时常出现。可是,在孙方友的笔记小说中,虽然也写了很多粗人,但“粗口”极少,由此可见孙氏兄弟不同的写作心态,一个是冷静的“无我”的叙述,一个是热烈的“有我”的叙述,文学创作往往就是这样文化生态与文学心态的情感交错。这种交错,构成了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就如俄国作家喜欢在作品中穿插大量的西伯利亚风光描写、作家路遥喜欢跳出来为主人公的情感辩解一样,都是文化生态与创作心态交错纠缠的呈现。
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颍河镇,孙氏兄弟的文化“心向”截然不同,孙方友是远离都市,在对故土的坚守中,在退回乡土的记忆梳理中,找到了自己赖以为系的生命支柱。墨白是远离乡土,在文化沉淀与文学积淀的精神歧路中进行着心灵的历险之旅,在文化归依与文学叛逆的生命对抗中坚守着文学写作的圣洁,在文化时空与文学心空的思想错位处找到自己广阔的写作属地。随着孙方友先生驾鹤西去,《陈州笔记》与《小镇人物》已成绝响,但是墨白先生的颍河镇却在继续构建着自己的文化群落与文学图景。
【本文系201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创作研究”(2013BWX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旅游管理系)
—— 《印象:我所认识的墨白》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