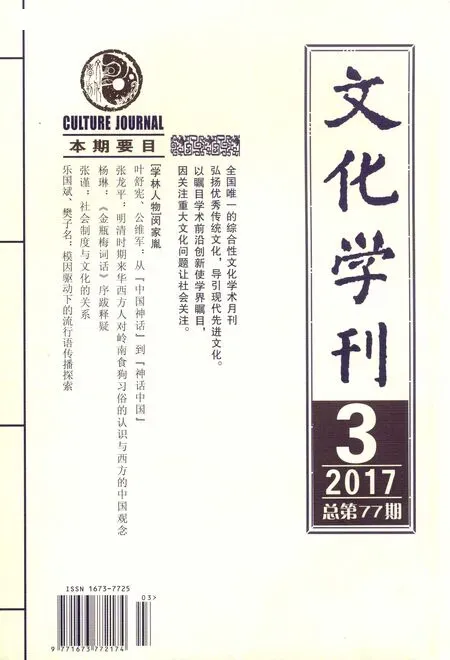哲学与科学
闵家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文化人物】
哲学与科学
闵家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放弃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认知过程感性-理性两阶段划分,采用德国古典哲学认知过程感性-知性-理性。三阶段划分。哲学是理性,科学是知性。创新实在层级结构的新模型,建立哲学同科学结盟的新关系。建立科学的哲学体系,哲学随着科学的发展向前发展。
哲学;科学;认知;实在;层级结构
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本来就复杂,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岂止复杂,简直就是相当混乱。讲清楚这个问题不光是有学理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将有利于哲学和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要讲清楚二者的异同和关系,我认为,首先要有关于人类认知系统结构的正确框架,人类认知活动到底是两个阶段还是三个阶段。这个首要问题解决了,然后才能为哲学和科学找到正确的位置,最后再来谈二者的关系。此外,我还要谈一谈我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想法。
人类认知阶段的划分
大家都知道,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笛卡尔开始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其发展有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分野。经验主义以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休谟为代表。总的来说,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或一切有关世界的有意义的陈述,都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或自我的内省经验,推崇归纳法,注重实验检验,相信只有运用归纳法从具体经验得出的又经过实验检验的命题才是可信赖的,因此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实在的可靠的认知。认知过程的划分,经验主义显然持两分法:经验的感性和科学的理性,认识总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大陆理性主义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为代表。总的说来,理性主义认为人类有先天的认知能力和理性判断,从一个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运用演绎法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用公理方法和形式逻辑构造出来的系统,内中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真的。因此,人类最可靠的知识是数学,或者具有数学严密性的自然科学。感性经验和归纳法不能保证真知,演绎推理及知识体系内部的无矛盾性才是真理的保证。认知过程的划分,理性主义显然也持两分法:不可靠的感性经验,可靠的理性结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做了意义重大的综合,创立批判哲学或曰先验哲学。康德哲学被称为批判哲学,是因为它对人类认知系统和认知活动做了批判性的全面考察;被称为先验哲学,是因为它发现在人类认知系统中有先天即先于后天经验就存在的范畴框架,如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十二个范畴,只有将后天的感性经验纳入先天的范畴框架,先天综合判断即知性的科学判断才有可能。这样一来康德就完成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不是前人普遍认为的“人的认识要服从外在事物,而是外在事物要服从人的认识”,进而得出“人为自然立法”哲学命题。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的这一命题与现代量子力学相通:量子属性跟观察者的观察活动相关。这样一来,康德就把人类的认知过程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三个层次或三个环节。
遗憾的是,从马恩最早的论述,经过列宁的反映论,到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再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国哲学界将近一百年一直把康德的认知三层次划分撇在一边,一直采用英国经验主义的两层次划分,这样一来,哲学和科学就混居在理性认识这一个层次,二者的关系就说不清。在中国,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一说是哲学,一说是科学,一说是信仰,一说是意识形态。因为,是哲学,那就要允许批判、否定和扬弃;是科学,那就要允许怀疑、证伪和推翻;是信仰,那就是宗教教义,只能灌输和背诵,一个字都动不得;是意识形态,那就是统治工具,只能宣传和捍卫,一切来犯都要击退。这样一来,像我们这样的哲学工作者的处境就很尴尬:既被要求创造性地发展,又被要求不违背基本原理,结果就只能一直在“联共党史四章二节”这个鸟笼子里飞,可还得飞出新花样:写出的论文要有新意,好像是做了创新,其实还是老一套,始终是在鸟笼子里头瞎扑腾。
有鉴于此,我坚决主张抛弃英国经验主义的认知两阶段说,采用康德发展的认知三阶段说:人类认知系统有感性认识、知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三个层次,认识过程一般来说是从感性上升到知性,从知性上升到理性。一方面,科学是知性,哲学是理性,其区分是清清楚楚的;另一方面,科学影响哲学,哲学影响科学,二者联系紧密,相互作用。
哲学同科学的关系
那么,哲学同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古代欧洲,具体说是从古希腊到16世纪的两千年,哲学诞生了,而科学还没有诞生,科学还在哲学、宗教、巫术、炼金术的混杂母体中孕育着。在这个漫长的时代,哲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主要部分,形成了大致由本体论、认识论、历史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美学组成的哲学体系。在这样的哲学体系中,追问终极实在的形而上学如日中天,自然哲学颇受重视。在这个时代,哲学走在科学的前面,同宗教和神学斗争,为科学的诞生开路和创造条件。由于既没有科学,又没有科学实在,这个时代哲学直接面对经验实在,直觉、顿悟和经验归纳是哲学家们做哲学的主要方法。
近代科学诞生之后,随着科学的成长壮大,并日益成为人类认知体系的主要部分,哲学的传统领地逐步丧失,哲学的地位日渐衰落,哲学同科学的关系呈现出极其纷繁复杂的局面
首先是笛卡尔用一个拉丁语命题“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肯定主体和心灵的存在,开启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主体同客体的关系,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上升为哲学的主要问题;研究本体论的形而上学退居次要地位,自然哲学开始淡出哲学家们的视野。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及其《导论》中,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肯定“经验综合命题”的真理性,质问“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为人类认识作出区分,为人类理性(哲学)划定界限,为经验性的自然科学开辟道路。康德继而断定,如果哲学超越他所划定的理性的界限,追问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就会像他例举的四个“二律背反”那样陷入悖论,从而失去认知意义。这显然是对形而上学的沉重打击。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科学的强势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哲学家转而想让哲学达到像科学一样语言准确,逻辑严密,结论可靠。于是,继认识论转向之后,在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推动下,二十世纪欧洲哲学又发生了“语言转向”,哲学被降低为科学的工具,其任务被局限为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拒斥形而上学”成为最响亮的号。
首先,二十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经验实证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坚持康德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语言,特别是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断言只有具备逻辑可证实性和经验可验证性的科学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将形而上学命题一律作为伪命题清除。其最具代表性的维也纳学派走得更远,试图在物理学基础上“统一科学”。同时代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干脆在实验室门上挂个牌子:“哲学家不要进来!”,可见拒斥形而上学达到何种程度。
与此同时,语言哲学在英国兴起。相信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派哲学家认为,“研究语言就是研究哲学”;哲学所能做的不是创造思想体系,不是发现规律,而是做语言分析。人工语言学派认为自然语言模糊,具有歧义,不适合表达哲学命题,于是另创符号语言,用以表述和研究哲学。反之,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则信任日常语言,认为问题出在语用上。“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语词即心灵”,通过对具体语境中语词使用的细致分析,他们为心灵哲学开启了新的路径。
然而,在初期的拒斥态度和激烈言辞过去之后,在分析哲学内部又涌现出冷静的向传统回归的声音。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分析实用主义的代表奎因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斥为不必要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并把哲学看作科学的延续。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斯特劳森做出“修正的形而上学”和“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区分,前者指思辨的形而上学,是理想的形而上学,应当拒斥;而后者指我们据以思考和谈论世界的概念框架,是现实的形而上学,应当保留。
同时期,欧洲大陆哲学选取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脱离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传统,疏远科学,转向非理性主义,转向人以及同人的主体性相关的存在、虚无、生命、精神、心理、意志、意向性、欲望、本能和无意识。非理性主义哲学主要采用内省、直观、本质还原的方法,先后产生出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洲大陆非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反实证主义,可是它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科学的影响,例如胡塞尔的志向就是要把现象学建成“精密科学”,而狄尔泰则一生都在构造他的“精神科学”。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抛弃黑格尔的体系,拯救出其中的辩证方法,然后把它颠倒过来并解释说:主观的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头脑中的反映。他们于是宣布对立统一、量变过渡到质变和否定之否定三条唯物辩证法规律就是宇宙规律,即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社会,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预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将导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定名为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且说它是建立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
简要地回顾了自从科学诞生和发达以来哲学同科学的关系呈现出的极其纷繁复杂的局面,以及在不同时间和地域曾上升为主流的这些哲学选项,我们可以对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首先,科学已经取代哲学占据了人类认知体系的主导地位,可是哲学——包括形而上学,仍然有不可取代的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并非万能,仍然不能回答人类对各种终极关怀的追问;另一方面,哲学不但能够在解答终极关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在提供全景画面、范畴框架、思维方法和逻辑-语言分析方面能继续对科学提供支持和帮助。哲学同科学的关系非常复杂,是一个需要长期探讨的问题;已经有许多选项,我们完全有权创新,也应当继续探讨,并提出新的选项。
哲学同科学的新关系
科学是硬道理,科学已经成长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主体,成为青少年十几二十年接受教育的主要内容。哲学则不断失去传统领地,节节退让——退守语言,退守逻辑,退守解释,退守非理性,退守无意识,退守存在,而现在几乎已经到了无处可退的地步;如果继续退的话,就只能退守感情,退守欲望。说句直白的话,这是哲学踏上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直至自我窒息而亡的死亡之路。那么,中国哲学为什么要死心塌地跟着欧美哲学走这条哲学自我窒息之路呢?为什么我们不另辟蹊径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路呢?中国有句源于《孙子兵法》的古语,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认为,中国哲学家们可以逆向思维,考虑重建哲学与科学的新型关系,进而不断收复哲学的传统领地。
为此,哲学必得首先端正态度和放下架子,不再妄想永远高踞于科学之上,或永远疏离于科学之外,而是谦虚地走下哲坛向科学学习,借助科学的成果、概念、模型和方法,重新研究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然后得出某些新的结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登高必自卑”。其实“metaphysics”(形而上学)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中的本意是“物理学之后”而不是“物理学之上”,现在重新回到“物理学之后”,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总之,重建哲学同科学相互尊重的关系,结盟的关系,互补的关系,互动的关系,肯定是一条新路,肯定会越走越宽,特别是在中国。因为,完全抛弃自己固有的哲学传统,跟在欧美哲学后面搞思辨,搞辩证,搞分析,搞存在,搞一百多年了,中国哲学还是没见有什么出息。
我自己准备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实在的层级结构”,探讨哲学和科学的新关系。
人类的认知系统已然形成具有四个层级的“实在的层级结构”(图1所示)。“0层级”是“自在的实在”,即康德讲的“自在之物”,或马克思讲的“客观世界”;它同人的主观世界永远有隔,任何人不可能直接认识其真相,一如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面孔,所看到的总是某种镜像。第一层级是感性实在,即经验实在;在实际生活中,在实践活动中,人通过感官、经验积累建立起的丰富多彩和触手可及的实在。社会上许多人,特别是文盲和受教育少的人,终生只生活在经验实在中。第二层级是知性实在,即科学实在;它是通过知识积累,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诸多学科建构的图解、模型、概念、定理、公式建立起来的实在。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的人,特别是科学家,他的精神经常是生活在这层科学实在中。第三个层级是理性实在,即哲学实在;它是由哲学家们用范畴、理念和哲学命题建构的最抽象的实在。少数具有理性头脑的人,特别是真正的哲学家,其精神才生活在这个纯粹理性的王国中。

图1 实在的层级结构图
如果把“信息”范畴引入哲学,取代传统哲学研究的“意义”范畴,我们就可以说:在自在的0层级和三个为我的认知层级之间,信息都是双向流动的。图中向上的箭头表示信息上行,逐级综合,从具象到抽象——殊相到共相,从单称、特称到全称命题,概念的数目逐级减少,内涵逐级缩小而外延逐级扩大,直到少数最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最一般的哲学命题。向下的箭头则表示相反的过程,逐级分析,从抽象到具象——共相到殊相,从全称、特称到单称命题,概念的数目逐级增多,内涵逐级扩大而外延逐级缩小,直到众多最具体的专名所指称的个体和单称经验命题所表述的对象。人类关于实在的认知系统就是这样建构的,关于实在的信息就是这样流动和保存的。
在这个四层级的“实在的层级结构”模型中,每两个层级之间的双向箭头又表示信息互动,互为信源和信宿:由下向上是提供信息,归纳推理;由上向下是提取信息,演绎推理。下一层级提供的命题的真实性,保证上一层级归纳得出的命题的可靠性;上一层级贮存的命题的可靠性,保证下一层级演绎得出的命题的实证性。因此,下一层级均是上一层级的基础,而上一层级均统摄下一层级;每一层级内部发生的信息编码结构的突变——新概念和新命题的涌现,以及相应的对旧概念和旧命题的顶替,都最终会引发相邻层级中信息编码结构的相应改变。
在这个模型中讨论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就容易讲清楚了;当然,首先应当声明,这里讲的“科学”是狭义科学,即关于实在的自然科学。
从远古时代,直到近代科学诞生之前,在人类认知体系中还没有第二层级——知性实在,即科学实在。哲学直接面对第一层级感性实在,哲人多从经验实在综合得出或直觉得出哲学命题,如老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庄子《庖丁解牛》结言“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孔子感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近代之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自然科学发达,几十个学科共同交织出第二层级——知性实在;哲学——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科学哲学,直接面对科学实在,而不再屈尊就下到经验实在中去体悟。试看二十世纪大有作为的哲学家,一般都接受过良好的数学-逻辑训练,有雄厚的自然科学背景;相反,缺少这种训练和背景的人,就根本成不了哲学家,只能在别人现成的哲学中讨生活。
世界是什么,实在是什么,永远取决于我们认为它是什么;人永远囿于自己的认知图像(cognitive map),不可能超越现有的认知图像认识实在,除非认知图像发生革命性的进化。事实上,人类社会生活的进化就是由认知图像的进化引导的。倘若我们拿当代科学的认知图像, 同古代神话-巫术的认知图像,同中世纪宗教的认知图像做比较,你一定会心悦诚服地承认,科学的认知图像是非常实在的。科学实在是人类几千年,尤其是最近几百年生产、科研和进行科学理论建构形成的实在,其实在性基于每一门学科、每个概念、每条定理、每个公式都具有经得起公开验证的实在性。科学实在是从无数实在殊相中抽象出来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共相,它比任何虚构的、感性-经验的实在都更实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就建立在科学实在的基础上,因为人类正是从科学实在中提取信息进行技术发明、生产和建设,以维持现代化的社会生活的运转。
因此,当代哲学同科学的关系的一个新的选项,是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的认知图像为基础,植根科学实在,发展一种“科学的哲学”,或者说“有科学根据的哲学”,“有科学性的哲学”。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不同于早已有之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后者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合理性、科学的研究活动、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发展的规律等等。这种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已获得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革命的结构、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等流派。作为一种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早已在大学和研究生院讲授,受到师生们的欢迎和重视。
有待创造的“科学的哲学”以“科学实在”或“科学的认知图像”为对象,研究传统哲学问题,但是不是在经验实在而是在科学实在的基础上重新研究这些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当代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用当代科学的概念、规律、模型、方法研究传统的哲学问题,包括描述科学的认知图像,建立当代科学的新形而上学,发展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社会理论、科学的人性理论,科学的心灵哲学、科学的文化理论、科学的价值理论、科学的进化理论、科学的全球问题研究,乃至有科学根据的伦理学说,从而建构新的理性实在,即新的哲学实在。这是有科学实在做根基的哲学,相对来说就是最可靠的哲学;它得出的哲学命题不是轻易能推倒的,因为有任何人都推不倒的科学成果做根基。这个工作不是轻易能够做好的,但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去做总是对的。我自己在社科院哲学所将近四十年,一直是按这个思路在做研究和构建。
让我们再听一听当代几位重要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声音,看他们对哲学的功能是怎样评价的。法兰福克学派创始人M·霍克海默尔认为,哲学的使命之一是“对科学根本解决不了,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作出解答”。[1]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承认,哲学“常常促进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指示科学如何从许多可能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爱因斯坦还有一句名言:“你永远不能用跟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那个问题”。同时代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则说:“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科学的进展“始终是通过哲学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我劝哲学和哲学家们不要过份清高,不要过分愤世忌俗和孤芳自赏,毕竟时代变了,必须承认现在是科技时代,在当代人的认知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中,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科学成了占据头脑的主要部分,成了推动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现代人从小到大接受教育,大部分时间是用于学习科学;解决实际问题更多地是援引科学。上世纪哲学被迫降低身份走分析哲学的道路,被迫另辟蹊径走非理性主义的道路,是有必然性的。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哲学还可以,也肯定会,沿这两个方向继续前进。除此之外,当然可以,也一定需要,开辟新的道路,即与科学结盟,在科学实在层级上研究哲学,随科学的发展向前发展。
浅议Materialism和Idealism 的汉译
在哲学的全部术语中,除“哲学”本身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最近,笔者对这两个术语做了重新审视,结果发现它们的汉译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似乎有提出来重新思考的必要。
当然,中国哲学界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称谓已经100多年了,早就用俗了,用惯了,似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静观西文原文,无论是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还是西班牙文,都跟英文“materialism”大同小异。在这些构成相同的西文词汇中,都只有“material”(物质)和“-sm”(主义)两个语素,全然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冠于词前。同样,“唯心主义”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里面,也都跟英文“idealism”大同小异,只有“idea”(理念)和“-sm”(主义)两个语素,也都是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冠于词前。再反观中文冠于词前的这两个“唯”字,顿觉突兀,分明是在汉译过程中译者加上去的。这一加,当然就增加了诸西文原文本词没有的意思。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误译或至少是不准确的翻译呢?
再进一步考虑,“material”一直汉译“物质”,没有问题。由柏拉图最早提出来的“idea”,汉译曾经有过“观念”“思想”“理念”“概念”等不同的译法,现在终于趋同译成“理念”了。这样一来,在汉语哲学术语系统中,由于“material”译“物质”,相应地“materialism”就应当译“物质主义”;同理,由于“idea”译“理念”,相应地“idealism”就应当译“理念主义”。这种新的译法既合乎逻辑,又理顺了哲学术语系统,还符合西文原词的构成,更重要的是消除了汉译增加的两个“唯”字及其语义。
大家都知道,日中两国的文字是相通的,日文大量采用汉字。日本是太平洋当中的岛国,是汉字文化圈的外围,门户开放早,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学术。中国是大陆国家,是汉字文化圈的核心,门户开放晚,后于日本接触西方学术。是故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学人,就便取材,便大量直接采用日本学界对西方学术用语的汉字译法。就我所知,中国哲学界采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直接引进的日文译法,而这日文译法我猜是套用中国六朝和唐代学者翻译佛经梵文的语素“摩怛剌多”用的那个“唯”字,如“唯心”“唯识”“唯识论”“唯识宗”[2]。可是,我猜得对吗?日本人这么套合适吗?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查阅了德国的汉学-日本学家李 博(Wolfgang Lippert)的专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3]。据该书记载:
“‘Materialismus’(=Materialism)在现代日语里的对等词是‘yuibutsu-ron唯物论’,它是由Nishi同时代的一个人创造的;1882年的时候,日语词汇中就已经有这个词了,这一点可以由Ei-Wa jii II(《英和字彙》)证明。这个词由两个语素构成,‘yui’就是‘只有’,‘butsu’符合中文语素‘物’,最后又从汉语借用了构词成分-ron(论),加在名词后面,用来表示哲学和思想学说以及理论。”
“我们可以推测,‘yuibutsu-ron’是按照其反义词yuishin-ron唯心论(idealismus)被创造出来的。yuishin-ron这个词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产生的,它源自于唐朝初年中国的佛教翻译经书。‘Yuishin’(汉语即‘唯心’)由‘yui’‘仅仅’和‘shin’‘精神’两部分构成,它指的是佛教当中把精神看作是惟一现实的一种思维方法。由于中国人认为,日本的新词‘yuibutsu-ron’恰好可以表达‘Materiualismus’这个概念,所以就在1900年前后将它借用过来,从此就有了汉语的‘唯物论’。”
“但是,在20世纪当中,‘唯物论’这个旧词渐渐被‘唯物主义’取代,因为,人们认为用‘-主义’来译‘-ismus’似乎更加贴切。”
这几段引文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测的正确性:
(1)“唯物论”(=唯物主义)果然不是对应西文直译出来的,而是由跟西周(Nishi)同时代的一个日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的。
(2)他在意译这个词的时候比照“唯心论”把这个词造成是“唯心论”的反义词,而“唯心论”则是中国唐朝人翻译佛经时的用词。
(3)日文“yuibutsu-ron”(唯物论)这个词实际是“三节棍”: “yui”源自梵文,“butsu”源自日文,“ron”源自汉文。
(4)上世纪初的中国学人根本没对照西文独立思考和独立翻译,而是按照“拿来主义”从日文拿过来就用。
待这两个日译术语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更有甚者按自己的两分法和阶级斗争历史观导出“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进而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线;凡被戴上“唯物主义”桂冠的中外哲学家都是进步的和伟大的,凡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的哲学家都是反动的和渺小的。这样一来,古今中外哲学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有定评的伟大哲学家,大部分都成了“反动的和渺小的”;许多没有多大影响的二三流哲学家都上升成“进步的和伟大的”,而持二元论的哲学家则经常被嘲笑为“摇摆不定”。最后,“唯心主义”还成了 帽子、棍子和刀子,不但用来打击哲学家,还用来打击自然科学家——当然是阻碍了哲学创新和科学创新,以及国外科学创新成果的引进和应用。
既然是这样,我们当然要继续追问:日本人用印度佛学解西方哲学恰当吗?采用日译的汉译加上两个“唯”字得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比西文原来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的“Materialism”和“Idealism”更准确和更全面地概括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诸多派别吗?更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应当建议西方哲学界在西文原词前面都加上“Only-”这个语素呢?——但我担心人家会反骂一句:“岂有此理!”笔者才疏学浅,不懂梵文,不懂日文,不通佛学,既不是哲学史专家,又不是译名术语专家,所以回答不了这些更细更深的问题,在此仅以这篇短短的“浅议”就教于大方之家。
不过我要声明,在没有上述几方面的专家站出来撰文驳斥和说服我之前,从今以后,本人在行文中开始慎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术语,尝试使用“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这两个贴近西文直译的新译名。
我开始尝试这样做,除了想忠实于原文和想同国际接轨之外,其实还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因为早在1935年就有一位中国学者余又荪“在对日本人创造的科学术语所作的一个非常严谨客观的研究中说:‘我国接受西洋学术,比日本为早。但清末民初我国学术界所用的学术名辞,大部分是抄袭日本人所创用的译名。 这是一件极可耻的事。”[4]“知耻近乎勇”,是以撰写此文。之所以冠“浅议”二字,是因为深究起来这个问题大了去了——过去一百年在中国出版的哲学史都要重写过。
值得高兴的是,《浅议Materialism 和Idealism 的汉译》这篇短文在哲学所主办的《世界哲学》2013年第一期获得公开发表,随后,跟我的另外7篇哲学短篇论文一起,在内部刊物《上海思想界》2014年第7-8合刊获得第二次发表。挂到“闵家胤:新浪博客”上,又获得许多响应。我相信这篇哲学短篇论文在中国哲学界有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国哲学的前路
中国文化最大的缺陷是没有进化出一神教,结果就出现梁漱溟在一百年前就指出的“以哲学代宗教”的特色。我要采用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哲学蜕化成宗教。后果就是,由于没有独立的发达的哲学,中国人思想僵化,缺乏创新能力;又由于没有一种强势的国教,民族凝聚力不足,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同时,中华民族是世界少有的缺乏宗教感情的世俗民族,很容易走向物欲横流,蜕化成经济动物,只追求权钱食色。过去三十年由于国家放宽了政策,各种宗教都有所复兴,但我认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是综合儒道释,创新发展出中华国教,以中华国教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彻底解放哲学,让哲学获得独立和自由。
获得解放的中国哲学的未来路径怎样,我愿提出一个号:回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中国古代哲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来可以同古希腊哲学媲美的诸子哲学。诸子哲学有一个特点:从问题出发,写短文章;没有教条束缚,不带八股文风。翻开十卷本《诸子集成》,除《论语》是语录体外,其余《墨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一两千字一篇的专论,譬如《墨子》的“兼爱”“非攻”,孙子的“始计篇”“谋攻篇”,《韩非子》的“孤愤”“说难”。有鉴于此,推陈出新。比照文学有“短篇小说”,我开创出“哲学短篇论文”一体。我已经写作将近百篇,前面《浅议Materialism 和Idealism 的汉译》就是其中一篇,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我的博客本来叫“哲人之悟”,后来要求实名制,被改成“闵家胤:新浪博客”了,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看,我很欢迎你阅读我的上百篇“哲学短篇论文”之后发表评论。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已经是七十几岁的人了,不可能再带研究生。有时我想,假如我还有带研究生的机会,我会对他们提出,哲学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灵感,灵感需要抓住,抓住才能积累。在日常生活中,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在思想的碰撞中,如果有顿悟式的灵感向你袭来,有新的思想火花出现,你一定要抓住,立刻记录下来。积累多了,加以梳理,选择最有价值的铺衍成文。倘若能写出10-15篇像样的“哲学短篇论文”,我就给你哲学硕士学位;倘若能写出30-50篇,足以结集成册,那我就同意你拿哲学博士学位了。
[1]燕宏远.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尔[J].哲学译丛,1979,(01).
[2]辞源(合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8.0286.
[3][4]李 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40-242.73
【责任编辑:王 崇】
2017-02-1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系统科学和社会发展”(项目编号:98BZX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闵家胤(1942-),男,四川泸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系统哲学和文化研究。
B01
A
1673-7725(2017)03-0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