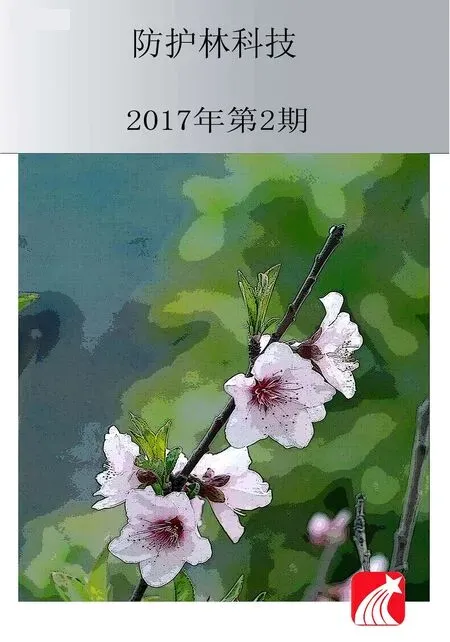红树林生态防护效应研究进展
李玫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20)
红树林生态防护效应研究进展
李玫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520)
红树林在沿海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重要的沿海防护林。文章从红树林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防风消浪效应、促淤造陆功能和抵御海啸功能等几方面综述了红树林生态防护效应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一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
红树林;防风消浪;促淤造陆;抵御海啸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低能海岸潮间带上部,受周期性潮水浸淹,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灌木或乔木组成的潮滩湿地木本生物群落[1]。红树林生态系统与珊瑚礁、盐沼、上升流区生态系统并称地球上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四大海洋自然生态系统[2]。Costanza等[3](1997)对全球各类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价,通过对红树林湿地在大气调节、气候调节、缓冲扰动、水文调节、水资源更新、水土保持、土壤形成、营养循环、废物处理、生物调控、栖息地维持、食品与原料生产、基因库构成、自然景观形成等多方面功能价值的估算和统计,得出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全球16种生态系统中名列第4。如果将上述服务价值折合成经济价值,每公顷红树林湿地每年可以产生高达9 990美元的效益,相当于珊瑚礁生态系统价值的1.64倍和热带森林的5倍[3]。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失在不断地增加,而沿海地区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4]。2004年底的印度洋大海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为此人们的焦点集中到如何用红树林来固筑天然防洪大堤和怎样去实践的思考中。生物学家萨尔巴姆是防御海啸方面有经验的专家之一。为了考察和防御洪灾,他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省的沿海岸线一带种植了一片片红树林。值得庆幸的是,大海啸中由于有了红树林的抗御,林区附近的村落均幸免于难,躲过了一场残酷的浩劫。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海啸,成片的红树林不仅没有被排山倒海之势的海浪摧垮而且能起到拦截海啸、疏通水道、泄水固堤的作用。实践证明当海啸来临时,海平面会徐徐上升。由于红树林的抗御,海啸就不可能一鼓作气以泰山压顶之势涌向内陆。在某种程度上,红树林起到的缓冲壁垒作用功不可没。
对印度洋大海啸进行反思之后,环境活动组织和自然保护团体都将目光投向了红树林。通过实践和比较发现,红树林防灾减灾效益显著,大面积种植红树林是防御海啸的最佳途径和最经济的手段。研究表明保护红树林,扩大其种植面积有百利而无一害。除了抵御海啸、风暴潮外,红树林的其他经济和环境价值亦不可低估。如在孟加拉国的泰加森林保护区,红树林不仅能防洪而且还是大量的鱼苗、螃蟹、软体动物等的栖息地,许多濒临灭绝的物种在红树林湿地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庇护场所。
1 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
红树林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与经济价值,尤其在固岸护堤、防治灾害、维持生物多样性和海岸带生态平衡、防治污染、净化环境、美化景观、发展旅游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1]。对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估算,可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加深人们对红树林资源价值的再认识。韩维栋等[5](2000)估算中国现存自然分布的13 646 hm2红树林的年总生态系统功能价值为236 531万元,其中生物量价值8 163万元,抗风消浪护岸价值99 206万元,保护土壤价值115 692万元,固碳以减弱温室效应和释放O2的价值6 706万元,生物多样性保护即动物栖地价值5 470万元,林分养分积累价值1 012万元,降解污染物和减少病虫害282万元。
赵晟等[6](2007)应用能值理论,对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值货币价值作了评估,结果表明,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值货币价值每年12.6×108元,每hm2价值9.24×104元,其中,凋落物的价值0.28×108元、木材价值0.12×108元、栖息地价值6.39×108元、抗风消浪价值1.05×108元、污染物处理价值4.76×108元、科学研究价值0.02×108元。邓培雁等[7](2007)应用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对湛江红树林湿地经济价值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显示,湛江红树林湿地总经济价值为206 638.75万元,直接使用价值为12 423.89万元,占总经济价值的6%;间接使用价值为152 887.11万元(护堤减灾10 783万元,占总经济价值的5.22%),占总经济价值的74%;非使用价值为41 327.75万元,占总经济价值的20%。
然而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在红树林的总价值或不同服务在价值上尚不能归一。其价值随着以下因素而变动:①进行了旅游开发的红树林区其价值将高于未开发地区;②部分(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者将给红树林以更高的评价;③所采用的价值评估方法和假设的不同。而且,红树林的生态旅游价值、社区价值以及与营养物质循环相关的生态服务价值是难以评估的。可以认为,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总经济价值随着各因素的差异而不同,且其社会福利方面价值以及系统整体的重要性有可能被低估。迄今研究表明,红树林最大的经济效益来自其生态系统产品(如渔业、木材和薪材)、文化服务(旅游)和调节功能(海岸保护)。
各国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经济价值评估差异较大:如在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不到0.5 km2红树林,其经济价值估计为104 000美元km-2(总价值约为5 000万美元a-1)[8]。在泰国估算出的红树林价值也非常高,达2.7~3.5百万美元km-2[9]。红树林经济价值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生态系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红树林在保护海岸方面的价值(通常以海岸线线性长度衡量)取决于沿着某一特定海岸线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活动。在印度尼西亚,有几种方法可用来估算红树林的价值。在斯里兰卡,红树林在抵御风暴潮方面的价值(2004年海啸发生之前)是7 700美元km-2(海岸线性长度)[10]。而一项在印度尼西亚研究,计算出红树林防海岸侵蚀方面的价值为600美元每户-1每年[11]。
3 红树林生态防护效应
尽管红树林沿海岸形成天然屏障保护了海岸,但至今尚无足够的科学数据来支持这一论断。大部分的证据仅仅是来自对正常的波浪能量和风暴的观测和某些传闻(轶事)。热带海岸线的红树林后面常常有平静的泻湖。渔民利用这些遮蔽水域航行和捕鱼,尤其是在恶劣的天气或季风季节里。而度假旅游者则在红树林区域开展各种娱乐休闲活动。
沿海社区往往非常了解红树林所提供的特殊保护作用。在印度和菲律宾[12],在有完整红树林的地方,村庄的生命和财产受到红树林的保护而免受飓风和台风的危害,但在红树林被转化为虾养殖场或用作它用的地方则损失惨重。1999年印度的奥里萨邦,一个强大的热带气旋和继之引起的狂浪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口死亡率,但被红树消浪林带保护的社区遭受的影响则较小[13]。在越南,已观察到红树林可减少气旋波(cyclone waves)和海啸带来的损害,而且大量节省了海堤的维修费用[14]。在越南北部Chidambaran区,红树林的海岸保护作用为当地居民所公认,有113 km2的红树林作为一种神圣的树林,被传统的泰米尔人称为Alaithi Kadukal,意思是“可控制波浪的森林”(WWF,2005)[15]。
尽管一般来说红树林对风浪具有缓冲能力,但其机理过程是复杂的,与人造防护设施和其他自然特征相比,红树林在提供海岸保护方面达到何种程度,迄今为止尚不清楚。此外,红树林生态系统本身也会遭到飓风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事件的破坏。飓风之后红树林不仅被风连根拔起和扫落枝叶,而且还受到波浪对海岸的侵蚀和泥沙掩埋的影响。1999年,米奇飓风摧毁了洪都拉斯群岛的瓜那佳湾(Guanaja Bay)97%的红树林[16]。因此,缓冲能力是红树林生态系统恢复能力和脆弱性之间的平衡,其中涉及诸多因素。在没有人类的影响条件下,一个健康的红树林可作为一个自我修复的防波堤,与(由海浪、风暴和其他进程引起的)海岸侵蚀保持均衡增长。
3.1 红树林的防风消浪效应
红树林茂盛的根系和茎叶能够削减海浪的能量和规模。但是其他因素也有一定影响力,包括岸滩剖面、水深、滩涂底部构型。红树植物具有发达的根系,纵横交错的支柱根、呼吸根、板状根、气生根、表面根等形成一个稳固的网络支持系统,使植物体牢牢地扎根于滩涂上,并且盘根错节地形成一道道严密的栅栏,增加了滩面的摩擦力,能阻挡水流、减弱流速,从而起到了防风消浪的作用。
红树林是海岸带极其重要的防护林。一般防护林的防护面积范围在迎风面为树高的5~10倍,背风面为树高的15~30倍。红树林具有抗御40年一遇强台风的能力,能有效保护海堤免于冲毁,减少堤内经济损失。据专家评估,分布在海岸线上1 km长的红树林带,每年在抗御台风灾害方面可提供约8万元的防护效益[5]。国外文献报道,当波浪通过200 m宽的红树林时波能可减少75%[17]。据国内的早期报道,当红树林覆盖度大于0.4和林带宽度在100 m以上时,其消波系数可达85%,能把10级大风刮起的巨浪化为平波[18]。
陈玉军[19](2012)通过与沿海互花米草植被和裸露海滩的消波效应作对照,对华南沿海11种不同类型红树林的消波效应开展了长期野外监测,提出了这些典型红树林的定量减波指标,分析了红树林消波效应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建立了红树林对波浪消减效应的模拟模型,初步提出消波红树林所具备的结构标准,为红树林消波功能的综合评价提供参考和依据。吴沿友等[20](2012)根据动量守恒方程和多孔介质源项为速度的幕率方程,建立红树林多孔介质水流阻力数学模型,并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Fluent分析不同影响因子对红树林水流的阻力效果。田野等[21](2014)通过对广东湛江白骨壤(Avicenniamarina)人工林林内距离林缘25 m、50 m、75 m、100 m 处的消波观测分析了红树林消波效应。研究表明,白骨壤人工林消波效果显著,波浪从林缘经过白骨壤01 样地(0~25 m)、02 样地(25~50 m)、03 样地(50~75 m)、04 样地(75~100 m)后的1/10 波高减低率分别为31.49%、35.23%、40.85%、38.88%,且其消波程度是随着林分生物量体积密度的增加而增加的。
3.2 促淤造陆功能
红树林湿地可捕捉径流中的泥沙,促进海岸沉积。在新西兰,至今仍然可看到早期几代的毛利人为了稳定海堤而种植的一排排红树林[22]。研究表明,有两种类型的红树林根系捕沙促淤功能最显著。红树型拱形支柱根系,每株可有一 、二百条之多,支柱根生物量可达总生物量的25%;海桑型笋状呼吸根系,密度可达 180~400 条m-2。 红树林潮滩沉积速度受区域性泥沙来源及海岸动态背景的重大影响,通常达每年数毫米,河口淤积区可达每年数厘米。海南东寨港林市村以密集支柱根为特色的红海榄林区标志桩观测结果显示,密林区普遍淤积,平均速率 4.1 mma-1。 淤积速度还与滩面高程(或浸淹频率)有关,即淤积速度随滩面高程的增大或浸淹累积频率的减小而减小[23]。这可以解释为滩面越高,潮水浸淹时间越短,带入和沉积的泥沙量越少。这一规律使红树林有可能在大潮高潮位附近建造沉积阶地,是红树林生物地貌功能的重要体现[24]。
3.3 抵御海啸作用
与风生波(wind-generated wave)相比,海啸(Tsunamis)有更长的波长,而且波能分布在整个水柱并具有更大的规模。当海啸接近海岸,水面快速涨高、波高急剧增加,能源转换到表层,这种效果在逐渐变浅的海岸上更加明显[25]。在免受风生波破坏的地点,海啸却能造成巨大损害,因为其波高往往在通过渠道和水湾时迅速增大。海啸波也可在遇到不同障碍物后反射并改变运行方向[26]。因此,在2004年的海啸中红树林起到缓冲器的作用也就不足为怪。
有许多观测表明,红树林既可消减海啸的强度又可冲走海啸引起的碎片,从而有助于减少海啸的破坏(WWF,2005)[15]。在一些情况下,红树林也有助于挽救生命,防止人陷入反激浪(the backwash of the wave)而被带入大海。然而,红树林的防护效益存在相当的变数。在印度,测深和海岸剖面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安达曼群岛,红树林后缘比那些没有红树林的地方遭受的海水侵蚀更小[27]。在斯里兰卡遭受最大损失的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沿海24个泻湖和河口的调查表明,在有高质量的红树林群落存在的海岸几乎未遭受破坏,且红树林本身也未受到严重损坏[28]。然而,以非典型的红树林树种占优势的红树林群落(即那些在过去已退化,优势种不是海桑或红树属的)却遭受破坏[12]。因此,除了其规模(即面积)和先前被清除之后的再生恢复情况,红树林缓冲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林分质量相关。红树林的密度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一项研究表明,一个100 m宽的红树林带,其密度为30株m-2时,将足以减少高达90%海啸带来的流动压力[28]。对受海啸影响地点的大量卫星图像分析显示, 红树林的存在与海岸线破坏的减少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29]。许多情况下,在报道有红树林防护作用的地方,其海岸线往往离开波的主路径或毗邻深水,因此不容易受到严重损害。这些结果表明,开发海啸预测模型的重要性,这就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卫星图像分析,以及详细的实地调查研究,来认真分析某一个地点的各方面情况。
通常认为当海啸发生时,红树林的存在与否不是海岸带受损害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近岸水深、海岸线的剖面结构很可能是关键因素,因为这些因素确定在任何特定的沿海位置上波的力度。海岸附近的深水地段往往比浅水缓坡段受到的影响更小。而海岸线的形状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岬往往为波浪提供保护,而海湾或河口湾则呈 “漏斗”状向陆趋于收缩,限制和放大波浪的能量。因此,在可能预测一个红树林将以何种方式、在哪里减少海啸的影响之前,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开展。
4 研究展望
红树林生态系统与沿海防灾减灾、渔业养殖、近海环境、林业、海洋旅游等密切相关,有着陆地森林不可取代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大量研究表明,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促淤造陆和抵御海啸等生态防护效应。然而,台风、暴潮等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各种生态过程和功能影响,以及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响应,如何进行结构优化配置以提高其防护能力等,均有待深入研究探讨。与此同时, 红树林生态防护效应的监测及评价研究亦亟须加强,为红树林防灾减灾功能的科学评估提供依据和计量手段,为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提供理论指导。
[1] 林鹏.红树林[M].北京: 海洋出版社,1984:1-104
[2] 林鹏.中国红树林湿地与生态工程的几个问题[J]. 中国工程科学,2003,5(6):33-38
[3] Costanza R,d’Arge R,de Groot R,et a1.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e capital[J].Nature,1997,387(1-3):253-260
[4] Walter V Reid,Harold A Mooney,Angela Cropper,et al.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DC. 2005:137
[5] 韩维栋,高秀梅,卢昌义,等.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生态价值评估[J].生态科学,2000,19(1):40-46
[6] 赵晟,洪华生,张路平,等. 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值价值[J].资源科学,2007,29(1):147-154
[7] 邓培雁,刘威.湛江红树林湿地价值评估[J]. 生态经济,2007(6):126-128
[8] Spurgeon J,Roxburgh T. A Blueprint for Maximising Sustainable Coastal Benefits: the American Samoa case study, Proc[C]. 10th International Coral Reef Symposium, Okinawa, Japan,2005
[9] Sathirathai S,Barbier E B.Valuing mangrove conservation in Southern Thailand[J].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001,19(2): 109-122
[10] UNEP/GPA . The Economic 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Uses of Mangrove Forests in Sri Lanka. Report prepared by Dr B.M.S. Batagoda.UNEP/Global Programme of A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 The Hague, Netherlands, 2003:82
[11] Ruitenbeek J. The rainforest supply price: a tool for evaluating rainforest conservation expenditure[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2,6(1): 57-78
[12] Dahdouh-Guebas, F, Jayatisse, L P, Di Nitto, D,et al. How effective were mangroves as a defence against the recent tsunami?[J]. Current Biology 2005,15(12): R443-447
[13] Mangrove Action Project. Loss of Mangrove Forest contributed to Greater Impact of Tsunamis. http://www.earthisland.org/map/tsunami.htm#1 downloaded 21 January 2005
[14] Ha N H. Summary of Mangrove Disaster Preparedness Programme and Its Impact. Procee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DRM. 2-4 December 2003
[15] WWF. WWF Tsunami Update 2. 7 January 2005. website: www.wwf-uk.org/news/n_0000001426.asp,2005.
[16] Cahoon, D R, P Hensel, J Rybczyk, et al. Mass tree mortality leads to mangrove peat collapse at Bay Islands, Honduras after Hurricane Mitch[J]. Journal of Ecology, 2003,91:1093-1105
[17] Massel, S.R, Furukawa, K. and Brinkman, R.M. Surface wave propagation in mangrove forests[J]. Fluid Dynamics Research,1999,24: 219-249
[18] 陈雪清.对红树林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全面认识及维护[J].林业资源管理,2001(6):65-68
[19] 陈玉军.红树林消波效应观测与模拟[M]. 北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2012
[20] 吴沿友,郭晓君,付为国,等.红树林多孔介质阻力模型与消波效果仿真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12,28(23):92-97
[21] 田野,陈玉军,侯琳,等.广东湛江白骨壤红树人工林消波效应初步研究[J].地球环境学报,2014,5(1):30-41
[22] Vannucci, M. Supporting appropriate mangrove management. Intercoast Network Special Edition,1997
[23] 张乔民,施祺,余克服,等.华南热带海岸生物地貌过程[J]. 第四纪研究,2006,26(3):449-455
[24] 张乔民, 温孝胜, 宋朝景,等.红树林潮滩沉积速率测量与研究.热带海洋,1996,15(4):57-62
[25] Kowalik Z. Basic relations between tsunami calculations and their physics—II. Sci Tsunami Hazards,2004,21(3):152-173
[26] Yeh H, Liu, P., Briggs, M. and Synolakis, C. Propagation and amplification of tsunamis at coastal boundaries[J]. Nature,1994,372: 353-355
[27] Department of Ocean Development.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mpact of Tsunami in selected coastal areas of India. Department of Ocean Development, Integrated Coastal Marine Area Management Project Directorate, Chennai, India,2005
[28] Hiraishi T.Tsunami risk and countermeasure in Asia and Pacific Area: applicability of greenbelt tsunami prevention in the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Sixth multi-lateral workshop on development of earthquake and tsunami disaster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and its integration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6th EqTAP WS) organized by Earthquake Disaster Mitigation Research Center, NIED, Ise-Kashikojima, Japan,2003
[29] Chatenoux B,Peduzzi P.Analysis of the role of bathymetr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in the impacts from the 2004, 2005.
1005-5215(2017)02-0054-04
2017-01-03
李玫(1971-),女,博士,副研究员,Email:1448890453@qq.com
S718.5
A
10.13601/j.issn.1005-5215.2017.0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