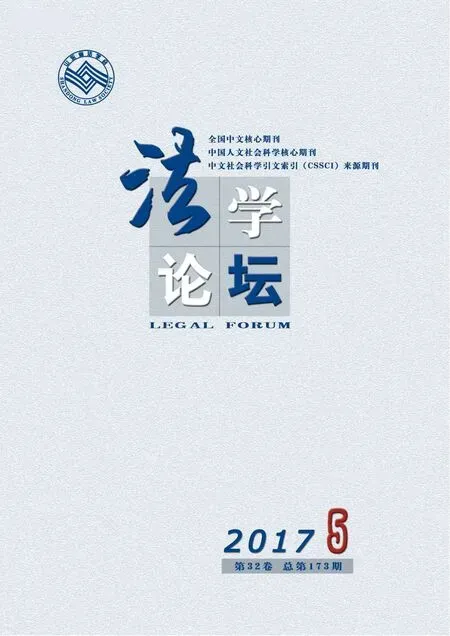经济法的司法空白之弥补
陈乃新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湘谭 411105)
经济法的司法空白之弥补
陈乃新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湘谭 411105)
由于经济法的立法尚未真正确认与设立经济法主体特有的权利,经济法的司法尚无法真正保护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当前,有些本属于经济法上的案件,却分别按照从属于民事和行政的司法问题作了处理。这使经济法出现了司法空白,已经非常不适应保障经济发展公平之需要。必须从经济法的立法上科学确认、设定和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劳动力权),并制定相应的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使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同样能得到司法保护。弥补经济法的司法空白必定能有力地保障劳动者、投资者、政府的合作共赢,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经济法;经济发展公平;经济诉讼法
如果承认经济法是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那么与之对应的我国经济法司法便处于空白状态。出于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的需要,197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负责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也许是因为经济纠纷案件(一是经济合同纠纷,如买卖合同纠纷、借款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技术合同纠纷等;二是经济侵权纠纷,如知识产权的专利权、商标权侵权纠纷、所有权侵权纠纷、经营权侵权纠纷等)大都属于民事案件,再加上处理这些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于是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做出决定,取消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改经济审判庭为民事审判庭。同时,我国至今也确实没有制定与经济法相应的经济诉讼等程序法。再者,经济法学界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两大组成部分不存在司法:一是对于宏观调控法律行为,事实上就不可诉。二是对于违反市场监管(规制)法的行为,又大都通过行政诉讼处理;市场监管法中也许存在的平等主体间的竞争纠纷等,则勉强通过民事诉讼做了处理。因此,经济诉讼本就不存在,可以说我国经济法的司法,迄今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一、经济法的司法必要性
(一)市场监管(规制)法的司法必要性
1.关于劳动法的司法问题。对于劳动法,有人把它归入经济法,如全国司法资格考试;也有人把它归入社会法,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2011年10月)。可是,处理劳动案件,一是,劳动争议的处理方式,不但包括了劳动争议的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而且其中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二是,人民法院审理劳动行政案件(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争议几乎涉及劳动保障的所有领域的问题,包括工伤认定、劳动监察、工龄认定、退休审批、档案转移、保险费额核定、账户转移单转移、失业等等)则是适用《行政诉讼法》。三是,人民法院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刑事案件,适用的是《刑事诉讼法》。我们看不出劳动法的司法(审判),是属于经济法的司法,也谈不上是社会法的司法,而分别是属于民法、行政法与刑法的司法。
但是,对于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人们的认知则已经日益改变与深化。首先,它不是劳动者把他所具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与用人单位给付工资薪金的商品交易关系。其次,它既不是政府公权力干预用人单位财产权的关系,也不是政府特别关照作为特殊群体的劳动者的关系。故劳动法不是民法的特别法,也不是行政法的特别法,虽然劳动法中也会有一些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但总的说来它是国家在以民法保护财产权的同时,保护劳动力权的法。因为行政主体既无充分的理由倾斜保护劳动者*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论者认为:倾斜保护主要是指保护弱者。就保护弱者而言,社会法是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种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弱者”身份的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种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公法与私法作为相对立的两大法域存在已久,然而,随着新型社会问题的产生,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已不限于简单的公法上的管理关系及私法中的平等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两者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类社会关系的产生促使了新法域的产生-社会法。市民法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社会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这点在法的价值上体现为:市民法实现了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起点的形式公平,而社会法则要求实现结果的实质公平。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权利政治,它主张国家对个人的私生活干预越少越好,政府越小越好,国家只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负责维护社会和平和自由竞争。然而,这种过分强调国家的消极无为的作法,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环境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在这种情形下,各国逐渐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并在观念上从夜警国家转变成福利国家,国家职能也从权利政治转向公益政治。这种转变的目的在于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公法私法化的原因所在。我们认为,这种理论强调意志决定是不充分的。因为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就同种类权利向所谓的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势必妨碍私法自治的发展,损害所谓的强势群体权利的实现;国家必须对同类权利实行公平的保护,方能维持法制。至于对弱势群体利益欠缺的弥补,只能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通过财政补助、慈善道德手段等去处理。但是,对于不同的权利,分别加以保护,这是符合法制原则的。例如,对于从事生产的企业,国家以民法保护企业及其投资者的财产权,又以劳动法保护与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的劳动力权。保护这两种不同的权利,可以并行不悖。不能采取直接侵犯企业及其投资者的财产权,把财产拿给劳动者,对劳动者的权利实行倾斜保护。在社会法中,法律规定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国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等权益作出特别保护的规定,也是因为他们对不可排他性占有的资源与环境的利用具有共享权利,或者他们对社会发展作出了更多贡献(如妇女)而应享有的权利加以保护,不是对他们进行权利倾斜性配置。,也不能违反民法去干预用人单位的财产权。
应当认为,劳动者所具有的劳动力,天然属于他个人所有,它不可能发生归属权争议,因而不需要通过法律设定劳动力的所有权;劳动力不能离开人体独立存在,也不可能出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从而不可能出现劳动者把劳动力使用权作为商品让渡给用人单位的问题,且劳动力也不存在继承问题。所以,劳动法的司法,即民事诉讼法并不适用劳动争议的处理。同时,行政诉讼法虽然可适用于审理劳动行政案件,但问题在于这里不仅仅是要调整行政主体代表全社会的既得利益而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劳动行政管理关系;而且还需要调整行政主体与全社会的发展利益关系,即行政主体的经济法行为,是否履行了促进劳资政合作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义务,从而劳资政三方共赢的权益是否得到了实现。行政主体可以有权代表社会整体(既得的独立的)利益,对加害人追究行政责任;也有权强迫社会个体的既得利益服从社会整体的既得利益,但造成社会个体既得利益损害的,须补偿或者赔偿。问题在于行政主体更有义务与市场主体依法为合作共赢的行为,同时才能享有共享发展的权利。这就可能只有通过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须另行研究)来配置权利义务了,而且需要有经济法的司法。
2.关于竞争法的司法问题。我国的竞争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其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再联系该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一)销售鲜活商品;(二)处理有效期限即将到期的商品或者其他积压的商品;(三)季节性降价;(四)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降价销售商品。”由此分析可知,经营者与经营者即竞争者与竞争者之间是存在侵权问题的,但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经营者作为销售者对购买者而言,是民事合法行为,也没有对相对的经营者构成民事侵权,所以,这里竞争者之间的侵权并非民事侵权行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而是一种有关市场竞争纠纷(竞争侵权)的诉讼,可惜我们并没有相应的诉讼法,而不是不需要。
3.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司法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这里,消费者在获得民事赔偿之外,还可要求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等。但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那么,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经营者,在被判决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之后,我们能否根据这个规定,认定消费者已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应当驳回其增加赔偿的诉讼请求呢?可见,既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规定消费者可享有提出增加赔偿请求的权利,那么这里也就需要有相应的诉讼程序法,这是在情理之中的。
(二)宏观调控法的司法必要性
在经济法学界,既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行为不可诉;也有学者认为可诉。事实上,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行为的主体,它可能是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先导,又通过具体行政行为去落实。在落实宏观调控中,它本是(经济)行政法问题,并已由行政诉讼法来处理,对此,我们可在众多的经济法律中看到这一点(虽然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及其可诉性,学界也还有一些不同看法)。现在的问题是,宏观调控主体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并通过职能机构去执行,这里,公权力是干预、改变了资源配置,但它只是对社会整体存量利益的一种再分配(而且政府合法干预造成社会个体损失的需要予以补偿,违法的则还要赔偿),可它并不一定能对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起直接保障的作用 。
所以,政府为什么进行宏观调控,受调控主体为什么须接受调控,这里必有它们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利益关系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就是要这样来设定权利义务,要不我们也就用不着什么经济法了。同时,宏观调控的主体与受宏观调控的主体,它们与全社会整体的发展利益关系或者增量利益关系,在经济法加以调整中,它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因而它就需要一种经济法的司法来处理。现在只是因为经济法律中的(经济)行政法被当成了经济法,所以有关经济行政的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也就被当成了经济法的实施。显然,这是不合适的。
二、经济法的司法首先要完善经济法的实体法
经济法的司法很有必要,然而通常被归入经济法的那些经济方面的法律,实际上多有民事法律规范和(经济)行政法律规范,而那些真正称得上经济法律规范的却比较少或者不太明确,这也许与我们长期实行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需要保障行政权对经济的干预有关。当然,这与我国现在实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又是不相适应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2011年10月)所说的“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经济法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的方向去完善呢?笔者认为,这在理论上还有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解决。
(一)经济法调整关系的理清
一是,应当明确,“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关系,而是经济干预关系;若是由政府行政来干预,那么所形成的就是经济行政干预关系。认为政府干预经济会产生经济关系,学界还是缺乏论证的。而且公权力干预虽然能够改变资源的配置,但不能直接解决保障社会财富的创造。政府干预的立法,属于行政的立法,不会因为政府干预什么,其立法就变成了什么法(如政府干预教育,就能形成教育关系,就是教育法吗)。立法授权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政府代表着社会整体的现存利益,但如果损害了个体私益是需要补偿的,违法干预的则要赔偿。政府干预经济可以改变既得利益的格局,但对于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并不直接;否则,世界各国的发展问题岂不都可通过政府干预而得以解决?应当承认,如果把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法作为(经济)行政法,确实可以与民法分开,对经济也有一定作用;但把(经济)行政法当做经济法,这种经济法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了,包括组成经济法的市场监管(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二是,也不能把民与民的关系,全部归属于民法来调整,经济法也有调整民与民之间关系的内容。新颁布的《民法总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可见民法没有规定它可调整民与民之间的一切关系;因此,就不能认为民法可调整民与民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如上述已经提到的一些劳动力关系,包括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力(利用)关系、市场经营者(竞争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力(即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关系、市场经营者与生活消费者之间的消费力关系(劳动力再生产关系)等,这也是民与民之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些民法肯定不作调整。
除了民法本身没有规定调整劳动力关系之外,还在于劳动力关系具有民法调整不了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劳动力天然属于自然人个人,它不能离开自然人而存在,劳动力不可能发生归属权纠纷;劳动力也没有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问题,不可能在主体间流转,故调整财产关系(归属关系与流转关系)的民法,就不能调整劳动力关系。此外,劳动力是人体的一种机能,人身则是劳动力的载体,故劳动力关系也非调整人身关系的民法所能调整。但是,劳动力却是创造财富的三大要素(另外还有财产要素,不可排他性占有的资源与环境要素)之一,而且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9页。劳动力对增量利益的创造起决定作用,从而对劳动力的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不可缺少。如果劳动力关系得不到相应法律的调整,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与经济社会不能持续健康发展,经济法就根源于劳动力关系须有法律调整而生成的。相反,如果人们硬是把劳动力当做商品(民法所称的物),纳入民法进行调整,那就会违反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民法就可能在这方面起反作用,从而难免加剧“市场失灵”。可见,既然民法不调整劳动力关系,就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可惜,经济法学界自己却未重视这一点,许多人一直只在民事私权(财产权、人身权)或者在公权(立法、行政、司法权分立制衡等)的框架内去研究经济法的一些具体制度,一旦出了点什么研究成果,最终也都免不了落入民法、行政法的框架里去。
(二)经济法的司法指向
沿着正确方向完善经济法,就应该确定一个经济法上的基础性权利。经济法的司法是保护经济法的实体权利的,但现在对经济法的实体权利,学界虽然总结出了市场监管权(或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有的还认为是保护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权),但这两种法权与民法的财产权、人身权,以及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关系是什么?迄今,这也没人证明它们是否是同一层级的、可相互并列的、独立的、基础性的法权形态;而且一些经济法律事实上还干脆用经营者权利、消费者权利等以主体特征来为经济法权利定性定位,这与财产权等以客体来定性定位的民事权利等相比,也没有可比性。所以,经济法的司法现在也还谈不上保护什么样的经济法权利。
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什么社会关系弄不清,经济法的法权没有确定,经济法的司法指向也是没法确定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可能需要通过经济法的司法来处理的事务,现在是很勉强地以民法或者行政法的司法去处理了。例如,在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外,当事人再增加的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也是通过民事诉讼去处理的;又如市场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权冲突,明明它们相互间没有民事侵权而只有竞争侵权时,为什么还是要按照民事侵权纠纷适用民事诉讼法来处理呢?再如,为什么所谓的市场监管或者宏观调控中的具体执行,都被当做经济法问题而采取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去处理呢?所以,不从经济法的实体内容入手,不确定经济法的法权,经济法的司法的缺失便没法弥补。
不过,也有些学者拿公益诉讼,尤其是拿私人公益诉讼来说事的,以为经济法的司法从此就有了奔头。实际上,公益诉讼只与私益诉讼相对应,它与现在已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分类方法不同,按照民事、行政与刑事这一分类,只有经济诉讼才可能成为经济法的司法。再说,公益诉讼也可分为既有公益(存量)的诉讼和将有公益(增量)的诉讼,也许经济法的司法中有的只可能是关于将有(增量)公益的诉讼;因为关于既有(存量)公益的诉讼,民法、行政法、刑法等的司法中是已经存在的。
三、在完善经济法的立法的同时完善经济法的司法
许多人非常费解的是经济法调整劳动力关系(增量利益关系),是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经济发展公平)的观点。因为这使坚持国家干预经济法论等的学者深感意外与离奇。但是,我们冷静下来分析已有的经济法律(这很关键),再想一想社会的需要,我们是能够理清这一点的。
(一)经济法的独特性
近现代以来只有社会法与经济法是新出现的两个法律部门。近现代以来,实际上有两种也只有两种法律现象是超越传统的民法、行政法与刑法之调整范围而新出现的。
一是为不可排他性占有的资源与环境的共用共享共护,配置权利义务的社会法。这在过去的时代,其利用者与未利用者之间是不会发生利益冲突的,而社会化生产的强大生产力与资本逐利的市场竞争,使资源迅速枯竭、环境迅速恶化,不但利用者与未利用者之间,而且现在人与未来人之间,都有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不可排他性占有的资源与环境,又不是民法中所指的物,它没有归属问题(为公众同处共享),也不能在主体间流转,故民法没法调整,民法只能处理其中发生民事侵权的一部分问题(这一点须另行研究);由于这种资源与环境之人力的不可管控,行政法也是无能为力的。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
二是为人的劳动力的自有自用自益,配置权利义务的经济法。现代人类进行物质的生产与生活,离不开不可排他性占有的资源与环境的利用,离不开民法所指称的物,还离不开人的劳动力;否则,整个社会生产就没法进行,社会生活也无从谈起。但是,对于劳动力的权利义务,为什么过去没有而现在会有经济法来加以配置呢?这也是因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逐利的市场竞争引发的,在过去个体生产的自然经济中,运用自己劳动力创造的多于所投入的增量利益,是自然属于他自己的,即使所投入的财产是租来的也只是支付对价(法定孳息)给出租人而已,增量利益归属于他自己,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但现在由一些人投资办企业(社会化生产组织),许多人一起参加劳动所创造的增量利益归属于谁?是仍然按照民法的天然孳息归投资者、还是适用法定孳息归投资者、或是按照劳动力孳息同创共享的原则配置*天然孳息归属投资者,符合民法,问题在于这里问的是协作的劳动力孳息归谁?投资者自己不经营而是出租给他人经营的,依照民法可获得法定孳息,但自己经营的就没法向他人去请求法定孳息了。这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盈利是劳动力孳息,它归属于谁,是个新问题:如果把劳动力孳息当做天然孳息,将它归属于投资者,那么过剩的危机、市场失灵就不可避免;如果不归属于投资者,那就会没有人投资了。因此,只能由投资者与其他劳动者合理共享,才是出路(如果投资者的所得不如将财产让渡给别人经营所能取得的法定孳息,他也不投资了)。,这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际上,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性的、系统性的法律问题的萌芽早已出现。1802年英国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做出禁止雇佣童工、限制工作日等规定,从而开创了保护劳动力权的先河。若把劳动力当做物,让购买者任意驱使劳动力权人,劳动力资源就会枯竭,资本就不可持续逐利,但国家又不能也不会强制处分投资者的财产权(否则违反民法),就只能通过其他方法另行保护劳动力权,来维持经济发展。因此,马克思称英国的“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此前,虽然已经有人提及经济法(如摩莱里、德萨米等早有提及),但经济法的实践却始于此,因为它调整的劳动力关系和设定的劳动力权,完全是一种新的法,一种可以与民法相并列,也不同于行政法的经济法。后来,调整市场竞争关系、生活消费关系的立法也相继出现并发展起来,这些立法实质就是调整财富创造力竞争关系、劳动力再生产关系的立法。不仅仅如此,在上述私人物品的生产、竞争与消费领域的劳动力关系出现了立法,而且在公共物品的生产、经营与消费领域的劳动力关系的法律调整也产生与发展起来了。
为什么产生这种法律是必然的呢?这是因为劳动力权如果没有得到更多的保护,即大多数主要靠劳动力谋生的人们得不到对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他们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就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框框内,于是1825年就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市场失灵”),财产权人投资可持续逐利遭到冲击,人类社会从此就进入了发展、危机、治理,再发展、再危机、再治理的循环。由于对劳动力权的保护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不真正主动,劳资冲突、官民矛盾等不断加深,终于爆发的经济金融危机、资源环境危机、人体能力危机与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等,催生了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力权的法律。不过,这一开始就被误认为这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法。这种对经济法有误解的理论,不但存在公权力介入、干涉私法自治的内伤,而且也不能协调财产权与劳动力权的权利冲突,从而难以持续存在和发挥应有作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就不提经济法,如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时很相信国家干预及其干预经济的法,但还是没有把它当作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又如日本搞了一段时间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法,现在只留下反垄断法等,经济法在日本六法全书中也不知去向。当前,我国正在实行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政府正在实行“放、管、服”*“放”就是中央政府下放行政权,减少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的行政权;理清多个部门重复管理的行政权。“管”就是政府部门要创新和加强监管职能,利用新技术新体制加强监管体制创新。“服”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将市场的事推向市场来决定,减少对市场主体过多的行政审批等行为,降低市场主体的市场运行的行政成本,促进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改革,如果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主要放到依靠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上来加以保障,这很可能是不合适的。
因此,虽然经济法确是针对市场失灵的法律对策设计,但它不能单纯地被说成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一方面,它确实是规范政府干预(相对人)市场主体,保障社会整体既有利益的法;另一方面它又是规范政府以其能力促进整体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行为,最终保障主体可普遍可持续地进行资本逐利*市场主体可普遍可持续地进行资本逐利和劳动增收,是驱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只有劳资共赢,才能使市场经济较好运转下去,使它所包含的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保护劳动力权,是服务于劳动增收的。而劳动增收,一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增加,可从需求侧拉动投资,防范过剩的危机等引发的市场失灵;二是劳动增收,为劳动力素质提高提供了物质保障,劳动力素质提高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而有利于资本可持续逐利。、劳动增收和政府获利的法,而这就是一种在保护财产权的同时,更自觉地全面地保护劳动力权的法律对策。它既有利于我们扩展“需求侧”,拉动投资与扩大生产;又有利于我们改善“供给侧”,支撑创新发展,使资本逐利、劳动增收与政府获益得到共赢。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国已经意识到经济法是对法制的创新,但经济法学界却缺乏法制理论创新,以致对公权力的介入笃信不疑,单纯从传统的公权力中弄出一种新的法权来,未理解政府也可以以能力而不是以权力来组织经济,也没理会国际竞争(包括相应的法制的竞争)是否已经开始。所以,弄清经济法变得异常困难,更不要说经济法的司法了。
(二)完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范围
经济法是调整劳动力自有自用自益关系(增量利益关系)和确认、设定、保护劳动力权(或劳动能力权)的法,当然这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一是经济法保护劳动力权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法律中有一定表现;不过在有关微观经济的法律中设定经济法特有的、尤其是能与民法相区别的权利,还比较薄弱。如在私人物品或商品(包括货物、服务、智力成果等)生产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以及用人单位中劳、资、管之间的劳动力关系;市场经营者(竞争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力(即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关系;市场经营者与生活消费者之间的消费力关系(劳动力再生产关系)等,在有关劳动、公司企业,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中,都有调整这些劳动力关系的法律规范,它们应当属于经济法。但问题在于除了劳动法有劳动权的概念之外,其他如股权、经营权、消费权等等,在有关法律中都缺乏经济法学的研究与立法表述。笔者认为,在有关微观经济的法律中存在调整劳动力关系的经济法的观点,也许并不难以理解。因为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仅仅限于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民法没有规定它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一切关系。生产、竞争和消费中的劳动力关系,民法没有也不可能加以调整,上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二是经济法保护劳动力权在宏观经济领域的法律中也有表现。这主要是指在国家监管(规制)、调控、参与经济活动的立法中有表现。这里,主要是应当把经济法与(经济)行政法相区别,弄清市场监管权、宏观调控权究竟为何物?笔者认为,在国家监管、调控、参与经济(或者说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法律中,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属于(经济)行政法,而配置政府对社会整体发展利益须履行义务与享有权利的法律规范,则属于经济法。它应当是存在这样两类法律规范中的。
此处,笔者以《反垄断法》为例做些说明。显然,《反垄断法》中,一是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实施的是市场监管或者市场规制行为,反垄断执法的有关规范只能属于行政法,因为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受到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是接受行政处罚,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这都在行政法框架内。二是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反垄断执法,如果处罚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是为垄断的受害人(经营者)弥补损失,并由此来保障公平竞争环境,以维护经济繁荣;然后,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经营者共享繁荣与发展,那么这些法律规范就可归入经济法了。这里,前者反垄断执法机构行使的是市场监管权或者市场规制权,属于行政权中的一种权力。后者则是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全社会,依法履行提供市场监管或者市场规制这种公共服务的义务,从而又使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公职人员等享有工薪福利、共享发展成果等权利;而这属于制造公共物品(市场监管或者市场规制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劳动力权,这里市场监管或者市场规制就不是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权了。
当然,这后一种法律规范现在并不一定已在《反垄断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反垄断法》关于“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反垄断法》第四条), 以及“ 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其职责(《反垄断法》第九条)等原则规定,尤其这次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6年),其中就意味着政府有履行构建公平竞争秩序、促进社会整体发展(增量)利益的义务;另外,它也可能在反垄断执法的绩效评估、反垄断执法公职人员的工作责任制的立法等之中有所规定。这些规定就是关于行政执法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劳动力(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的权利义务的规定。显然,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者是政府有反垄断、促进公平竞争、保障整体的经济发展(增量利益),使经营者市场竞争力竞相迸发的义务,同时政府及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经营者,在对社会整体共同履行了促进发展义务的同时,可享有共享发展成果(增量利益)的权利,以保障政府与市场主体、官与民合作共赢。前者是政府运用立法授予的行政权,代表社会整体(存量)利益,对经营者损害这种社会整体(存量)利益的垄断行为,给以行政处罚,当然政府也有依法行政、维护竞争秩序的义务,即可对行政实行控权限权,那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市场主体、经营者)的权益,如果损害了经营者(存量)私益的则要补偿,违法强制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就要赔偿(这在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中是常见的)。这里,由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政府与全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故这两种法律关系可以并存也可以分别加以处理。
应当认为,上述在有关宏观经济的法律中存在调整劳动力关系的经济法的观点,也许较难理解。但是,由于市场失灵,在经济上无疑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不足有关,在法律上就无疑与保护劳动力权不足有关。如果我们能顺着这一思路,同时联系有关法律文本的各种规定,上述观点还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为了应对市场失灵,一方面,在微观经济领域,就是要加强对企业劳动者的劳动力权的保护、对竞争者(包括企业等劳动者群体)的市场竞争力权(本质上是竞争者的财富创造能力权即劳动力权)的保护、对消费者的消费力权(劳动力再生产权)的保护。这必然能为增加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提供法律保障,从而既能因消费增加而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发展;又能因提高劳动力素质,从供给侧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劳动力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宏观经济领域,国家以宏观调控方式等干预经济,相对于受干预主体而言,宏观调控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但国家作为全社会的代表人,相对于被代表人的全社会整体而言,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也不过是为全社会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公共服务,而这正是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公共物品,按照我国《宪法》与有关法律的规定,国家公职人员(通过国家机构)也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的,因而这不过是以生产经营“公共物品”为特征的工作与劳动而已,它与微观经济中以生产经营私人物品为特征的劳动,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一场合,对一切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我们不能只看到调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经济干预关系的法律规范,而对调整政府与全社会整体之间的经济发展(劳动力)关系的法律规范视而不见(这在政府绩效评估审计,以及各种工作责任制的规定中,已比较明显)。在宏观经济中,各种国家机构及其公职人员进行宏观调控,是对全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享有经营权的“生产经营者”,全社会民众(履行了赋权与纳税的义务)是享有这种公共物品消费权的“消费者”。因而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法,也是调整劳动力关系,规范国家机构及其公职人员的工作(属于劳动)行为,设定劳动力的权利与义务的经济法;当然这不排除宏观调控法中存在着调整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干预关系的法律规范,但这是对政府授权又对政府控权、限权的(经济)行政法。
因此,只有对横向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和纵向的、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动力关系,统一由经济法调整,才能有力地保障劳、资、政的合作共赢,必定能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构建经济诉讼程序,完善经济法的司法
在确定什么是经济法中展开经济法的司法。如果我们真的弄清了什么是经济法,那么经济法的司法又如何,如经济诉讼法是什么等,也就比较容易研究清楚了,构建与完善经济诉讼法也会有较大的进展了。经济诉讼法应当是一种公共经济发展利益诉讼法。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包括私人产品(商品)的劳动诉讼、竞争诉讼与消费诉讼,是以共同所在的整体的经济发展利益为媒介的、平等主体之间因劳动力自有自用自益所发生的纠纷引起的诉讼;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是以全社会整体的经济发展利益为媒介的、不是平等主体之间因劳动力自有自用自益所发生的纠纷引起的诉讼,主要指公共物品的生产经营诉讼、发展成果共享与风险共担的诉讼、公共物品的消费诉讼等。显然,凡是既得利益(包括存量的私益、公益)纠纷,是用不着经济法与经济诉讼法来处理的。因此,从公益诉讼为经济诉讼法找出路,还需要分析;因为公益可以是现成的、独立存在的存量公益,它早已由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应的诉讼法去保护;公益也可能是预期的、同创共享的增量公益,这才需要一种新的、或可被称为经济法及其经济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来保护,这都需要另行研究。不过,它并没有那么简单,即不能说经济诉讼就是公益诉讼,因为经济诉讼是应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相并列的一种诉讼。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应的一种诉讼。我们可以论证经济诉讼中有公益诉讼,但不能说经济诉讼就是公益诉讼。
总而言之,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争取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除了国家重视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物)的地位下不断解放出来,也就别无他途,因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时习近平讲话。访问于http://china.newssc.org/system/2012/11/15/01367078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2月25日16:21。因此,以经济法及其司法来保护劳动力权是非同小可的法制领域的大事变,它迟早会引起法治生活的大变化,从而为国家、大众与学界所关注。
Subject:Make up For the Economic Law of Judicial
Author&unit:CHEN Naixin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Hunan 411105,China)
Because the legislation of economic law has not really confirmed and established the unique rights of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law, the judicature of the economic law can not really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law. At present, some cases that belong to economic law ar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issues. This makes the economic law appear judicial blank, and has been very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fair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must from the economic law legislation on scientific confirmation, setting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arties (labour rights), litigation and non litigation procedural law and the corresponding formulation,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law rights can also get judicial protection. Making up the blank of the judicial of the Economic Law, must be able to effectively protect workers, investors, govern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hina.
economic law;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ustice; the economic procedural law
D922.29
:A
:1009-8003(2017)05-0014-08
[责任编辑:吴岩]
2017-07-10
陈乃新(1946-),男,浙江绍兴人,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