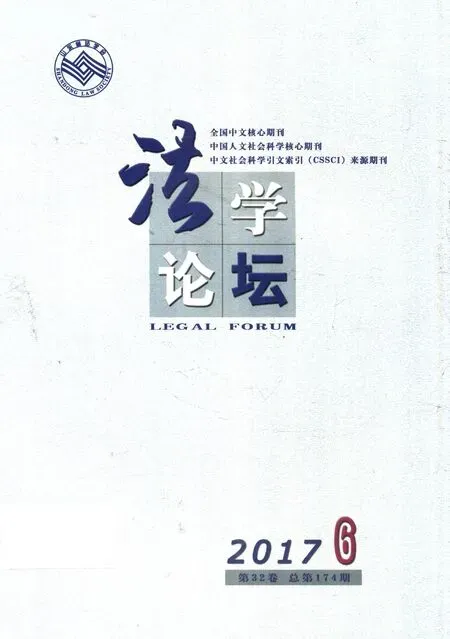健康环境权之溯源与辨正——司法适用的视角
陈海嵩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学术视点】
健康环境权之溯源与辨正——司法适用的视角
陈海嵩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健康环境权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并为目前国际人权法的司法实践所认可。尽管以生命健康权为代表的既有人权保障机制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毕竟不能对环境利益予以整全性的保护,不符合现代环境保护的需要,也不适宜作为证成“环境权”的例证。实证分析表明,拉丁美洲各国法院在多起案件中加以直接运用的“健康环境权”并不意味着是对“环境权”的直接适用;美国各州宪法中相关条款的司法适用也表明,“健康环境权”与“环境权”在司法适用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效力。“健康环境权”是作为人权的健康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适用,而不是“环境权”的组成部分。
健康环境权;环境权;健康权;实证分析
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是保障人体健康的基础性条件,如何通过相应国家义务的践行,来实现公民环境健康权益的有效救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的课题。①陈云良:《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研究》,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2期。由此,国际上产生了“健康环境权”(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司法适用。②Sumudu Atapattu, The Right to a Healthy Life or the Right To Die Polluted? , 16 Tulane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101(2002).但也必须注意到,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将健康环境权的司法适用视为“环境权”司法适用的例证,③如有观点认为,相较于传统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后来居上”,拉丁美洲地区则是“全球先锋”。参见吴卫星:《我国环境权理论研究三十年之回顾、反思与前瞻》,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这不仅在概念上造成混淆,更是造成“环境权已经得到一定的司法适用”的错误认识。基于此,有必要从司法适用的角度,对健康环境权的由来及其内涵予以辨正,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一、健康环境权的缘起及国际法实践
对健康环境权的关注,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环境运动。在环境运动的初期,人们就已经普遍注意到,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会对生命健康构成威胁,并对现有的人权体系形成了挑战。这对1972年首次联合国环境会议所达成的《人类环境宣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就明确宣示“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基本生存的权利”。在1997年国际法院所审理的“匈牙利大坝案”中,Weeramantry法官在判决中明确提出:环境保护应当同样构成当代人权的一项必备条件,因为良好的环境对各类人权、尤其是生命权和健康权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对环境条件造成的损害也就同时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际人权公约所宣示的所有基本人权。*参见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料选编》,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31页。这就意味着,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也就对现存的基本人权构成了侵害,应当运用人权保障机制予以救济。*M.T.Acevedo.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8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452(2000)。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基于已有的人权保障机制而达到环境保护目的已经获得判例的支持,其优势在于:从已有的独立人权(如生命权、财产权)来看待环境保护问题,可以聚焦于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环境损害对受到国际公认的主要人权价值的侵犯)。这就有效避免了如何对“良好、适宜环境”加以定义的难题,也能适应已有的人权组织并与相关司法管辖权限保持一致。*Alan Boyle,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lan Boyle amp; Michael Anderson (eds.), Human Rights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p.43.对目前国际人权法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案例进行考察也能发现,其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逐渐达成的共识是运用现有人权规范(如生命权等)而开展相应审理工作并作出判决。随着环境运动的深入和全社会环保意识的加强,欧洲人权法院也改变了其对待环境案件的态度,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生活隐私权”为规范基础、从“环境保护与人权两者相互关联”的角度对环境案件进行裁判。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Guerra等诉意大利”案。
在这一案件中,原告是以Guerra为代表的40位意大利公民,其针对被告(原告居住地附近的农药化工厂)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起诉讼,指控其环境污染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中有关获得信息权利(第10条)的规定。1996年6月,欧洲人权委员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不利于意大利政府的裁定,认定其没有公布足够的环境信息以制止原告遭到环境侵害。意大利政府对该判决提出上诉,案件在同年9月移送到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的审理中,围绕《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是否适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最终认定该条款的规范含义是禁止政府对个人获取信息作出不必要的限制(消极义务),但并未对政府确立搜集和发布信息的积极义务,因此本案不适用公约第10条,但被告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有关个人隐私权的规定。人权法院指出,从原义上看,《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主要是为了使个人免于遭受公权力机构的非法干预,但考虑到现代社会的生活标准,为有效的实现家庭生活和隐私权的目的,政府负有采取一定措施的法定义务;对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会明显影响到个人福祉,以至于不能安居于此并实现有效的家庭生活。本案中的化工厂在1994年停止生产之前,原告一直都没有获得相关信息,无法评估生活在此地的环境风险。因此,意大利政府未能有效履行保护公民家庭生活的法定义务,侵犯了《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确立的“生活隐私权”,判决向40位原告提供经济赔偿(1000万里拉/人)。通过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理由,可以明确地看出通过现有的人权体系及其保障机制来实现环境保护的可行性和适应性。
当然也必须看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现有的人权体系对环境被害人提供救济的确是最为高效和可行的路径,但从环境保护内在特质出发,由于目前主流的人权法律规范及其体系具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c)特征,在适用范围上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无法对无涉人体健康的生态破坏行为、或者暂时无法确认其生态环境损害之行为构成有效的约束。有观点就明确提出,从自然环境角度看,已有的人权路径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仅仅只能对人类健康加以一定的保障并提供救济,对非人类生物和生态环境自身损害就无能为力。*Dinah Shelton, Environmental Rights, in Philip Alston(ed). Peoples’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88.因此,目前国际人权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所保障的“健康环境权”,其规范基础是通过环境保护与现存人权(生命权、财产权、知情权等)的相互联系而实现有限度的环境目标,并不能对环境利益给予全面性、整体性的保护,与一般意义上“环境权”的含义有着较大差异,也就不适宜作为环境权适用的例证。
二、健康环境权的国内法适用
一般而言,“可司法性”是宪法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因此,主张环境权是一项独立基本权利的学者非常注重寻找各国司法实践中的相关案例作为佐证。有观点提出,目前已经有9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环境权,其中至少有44个国家在司法判决中对健康环境权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典型例证包括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等国,这是向环境权司法适用所迈进的一大步。*参见吴卫星:《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182页。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上述各国宪法中的环境权条款已经具有了直接“诉诸司法”的效力,尚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考察南美洲各国法院的相关判例,*相关案例的详细介绍,参见Adriana Fabra amp; Eva Arnal, Review of Jurisprud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Joint UNEP-OHCHR Expert Seminar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 Background Paper No. 6, 2002.其加以确认和保护的权利在用语上即为“健康环境权”(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这一司法惯例的来源,可追溯到1988年《美洲人权公约》的议定书之中。在该文件(圣萨尔瓦多议定书)中,第11条规定“每个人都有在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可以看出,南美洲国家在环境案件中给予法律救济的所谓“环境权”,正是健康环境权。这提醒我们应注意“环境权”和“健康环境权”的区别,不能简单的将两者相互混同:
1.从内涵上看,健康环境权的价值内核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保护人体健康并“免于污染”,并不涉及现代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所越来越重视的生态系统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有观点即提出,传统法律体系的价值取向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在“人类”面向的个人主义或者团体主义之上,而新的环境时代所要求的法律和宪法需要在价值上有所突破,应建立在生态主义之上,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予以尊重并在法律上加以适度体现,将其他有生命的物种利益也纳入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范围之中,即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人类与自然共同利益”为中心。*参见陈泉生:《环境时代宪法的权利生态化特征》,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该变化表现在人权体系之中,就是“生态人权”(Ecological Human Rights)的产生与确认。*Prudence.E. Taylor ,From Environmental to Ecological Human Rights: A New Dynamic in International Law?. 10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309(1998)可以看出,作为环境时代代表性权利的“环境权”,其所保护的范围自始就不局限于人体健康的领域,而是关涉到更大范围内的生态利益与自然物种利益,同基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健康环境权在内涵上有着较大差异。
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生态平衡与物种多样性问题,仅仅从人类利益出发,“健康环境权”也远不足以实现“环境权”的保护宗旨:(1)从环境权理论所预设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目的看,每个人不仅仅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还享有在适宜的、令人感到愉悦的、能够产生美学利益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就超越了“人体健康”的范围,而是涉及更高层次的精神与美学价值利益。(2)从可持续发展和代际正义的角度看,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要考虑到未来世代人的需要,不能对后代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构成损害,这是现代意义上环境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健康环境权显然无法适应这一全新的广阔领域。总结而言,“环境权”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愿景,是身体健康、生态安全、精神愉悦、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综合形成的权利诉求,而“健康环境权”仅仅关系人体健康领域,在范围和内涵上显然存在较大差异。从制度功效上看,如果将“健康环境权”和“环境权”相互混同,这就意味着只有因破坏环境而对公民的健康构成明确损害时,才能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这是无法对整体性环境形成有效保护的。*参见[日]竹下贤:《环境法的体系·理念与法治主义的实质化》,李桦佩译,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7期。
“健康环境权”和“环境权”在内涵上的差异,可以从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具体规定上得以证明。根据南非宪法第24条,其对环境权的内涵进行了分类说明和详细列举:“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a)得到不损害其健康和无害的环境;(b)为了保护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法律和相关措施,这些法律应当能够:(i)治理污染并减缓生态破坏;(ii)促进环境管理和生态保护的发展;(iii)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进行。”这一规定明显表明,“健康环境”只是环境权保护范围的一部分,两者不能简单的划等号。
2.从概念溯源上看,“健康环境权”不能视为是环境权的一部分或者由环境权“发展而来”,而是起源于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right to life)和“健康权”(right to health)。这意味着,“健康环境权”并不是归宿于“环境权”的子项,两者并不存在相互隶属的关系,仅仅在保护范围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从目前的国际人权法体系看,“环境权”也并未被广泛接受为一项新的独立人权。*参见[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国际法与环境》,那力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那立:《环境权与人权问题的国际视野》,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6期。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也没有实证法上的依据来证明“健康环境权”起源于所谓“环境权”。而根据国际人权法体系,“健康环境权”则可以找到其规范依据,即在国际人权公约中得到认可的“健康权”。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第12条,健康权已经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一项新的社会性人权;在健康权的具体涵义上,根据2000年联合国专门委员会对该条款的解释(第14号评论),健康权不仅仅涉及身体健康水准的保养,而且也包含保障健康水准的各种基础性条件,例如获得充分保障的卫生条件和设备、获得安全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有充分的食品并获得足够营养、有良好的职业环境与居住环境等。*United Nations. The Right to the Highest Attainable Standard of Health , General Comment No.14, E/C.12/2000/4.总计而言,从目前国际人权法角度看,其承认环境是影响到健康权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健康权”为起源(starting-point),根据生态环保相关需要进行相互结合,由此生成“健康环境权”。更直接的说法是,健康环境权是健康权、生命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和延伸。*A.Cançado Trindade,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Edith Brown Weiss(e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International Law: New challenges and dimensions,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1992.
对南美洲国家的相关案例加以分析,也能得出与规范分析相类似的结论。在哥伦比亚法院1993年所审理的“Antonio Mauricio Monroy Cespedes”案件中,法院就明确指出,不能将人权公约中的“健康环境权”和已有的健康权、生命权分割开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同样会对人体健康和生存造成无法填补的损害。*Adriana Fabra amp; Eva Arnal, Review of Jurisprudence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Joint UNEP-OHCHR Expert Seminar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 Background Paper No. 6, 2002.根据哥斯达黎加法院对环境相关的案件判决,其也明确提出,“健康环境权”和“环境权”都起源于(emanate from)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命权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所承担的基本义务;之所以承认健康环境权,是因为如果对此加以忽视或者否认,就会使得生命权受到极大的限制。*同④。
综合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南美洲国家法院在相关环境案件中所适用的“健康环境权”,并不能视为是“环境权”的司法适用,而是基本人权的生命权通过司法适用得到的结果。有必要说明的是,在理论层面的研讨中,并不排斥将免除污染和不良环境作为环境权的内涵之一;各国宪法的环境保护条款中,也多有“在健康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表述。但从严格司法适用的角度看,一些国家法院之所以将“健康环境权”予以司法适用,并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权”具有可司法性,而是因为其与传统意义上的健康权、生命权具有事实上的联系而具有了规范效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环境权”难以司法适用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内涵的模糊性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健康环境权正是因为能够将其范围限定在一个较为明确和易于判断的领域——人体健康——之内,*针对健康权的内容界定与法律救济,国际上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成熟的标准。参见夏立安:《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可裁决性——从健康权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2期。而不是难以准确界定的“良好环境”,方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和“可司法性”。
三、联邦国家州宪法中的健康环境权及其适用
除前述各国宪法规定外,还必须注意到联邦制国家中宪法所具有的独特属性。根据联邦制国家的制度安排,其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拥有各自的宪法,都具有相应的、彼此独立的政府及其法律体系。*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如此,即使联邦宪法中没有环境权利的相关规定,各州宪法中也可能存在相应条款,其关于“健康环境权”的规定及司法实践值得加以关注。这方面的代表性国家是美国。具体而言:
(一)美国各州宪法环境权利条款的不同类别
由于受到种种因素限制,美国联邦宪法自1787年诞生以来,一直没有加入环境保护的相关条款。而相较于联邦宪法,美国各州宪法在环境保护条款上的进展要顺利一些,其中有公民环境权利条款的代表性宪法有:伊利诺斯州宪法、蒙大拿州宪法、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夏威夷州宪法、马萨诸塞州宪法、罗德岛州宪法。这其中,伊利诺斯州、蒙大拿州和夏威夷州宪法对个人健康意义上的“健康环境权”进行了规定。例如,根据《伊利诺斯州宪法》第11条的规定,任何人都拥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并能够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对该权利加以实施,从而能够抗衡任何政府、个人或者团体的侵犯。根据《蒙大拿州宪法》第2条的规定,任何人生来就享有一些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包括享有清洁健康环境的权利。《夏威夷州宪法》则对健康环境权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其第11条规定,每个人享有清洁健康环境的权利,包括对污染物的防治和对生态资源的保护、保持、增进;这一权利是由涉及环境质量的法律所明确界定的。每个人都可以遵循一定的程序提出相应诉讼,防止任何团体和个人对健康环境的侵犯。
同其他州宪法中的环境权利相关条款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前述三个州宪法对“健康环境权”规定的独特性。在《宾夕法尼亚州宪法》中,其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良好的环境,也包含保护生态环境的景观、历史、美学价值等”(第1条第27款);在《马萨诸塞州宪法》中,其规定“每个人应当拥有清洁空气和水的权利,不受到噪声的侵犯,有权享受环境的景观性、历史性、美学性价值”(修正案第49条);在《罗得岛州宪法》中,其规定“人民应当享有在海边钓鱼、在海滩休闲的权利;应当保护人民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并关注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和保持”(第1条第17款)。显然,宾夕法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宪法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限定在“人体健康”的领域,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是对一般意义上“环境权”的宣示,同伊利诺斯州、蒙大拿州和夏威夷州宪法中的“健康环境权”形成了区别和对比。概括而言,美国各州宪法中的环境权利条款可以归为两大类别:一类是限定在个人健康领域内的“健康环境权”,另一类是更为一般性、普遍性的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
(二)各州宪法环境权利条款的法律效力
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前述美国各州环境权利条款是否能够具有“独立实施”的能力,是区别“健康环境权”和一般意义上“环境权”的一个主要标志。换言之,根据不同的规范类别,各州宪法中的相关条款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具体而言:
1.针对单纯的“健康环境权”,可以独立实施。从文意解释上看,在规定了“健康环境权”的州宪法中,往往同时规定公民可以通过正式的法定程序对该权利予以实施,如在前述伊利诺斯州和夏威夷州宪法中,在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健康环境权后,即规定公民“能够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对该权利加以实施,从而能够抗衡任何政府、个人或者团体的侵犯”。从宪法条文分析,这就明确赋予了“健康环境权”具有司法上的可适用性。*Barry E. Hill, Steve Wolfson, Nicholas Targ,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 Synopsis and Some Predictions, 16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 392 (2004).从司法实践看,蒙大拿州1999年“环境信息中心诉蒙大拿州环境保护部”一案的判决,为“健康环境权”的司法适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该案中,原告(环境信息中心)对蒙大拿州环境保护部提出诉讼,要求其禁止对采矿公司发放排污许可证。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对原告的诉求给予支持,其在判决中提出,原告尽管并不会因为许可证的发放而遭到特别危害,但基于立法目的和基本权利保障,原告仍然具有法定的起诉资格;环境部门针对采矿公司所制定的排放豁免对若干重要因素缺乏考虑(排放污染物质的特点及相应的环境容量),因此对原告的健康环境权构成了侵害。*Montana Envtl. Info. Ctr. v. Dep't of Envtl. Quality, 988 P.2d, 1243-49 (Mont. 1999).
必须看到,和前述拉丁美洲国家“健康环境权”的司法判例相类似,蒙大拿州的“健康环境权”判例具有明显的限定性,其适用范围限定在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损害的场合,并不涵盖一般意义上环境权对环境舒适度、精神愉悦、生态利益保护等方面的要求。这一特征也可以从蒙大拿州随后的司法实践得到印证。在2006年的Lohmeier vs. Gallatin County案中,蒙大拿州最高法院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理由是原告并未证明污染物增加及生态破坏的后果,不属于州宪法环境权利条款的保护范围,不能援引环境权条款提起诉讼。*参见陈海嵩:《从环境宪法到生态宪法》,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该州法院针对类似案件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态度表明,“健康环境权”具有严格的法定限制和适用范围,与一般意义上的公民环境权相差甚远,不宜作为“环境权”可实施性的依据。
2.针对一般性的“公民环境权”,不具独立实施性,而是需要通过立法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在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罗得岛等规定一般意义上“环境权”的州宪法中,司法机构并不承认该条款具有“独立实施”的属性。在著名的1973年的葛底斯堡战场瞭望塔案件中,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就明确提出,原告援引《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第1条有关环境权条款提出诉讼的行为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具体原因是:①该环境权条款创造性的将适用范围扩大到“美学或者历史领域的利益”,但宪法中并未确认到底应由谁行使、如何行使这一权力,这需要由立法加以具体确定,而不是由法院加以确认。②该条款中所规定的“良好的环境”、“生态环境的景观、历史、美学价值”等概念缺乏明确的内涵,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应由立法机构对行政行为建立具体的标准及程序,而不是司法机关来确定。③《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对环境权的规定(第1条第27款)和马萨诸塞州宪法的相关条款一样,不是可以“独立实施”的条款,需要基于立法才能得到具体执行。*Commonwealth v. National Gettysburg Battlefield, 311 A.2d 588,595 (Pa. 1973).从该案判决可见,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和马萨诸塞州宪法中的环境权条款并不具有司法直接使用的效力。在另外一个规定了环境权的州——罗得岛州,其主流观点也是将该条款阐释为需要通过立法方式加以具体实现,并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Bret Adams et al.,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visions in State Constitutions, 22 Journal of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Law ,213(2002).显然,针对一般性的“公民环境权”,美国的主流观点是由立法机关加以实现,这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宪法中的“宪法委托”效力,也与各国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实证效力相一致。*对各国宪法环境权条款规范效力的具体分析,参见陈海嵩:《环境权实证效力之考察》,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美国各州宪法中的环境权条款不具有直接的司法效力,“健康环境权”与“环境权”在司法适用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效力。
四、迈向“精细化”的环境法研究:代结语
综上,“健康环境权”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是对单纯个人权益的保护,和当代环境法加强生态整体性保护的趋势并不完全吻合;拉丁美洲国家和美国个别州对“健康环境权”的适用,并不适宜作为独立权利的“环境权”司法适用的例证。从理论上看,我国传统上以“司法适用为中心”的环境权理论难以有效应对现实环境问题,更是对环境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造成了阻碍*参见张恩典:《“司法中心”环境权理论之批判》,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有学者对“环境权”学说的发源地——日本的司法实践与理论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指出日本主流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都对环境权表示怀疑和拒绝*参见徐祥民、宋宁而:《日本环境权说的困境及其原因》,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3期。。所谓“环境权”难以通过司法适用的方式得到证立,很大程度上并非规范意义上的独立权利。相较于抽象、模糊和歧义的“环境权”,与人体健康直接相关的“健康环境权”才是更具有紧迫性、重要性和规范性的法律议题。“健康环境权”是作为人权的健康权在环境保护领域的适用,是公民针对“免于污染”的清洁环境的请求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环境权”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魏治勋]
Subject:The Origi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The Perspective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Authoramp;unit:CHEN Haisong
(School of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originates from environmental movement since 1960s, as well as recognized by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Although the right to life and health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isting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However,It can not be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environment, and can’t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 and "environmental right" have different legal effect in judicial application.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ight to health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right to a healthy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right; Right to health; Empirical analysis
2017-06-26
陈海嵩(1982-),男,湖北武汉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资源法。
D922.68
A
1009-8003(2017)06-00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