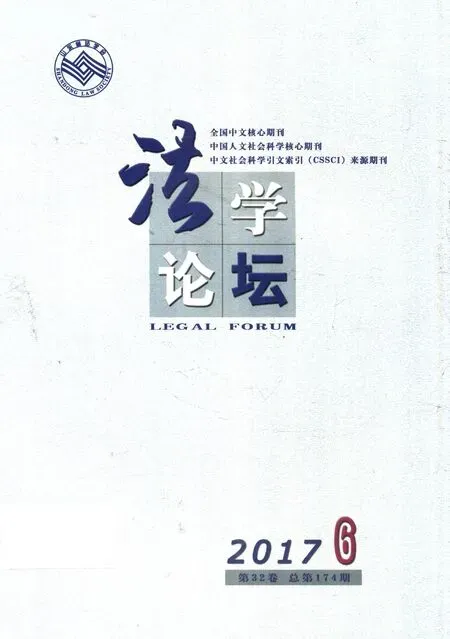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张明楷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张明楷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刑法理论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与解释并不是对立关系,批判性解释可以使刑事立法的形式缺陷得到弥补,也能为刑事立法的完善奠定基础。刑事立法也应当善于类型化,从而为解释提供应有的空间,使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合理规制;正确解释;良性互动
刑事立法相对稳定的时代,就是刑法解释的时代。亦即,面对相对稳定的刑法条文,刑法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刑法。反之,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刑法理论就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而是要关注刑事立法本身。一方面,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会征求刑法学者的意见(是否被采纳则是另一回事),刑法学者必须对相关立法草案进行研究,以自己认可的理论标准进行评判。另一方面,“立法也难以避免盲目性。法律规则是由立法者提前用概括性的语言加以制定的,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境况一无所知。”①[美]布赖恩·Z.塔玛纳哈:《法律工具主义:对法治的危害》,陈虎、杨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刑事立法越是活跃,其暴露出来的立法问题也就越多,这不仅给解释带来了困难,也会促使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展开批评。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的立法机关“像金字塔一样的沉默”②[日]松尾浩也:《刑事法学の地平》,有斐阁2006年版,第48页。,刑法修改相当缓慢。“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当罚的社会脱轨行为,都是通过对刑法的柔软的解释、适用来应对的,这是日本刑事司法的一个特色。”③[日]曾根威彦:《现代の刑事立法と刑法理论》,载《刑事法ジャ-ナル》2005年第1号,第7页。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留给刑法理论解释的余地与空间就减少。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刑事立法异常活跃,不仅制定了诸多的单行刑法,而且不断地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甚至一年修改多次。“由于这种‘立法时代’的到来,长时期关闭在解释论里的刑法学者,再次将目光转向了立法论。近年来,不仅就个别的立法予以检讨,而且出现了将刑事立法的一般性理想状态纳入视野的著作、论文,促进了‘刑事立法学’的确立。”④[日]松原芳博:《刑事违法性と法益论の现在》,载《法律时报》2016年第7号,第25页。概言之,由于刑事立法的活跃化,日本的刑法学界已经从以往纯粹的刑法解释学转变为刑法解释学与刑事立法学并存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全面引进苏联的刑法理论。改革开放后,刑法理论基本上不是从事刑法解释学的研究,而是从事刑事立法学的讨论,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苏联的刑法理论原本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难以在其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还没有介绍、引入到我国。另一方面,1979年刑法的确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有的是自身存在的缺陷,有的是社会急剧变化使刑法产生了缺陷。1997年修订刑法之后,由于需要解释的法条大量增加,更主要的是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不断引入,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片天地,许多刑法学者发现了自己的理论差距,刑法解释学得以明显的发展。诚然,解释方法无穷,但解释结论总是有限。由于刑事立法的活跃化,刑法修正案的层出不穷,刑法理论不得不再次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因而不得不思考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关系。
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关系,可谓既简单也复杂。一般来说,刑法理论指导刑事立法,同时也阐释刑事立法。没有理论指导的刑事立法,必然呈现杂乱无章的局面;刑事立法如若没有刑法理论的阐释,就难以得到妥当的适用。但从事实上来说,二者的关系远非如此简单。例如,我们必须坚持什么样的理论,以该理论检验刑事立法,进而要求修改刑法,从而使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起规制作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修改既有理论,而不需要修改刑法,从而通过解释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既需要修改刑法理论,也需要修改刑法条文,从而使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如果不能妥当处理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关系,二者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本文侧重于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作用,将上述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规制、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解释、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补正。
一、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规制
刑法理论包括许多内容,源于刑法规定的理论可谓具体理论,随着刑法的修改变化而变化。所谓“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话,全部藏书就变成废纸”,实际上是指源于具体法条的理论随着法条的修改而丧失意义。不是源于刑法条文的理论,而是有关刑法性质、犯罪本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理论,则不可能因为刑法的局部修改就立即发生变化。这种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规制作用表现在两个过程中:在刑事立法之前或者立法过程中,对刑事立法起指导作用;在刑事立法之后,对刑事立法具有批判性功能。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法律,所以,本文在此强调的是两个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规制作用,即关于犯罪本质的理论以及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理论。质言之,我们必须以法益保护主义以及刑罚的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综合理论,规制刑法条文的增加、删除与修改。
(一)关于犯罪本质的理论
在刑事立法中,不可能根据形式的违法性标准,判断刑法应当禁止哪些行为;只能以实质的违法性即犯罪的本质为标准,判断哪些行为值得科处刑罚。“从形式上说,刑法上的违法性,是指对刑法规范(评价规范)的违反,但是,由于违法性是根据刑法规范的评价应当被否定的事态的属性、性质,故其内容便由刑法规范的评价的基准即刑法的目的来决定。将什么样的行为作为禁止对象,是由以什么为目的而禁止来决定的。因此,对实质违法性概念、违法性的实质的理解,是由对刑法的任务或目的的理解推导出来的。”*[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3版),有斐阁2016年版,第105页。
如所周知,“耶林法律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目的,他在一部他所撰写的重要的法理学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基本观点是,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他宣称,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些可欲的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根据他的观点,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有意识地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倘若刑事立法不以目的为指导,其内容必然杂乱无章,而且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刑事立法的目的也是刑法本身的目的,是立法机关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的意义之所在。
关于刑法的目的,当今刑法理论主要存在法益保护说与法规范维护说之争。可以肯定的是,从刑法解释论的角度来说,法规范维护说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学说(尽管笔者并不赞成*参见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357页以下。),但是,就刑事立法论而言,或者说就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规制作用或者贡献而言,只能采取法益保护说。这是因为,即使承认法规范维护说具有解释规制机能,但它不可能具有立法规制机能。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法规范,判断已经发生的某种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但是,对于刑法并没有规定的危害行为,我们不可能以现有的法规范为根据或者标准判断其是否值得科处刑罚。法规范维护说只有借助法益保护说,才能为犯罪化(增设对新型犯罪的处罚规定)提供合理根据。当下,各国基本上都在实行犯罪化,不断增设新的犯罪。然而,法规范维护说基本上不可能为增设新的犯罪提供根据,因为这些行为并没有否定法规范。所以,只有借助法益保护说,通过证明某种行为严重侵害了国民的生活利益,才能使其犯罪化具有合理根据。同样,法规范维护说也难以为非犯罪化提供根据,因为已经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都是对法规范的否定。只有借助法益保护说,通过证明某种行为没有侵害法益,才能使其非犯罪化具有合理根据。
法益概念可以分为自由主义的法益概念与实定的法益概念。前者是指基于国家的任务在所有犯罪中作为核心要素所要求的法益概念,这一概念是实质的犯罪概念的前提,是基于保障国民自由的观念的前实定的概念,它前置于刑事立法或者说直接指向刑事立法者。*Vgl.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4.Aufl., C.H.Beck,2006,S.13ff;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台湾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2年版,第103页。后者将法益理解为法所保护的利益,故法益不是前实定的概念,但是,在解释某个刑罚法规的保护法益时,以及在立法者决定什么值得刑法保护时,都必须以实质的法益概念为基准。*参见[日]上田正基:《その行为、本当に处罚しますか—宪法的刑事立法论序说》,弘文堂2016年版,第28~29页。显然,二者并不是对立关系。法益的内容本身是前实定的,但这种内容要受到法律保护还必须依靠实定法。于是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前实定的利益中,一部分受到了刑法的保护,另一部分却还没有受到刑法的保护。就已经受到刑法保护的部分而言,刑法理论一方面要以保护法益为根据解释法条,另一方面要反思该利益是否值得刑法保护;就没有受到刑法保护的部分而言,刑法理论要考虑在社会发展变化后,其中哪些值得刑法保护。自由主义的法益概念侧重的是立法规制机能,实定的法益概念侧重的是解释规制机能。
概言之,法益概念不仅具有解释规制机能,而且具有立法规制机能。法益概念为刑法的保护对象提供经验的、事实的基础,法益是作为人们的生活利益而成为保护对象的。不管是在解释论上还是在立法论上,法益概念都起着指导作用。反过来说,法益概念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作用,就是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机能。法益概念的属性是经验的实在性以及对人的有用性,因此,对纯粹的道德以及单纯的价值观的保护可以排除在刑事立法之外。具有经验的实在性的法益概念,成为检讨刑事立法事实的基础。*参见[日]松原芳博:《刑事违法性と法益论の现在》,载《法律时报》2016年第7号,第26页。亦即,法益概念在刑事立法的过程中起作用,使国家动用刑罚具有正当化根据,同时划定了处罚界限:只有当某种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时,对之设置处罚规定才是正当的。*参见[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有斐阁2008年版,第20页。具体而言,法益保护原则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刑事立法做出贡献。
1.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刑法应当规制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换言之,所谓犯罪化,就是指将严重侵害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当然以有责为前提)。
例如,意思决定自由与意思活动自由,是公民的重要法益,所以,旧中国刑法与国外刑法普遍规定了胁迫罪与强制罪(或强要罪)*参见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304条和第305条、《日本刑法》第222条与第223条、《德国刑法》第240条与第241条、《法国刑法》第222-17条和第222-18条、《意大利刑法》第610条和第612条等。,以便保护国民的意思决定自由与意思活动自由。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刑法理论有理由主张在今后的刑事立法中增加胁迫罪与强制罪。再如,与私人文书、印章具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的信用,是一种传统法益,在旧中国刑法与其他国家刑法中均受到保护。*参见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210条和第217条、《日本刑法》第159条、《德国刑法》第268条、《法国刑法》第441-1条、《意大利刑法》第485条和第486条等。但是,我国《刑法》第280条仅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以及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而没有对私文书、印章、署名的信用这一法益予以保护。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将来也有必要增设这类犯罪。
2.反过来说,即使刑法已经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我们也可以按照法益保护原则,否认这种立法的正当性,从而在刑法中废除这种犯罪。
如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刑法理论对于法益侵害的探讨迈入了新的阶段,使法益概念具有刑事立法的价值,并将法益概念的重点推移至刑事政策领域,作为研讨制定新条款或者修改旧条款的重要依据。亦即,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种社会生活之利益是否应以刑法保护,莫不以法益概念作为决定性的依据,法益概念成为确定刑法的处罚范围的价值判断标准。*参见林山田:《刑法特论(上册)》,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4页。例如,德国在战后将已经完全有责任能力的成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如同性恋、性虐待狂、色情受虐狂等)排除在刑法规制之外,就是因为这种行为只是违反了性道德观念,而没有侵犯法益。*参见[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马君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80~381页。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自杀行为、堕胎行为、21岁以上男子间的自愿且秘密的同性恋行为实行非犯罪化,也是因为这些行为仅违反了道德准则,而没有侵犯法益。*参见[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以下。同样,我们也应当以法益保护的标准判断现行刑法分则的法条是否具有正当性。
例如,现行《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根据《刑法》第294条第5款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与非法控制特征。显然,如果不具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行为特征,某个组织就不可能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然而,侵害法益的是这些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的行为,而不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因此,不能认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本身侵害了什么法益。另一方面,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又必须根据刑法与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本身规定为犯罪。与其他组织相比,也能得出相同结论。例如,现行刑法废除了旧刑法中的反革命集团罪,也没有增设组织、领导、参加危害国家安全集团罪。这是因为,凡是实施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直接以相应的犯罪论处即可,完全没有必要将组织、领导、参加危害国家安全集团的行为本身作为犯罪处理。再如,即便存在杀人集团、抢劫集团,组织者、领导者也只是对杀人、抢劫负责,而不会对组织、领导集团本身承担任何责任。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实施犯罪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其实施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即可,故应当废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立法机关之所以增设本罪,是因为这种行为具有两个方面的社会危害性或者说侵害了两个方面的法益:“第一,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造成不利影响。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一旦泄露并公开传播,往往形成舆论的焦点,对其依法独立公正审判造成干扰。特别是有的当事人一方有选择地泄露部分案件信息,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有时一方当事人制造了舆论,对方当事人为应对也不得不公开发声回应,不可避免进一步泄露了案件信息,甚至形成舆论对垒,给审判机关带来更大压力……第二,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249页。但是,这一说明是难以成立的。
其一,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的行为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的,完全可以直接按相关犯罪处理;如果不构成犯罪的,没有必要作为犯罪处理。《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第274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显然,如果行为人泄露国家秘密,可以按泄露国家秘密罪论处;如果泄露他人隐私,可以认定为侮辱罪;如果泄露他人商业秘密,也可能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论处。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是,泄露未成年嫌疑人相关信息的部分情形。但是,如果对未成年嫌疑人相关信息的泄露,并没有侵害其名誉或者个人信息等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不以犯罪论处也是完全合适的。
其二,认为泄露案件信息妨害司法公正的说法并没有根据。审判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倘若认为泄露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妨害了司法,那么,披露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也会妨害司法。这是因为,即使是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一旦披露并公开传播,也会形成舆论的焦点。但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这对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判造成了干扰。正如美国联邦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所言:“尽管法官受任职终身制保障,得以免受民意干扰,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公众情绪。对法官及其判决的批评之声,时常会传到我们耳中。这在民主社会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法官也会看报,会阅读批评他人判决的学术文章,也会审阅劝说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裁判案件的诉状。”*[美]史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就公开审理的案件而言,当事人一方也可能有选择地披露部分案件信息,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另一方当事人也会为了应对而不得不公开发声回应,同样形成舆论对垒。但不能认为,这就给审判机关带来了压力、妨害了司法。公众对哪些案件有兴趣、希望知道哪些案件的审理情况以及对哪些案件发表看法,并不取决于该案件是公开审理还是不公开审理。例如,对于不公开审理的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未成年人的盗窃、伤害等案件,一般公民都不会关注。反之,对于公开审理的许多案件(如贾敬龙案),一般公民也会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法官的中立立场,并不意味着其不得关注公众对案件的看法。如果一位法官在公众发表不同看法时就不知道该怎么作出判断,他恐怕就不配做法官。显然,通过避免公众关注案件的审理情况,来保证法官的公正审理,既不明智,也得不偿失。概言之,泄露、披露案件审理情况的行为,只要没有侵害当事人的法益,就不可能侵害司法秩序或者其他公共法益。
由上可见,法益保护原则不仅可以说明现行刑法多数法条的合理性,而且可以成为增设新罪的实质根据,以及废除相关犯罪的实质根据。
冯军教授指出:“只要刑法是有效的,就应当服从刑法的权威,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当然要求。任何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自然法、不符合正义或者脱离社会实际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都不会具有正当性。”*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176页。问题在于,“刑法是有效的”是什么意思?例如,违反宪法的刑法条文是否有效?与实现刑法的目的与任务相违背的法条是否有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刑法理论可否根据某种标准判断刑法的某个条文应当是无效的,并且建议删除该条文?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法学对于法律实务的意义不仅止于对司法裁判提供助力。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现一些现行法迄今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借此促成司法裁判或立法的改变。”*[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3页。概言之,当对刑法条文的解释结论无论如何都会违反宪法时,必须对该条文进行批判。正因为如此,国外不少学者总是会判断某些刑法条文是否违宪,一些法治国家还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宪法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在现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具有正当性;在这种场合,就不可能服从该违宪条款的权威。同样,当刑法条文的表述不能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时,刑法理论也不会袖手旁观。换言之,以刑法条文的内容不符合刑事政策、不能实现刑法的任务和目的为由而否定刑法效力的做法,则具有正当性。
冯军教授还指出:“法益保护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德国刑法上的某些规定;相反,法规范维护说则能够作出较好的解释。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73条规定了亲属相奸罪,行为人与18岁以上的具有血缘关系的晚辈发生性交,即使是双方自愿的,也要被处3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罚金;行为人与18岁以上的具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发生性交,即使是双方自愿的,也要被处2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罚金;具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自愿发生性交的,也要被处2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罚金。一种双方自愿的性行为,不可能对其中的任何一方产生法益侵害,因此法益保护说的主张者建议放弃对亲属相奸罪的处罚。但是,提出这种建议并不是刑法教义学者的事情,因为它不是对现行刑法规定的解释。德国刑法教义学者有义务对《德国刑法典》第173条的合理性作出说明,法益保护说却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相反,法规范维护说的主张者认为,只要社会还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家庭,就不允许损害家庭的构造,不允许混淆家庭成员的角色与性伴侣的角色,处罚这种角色混淆行为的法规范就具有合理性。”*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186页。
问题是,倘若亲属相奸罪确实没有侵害任何法益时,刑法理论是应当通过法规范维护说肯定设立本罪的合理性,还是应当通过法益保护说否定设立本罪的合理性?本文只能持后一种回答。制定刑法的是人而不是神,任何一部刑法典都可能存在缺陷。即使在制定的当时似乎没有缺陷,但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稍微经过一段时间也会显现出缺陷。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而不应当是恶法之治。一概无条件地全面肯定刑法条文的做法,并不符合以限制权力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精神。
3. 在根据法益保护原则肯定一个行为值得科处刑罚之后,法益概念还能在刑事立法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分类机能。
刑事立法不可能按照法规范的种类或者行为违反法规范的方式对犯罪进行分类。事实上,不管是宏观层面的分类还是具体层面的犯罪,各国刑事立法都以行为侵害的法益为标准。*只有在侵害某种法益的行为存在许多不同类型时,才可能再以行为方式对法益的侵害程度不同进行分类(如侵犯财产罪)。例如,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对犯罪采取二分法还是三分法,就是以行为侵害的法益为标准的。也因为如此,在刑事立法上,既不应当将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规定为对社会法益的犯罪,也不应当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规定为对社会法益的犯罪。就此而言,我国的现行刑法还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妨害司法罪并不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而是对国家司法作用的犯罪。再如,强迫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具有完全不同的罪质,前者是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后者是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将二者规定在同一法条并不妥当,对二者规定相同的法定刑也不合适。同样,虽然聚众淫乱罪是对社会法益的犯罪,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的行为,则是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
就具体犯罪的设置而言,刑事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法条增设新罪所要保护的具体法益,并且根据该具体法益描述构成要件。不能因为行为方式相同,就将侵害不同法益的行为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
例如,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1款就虚假诉讼罪所描述的构成要件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难看出,只要妨害了司法秩序或者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就可能成立犯罪,而不要求行为同时妨害司法秩序与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换言之,本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司法秩序与他人合法权益。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法院受理案件,就妨害了司法秩序。反之,如果虚假诉讼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也就必然妨害了司法秩序。在此意义上说,将“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结果,完全没有意义。不仅如此,两种不同性质结果的并列规定,必然导致本罪认定的不协调。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第287条之一第1款规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的;(二)发布有关制作或者销售毒品、枪支、淫秽物品等违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违法犯罪信息的;(三)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保护法益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倘若认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信息网络的正当利用,那么,其他任何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行为,都侵害了这一法益。而且,本条不仅使用“违法犯罪”的表述,还多处使用了“等”、“其他”之类的用语。倘若按照字面含义解释,一般违法行为的预备行为也会受到刑罚处罚,这显然不当地扩大了刑罚处罚范围。事实上,只有当上述行为构成相应犯罪的预备犯并且情节严重时,才可能以犯罪论处。可是,毒品犯罪的预备犯、枪支犯罪的预备犯、淫秽物品犯罪的预备犯以及诈骗犯罪的预备犯分别是对不同法益造成的一定威胁,而且威胁程度并不相同,对这些行为给予相同的处罚,就明显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不难看出,将不正当利用信息网络的各种行为作为一种具体犯罪予以规定,并不是理想的立法模式。
近些年来,日本刑事立法出现了“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处罚的早期化”、“重罚化”现象,井田良教授因此指出:“有必要探求替代法益保护原则的刑事立法的指导原理。”*[日]井田良:《最近の刑事立法をめぐる方法论的诸问题》,载《ジュリスト》第1369号(2008年),第63页。然而,“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处罚的早期化”、“重罚化”并不表明法益保护原则不再是刑事立法的指导原理。
首先,关于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在结果无价值论看来,法益概念要为刑法的保护对象提供经验的、事实的基础,不应当承认所谓抽象的法益。“‘法益’是从‘财产’、‘财物’派生出来的概念。盗窃等罪的对象是财物,并不是作为物体就具有价值,而是所有者或占有者在可以使用、收益、处分它的效用中承认其价值。同样,法益意味着与人和某种事物的联系。因此,要能够说是法益,必须具有经验上可能把握的实体,而且,该实体对人是有用的。可以说,法益概念在与人和事物相联系的同时,通过价值与事实的联系,给刑事立法提供价值的正当性与事实的基础。没有满足这种经验的现实性及其与人的关系性的要求的存在,不能说是刑法应当保护的法益,将其作为理由的刑事立法就不具有正当性。”*[日]松原芳博:《刑事立法と刑法学》,载《ジュリスト》第1369号(2008年),第71页。
刑法理论不应当要求法益概念具有绝对的明确性。这是因为,不管采取什么观点,都不能否认的是,刑法必须保护某些“东西”,将刑法必须保护的这些“东西”归纳为任何一个概念时,这个概念都不可能是绝对明确的。其实,将刑法必须保护的这些“东西”归纳为法益,是最合适的。就一些犯罪而言,是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导致对保护法益出现了抽象的表述或者不准确的表述。例如,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日本有“公众的性感情”*参见[日]町野朔:《刑法各论の现在》,有斐阁1996年版,第262页。以及“不想看到淫秽物品的人的自由”*参见[日]林美月子:《性的自由·性表现に对する犯罪》,载芝原邦尔等编:《刑法理论の现代的展开·各论》,日本评论社1996年版,第263页以下。。但是,前者的表述过于抽象,因为“感情”千差万别,难以确定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后者的表述也不准确,因为不想看的人不看就可以了,不必动用刑法。于是,松原芳博教授指出,淫秽物品犯罪的保护法益是,“成人的性欲自己控制权,以及为保障未成年人获得性信号的正当接受能力(性的社会化)的环境。”*[日]松原芳博:《刑事违法性と法益论の现在》,载《法律时报》2016年第7号,第28页。据此,对希望获得淫秽物品的成年人出售淫秽物品的行为,就可以排除在犯罪之外。
其次,所谓处罚的早期化,实际上是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即在法益面临危险时就处罚行为,而不是等法益受到侵害时才处罚。“在刑法‘超前保护’(Vorfeldschutz)的场合……虽然没有损害法益,但是只要通过危险行为威胁到了法益就可以肯定刑事不法的存在。”*[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周遵友、江溯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概言之,处罚危险犯并不违反法益保护原则,相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
最后,所谓重刑化,显然不是法益保护原则造成的。诚然,比例原则有利于防止重刑化,但不能因此认为,法益保护原则是重刑化的理论根据。如后所述,明确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并将之贯彻到刑事立法中,才能避免重刑化。*参见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第97页以下。
(二)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理论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与刑罚目的不是等同的概念。但是,将不正当的目的作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肯定是不可取的。笔者一直认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义性与预防犯罪的合目的性。“刑法性干预只能是出于相对(也即以理性为导向)的刑罚目的,尤其是预防将来的刑事犯罪。这一预防目的不仅包括……在刑罚目的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普遍规范意识的强化和巩固(积极的一般预防),而且也包括对一般大众的威吓(消极的一般预防)以及对行为人的影响(特殊预防)。特殊预防则涵括了对行为人重新社会化的改造(积极的特殊预防)以及通过剥夺行为人的自由确保大众的安全(消极的特殊预防)等内容。”*同⑥。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理论不仅对法定刑的正当性起验证作用,而且对犯罪的设立起制约作用。这是因为,如果某种行为通过刑罚也不可能予以预防,或者适用刑罚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就意味着不能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例如,德国学者根据相关实证材料指出: “随着性道德的自由化和新闻媒介对性内容的直露表演,男性露阴的被害人遭受比暂时的惊恐更严重的损害的危险性也随之而消失。因男性露阴而判罪,对作案人所造成的严重而又深刻的后果与被害人遭受的轻微危险不成合理比例。随着对男性露阴行为处罚的增加,那些人进行一般犯罪的倾向也上升。因此应当将男性露阴非犯罪化。”*[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马君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81页。换言之,如果以刑罚处罚一种较轻的危害行为却普遍导致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发生,就意味着处罚这种行为缺乏正当化根据。
本文在此主要讨论的是刑罚制度与刑罚的适用问题。如所周知,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限制减刑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增加了终身刑的规定。刑法理论必须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基准,判断限制减刑与终身刑的规定是否具有正当性。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要求妥当处理报应刑(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关系。按照责任主义与点的理论,在裁量了责任刑的点之后,就应当在责任刑的点之下、法定刑最低刑以上裁量预防刑;*如果采取幅的理论,则在确定了责任刑的幅度后,在责任刑的幅度内(也可以低于幅度的下限)裁量预防刑。如果有减轻处罚的情节,当然可以或者应当在法定刑之下裁量预防刑。量刑时不应过度考虑一般预防的需要,而应当坚持特殊预防优先的立场。不管发生在什么地区、什么时期的所谓相同案件,犯罪人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大小都不可能相同。*参见张明楷:《责任刑与预防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以下。
各国刑法的相关规定,都要求法官在量刑时考虑特殊预防的目的。例如,《德国刑法》第46条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考虑犯罪人的履历、人身和经济情况,及犯罪后的态度,尤其是为了补救损害所作的努力。《奥地利刑法》第32条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当考虑刑罚和行为的其他后果对行为人将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在决定是否暂缓起诉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性格、年龄和境遇,犯罪的轻重和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态度。”我国《刑法》第5条所规定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实际上也是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再犯罪可能性相适应。*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5版,第544页。特殊预防是刑法所期待的未来的目的,量刑时所注重的正是特殊预防。如果行为人再犯罪可能性大,就会在责任刑的点之下从重处罚;反之,则从轻处罚;如果行为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性,当然就没有科处刑罚的必要。
但是,在判处刑罚的情况下,法官对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犯罪人的行为态度、规范意识等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刑法特别规定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是特殊预防目的的产物,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动态实现。但是,限制减刑制度与终身刑的规定明显不符合特殊预防的目的。
《刑法》第50条第2款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倘若在上述罪犯执行一段时间后,没有任何悔改,再由人民法院宣告对其限制减刑,本文是可以勉强接受的。但是,“同时决定”限制减刑,是指在做出死缓判决时就决定限制减刑。据此,即使罪犯在此后的服刑过程中有明显的悔改,特别预防的必要性明显减少,也要执行限制减刑的判决。事实上,“任何被拘禁者,都不可能在其人格不遭受重大障碍的情况下忍耐15年以上的拘禁,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后他所剩下的并不是真正的生存,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的人的空壳。”*[德]Arthur Kaufmann:《转换期の刑法哲学》,上田健二监译,成文堂1993年版,第262~263页。我国相关实证材料也表明,在犯罪执行15年左右刑罚被假释或者释放后,再犯罪率特别低。*参见张明楷:《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79页以下。既然如此,实际执行15年左右就成为执行的极限。不能不认为,限制减刑的规定明显与特殊预防的目的相冲突。
《刑法》第383条的规定,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这里规定的‘同时’,是指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同时,不是在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以后减刑的‘同时’。”*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657页。然而,如果贪污、受贿罪犯彻底悔改,完全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为什么还要终身监禁呢?这显然违反特殊预防目的。现在通行的说法是,他们原本是要被判处死刑的,现在判处终身监禁当然是对他们有利的,而且有利于一般预防。可是,其一,既然按照现在的死刑标准不应当判处死刑,那么,对他们不判处死刑就不是所谓对他们有利无利的问题。况且,“确切地讲,终身监禁也是一种死刑,一种‘分期’执行的死刑,它损害了犯人的个性。”*[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学》,吴鑫涛、马君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984页。“从根本上说,终身的拘禁正是一种死刑。只不过它不是由死刑执行人执行的,而是由时间执行的。”*[德]Arthur Kaufmann:《转换期の刑法哲学》,上田健二监译,成文堂1993年版,第262页。其二,是否具备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不是以是否有利于罪犯为标准,而是要看是否在报应刑之下有利于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其三,终身监禁意味着法官在宣告死缓时,就做出了罪犯终身不会悔改的判断,但这样的判断是不能被人接受的。其四,对特定罪犯判处终身监禁以便预防其他人犯贪污受贿罪,实际上是将罪犯当作预防他人犯罪的工具,也不可取。
特别要指出的是,立法机关应当对重刑保持克制态度。如所周知,法本来是稳定与进步的对立的妥协,是各种力量、各种价值观、各种立场、各种学说的妥协。在当今社会,立法是一个协商、妥协的过程,根据加达默尔的观点,“法律不仅仅受限于立法者及其意图,法律是一系列价值观的集合。”*[挪威]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威格莫尔坚持认为法律绝非一种文明因素所造就的,而是无数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一个行星系统的特定位置是此系统内外所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样。由此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不同文明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历史的连续性;因此,根据一种或非全体的一些因素解释法律进化,等于将结果归因于原因之一部分,而非原因之全部。科学地讲,原因之一部分不等于原因,犹言五不等于十一样,虽然五是十的一部分。因此,虽然一种观念可能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社会上确实拥有强制力,但认为依此观念即可推导出整个法律进化的看法仍然是不科学的,这是一切非清晰思维(clear-thinking)的罪恶根源。总之,一切法律制度都是无数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大的、小的,相反的或一致的’*庞德:《法律史解释》,1923,34页。——原文注释。。”*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但是,其中的“无数力量”在某些立法中可能是势均力敌的,在某些立法中则并非如此。例如,在民事法、经济法等领域,存在经营者团体与劳动者团体这样的对抗势力,具有利害关系的利益团体可能以不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立法活动中,从而使各方面的利益得到照顾,从而形成妥当的结论。但是,在刑事立法中一般不是如此。当刑法要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者对某种犯罪规定重刑时,总是会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赞成,而且一般人总是容易想象自己会成为被害人,但不会想象自己成为被告人(缺乏立场的交换可能性),故犯罪化与重刑化容易得到赞成。被告人、犯罪人及其家属,不可能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意见一般也不可能传达到立法机关。于是,刑事立法中的要求惩罚犯罪的势力与要求保障犯罪人权利的两种势力,明显不均衡。*参见[日]松原芳博:《リスク社会と刑事法》,载日本法哲学会编:《リスク社会と法》,有斐阁2009年版,第82页。例如,公安部可以代表全体警察要求立法机关增设袭警罪或者规定对袭警行为从重处罚,但是,不可能有另一个机关站出来发表相反看法。在这种局面下,如果立法机关不自觉地对重刑保持克制,就会导致刑罚越来越重,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而要使立法机关对重刑保持克制,学说则是形成妥协的一种力量、是达成合意的一方。只要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运用到刑事立法中,限制减刑、终身刑就没有存在的余地。
由此看来,刑事立法应当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指导,合理选择刑罚制度、合理确定法定刑。当下,应当对刑罚的现实效果尽可能地进行调查与验证。
总之,“学说不是中性的,因为法不是中性的。因此学说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必须不断注意使法符合正义。对来自立法机关或者法官的规则,或者对其同行发表的观点,它必须始终持批判的眼光。简言之,它必须表态。对法作出有价值的判断,有力地揭露一切对正义的违背,此乃学说的基本作用之一。”*[法]雅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二、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解释
上一部分旨在说明,法益保护原则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理论,是指导刑事立法的原理,这两个基本理论也对刑事立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如果刑事立法对犯罪的规定违背法益保护原则,或者对刑罚的规定缺乏刑罚的正当化根据,那么,该刑事立法就不妥当,因而需要修改。本部分旨在说明相反的情形,亦即,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需要修改刑法,而是只需要解释刑法;通过解释发挥刑法应有的作用,并且使刑法保持相对稳定。这里的解释刑法,也存在不同情形:其一,在以往的刑法理论对于刑法规定没有作出相关解释时,需要进行解释,从而使刑法规定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二,在以往的刑法理论对刑法规定作出了相应的解释,该解释结论仍然能适应变化后的社会生活事实时,刑法理论应当维持原有的解释。其三,在以往的解释结论不能适应变化后的社会生活事实,但只需要修改理论的情况下,就不应当修改刑法,刑法学者也不应该要求修改刑法以适合传统的、陈旧的刑法理论。显然,前两种情形没有疑问,问题出在第三种情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修改理论来解释刑法,而不需要修改刑法?
例如,对于盗窃、诈骗财产性利益(包括虚拟财产)的行为,是通过扩大解释刑法上的“财物”概念,直接以盗窃、诈骗罪论处,还是通过修改刑法,在“财物”概念之外增加“财产性利益”的规定,以应对盗窃、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这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激烈争论。*参见黎宏:《论盗窃财产性利益》,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124页以下;姚万勤、陈鹤 :《盗窃财产性利益之否定——兼与黎宏教授商榷》,载《法学》2015年第1期,第63页以下。“在这样的场合,理论上显著对立的问题大多是,发生了立法当时没有预想到的行为样态所造成的财产损害时,是扩张解释以往的条文予以应对,还是交给立法来处理。”*[日]佐久间修:《最先端法领域の刑事规制》,现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换言之,在面临新的法益侵害现象时,是通过刑法解释来应对,还是通过刑事立法来应对,历来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
大体上可以认为,越是采取所谓“严格解释”,就越是主张修改刑法;反之越是采取“灵活解释”,就越会主张修改理论,即通过不断的重新解释使现行刑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严格解释”究竟是什么含义呢?美国学者索伦归纳了严格解释的可能意义,*参见[美]劳伦斯·索伦:《法理词汇》,王凌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页以下。下面逐一简要分析。
第一是“文本论”的严格解释,即所有的法律解释必须立基于法律文本之上。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严格解释,没有现实意义。刑法是成文法,解释者当然必须基于刑法文本做出解释。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解释是或者不是“基于刑法文本做出的解释”?这是“文本论”的严格解释概念没有回答的问题。例如,认为《刑法》第264条所规定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是不是“基于刑法文本做出的解释”?对此问题的回答,必然因人而异。
第二是“字面论”的严格解释,即解释只是涉及刑法文本的字面含义,而非进行目的解释。但是,其一,按照所谓刑法文本的字面含义解释刑法,意味着没有解释。例如,解释者做出“出售是指出卖”、“家庭成员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遗忘物就是所有人遗忘之物”、“聚众斗殴就是聚集多人进行斗殴”、“毁坏就是指砸毁、撕毁、压毁等”之类的“解释”,其实是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解释。换言之,这种解释要么只是用另一个相同的用语替代刑法条文中的用语,要么只是同义反复。其二,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是任何一般人都可能读出来的含义,但是,一般人读出来的含义,并不一定是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例如,在一般人看来,凡是通过欺骗行为获得他人财物的,都是“诈骗”。但是,《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的真实含义却并非如此。其三,在一些场合,人们也很难明确法条的字面含义是什么。例如,“财物”的字面含义是什么?是仅指“有价值的有体物”,还是指“财产”与“物品”?其四,字面上有多种含义时,刑法理论该如何取舍?例如,“持有”的字面含义至少有三:一是拿着,如“我持有入场券”;二是拥有,如“你持有股票”;三是心里存着,如“他持有不同看法”。那么,一个人在网上阅读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电子图书并且记忆在大脑中的,能否因为他心里存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电子图书内容,而认定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呢?依靠字面论的解释如何得出否定结论?显然,刑法上的持有既不限于拿着,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拥有,更不包括心里存着。其实,“法学的永久的重大任务就是要解决生活变动的要求和既定法律的字面含义之间的矛盾。”*[奥]欧根·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字面论的严格解释,只会导致刑法学成为汉语文字法学。
第三是“原意论”的严格解释,即解释是指某种形式的原意论,包括原初意图原意论与原初意义原意论。前者注重制定者的意图,而后者注重刑法颁布后公民理解文本的方式。但是,所谓原初意图原意(即制定者的原意),并不是法律的真实意思,充其量只是起草者的意思;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原初意图原意;即使存在,也可能具有缺陷或者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原初意图原意论意味着活人必须永远生活在死人的统治之下,这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另一方面,原初意义原意(原初公共意义)也只是一种虚构而已。解释者何以知道刑法的某个条文在颁布时形成了所谓原初公共意义呢?
第四是“合宪性推定”的严格解释,将其运用到刑法解释中来,或许意味着必须防备解释挑战宪法。这一点没有疑问。刑法解释必须具有合宪法,违反宪法的解释当然是无效的解释。不过,具有合宪性的解释也未必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在具有合宪性的前提下,还必须进一步判断解释方法与解释结论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第五是“作为被授予权力的狭义解释”的严格解释,即严格解释立法机关被授予的权力。将其运用到刑法解释中来,可能意味着即使是立法机关,也要受到罪刑法定主义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禁止处罚不当罚原则的限制。换言之,在刑法用语可能导致处罚范围过于宽泛时,必须对之进行限制解释,将不能科处刑罚的行为排除在法条之外。显然,这个意义上的严格解释,已经与字面论的严格解释完全不同。
不难看出,本文论与字面论实际上是形式解释,原意论则是解释目标,合宪性推定是刑法与宪法的关系,作为被授予权力的狭义解释可谓实质解释。“‘严格解释’的意义实在是不够清晰。实际上,一旦你赋予严格解释这个理念以实质内容,那么这个标签就算不上是什么特别准确的描述,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名字来指称这种理念。”*[美]劳伦斯·索伦:《法理词汇》,王凌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在刑法上,严格解释不外乎就是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例如,《法国刑法》第111-4条明文规定“刑法应严格解释之”,但是,“刑法‘严格解释规则’并不强制刑事法官仅限于对立法者有规定的各种可能的情形适用刑法。只要所发生的情形属于法定形式范围之内,法官均可将立法者有规定的情形扩张至法律并无规定的情形。”*[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达维指出:“在法国,法官不喜欢让人感到自己是在创造法律规则。当然,实践中他们的确是在创造;法官的职能不是也不可能只是机械地适用那些众所周知的和已经确定的规则。”*转引自[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3页。由此可见,在刑法明文规定了“应当严格解释刑法”的法国,严格解释也只是意味着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即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与国民可以预测的范围内,对刑法条文当然可以进行灵活解释。*尽管总是有人一听“灵活解释”就指认是类推解释或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但笔者仍然要指出的是,灵活解释当然是指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的灵活解释。在社会发展变化,出现了新类型的犯罪时,就需要重新解释刑法条文。例如,在法条文字含义发生变化时,刑法理论可以采用变化后的文字含义,而不必永远按照变化前的含义解释刑法。再如,法条文字具有多种含义时,不能总是只选择其中一种常用的含义,而是可以选择其他含义。又如,字面含义具有多样性时,还可能综合字面含义。如前述“持有”概念,刑法理论不可能完全按照词典含义解释,也不能仅选择词典含义的某一个含义,而是需要综合词典含义。还如,法条字面含义可以分解时,刑法理论完全可以进行分解,而不必总是按照没有分解的含义解释。如“财物”一词,人们长期以来实际上是按没有分解的含义来解释的,亦即,将“财物”解释为“有价值的物”,进而出现了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财物的争论,于是部分学者要求修改刑法。但是,倘若重新将“财物”解释为“财产”与“物品”,则不需要修改刑法。
如所周知,修改刑法需要很高的成本。不管是增设新的法条,还是修改原有的法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法条的表述稍有不当,就可能形成处罚漏洞或者导致处罚宽泛。所以,总体来说,能够修改理论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刑法学的任务原本就是通过解释使陈旧的法条具有鲜活的生命,以便应对新类型的犯罪,而不是让陈旧的法条死亡。陈旧的法条总是具有解释的空间和余地。这是因为,“法律经常利用的日常用语与数理逻辑及科学性语言不同,它并不是外延明确的概念,毋宁是多少具有弹性的表达方式,后者的可能意义在一定的波段宽度之间摆摇不定,端视该当的情况、指涉的事物、言说的脉络,在句中的位置以及用语的强调,而可能有不同的意涵。”*[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3页。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要在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得出的入罪结论,没有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就可以使陈旧的法条应对新类型的犯罪。基于同样的理由,在刑法理论对某个法条或者某些案件的处理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也不应当修改刑法。这是因为,既然存在争议,就不是单纯的字面含义的争议,而是背后的价值观的争议,是某种行为是否值得处罚的争议。反复争议后,才能弄清问题所在。如果此时以刑事立法一锤定音,必然导致问题得不到澄清。但是,在这方面,我国的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都存在需要讨论的现象。
从刑法理论上说,不少学者总是习惯于在刑事立法不符合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时,要求修改刑法。虽然不排除这种做法在某些场合的合理性,但总体来说,这种做法并不是刑法理论的应有姿态。
例如,有学者根据德国关于先行行为的义务违反标准,认为行为人无罪责地意外引起他人伤害而故意不救助致被害人死亡,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遗弃罪。但是,德国关于先行行为的设定,是以其刑法规定了见危不救罪为前提的。如果照搬德国刑法理论的观点,在我国就会形成明显的处罚漏洞。于是,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主张“增设这一罪名(即见危不救罪——引者注)或者在否定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同时扩大第261条遗弃罪的适用范围,以避免要么适用故意杀人这一重罪,要么不科以任何处罚的两极化的解决方式。”*王莹:《论犯罪行为人的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载《法学家》2013年第2期,第128页。其实,只要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设定先行行为,即使不修改刑法,也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况且,在我国增设见危不救罪的时机并不成熟。
再如,有学者主张利用他人信用卡在机器上取款的行为成立信用卡诈骗罪。然而,这种观点显然难以说明行为人利用信用卡以外的磁卡从 ATM上取款的行为性质,难以解决行为人使用他人存折从机器上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于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这一缺陷不是自己的理论观点造成的,“而是立法不完善造成的……只有通过立法来弥补”*参见刘明祥:《再论用信用卡在 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性质》,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1期,第84页。。可是,只要承认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承认利用机器转移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属于盗窃行为,对上述行为均可以认定为盗窃罪,而不需要修改刑法。
又如,有学者认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存在一些问题,如职务的影响力被收买、若有若无地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便利是否与所收贿赂具有对价关系、他人代为支付的行贿款是否属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等等均存在疑问,建议将《刑法》第385条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不正当好处的,是受贿罪。”*参见李卫红:《受贿罪的司法认定》,载《法学杂志》2016年第4期,第19页以下。然而,《刑法》385条关于受贿罪存在很大的解释空间。例如,对“职务”作扩大解释,就可以认为包括职务行为以及与职务有密切关系的行为;*例如,在日本,成立受贿要求贿赂与职务具有关联性。日本的判例认为,其中的职务,不仅包括公务员本来的职务权限,而且包括与其职务权限具有密切关系的行为。“其中的第一种类型是,并非自己本来的职务,而是习惯上担当的职务,由自己本来的职务派生出来的职务;第二种类型是,利用基于自己的职务所产生的事实上的影响力”([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弘文堂2012年版,第494~495页。“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上所强调的是贿赂与职务的关联性,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收受了他人财物,就可以肯定行为人满足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职务便利是否与所收贿赂具有对价关系”,也并非难以判断的问题;所谓“他人代为支付的行贿款”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指使有求于己的他人支付本应由自己支付的费用,对此当然能认定为受贿罪。不仅如此,上述立法建议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按照上述建议,索取、约定贿赂的行为充其量只能成立受贿预备,这显然不合适。
概言之,即使是在刑事立法相当活跃的时代,解释者首先要思考的是,自己的解释是否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如果不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那么,是应当修改刑法还是修改理论?如果修改理论也能获得修改刑法的效果,是否还需要修改刑法?换言之,当解释者心中秉持着合理的结论时,就应当通过各种解释方法,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使现行刑法与合理的结论相吻合。
从刑事立法上看,我国近几年来以传统理论为根据进行的刑法修改,以及为了避免理论争议而进行的刑事立法,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根据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只有当二人以上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并且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时,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版,第164~166页。按照这种观点,倘若没有查明正犯是谁,就不可能知道正犯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否具有故意,以及帮助者与正犯是否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因而不可能认定实施帮助行为的人与正犯构成共同犯罪。有学者意识到了传统共同犯罪理论的问题,看到了传统共同犯罪理论难以解决网络共同犯罪的相关问题,便建议在《刑法》第25条增加一款:“网络空间下的共同犯罪,本法有特殊规定的,依照特殊规定处理。”*孙道萃:《应对网络共同犯罪还需完善立法》,载《检察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3版。《刑法修正案(九)》也是以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为根据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参见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505~506页;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第4版,第695~696页;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280页。其实,只要重新解释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只要以不法为重心、以正犯为中心、以因果性为核心,并且采取限制从属性说,就能妥当处理各种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参见张明楷:《共同犯罪的认定方法》,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3页以下。换言之,即使《刑法修正案(九)》不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完全能够妥当处理所有的帮助行为。*参见张明楷:《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2页以下。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倘若说原本就没有必要设立本罪,进而废除本罪,笔者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刑法修正案(九)》废除本罪,却是以传统理论为根据的,并且试图避免理论上的争论。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指出,之所以废除本罪,是考虑到以下几点:“一是,与强奸罪相比,嫖宿幼女罪最高刑只有十五年有期徒刑,难以严惩犯罪分子。二是,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不好区分,执法中对如何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也有困惑,一些案件难以把握,在幼女自愿、被告人又给付一些财物的情况下,到底如何定性,执法上认识不一,存在一定混乱。三是,规定嫖宿幼女罪等于认为幼女具有同意性行为的意思表示能力,不妥当。四是,嫖宿幼女罪是对幼女贴标签,将幼女认定为卖淫女,不利于幼女的成长。五是,嫖宿幼女罪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定位不准确,应当规定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六是,面对社会舆论呼声,取消嫖宿幼女罪,可以更好地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7~298页。然而,上述涉及刑法理论的几点理由,并不成立。
其一,认为对一切嫖宿幼女的行为均只能判处最高15年徒刑,显然是以“嫖宿幼女罪属于奸淫幼女的特别法条”这一观点为根据的。可是,这一观点并非不可修改。易言之,只要放弃这一理论,认为二者不是特别关系,而是想象竞合关系,进而对具有《刑法》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加重情节的嫖宿幼女行为,适用该款规定处罚,反而更能严惩犯罪分子。其二,上述第二个理由也是以二者属于特别关系为前提的,甚至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可是,如果承认二者是想象竞合关系,就基本上不需要区分,要区分起来也不困难(行为对象是不是卖淫的幼女)。其三,认为“规定嫖宿幼女罪等于认为幼女具有同意性行为的意思表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说法。既然嫖宿幼女构成犯罪,就意味着没有承认幼女具有同意能力;嫖宿其他卖淫女的不构成犯罪,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四,上述第四个理由更为牵强。这是因为,卖淫女的标签不可能贴在所有幼女身上;嫖宿幼女罪不会公开审判,新闻报道时也不得公开被害人的真实姓名。所以,即使对卖淫女而言,也不会公开贴标签。倘若认为嫖宿幼女罪是给幼女贴标签,那么,对其他未成年犯罪的怎么办?因为如果定罪量刑就给他们贴了罪犯的标签,就都不能称之为罪犯了。其五,上述第五个理由是可以成立的。可是,立法机关只是删除本罪,而没有将本罪移至第四章中。现行刑法只是由于本罪与卖淫嫖娼犯罪的关联性才放在第六章,如同聚众淫乱罪虽然是扰乱公共秩序的犯罪,但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也规定在同一条一样,后者也应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中。其六,立法机关需要了解社会呼声的产生原因与真实内容。倘若按想象竞合处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犯罪的关系,并通过判决的形式向社会说明,即使不删除嫖宿幼女罪,也可能很好地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
刑法的每一个条文都与其他条文有密切关系。不管是增加一个法条还是删除一个法条,都会使其他相关法条的含义发生变化,也可能使其他相关法条更难理解和适用。例如,既然嫖宿幼女罪废除后,对于嫖宿幼女的行为一概以奸淫幼女论处,那么,引诱幼女卖淫罪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为什么对引诱幼女卖淫的行为不以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间接正犯论处?对于引诱多名幼女卖淫或者引诱幼女长时间卖淫的行为,仅按《刑法》第360条处罚,是否与其他相关犯罪(如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罪)相协调?这些都是删除嫖宿幼女罪后带来的新问题。在刑法已经废除嫖宿幼女罪的情况下,刑法理论就需要研究这些新问题。
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大多比较简单,解释空间很大,或者说重新解释的可能性特别大。涉及刑法分则规定的许多定义,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刑法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恢复阶段,在定义概念时没有足够的案件事实,也未能借鉴国外的定义,故许多定义是经不起推敲的。30多年过去了,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刑法理论应当对许多概念做出重新定义,刑法学者没有必要对过去的定义依依不舍,更不应将过去的定义视为绝对真理。“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因为具体的知识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万物来说永远是不完善、不全面和局部的。”*[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解释学调动起充分的自我反思去同时反思自身的批判工作,也就是反思自身观点的局限性与相对性,正是在这个时候,解释学才获得实际的成果。”*严平选编:《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所以,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适用法律规范与创造性的解释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认为,没有创造性的法官只是在适用成文刑法的文字,而不是在适用真正的刑法。概言之,刑法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具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并不是指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而是必须并且善于从新的生活事实中发现刑法的真实含义。“在决定犯罪成立与否时,作为法律家必须具有一种超越条文的文理解释的见识,思考如何调整所预想的保护法益的对立。*犯罪的法律后果是刑罚,刑罚的适用在对法益起保护作用的同时,会给国民的各种活动产生影响(附随的萎缩效果)。这种法益之间的对立与协调,既是刑事立法要考虑的,也是刑法解释要考虑的——引者注。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日]佐久间修:《最先端法领域の刑事规制》,现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诚然,超越文理解释不是指超越罪刑法定原则。但可以肯定的是,刑法学是需要不断重新审视传统解释结论的反思性学问,也是不断地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的创造性学问。
三、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补正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刑法,也没有不变的理论;刑法与理论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如何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是立法机关与刑法学界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立法者不要奢望通过立法路径解决一切问题,解释者也不能将所有疑难问题都推向立法者;动辄要求修改刑法,不是解释者应有的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立法者也不能要求解释者解决一切问题,解释者也不能认为自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立法者像金字塔一样沉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换言之,立法者与解释者都应当明确各自的责任所在;立法者应当给解释留下空间,解释者应当在解释上下功夫。
刑事立法要使法条有解释的空间,就必须使规制犯罪的法条类型化。“对于立法者而言,类型是既存的,‘前者对于后者负有描述的任务’。如立法者尝试,尽可能精确地以概念来容纳典型的生活事实,司法裁判‘为适当解决生活事实,就必须再度突破这些概念’。然而,‘逆向的发展过程’随即开始,其结果是对概念重新作‘改良’的定义,而其不久之后又会显得过于狭隘。由是,在法秩序的实现过程中,我们所作的是‘一再地闭阖、开放及再次的闭阖法律概念’。‘我们不可能将类型无所遗漏地概念化’,因此,在寻找具体的法规范时,我们必须一再求助于法律所意指的类型,求助于类型赖以存在的模型的想法。”*[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16页。“立法以及法律发现的成功或失败,端赖能否正确地掌握类型。”*[德]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吴从周译,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5页。概言之,“立法者不能局限于对事实的观察”,而是要对相关信息资料进行“删除、塑造、修改,构建成他物”。*参见[德]雅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但是,我国的刑事立法在这方面还明显不够。
首先,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许多传统的犯罪一直没有被类型化,而是代之以根据具体个案的描述,于是形成了诸多具体法条。具体法条越多,处罚漏洞越大;法条描述的越具体,解释空间就越小,越难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例如,背信罪是一种传统的犯罪,各国刑法以及旧中国刑法均有规定,但是,我国现行刑法没有规定背信罪,而是找之以各种各样的具体法条。例如,我国《刑法》第166条规定的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第168条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第169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第169条之一的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185条之一的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和违法运用资金罪、第186条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第189条规定的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第223条第2 款规定的(招标人与投标人的)串通投标罪、第272条规定的挪用资金罪、第273条规定的挪用特定款物罪、第325条规定的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第327条规定的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第385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第404 条规定的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405条规定的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第407条规定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第410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等,在国外都属于背信罪的内容。在国外刑法中只需要一个法条规制的,我国刑法中却用了近20个法条。尽管如此,仍然有诸多应当作为背信罪处理的行为不能得到处理。例如,乙身处国外,委托甲以合理价值将房屋出租给他人。乙的房屋每年的租金为20万元,但甲出于损害乙的利益的动机,以10万元的年租金与丙签订协议,租期5年。甲的背信行为导致乙遭受了财产损失,但在我国刑法中却不可能构成犯罪。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刑法没有将背信行为类型化。
其次,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对于行为方式与行为对象的描述总是过于具体化,而没有使用相对抽象化的用语,因而导致解释空间过小,也不利于规制犯罪行为。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法条表述的构成要件是,“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指出:“本条规定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指的是穿着、佩戴的服饰、标志包含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符号、旗帜、文字、口号、标语、图形或者带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色彩,容易使人联想到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实践中比较普遍的是穿着模仿恐怖活动组织统一着装的衣物、穿着印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符号、旗帜等标志的衣物,佩戴恐怖活动组织标识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标志,留有象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特定发型等。”*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150页。可是,一方面,“留有象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特定发型”的行为,怎么可能属于“穿着”或者“佩戴”?再如,将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标志作为纹身图案的,也不可能属于“穿着”或者“佩戴”。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应当使用“穿着”、“佩戴”这样的用语来描述行为方式,而是可以直接表述为“强制他人在公共场合显示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即可。*事实上,《刑法》第120条之三规定了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的行为,属于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间接正犯(被强制者也可能成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共犯)。《刑法》第120条之五的规定不仅没有类型化,而且是多余的。
再如,《刑法》第177条之一第1款规定了妨害信用卡犯罪,第2款规定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但是,在当今时代,作为支付工具的不只是信用卡,即使对信用卡作扩大解释,也仍然不能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反之,日本刑法就没有使用信用卡的概念,而是使用了“支付用磁卡”这一概念,其中信用卡以及其他用于支付货款或者费用的磁卡(如各种充值卡、ETC卡等),以及用于提取存款的磁卡。*参见[日]山口厚:《刑法各论》,有斐阁2010年第2版,第488页。持有伪造的信用卡之外的支付用磁卡的行为,在我国不能受到刑法规制,但在日本却能追究刑事责任。
不难看出,缺乏类型化的法条表述,必然导致徒增法条。法条越多,解释起来就越困难,容易形成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恶性互动。
就刑法理论而言,面对刑事立法时,应当在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阐明法条的真实含义。在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良性互动方面,刑法理论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其一,利用各种解释方法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出合理结论的情况下,明确批判现行刑法,发挥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规制作用,促进刑事立法尽快完善。刑法理论在这一方面发挥的作用,大体上可以称为立法论。“所谓立法论,就是对立法者做工作,是为说服立法者而进行的活动。”*[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这是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的问题。其二,利用各种解释方法(包括变更以前的解释即修改理论)解释现行刑事立法,使刑事立法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工作不是支离破碎地进行的,而是作为整体而进行的,是被称为‘法解释学’的实践性工作,是意图控制法官的实践活动。法官意图通过适用法律来控制社会生活,法解释学通过说服法官,进而对法官的行动进行控制。法律学被称为‘控制的控制’,法解释学不是科学,而是技术,说的就是这种意思。”*[日]平野龙一:《刑法的基础》,黎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这是本文第二部分大体说明过的情形。其三,通过批判性解释,使刑事立法的形式缺陷得到弥补,也能为刑事立法将来的完善奠定基础。这种情形显然介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在此略作讨论。
解释本身就包含了批判,但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必须立即修改法条,而是通过补正解释等方法,得出合理结论。例如,日本学者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日本刑法》第109条第1项中的“或者”解释为“并且”即“而且”。*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纲要各论》,创文社1985改订版,第194页;[日](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47页;[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有斐阁1992改订增补版,第365页。这种解释本身就包含了对该法条用语不当的批判。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在1995年将该条的“或者”修改为“并且”。事实上,在刑法条文的表述存在缺陷的情况下,通过解释弥补其缺陷,是刑法解释学的重要内容或任务之一。换言之,将批判寓于解释之中,是刑法解释学的常态。将乱糟糟的刑法条文解释好,是解释者的责任。解释者的智慧,表现在既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又使解释结论实现正义理念,适合社会生活的需求。可以认为,刑法完善的路径为,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后,解释者根据正义理念与文字表述,并联系社会现实解释法律;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解释者不得不对法律用语做出与其字面含义不同的解释(对刑法的解释当然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立法机关会采纳解释者的意见,修改法律的文字表述,使用更能实现正义理念的文字表述;然后,解释者再根据正义理念与文字表述,联系社会现实解释法律;再重复上面的过程。这种过程循环往复,从而使成文法更加完善,使司法不断地追求和实现正义。
反之,如果在该进行批判性解释的时候不进行批判性解释,反而按照字面含义进行不合理的解释,只能导致刑事立法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导致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形成恶性互动关系。下面以强制猥亵、侮辱罪的立法与解释为例展开说明。
如所周知,我国1979年旧刑法没有规定强制猥亵罪,但第160条规定了流氓罪(其中包括侮辱妇女),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进行了分解,《刑法》第237条所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就是其中之一。问题是,第237条中的猥亵与侮辱是否存在区别?换言之,刑法理论在将猥亵与侮辱进行同一性解释,还是将二者解释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刑法理论一直认为,猥亵与侮辱具有不同含义。例如,有的教科书写道:“猥亵妇女,是指对妇女实施奸淫行为以外的,能够满足性欲和性刺激的有伤风化的淫秽行为,例如,搂抱、接吻、捏摸乳房、抠摸下身,等等。侮辱妇女,是指对妇女实施猥亵行为以外的、损害妇女人格、尊严的淫秽下流的、伤风败俗的行为,例如,在公共场所用淫秽下流语言调戏妇女;剪开妇女裙、裤,使其露丑;向妇女显露生殖器;强迫妇女为自己手淫;扒光妇女衣服示众,等等。猥亵行为必然是行为人的身体直接接触妇女的身体,通过对妇女身体的接触达到性心理的满足。而侮辱行为,则不一定以自己的身体接触妇女的身体,来满足精神上的性刺激,这是二者在形式上的一点区别。”*高铭暄主编:《新编中国刑法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2~703页。
但这一观点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刑法》第237条的侮辱妇女行为,也必须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方法实施的,而该观点将“在公共场所用淫秽下流语言调戏妇女”等不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包括在内,显然有违反罪刑法定则之嫌。第二,露阴行为完全属于公然猥亵行为,也不具有强制性。一方面,刑法并没有规定公然猥亵罪,另一方面,即使露阴行为属于犯罪,它也是标准的猥亵行为(但不属于强制猥亵行为),而不能认为它是猥亵行为以外的侮辱行为。外国刑法以及旧中国刑法规定的公然猥亵罪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第三,该观点认为侮辱行为“不一定”接触妇女的身体,这个留有余地的表述表明侮辱行为也可能接触妇女的身体,事实上,该观点已经将“强迫妇女为自己手淫”这种接触身体的行为认定为侮辱行为。既然如此,二者实际上从形式上也难以区分。第四,该观点强调侮辱行为“损害妇女人格、尊严”,希望由此区分猥亵与侮辱行为。事实上,强奸罪、强制猥亵罪都在侵犯他人性行为自主权的同时,侵害其人格与尊严,因此,这种区别也不可能存在。
《刑法》第237条虽然将猥亵与侮辱并列,但其第3款却只规定了猥亵儿童一种行为。如果认为必须区分猥亵行为与侮辱行为,必然造成以下两种结局之一:其一,猥亵儿童的是犯罪行为,但侮辱儿童的不是犯罪行为。例如,按照上述观点,“让儿童为自己手淫”的不属于猥亵儿童,只是侮辱儿童,因而不成立犯罪。但这种结论显然不合理,因为刑法对儿童的合法权益都是给予特殊保护的,就本罪而言,不仅在客观上不要求实施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而且应当从重处罚。既然侮辱妇女的行为是犯罪,那么,侮辱儿童的行为也必然是犯罪。其二,猥亵儿童的行为是猥亵儿童罪,侮辱儿童的行为成立第246条的侮辱罪(侵害名誉的犯罪)。这显然不妥当。因为儿童也有性行为自主权,而不是只有人格、名誉权,而且儿童的性行为自主权是一项重要法益,将侵犯儿童性行为自主权的侮辱行为均归入刑法第246条规定的侵犯人格、名誉的行为,必然造成刑法保护的不均衡现象。
正是因为刑法理论一直明确区分猥亵与侮辱,所以,《刑法修正案(九)》仅将本罪中的猥亵对象修改为“他人”,但没有删除侮辱妇女的规定,也没有将作为侮辱对象的“妇女”修改为“他人”。据此,有些属于侵害妇女性自主权的侮辱行为不能归入猥亵行为;有些属于侵害男性的性自主权的侮辱行为依然不能认定为强制猥亵罪。例如,根据前述区分二者的观点,“强迫男性为男性手淫”的,属于侮辱行为,但不构成犯罪。显然,从立法论上来说,这一修改存在明显的缺陷。立法机关工作人员指出:“妇女、儿童虽然是猥亵行为的主要受害群体,但实践中猥亵男性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猥亵十四周岁以上男性的行为如何适用刑法并不明确,对此,社会有关方面多次建议和呼吁,要求扩大猥亵罪适用范围,包括猥亵十四周岁以上男性的行为,以同等保护男性的人身权利。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将第一款罪状中的‘猥亵妇女’修改为‘猥亵’他人,使该条保护的对象由妇女扩大到了年满十四周岁男性。”“本款规定的‘侮辱妇女’,主要指对妇女实施猥亵行为以外的,损害妇女人格尊严的淫秽下流、伤风败俗的行为。例如,以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追逐、堵截妇女等手段侮辱妇女的行为。”*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6版,第389~390页。也有教科书指出:“所谓猥亵,是指除奸淫以外的能够满足性欲和性刺激的有伤风化、损害他人性心理、性观念,有碍其身心健康的性侵害行为。所谓侮辱妇女,是指实施具有挑衅性有损妇女人格或者损害其性观念、性心理的行为。如公开追逐或者堵截妇女、强行亲吻、搂抱妇女等。”*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版,第465页。但是,这样的说明不无疑问。其一,既然要平等保护男性的人身权利,为什么对针对男性实施的上述“侮辱”行为(如向男性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不处以相同的刑罚?其二,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的行为,没有侵害妇女的性行为自主权,不可能与强制猥亵相提并论,只能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的侮辱罪。倘若偷剪妇女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导致妇女身体裸露,当然属于强制猥亵。其三,如前所述,行为人显露生殖器时没有使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方法强迫妇女观看的,只是公然猥亵行为,根本不构成强制猥亵、侮辱罪。其四,“追逐、拦截”是《刑法》第293条明文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倘若将追逐、拦截妇女的行为认定为侮辱妇女,就意味着第293条的追逐、拦截对象仅限于男性,这显然不合适。更为重要的是,《刑法》第237条第2款规定“在公共场所当众”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根据上述观点,在公众场所当众追逐、拦截妇女的,就必须适用该法定刑,这显然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五,强行亲吻妇女或者强行搂抱妇女的行为,当然属于强制猥亵行为。总之,上述观点所归纳的“侮辱妇女”行为,要么属于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的行为,要么属于强制猥亵行为,要么不构成犯罪。事实上,上述观点是以旧刑法时代的司法解释为根据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4年11月2日《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侮辱妇女情节恶劣构成流氓罪的,例如:1.追逐、堵截妇女造成恶劣影响,或者结伙、持械追逐、堵截妇女的;2.在公共场所多次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向妇女身上泼洒腐蚀物,涂抹污物,或者在侮辱妇女时造成轻伤的;3.在公共场所故意向妇女显露生殖器或者用生殖器顶擦妇女身体,屡教不改的;4.用淫秽行为或暴力、胁迫的手段,侮辱、猥亵妇女多人,或人数虽少,后果严重的,以及在公共场所公开猥亵妇女引起公愤的。”但是,旧刑法流氓罪中的侮辱妇女是对公共秩序的犯罪,现行刑法的强制侮辱罪是对个人法益犯罪。原封不动地照搬旧刑法时代的司法解释,明显不当。
不难看出,不管是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之前还是之后,从形式上将猥亵与侮辱解释为两种不同的行为,并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传统观点导致《刑法修正案(九)》未能妥当地修改《刑法》第237条。
倘若在1997年《刑法》通过之后,刑法理论对《刑法》第237条进行批判性解释或者补正解释,主张侮辱与猥亵的内涵与外延相同,那么,《刑法修正案(九)》就完全可能将《刑法》第237条第1款修改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就不会出现本罪中的猥亵对象是他人,而侮辱对象仅限于妇女的奇怪现象,也不至于将公然猥亵行为、寻衅滋事行为认定为强制侮辱罪。
由此可见,刑法理论对刑事立法的补正解释,既具有立法论的作用,也具有解释论的作用。其中的立法论的作用,不同于典型的立法论(本文第一部分)对现行刑法条文的否定,而是在可以暂时维持现行条文的前提下,在将来适时修改刑法条文的表述。其中的解释论的作用,则与典型的解释论相同。
总之,刑法学的本体是刑法解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运用刑法理论检视、批判现行刑法条文。即使采取刑法教义学的概念,也不意味着刑法学将刑法条文当作绝对权威。 “刑法学的目的在于‘理解刑法’。所谓理解刑法,就是要理解人,理解法的本质与机能,理解文化,理解社会。如果以为了探究对实务起作用的法解释的理想状态为目的研究刑法的形式进行自我限定、自我制约,就意味着刑法学的难以救济的矮小化。刑法学作为跨学科的科学,在展开‘没有制约的思考’的同时,也必须探明‘与瞬间积累不同的[原理]、超越时代的[原理]’。只有这样,刑法学才能揭示出‘与时代的风潮相对立、相对抗的理论’。”*[日]井田良:《最近の刑法学の动向をめぐる一考察》,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9号,第228页。刑法教义学不能单纯具体描述刑法,而是要致力于刑法的理性发展;刑法教义学不仅要说明法条的真实含义,还要说明该含义的正当根据。例如,在讨论终身监禁时,我们只是从《刑法》第383条的规定中获得了形式的合理性,但仅此还不够,我们必须说明终身监禁的正当化根据何在。换言之,刑法教义学也必须判断刑法规定是否具有正当化根据。缺乏正当化根据的刑事立法,不应当受到刑法教义学的肯定。“如果一种法律解释……能够推动我们的法学论者和法学教师去引领法院和立法机构的工作,而不是跟随法院和立法机构的工作并满足于做一些条理化、系统化和协调化的分析,那么这种解释就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美]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1页。所以,刑法教义学对刑法的具体条文的体系性批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走向极端,使刑法学成为刑事立法学。凡是可以通过解释使刑法条文适应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主张修改刑法。此外,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解释与批判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批判性的解释事实上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吴岩]
Subject:Crirninal Theory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Authoramp;unit:Zhang Mingkai
(Law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In the era of the very active criminal legislation, not only ca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explain the criminal law, but als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itself.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can regulate the judiciary as well as legislatio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especially the legal interests protectionism and the justification doctrine of the punish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must make valuable judgments on criminal law provision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However, if the amendment of the theory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can deal with the social life, the criminal law should not be modified. Any knowledge is a prejudice, imperfect and not comprehensive.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is by no means the rigid and tedious knowledge of the form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 Criminal law scholars should be good at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social lives, have the courage to reflect on their previous understandings, and deal with their own prejudice correctly, so that the old law adapts to the new era. Criticism and interpretivism of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is not an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The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can make up for the formal defects of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should be skilled in typing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spac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the criminal theory.
criminal theory; criminal legislation; reasonable regulation; proper explanation; positive interaction
2017-09-10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刑法修正的理论模型与制度实践研究》(16ZDA060)的阶段性成果。
张明楷(1959-),男,湖北仙桃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
A
1009-8003(2017)06-00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