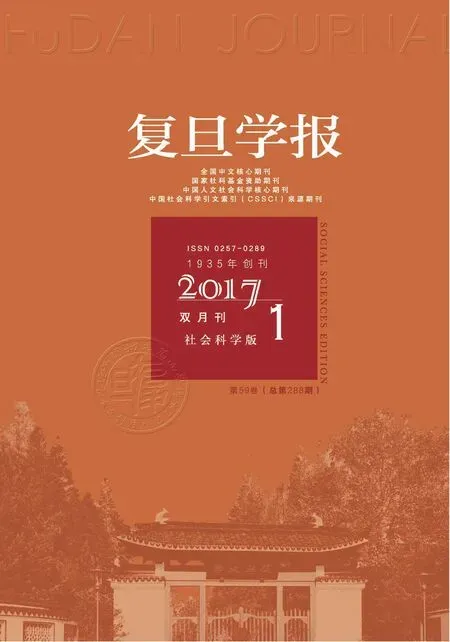诠释学与现象学的汇通之路:从“意识事实”到“此在的实际性”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ZHANG Qing-xi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西方哲学研究
诠释学与现象学的汇通之路:从“意识事实”到“此在的实际性”
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在二十世纪德国的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中,曾开展出以生命和生存为根基综合诠释学和现象学的路向。确实,“生命—生存”、“意义”和“体验”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所以这种综合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然而,由于生命哲学、存在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有着不同的渊源,所关心的问题和涉及的范围各不相同,所以它们之间的综合存在不同的方式或路向转换问题。诠释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它脱胎于古代圣经学、历史学、文学的研究,在近代才有哲学诠释学出现。不同的哲学基础塑造不同的哲学诠释学。其中,施莱尔马赫的建立在近代主体哲学基础上的诠释学和狄尔泰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诠释学在诠释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它把现象学方法视为一条通向严格科学的途径。狄尔泰为了寻找诠释的可靠基础尝试援用现象学的直观方法,但这导致先验的主体意识现象与历史中发生的生命—生存的现象之间的矛盾。狄尔泰可谓近现代第一个尝试把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而又发现其中困难的哲学家。虽说狄尔泰解决这一困难的方案还不能令人满意,但他为海德格尔的“实际性诠释学”(以此在为出发点的一种把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的途径)开了先河。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出发点,提出了“此在的实际性”并由此开辟了将现象学与诠释学相结合的新途径。
实际性 生命哲学 诠释学 现象学
在二十世纪德国的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中,开展出了以生命—生存为根基综合诠释学与现象学的路向。其中,狄尔泰在生命哲学构架内将诠释学与现象学综合和海德格尔在存在哲学构架内将两者综合意义特别重大,这两次综合是有关联的。可以说狄尔泰的以生命体验的“意识事实”为出发点的第一次综合为海德格尔的以“此在”为出发点的“实际性诠释学”的综合开了先河。
以生命—生存为根基综合现象学和诠释学的路向并非偶然,因为“生命—生存”、“意义”和“体验”之间确实存在内在关联。然而,生命哲学、存在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有着不同的源流和旨趣。诠释学主要关心的是对意义的理解和诠释,现象学主要关心的是认识的明证性基础和知识构成的奠基与被奠基关系;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虽然都强调生命—生存的源发性和意义,但前者主要关心生命的知情意的统一和生命的体验,后者主要关心此在的在世的生存方式。以生命—生存为根基综合诠释学与现象学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海德格尔要以“此在”为出发点的“实际性诠释学”来取代狄尔泰的以生命体验的“意识事实”为出发点的综合诠释学和现象学的方式?我们有必要做一番思想史的考察和问题意识的剖析。
一、 诠释学的渊源
在生命—生存哲学、现象学和诠释学三者中,诠释学是最古老的,所以我们从诠释学谈起。诠释学亦称“解释学”,指一门有关解释的学科。从词源上看,诠释学(hermeneutics)源于“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信使,他传达宙斯的旨意和为诸神传送信息。信使的工作如何成为诠释的工作呢?可以这样设想,当赫尔墨斯传递话语时,若遇到含意不甚清楚的地方,听者会问这是什么意思、这该作如何理解,赫尔墨斯不免要承担起解释的工作。把信使的工作推而广之,就意味一方传递到另一方的文本或古代流传到现代的文本,通过诠释得到理解,诠释学成了一门沟通作者和读者的促进文化交流的学问。
诠释学在西方有希腊和希伯来两个源头。希腊的神话、荷马的史诗、城邦的礼法、寺庙的神谕等都需要加以解释才能理解。尘世的人该怎样去理解希腊诸神的活动和话语呢?该怎样去理解诗歌所蕴含的意义和所激励的情志呢?为什么要执行或修正城邦的礼法呢?寺庙的神谕向人暗示了什么呢?古代学者早已在做诠释的工作。流传至今的希腊古典文献大多是原典和注疏的汇编,历代思想家的注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原文,而且还清理和发展了其中的思想。尽管这种注疏活动早已有之,但并不等于诠释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古希腊诞生。那时,对诠释的某些理论研究主要出现在诗学、修辞学和法学中。诗学要讨论字面意义与象征意义的关系,修辞学要讨论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力的问题,法学要讨论如何才能依据法律条文和结合案例做出令人信服的合情合理的审慎的判决。这都涉及对文本的意义解释。
诠释学在希伯来文化中主要起源于对圣经的解释。摩西五经是希伯来圣经中最主要的经典。摩西五经中记述了摩西律法的神的来源和神与人立约的过程,它们运用于希伯来人的生活中,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该怎样结合人世间现实的语境来理解和执行这些神的诫命和律法?对此,历代犹太的经师进行了解释,形成许多口传的文献。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面临罗马的法律和犹太的律法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犹太人不得不遵守罗马的法律,另一方面犹太人依然想保留和传承他们的文化传统,在他们自己的宗教和道德生活等领域内继续执行摩西律法。于是犹太的经师想到整理和汇编他们流传下来的释经文献,以便以这些文献为依据诠释摩西五经中的律法,在新情况下有所变通地执行经书中规定的律法。这些释经文献的汇编总称为塔木德(talmud)。在这里,虽然没有诠释学的专论,但包含大量对他们的法律条文、道德规范、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诠释文献,从这些诠释的实际工作中已经能大致看出到诠释的基本方法和准则。
诠释学到了近代才成为一门普遍性的学科。在古代和中世纪,诠释的工作分别与特殊的学科相关,如对诗的诠释、对圣经的诠释、对法律的诠释等。在所有这些分门别类的诠释中有没有普遍适用的诠释原则和技巧呢?能否建立起一门通用的诠释学呢?这也就要诠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按照狄尔泰的看法,沃尔夫学派的迈依尔(Meier,1718~1777)在其1757年发表的《普遍解释技术试探》迈出了这一步。他尝试制定出在对符号的任何解释中都可观察到的规则,但由于缺乏必备的哲学素养没能实现这一目标。真正奠定具有普遍意义的诠释学基础的人物则是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一种富有成效的诠释学只能产生于这样一个把语文学解释技巧与真正的哲学能力相结合的头脑中。施莱尔马赫就是具有这样一个头脑的人。”*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于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6页。
狄尔泰这里所说的哲学能力是指近代哲学的能力。近代哲学是主体性的哲学,这种哲学把人置于意义的中心。近代的主体性哲学不再把文字所描述的对象和神的旨意作为诠释的中心,而是把人的主体作为一切意义的枢纽。意义来自人的主体,是人的主体生产和再生产文本的意义。意义以人为中心,离开了人的主体就不能生成和理解意义。施莱尔马赫的贡献在于对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发挥。康德主张,在提出关于事物本质的问题之前,首先要考察我们的认识可能性的条件是什么。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认识能力、认识方式和认识有效性的范围弄清楚之后,才谈得上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施莱尔马赫接着康德追问有效诠释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在他看来,如果不深入到文本创作者的主体的心理活动中去,就不能真正理解文本的意义。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心理活动的涵盖面要比康德的认知活动的涵盖面更加广阔,它包括对情感、欲望、目的、动机的体认。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离开了这种内在的体认,单凭对外在对象的认知是不能阐明生活意义的。
施莱尔马赫主张诠释学必须包括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两个部分,但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语法解释类似于上述提到的字面解释,通过考察文本的语言用法解释文本的意义,这种方法只能解释文本的通常意义,不能解释作者的独创的意义。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独具魅力的创造性作品。要理解这样的作品意义,就要深入到作者的心境中去。但是,诠释者不是作者,如何才能进入到作者的心境中去呢?施莱尔马赫提出了模仿作者的体验和再造作者的体验的途径,即尽可能逼真地设想作者当时面临的情景、性格和思想方式,把自己移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中去,从而赢得共通感。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的关系如同翻译一篇外文文学作品时的两种境界:语法解释停留在分析外文的语法、寻找适当的本国语言表达法的层次上;心理解释则是译者进入到作者的内心中去,产生共鸣,达到得心应手地翻译的境界。
虽然施莱尔马赫强调心理解释,但并不反对语法解释。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两者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个作者在进行创作时,他是基于共同体的共同语言的。由于语法的结构和语词的基本意义具有较为稳定的延续性,作者的特殊发挥才会被当时和后来的读者所理解。由于诠释涉及这种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故诠释的过程不免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从对语言的一般意义的理解进入到对特定文本的特定意义的理解,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活动方式进入到特定作者的特定的处境和心态,然后再从这种特定的状况和特定的意义进入到普遍的形态和普遍的意义;反之亦然。施莱尔马赫甚至认为,借助诠释,能达到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作品的目的,这是因为作者在进行创造时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自己所使用的概念的思想史渊源和语言上的传承关系,以及他的作品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一个诠释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他就可能弥补作者在创作时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施莱尔马赫的这一灵感很可能来自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个见解:“我只是提请注意,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著作中,通过比较一位作者关于自己的对象所表达的思想,甚至比他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他,这根本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他并没有充分地规定自己的概念,从而有时所言所思有悖于他自己的意图。”*康德著,李秋零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二、 狄尔泰以“意识事实”为出发点综合生命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的尝试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思想经狄尔泰的介绍在二十世纪初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于狄尔泰本人对诠释学的贡献则表现为他把生命和对生命的体认作为诠释的根基的努力,以及他克服历史主义思潮所带来的相对主义的尝试。在二十世纪初,实证主义思潮泛滥。实证主义主张科学要以经验事实为依据。任何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得不到经验证实就不能称之为科学。在狄尔泰看来,语文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涉及经验事实,但主要关注的是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对于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不同于对自然现象间的规律的研究,有其独特的方法,这方法就是诠释学。他提出与“自然科学”相对峙的“精神科学”的概念。精神科学有其自主性,其要旨是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因此,对于语文学、历史学、法学等精神科学来说,实证主义的方法是不适用的,诠释学才是与其相适应的科学方法。
然而,狄尔泰在这里遇到一个问题:诠释学若想成为“精神科学”的“科学”方法,它当怎样克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如何才能让诠释不成为任意的诠释?它如何具有科学所要求的那种认识上可验证的准则呢?十九世纪初在德国流行历史主义思潮,兰克(L.V. Ranke)和德洛伊森(J.G. Droysen)是其代表人物。狄尔泰本人听过兰克等人的课。他一方面认识到历史主义有其合理性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了历史主义的问题。历史主义主张,一切属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东西都处于历史流变的过程之中,人是历史的主体,人创造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塑造自己的文化类型,每一时代都有其时代精神,每种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这听起来没有错,但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历史之流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精神文化没有普遍统一的评判标准。狄尔泰从历史主义那里找到了一种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式。生命具有历史性,历史性体现为生命意义的展开,精神科学就其主旨而论是对生命意义的阐释,因此精神科学确实不同于自然科学。但是历史主义还断言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相对的。这种相对主义能与科学相容吗?历史学、语文学、法学等人文学科还谈得上属于科学吗?“精神科学”这个名称能够成立吗?狄尔泰主张诠释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如果对意义的诠释只能是相对于每一时代、每一文化类型和每一主体的相对的诠释的话,那还有什么科学的普遍性和可检验标准可言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狄尔泰的生命意义的诠释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走到一起来了。科学为什么牢靠呢?因为科学以事实为基础,依据事实建立理论和依据事实检验理论。在狄尔泰看来,自然科学所说的事实是向外的感性经验所感知到的有关客观事物的事实,但外在事实不是事实的全部,还有内在事实,即“意识事实”。人的喜怒哀乐是人能够直接体验到的。人有美好生活的愿望,并能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什么是美好或苦难的生活滋味。这种生活体验虽然是内在的,但像自然科学中的外在事实一样具有确切的事实性,可以作为精神科学中诠释意义的判据。狄尔泰写道:“只有在内在经验中,在意识事实(Bewußtseinstatsache)中,我才能为我的思想找到牢固的抛锚地,并且我敢说,没有读者能在证明中离开这一点。一切科学都是经验的科学,但是一切经验都将追溯到产生它们的意识的条件,即我们的本性的整体中去,并在那里找到它们确确实实的有效性。”*Dilthey,Gesammelte Schriften,Bd.1,S.XVII.《狄尔泰全集》自1914年起出版,第1-12卷最初在Leipzig,随后在Stuttgart:B.G.Teubner 和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第13卷起由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迄今已经出版了26卷,以下简称Dilthey, GS。
胡塞尔主张现象学是严格的科学,它以“纯粹现象”为严格科学的“阿基米德点”。所谓“纯粹现象”就是向意识所直接显现的现象,即“直接给与”,它是直接的经验。按照胡塞尔的看法,我们能直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意识活动和意识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见与所见、听与所听、爱与所爱、思与所思,总是关联在一起,这就是意识的意向性结构。这些直接的给与是一切知识的阿基米德点,有了这样的基点,科学知识才有牢靠的基础。狄尔泰没有谈知识的“阿基米德点”,但是谈到思想的牢固的“抛锚地”。他认为胡塞尔所说的“纯粹现象”就是他所说的“意识事实”,有了这样的“抛锚地”,才能克服相对主义。狄尔泰在读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后发现,现象学对意识现象的描述和对意向结构的分析工作与他正在研究的“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有共鸣之处,有助于克服历史主义思潮所带来的相对主义的问题。为此,他于1905年邀请胡塞尔到柏林来讨论相关的问题。对此,胡塞尔留下这样的回忆:
当我亲耳听到狄尔泰本人的如下判断时吃惊不小:现象学,特别是《逻辑研究》第二册中有关现象学的描述分析的部分与他的《描述的和分类的心理学的观念》在本质上相谐和,并可视为作为一种理想展现出来的在方法论上完全成熟的心理学的最初根基。由于这一关联,狄尔泰始终非常重视我们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展开的研究,并且在他晚年又满腔热情地重新拾起他一度中断的有关精神科学理论的研究。这一结果就是他有关这一论题的最后和最精美的作品《历史世界的构造》。它(于1910)发表在《柏林科学院的论文汇编》上,可惜他在这一工作中与世长辞。我本人随着越来越进一步完善现象学的方法和取得对精神生活进行现象学分析的进展,也越益认识到,狄尔泰的这一当初使我很惊讶的有关现象学与描述—分类的心理学有着内在统一性的论断,在事实上是合理的。他的作品包含着现象学的天才预见和初步认识。这些作品决非过时了,即使在今天仍然能从中获得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具体启示,能激发在方法论上取得进展的和完全从另外的问题出发进行建构的现象学的工作。*Edmund Husserl,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5), Husserliana Band IX, Martinus Nijhoff, 1962, S. 34-35.
尽管狄尔泰和胡塞尔都认识到他们之间存在某些“内在统一性”的地方,但分歧依然是巨大的。胡塞尔认为,狄尔泰依然没有能够克服相对主义,因为狄尔泰所说的“意识事实”依然是经验心理学中的心理经验,依然是相对于经验的人所形成的思想习惯和偏好。为了克服经验心理学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必须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即必须去除一切预先假定和先入之见,把历史上所形成的一切观点存而不论,把带有前见的经验的心理现象还原到没有前见的纯粹的、直接给与的意识现象。胡塞尔主张,现象学的心理学不是经验的心理学,而是先验的心理学,即经过现象学还原之后的心理学,只有在现象学意义上的心理体验才是真正的“意识事实”,才是可靠的思想抛锚地。
狄尔泰并不完全接受胡塞尔的这种批评,他继续坚持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性和经验性。在狄尔泰看来,历史主义依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人总是生活在经验的世界之中,人割不断自己的历史,人在文化传统中形成自己的思想,任何理解都有前理解,因此要找到不带任何前见的纯粹现象是不可能的,绝对确定的基点是没有的。那么狄尔泰如何克服历史主义所导致的相对主义呢?在狄尔泰看来,尽管没有绝对确定的支撑点,但有相对确定的支撑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相对安全的抛锚地。意识事实不能提供绝对可靠的阿基米德点,但能提供理解生命意义的较为安全的通道。我能体验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由我的内省所提供的意识事实,并且我也立足于这样的意识事实通过移情作用理解别人的情感。但我的内省依然是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我对它的观察和描述依然是经验性和历史性的。
为此,狄尔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为我侄子的死感到悲痛。在此经验中,我仍然处于空间和时间中。现在,我通过内省把这种经验作为观察的对象。我可以把一门科学建立于其上吗?”*Dilthey, GS, Bd.6, S.317.狄尔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部分肯定和部分否定。肯定的方面是,我体验到我为我侄子的死而感到的悲痛。这样的体验是直接、亲历、逼真的。这是我据以理解和诠释生命意义的相对来说最可靠的支撑点,舍此我找不到更加安全的通道。否定的方面是,这不是绝对确定和可靠的支撑点和安全通道。狄尔泰从观察和语言两个方面考察这个问题。为观察本身是由我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的,我可以从亲友的角度进行观察,即我感到悲痛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亲戚;我可以从辈分的角度进行观察,即伤心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可以从普遍生命的角度进行观察,即我珍爱生命,我为失去一个生命而痛心。狄尔泰还认为用于描述心理体验的语词也是相对于各种各样的语言的用法的,它们是在很多方面受到语境限定的,是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的。
由此可见,不存在绝对牢固的阿基米德点和绝对可靠的安全通道。那么是不是又要回到历史主义思潮所持的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去呢?狄尔泰不想走回头路。他提出了既把体验作为出发点又结合生命结构关联的整体主义思路。精神科学的出发点是体验。体验总是处于生命的结构关联体之中。“价值和目的等历史范畴产生于体验。体验的主体,当其检查过去时,就已经在理解的过程中看到了意义,已经将关联体的范畴形式与自身联系在一起。”*Dilthey, GS, Bd.7, S.255.但在精神科学中把体验作为出发点与自然科学中基础主义的途径不同。自然科学把经验事实作为基础,通过逻辑与数学建立一层层的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这条路线不适用于人类的生命现象。意识事实是在心理结构脉络中的事实,而心理活动又发生于生活结构的关联中,理解生命的意义不是逻辑奠基与推导的过程,而是一种“诠释学的循环”。人类的心理结构关联和生活结构关联是相对稳定的,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处境中存在一些差异性,但它们之间有连贯性和谱系性,所以我们能够依托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理解他人的生命体验。狄尔泰在其晚期著作《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的结构》中还专门研究了世界观的谱系。人类的世界观尽管形形色色,但仍然有谱系可寻,仍然存在理解和沟通的可能性。个体、共同体和文化是历史生命的共同承载者。由于历史生命的贯通,通过“诠释学循环”迂回曲折地摸索前进,人类能够逐步增进理解,从而在照亮整体生命的意义中也增强自己独特视角中的观察。尽管一个人的内省式的自我知识的方法具有狭隘性,但是通过把他所体验到的意识事实与他自己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结构相关联,再通过他的行动和言谈与他人的生活相关联,一个人便能在这一迂回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狄尔泰总结道:“简言之,只有通过理解过程,生命的深渊才会被照亮。只有通过把我们所实际体验到的东西投注于我们自己生命和他人生命的每一表达之中,我们才能理解自己和他人。所以,体验、表达和理解之间的关系,反映着一种特殊的程序;只是由于它的存在,人类才作为精神科学的对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精神科学植根于生活、表达和理解的关系之中。”*Dilthey, GS, Bd.7, S.87.
三、 海德格尔以“此在的实际性” 为出发点综合存在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的尝试
有关海德格尔对存在哲学、诠释学和现象学的综合,我想最好从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1919~1923年)的思想说起。海德格尔在那时把现象学和诠释学结合在一起探讨存在论(本体论)的问题。海德格尔在1923年夏季学期开了一个名为“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的讲座,其中第二部分的标题为“实际性的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在这一讲座中,海德格尔简要地介绍存在论、诠释学和现象学的历史,提出他自己对这些论题的看法,主张诠释学和现象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论,现象学只有以此在为基础才能找到明证性的开端,诠释学只有立基于此在的在世的活动才能阐明存在的意义。这一讲座是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雏形。他指出,“存在论——实际性诠释学”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第一个笔记”。*转引自海德格尔著,何卫平译:《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附录:英文版译者后记,第119页。在这一讲座中,海德格尔的话语相比《存在与时间》较为平直易懂,向我们透露他的哲学——至少是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早期哲学——就是通过实际性的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来研究存在。
为了阐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实际性诠释学”,我们沿着海德格尔讲座的次序,先从“存在论”(本体论)说起。海德格尔主张“存在论”应该研究存在(Sein)本身,而传统的存在论研究的是存在者,因而走到歧途上去了。在这一讲座中,海德格尔非常明确地把这种传统的存在论与“现代的存在论”联系起来,并把它与“对象论”和“现象学”联系起来。海德格尔说道:
存在论这个词的现代用法等同于“对象论”(Gegenstandstheorie),而且首先是一种形式上的对象论;在这个方面,它与传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一致。然而,现代的存在论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以一种特别紧密的方式与狭义的现象学所理解的东西相关。正是在现象学中,一个恰当的研究观念才得以形成。自然存在论、文化存在论、各种实质存在论(materiale Ontologien),它们构成了这样一些学科:在这些学科中,这些区域的对象内容根据其所含事情的范畴性质展现出来,那么这样提供的东西可用作研究构成问题——研究意识与这种或那种对象之间的结构和发生关联的问题——的指导性线索。*M. Heidegger, 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 Gesamtausgabe Band 63, Frankfurt am Main, 1988.(以下简称Heidegger, GA,)S.2. 中译文参见海德格尔著,何卫平译:《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第2页。
当时听海德格尔讲座的学生显然知道,这段话是针对布伦达诺(F. Brentano,1838~1917)、梅农(A.Meinong, 1853~1920)、胡塞尔和狄尔泰的。布伦塔诺讨论了“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含义,指出其中一种重要含义指“对象”。布伦达诺的学生梅农发挥了他老师的观点,从语言和心理活动的角度考察存在。梅农主张,“存在者”(beings)是相关于语言所指的对象的,而对象是通过意识内容来呈现的。有些对象是不存在的,如“金山”,但它们仍然是语词所指的对象,仍然可以通过意识内容呈现。因此他提出“对象论”,并主张“对象论是超越存在与非存在的本体论”(Object Theory — Ontology beyond Being and Non-Being)。梅农的这种对象论,引发语词的所指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争论,导致罗素建立摹状词理论对此进行逻辑和语言分析。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也使用对象论这一概念,后来又改用本体论。胡塞尔在1913年发表的《纯粹现象学通论》(《大观念》第一卷)的第10节中加了一个注,指出在《逻辑研究》中:“我[胡塞尔]未贸然用那个在哲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本体论’(存在论)一词,而是将此研究(该书第一版第222页上前引部分)作为‘对象本身的先天理论’的一个部分,这个词组被梅农缩约为‘对象理论’。然而时代改变了,我认为现在相应地恢复旧的‘本体论’一词更为正确。”*Husserl, Husserliana Bd.III, 1, S. 28;中译文参见《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4页。
胡塞尔为什么在《逻辑研究》中要使用对象论的概念,后来在《大观念》中又要恢复旧的“本体论”一词呢?因为“本体论”这个概念容易引起争论,它的词源意义是“存在”,而逻辑的对象是否存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胡塞尔在《大观念》阶段已经明确采取先验唯心主义的现象学观点,主张通过现象学还原把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悬置起来后,研究各类存有者的本质规定性问题,主张一切存有者无非是先验自我的意识活动的相关项,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再顾忌“本体论”这个概念的歧义了。他有关本体论的观点与梅农相一致,本体论就是对象论,是超越存在和非存在问题的。
胡塞尔所说的本体论是对存有者进行分类的理论。它与传统的本体论的区别在于,传统的本体论直接按照存有者本身的规定性对存有者进行分类,胡塞尔则看到所谓存有者无非是意向活动的相关项,即意识的对象。意识总是有关某物的意识(Bewußtsein von etwas),这些某物就是意识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由意识活动构成的。当然,意识不是凭空构成某物,意识构成实在对象和非实在对象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这里存在着奠基与被奠基关系。现象学的本体论就是依据直接向意识所显现的东西研究意识如何构成对象,并依照对象的本质规定性进行分类,由此区分出各类实质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实质本体论也被称为区域本体论,它包含上述海德格尔所提到的“自然存在论”、“文化存在论”,形式本体论包括逻辑和数学等对象。狄尔泰区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其思路也是对象论,即自然的对象(如一块岩石)和文化的对象(如一本书)。
海德格尔认为,按照对象论来理解存在论,存在如下双重缺陷:
1. 它只关注对象的存在和对象的分类问题。如:有关各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对象存在和分类的问题;对象的存在问题又被理解为各种对象的对象性问题,这样有关存在本身的问题反倒不被放在存在论的探讨范围内。它按照对象的领域来理解世界,而不是通过此在和此在的可能性来理解世界。这样,作为世界的“自然”就失去了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意义,“身体”同样如此。
2. 它把本体论限制在狭隘范围内,阻碍人们去追问存在本身的问题,阻碍我们从此在(Dasein)出发研究哲学。它不知道存在不等于对象,不懂得存在本身只有摆脱了对象才得以彰显其源出的含义。它不懂得真正的存在论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从此在出发和为此在的。
由此,海德格尔提出了他自己的存在论,即从此在出发研究存在本身的存在论。这种存在论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存有者(在者)及其分类的本体论,也不同于现代的研究对象及其分类的本体论。在这里,我们感到一个语言上的问题。尽管 “本体论”和“存在论”用于翻译西方语言中的同一个词“ontology”,但用到海德格尔那里译为“存在论”很恰当,而在胡塞尔那里译为“存在论”会感到实在不妥帖,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本体论(研究意识的对象及其分类的学说)是把存在悬置起来的。与此相关,“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产生出与胡塞尔不同的意义。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现象”指意识现象;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的“现象”指存在本身的显现,存在的显现不是通过意识现象而是通过此在的“实际性”彰显出来。从此在的“实际性”出发解释存在的意义,就成为一条通达本体论的实际性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
为什么“实际性”(Faktizität)与现象学有关呢?因为现象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面向事情本身”(Zur Sache Selbst)。它的含义接近于中文成语“实事求是”。“面向事情本身”就是要尊重事实,以事实为依据。从认识论上说,任何间接认识都要以直接认识为依据;从论辩来讲,推理要立足于事实,这犹如法庭上的审判和申辩要以事实为证据。现象学是一门讲究明证性的学问,“面向事情本身”或“回到事情本身”的口号意味思辨的推论要回归或立基于事实性的证据。
什么是事实性呢?这在哲学上存在争论。英国经验论者只承认感性经验(观察事实)是可靠的科学研究的证据。胡塞尔扩大了“事实性”的范围。在他看来,我们自己的意识活动和意识活动指向意识对象的方式是自身显现的,而且只有首先弄清楚了我们的意识行为是如何在综合感性材料的过程中构成感性对象的,有关观察事实的感性经验的明证性才能被一步步揭示出来。如上所述,狄尔泰提出“意识事实”(Bewußtseinstatsache)这个概念,主张对生命的体验是一种“内在经验”,具有明证性,能为生命意义的解释找到一个抛锚地。他讲的事实性也是指意识现象。而海德格尔提出“实际性诠释学”(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他将事实性定格为“此在”。海德格尔意识到,他所讲的事实性与狄尔泰和胡塞尔的不同,所以专门用了一个拉丁语源的词“Faktizität”来表达事实性,以示与狄尔泰和胡塞尔所讲的事实性(Tatsächlichkeit)的区别。实际上,这两个词在普通用法中是相同的,只不过一个是日耳曼词源,另一个是拉丁词源。中译文为示区别,把“Faktizität”译为“实际性”。由此可见,围绕“事情本身”、“事实性”、“实际性”的问题,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各自的哲学思路在现象学主题上交汇在一起,但在理解什么是现象学的问题上依然有所区别。
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谈论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可谓先验意识的现象学,狄尔泰的现象学可谓生命哲学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可谓存在哲学的现象学,他们之间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事实性”或“实际性”的理解上。在海德格尔看来,胡塞尔和狄尔泰在考虑“事实性”的时候,是从对象性的思路出发的,事实是主体所直观到的对象。因此,他们从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出发。然而,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呢?在意识之内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只有澄清了此在的生存方式,才能澄清意识如何指向对象和构成对象的方式。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生存方式优先于意识活动的方式。从现象学追求的明证性角度来说,此在的生存方式的明证性是意识现象的明证性的基础。因此,海德格尔强调,“实际性是用来表示‘我们的’‘本己的’此在(Dasein)的存在特征”。*Heidegger, GA. Bd.63, S.7.这种存在特征是就存在方式而言的,它不是指被直观到的对象或被直观到的作为本质的规定性的对象,不是作为知识的对象,而是此在在其最本己的存在方式中的自身在场。对于此在的“实际性”,海德格尔不是从现存的、已有的特征方面加以刻画,而是从生成的角度加以刻画,强调它在存在方式上是“敞开的”,是“当下的可能性”,是自己的“实际的生活”,是对“可能的觉醒(Wachensein)之路的指示”*Heidegger, GA. Bd.63, S.7.
由于海德格尔把“实际性”理解为“本己的”(eigenen)或“本真的”(authentischen)此在的存在特征,就产生了他的“实际性的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在这里,现象学与诠释学的关系是打通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诠释学”应用来表达“进入、介入、走向、询问和说明实际性的连贯的方式”*Heidegger, GA. Bd.63, S.9.,那么诠释学也就应该成为显示此在的本己的或本真的的存在方式的一条道路。按照胡塞尔的看法,现象学的通达事情本身的道路是“现象学的还原”,通过“终止判断”清除一切不合理的先入之见,直面事物的自身给予,如实地描述现象。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观察者自身不本真,处在一种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中,把自己混同为“常人”,人云亦云,甚至见利忘义,党同伐异,何以清除偏见,如实地看待和描述事情本身?此在自身是否本真,取决于此在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因此,海德格尔认为诠释学的主要任务是诠释此在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特征,使得此在从非本真的生存方式回归本真的生存方式。海德格尔写道:“诠释学具有这样的任务:使每个本己的此在就其存在特征来理解这个此在本身,来传达这个方面的信息,来探究此在自身的异化(Selbstentfremdung)。在诠释学中,构建起一种此在自为地理解自己和成为自己的可能性。”*Heidegger, GA. Bd.63, S.15.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常常处于沉沦状态中,人在现实环境中常常失去此在的本己性,发生异化。由此,海德格尔提出“常人”的概念。常人就是沉沦的人,常人随大流,把自己当作物一般必然的东西,看不到自身存在的可能性。然而,本己的此在的实际性不是体现在既成性上,而是体现在可能性上,体现在自己的筹划和实现自己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选用拉丁词源的“生存”(Existenz)来表达这一思想。按照他的解说,“Ex”加“istenz”意味“站出来”,意味“从中绽放出来而实现自己”。由此,海德格尔建立了他的存在哲学的思想,后来掀起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就是从这一核心观点中发展出来的。
由于此在的事实性中包含沉沦的向面,此在的本真性往往被遮蔽,而且这种遮蔽由来已久,人们往往把掩盖当作事情本身了,诠释学就包含解蔽的工作。海德格尔写道:“为此有必要揭开遮蔽事情的历史,哲学问题的传统必须一直回溯到事情的源头,传统必须被拆解(abgebaut),只有这样,事情的本源状态才是可能的,这种回溯重新使得哲学处于紧要关头。”*Heidegger, GA. Bd.63, S.75.
现在,我们可以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作为实际性诠释学的现象学的区别总结如下: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求面向事情本身,要求研究者不带先入之见地、如其所是地、原原本本地观看和描述事情本身。但是海德格尔质疑:一个人如果昏睡了,何以看清事物?而且,人的这种昏睡属于人的生存状态中的一个向面,人沉沦已久,只有把人唤醒,使其回归此在的本真状态,才能使其看清事情本身。因此,海德格尔主张:“诠释学研究的主题乃是每一本己的此在,并且旨在通过诠释性地探问它的存在特征,使之从根本上觉醒。”*Heidegger, GA. Bd.63, S.16.在此,海德格尔把存在哲学与现象学和诠释学结合在一起。
四、 结语:意义和遗留问题
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曾经是穿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两场轰轰烈烈的哲学运动,如今它们都已经偃旗息鼓了。诠释学和现象学作为方法论,依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以生命、生存为根基综合诠释学和现象学的尝试有何意义呢?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1. 把诠释学与现象学结合起来确实有助于克服相对主义。诠释学遭遇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防止任意诠释。这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现象学的口号是面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就是一门寻求明证性的学问。狄尔泰的时代,精神科学陷入相对主义的危机。狄尔泰意识到,精神科学要成为一门自主的科学,除了要看清精神科学自身的特点和依照这种特点建立起自己的方法论外,还需要完善这种方法论。精神科学的特点是精神现象的历史性和对其意义的阐明。因此,精神科学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要建立适合于自己的诠释学的方法。但是若缺乏明证的依据,诠释就会成为任意的诠释而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为了使诠释学具有牢靠的认知基础,狄尔泰以生命体验的意识事实为抛锚点,把诠释学与现象学结合起来。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出发点开辟“实际性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其目的也是为了克服相对主义。海德格尔强调实际性,也就是强调面向事情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最具有实际性的就是此在本身,因为此在是一切存有者中唯一本己的存在,从此在出发才能依据实际性探明存在之真理。近来,有些诠释学家主张,由于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之间存在“间距作用”,“事实”或“实际性”无从把握,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认为误解具有正当性,诠释不需依据事实或实际性。然而,正因为间距作用的存在,正因为在理解中往往发生误解,所以要通过诠释寻求正解。如果只有误解,没有正解,人们何必要相信诠释呢?诠释学难道不就成了哄骗的技巧或作弄人的游戏吗?为增进读者对文本的理解,需要有根有据、“靠谱”的诠释,而不是胡编乱造的诠释。面对当今甚嚣尘上的相对主义风气,狄尔泰和海德格尔寻求把诠释学与现象学相结合,以使诠释具有令人信服的可靠基础,不仅不过时,而且更加值得回味和重新开发。
2. 当我们要诠释一个作品和一个事件的意义的时候,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价值规范和理论系统。这些价值规范和理论系统对于诠释或许有参考价值,但是一旦我们忘记了对这些价值规范和理论体系本身的审视,一旦我们盲目地依据这样或那样的价值规范和理论体系,我们的诠释势必五花八门、自相矛盾。要知道价值规范归根结底是人依据切身的经验制定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长青的,生命—生存是一切意义的活生生的源头。近来听到“人死了”之类的哲学口号,主张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上帝死了”意味不再有上帝那样的为人类制定价值规范的最高存在者了,“人死了”意味人不是制定价值规范的主体。在我看来,“人死了”的说法至多在修辞的意义上对批判近代主体哲学过分夸大意识的作用有某些意义,如果以此否定人的生存活动,否定人对生命—生存的体验是一切意义的活生生的来源,如果把“结构”、“权力”、“无意识的冲力”放在决定一切的位置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真的人死了,何来认识“结构”、“权力”、“无意识的冲力”?说“人死了”的人,自己是否死了?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反倒证明他必须活着。“无意识的冲力决定一切”本身就是一个有意识的判断。
3. 从狄尔泰的以“意识事实”为出发点的综合现象学与诠释学的路向到海德格尔的以“此在的实际性”为出发点的综合现象学与诠释学的路向标志着从意识哲学到存在哲学的过渡。虽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分享许多共同点,生命和生存本是关联的,但这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强调生命是知情意的统一体,依然偏重于生命的主体意识的一面,因而依然保留在“意识哲学”的窠臼内;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则强调生存活动对于生存体验的优先地位,因而从“意识哲学”转向“存在哲学”。就现象学而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是典型的意识哲学,因为这种现象学主张把有关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悬置之后考察纯粹的意识现象。狄尔泰提出“意识事实”的概念,也意味他认为意识现象是意义诠释的事实性基础。尽管狄尔泰已经认识到对生命体验的意识现象是与生存活动相关联的,但他没有断然地抛弃“意识事实”的概念。海德格尔把意义诠释的出发点移至此在的“实际性”,即此在的在世的生存活动,在此在的最基本的“操心”或“操劳”的活动中沟通意识和行为、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这意味他改造了胡塞尔的作为“意识哲学”的现象学,转向作为“存在哲学”的“实际性的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
海德格尔的这一转向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依然存在一些留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海德格尔对于此在的解释仍然不够具体。海德格尔把“忧”、“畏”、“操心”等作为此在在世活动的基本方式,意在表明它们是在从古至今所有的生活形态中都能发现的基本方式。我们姑且不争论是否如此,但它们过于“抽象”,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在历史中具体发生的生活形态的类型和它们具体演变的规律。在这方面,胡塞尔后期哲学对生活世界的论述要比海德格尔显得具体和更具有现实意义。胡塞尔对日常的生活世界、科学的世界和文化的世界的相互关系的论述开辟了一条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的道路,在当代受到哈贝马斯等社会理论家的重视。其次,此在如何能够通过诠释阐明真正的生存意义呢?或者,此在如何能够解除遮蔽明见存在的真理呢?海德格尔在开辟“实际性的诠释学的现象学道路”时已经注意到,此在的现存状况往往是“被抛的”、“堕落”(“沉沦”)的状况;要使得此在转为本己(本真)的此在,要依靠“存在”本身的照明,由此才能从沉沦中“觉醒”,才能去伪存真,明见生存的真正意义。但是这样一来,从此在出发的“基本存在论”就会倒转过来,变成从“存在”出发到“此在”了。由此产生新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呢?存在如何透露自身的意义和如何进行照明呢?无论是通过存在本然的自发事件(Ereignis)还是通过对存在的诗意的诠释,都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这里带来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从“人道”的角度还是从“天道”的角度看待存在?从“天道”的角度看待存在,导致一种神秘主义的神学,导致“最后的上帝”。当代的某些基督教的神学流派正是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灵感。我本人觉得这条路线贴近于晚年海德格尔的真实思想。从人道的角度看待存在,导致从人在世的实践活动的方式和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认识和诠释存在的意义。我本人倾向于后一条路向,由此能找到现象学、诠释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进行对话和沟通的地方。
ZHANG Qing-xiong
(College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责任编辑 晓 诚]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Hermeneutics and Phenomenology: From “Fact of Consciousness” to “Facticity of Dase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s German philosophy there were the tendencies of combining of hermeneutics and phenomenology on the basis of life and existence. Indeed, there was an intrinsic association in life, existence, experience and meaning, so this kind of integration had its inherent rationality. However, life philosophy, existential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and phenomenology had different origins, and their concerns covered various subjects, so there were different ways to combine them, and it was no wonder that shift of path direction for this combination would happen. Hermeneutics has a long development process. It was generated from the study of ancient Bibl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The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ame into being in modern times. There ar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ased on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s. Among them, the hermeneutics developed by Schleiermacher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rn subject philosophy and the hermeneutics developed by Dilthey on basis of the life philosophy were significant. Husserl was the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Husserl treated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s a path to rigorous science. In order to find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Dilthey attempted to invoke phenomenological intuitive method, but this led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henomenon as transcendent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phenomenon as living experience occurred in historical world. It may be said that Dilthey who made the first attempt to combine hermeneutics with phenomenology. Although Dilthey’s approach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still not satisfactory, his motivation brought about Heidegger’s new approach of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in which Dasein is treated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bination of hermeneutics and phenomenology.
facticity; life philosophy; hermeneutics; phenomenology
张庆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