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 行
王石平
A小时候最怕夜行。80后以降一向是无法理解我们的童年的,比如晚上,他们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那时的晚上太热闹了,暖和的日子,我们在院子里马路上跳绳踢毽子抽懒老婆打架,天冷了串门打扑克织毛活钩桌布拉呱。当然夏天也在路灯下打扑克,大人下棋,我们打扑克,大人也打扑克,我记得大人打“拱猪”,我们打“争上游”——名字的能量很正。
没有电视。现在想想没有电视挺好哒。只有极少的人一天到晚下了班就待在自己家里忙活,大部分人推了饭碗就出了门,以前叫串门,现在叫社交。
老百姓无论玩什么都是一窝蜂,今天如此,过去也一样。社交名人引领着一代人的时尚。
有一阵兴打鸡血,应是“文革”后期了,忽然我们家买了只大公鸡,鸡冠子红彤彤的,早上器宇轩昂地打鸣报时,一撒出去就追芦花鸡,往它们身上跳,叼住芦花鸡的头顶,一点一点地点头,尾毛一翘一翘的。我到结了婚才知道这件事的深意。
有一段时间,我妈在前面走,大哥抱着那只鸡去医院,在路上很快乐地跟人打招呼:“打鸡血去啊!”据说是把鸡身上的血抽出来打到人身上去。不知是啥大神的偏方,母亲神经衰弱,睡眠不好。后来我一直想这事儿从科学上是说不通的,你想,不同血型的人,输了血都会完蛋。又有人说是肌肉注射,打在腚上,那也能吸收么?
那只做了贡献的鸡需要好的照料,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奉献鸡”是要加宵夜的,夜里给它点了灯,喂窝头。夜间的照明打乱了鸡的生物钟,它开始不分时辰地乱打鸣,母亲就是吃两片安定药片也无法入睡了,那只鸡的命运就此结束了。我看大哥星期天捞不着抱着鸡去医院了,有点儿失落。
打鸡血之后是红茶菌。又不知什么大仙的方子,我们的晚上开始交流培养出来的红茶菌如何更好喝。太酸了,喝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后来我想想红茶菌对人应该有益,比鸡血靠谱。
再往后,四川人义务教全院的人腌泡菜,家家都托人从四川扛回来泡菜坛子。再往后是自己用大米做酒酿。
晚上总是交流各种时尚情报并传授生活经验的好时光,酒酿是有度数的,喝得我们晕乎乎的挺舒服。
一九七六年,从一月开始,学校就组织学生扎纸花,各种技法快速流传,最后形成了一条龙,有的染纸,把白色的皱纸染成五颜六色,染了之后是晒,然后做花。玫瑰是最简单的,裁成细条的纸用圆珠笔一搓,做成菊花,可以乱真。
整个七六年都是悲伤的,人们敬爱的人相继离世。老百姓可以做的就是献上各种漂亮的花,纸花的升级版是蜡花。
买来白蜡烛,用化学实验室的烧杯化了,加上美术课用的颜料,待蜡温热的时候用手压成小花瓣,再一片片粘起来,最后做梅花。红梅白梅腊梅,美轮美奂。
晚上从学校回家,要经过苹果园中的一条路,再过桥,那条路有点儿长,有个伴儿还好说,一个人走,路就更长了。路灯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总觉得后面有人,脚步声时远时近,回头看看啥也没有,但是影影绰绰的像是什么人跟着,心里吓得要死,抄近路直接过了大操场,再踩着石头过一条小河,这里已经没有路灯了,河水哗啦哗啦响,河的两岸是深深浅浅的草,会不会有什么伏在草里呢?心一慌踩空掉到河里,水很浅,只到脚踝,可是鞋里都是水了,压根儿顾不上倒。慌不择路地爬上河堤,前面有灯了,挺暗,一晃一晃的,是职工医院,靠着小河是太平间,各种从前听过的神鬼故事突然活了起来,前前后后地翻花样,越想越怕,终于撒丫子大跑,回到家,魂已经吓掉了一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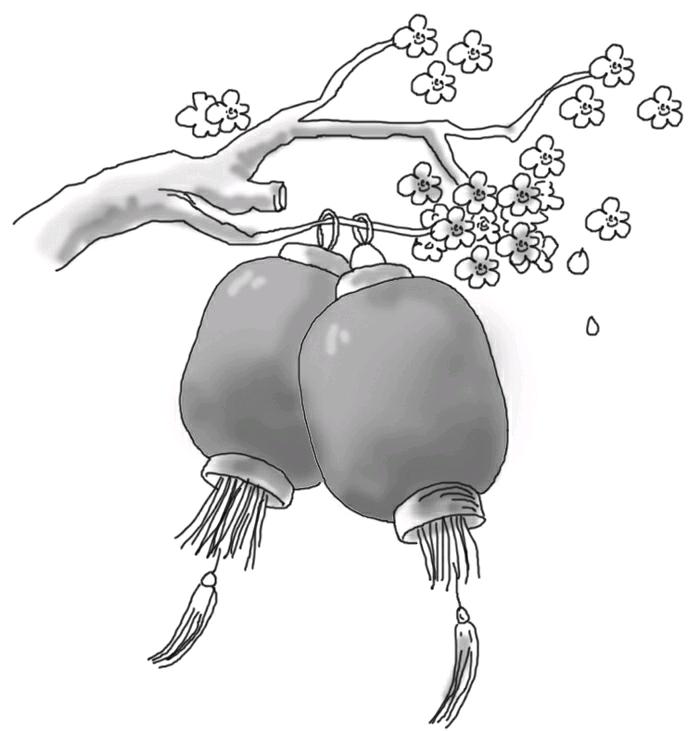
B所有的影视剧在说山里人走夜路时,都让他们打着个火把,其实不然。
我们大院的子弟学校也动员周围山上的孩子上学,有的家住得好远,冬天放学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从没见他们拿着手电揣着火把,回到家里应八九点了。一个女生也就背着个粗布做的书包回家了。
山里的天气阴晴不定,有时候下雪了,我回到家里吃过晚饭,快速地刷碗,一心惦记着到晓荣或亚莉家打扑克牌,间或也会想起来走夜路的女同学黄彩霞,她到家了么?还能看得清路么?
我们的寒假要到山上砍柴。三五个女生做个伴儿,往大山的深处走,有一种树结下绿豆那么大的红色果子,上面有斑点,树枝上长成一片,树叶已经落尽了,站在不高的树下,用手扳了树枝来吃,酸、甜、汁多,好吃得不要不要的。我们一边吃一边傻乐,太好吃啦!当地人叫它“简子”。把嘴巴都吃红了。
冬天的天特别短,山里尤其短。你看着太阳还架在山上一竿子高呢,忽然就掉到山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就乌漆麻黑了。
但是月亮從东山上爬出来了,如果是好天,月光照得山路雪一样白,清清楚楚的山脉,松林、竹子、溪水泛着月光,连课本上的字都可以看清。走累了坐在路边,不说话的时候,心是静的,清亮亮的,像水洗过一样,无垢无尘。那时候我们都相信精灵是存在的,它们会在山上的树尖上跳舞。
所以,黄彩霞没有火把也可以轻轻松松地走回家。
落了雪的山上,让月亮一照,更是明亮如昼了。人也跟着兴奋了起来,大声地说话,“今年寒假的返校日可以不去了,哈哈哈哈!”“最刻薄的老师回老家生小孩了,哈哈哈哈!”满月真的会影响到女孩子的心情,我们也大声地说各自的“大姨妈”,反正没人听得到。
快乐是洋溢了群山的。
但是黑月的那几天就不妙了。阴历的月末,山趴在那里,完全是深黑色的,夜鸟的叫声凄厉,就是在白天我们也不敢去的山坳,经过的时候一定偏着头,不敢往那边看,加快脚步拼命走啊。
一身大汗往家里狂奔,终于可以看到大院的灯光了,山脚下几个大人在吸烟,烟头一明一灭,发现了我们便吆喝:“是亚莉吗?”“是冬梅么?”我们忙不迭地回应。
大人们不放心,来接我们了。
C大学寒暑假回家,回山里,只有一趟火车可以一直坐到西安或宝鸡,在那里再倒一次车。那趟车经过济南是凌晨四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夜里没有公汽,不记得有出租车。
拼人品的时候到了。
每次都是系里的男生骑自行车送站。
夜里两点闹钟响了,从热乎乎的被窝爬出来,把胳膊伸到寒冷的夜里抓衣服,好冷,那时山大宿舍还没暖气,能看到自己吐出的气冒着白烟。悄悄地起床,简单洗洗脸,背着行李下楼。
男生哈着手跺着脚取暖,见我下来,打个招呼就出发。都是交往一般的同学,高年级的连名字都说不出,把行李交给一个男生,跳到另一个车的后座上,毫不犹豫地抓住他的棉大衣。
两辆自行车前前后后地一路奔火车站骑。
一路上都有步行去车站的学生,有的从北门出,去黄台,有的从南门出,去天桥火车站。都是一身笨重的棉衣,扛着行李,大声交谈着,也有的男生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撒欢儿一样的快乐,票是放假前半个月就在系里订好的。
冬天,夜里的空气有砸破松枝的清香,从保温瓶厂下中班的工人,说着粗话,从我们身边掠过。
长大以后无数次梦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家的夜晚,风神鼓足了劲儿,把清冽的风吹到脸上,双脚已经麻了,从脚尖开始往上,渐渐地失去知觉,到了解放桥,骑在边上的男生喊换一换吧!从车上跳下来,哎呦!脚丫子钻心地疼了一下,缓过来,再跳上另一辆车。接力一样的路程,路灯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哈气,但是看不清他们的五官。
想不起来了。四十年前的从前。
不曾记住他们的名字,也不曾记住他们的脸。
车站里乌泱乌泱的人。奋力地在各种大包之间往前挤,终于进了站,火车已经来了,每一个打开的门都像是生死的考验,车上的人要挤下来,站台的人要冲上去。丢了的行李,挤歪的脸。
送站的男生抓着我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看,里面是各种姿势昏睡的人,期望找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敲打窗子,冲里面喊麻烦开一下送点东西。里面把窗户提起来,一个男生马上奋力托住窗户,我抓住窗框玩命地往火车里爬,里面如果人太多了,就有人拼命地往外推我,推头,用拳头砸我抓着窗框的手,不能松手啊,费多大劲儿买上的票,不可能改签呀,我要回家呀!
仿佛这是人生的最后一列车,上不去就再也回不了家。回回我都能进车厢。
还没等回过头说声谢谢,火车一声长鸣离开了济南站。
D夜行火车是成年后最深刻的记忆。
永远的哐当哐当声。
寂静的夜因了这么单调而空旷的声音而更静。
窗外是黑色的原野,窗户上映出的是东倒西歪的人,各种睡相,自己肿胀失神的眼。要把脸紧贴到玻璃上,才能看到烟一样的黑色。偶尔与另一辆夜车相会,快速闪过的光,人的轮廓,唰的一下,像星际航行的飞船相见。
有时渐渐地睡着了,哪里会有座位呢,站着就睡着了,能靠着座椅就是幸运。遇到好人,看快站不住了,简直站不住了,会悄声招呼:“姑娘,来,坐会儿吧。”说话的使劲儿挤出巴掌大的地儿,“来坐过来吧,我闺女跟你这么大。”怀着感激地坐下,心里喊着:“您女儿一定要长命百岁啊!”
工作以后出远门,可以坐卧铺了。有时夜里突然醒来,是靠站了。在郑州、徐州、西安这样的大站,可以停上好长时间。
四面八方都是此起彼伏的鼾声。
胳膊上戴着“乘警”臂章的人,东张西望,警觉地穿过车厢,看了让人心安。
偶尔有上下车的人。
厕所的味道在任何一个季节毫无障碍地漂浮在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车站的喇叭响了,拖着疲惫长音的男人或女人开始报站名:“郑州站到了——郑州站到了——”声音与白天完全不同。真奇怪为什么会完全不同,完全是梦话的感觉阿。
最奇怪的是,喇叭也会说出乘客完全听不懂的话,好像是编码,是夜的密码,与夜神的交易。
有人喜欢在卧铺车厢吃东西,有瓜子有苹果也有麻花,会发出咔咔的声响,吃得津津有味,总会令人想到小兽,大的田鼠,双手抱着食物,不停地吃,吐皮。
治安特别乱的那几年,会看到有人用手挨个摸行李架上的各种箱子和包。他的手停留的时间有时候长点,有时候短点,是贼没错了,我的心猛地狂跳起来,震得枕头都一跳一跳的。
就这么吓着也还是睡过去了。早上听到有人大叫:“我的钱呢?我的钱让贼偷啦!”气急败坏的叫声。压根儿不敢看那个大叫的人,因为夜里没有阻止了贼,就像自己也成了一个贼。
E刚结婚那几年春节回家,那时候父母已经迁回河北,只有一趟直达车,半夜到站。
下午坐上车看了一会儿什么杂志睡着了,在一个双人座位,我靠窗,旁边是一位大姐。
夜里突然一个东西砸到我身上,睁眼一看是那位大姐发了癫痫,挺到我身上一抽一抽地口吐白沫,她的眼神把我吓翻了,我尖叫一声就到了后面的座位上,把睡着的两个孩子砸醒了哇哇大哭,我也在哭,吓得。
有经验的人冲上去,掐了发病大姐的人中,看她慢慢静了下来,哭着的孩子也止住了,不停地跟对面的妈妈说:“这个姨(指着我)咚的一声从天上掉了下来,砸中了俺。”
坐在我对面的一个老人指着我说:“俺看你嗖的一声从这个座位飞到那边那个座位去啦。”
这是最奇特的夜行经历。
原来我飞过一次。
这世界有一半的昼,就有一半的夜。无非是白天长一点,或夜长一点儿。
有时候夜里,我会在我住的后山上散步,夏天九点钟以后,山上起了凉风,一个人慢慢走着,很惬意。山的后面是一大片墓园。
有一回下了雨,雾又深,有点犹豫还走不走呢,可架不住空气是甜的,非常地好,就走到雾里去了。夜里散步的人少,雨天就更少了。只见到一个小老太太,我上山的时候她下来,等我回来的时候又见到她。
她招了招手,我看了没有别人肯定是叫我,就过去了。
老太太凑过身子说:“你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什么啦?”
老太太欲言又止,指指我身后。
我回头看看,只有雾,浓的雾。
老太太又说:“以前就听人说过——”说到这里又止住了。定定地看着我。
我没工夫和她打哑谜,就走了。老太太更快地走了。
F有了微信,四十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又联系上了,各叙别情,我们山里那个所整体迁了。相约着再回山里去吃简子,去看看当地老乡的孩子,如今都是老太太了。他们告诉我黄彩霞已经没了。我没反应过来,又说四十多岁就没了,嫁给了一个村里的男人,那男人打她,早早就病了,就没了。
我总觉得和我们一起上学的山里的孩子,他们的生命少了一支火把,一盏灯。小时候和他们谈到未来,黄彩霞只是笑而不语。
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未来呀?”
她还是笑:“像我們这样的人,还能怎么样。”
我喜欢她的笑,灿烂,有砸破松枝的清香。她人长得也好看,个子又高又苗条,眼睛大大的。我总是有点担心她走夜路会出事。
她的人生有点像夜行人,少了一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