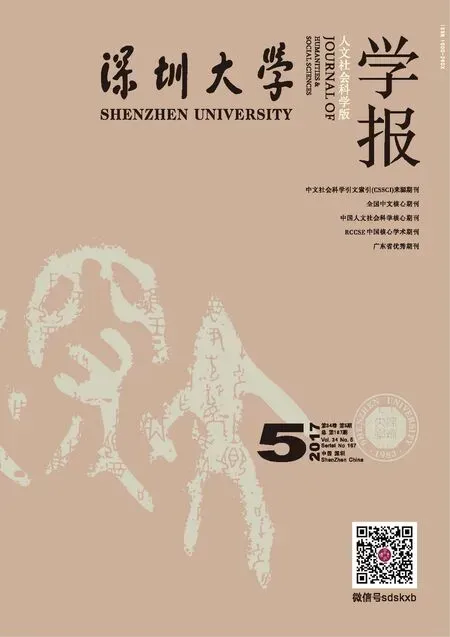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史学渊源与价值指向
何悦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生成的史学渊源与价值指向
何悦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史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观念之一,其生成主要源于史学家对小说“史补”功能的界定。此界定主要发生于唐代,此后,便成为小说创作与批评自觉意识。在“史补”中,出现了三种向度的不同发展:一是对“史”之功能进行攀附,把小说看成如“史”一般具有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的功能。二是从“史”之教化功能不足处入手,认为小说可以辅“史”以演“义”,同时还可作为通“史”之阶、纠“史”错之具、补“史”之遗而存在。三是认为小说可以补“史”审美娱乐功能之不足,使人们在正史阅读之外,获得别样的审美享受。前种“史补”观贯穿唐后小说始终,尤其在文言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后二种“史补”观则主要流行于宋元以后,尤其在白话小说中获得长足发展。三种“史补”观念交融递变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个性不断成熟的过程,是其存在价值与艺术品位不断提升的过程。
中国古代小说;“史补”观念;史学渊源;价值指向
“史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观念之一,不论其理论生成,还是其价值指向,都与中国古代史学存有紧密的渊源联系。对此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的亲缘关系,且能看出中国经史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统摄能力,同时还有助于对古代小说思想内涵与审美特征作出恰切理解。尽管目前学界不乏对古代小说“史补”观念进行研讨的文章,但对其“发生学”的“史学”渊源与价值追求分析尚未充分全面展开。基于此,本论文拟以古代小说创作与批评实践为据,对此论题给予全面深入分析。不足之处,祈请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一、“史补”功能的界定,史学期待的回应
在中国,对小说给予“史补”功能的界定,经历了发展的过程。
“小说”一词最初见于《庄子·杂篇·外物》,其中所谓的“小说”,与“大达”对举,指不关乎真正道术的琐屑言谈与浅薄道理[1],与后来所谓的文体概念并不等同。但尽管如此,“小说”一词所包含的琐屑、浅薄内涵却为后来命名“小说”为文体概念所借鉴,并由此形成中国后世对小说文体的基本看法。
对小说文体最初发表论断的是东汉桓谭。《新论》中,桓谭指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卷三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李都尉陵从军注)[2]可见,在桓谭心目中,小说文体是以琐碎、驳杂、虚妄为特征,它与“圣人文语”明道治国平天下功用不可同日而语①,只是于个人“治身理家”方面有“可观之辞”而已。
桓谭之后,对小说文体给予发论的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班固认为小说“盖出于稗官”,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刍荛狂夫之议”,它尽管“弗灭”,也有“一言可采”之处,但与“诸子十家”中其他九家相比,作用要小得多。基于此,班固将“小说”系之于“十家”之末,并将其排除于“可观者”之外[3]。
桓谭、班固的认识,代表了东汉前正统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对于小说文体的基本认知。在此时认知中,虽然普遍看到了小说虚妄、琐碎、驳杂、浅薄等内容与形式特征,也认为小说于“治身理家”方面有“可观”之处,但总的来说,对小说的价值判断主要以“圣人文语”为参照得出,小说属于“子”的范畴,与史传之间并未建立起明确的渊源联系,更不用说对其给予“史补”功能的界定。
对小说给予“史补”功能的界定,主要发生于唐代。唐时,史学高度发达,史籍重要性不仅得到官方认可,并获得积极支持。此时,顺应小说实践中长期对史家所遗、所弃之事拾取记载的现实,始有了对小说史传渊源、史补功能的明确界定,而且此界定主要由史学家来完成。《隋书·经籍志》中,编著者认为杂传类作品“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杂史类作品“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迂怪妄诞,真虚莫测”,它们存在之所以有价值,一是可以备正史“遗亡”,二是可以为“通人君子”“博采广览”提供资料[4]。这里,编著者虽然未以“小说”言之,但所谓的杂传、杂史类作品最易和小说相混淆,而且其中所引作品,后世也常以小说看之,所以不妨看作是对小说地位与功能的阐释。《史通·杂述》中,刘知几将偏纪小说视为“史氏流别”之一,认为其虽能“自成一家”,可“与正史参行”,但由于所表现的“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内容与形式特征,实难以和“五传”、“三史”相提并论,其存在价值是可以为学者“博闻旧事,多识其物”提供别录、异闻。《史通·采撰》中,刘知几指出“史文有阙,其来尚矣”,“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小说存在还可以为史书编撰提供阙失资料[5](P194-196,84)。
以两人所论为据,可看出,唐人对小说的认知,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突破。在此时认知中,虽然也如以往看到了小说“言皆琐碎,事必丛残”、“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等内容与形式特征,但却使小说与史传之间建立起明确的渊源联系,把小说看成是“史官之末事”、“史氏流别”之一。更重要的是,在此时认知中,确立了小说与史传“卑”与“尊”的等级关系,把小说存在价值确定为可为正史编纂提供阙失资料、能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有助于人们博闻强见等。至此,小说始有了明确的“史补”的功能。
小说与史传同属叙事文学。在中国,史学地位极为尊隆,其重要性仅次于“经”之下。另一般来讲,史学家不仅眼界高,论断也客观公允。如此之故,以史学家为主体形成的对小说文体“史补”功能的界定,便逐步成为中国正统文化,或者说是大传统文化对小说文体的基本认知。在此认知笼罩下,无论是小说作家,还是小说评论家,均始终难以摆脱面对史传的卑微心理,因而不论是对小说作品题材内容的选择、功能的论定,还是对于小说作品评价标准的选取,都出现了向史家所期望的“史补”角度的有意靠拢。
这一靠拢,立足于整个小说发展的实际变迁来讲,体现得较为清楚。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以志怪、博物为主。此时小说的“史补”,主要体现为创作实践上对史家所遗、所弃之事的拾取记载。如《洞冥记》传为汉郭宪编撰,在《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中,郭宪强调“古囊馀事,不可得而弃”,其《洞冥记》是“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结撰而成[6](P123)。 《西京杂记》为晋葛洪编撰,在书跋中,葛洪交代:昔刘歆欲编《汉书》,积累了大量资料,但书未行结构其人却亡,其所收集资料遂以零散、杂乱状态存在;后班固编撰《汉书》,书中大量资料,即取自于刘歆所记,但同时也对部分材料给予了删削;考虑到刘歆所记“世人希有,纵复有者,多不备足”,其《西京杂记》“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钞出为二卷”而成[7]。葛洪此话真实性暂不可论[8],但其书拾史之遗、取史之弃的题材特征却十分明显。上述作品而外,他如王嘉《拾遗记》、吴均《续齐谐记》、刘义庆《幽明录》、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等,也都呈现出大致相同的特征。这说明,拾史之遗、取史之弃的题材特征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中具有普遍意义。
但尽管如此,它们与后世有意而为的“史补”并不相同。《山海经序》中,郭璞力证自己所记真实不虚,说《山海经》“于戏!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9](P6)《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序》中,郭宪称赞东方朔“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说自己《洞冥记》“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 ”[6](P123)《搜神记自序》中,干宝一方面称叹其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一方面自谦“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本,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9](P50)在诸如此类自陈中,均明确把所编撰之书定性为“一家”之言、“微说”,并同时说明书的功能是“明神道之不诬”、游心寓目、博闻强见。其中虽有如后世“史补”观下对于作品“博闻强见”功能的强调,但却不是以史传补足为目的。所以总体来说,此时小说的“史补”,主要体现为创作实践上对史家所遗、所弃之事的拾取记载,这一记载尽管呈现出补“史”之“阙”的题材特征,但却是以人们博闻强见、好奇猎异审美需求的满足与“明神道之不诬”的宗教目的为主,与后世有意而为的“史补”并不相同。除此而外,理论上的表述也显得较为稀少。这说明,“史补”作为一种创作意识,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这种状态,到唐后的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始有了明确变化。《唐国史补》为唐李肇编撰,书以“史补”为名,是出于“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编撰中,作者以史传观念为标准,“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10]《夷坚志补》卷一《芜湖孝女》,叙述芜湖孝女舍身从贼救父兄,后投水全名节故事。故事叙述末尾,作者感喟:“今世士大夫,口诵圣贤之言,委身从贼,徼幸以偷生者,不可胜数,曾一女子之不若,故备录之,异日用补国史也。”[11]《山居新语》为元杨瑀编撰,书以当时民间传闻、朝廷典故与嘉言懿行记载为主,同时兼及鬼神怪异之事。书成后,杨瑀交代成书经过与创作动机云:“予归老山中,习阅旧书,或友朋清谈,举凡事有古今相符者,上至天音之密勿,次及名臣之事迹,与夫师友之言行,阴阳之变异,凡有益于世道,资于谈柄者,不论目之所击,耳之所闻,悉皆引据而书之。……其不敢饰于文者,将欲使后之览者便于通晓,亦且为他日有补信史云。”[12]《混唐后传》为明人锺惺编次,书凡八卷三十二回,主要以隋、唐历史作为演绎对象。书序中,锺惺交代:“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账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账簿,又当有杂记之小账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然则斯集也,殊亦古今大账簿之外,小账簿之中所不可少之一帙欤!”[9](P965-966)清人小说中,钮琇自称其《觚剩》“姑存此日琐言,岂曰珠能记事,倘附他年野史,亦云稗以备官焉尔。”钱徵评价钱学纶《语新》“虽未足据为掌故,然亦见有足补志乘之未及者。 ”[9](P158,477)在上述唐、宋、元、明、清诸小说作品序跋中,无论是作家自陈,还是他人说明,也不论是对于作品可存故实、能为正史编纂提供资料、可有助于博闻强见等价值功能的论述,还是对于创作过程中征实尚信选材标准的交代、“文”之润饰特征的有意限制等,都体现出明确的自觉而为的“史补”目的。
事实上,这一目的表达并不局限于上述作品,在唐及以后的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其表达的频率尽管会有历时、文体的差别,但存在之久远、涉猎文体之广泛却是不争事实[13]。这一事实于史家对小说史传渊源、史补功能论定之后大量出现,充分说明史家对小说“史补”功能的界定,诚对小说创作与批评中“史补”目的的强化具有规引之功。后世小说创作与批评中对小说作品可存故实、能为正史编纂提供资料、可有助于博闻强见等价值功能的论述,正体现出对史家关于小说“史补”功能期待的自觉迎合。
二、“史”之地位的尊仰,“史”之功能的攀附
在中国,“史”具有崇高地位。《史通·史官建置第一》中,刘知几称“史之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5](P215)给《资治通鉴》作注时,元人胡三省指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14]诸如此类评判,皆代表中国正统文化对于“史”之地位与功能的认知。
在此认知笼罩下,中国历代政府不仅将史官建置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史籍编撰人员以“馆宇华丽,酒馔丰厚”的待遇。在此待遇下,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能承职于史馆,是一件极为值得荣耀的事情,不仅“趋竟之士,尤喜居于史职”(《史通·史官建置第一》),就是才、学、识兼备而有志于史书编撰的历史学家,也同样以其为荣。对此,我们通过刘知几的一段表述可充分看出。公元702年,刘知几出任著作郎、左史等职,从事国史与起居注编纂。后来,刘知几转为中书舍人,暂停史职。及“今上即位”,刘知几被“除著作郎”,“兼修史皆如故。”等“大驾还京”,刘知几复被“驿征入京,专知史事。”对自己一生能多次承担史职,刘知几颇为自豪,感喟说:“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 嗟予小子,兼而有之。 ”(《史通原序》)[5](P1)这一感喟,体现的是刘知几对能承担史职的满腔欣喜。
慕“史”心态发生,还同时源于对史学家才、学、识兼备人文素养的认可与称扬。
由于对图书有优先接触权,中国古代史家一开始便表现出博学多识的深厚修养。如孔子作为中国史学第一巨人,不仅深知周“礼”,删《诗》,撰《春秋》,“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更对世间诸如坟羊、骨节专车等奇异之物颇知来历[15]。孔子之后,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大家同样如此。唐后,随着史学实践日益积累,才、学、识兼备人文素养逐步成为史学界对史籍人才的普遍要求。如据《旧唐书》记载,刘知几认为要成就“史才”,须有三长,一是“才”,二是“学”,三是“识”,三者缺一不可[16]。 《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中,章学诚以“史德”统合“才”、“学”、“识”三者,并同时指出:“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17]在国家政府活动中,为保证史籍编纂质量,更同时以行政方式对史籍人员才、学、识进行有意规引和培养,如唐高宗就曾下诏云:“修撰国史,义存典实,自非操履忠正,识量该通,才学有闻,难堪斯任。……自今宜遣史司,精简堪修史人,灼然为众所推者,录名进内。自余虽居史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5](P226)在国家科举考试中,史才也经常被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普遍规定与要求下,一个人晋升史官,不仅意味着其才、学、识兼备素养的被认可、其较之于单纯“文人”的超越,更意味着其会赢得社会普遍的尊重与好评。
在史之功用如此重要、史之地位如此尊贵、史之编纂如此荣耀、史之才能如此被认可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表现出浓郁的慕“史”心态。此心态于“小说”这一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如《次柳氏旧闻》为唐李德裕编撰,书以高力士所述唐玄宗宫中事记载为主。该书序中,李德裕自暴其“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次旧闻”。“惧”历史事实“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其书“谨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18]《锺情丽集》为明邱濬编撰,主要叙述琼州书生辜辂与其祖姑家表妹梁瑜悲欢离合事。明简庵居士为该书作序时,指出“大丈夫生于世也”,应“达则抽金匮石室之书,大书特书,以备一代之实录;未达则泄思风月湖海之气,长咏短咏,以写一时之情状”,认为邱濬《锺情丽集》编撰不过是“游戏翰墨云尔”,等作家有朝一日“操制作之任,探笔法之权,必有黼黻皇猷,经纬邦国,而与班、马并称之矣。”[9](P595-596)清彭一楷称赞《台湾外志》“笔力古劲,雅有龙门、班掾风”,慨叹“江子始负此才,不获纂修史馆,而乃沦兹草野,成一家言以自见,其以劳瘁矣乎!”,断言此书“有功名教,良非浅鲜。异日之以登对大廷,备史氏之阙文,江子与是书不朽矣。”[9](P1044-1045)在这些无论是作家自陈还是他人说明中,流露的均是对于“史”的尊仰,以及对于小说作家不能从事史书编纂的遗憾。
事实上,这一对“史”的尊仰情绪,在中国古代小说序跋与评点中普遍存在,实难以详尽叙述。这一“慕史”心态与唐后史学家对小说“史补”功能论定两相结合,便导致唐后小说创作与评论中普遍流露出浓郁的自觉而为的“史补”目的。
这一目的突出体现于创作与评论中对“史”的功能的攀附。“史”的功能具体来说,是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消闲娱乐”是现世中国人对小说存在价值的基本认知。若以此认知为据,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对小说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等价值功能的赋予正是出于对“史”的功能的攀附。这一攀附,我们从小说作品相关功能阐释中大量溯源于“史”的论断可充分看出。如《洛阳搢绅旧闻记》为宋张齐贤编撰,书凡21篇,主要叙述唐梁以来至五代间洛阳见闻。对该书创作宗旨,张齐贤交代说:“约前史之类例,动求劝诫。”[19]《稗海》为明商濬编辑,书序中,他首先肯定“自六经、《语》、《孟》之外,称繁巨者,莫逾左右史。……故周志、晋乘、郑书、楚杌,与尼父麟笔并垂霄壤。离是而还,龙门世授,班氏家承,其文艺体裁为百代称首。历世沿袭,类相仿效,大都才望名位,俱表表人伦。虽极之舆统崩析,方策零落,然先后嗣续,掇拾修纂,终无泯灭。”在此基础上,他进而肯定古往小说“亦足识时遗事,垂示后人耳目所不及。 ”[9](P1786)酌元亭主人编次《照世杯》,以“照世”为名,旨在于洞照“世事”。在此目的传达中,他也是先将“小说”视为“史之馀”,然后说小说“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的叙述可“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 ’”[9](P836)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演义”标目,旨在于借“事”演“义”,通过相关历史事实的叙述,起到对求仁政、尚忠贤、恶奸诈等价值观念宣扬的目的,同时对后人以某种经验的启迪。对这样的创作宗旨,明庸愚子解释时,也是先将其溯源于“史”,指出:“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20]。事实上,不惟以上作品,在中国古代小说序跋中,诸如此类言语还有很多,因篇幅所限,难以尽述。对小说作品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等相关功能阐释溯源于史,在这样的论证方式中,体现的不只是小说较之于史传卑微的处境,流露的更是企图通过攀援史传功能以抬高小说地位,提升小说价值与品位的深刻用心。在此用心中,小说“史补”的内涵所指显而易见。
对“史”之功能进行攀附,小说“史补”的这种价值指向对小说发展首先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中国古代小说来说,无论是原初形态的“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拾史之遗、取史之弃,还是唐以后小说创作的幻设为文,小说之所以流行,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具有传奇述异、令人赏心悦目的娱乐审美功能。这一功能倘若没有基于“史补”观下“史”的功能的规引及因之而具有的征实观念的限制,小说创作很可能滞于“牛鬼蛇神”之奇而难以自拔,“日用起居”叙述中造“奇”的叙事能力不会获得积极发展;审美娱乐而外倘若没有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等“史”之功能的注入,小说的内涵会显得单一,小说存在的价值与品位不会获得提升。从这些方面来说,小说“史补”的这种价值追求诚对中国古代小说兼具审美娱乐与“史”之功能、重视“日用起居”中造“奇”叙事能力等民族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小说的叙事内涵日益丰富,小说的价值品位不断提升,倘要追根溯源的话,也当与小说“史补”的这种价值追求具有紧密联系。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小说“史补”的这种价值追求对小说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序言中,郭豫适先生指出:“封建史学家那种崇实斥虚的思想倾向,那种过于强调文学著述劝善惩恶、宣扬封建纲常的教化功能的观念和意识,对小说的创作却是一种束缚;史学家的‘实录’精神也被不正确地解释和运用到小说批评中去,要求小说创作也象史学著述那样严格地记录史实和事实,这些都不利于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发展其独立的个性,影响到小说的创造精神和艺术的想象及虚构。”[21]《中国小说源流论》中,石昌渝先生申论说:“中国小说是在史传文学的母体内孕育的,史传文学太发达了,以至她的儿子在很长期不能从她的荫庇下走出来,可怜巴巴地拉着史传文学的衣襟,在历史的途程中躅躅而行。这样的历史事实,反映到理论家、学问家的观念里,自然是对小说的轻视。”[22]两人所论,虽立足于小说与史传的关系而言,但倘若移来论述这种史补取向对小说的不利影响,也同样合适。对“史”之功能长期而执着的攀附,使得小说的审美娱乐功能长期处于被忽略、被轻视的地位,对如何提高小说审美娱乐品位、如何以有效手段实现小说审美娱乐功能等有关小说发展的紧要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基于此“史补”目的下的实录观念,对小说想象和虚构的本质特征也经常是一种否定的态度。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小说本身个性的成熟与发展。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步伐缓慢而曲折,说到底,皆与小说的这种“史补”观具有紧密关联。小说只有摆脱了这样的“史补”观念,才能走上自身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补“正史”之“未备”,做“正史”之“辅佐”
宋元以后,伴随文化下移与市井“说话”活动空前发展,小说“史补”观念有了明显变化。此时,攀缘正史以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等主流“史补”观念依然十分盛行,但与此同时,却也出现了新的“史补”观念的流行与发展。此“史补”观念即是出于对“史”的教化功能实现不力而所采取的补“史”行动。
这一“史补”观念于宋文言小说中初显端倪。其中,《续世说》的创作与评论可谓首开其功。《续世说》为宋孔平仲编撰,书成后,宋人秦果为其作序。序中,秦果指出:“史书之传信矣,然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小说诚可悦目,往往或失之诬”,孔平仲《续世说》编辑“囊括诸史派,引群义疏剔繁辞,揆叙名理”,“可谓发史氏之英华,便学者之观览,岂曰小补之哉?”[23]秦果此序,不容小觑,它代表着小说“史补”观念的重要变化:正史固然可以传信,但“浩博而难观”;诸子百家小说诚可悦目,却往往失之于“诬”;既简明扼要,信而可考,又能发覆史书主旨使其容易为人接受,当是《续世说》之类的作品。这样以来,小说“史补”观念便由以往对“史”单纯地顶礼膜拜、参照仿效转而为对史书主旨的发覆与表达方式的转换上来,小说的文体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小说达“义”的优越性得到了积极承认,小说的叙述方式成为明确肯定的优点。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史补”观念在宋文言小说作品序、跋中,仅此一例,它表明这样的“史补”观念在当时尚处于萌芽阶段,并未获得普遍认同。
元、明以后,这样的“史补”观念在文言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表达的内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如《浇愁集叙》中,清朱康寿把小说看成史家“别子”,认为小说“综厥大旨,要皆取义六经,发源群籍,或见名理,或佐记载;或微辞讽喻,或直言指陈,咸足补正说所未备。”《语新跋》中,清钱徵评价钱学纶《语新》“虽未足据为掌故,然亦间有足补志乘之未及者。”《秦淮画舫录自序》中,清捧花生认为“良一代之兴,有铭钟勒鼎者,黼黻庙堂,以成郅隆之化。即有秦歌楚舞者,点缀川野,以昭升平之休”,把《烟花录》、《教坊记》等小说看成是“副载经史”。《今世说序》中,清冯景认为国史为“大”,重在“传其人”,小说为“细”,重在传其“神”,认为借“传神”之穿隙日影,有助于窥见国史“全日”。《生绡剪弁语》中,清谷口生把六经子史看成“庙堂铮鋐之声”,把小说看成“茅茨纤细之韵”,认为若只有“庙堂铮鋐之声”,而无“茅茨纤细之韵”,则又为“文人之罪也。”[9](P200、477、483-484、469、616-617) 在诸如此类阐述中,或从记述题材,或从审美特征,或从感人效果等,均把小说看成具有补足正史“未备”、“未及”的作用。在此作用说明中,虽然所使用的仍是“补”的字眼,但较之于对“史”一味攀缘和仿效的“史补”观念来说,小说的文体地位有了明显提高,小说不同于“史”的特征不仅得到了明确承认,并获得了积极发展。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与对“史”一味攀缘和仿效的“史补”观念来相比,这样的“史补”观念在文言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出现的时间不仅较晚,表达的频率与强度也相对要低得多,它表明,文言小说与史传存在更为密切的血缘联系,两者在内在精神与行文笔法上存有更多的“家族相似性”特征。
相对来说,这样的“史补”观念在白话小说创作与评论中则获得了充分发展。此中,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与评论可谓具有先声与代表意义。“演义”一词最初出自于《后汉书·逸民传·周党》,其中云:“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易·系辞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高亨注解云:“《释文》引郑云:‘衍,演也。’先秦人称算卦为衍,汉人称算卦为演,演与衍古字通也。”若以此解释为据,可看出,“演”与“衍”相通,均含有引申、推广、发挥的意思,所谓“演义”,就是要对其中蕴藏的深刻道理进行阐发。《三国志通俗演义》正蕴涵着这样的创作目的。何以要通过通俗小说这种形式对《三国志》所蕴藏的深刻道理进行阐发,其中原因,明庸愚子蒋大器、修髯子张尚德分别给予了明确说明。《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庸愚子指出:史“非独记历代之事”,“有义存焉”,“然史之文,理微义奥。”“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之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修髯子交代:“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愚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 ”[9](P886-887,888)综合两人所论,其中共同蕴涵着这样的“史补”观念:“史”以达“义”为宗,固然可敬,但“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并不“通乎众人”;相对来说,小说语言通俗易懂,叙事生动形象,其对“史事”的敷衍,更易促进读者对“史”的了解,更能激发读者对“史”中所蕴涵的“义”的把握与践行,从此角度来说,小说实起着羽翼正史之“不足”而使“万古纲常期复振”的重要作用。
《三国志通俗演义》创作与评论所表达的这一“史补”观念,在白话小说领域得到广泛继承。关于此,从明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清醉犀生《今古奇闻序》、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管窥子《今古奇观序》等大量白话短篇小说集序、跋,以及明清时期很多历史演义小说作品序、跋中,均可充分看出,此无须再赘。这种情况说明,在白话小说领域,以小说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等审美特征为凭借,来补救正史因语言艰涩、叙事板滞庄重带来的播“义”困难,辅佐正史实现对社会世风的教化,是较为普遍流行的“史补”观念。
在此观念表达中,也如同文言小说一样,出现了“史补”内涵的不断扩展。其扩展具体来说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视小说为通“史”之阶。如《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余邵鱼称《列国志传》编撰是“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所以“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 ”[9](P861)《痛史序》中,清吴沃尧慨叹中国史籍浩如烟海,“精华”颇多,但其传播、研读却存有“六端”之弊,“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所以历史小说《痛史》编撰是期望“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临其境。”[24]二是视小说为补“史遗”之具。如《隋史遗文》创作中,袁于令慨叹“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其书编撰“十之七皆史所未备”,“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 ”(《隋史遗文序》)[25]《大宋武穆王演义序》中,熊大木称“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26]《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序》中,清李雨堂认为“史乃千百年眼目之书”,“述史不得不简而约”;此“简而约”,易使读者产生“纸短情长”之憾,阅读过程也会觉得“枯寂”;相对来说,小说虽“无关于稽考扶植之重”,但“如舟中寂寞,伴侣已希,遂觉史约而传详博焉。”[26]三是视小说为纠“史失”之具。相对前两者来说,这一看法在白话小说中表达较为稀少,但其存在也是客观事实。如《南北宋传》为明熊大木编撰,书成后,明织里畸人为其作序。序中,织里畸人称:“史载宋太祖事,类多儒行翩翩。”但“揽五代传志”,却“罄同任侠,杀人亡命,作奸犯科,不异鲁朱家之为,与正史乃不尽符”;以《闻见录》所记为据,知“五代志传”所记非虚,并由此感叹:“史固非信哉”,“一人之见斯狭,一史之据几何。若其失而求之于野,传志可尽薄乎? ”[9](P973-974)这一阐述中,织里畸人显然认为稗史志传等作品可对“史”之“失”起到纠偏、印证作用。
综合以上阐述,不难看出,以小说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等审美特征为凭借,补足正史“未备”、“未及”处,辅佐正史实现对社会世风的教化,是宋、元以后普遍流行的“史补”观念。此观念在宋元以后文言小说领域只是获得有限发展,而在白话小说领域则获得充分发扬。在此“史补”观念表达中,无论是辅“史”以演“义”、借“说”以通“史”,还是视小说为拾“史遗”、纠“史失”之具,小说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等审美特征都得到了积极承认。这一承认,自然会为小说这些特征的进一步开掘提供可能,拓展空间。在此可能与空间开拓中,较于史“成郅隆之化”、重在传“人”、为“庙堂铮鋐之声”等文体特征来说,小说“昭升平之休”、重在传“神”、表现“茅茨纤细之韵”的文体特征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此发展中,小说区别于“史”的文体特征是越来越明显。
四、籍“正史”之“不载”,成“精神”之“欢娱”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补”中,除上述两种“史补”观念外,还存在一种暗性的、似乎不易为人所察知的“史补”观念,此观念即是出于对“史”的审美娱乐功能不足的认识而所具有的“补史”行为与心理。
此“史补”观念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创作与批评中已露端倪。如《洞冥记》传为汉郭宪编撰,《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词句缛艳”[27](P1207)。对这样一部书,郭宪作序时称,其家“世述道书”,“犹有漏逸”,“或言浮诞,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考虑到“古囊馀事,不可得而弃”,其书“籍旧史之所不载”,“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6](P123)从这些说明中,可看出,书所记载的内容是对“经文史官”叙事略而不取“浮诞”材料的拾取,记述的目的是“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记述使用的语言是具有“缛艳”特征。这些方面特征的明确说明,与史书的编纂标准来相比,不正体现出对与史书截然不同的审美风格与艺术风致的追求吗?
唐时,“史补”成为小说创作与批评自觉意识。在此意识下,文言小说“史补”呈现为两方面自觉地发展,一方面诚如前述,体现出对“史”的功能的强烈攀附,另一方面则是坦然以“小”自居,并逐渐突破“史统”征实、尚信、重道观念的限制,体现出对有别于经史高文审美娱乐特征的有意开发与追求。《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明胡应麟评价唐人小说“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若《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元无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28]。《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之高文”;……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劳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 ”[29](P44-45)胡应麟、鲁迅的这些评价,均站在与前代小说、经史高文比较的高度,来把握唐代小说新的艺术个性。在他们看来,与经史高文和前代小说相较,唐代小说“作意好奇”,内容虚构,叙述近于“俳谐”,文气亦显“卑下”,创作的“大归”是在于“文采与意想”,具有鲜明的“假小说以寄笔端”、“但可付之一笑”的审美娱乐特征。
唐人对小说这些特征的有意开发与追求,在当时新兴的传奇小说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对此,前人已颇多论述,此无须再赘。传奇小说而外,传统的志怪、杂录类等小说创作也体现出同样的审美追求。关于此,从当时作者与评论者对小说作品阐释时将其与“史”有意区分可充分看出。如《刘宾客佳话录》为唐韦绚编撰。自序中,韦绚称该书“解释经史之暇”的产物,说书记载的内容是“国朝文人剧谈,卿相新语,异常梦话,若谐谑卜祝童谣之类。”作这样一部作品,是为了“传之好事者以为谈柄”[9](P296-297)。 《酉阳杂俎》为唐段成式编纂,书中所记,多杂诡怪不经之谈,充满荒渺无稽之物,标目亦称奇诡,乃至自唐以来,被“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 ”[27](P1214)对此作品,段成式作序时,也明确将其与“史”区分开来,称该书“无若诗书之味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自己“固役而不知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9](P301)唐参廖子创作《阙史》,以“阙史”为名,旨在补“史”之“阙”。 在史“阙”补遗中,凡“雅登于太史者”,皆“不复载录”。作这样一部书,是为了“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9](P316-317)。 在诸如此类作家自陈中,从成书状态、选材标准、叙事风格与创作目的,都明确将其与“史”区分开来。这一区分,表现的正是对于有别于“史”的审美风格与艺术特征的追求。
宋元以降,文言小说“史补”虽主体上仍呈为对“史”的功能的攀附,但若立足于小说发展的大势来看,小说“史补”的这一价值指向是表现愈来愈明显。这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在小说作品命名与相关序跋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小说审美娱乐功能的追求。 如《笑林》、《苏黄滑稽录》、《拊掌录》、《雪涛谐史》、《解人颐》、《笑林广记》、《新齐谐》、《浇愁集》、《埋忧集》等作品即如此。这在清文言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二是在小说作品批评中,将其与“史”在审美特征与价值功能上进行区分的表述愈来愈多。如明王思任为何良俊《语林》作序时,批评晋代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晰,虽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赞扬刘义庆《世说新语》“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并进而断言《语林》等作品似“兰苕翡翠”、“珍错小品”,它虽不如“碧海之鲲鲸”的“明旨大肉”,但“泥沙既尽,清味自悠,日以其佐之《史》、《汉》炙可也。”[9](P415)清袁枚创作《新齐谐》,自述“文史外无以自娱”,所以“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目的是为了“以妄驱庸,以骇起惰。 ”[9](P156)清梅鹤山人为《萤窗异草》作序,称“杂记又有二种,大儒之语录不与焉。其搜求典坟,博览载籍,引古证今,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记载时事,传述闻见,舒广长之舌,斗雕缕之心;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采颐索隐,文不嫌夫诡奇。仰《齐谐》为谭宗,慕《虞初》而志续。如杜牧之寄托风情,李伯时摹绘玩具,亦足以消长日,却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无墨瀋,动谓立言,务黜浮华,以为补救人心,挽回风气起见,则六经、廿二史,圣贤遗训,般般可考,又何必如此迂腐陈言狗尾续貂耶! ”[9](P168-169)在这些阐释中,均揭示出小说较之于“史”所具有的“事不必问其虚实”、“文不嫌夫诡奇”、有助于“消长日、却睡魔”的审美娱乐特征。三是在传统志怪小说发展中,出现了对于传奇手法的借鉴与继承。《聊斋志异》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以抒发作家“孤愤”为宗,鲁迅评其书“用传奇法,而以志怪,”[29](P147)纪昀称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批评其“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见之?”[30]这些评价,都道出该作品对于传奇手法与创作目的的借鉴与继承。立足整个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传统的创作特征中加入进传奇的表现手法与审美意趣,无疑就是对小说本身审美娱乐特征的进一步开发。
相比来说,小说“史补”的这种价值指向在白话小说中发展更为充分。这也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小说传“奇”的审美特征获得普遍认可。如《拍案惊奇》、《古今传奇》、《巧奇冤》等作品的命名、“三大奇书”、“四大奇书”的称谓等,在“奇”字眼的选择中,就蕴涵着对小说传“奇”特征的把握与定性。在小说作品序跋中,更充溢着大量的对于作品传“奇”目的说明的文字,并将其与“史”传“信”的特征给予区分。二是小说作品虚构、铺张文采的叙事能力获得充分肯定。如《金瓶梅序》中,清观海道人断言“小说家语,寓言八九,固不烦比附正史以论列。”[31]《读第五才子书书法》中,金圣叹用“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来区分《史记》与《水浒传》,并说明“因文生事”者,“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32]小说评点中,也动辄以“才子书”命名评点作品,并对作者非凡的叙事能力啧啧称奇。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对于小说作品虚构特点的把握,对其叙事文采的充分肯定。三是小说作品叙事,往往体现出浓郁的抒情色彩。这从作品中作家的自陈与叙事中所运用的诗词可首先表现出来。《三国志通俗演义》开篇词中“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喟,《儒林外史》末尾作家“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的感叹等,都是对这一抒情色彩的明确说明。除此而外,作品本身的叙事,也包含着启发读者情志的能力。明李卓吾评价《水浒传》“发愤之所作也”,观海道人评价《金瓶梅》“匪仅使人知所戒惧,抑亦可使人怡悦心性焉”[9](P1110),鲁迅评价《红楼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诸如此类,都是对作品这一发人情志能力的明确说明。
史籍编纂旨在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它的记述中尽管不乏“浮诞”的笔墨,对“文”的使用也很明显,但总的来说,却对其抱以警惕的态度,并不主张对其的过分使用。这一状况,必然造成史籍作品板质庄重、审美娱乐功能的不足。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喜欢读史书的原因所在。“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33],从此角度来说,小说作品对于“浮诞”内容的大量记述,对于叙事文采的恣意张扬,对于个人感情的任意抒发等,都具有了补史传之不足的作用。《阙史自序》中,参寥子称“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小说,“犹至味之有菹醢也。”《世说新语序》中,明王思任称史传作品为“碧海之鲲鲸,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当厌去”,认为《世说新语》等小说作品似“兰苕翡翠”、“珍错小品”,“泥沙既尽,清味自悠,日以佐之《史》、《汉》炙可也。”《新齐谐序》中,袁枚称“文史外无以自娱”,所以“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餍八珍矣,而不广尝夫蚳醢、葵菹则脾困;嗜音者备《咸》、《韶》矣,而不旁及于侏俪僸佅则耳狭。”“是亦裨谌适野之一乐也。 ”[9](P317,415,156) 诸如此类阐说,都是在审美娱乐的基础上,来说明小说所具有的“史补”价值的。
综上,“史补”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观念之一,其生成主要是源于史学家对小说“史补”功能的界定。此界定主要发生于唐代,此后,便成为小说创作与批评自觉意识。在“史补”中,出现了三种向度的不同发展:一是对“史”之功能进行攀附,把小说看成如“史”一般具有存故实、寓鉴戒、播道义的功能。二是从“史”之教化功能不足处入手,认为小说可以辅“史”以演“义”,同时还可作为通“史”之阶、纠“史”错之具、补“史”之遗而存在。三是认为小说可以补“史”审美娱乐功能之不足,使人们在正史阅读之外,获得别样的审美享受。前种“史补”观贯穿唐后小说始终,尤其在文言小说中表现更为明显,后二种“史补”观念则主要流行于宋元以后,尤其在白话小说中获得长足发展。前种“史补”观表现出与“史”相依的特征,它对中国古代小说兼具审美娱乐与“史”之功能、重视“日用起居”中造“奇”叙事能力等民族特征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古代小说自身艺术个性迟缓发展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两种“史补”观则表现出与“史”相离的特征,它为小说本身艺术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拓展了空间。三种“史补”观念交融递变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个性不断成熟的过程,是其存在价值与艺术品位不断提升的过程。
注:
① 所谓“短书”,按王充《论衡·谢短》中“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的记载来看,当是指与圣人文语二尺四寸记载规格相比要低一些的记载形式。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94.706-707.
[2](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53.
[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78.
[4](唐)魏征,令狐德棻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8.982,962.
[5](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75.
[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07.
[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唐)李肇撰.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
[11](宋)洪迈撰.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54.
[12](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239.
[13]程国赋.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27.
[1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6.28.
[15](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42.
[1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73.
[17](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0.
[18](唐)李德裕撰.次柳氏旧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1.
[19](宋)张齐贤撰.洛阳搢绅旧闻记,笔记小说大观[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
[20](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卷首.
[21]方正耀.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03.
[22]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1.
[23](宋)孔平仲撰.续世说,历代笔记小说集成[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67.
[24](清)吴趼人.痛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卷首.
[25](明)袁于令编撰,冉休丹点校.隋史遗文[M].北京:中华书局,1996.407.
[26](明)熊大木编.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7](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8](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71.
[2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0]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498.
[31]黄霖.金瓶梅资料彙编[Z].北京:中华书局,2006.12.
[32](明)施耐庵、罗贯中著,(清)金圣叹,(明)李卓吾点评.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33]王充.论衡[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442.
【责任编辑:向博】
Historical Origi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History Supplement”Idea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HE Yue-ling
(College of Art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710062)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history supplement”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definition of the function of"history supplement"by ancient novels by historians.This definition mainly occurred in Tang Dynasty,and then became consciousness in novel writing and criticism.“History supplement” developed from three dimensions:One i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function of“history”,and consider novels as writing like“history”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preserving historical facts,providing reference,and disseminating moral principles.Second is to make up for the insufficient education function of“history”,and novels can interpret“righteousness” through“history”,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help understand“history”,correct mistakes in“history”,and supplement omission in“history”.Third is that novels can be a remedy for the deficient aesthetical function of“history”,making people achieve special aesthetical enjoyment.The first idea of“history supplement”is permeated in novels after Tang Dynasty,especially obvious in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The other two ideas of“history supplement”was mainly prevalent after Song and Yuan Dynasties,and gained ground in vernacular novels.Blending and alteration of these three ideas of“history supplement”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China’s ancient novels gradually mature,and their value of existence and taste for arts constantly improved.
ancient Chinese novels;the idea of“history supplement”;historical origin;value orientation
I 207.41
A
1000-260X(2017)05-0124-10
2017-07-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
何悦玲,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及元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