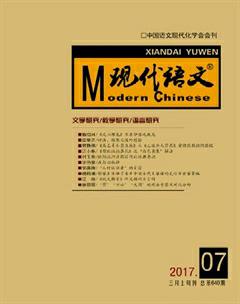欧阳江河诗歌写作的经典意识
摘 要:在当代众多的诗人当中,欧阳江河是一个经典化意识非常强烈的诗人。具体来说,他追求不朽的文人情怀,为自己的诗歌写作进行命名,以长诗写作挑战当代消费文化,都是这种自我经典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欧阳江河 诗歌写作 经典意识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已成为文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它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也有学者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还为时过早,杨厚均认为:“当代文学还不具备经典化所必需的条件。一个时代的文学能成为经典,一方面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构成经典的基本品格,另一方面,这种品格是通过历史来指认的……它不可能由同时代的人来完成。”[1]可以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过程,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可以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作家、诗人就没有希冀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的主观意识。相反,经典化意识往往伴随着作家、诗人写作的始终。在当代众多的诗人当中,欧阳江河是一个经典化意识非常强烈的诗人。他的经典化意识不仅表现在他的诗学观念中,而且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写作中,他的“大师情结”,他独特的诗歌艺术特征,他对写作立场的自我命名,他通过诗歌对时代进行复杂的观照,他以长诗写作挑战消费文化,都是这种经典意识的体现。
一、追求不朽的文人情怀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欧阳江河就以强烈的经典意识来界定诗人的身份,他说:“至于诗人,我认为除了伟大他别无选择……伟大的诗人乃是一种文化的氛围和一种生命形式,是‘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2]另外,欧阳江河还在《关于现代诗的随想》中提出了“大师论”,以此作为诗歌写作的努力目标和评价尺度,认为诗人应该“从事王者的事业”。他认为:“大师是一种文化氛围和一种生命现象,是种族精神进化过程中的一次突变,是一代乃至几代人的总结。”[3]这也说明欧阳江河的经典化意识觉醒是比较早的,他在当时中国现代诗进展中保持着超前的观念,而这种经典化意识又是一种主观的积极态度,是诗人对自己诗歌写作的自我期待。到了90年代,欧阳江河又提出了“经典写作”这一概念,面对90年代诗歌写作的日益边缘化、日常化、碎片化,他感慨道:“我们离经典写作还相去甚远,但正如孙文波在一篇短文里所说:‘没有朝向经典诗歌的产生的努力,诗最终是没有意义的。”[4]欧阳江河认为经典写作是真正有效的写作,而“真正有效的写作应该能够经得起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包括政治话题系统)中被重读和改写,就像巴赫的作品既经得起古尔德的重新发明,又能在安德列斯·希夫带有恢复原貌的正统演绎中保持其魅力。”[5]可见,对于诗歌写什么、为什么写、怎么写等问题,欧阳江河都是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对于有作为、有抱负的诗人而言,追求诗作的经典性不仅仅是为了名垂史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和“可读性”。这也意味着诗人的责任感和对自身的“职业要求”,同时意味着当代诗人在面对所处时代时的角色焦虑感和身份危机感。因为在90年代以后,诗人的社会角色日益模糊和微弱,曾经诗人作为启蒙者和代言者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商品化的时代,诗人不能代表时代主流;在多元化的时代,诗人不能代表精神的标杆。欧阳江河的经典化意识,表面上看是一种个人意识,实质上是当代诗歌整体困境的一种折射,从80年代初诗歌作为民族精神殿堂上的明珠,诗人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的盛况到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轰轰烈烈的反文化、反抒情、反崇高等精神大反叛,再到90年代的个人化、边缘化、叙事性、修辞性,当代诗歌经历了从神坛到地面的迅速跌落过程。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经典化”则意味着诗人逆流而上、不甘平庸,力图与时代互博,与社会对话,用诗歌重新勾勒时代精神的图景,以诗歌重塑时代精神的价值追求。
新世纪以来,欧阳江河的诗歌写作由早期亲历性的视角转变成了俯视性的视角,使自己的诗歌书写充满历史意识和宇宙意识,强调“万古闲愁”的历史感。对此欧阳江河在一次访谈中做出了如下解释:“我们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它理当如此。它就该是俯视性的……如果我们时代里,最好的诗人都不去关心大国写作,那这样的诗歌就没有了。实际上……这是只有极少数诗人,甚至是大师才能干的事情。”[6]在这里,欧阳江河又一次重申了他的“大师”情结,这里的“大师”与“大国写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欧阳江河看来,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历来为诗人提供了“大国写作”的历史和土壤,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百年来的民族屈辱一度让国民自信心丧失殆尽,遂不知大国为何物。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日益复兴,中国再次显现出千年贯之的大国风范。作为当代诗人,应该与这种时代气象相融合,书写具有中国气派的辉煌诗作,表现出时代应有的强健、明亮、恢弘的进行曲,而不应该沉溺于90年代以来的局促、狭隘、碎片的个人化写作,在苍白孱弱的自我窥视中孤芳自赏。某种意义上讲,欧阳江河在为民族记忆中的盛唐气象招魂,他看到了这个时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恢弘磅礴、除旧布新、蒸蒸日上、势不可挡的发展气象,他希望有抱负、有气魄的诗人参与到这一伟大时代的行列中来,像惠特曼一样记录这个时代广大而浩瀚的一切。可以说,渴望诗歌成为经典的期待是诗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外化,也是千百年来在儒家文化浸染子下的知识分子“不朽”意识的当代重现。在当代中国,虽然儒家文化已不再是主流的价值信仰,但诗人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力量,身上仍然潜藏着千年儒家文化遗传基因,“立功、立德、立言”,青史留名而不朽于后世,依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梦寐以求的渴盼,欧阳江河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倡导者,这种不朽于后世的经典化意识尤为强烈。
二、对写作立场的自我命名
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一个因素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在一个文学理论貌似繁盛实际上却芜杂凌乱的时代,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多元的、眾声喧哗的。作为诗人,能够在复杂、繁乱的时代留下自己的声音,保持诗歌文本的有效性,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为自己的诗歌写作命名,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构建自己的诗学体系,进而反作用于诗歌评论的价值取向。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从“新传统主义”“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个人化写作”“亡灵意识”,再到技术层面的“反词修辞”,欧阳江河先后多次为自己的诗歌写作命名,阐述自己的诗学主张。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第三代”诗歌的兴起,欧阳江河和廖亦武举起了“新传统主义”的旗帜,将目光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以反对旧传统,建立新传统的诗歌壮举树立自己的精神标杆:“我们否定旧传统和现代‘辫子军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反对把艺术感情导向任何宗教和伦理,我们反对阉割诗歌。”[7]这是欧阳江河追寻的“新传统”,作为欧阳江河第一次自我命名,显示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年轻的诗人们渴望经典、渴望被历史铭记的热情。而那首著名的长诗《悬棺》作为欧阳江河剖析和怀疑旧传统的试验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自己特殊的理解与延展,同时也是欧阳江河经典写作的开端之作,一经面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诗人杨炼阅读之后,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一举奠定了欧阳江河的诗坛地位。1993年,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中,欧阳江河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写作”,他主要从“专业性质”和“边缘人”来理解“知识分子”:“我所说的知识分子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的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因为我们既不属于行业化的‘专家性的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普遍性的知识分子。”[8]这段陈述是耐人寻味的,欧阳江河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是边缘人身份,但同时他又通过对这种边缘身份的命名来获得时代的认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欧阳江河的边缘身份意味着对现实带有一定距离感的冷静审视、独立的立场、批判的态度和新价值的创立等,因为欧阳江河明确表示:“在转型时期,我们这代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9]除了写作立场上的自我命名,欧阳江河还提出了“反词”的修辞立场,主张通过“反词”来抵达事物本身,这是对“词”的一种新的塑造,也为“词”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可能。它不仅动摇了可公度的“词”的意义,也使“词”的意义结构面临着偏离。在颠覆了“词”的传统意义的同时,赋予了“词”以崭新的意义:“词与反词在经验领域的对立并非完全绝对,它们含有两相比较、量和程度的可变性、有可能调节和相互转移的异质成分。”在写作实践中,“反词”修辞构成的二元互搏成了欧阳江河诗歌修辞的标志性特征,以一种极端的‘差异链能指的形式出现,这成了欧阳江河所独有的只可观赏、不可模仿的“个人专利”。陈晓明认为:“欧阳江河是90年代最出色的诗人,在80年代,北岛挑战了思想的极限,90年代,欧阳江河的诗歌则挑战了汉语言的极限……”[10]这是对欧阳江河的“词语的诗学”的最高肯定。通过一系列的自我命名,欧阳江河逐渐构建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并且通过不懈的诗歌写作实践形成了独特的个人诗歌风格,迥异于当代其他诗人的诗歌风格,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了深广的可阐释空间,使其诗歌在走向经典的阶梯上不断攀沿前进。
三、长诗写作的经典化努力
作为诗人来讲,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走向经典,首要的是写出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有深广的可阐释空间的作品。从命名角度渐次树立的“经典化”书写,还需要文本意义上的事实“经典”,每个属于某一时代并对相关“经典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除了被命名以外,诗人具有“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作品,也应该在文学接受的角度上呈现出类似的效果。欧阳江河认为,技艺和经验成熟与否是一个诗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80年代的《悬棺》,到90年代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纸币、硬币》,到21世纪初的《泰姬陵之泪》《凤凰》《黄山谷的豹》,这些作品显示了欧阳江河对长诗、组诗纯熟、老练的驾驭水平。在欧阳江河看来,一方面,长诗的写作是对抗快餐式的消费时代的有力方式,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和诗歌阅读彻底降低了读者的智力参与和精神投入,诗歌阅读成了走马观花和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的观览,也使得诗人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崇高感,更让诗人感到焦虑的是,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使得诗人将彻底丧失诗歌价值实现的可能,而长诗的体量和含量将逼迫读者静下心来,以虔敬的态度、以仰望的视角重新面对诗歌。另一方面,长诗是实现诗歌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因为鸿篇巨制的长诗写作意味着对诗人才能和诗艺所能达到的极限的挑战,从而显示了诗歌本身的分量,是诗人希望其诗歌能流传于后世的尝试和努力。
从长诗的创作动机来说,欧阳江河主要以荷尔德林、庞德、帕斯、保罗·策兰、圣琼·佩斯为榜样和楷模。这些世界级的大诗人之所以在文学史上留名,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通过长诗的创作挑战了普通诗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和技巧高度,使自己的诗歌创作成为很难逾越的高峰。欧阳江河是有这个雄心的,他不仅创作了一系列有影响的长诗,而且引起了诗歌批评家的关注,如吴晓东、杨庆祥对《凤凰》的关注和评论。一部长诗的地位不是作者一人可以完成的,还必须借助于批评家的解读和评价。诚如欧阳江河自己所说:“长诗所达到的高度和强度,不仅仅是写作的结果,也是批评和阅读参与进来的结果。像荷尔德林,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阅读,他就不是荷尔德林。”[11]显然,欧阳江河在写作中有一个“隐含的读者”,这个“隐含的读者”主要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具有艺术识别能力的权威的理论家或批评家。相对于普通读者的反应和评价来说,欧阳江河更关注的是有影响力的诗歌评论家的态度和解读,即通过诗评家的解读和评判,赋予诗人的诗作以他所期待的历史地位。在这一点上,欧阳江河甚至对国内的诗歌阅读和评论现状表示了不满:“我们中国的长诗与刚刚提到的这些西方经典长诗的差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写”的问题了,也是一个阅读的。我们的阅读和批评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12]这显示了欧阳江河对诗歌的自负和对诗歌批评界的居高临下的期待。当然,对于当代诗歌的经典化问题,欧阳江河还是保持着应有的清醒:“中国的长诗,包括我在写的长诗,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高度,第一,它们离我们太近,离写作和阅读太近;第二,是不是批评家有一个缺席,我不知道……长诗的写作,它的成败,不仅仅是‘写的问题,也是一个批评的问题,和阅读的一个产物。”[13]通过长诗的写作,欧阳江河以一种超拔的高度对时代进行超越性书写,在揭示生存真相、探寻语言奥秘方面做了颇有力度的探寻,有效地反映了时代复杂多变的现实场景,切入到了当代最隐秘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为中国先锋诗歌的继续前行做了开拓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江河的长诗写作也是一种朝向经典的有力探索。
诗评家陈超在论及欧阳江河时说:“一个时代的真正结束不是物理时间的结束,而是以一个或几个文本来结束的。如果没有一个文本来‘付账,时代就永远无法结束。”这是诗評家对欧阳江河的期待,也是欧阳江河诗歌写作的经典意识在诗评家那里引起的共鸣。一切尚在路上,但诗人的努力目标也许并不仅仅是经典,因为对欧阳江河来说,“诗歌意味着我的一个存在方式。”[14]也就是说,朝向经典毕竟是一种功利性的考虑,而诗对于诗人来说却是一种来自生命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江河朝向经典化的写作,作为面向未来的存在,终究不过是一种姿态。
注释:
[1]杨厚均:《经典化:一种姿态》,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01期。
[2]唐晓渡,王家新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3]陈超:《欧阳江河——精神肖像和潜对话之一》,诗潮,2008年,第1期。
[4][5]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站在虚构这边》,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
[6]傅小平:《欧阳江河:我的写作要表达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文学报,2013年1月31日,第003版。
[7]徐敬亚,孟浪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8]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站在虚构这边》,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6,87页。
[9]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写作·站在虚构这边》,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3,84页。
[10]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12][13][14]王辰龙:《消费时代的诗人和他的抱负——欧阳江河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付玉东 新疆库尔勒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育学院 8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