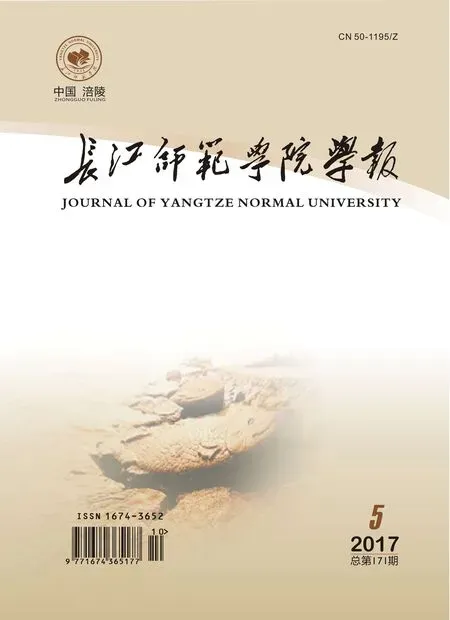刘恭冕“广经说”初探
张超凡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刘恭冕“广经说”初探
张超凡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晚清学者刘恭冕在历代“经目”衍变的基础上提出“广经说”,将若干史书与子书纳入“经书”范畴,并简要介绍了此说与其他“广经”的不同。这一理论改变了传统的“经”的涵义,扩大了“经”的范围。“广经说”一方面表明传统经学发展至此时已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代学者在治经上“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的趋势。
广经说;经学;刘恭冕
清代是经学复兴的时代,也是对既往成果进行清理总结的时代。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经学在乾嘉时期臻于极盛。嘉道以降,考据学褪去了极盛时期的光芒,其逃避现实、埋头考据的弊病遭到学界的猛烈批判。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考据学弊端的显露,使得学风为之一转,清初学者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又开始逐渐兴起。以扬州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治经不囿于考据学专于一经的路径,摒弃了其佞古、繁琐的弊病,提出了“通经”“通儒”的理念,形成了“能见其大、能见其通”[1]11的治学风格。作为扬州学派后学的刘恭冕,秉承学派学风和家学传统,提出了“广经说”。本文以刘恭冕的“广经说”为例,拟就“广经说”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及其意义与评价等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广经说”的产生
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历代“经目”[2]不尽相同,有“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说法。因此,历代“经目”的衍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六经”一词最早见于 《庄子·天运》,指 《诗》《书》《礼》《乐》《易》《春秋》。因 《乐》经失传,故汉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七经”之说见于东汉,是将 《论语》 《孝经》与五经并列,称为“七经”。唐太宗贞观年间,孔颖达、贾公彦依旧注撰定 《五经正义》,即 《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后又增撰 《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4部经疏,与前5部 《正义》并称为“九经”。唐文宗时,“开成石经”有“经目”12种:《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 《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宋代的“九经”是指 《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和 《孟子》。此外,宋朝时“经目”产生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变化,其一是将 《孟子》与开成石经的“十二经”并列,成为“十三经”;其二是因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合刻本的“十三经注疏”,流传于世。从此,“十三经”之名便确定下来。
到了清代,“经目”又几经变化。康熙朝御纂7经:《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乾隆初年,惠栋与纳兰性德都以“九经”为经目”,但具体篇目上略有不同:除 《易》《书》《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论语》8种典籍外,惠栋增 《公羊传》;纳兰性德则加入 《孝经》《孟子》《四书》3书,并将“三礼”合一,称 《三礼》。戴震的 《七经小记》则取 《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嘉庆年间,学者沈涛提出“十经”说,他认为应取“五经”“五纬”合称“十经”。后来,沈涛的老师段玉裁又提出“二十一经”的说法,将“十三经”与 《国语》《大戴礼》《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8书相合,合为“二十一经”。龚自珍反对段氏的“二十一经”之论,提出“六经正名”之说,其“经目”为:《诗》《书》《礼》《乐》《易》《春秋》。
“经目”的变化不仅体现着“经”与“经学”在传统的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演变,而且体现出各个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价值追求的不同。“广经说”的出现,除经学自身的因素外,学风的转变、知识范围的扩大以及诸子学的兴起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前文所述历代“经目”的衍变表明“经学自一开始就是开放性的学术”[3]22。自先秦至清代,伴随着经学的发展,“经目”也不断增加,这一变化过程已经昭示了经学是一种具有极强“开放性的学术,而不是封闭的、排他的学术”[3]22。此外,经书内容广泛,这就使得经学家治经的视域十分开阔,可以做各种探索与研究。再者,经学自身所具有的经世的精神,因不同时期所面对的问题不同,经学家们所表现出的经世精神也各有所异。经学自身的开放性、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经世的精神,是清代后期“广经说”出现的内在原因。
从外部环境看,嘉庆至道光年间,清朝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这就使得自康熙朝以后沉寂多年的“经世”思潮再度崛起。在乾嘉时期处于极盛的汉学在此时已步入补苴缀拾的死角,其弊端亦逐步突显:学者多为考据而考据、为经学而治经学;对章句考据太多,义理发挥较少,往往一字之证,博及万卷。当时士人多以考证为尚,以旁征博引为荣。这种埋首于故纸堆的繁琐考证已无法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汉学在发展到高峰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一些士人在批判汉学的同时,倡言改革,力主义理、考据、词章之学,要求恢复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由此,一批学者将汉学的“实学”由经学衍及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子百家、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
梁启超在论述清代经学著作时曾言:“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阮氏 《皇清经解》、王氏 《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4]179仅私人编撰的两部 《经解》所包含的经学著作已有数百种,2 000余卷。若再加上清代官方组织编修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巨著,那么清代经学著作的数量已不可计数。此外,《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中还收录大量的史学、诸子学、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再加之考据学家们对经典诠释的新的成果的出现,在为清代中后期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的同时,也为诸子学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乾嘉学者以考据之法遍治群经。但由于缺少更多的材料,学者遂将研究的焦点转向诸子学说,引诸子以证经。由此开始了对诸子之书的普遍整理,进而引发了诸子学的兴起。嘉道以后,诸子学的研究逐渐活跃起来。此时学者们依旧沿袭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以文献考证的方式研究诸子之书,论及的范围包括 《韩非子》《吕氏春秋》《荀子》等。以 《荀子》为例,自清中期汪中著 《荀卿子通论》为 《荀子》作阐释以后,《荀子》受到学者的关注。此后又有顾广圻著 《荀子异同》、刘台拱作 《荀子补注》等。至王先谦作 《荀子集解》,是为 《荀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些有关 《荀子》的著述,对后来的 《荀子》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广经说”的主要内容
刘恭冕 (1824—1884)字叔俛,号勉斋,江苏宝应人,清代经学家刘宝楠次子。他少时受学于叔祖刘台拱,后随父刘宝楠生活于知县任所。刘恭冕初治毛诗,未就;后续补其父 《论语正义》手稿付梓;晚年又治 《公羊》,“发明新周之义,盖父子均接近今文家矣”[5]1880。其学术素养如其族弟刘岳云在 《族兄叔俛事略》中所言:“所学,于训诂文字,辨核极精确,尤喜寻绎微言大意,无主汉奴宋之习。”[6]593《清史稿》中记载其“守家学,通经训”[7]13291。刘恭冕治经深受家学熏陶:其叔祖刘台拱治经范围广泛,义理考据兼采,重视考证训诂,反对虚词臆说,著成 《论语骈枝》;父亲刘宝楠知识广博,视野开阔,完成 《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论语正义》。刘恭冕受深厚家学底蕴的浸染,造就了他独特的治经理路。除承其父未竟之业续成 《论语正义》外,刘恭冕还有撰有 《广经室文钞》《何休注训论语述》《论语正义补》等。
刘恭冕生活于清代中期稍后的咸丰同治年间,学术研究方法基本继承了乾嘉汉学的风格,治经思想更不乏创新之处。而他所提出的“广经说”正是其治经思想创新的体现。其文集 《广经室文钞》中“广经室文记”一文记述了刘氏的“广经说”:
广经室者,家君授恭冕读书之所。既以所闻思述前业,而旁及百氏,凡周秦汉人所述遗文逸礼,皆尝深究其旨趣,略涉其章句,欲撰为一编,以附学官、群经之后,而因请于家君为书以榜之,复私为之记。曰:今世治经者言十三经尚矣。金坛段若膺先生谓宜以 《国语》《大戴》《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为“二十一经”。嘉兴沈匏庐先生又以五经合诸纬书,取周续之之言为“十经”,若膺先生为之记。冕谓纬书杂出附会,不足拟经,而 《史》《汉》《通鉴》又别自为史,不比 《国语》之与 《左氏传》相辅以行也。冕则取《国语》《大戴礼》《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说文解字》,而益以 《逸周书》《荀子》入焉。《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此明是百篇之遗,与张霸、梅赜 《书》不同。《荀子》源出圣学,当时与孟子并称,故太史公以孟荀合传;《汉书·古今人表》孟荀同列大贤;《艺文志》孟荀并列诸子,而 《劝学》《修身》《礼论》《乐论》《大略》《哀公》诸篇,大、小《戴记》并见称述,则信乎为圣门大义之所系矣。[6]575
“广经室者,家君授恭冕读书之所,”可见刘恭冕的“广经说”的形成一方面受到了其父刘宝楠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提到这一理念与经学家段玉裁有关。他赞同段氏的“二十一经”说,但对段玉裁的学生沈涛所提出的“十经说”不甚同意。他认为,“纬书杂出附会”,不应入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别自为史”,《国语》与 《左传》“相辅以行”,故应将 《国语》入经。 《逸周书》为周史所记;《荀子》为圣门后学,《史记》《汉书》将孟荀并称,因此 《荀子》《逸周书》应入经。刘恭冕的“广经说”中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将 《荀子》纳入“经”的范围。
荀子与孟子同为孔子以后儒家的两位大师。但至宋代,《孟子》被尊为儒家经典,而 《荀子》则被视为孔门“异端”,长期受到儒学正统学派的排斥。清代中期,学者汪中著 《荀卿子通论》,对 《荀子》做阐释,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8]集部·别集类,415。此后,《荀子》开始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刘恭冕将 《荀子》入经,理由有二:一是继承了汪中的“荀子传经论”,并进一步发展;二是借其父刘宝楠之言为荀子的“性恶论”正名。
刘恭冕以 《经典序录》《汉书》《盐铁论》《儒林传》等书中有关荀子的记载,结合汪中 《荀卿子通论》中所言,认为荀子传三家 《诗》 《左传》与 《谷梁传》。此外,荀子所学,长于 《礼》,《二戴礼》中数篇均出自 《荀子》。刘氏以为曲台之 《礼》,是荀子余裔。据此可知,《二戴礼》也由荀卿子所传。因而刘恭冕力赞荀子传经之功,甚至提出“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6]576的说法。
对于荀子的“性恶论”,刘恭冕引用其父刘宝楠 《戴筠帆侍御文集序》中所述为荀子正名:
乃世之论者只以 《性恶》《非十二子》为荀子诟,不知性恶乃感时之激论,家君作 《戴筠帆侍御文集序》曾发明之。大旨谓性恶乃说当时之人,篇中屡明言,今人可证其云善者伪也。“伪”与“为”同义,为善即孔、孟为仁求仁之学,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则言“性善”。惟性相近而乃得为善也,荀子见当时之人多恶少善,故以“性恶”为言,而求其反恶而归于善,不能无待于人,为此感时之激论,非谓古今人性皆不善也。[6]576
刘氏父子认为荀子的“性恶论”乃是“感时之激论”,是对时人的看法,并非荀子本意。而且荀子的“性恶论”虽与孟子“性善论”相悖,但二者是孔子“仁学”的两个方面,不能因此而批判“性恶论”,更不能抹杀荀子传圣门之学的功劳。刘宝楠还举出韩愈、王阳明的例子来说明荀子立言之难:唐韩文公作 《原道》,后人多有所訾议;明王阳明提出良知之学,儒者多斥之。由此,刘恭冕 《荀子》入经的理念渊源于刘宝楠。
在文末,刘恭冕还认为 《吕氏春秋》中有关礼乐、农耕的记载,以及贾子 《容经》中诸篇可“羽翼群经”“如此而古经略具”[6]576。可见其“广经”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前文所述的经典。刘恭冕以此扩充经典范畴,反映出其宽阔的学术视野。
除 《广经室记》外,在 《致刘伯山书》一文中,刘恭冕也论述了“广经说”,但与 《广经室文记》中所列篇目略有不同:
《大戴礼》中多记孔子、曾子之语,其警言粹义多与 《表记》《大学》相出入,故 《汉志》、《隋志》咸以 《大戴记》与 《小戴记》并列。今人只知习 《小戴记》,而读 《大戴记》者千不得一。此当补列为经者一也。荀子亦传孔门之学,遍治群经。西汉之学,皆荀子一脉之传,其功不在孟子下。后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并弃其书,不使与孟子并列。此当补列为经者二也。太史公作 《史记》,备列古今兴废之迹,以论其得失,而“八书”尤足与 《礼经》相辅。盖史公本治 《易》《书》之学,俨然西汉之经生,班氏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斥之,非通论也。此当补列为经者三也。孟坚 《汉书》,为断代作史者之祖。后世史家,咸禀其法。故后世皆以“马班”并称。此当补列为经者四也。温公 《通鉴》,备列古今之政事,乃古论治之书也。其所论断,悉取法于《春秋》,足以善善恶恶,儆戒百世。此当补列为经者五也。《楚辞》为词章之祖,然讽一劝百,怨而不怒。史公称 《离骚》一篇,兼有 《小雅》《国风》之旨,可谓知言。此当补列为经者六也。《说文解字》集小学之大成,古今以来,欲通经学,悉从小学入手,而此书实经学之七也。《九章算法》,亦为西周旧籍,乃商高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书数二端列于六艺,而此书实为算法之祖。此当补列为经者八也[1]49-50。
两文相较,《广经室记》侧重于对 《荀子》入经的解释,而 《致刘伯山书》中则较为详细地对“入经”的典籍做了理论阐述:《大戴礼记》中多为孔子、曾子之言,且 《汉志》 《隋志》均将大、小 《戴记》并列,故 《大戴礼》应入经。三部史书, 《史记》论古今兴废得失,“八书”又可与 《礼经》相辅;《汉书》为断代体史书之发端,后世史家皆循其体例; 《通鉴》取法于 《春秋》,备列古今政事,用以儆戒百世。因此三者均可以补列为经。《楚辞》《说文》与 《九章算法》,一为词章之祖,一为小学之大成,一为算法之肇始,其意义不言自明,故此三书也应入经。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刘恭冕在对待“入经”篇目的态度上曾有过反复:先否认“史书”入经,后又赞同;且其个人文集 《广经室文钞》中并未收入 《致刘伯山书》一文。虽仅是个别书目作了调换,但大体不殊,均体现了刘恭冕“广经”的理念。刘恭冕在最后强调了“广经”的目的和意义:若能家弦户诵,则人人皆可为“通儒”,其目的是为了建立所谓“通儒”的形象。这不仅体现了其作为扬州学派后学传承“通核”治学的理念,也表现出其继承先辈治学遗规、浸染家学的传统。
与传统的十三经相比,刘恭冕的“广经说”不仅仅是个别经目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其中增加的子史诗词、天文历算等书籍已不在传统的儒家经典的领域内。而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史书入经”和“以子为经”。
刘恭冕将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国语》四部史书纳入经的范围,表明他认为史书应有经。从经史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六经”之中的 《春秋》是最接近后世所谓的“史书”著作;另一方面,经书本身就包涵丰富的历史讯息,是研究古代历史不能不阅读的典籍。所以,有学者提出经书即史书的说法,如明代王阳明的“五经皆史”、清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由此可见经学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刘恭冕的“以史入经”也是对“五经皆史”“六经皆史”的进一步发展。
诸子学历来被视为经学的附庸。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中 《诸子略》篇所列诸子十家,在介绍了各家源流的同时,也点明了诸子与经的关系:诸子学渊源于六经,而且可以弥补经学的不足。虽然二者关系紧密,但依班氏所言,诸子之学仍是经学的流裔。此后历代学者均秉持这一传统。刘恭冕的“以子为经”,是对历代以来“经为主而子为辅”的尊经理论的突破。在重新定义“经”的内涵的同时将子书融入进来,这是刘氏“试图重建经子一体的经书系统”[9]的尝试。
三、“广经说”的意义与评价
刘恭冕的“广经说”表明他在经学研究方面要求重视史学、小学、文学及算学等实用科学,其目的是“要建立起新的通儒形象。”[10]他的这一“通儒”之理想,确实对当时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刘氏的“广经说”重点在于把史书与子书纳入经的范围,突破了“子史为经之附庸”的传统观念的桎梏。如他主张将 《荀子》入“经”,就体现了他力图改变儒家学派一直以来尊孟抑荀、重 《孟子》轻 《荀子》的现象,希望揭示荀子的传经之功,从而恢复儒学“孔荀”学派的传统。其“广经说”突破了狭隘的学术视野,丰富了经学研究各方面的内容,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治学倾向,反映了对当时专经研保守僵化、缺乏融通之弊的补救。以刘恭冕为代表,晚清时一些学者在面对传统的知识范畴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有利于拓宽学者的视野和学术研究的范围。与传统的固守“六经”的学者不同,他们力图将经学、史学、子学、小学、历算学等融汇贯通,以达到他们提倡的“通核”的目的。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广经说”这一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矛盾。譬如“《荀子》入经”“《楚辞》入经”就造成了与传统经学理论的冲突,它混淆了“六经”这一传统经学的基础,依龚自珍言即“以传为经,以记为经”[11]37。因此,一些学者对“广经”这一说法不甚同意。康有为强调孔子所作只有“六经”,后世所谓“十三经”“十四经”乃是“僭伪纷乘,经名谬甚”[12]128;廖平则以“六经”合“六艺”为十二经[13]210。近人周予同、张舜徽二位先生也不同意“广经”的观点。周予同先生反对“二十一经说”,他认为“现在依普遍的习惯,以十三经为限。十四经的名称不甚普遍”,“二十一经说”则不过是“个人的主张而已”[14]15。张舜徽主要从后人读书的角度来阐释对“儒家经传名数”的看法。他提到刘恭冕服膺段玉裁的“二十一经说”,并“名所居曰广经室,为之记以张之”。虽然篇目略稍异,但“意无不同”。张先生认为:“古初本无经名,虽后世,增为十有三……繁缛无以复加,早已成为陈迹,于后世复何所用?读之无得,不读何损。”依张先生所言,古时并无经名,乃是后人所强加。若于后世无用,不如不读。他进一步指出:“以不切于今用,虽早列在经,固犹可废也。昔人恒以经名崇高,不敢增减。徒徇虚号,夫亦奚益哉?若夫应读之书甚广,正不必拘泥于是经非经也。”[15]54可见就读书治学而言,张先生不甚赞同“广经说”。
总的来说,“广经说”是学术发展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的学者试图冲破传统经学研究的藩篱,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倾向。刘氏的“广经说”扩大了传统经学的概念范围和内涵,尤其是纳入史学、小学、算学、文学等类目入经,虽与传统的“六经”“十三经”相抵触,但对于传统经学来说是一种进步。正如梁启超先生评价清代学术之进程时所言:“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故,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16]9刘恭冕的”广经说”正体现了“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的趋势。
[1]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4.
[2]程苏东.“经目”释论——以经学史为论域[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41-48.
[3]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M].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22.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79.
[5]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80.
[6]刘台拱,刘宝树,刘宝楠,等.宝应刘氏集[M].秦跃宇,张连生,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6.
[7]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91.
[8]续修四库全书(第1 46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15.
[9]吴根友,黄燕强.经子关系辩证[J].中国社会科学,2014(7):26-49.
[10]张寿安.从“六经”到“二十一经”——十九世纪经学的知识扩张与典范转移[J].学海,2011(1):146-163.
[1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王佩诤,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37.
[1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8.
[13]廖平.廖平全集[M].舒大刚,杨世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10.
[14]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外二种)[M].朱维铮,编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5.
[15]张舜徽.爱晚庐随笔[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4.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朱维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Liu Gongmian’s“Guangjing Theory”
ZHANG Chao-f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9,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holar Liu Gongmian put forward his own“Guangjing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classics” of the past dynasties,incorporated into the category of“classics” several historical books and works of ancient philosophers other than those of Confucius,and briefly explain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theory and other“Guangjing” theories.This theory changed the meaning of traditional“classics” and enlarged the scope of them.“Guangjing Theory”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classics had changed at that time,but also reflects that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s’trend“to restore the ethos of the early Qin period and write commentaries for all classic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minds”.
Guangjing;study of classics;Liu Gongmian
K249.3
A
1674-3652(2017)05-0115-05
2017-04-25
张超凡,男,安徽宿州人,主要从事文献学与国学研究。
[责任编辑:庆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