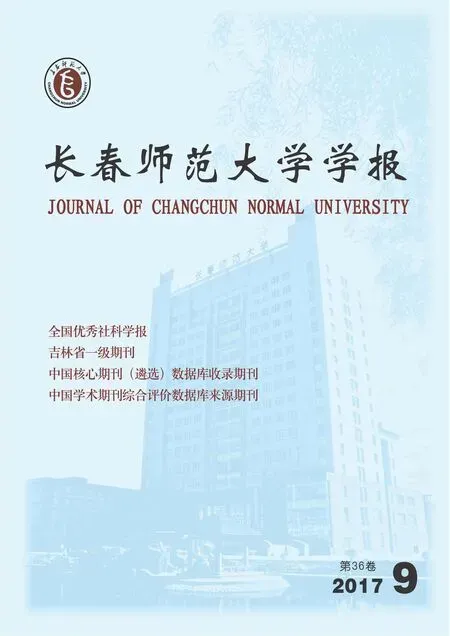唐前喜雨诗及其情感旨归
王 雪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唐前喜雨诗及其情感旨归
王 雪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喜雨诗是以因久旱逢甘霖的喜悦心情作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作为农事诗的一种,喜雨诗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和脉络,是反映农业发展水平和农业文明进程的一面镜子。“雨”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在唐宋时期达到巅峰,从一种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的自然现象发展为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抒情意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审美价值。喜雨这种情感模式多被诗人运用,是因为它能给人以喜悦和希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喜雨诗数量虽然不多,却为后世喜雨诗的创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唐前;喜雨诗;奉和诗;关心民瘼诗;祈雨诗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讲到了情与景的关系问题,提出外界景物对人思想感情的影响。“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象来举例,说春天气象万新,所以人们会有欢乐舒畅的感受;夏天艳阳烈日,会令人感到烦闷躁动;而秋天气象萧森,人们的情绪往往阴郁深远;寒冷飘雪的冬天,则会使人变得严肃深沉。可以看出,不同的景物会带给人不同的审美体验,文辞便随情感而产生。雨作为大自然中常见的意象之一,往往会根据文人不同的心境生发出不同的情感。当久旱不雨、忽降甘霖时,对雨的描述往往寄托了诗人的喜悦之情;相反,当久雨不晴、出现洪涝时,诗人则经常抒发苦雨的忧愁感情。
中国诗歌虽肇始于《诗经》,但是喜雨诗作为特殊的诗歌题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在诗坛,虽然数量不多,却能够反映出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据笔者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共出现了九首喜雨诗,分别是曹植《喜雨诗》、谢庄《喜雨诗》、谢惠连《喜雨诗》、鲍照《喜雨诗》、谢朓《赛敬亭山庙喜雨诗》、庾肩吾《从驾喜雨诗》、魏收《喜雨诗》、庾信《奉和赵王喜雨诗》及《和李司录喜雨诗》。笔者通过对这九首诗的整理与分析,将其分成奉和诗、关心民瘼诗、祈雨诗三类,并对这三类诗歌进行深入探究,以期找寻出唐代之前喜雨诗的发展轨迹及规律。
一、奉和诗
奉和作为一个独特的题材出现,多与应制诗并称。然而“应制诗是宫廷御用文人应帝王或太子、诸王之命而创作的诗歌,御用性是应制诗的本质特征,应命而作是应制诗的外在表现。”[1]奉和诗是文人士大夫和王公贵族之间的一种自发性创作,可以说是群体间进行的文学交流活动,如鲍照《喜雨诗》、庾信《奉和赵王喜雨诗》及《和李司录喜雨诗》。
鲍照在诗文方面较为突出的贡献是咏物题材,他擅于把无形的事物通过侧面描写或者烘托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被描述之物在读者的头脑中形成具体鲜活的画面。有《喜雨诗》:
营社达群阴,屯云揜积阳。河井起龙蒸,日魄敛游光。
族云飞泉室,震风沉羽乡。升雰浃地维,倾润泻天潢。
平洒周海岳,曲潦溢川庄。惊雷鸣桂渚,回涓流玉堂。
珍木抽翠条,炎卉濯朱芳。关市欣九赋,京廪开万箱。
无谢尧为君,何用知柏皇。
鲍照选择独特的角度和艺术表达方式,既吟咏出雨这种无形的东西的外在形象,又传达出了雨的内在精神气韵,足见其咏物诗的高超水准。作者力求突出“喜雨”中强烈喜悦的感受,故将目光投向被这场雨滋润的事物以及随之产生的想象。首先用“群阴”“屯云”等词表现一种黑云压城城欲雨的视觉感受;接着用“泻”“洒”等字体现出雨势之大,山川海岳都受到雨的洗刷;继而连用四个对仗句,从实虚两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喜雨图”。其中“珍木抽翠条,炎卉濯朱芳”是实景描写,运用动词“抽”“濯”以及形容词“翠”“朱”,不仅表现出雨后万物竞相生长的勃勃生机,还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关市欣九赋,京廪开万箱”则是虚景描写,是由实入虚生发出的联想。这两句中用到了四个典故:“《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周礼·天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论衡·程材篇》:‘京廪如丘,孰与委地如坻也’;《诗经·小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2]典故的运用使喜雨和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联系起来,大大增加了所咏之物的厚重感和历史感。
庚信是我国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生于一个政权更迭频繁且混乱的时期,在南梁度过了悠闲的前半生,却在北朝走完了他哀伤的后半生。他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自觉地吸纳了南北文化的精华,有了较高的诗歌造诣。庾信的两首喜雨诗虽然都是奉和之作,但与南北朝时期其他诗人的喜雨诗有很大不同,其思想内涵和实用性上皆有所提升,可以说是在保持审美意趣的前提下更多地倾向于实际功用。
《奉和赵王喜雨诗》:“投壸欲起电,倚柱稍惊雷。白沙如湿粉,莲花类洗杯。”“赵王”即宇文招,宇文泰第七子,封赵王,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庚信体,词多轻艳。”[3]庾信现存作品奉和酬答他的最多。
《和李司录喜雨诗》曰:“纯阳实久亢,云汉乃昭回。临河沉璧玉,夹道画龙媒。离光初绕电,震气始乘雷。海童还碣石,神女向阳台。云逐鱼鳞起,渠随龙骨开。崩沙杂水去,卧树拥槎来。嘉苗双合颖,熟稻再含胎。属此欣膏露,逢君掞藻才。愧乏琼将玖,无酬美且偲。”写喜雨之情。“李司录”即李昶,因宇文泰赏其才,故赐姓宇文氏。历任“内史大夫”“中外府司录”等,因此还被称作“宇文内史”“李司录”。今存四首他们二人互唱互答的诗歌。这首诗是为明帝安排活动而作的奉和诗,诗歌一开始写因连日不雨导致大旱之年,接着写电闪雷鸣大雨将至,最后写君臣欢喜迎接这场大雨,并预示因为雨的到来庄稼会丰收。这首五言律诗对仗工整,且化用了很多典故,足见李司录文学素养之高。
庾信的这两首诗都写出了对久旱不雨的苦恼及对天降甘霖的喜悦,喜雨情感成为了君臣同乐的诱因。因此,这两首诗可谓喜雨诗中奉和题材的典范之作。
二、关心民瘼诗
这类喜雨诗大多抒发的是诗人对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以及天降适时雨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而产生的欣慰之情,反映出诗人对农业及农民生活的关心。这类诗包括曹植《喜雨诗》、谢庄《喜雨诗》、谢惠连《喜雨诗》、魏收《喜雨诗》。
曹植《喜雨诗》作于魏明帝太和二年,是其后期作品,更是诗人连遭流徙、饱尝窘困之后的产物。他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邑,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4]《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六引《喜雨诗》有序云:“太和二年大旱,三麦不收,百姓分为饥饿。”[5]这篇序虽然不全,却能让我们对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有一定的了解。《魏书》中对太和二年五月大旱有明确记载,故此诗的创作确与旱灾有关。因久旱无雨,庄家颗粒无收,百姓忍受饥饿,此时突然降雨让曹植感到极为振奋,他带着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这首《喜雨诗》。“天覆何弥广,苞育此羣生”,表明诗人的看法,百姓离不开粮食,而粮食有无收成又得看老天。“惠之则滋荣”一句则是说老天下雨,庄稼有了指望,老百姓也就有了指望。“嘉种盈膏壤,登秋毕有成”两句是全诗的精髓,点明诗人“喜雨”的善良动机。可以说,《喜雨诗》直接而强烈地抒发了曹植体恤民生疾苦的思想感情。然而诗人把百姓的饥饿仅仅归咎于天旱,并未看出真正导致人民困苦的是阶级压迫和严重的剥削,实为时代的局限性。
再看谢庄《喜雨诗》:“燕起知风舞,础润识云流。例泉承夜湛,零雨望晨浮。合颖行盛茂,分穗方盈畴。”这首诗虽然短,但言简意丰、语短味浓。首先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其次抒发了作者的胸怀。冷冽的泉水在夜晚静谧而澄清,又细又慢的小雨蒙蒙然洒下来,清晨可以看见漂浮在水上的木头。最后两句点题,作者喜雨是因为看见雨后禾苗一根茎上长出两股穗子,以此生发出联想,似乎看到麦穗充盈在田地上的大丰收景象。可以说,谢庄以“喜雨”命题,既表述了自己“有志于民”、关怀民瘼的心情,也隐含“公待则心喜”的“颂圣”之意。
谢惠连《喜雨诗》一诗中,多化用典故,表现出诗人对天的崇拜、敬畏以及对雨的喜爱之情。诗曰:
朱明振炎气,溽暑扇温飙。羡彼明月辉,离毕经中宵。
恩此西郊云,既雨盈崇朝。上天愍憔悴,商羊自吟谣。
诗中的憔悴代指穷困潦倒的劳动人民。诗歌写出久旱之后一场及时雨让人们免除灾害而产生的无限欣喜之情,是一首表现对劳动人民同情的作品,而且出自于一个贵族青年之手,实在难能可贵。
魏收《喜雨诗》:“霞晖染刻栋,础润上雕楹。神山千叶照,仙草百花荣。泻溜高斋响,添池曲岸平。滴下如珠落,波回类璧成。气调登万里,年和欣百灵。定知丹甄出,何须铜雀鸣。”魏收这首诗运用“兴”的手法,诗作开篇并未直接对雨进行描写,却描写了夕阳。第五句话锋一转,用了“泻溜”“添池”等词描述了一场突然而来的雨,这种写法更加突出作者对这场及时雨的喜爱之情。
三、祈雨诗
我国作为农业文明古国,农业的丰收与否决定国家的兴衰。而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古代社会,天气好坏尤其是雨水是否充沛直接决定庄稼是否丰收。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农业生产要依靠农时和天时,民间便形成祈雨习俗。经过后代的不断完善,逐渐发展成有固定仪制的祈雨文化。喜雨诗中有一类便是关于祈雨题材的,这些诗歌或叙写官方祈雨安抚民心的宽慰或抒发祈雨之后降雨的喜悦,包括谢朓《赛敬亭山庙喜雨诗》、庾肩吾《从驾喜雨诗》。
谢朓的这首诗写作略后于《祀敬亭山庙》[6]。在敬亭山的庙中举行祈雨祭祀仪式后,天果然降雨。古代称酬神为“赛”,清代学者郑珍指出汉代之前作“塞”,六朝时才作“赛”。故从诗题“赛敬亭山庙祈雨”可知此诗为作者喜雨谢神而作。诗曰:
夕帐怀椒糈,蠲景洁膋芗。登秋虽未献,望岁伫年祥。
潭渊深可厉,狭邪车未方。朦胧度绝限,出没见林堂。
秉玉朝群帝,樽酒迎东皇。排云接虬盖,蔽日下霓裳。
会舞纷瑶席,安歌遶凤梁。百味芬绮帐,四座沾羽觞。
福被延民泽,乐极思故乡。登山骋归望,原雨晦茫茫。
胡宁昧千里,解佩拂山庄。
诗的前两句,“夕帐怀椒糈,蠲景洁膋芗”中的“椒糈”“膋芗”为祭品,并分别用了动词“怀”“洁”,足见人们对这次祭祀活动的重视,对祭品恭敬对神灵敬畏。“登秋虽未献,望岁伫年祥”,是说“去年”秋天丰收虽然没有献祭,但仍希望年岁吉祥。下面几句中,用“秉玉”“樽桂”“会舞”“安歌”等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向众神进献美玉、美酒、美味以祈求风调雨顺的图画。诗人因喜雨赛庙而想到了故乡也恰逢春旱。诗的最后,写诗人登山纵目远望归乡之路,点出喜雨之情。
庾肩吾《从驾喜雨》一诗曰:“湿风含酒气,阴云助麦寒。典农欣受职,治粟喜当官。复此随车雨,民天知可安。”这首诗先写祈雨的过程,再写天降甘露,最后抒发欢喜之情。较为难得的是,此诗关注到了民生疾苦。诗人的喜更多的是因为这场雨给百姓带来了安心,这是此诗值得称道的地方。
四、结语
唐前喜雨诗数量虽然不多,却为唐代及其后喜雨诗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唐代才出现了喜雨诗的创作热潮。唐代的喜雨诗大多沿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传统,有一些奉和应制的作品,但更多的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因体恤民生疾苦而产生的喜雨情感,这种喜悦是自发的、饱满厚重的情感体验,因此有不少佳作问世。
[1]李玲.唐代应制诗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
[2]丁福林,丛玲玲.鲍照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541.
[3]令狐德芬.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第十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1:202.
[4]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798.
[5]虞世南.北堂书钞[M].北京:中国书店,1989:556.
[6]孙兰.谢朓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4:268.
I206.2
A
2095-7602(2017)09-0097-03
2017-06-23
王雪(1987- ),女,讲师,博士,从事唐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