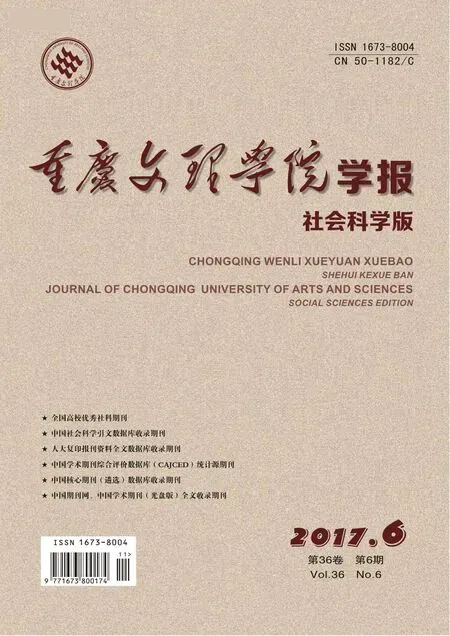中国第四代女性导演电影中的婚姻问题表达
任璇宇
(弗林德斯大学 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阿德莱德 南澳洲,澳大利亚5043)
文化·艺术·传播
中国第四代女性导演电影中的婚姻问题表达
任璇宇
(弗林德斯大学 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阿德莱德 南澳洲,澳大利亚5043)
中国第四代导演中的女性导演是数量激增的一代,她们进入主流电影界并拍摄了大量成功的影片。但是,中国女性导演受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以及女性文学发展的约束非常大。中国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使得第四代中国女性导演可以就中国女性主义运动早期(五四运动时期)所探讨的女性出路问题进行解答,即女性有能力脱离家庭独自生活。但是,中国女性导演极其有限地触及了社会中限制女性最多的领地“婚姻”。对于婚姻问题的躲避,是由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以及女性文学发展的天然缺陷导致的。
女性主义电影;第四代导演;婚姻
一、女性地位的上升与迷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在法律和社会层面的男女绝对平等阶段。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的颁布,中国女性在社会范畴中拥有了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时至今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领先地位。此时,女性在文化艺术产业中也开始大量出现。女性艺术家的数量较之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了大幅提高,甚至电影产业这种以男性为绝对主导产业中也开始出现女性导演的身影。王苹作为一名女性导演进入主流电影导演范畴,成了第三代导演中坚实的一员。但是,王苹所指导的影片与大量第四代女性导演所指导的影片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表现的题材和拍摄手法与同时期男性导演没有任何差异[2]。这样一种无性别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男性化的艺术风格,成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量女性导演所遵循的表达手法。
在经历了电影业几乎停止的“文革”时期之后,中国电影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导演数量在世界范围都引人注目。80年代,中国能够独立执导影片的女性导演就超过30名,在世界范围中,仅次于苏联[3]。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对中国影片中男女关系的表达一直处于一种避而不谈的状态,8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反而逃离了劳拉穆尔维所提出的“男性凝视”[4],给了女性导演一个回归女性本身的机会。程式化的好莱坞式影片风格以及物化女性的影片类型并没有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中出现。与此同时,“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坛兴起,并逐步影响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对于“电影语言的现代化”[5]所推动的大陆“新电影”向前发展,使得纪实手法在中国电影界逐步被接受及使用。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电影中更多地折射出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困惑与迷茫。
不仅仅是在电影语言方面,而且在题材类型上中国电影较之以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社会及艺术(电影艺术)转型的时期,大量的影片,无论是男性导演影片还是女性导演影片,都将视角对准了女性。因为在社会中,哪怕是表面上男女绝对平等的社会中,女性依旧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仍为“女性”的女性。将视角对准最底层的女性更容易体现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对于一个人的影响。第四代的男性导演拍摄了大量以女性为主体的影片,例如谢飞所执导的《湘女萧萧》(1988)、《香魂女》(1993),黄健中执导的《良家妇女》(1985)等等一系列电影都是表现封建社会中女性在婚姻家庭中所遭受到的不幸待遇。可是这一切对于女性的表达并非是真正讲述女性困境的,而是正如戴锦华所指出“第四代的导演们将欲望与压抑的故事,将典型的男性文化困境移置于女性形象”[2]。
与男性导演形成对比的是,在第四代女性导演作品中,对于感情的探讨逐渐增加,而婚姻却开始缺失。这样的缺失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以张暖忻的《青春祭》《沙鸥》这类影片为代表的,结婚对象(男友)的死亡导致无法进入婚姻;第二类是由女性对于婚姻本身发出质疑的,例如史蜀君导演的《女大学生宿舍》(1983)和陆小雅导演的《红衣少女》;第三类是对于婚姻、爱情及两性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的影片,这一类影片中非常典型的是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女性电影”的由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1987)[6]。
这三类不同类型的女性导演的电影都反映了同样一个困扰女性的问题,女性是否应该进入婚姻这个“围城”?婚姻究竟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者抑或是寻求自由解放的当代女性为什么恐惧于婚姻本身?这样一个困惑不能单单从80年代这一时代限定中寻求答案,而是应该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中寻求历史根源。
二、第四代女性导演作品:对于“五四运动”所提出的女性问题的回答
在世界文化历史中,有两位女性对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位是花木兰,另一位是娜拉。
在中国历史上,男女的界限并不是完全不可逾越。相较于欧洲中世纪严苛的男女区别,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超脱性别本身而存在的女性神话——花木兰。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这样一个特殊的性别救赎方式,成了现当代中国女性一种常见的自我救赎方式。从身着男装的秋瑾到“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中国女性主义发展道路似乎呈现了一种“反女性”的趋势。“女性”这个词语成了被中国女性主义所歧视的本体,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在努力逃脱出“女性”之外,从“男性”这一性别身份上取得救赎。
而《玩偶之家》被引入中国之后,娜拉所塑造的一个摆脱母亲、女儿、妻子身份的女性形象正好撞上了当时中国女性主义者们的需求。娜拉在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心目中成了新一任的“花木兰”。逃脱婚姻,成了中国女性主义者的一大诉求。而与此同时,鲁迅先生对于“娜拉出走之后”的发问似乎成了为中国女性主义者敲响的一个警钟。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中国女性主义运动的迅速展开,中国女性主义运动彻底沦为“他者”的解放运动。中国女性又再次向历史中的偶像“花木兰”寻求帮助,一场带着浓重“去性别化”色彩的中国女性主义发展拉开序幕。
20世纪80年代到来,中国社会以及经济结构开始改变,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同时,整个世界格局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Hobsbawn)所定义的“短二十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接近终结,世界历史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改革和急剧变化的中国突然开放于一个新思潮涌动、新格局形成的世界结构中,全部原有的社会意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受到了来自这个“新世界”的冲击。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环境下,中国开始了“重新社会性别化”(regendering)[7]。
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第四代女性导演的作品呈现了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改变过程。所以,第四代女性导演的作品是在对女性身份的质疑以及对“娜拉”所处地位的忧虑中向前发展的。除了王好为导演的《瞧这一家子》(1979)这样的完全没有女性导演色彩的影片,其他女性导演的影片基本上都是对婚姻排斥的。而这种排斥就来源于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和女性文学中对于“娜拉”现象的过分重视而导致的,同时,这也是女性主义发展的一种缺失。
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控制力开始减弱。女性退休时间提前、私企的增加等因素大幅增加了女性的就业难度,一定程度上逼迫女性回归家庭。而此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女性的可支配时间其实是大幅增加的。这两点使得婚姻中的女性面临一个困境,需要融入社会却被社会拒绝。《红衣少女》中的母亲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处于困境中的女性,两个女儿都长大了,想重新融入社会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社会中需要的是花木兰式的女性,而“母亲”所代表的最普通的女性就变成了宛如小丑一般的角色,成了通情达理的“父亲”的反面形象。而母亲是怎么从一个知书达理,会写诗,会英文的知识分子女性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却并没有展现。
所以,这一时期的女性导演急于表现对婚姻的远离,她们嘲讽婚姻中的女性,希望在婚姻之外寻找到合适的爱情与生活。这是一种对于“娜拉”的解答,女导演们回答了娜拉离开婚姻之后的生活,为娜拉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出路。而对于大部分中国女性,尤其是普普通通的无法或不愿逃离婚姻的中国女性的生活应该是怎么,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导演们集体“失声”了。
在解答了鲁迅所提出的问题之后,中国女性导演们又有了新的问题,婚姻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拆解了婚姻就可以得到女性主义的答案。而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女性导演并没有给予回答,而是陷入了一种集体的迷茫。
三、悬而未决:并未在婚姻中寻求出路与答案的第四代女性导演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同时也禁锢了女性,妇女受到压迫主要是发生在家庭中。“家庭通过确立社会性别作用和按性别的劳动分工,使妇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8]。尤其是在由“娜拉”启蒙又深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影响的中国女性主义中,第四代女性导演对于家庭和婚姻的反叛可以视为是一种利用艺术对于社会大环境中的封建男权社会回归的一种抵抗。《沙鸥》中,沙鸥在未婚夫死后不顾身体伤残去追求自己事业的这种牺牲与毅力,甚至有一种无以名状的英雄主义色彩。沙鸥的性格本身娇气软弱甚至挑食,却在未婚夫死后不顾瘫痪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影片中似乎在展示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远离婚姻,如同一个独立个体一般存在。可是,这个看上去完全吻合我国女性主义需求的女性形象却仍需要男性的鼓舞(男友攀登珠峰的消息),而不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去汲取教训经验。拿到银牌后,沙鸥选择的是把奖牌丢入海中,她依旧是在逃避自己的失败,从男友的成功中取得营养。
再例如电影《女大学生宿舍》是对于婚姻的彻底否认。电影里面的台词直白露骨地否定婚姻,女主角匡亚兰说出了:“作为一个女性,要想被人家瞧得起,首先就要在事业上站得住。要有超强的自信心才行。”甚至直接地说出“选择贤妻良母……那她干吗来上大学呢?”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对于婚姻和贤妻良母的抨击的背景下,影片女主角匡亚兰的母亲却为了自保而选择抛弃婚姻成了整部影片的一个反面形象。
这一系列的影片都在解答鲁迅所提出的“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女性独立,自主,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让人羡慕的事业,她们可以轻易地拒绝婚姻,拒绝男性。而同时,在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此时的家庭结构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女性仍处于家庭受害者的位置。长时间处于婚姻中的女性必然变得如同《红衣少女》中的妈妈一样,唠叨、抱怨且势利。而男性,也如同《红衣少女》中的父亲一样,温和且有才学。传统思想中对于男女的社会定义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一时期的女性导演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色彩就变得软弱且没有说服力。她们依旧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赞赏未婚女性的才学,而不去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已婚女性发生转变。
而被喻为“当之无愧的女性电影”的《人·鬼·情》在男女性别问题上做了更深入的探讨,穿插于电影中的“钟馗嫁妹”片段时刻提醒着观众有关婚姻的警示。这部影片并没有真正地给婚姻出路一个答案,而是将问号悬于头上。秋芸的成功甚至可以等同于她成功地逃脱出女性的性别身份,在男女的性别夹缝中寻找到了她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却恰如其分地舒服,让她摆脱了儿时母亲出轨的阴影,摆脱爱上有妇之夫的污点。秋芸可以利用男性的这一半灵魂去掩盖她过往的不幸,因为这些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审判都是社会苛求女性的,而对于男性却可以放宽,并且她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也让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成功男性一样掩盖过往。但是这样一个事业上极大成功而且没有被性别拘泥的女性,依旧无法在婚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可以轻松地逃离婚姻,却无法改变婚姻中令女性绝望的两性关系。
四、结语
通过第四代女性导演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的女性导演们陷入了一种婚姻的困境,她们无法像王苹一样避而不谈,却也寻找不到女性在婚姻中的出路。在经历了近80年的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之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而女性艺术包括女性电影对于中国女性未来发展的走向尤其是在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的家庭中依旧是迷茫的。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以及女性主义艺术与文学的发展限制了中国女性导演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表达。中国女性导演应该从被动接受女性文学、艺术发展转变为主动探讨女性问题,推动女性主义发展。这样,女性导演作品才能够触及女性观众所关心的问题,成为吸引女性观众并推动女性地位提升的作品。
[1] 新华时事丛刊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M].北京:新华书店,1950.
[2] 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J].当代电影,1994(6):37-45.
[3] BERRY C.China’ New “Women’s Cinema”[J].Camera Obscura Feminism Culture&Media Studies,1988(6):8-19.
[4] 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62-575.
[5]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J].电影艺术,1979(3):79-80.
[6] 戴锦华.昨日之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 岳素兰,魏国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83.
[8]秦美珠.困境与选择——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走向[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7(4):8-11.
View on the Marriage in the Movies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Female Directors of China
REN Xuanyu
(Faculty of Humanities,Arts and Social Science,Flinders University,Adelaide,South Australia,5043,Australia)
The number of female directors in the Chinese 4th generation experienced a dramatically increasing.They entered the main stream film industry and produced a lot of successful movies.However,the restriction from the Chinese feminism and feminist literature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ale directors.Accompanied with the constantly improving of the Chinese female’s status,the 4th generation female directors could solve the feminist problems that was proposed by the feminists from early stage of Chinese feminist movement,that is,the female c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leave the family and live independently.However,the Chinese 4th generation female directors had been limited by the discussion of“marriage” which maintains the most of discrimination towards women.The escape of marriage is a result of nature defec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eminism and feminist literature.
feminist movies;fourth generation directors;marriage
J909.8
A
1673-8004(2017)06-0069-04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6.012
2017-05-28
任璇宇(1988— ),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主要从事女性主义电影研究。
责任编辑:罗清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