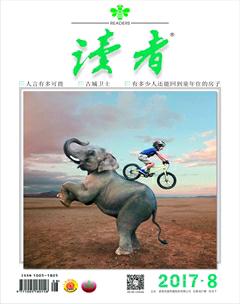十九岁以下的誓言才美丽
2017-03-29 13:30王鼎钧
读者 2017年8期
王鼎钧
傍晚,雷声隐隐不断,是我今年第一次听到的春雷,温和如在试探。
这声春雷来得太晚了吧,我几乎把它忘记了,按照农历的节气,通常“驚蛰闻雷”,现在惊蛰过去已一个多月,连“谷雨”也被抛在后面了。
听到雷声,老伴流下眼泪。为什么?她说她记得此生第一次听见雷声是在贵州,大约六岁,她问大人:“老天为什么要打雷?”她爸爸说:“因为小孩不乖。”
为了这个流泪?就为了这个。
也许是为了她已是一个乖女儿,可是老天仍然年年打雷。
也许为了她已为人母,而她的父母都老了。
有时候,你的亲人正是难以了解的人。
她泡了一壶茶坐下,我们喝茶,人在喝茶的时候不流泪(喝酒的时候流泪)。
然后她慢慢地说起另一件事。她来到台湾以后,她的一个同学有了男朋友,这一对小情侣不断偷偷约会。有一次,雷声打断了他们两人的情话,男孩指着空中说:“我若有二心,就被天雷劈死!”
可是他仍然负了她。以后她为人妻,为人母,听见打雷,就悄悄地流泪,唯恐誓言灵验,雷真的劈死他。她还是爱他。
为了转变气氛,我们互相挑衅,我问老伴是否也曾有男孩为她发誓,她问我年轻的时候是否也曾为女孩发誓。没有答案,谁也不需要答案。
我暗想,如果能再年轻一次,我倒希望在雷劈之下有男孩为她起誓,我也曾经为女孩起誓——十九岁以下的誓言才美丽。
(凌 雁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流过,星月留下》一书)
猜你喜欢
做人与处世(2022年2期)2022-05-26
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2年4期)2022-04-08
健康体检与管理(2021年10期)2021-01-03
动漫界·幼教365(中班)(2020年3期)2020-04-20
赢未来(2018年24期)2018-12-20
幼儿教育·父母孩子版(2017年4期)2017-06-13
读写算·小学中年级版(2015年4期)2015-05-25
小溪流(画刊)(2009年8期)2009-11-16
娃娃画报(2009年9期)2009-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