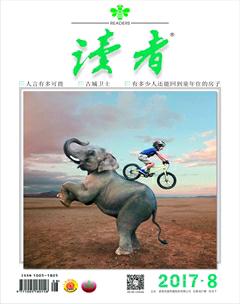巴黎絮语
于坚
人们选择巴黎,是因为巴黎适合生活——生活,而不是权宜之计,是巴黎最深刻的传统。
有一天,我的朋友F带我去她的同事雅克琳夫人家拜访,那时她正在与F一道翻译我的《尚义街6号》。“你写了生活,我喜欢。”她家住弗兰索瓦·米隆大街,这条街是林荫大道,街道上没有铺面,安静,森严。大门上镀金的扶手闪闪发光,门面泛黄,多年来被小心翼翼、暗怀敬畏地使用着,没有划痕,包浆深厚,显得贵重、豪华。这个街区住的都是富有的老巴黎,宽阔的楼梯仿佛通向歌剧院。这一家的门与街区同样古老,只有钉在门框右侧的小铜牌上刻着的屋主姓名换过。这是经历过生死的房间,曾经有人被抬出去,也有人在里面出生。门很重,徐徐打开,仿佛后面有一处大厅。里面却不大,不是什么高宅大院,只是一些小房间而已。世界在这些房间里慢下来了,这里有无边无际的细节,仿佛海水退去,散落着各种物件的海滩。你必须慢慢地走,才能避免碰到什么。各种各样的玩意,壁画、挂毯、雕塑、油画、猩红色的沙发、瓷器、铜器、镶着镀金框子的镜子、路易时代风格的家具……地上、书架上,到处堆着书。都是旧书,好像已经陪伴了主人很多年,里面夹着小纸条。有一沓丝带束着的旧纸,是谢阁兰的手稿。每一间都是一个细节博物馆。就像《追忆逝水年华》中说的:“您如果还想看到一张跟这张同样好看的沙发,那我就勸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这种款式的沙发,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第二张。那些小椅子也都是珍品,您一会儿可以去看看。每一个青铜铸件都是跟椅子上的图形相配的。如果您有意看一看,既能学到东西,又能得到享受,准能感到没有白费时光。请看看这椅子的镶边,那‘熊与葡萄红底上的小葡萄藤,画得多好!您说呢?”轻微的灰。房间装修过,几根栗黄色的木柱故意露出木纹。这个家就像被巴尔扎克写过,在《邦斯舅舅》的某一段里,又仿佛是王世襄的家。
巴黎人普遍住在古董里面,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古董。收集古董是巴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种爱好令巴黎充满了发霉的历史感。不只是罗浮宫,历史在家家户户,通过无数被小心保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而存在。这不是国家或社会运动那种大历史,而是私人生活的小历史——父亲的,祖父的,外祖母的,外公的,曾祖母的……那些来自时间深处的小玩意,永不消逝的微光,在一只18世纪的首饰盒的镀金盖子或者一个拿破仑时代制造的相框上安详地梳着头。“对于私人来说,居室的幻境就是整个世界。在居室里,他把遥远的和久远的东西聚合在一起,他的起居室就是世界大剧院的一个包厢。”“居室是艺术的避难所。收藏家是居室的真正居民,他以美化物品为己任。”(本雅明语)
时间将价值连城者和一文不值者都纳入美的宰治,在美面前万物平等。往往是那些廉价的收藏更具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人的斗争不再是对物的弱肉强食,而是审美境界的犀利。巴黎是一个左倾的城市,它繁华、时髦,然而暗地里却鄙夷珠光宝气而向往旧物,向往着波希米亚式的浪漫主义——那是一种穷人的时髦。巴黎的左倾气质正是通过这些储存着时间的居室暗示着。这是一个世界上跳蚤市场最发达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一到星期六,就蜂拥向那些遍布在街头、地铁车站出口的臭气冲天的地摊,在那些逝者的旧物里翻啊,刨啊,拣啊,挑啊——那位住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女士的梦想是一条19世纪的蓝围巾。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相当地精打细算,她知道,这样一条围巾可以通向那种深刻、持久而如胶似漆的爱情。
趁着前图书管理员雅克琳在厨房里烹调午餐,我跟着她丈夫在各个房间里转悠。这里真是时间的仓库——在这个小玩意面前,时间显示为18世纪的某日;在那个座钟前,时间显示为今天下午3点;在另一个转角处,时间又回到20世纪早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使巴黎得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保存着记忆。那么多旧相片,在这些发黄的纸片上,记录着私人生活最生动的历史。逝者并未逝去,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瞧,多年前的夏天,他们站在马德里安的风景中。时间没有过去,如果雅克琳家的某扇门里走出来一个人,被介绍说是邦斯舅舅,我一点也不会吃惊。
雅克琳的丈夫以前在电视台工作,他皮肤白皙,皱纹优雅,天真而傲慢,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巴黎,就是外省都没有去过。“为什么要去呢?”他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其实我外祖母也一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昆明,她死在故乡那些黑暗的细节中。我都忘了曾经有那样的时代,人们老死于故乡。在中国,自五四以来,故乡已经不被信任,故乡在作家的笔下,只是进步的绊脚石、批判对象,拆迁势在必行……“面向未来”“故乡批判”的写作成为文学的主流,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凤毛麟角。将故乡描述成一潭潭窒息生命的绝望死水的作品,非常普遍。网络上有普鲁斯特语录,其中一句是:“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一位中国读者在这句话后面评论道:“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他唯一能做的才是忘记。这样你才能拥有现在,更多美好的东西才能进来。小孩都是玩具坏了就扔了,便拥有了新的玩具,因为小孩的接受性强;而成人不一样,总是用一些世俗和原则禁锢自己。”
故乡是一种对存在的信仰。荷尔德林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还乡。”这个乡就是语言之乡,语言是细节的守护者。历史、经验、时间,只在细节中存在。失去细节意味着语言的贫乏。写作就是回到故乡,故乡就是记忆、细节。
普鲁斯特是一位细节大师,他关注的不仅是现实的细节,更是意识深处的细节。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时间之书,在西方书籍中是罕见的——西方小说总是充满空间占有的野心,时间只指向某个未来。在普鲁斯特这里,时间深植于细节中。这些细节,极大地扩展了意义的空间。时间不舍昼夜,但是时间不是抽象的,只有在细节中才能被感觉到。普鲁斯特的记忆保存并虚构了生活的各种细节,只有保存才能虚构,没有记忆的细节是欺骗。所以齐白石说:“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在充满细节的世界中诞生的细节之书。人们可以通过这些细节去学习生活。
雅克琳夫人的午餐做好了,那是一条沙滩般细腻的欧鲌,躺在一张锡纸上。她放了一点胡椒粉,几乎没放盐,非常可口。
(彭慧慧摘自凤凰读书,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