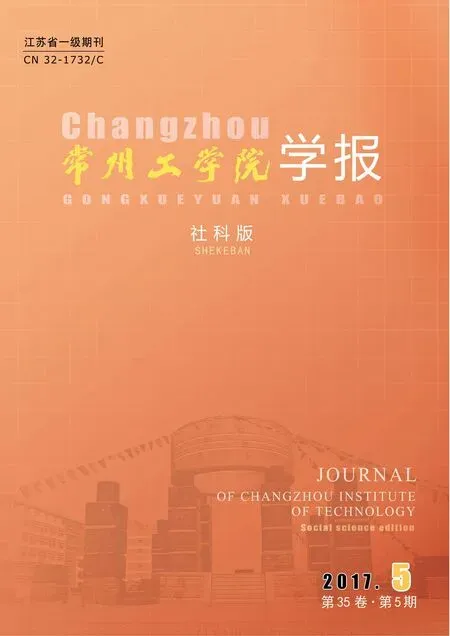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屠岸先生访谈录
戎林海,戎佩珏
(1.江苏译协翻译研究与实践基地(常州),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2.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屠岸先生访谈录
戎林海1,戎佩珏2
(1.江苏译协翻译研究与实践基地(常州),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2.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文章是对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先生的访谈录。屠岸先生几十年来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丰硕,成就巨大。在访谈中,屠岸先生就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翻译作品的选择、诗歌翻译的策略和精髓、诗歌翻译的“真”与“美”以及翻译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发表了他的真知灼见,并对有志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青年学者提出了希望与建议。
诗歌创作;诗歌翻译;“真”与“美”
G127
屠岸,原名蒋璧厚,1923年出生,江苏常州人,是我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当代诗坛》汉英双语诗学季刊主编。几十年来,屠岸先生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领域辛勤耕耘,收获丰硕,成就巨大。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等;主要的诗歌译作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等,其中《济慈诗选》译本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2010年屠岸先生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15年7月底,我们有幸始与屠老通信。除向他汇报我们在赵元任翻译研究方面的事宜外,也谈及他的诗歌和诗歌翻译。9月中旬,我们与屠老通电话,征求他的意见,问是否能就翻译方面的一些问题用笔谈的方式对他进行采访。屠老(虽然已是耄耋老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大概是因为我们是家乡人的原因吧!),这使我们由衷地感动。9月底,我们将拟好的12个问题寄给他,请他有空慢慢解答。想不到两周时间不到,屠老就将答复寄给了我们。答复是用老式的方格稿子写就的,字迹工整清楚。这对于一个93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不易!
下面是具体的访谈内容。提问方:戎林海、戎佩珏,以下简称“戎”。回答方:屠岸,以下简称“屠”。
戎:屠老,您是我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今天有机会以笔谈的方式采访您,真是我们莫大的荣幸。首先,作为诗人,请您谈谈诗歌能不能翻译。
屠:诗歌能不能翻译?有人认为能,有人认为不能。雪莱称不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经过翻译而失去的东西。我则认为诗能翻译。《圣经》上说,人要造巴别通天塔,遭致上帝震怒,上帝把人类分散到各地,说各种不同的语言,以为惩罚。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类各民族语言不同的由来。但我认为,人类各民族的语言虽然不同,他们的感悟是相通的,都有喜怒哀乐,离合悲欢,因为他们都是人。这就是翻译之可能的根本依据。诗,正是人类感情抒发的成果。既然感情相通,那也就奠定了翻译之可能的基础。
戎: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情有独钟的?
屠:我最早翻译的是惠特曼的诗集《鼓声》,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其次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于一九五年。我读小学时,母亲教我《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使我亲近了诗歌。我读中学时,住在姨母家,表兄奚祖权在光华大学读英文系,他读的《英诗全库》原文吸引了我,使我沉醉于英诗的艺术魅力中。见到《沫若译诗集》,佩服郭沫若的开拓精神,却也发现郭老译诗的缺点和疏误。窃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一九四八年,我在《大公报》连续发表《译诗杂谈(一)》和《译诗杂谈(二)》,批评了一批诗歌翻译家,有的批对了,有的批错了,幼稚狂妄,不可一世。年龄渐大,稍有觉悟。但译诗的兴趣,始终未减。初,全凭兴趣,后来,渐有使命感。
戎:您的翻译活动似乎聚焦在诗歌翻译上,有没有其他文学体裁的翻译?
屠:这个问题,我似在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中说过了。现再作补充。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是带有使命感的。日本有坪内逍遥的莎翁戏剧和诗的日文全译本,中国没有,朱生豪感到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感到,英国文学中莎翁的戏剧和诗创造了黄金时代,英国诗歌直到二十世纪末在欧洲文学中始终灿烂辉煌,若没有中文译本,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缺憾。于是我殚精竭虑,译出了155位英国诗人的583首诗,时间跨度为中世纪到当代,书名叫《英国历代诗歌选》,分上下两册,于2007年出第1版。我翻译过剧本、散文。我译的南斯拉夫剧作家弩西奇的剧本《大臣夫人》于一九五八年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由西安话剧团搬上舞台。
戎:诗歌翻译不容易。有人说,非诗人不能进行诗歌的翻译。在这方面,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能否请您谈谈您的诗歌创作对诗歌翻译有影响吗?翻译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韵律问题、意象问题还是其他什么?您是如何处理的?
屠:说非诗人不能译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绝对化。诗人有创作经验,了解创作情绪,因此能较深地进入原作的内里。诗歌翻译的佼佼者如戴望舒、绿原,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也有人不以诗人知名,但所译诗歌达到极高的水平,因为他们具有诗人气质。杨德豫写过诗,但后来不写诗了,他全身心投入诗歌翻译,达到无人能超过的高超水平。杨德豫就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翻译家,我称他为译诗圣手,绝不为过。译诗过程中遇到的要解决的问题,有韵律问题,意象问题,而最难的,是要译出原诗的神韵。神韵包含风格、气质、意蕴、人格、个性。要译出神韵,是最难的。若不能很深地进入原著的内里,就不能捕捉到原著的神韵。
戎:有学者认为诗歌翻译必须讲究音韵美、形式美、意象美,也有人认为诗歌翻译要忠实地传达原著的文体美、风格美,译语也要优美等等。能否请您谈谈您的经验与感受?
屠:文体美可以包括在形式美之中。音韵美、风格美、意象美都是交叉存在的。严复提出翻译三原则:信、达、雅。我认为信是根本。讲究信,就不仅要忠于原著的形式,也要忠于原著的内容。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不可分割。英语诗绝大部分是有格律的(惠特曼的自由诗除外,虽然它也有内在的音乐性),因此译成中文,我认为,也必须保持它的格律。英诗的格律包括一首诗的诗节数(stanza),各诗节的行数(line),诗行的步数(foot),诗节的韵式(rime-scheme)。卞之琳先生的译诗原则是:以顿代步,韵式依原诗,亦步亦趋。顿就是中文的音顿。孙大雨创造的术语叫“音组”,其实就是顿。我是卞之琳先生的学生,我译诗就遵循卞先生的原则。遵循这一原则的译诗家还有杨德豫、袁可嘉、傅浩等。还有,译界还有人主张直译,有人主张意译。有过论争。卞之琳先生不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分类。他主张“全面求信”,在“信”的主宰下,无所谓直译和意译。
戎:严复对翻译的要求是信、达、雅,这是翻译的“三字经”,被许多人奉为翻译的圭臬。您觉得诗歌翻译是否也同样要遵循这个原则?
屠:严复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条原则,我服膺,认为对。但我有一条“但书”:严复提出的“雅”,原是指他的桐城派古文的风格。我们现在又不写古文,所以对“雅”要加以改造,以符合我们的要求。我认为“雅”应该是原文的风格。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物的对白或独白,有的出自达官贵人之口,那当然雅;但有的出于市井小人、引车卖浆者之口,那只能俗(通俗,非庸俗,更非恶俗)。译莎翁戏剧中人物的台词,也必须该雅则雅,该俗则俗。这样来理解信、达、雅的雅,才不至陷入教条主义。
戎:传统中国译论和当代西方译论中都有一个“似非而是”的争论,那就是翻译的策略。也就是“归化”与“异化”问题。您曾经就此论题发表过意见。能否请您再谈谈我们应该怎样有机地、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屠:关于“归化”和“外化”的问题,我曾说过多次,也都发表过。鲁迅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里可以不必重复。我认为翻译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归化”,这是为了读者易于接受;又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外化”,是为了使读者知道原著是外来的。“归化”过度,会使读者不知道原著是什么模样;“外化”过度,会使读者难以接受(或弄不明白)这样的译文。所以,“归化”和“外化”都有一个“度”。这个度怎样掌握,很难说清。只能说,译者应该是“一仆二主”,既要对得起作者,也要对得起读者。
戎:有翻译家认为,翻译必须“择爱而译”,也就是说选择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您的诗歌翻译主要集中在英国的诗歌翻译上,尤其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济慈的诗歌。您为什么选择莎士比亚和济慈?是诗歌语言上的“情投意合”,还是诗人心灵上的共鸣,精神上的同振?您还选择翻译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作品,您对翻译作品的选择遵循了什么样的原则?
屠:我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因为被莎翁的诗艺所征服,产生了极爱。我译济慈的诗,是因为我与济慈在精神上的共鸣与沟通。济慈22岁时患肺结核,我也在22岁时患上肺结核,济慈活到25岁,我当时也以为自己只能活到25岁(当时肺病特效药还没有出现在药房里)。济慈诗歌中的诗美,使我震惊,占有了我的心灵,我成了他的俘虏。他生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我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但,尽管“萧条异代不同时”,他和我却在冥冥之中相遇,相交,成为兄弟、手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到伦敦、罗马,访问了济慈故居和他的灵宅、墓葬。我把我用三四年时间呕心沥血译成的《济慈诗选》送给了济慈故居纪念馆,工作人员说一定好好保存。
戎:说到济慈,我们想起了他的名言:beauty is truth,truth is beauty(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怎样全面理解这句话,对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有什么样的启示?
屠:济慈在他的诗《希腊古瓮颂》的最后一个诗节的末尾写道:
等老年摧毁了我们这一代,那时,
你将仍然是人类的朋友,并且
会遇到另一些哀愁,你会对人说: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是
你们在世上所知道、该知道的一切。
这里的“你”是希腊古瓮,“人”是人类,最后一行中的“你们”指人类。“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是古瓮说的话,古瓮认为人类知道、并且应该知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句箴言。这使人想到人生三原则:真、善、美。这三者,真是基础,根本,善是内涵,美是外延。这三者又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济慈说的真,其实包含了善,可以不说,不言自明。古瓮对人说,也就是济慈对人说。他说,没有美,就没有真,没有真,就没有美。诗美,人生美,都源于真。真,就是真诚性。人若没有真,就是丧失了真诚性。那不就成了伪君子了吗?济慈在这里,讲的是怎样作诗,也是怎样做人。
戎:济慈对诗歌创作与诗歌美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诗学概念,叫做negative capability。对于这个“术语”,译界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比如周珏良先生曾译为“天然接受力”和“反面感受力”;梁实秋先生曾将其译为“否定的能力”;袁可嘉先生则将其译为“消极的才能”;还有人将其译为“自我否定力”。先生您的翻译是“客体感受力”。您认为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您为什么要将其翻译成“客体感受力”?
屠:济慈在给弟弟的书信中提出了一个诗学概念:negative capability。这个概念,有不少中文译法。周珏良译为“天然接受力”“反面感受力”,梁实秋译为“否定的能力”,袁可嘉译为“消极的才能”,还有人译为“自我否定力”。对这些译法,都可以认为,都没有错误。negative原本是“反面”“消极”“否定”的意思。只是“自我否定力”的译法会产生一些矛盾。若是已经否定了自我,那还会有capability(这也是一种力)吗?
按我的理解,济慈的这个诗学概念所要说明的,是放弃自己原有的一切定势思维,而与吟咏对象拥抱,感受吟咏对象的一切,合而为一。原有的一切定势思维,属于诗人的主体。主体即是positive,它的反面是negative,即客体。我不采用“消极”,因为我不认为济慈消极。我也不采用“否定”,因为我不认为济慈否定了自己。济慈这个诗学概念,不妨说是积极的。中国诗学中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客体感受力”与“无我之境”似有相通之处。济慈认为只有拥抱对象,才能写出好诗。
戎:您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什么样的看法?翻译在其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屠: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最近有两件事引起广泛关注。一是莫言的文学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一是屠呦呦因创制治疟疾的“青蒿素”获诺贝尔科技医学奖。这似乎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即西方开始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文化。中国自唐宋以来,长期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或中心之一。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甲午战争,中国又失败,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西方中心主义瞧不起中国,把中国贬为二三等国家。中国的弱国地位,长期得不到翻身。但中国人并不自馁,始终奋斗不息,这突出地表现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西方中心主义一度漠视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认为战败日本法西斯只是美苏的功劳。最近欧洲的学者著书充分肯定中国在二战中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作用,得到世界的承认。文化方面也如此。西方中心主义认为科学创造全部归功于西方。诚然,电灯电话、火车轮船始创于西方。但是,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都是中国的创造,由中国传到了西方。谁能否认?文学也如此。当年斯文赫定征求鲁迅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参赛人名单,鲁迅说“我不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又提名老舍、沈从文。只是这个奖不颁给已经逝世的作家,而老舍、沈从文那时都已辞世。有一位中国作家,放弃中国国籍,取得了法国国籍,他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未始不是好事。但如果说鲁迅还不如这位改换国籍的原中国作家,那是缺乏常识。正确的看法应该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各自的贡献,共同创造了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诺贝尔奖颁给莫言和屠呦呦,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说明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注意到了过去的偏颇,开始正视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依靠翻译,翻译是纽带,没有翻译,此路不通,怎么走出去?莫言的小说,如果没有外文翻译,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怎么能读懂莫言的作品?他们中有几个人懂中文?鲁迅称翻译家为普罗米修斯,这个比喻极好。外译中者,是把外国文化之火播到中国来;中译外者,是把中国文化之火播到外国去。没有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人类永远生活在黑暗中。没有翻译家把各民族文化之火传给其他民族,人类也只能老死不相往来,不能共享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戎:最后,请您老对有志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青年学者提点希望和要求好吗?
屠:今天有志于从事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青年学者,必定是有着高尚的志趣或使命感而不为名利所动的人。翻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能得到多少稿费和版税?稿酬之低,与翻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无法相比!版税更不要谈起。一些译家为了出版他的译著,要给出版社“倒贴”一笔钱,而且为数不小。这不能怪出版社,因为出版社没有为出你的译著而赔本的道理。为什么译著销路不畅?未必是你的译著质量低劣,即使是名著佳译,也不一定畅销。这是当前社会的风气所决定的。当前流行的是“快餐文化”。真正的经典,未必合乎事宜。十九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访问英国,写成一本《旅程札记》(SketchBook,林纾译为《拊掌家》),其中有一篇《造书的艺术》(TheArtofBook-Making),写的是一些英国学者如何“造书”,即是拿已出版的书来,抄录拼凑,改头换面,变成一本本新书,投放市场。这些年来,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造书的艺术”。一些人把同一原著的几种不同的中文译本,剪贴拼凑,改动几个文字,便变成一本新译,投向市场。原译者也难以对簿公堂,你说他是剽窃,他说他是新译。是吗?这种丧失道德原则的行为,青年学者必须坚决摈弃,不能沾染丝毫!
翻译是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翻译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自觉。
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的联合体,如果没有翻译(口头的,文字的),那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伟大的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翻译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大家知道。那么,共产党又是怎样诞生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共产党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是德文、俄文,送到中国,得到中国人的接受,不通过翻译怎么行?《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者是陈望道,他功不可没!马列著作中文翻译的后继者“代有才人出”。现在《马恩全集》中文版也已面世。我要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
有一位领导干部,说:“翻译有什么难的?只要手头有一部字典,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比如你遇到一个外文字,good,你查一查字典,这个字的中文解释是‘好’,你把‘好’写下来,不就译成了?其他字,全可以此类推。”这位领导干部,以无知为聪明,令人笑,亦令人叹。
尊重翻译,尊重翻译工作者。但也不要把翻译抬到可怕的高度。
翻译工作者既不要瞧不起自己的工作,也不要拿乔。只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才是正确的态度。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5.001
2017-03-04
戎林海(1957— ),男,教授。
B
1673-0887(2017)05-0001-05
责任编辑: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