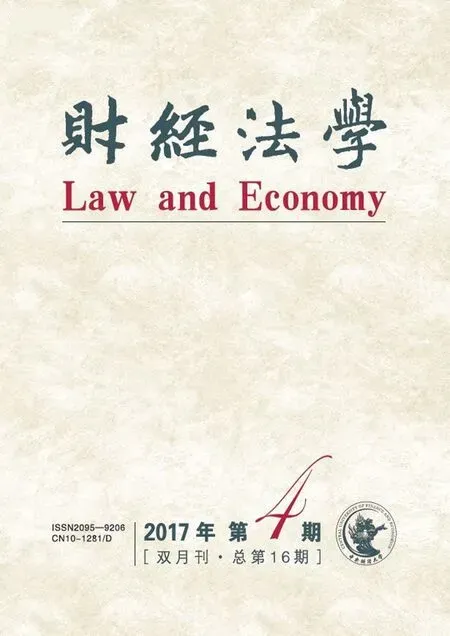民法典立法方法论
——以《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为例
张永健
一、导论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法学研究日趋兴盛。民法研究累积数个世代后,民法典即将出台。民法典的样貌必定反映了中国民法学界在比较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多种研究路径的研究成果。笔者观察大陆法学发展,欣喜社科法学在法学界的高度发展(相较于邻近的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但忧心社科法学在法理学外的部门法中影响有限(这和台湾地区的社科法学,尤其法经济学,大多寄生在部门法中不同)。在民法典即将出台之际,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在民法学中的整合发展,有高度的理论与实用价值。
本文是笔者反省法经济学方法论与思考具体民法问题经济分析的成果。本文第二部分在法教义学不同于立法论方法论的前提下,提出中国民法典立法过程中所应思考的“立法方法论”。完善的立法必然需要考虑社会多元价值,以及达成这些价值之各种手段之良窳。就此而言,法经济学的方法论会占有重要角色。其一,除了追求公平、正义、分配之外,民法典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不可能不考虑效率——用白话说,就是物尽其用和避免浪费。其二,目的手段关系虽然内建于许多法律思维中,但经济学是最能一贯处理目的手段关系之理论。即令民法典有时追求效率以外之目标,也应该注意以最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法为之[注]一个具体实例是遗失物拾得的规则设计,参见王鹏翔、张永健:“被误解的恋情——经济分析与法学方法”,载《经济分析与法学方法研讨会论文》,“中研院”法律所主办,台湾台北。。忽略了法经济学的政策建言,几乎可以断言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第二部分总结了经济分析理论在立法论上的三个洞见,作为思考制度设计问题之起点。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民法典物权编的立法问题,本文第二部分提炼出两个互相配合的经济效率标准: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配置效率关心的是资源有无流转到最能利用者之手中。透过自由市场与价格机制,最能利用资源者,一般而言,能出最高之价钱,将资源盘到手上。但若现有制度环境下有高制度费用,使最适配置效率无法达成,物权法经济分析学者就会想透过立法、修法来改变制度环境、降低交易与资讯成本。重点是,降低制度费用,本身需要支出费用,而此费用若超过改造制度环境所带来的配置效率改善,则此改革并不划算。若将“降低制度费用”看成产品,则是否应生产更低总成本的制度环境的标准,就是生产效率标准[注]See Harold Demsetz,From Economic Man to Economic System:Essays on Human Behavior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9~114; Harold Demsetz,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What Problem? A Critique of the Reasoning of A.C.Pigou and R.H.Coase,7 Rev.L.& Econ.,2011,pp.1,8~9.Demsetz教授的洞见之后由Fennell教授延伸。See Lee Anne Fennell,The Problem of Resource Access,126 Harv.L.Rev.,2013,pp.1471,1502.See also Pierre Schlag,Coase Minus the Coase Theorem—Some Problems with Chicago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99 Iowa L.Rev.,2013,pp.175,214~215.。换言之,在物权法的范畴中,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可以结合为单一的经济效率标准,在该标准下,法律政策应尽量压低交易成本与资讯成本[注]Fennell教授和Demsetz教授理论架构的关键不同是后者将法律当成外生给定,前者则有倡议修法之雄心。参见前注〔2〕,Fennell文,第1480~1482页。这恰恰反映了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研究路径与背景假设不同。,直到执行该法律政策的边际社会成本高于其边际社会利益为止[注]本段内容改写自张永健:《物权法之经济分析——所有权》,元照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47~48页。本书简体字版预计于201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鉴于社科法学在部门法研究的能见度有限,本文有意识地将立法方法论落实到具体物权法问题——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动产与不动产善意取得问题,在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中被冶于一炉;但立法论上,动产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应该分别规定[注]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本文不讨论不动产善意取得问题,因为此问题的适当处理,取决于中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走向与运作实况,而不动产登记的运作有许多细致的制度细节需要考究,包括不动产交易专业中间人的专业化、一般人利用专业中间人的意愿、负责不动产登记的公务员之素质……;目前尚超出笔者能力范围。因此,以下讨论聚焦在动产善意取得问题。
无论中国民法典究竟有多大程度为现行单行法的整合与反省,民法典物权编都会受到2007年《物权法》规范的一定影响,应该毋庸置疑。因此,本文第三部分由《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规范的经济批评着手。《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在动产善意取得情境的产权分配上,其实与台湾地区“民法”第948条到950条的产权分配规则,相当类似。尤其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比较后,其相似性更为突出[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比较,参见Arthur F.Salomons,Good Faith Acquisition of Movables,in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Wolters Kluwer,2011,pp.1065,1066~1074 (Arthur S.Hartkamp et al.eds.); Alan Schwartz & Robert E.Scott, Rethinking the Laws of Good Faith Purchase,111 Colum.L.Rev.2011,p.1332(但请注意,Schwartz & Scott对其他国家民法之理解不尽正确,例如其对《物权法》之规定,就几乎全盘误解)。。在《物权法》与台湾地区“民法”的规范下,善意买受人原则上即时取得动产所有权,但受无权处分之标的为遗失物时,原所有人两年内可以请求返还;但若善意买受人是在特定场所或透过特定交易方法购得,则原所有人必须支付买价才能请求返还。笔者已以四万余字之篇幅,详细论述台湾地区法律动产善意取得规则的解释论与修法建议[注]参见张永健:“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之经济分析”,《“中研院”法学期刊》,2017年第21期。,其中许多可以直接提供民法典立法者参照之处,本文将不多赘述。但有鉴于《物权法》的具体规则仍与台湾地区“民法”有相异之处[注]例如:在概念体系上,台湾地区“民法”以“原占有人”作为其中一方保护主体,《物权法》以“原所有人”作为其中一方保护主体。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物权法》之规定更为妥适。占有与占有移转之方式,可以帮助判断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但占有本身没有值得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之处。学者认为,《物权法》第106条的“受让”不包括指示交付与占有改定[参见王利民:《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8页],本文赞成之。详细原因请参见上注,张永健文。,且两地制度环境不同,本文第三部分仍由反省现行《物权法》入手。
第三部分都是经济批评,有破而无立。第四部分由第二部分的经济分析式立法方法论出发,完整建立一套最能增进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简言之,这套制度下,买受人在公开市场上善意以市价购买系争物,就会确定取得所有权。其他的构成要件,有些发生几率很低,有些可以用推定规则解决,仅为枝节问题。此核心主张的优点是,买受人在购买系争物“当时”,就可以判断其是否能适用善意取得规定,从而降低其征信成本;而且,此种制度下的资源配置,才可能符合经济效率。在此简单二分的架构之上,本文只愿意提倡两种例外:第一,当买受人善意非可得而知,但不符合公开市场规则(如支付市价在非大众可任意参与的拍卖会上购物),而原所有人防范无权处分又有重大过失,原所有人例外地丧失对善意取得者请求返还之权。这是额外让买受人得以取得所有权。第二,当系争物为替代物,但对原所有人有特殊意义,原所有人可以支付买受人其当初给付之价金以赎回。在此例外中,买受人仍先取得所有权,只是可能事后换回价金,回到原点,但不至于物财两失。
二、建立立法方法论
虽然法学方法的教科书常会区分立法论(de lege ferenda)与解释论(de lege lata),但立法论的“方法论”为何在中文世界却罕见完整的讨论[注]苏永钦教授针对中国民法典立法提出不少系统性看法,为中文文献中探讨立法学的重要例外,参见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8页。其他探讨,参见例如朱志昊:“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0~65页;姜孝贤、宋方青:“立法方法论探析”,《廈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35期,第38~45页。。要制订民法典,除了宪法设下的框架,以及与既有法律(例如《立法法》)规范、概念、用词接轨的束缚外,立法者享有全然的“立法形成自由”。若人大法工委要求学者以立法方法论的分析架构逐步推导出其主张,则目前并没有这样为多数人共同接受的分析架构存在。
教义学研究者“或许”可以逃避价值取舍,奉行立法者的价值决定为依归;但立法论研究者是以立法者为说服、帮助的对象,而立法者在宪法框架下正是要处理价值取舍问题。无论是中国或外国的法律人,惯常以分配、公平、正义或其他的主义、思想作为私法立法的指导纲领,但以效率为规臬的立法思考架构,似乎还非常少见。以下第一节扼要勾勒效率观点的立法论,第二节则更具体指出物权法立法所应掌握的效率准则。
(一)效率观点下的立法方法论[注]本节内容改写自前注〔1〕,王鹏翔、张永健文。
笔者曾在另一篇合著、长达六万余字的论文中详细论证:经济分析的思维可以透过目的或结果论证的架构整合成为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方法[注]参见前注〔1〕,王鹏翔、张永健文。。因此,以效率作为结果评价标准,以人的行为模式作为结果预测根据的经济分析思维,在受制度性拘束较少的立法论领域,将更有施展余地。以下勾勒经济分析在立法方法论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注]苏永钦教授认为,民法典立法的六个实体方面的规则中,其中之一就是效率规则。参见前注〔9〕,苏永钦书,第92~93页。。
1.所有的立法选择都有机会成本
立法方法论中,必然有价值权衡。曰“价值权衡”而不曰“价值选择”,是因为良善的立法本来应该考虑“所有”的价值后斟酌损益,而不是偏狭地考虑一两个立法者自己在乎的少数价值。价值往往冲突,所以最终的立法往往为了实现某些价值而必须一定程度地牺牲其他价值,但这就是价值权衡——新法通过施行,有人获益、有人受害,有的权利被重视、有的权利被牺牲。这其实正是经济分析思维对立法方法论的第一个启示:所有的立法选择都有“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选择了A价值,就会牺牲B价值。
纵使价值不容易量化,价值不容易共量,但价值权衡始终存在。若全然采取“权利岂能以金钱衡量?”的态度,则漠视了立法时必然发生的价值权衡。即认为人命无价,无法共量,也应该会认为救多人优于救少人。以各种环保法规为例,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都是为了增进健康、减少死亡,但每一种环保管制“救一命”的成本不一样。若认为救一命是一命,救越多命越好,则应该将资源投入在“救人本益比”最高的管制项目。换言之,国家税收有限,政策决定者必然要做“权利保护的权衡取舍”(rights-rights trade-off)[注]See Stephen Holmes & Cass R.Sunstein,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WW Norton & Company,2000,p.126.。此种权衡的决策程式,就是成本效益分析。
在民法立法时,在动产善意取得问题上,要考虑原所有人和善意受让人权益的衡量;在斟酌是否要制订房屋时效取得制度时,要权衡所有权的安定性和物尽其用的效益;因为物权有对世效力,在设计物权公示制度时,要考虑公示的耗费(例如全面实施强制不动产物权移转登记生效制的成本)和若采取任意登记制对有意购买不动产物权者的资讯负担。
2.经济效率作为其中一种立法价值
经济分析思维对立法方法论的第二个启示,是揭示经济效率作为其中一种(而非唯一)[注]See,e.g.,Matthew D.Adler & Eric A.Posner,New Foundations of Cost-Benefit Analysi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p.6; 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Aspen,2011,pp.34~35,319; Richard A.Posner,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00.长期任教于哈佛法学院的两位经济分析巨擘Steven Shavell和Louis Kaplow,在其合著的堂皇大作Fairness versus Welfare中,对比“公平、正义”与“福祉、效率”;主张当两者结论相同时,当然只需考虑后者;而当两者结论不同时,若抱持前者则长期而言会让“每个人”福祉降低,因而是不好的立场。See Louis Kaplow & Steven Shavell,Fairness Versus Welfa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 4~5,8。但本文阅读的多数法经济学文献,则多半抱持比较折中的立场,认为效率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价值。立法价值,与公平、正义等法律人珍视之价值同列。经济效率当然不是只考虑成本,也考虑效益(benefits)——更宽广地说,就是福利或称福祉(welfare)。福祉的定义,福利经济学和法经济学有许多讨论[注]参见上注,Adler & Posner书,第9~16页(成本效益分析是最能达成社会整体福祉的决策程序)。,但就本文目的,细节的争论并不重要。
福利可以用金钱价格作为“代理变数”(proxy)[注]一个不一定有代表性,但广为人知、引起争议的立场,是Judge Posner用“财富极大”(wealth maximization)作为福利的代理变数。意思是,法官很难衡量抽象的福利,但较能掌握其判决所影响之社会财富,所以法官应该尽量关注于极大化财富。而“财富”不应被狭隘地理解为金钱,而是社会大众所珍视的有形、无形的东西。依Posner之见,财富极大,或法律经济学,与哲学上的功效主义/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不尽相同。参见前注〔14〕,Posner书[Frontier of Legal Theory],第96~98页;前注〔14〕,Posner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第34页。。经济分析强调把饼(=福利)做大,而且不要浪费既有的饼[注]See Robert Cooter & Thomas Ulen,Law and Economics,Pearson/Addison Wesley,2012,p.4(“Efficiency is always relevant to policymaking,because public officials never advocate wasting money.”) 如同正文所论,同样要救人一命,花10元的A管制与花1 000元的B管制之间,当然应该选择前者。。即便认为如何分配饼的问题不属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公平、正义理论的范畴,但经济学可以更精准地预测重分配法律的效果。例如:假设政策决定者有意加强对中低收入户之保护与扶助,应该要用累进所得税制为之,还是在每个具体的法律条文中都加上对弱势者的特殊保护[注]关于此问题的辩论,请比较Louis Kaplow & Steven Shavell,Why the Legal System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23 J.Legal Stud.,1994,p.667; Louis Kaplow & Steven Shavell,Should Legal Rules Favor the Poor? Clarifying the Role of Legal Rules and the Income Tax in Redistributing Income,29 J.Legal Stud.,2000,p.821; Steven Shavell,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647~660;上注,Cooter & Ulen书,第7~8页,与 Lee Anne Fennell & Richard H.McAdams,Introduction,in Fairness in Law and Economics,Edward Elgar,2013,p.xiii(Lee Anne Fennell & Richard H.McAdams eds.); Lee Anne Fennell & Richard H.Mcadams,The Distributive Deficit in Law and Economics,99 Minn.L.Rev.,2016,p.1051; Daphna Lewinsohn-Zamir,In Defense of Redistribution through Private Law,91 Minn. L.Rev.,2006,p.326.?经济学可以预测各种不同手段的分配效果[注]参见前注〔17〕,Cooter & Ulen书,第4页。。
有些增加社会全体人民总福利的政策,会造成不平等或不正义;就如某些符合正义或平等的规范,会降低社会总福利。经济分析式的立法方法论,强调不能完全忽略福利,并呼吁政策决定者重视福利与其他价值间的取舍[注]See generally Arthur M.Okun,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5.。
3.以人的行为理论作为立法基础
经济分析思维对立法方法论的第三个启示,是重申“徒法不足以自行”,并提出人的“行为模型”(behavioral model),以说明何以“徒法不足以自行”,并提出内建行为反应考量的立法建议。传统的法经济分析强调人的理性自利面,并认为人会对法律规范做出反应(law as price)[注]See Nicholas Mercuro & Steven G.Medema,Economics and the Law:From Posner to Post-Modern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04.,因此强调诱因(incentive)[注]See Richard A.Posner,The Economics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75.对于法律作为诱因的批评,参见简资修:“法律作为合约安排”,《交大法学》2015年第3期,第42~43页。。在“命令控制式”(command-and-control)的行为管制和“诱因相容”(incentive-compatible)的行为管制中偏好后者[注]两者比较,参见叶俊荣:《全球环境议题——台湾观点》,巨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4页。。
而传统法经济学分析(常常被称为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分析)的一个同门师兄弟,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奠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nald Coase[注]See,e.g.,Ronald H.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4 Economica,1937,p.386;Ronald H.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2 J.L.& Econ.,1959,p.1;Ronald 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3 J.L.& Econ.,1960,p.1;Ronald H.Coase,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Ronald H.Coase,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Ronald H.Coase & Ning Wang,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Palgrave Macmillan,2012.和Douglas North[注]See,e.g.,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等人的研究,则强调“制度”(institution)的重要。在契约法与侵权法,新制度经济学倡议的手段是设置可以降低制度费用[注]关于制度费用的概念,以及与新制度经济学健将张五常思想的关联,参见张永健:“张五常《经济解释》对法律经济学方法论之启示”,《交大法学》2015年第13期,第28~30页。张五常代表性的看法,参见张五常:《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的制度,以利当事人自行协商交易。
结合认知心理学的新兴“行为法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注]See generally Christine Jolls et al.,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50 Stan.L.Rev.,1989,p.1471; Cass R.Sunstein,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A Progress Report,1 Am.L.& Econ.Rev.,1999,p.115;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Cass R.Sunstein ed.).则凸显人容易犯错的一面。以Cass Sunstein为首的“推力”(nudge)一派[注]See Richard H.Thaler & Cass R.Sunstein,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化性格缺陷为推力,主张在政策中使用人常受到的偏见、捷思(heuristics),把一般人推往较好的状态(像是存较多的钱、签署器官捐赠卡等等)。此派学者不讳言自己是“自由人式的家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注]See Cass R.Sunstein & Richard H.Thaler,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70 U.Chi.L.Rev.,2003,p.1159; Cass R.Sunstein,Why Nudge?:The Politics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不当然赞成使用“推力”的行为法经济学学者[注]See Ryan Bubb & Richard H.Pildes,How Behavioral Economics Trims Its Sails and Why,127 Harv.L.Rev.,2014,p.1594; Avishalom Tor,The Critical and Problematic Rol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n Nudging,in Nudging-Possibilities,Limi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European Law and Economics,Springer,2016,pp.3,3~10(Klaus Mathis & Avishalom Tor eds.).,则指出许多法律缺乏认知心理学思维,导致从公法到私法的管制失灵[注]See,e.g.,Oren Bar-Gill,Seduction by Contract:Law,Economics,and Psychology in Consumer Marke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立法论缺乏人的行为理论,无法有系统地评估立新法或修法对受法律规范者之影响,将难期成效。
(二)物权法立法的效率目标[注]本小节内容摘录自张永健:“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之经济分析”,《“中研院”法学期刊》,2017年第21期。
物权法之经济分析,以极大化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为依归[注]知名法律经济学者Steven Shavell分析善意取得问题时,采用之极大化目标为“the expected value of property minus the costs of efforts”。See Steven Shavell,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9.笔者找不到Shavell更精细之解说。抽象来看,Shavell所刻画之目标与本文设定之目标,应属相合。。经济效率包括“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与“生产效率”(production efficiency)[注]参见张永健:“物权法之经济分析导论(二)——效率”,《月旦法学杂志》2014年第231期,第194~201页。。配置效率就是将财产权分配给较能利用者[注]参见张永健:“法定通行权之经济分析”,《“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12年第41卷特刊期,第1329页。See Richard A.Epstein,On the Optimal Mix of Private and Common Property,11 Soc.Phil.& Pol’y,1994,pp.17,31; Thomas W.Merrill,Accession and Original Ownership,1 J. Legal Analysis,2009,pp.459,488.。换言之,制度设计者要问,在善意取得之情境,系争物对原所有人或善意买受人价值孰高。若把配置效率看成是物权法欲产出之制度产品,就不容忽略生产效率。亦即,制度设计者必须谨记:配置效率之达成,也有成本考量[注]See Lee Anne Fennell,The Problem of Resource Access,126 Harv.L.Rev.,2013,p. 1471; Harold Demsetz,From Economic Man to Economic System:Essays on Human Behavior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9~114.。此处之成本,广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下面包含“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和“资讯成本”(information costs)两类[注]参见张永健:“物权法之经济分析导论(一)——事前观点与交易成本”,《月旦法学杂志》2014年第230期,第254~260页。。市场交易者需要征信,以了解买家的财力、卖家的信誉与商品品质、系争物是否有权利瑕疵,是资讯成本。买家担心征信不完美而制订复杂的契约条款,要求卖家提供担保或保证,是交易成本。就民法典物权编立法而言,两者的区分并不特别重要,因为都是成本,而制度设计者之部分目标是极小化制度费用,不管是哪一类的制度费用。设计、探究最有效率之善意取得制度时,必须兼筹并顾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
(三)比较法作为法学方法?
中国民法典立法过程中,应该反省比较法在立法论中的角色。本文认为,用于立法论中的比较法,必须是社会科学式的比较法。而社会科学式的比较法研究,是两重的因果推论[注]以下内容,改写引用自张永健:“社会科学式的比较法研究——评Mark Ramseyer.2015. Second Best Justice:The Virtues of Japanese Private Law.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研院”法学期刊》2017年第20期,第226~229页。。假设论者看到德国法有A条文,B法律现象或结果,中国没有A条文,而有C法律现象或结果。论者若认为B优于C,而倡议中国引入A条文,严格说来,必须立基于下述的两重因果推论:
1)德国若无A条文,不会有B现象(可能产生C现象或其他现象);或者,制订A条文使B现象出现的几率增高,或B现象更为普遍。用法哲学行话来说,A导致B是“差异制造事实”(difference-making facts)[注]关于差异制造事实在法学中的运用,参见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学期刊》2015年第17期,第234页。;用白话讲,A是因,B是果。
2)中国制订A条文后,由C法律现象转为B法律现象的几率增加。
然而,条文虽然是法律人最容易关注的面向,却不一定是某个法律现象真正或重要的成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相关的制度环境。因此,即令A导致B这个差异制造事实在德国成立,也不表示在中国一定成立。毕竟,两国的司法体系仍有不同,法院的诠释可能产生落差。两国的民族性不同,在德国会被完全遵守的条文,在中国可能会被绕过。换言之,两国的“背景条件”(background conditions)[注]关于背景条件,参见上注,王鹏翔、张永健文,第235页。不同,使得差异制造事实不会放诸四海而皆准[注]See Cf.Mathias Reimann,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839,847 (Mathias Reimann & Reinhard Zimmermann eds.).。
在所比较的国家(如上例德国)研究A是否导致B,不总是容易。如果德国从1900年制订民法后,一直有A条文和B法律现象,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很难论证A导致B,因为可能是X导致B,或者A+X+Y+Z导致B。若德国有修法,增加或修改或删除A条文,而法律现象随之变动,因果关系才可能确立。若德国没有修法,贸然倡议引入A条文至继受国,成效难期。
在继受国要论证A能否使C转轨成B,恐怕更为困难,因为A从来没有实施过,其效果必然基于预测。而预测的基础是其他条文与其他法律现象的因果关系之实证研究,对继受国背景条件的深刻掌握等等。而若研究背景条件后,发现法学先进国与继受国的背景条件有差异,则比较法律制度的政策制订者,还必须积极在继受国创设与先进国类似的制度背景条件。橘逾淮为枳,是因为水土不服,所以移植橘树之外,还要移土运水。但若橘逾淮为枳是导因于一般性的天气因素,则只能放弃种植橘树,改栽培其他可替代之植物。
或有认为,社会科学式的比较法研究,因为太过困难,几乎不可能形成政策。但学者研究本来就不可能只基于常识,否则何来创新?而且未经严格检验的常识,也可能奠基于错误的因果推论。再者,即使不是每个问题都能用最高标准研究,但如果时时能将最高标准放在心上,研究设计就可能尽量逼近最高标准,并且在呈现研究成果时,揭露研究路径的局限。例如实证研究的黄金律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但不是每个法律政策问题都可以用此种方式研究。实证研究学界退而求其次的实证方法,有“回归不连续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等方法[注]关于随机控制实验与回归不连续法的简要介绍,参见前注〔39〕,王鹏翔、张永健文,第248~251页。。而研究者因为现实世界的限制而只能使用观察式的数据、一般的多元回归模型时,更要对读者强调只能观察到相关性,不能做因果推论之局限。换言之,有高标准存在后,即使做不到高标准,也可以向上看齐,或承认研究局限所在。再者,中国仍然可以用试点的方式,在某些县市、某些法院实施,以评估政策改变的可能结果。
最后,主流的比较法研究,关注更短的因果链——A条文引入后,法院是否能据以采取某种法律见解。在法院依法判决的国家,此种因果关系通常会成立。但是A条文是否会在法院以外改变交易者的行为,同样必须考虑。所以,所有立法论中的比较法,都带有社会科学的因果问题,必须适切处理,必须以实证证据支持,而不能想当然尔。
三、现行中国物权法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批评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还没出台,但可以预期应该会受到现行物权法善意取得规定的重大影响。因此,从经济分析方法检讨《物权法》规定,将有助于展现经济分析的威力,并说明民法典物权编应该修正之处。《物权法》中关于善意取得之规定,是第106条[注]《物权法》第106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和第107条[注]《物权法》第107条:“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其中一大特色是将不动产与动产之善意取得并列规定。由于两者的资讯成本问题不同,实在不应该混为一谈。以下将聚焦于动产之善意取得。
(一)以“是否为遗失物”为区分,难助于配置效率
《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以“是否为遗失物”为区分,难助于配置效率。依据《物权法》第106条即时取得动产所有权的善意“买受人”[注]《物权法》第106条使用“受让人”,其概念广于“买受人”。但买卖不但是最典型的善意取得案型(至少在台湾地区是如此,参见前注〔7〕,张永健文),也是最容易清楚思考相关利弊的案型,故本文以买卖为情境,贯穿全文。,若买到的是遗失物,则两年内都可能遭原所有人追索。相较于德国法和台湾地区法,《物权法》较保护原所有人的情境不包括盗赃物,也不包括其他“非基于原占有人之意思丧失占有”之物,是特殊之处。然而,即令把盗赃物等非基于原占有人之意思丧失占有之物都纳入,仍无助于配置效率。
《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之规范方式要促进配置效率,必须原所有人和买受人的“保留价格[注]亦即,“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或在卖方称为“愿售价格”(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在买方称“愿付价格”(willingness to pay; WTP)。”(reservation price),符合以下关系:
遗失物:原所有人>善意买受人
(1)
非遗失物:善意买受人>原所有人
(2)
若此两不等式成立,《物权法》第106条使非遗失物的买受人获得所有权,《物权法》第107条使原所有人有机会取回遗失物,就是促进配置效率的法律规则。但是,这两个不等式会成立吗?任何动产都可能成为遗失物,为何在某物遗失时,原所有人的愿售价格会高于善意买受人之愿付价格;而在某物不是遗失物而被无权处分时,原所有人的愿售价格会低于善意买受人之愿付价格?很难想象此两不等式会成立!
换个角度想,若随意选定一个动产,如名牌钻表,若原所有人在遗失时,愿售价格较高,不是因为遗失而被无权处分时,愿售价格较低,则此两不等式可能成立。但为何有人的保留价格会以此种方式波动?原所有人会一般而言珍视自己遗失之物胜过自己未遗失之物,违背了至少是笔者的直觉。
或者,善意买受人在得知系争物为遗失物时,愿付价格较低,得知系争物并非因遗失而出卖时,愿付价格较高,此两不等式可能成立。或许有些买受人会因为得知系争物为第三人所遗失,而非卖方拥有,因而降低了其愿付价格。但若如此,买受人也可能会在得知系争物乃由第三人处偷抢拐骗而来时,降低其愿付价格。所以,为何单独保护遗失物?即使把盗赃物纳入特殊保护的类型,在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类型中,无权处分人能擅自处理他人之物,总是导因于某些见不得人的坏事,为何买受人不会降低其愿付价格?
总之,此两不等式要成立,必须原所有人和善意买受人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而多数人似乎并非此类人。如果没有坚强的说理,可以论证在(1)和(2)中不等式多半会成立,则从配置效率的理论观点,就无法证立《物权法》第107条的规范模式。
(二)以“是否为遗失物”为区分,难助于生产效率
《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以是否为遗失物而异其处理,无助于配置效率,但是否能节省制度费用(即有助于生产效率)?本文亦持否定见解。与动产善意取得问题相关之制度费用有三种[注]参见前注〔6〕,Schwartz & Scott文。:原所有人的防范无权处分成本(简称“防范成本”);原所有人之物被无权处分后,其搜寻失物成本(简称“搜寻成本”);受让人征信、确定出卖人是否为有权处分之确权成本(简称“确权成本”)。多保护遗失物,少保护非遗失物,若要有助于节省防范成本与确权成本,下列两项宣称至少要有一项成立:
1)原所有人防范动产遗失的成本高,而原所有人防范动产因其他原因被无权处分的成本低
此处之逻辑必须是:防范遗失、非遗失两种无权处分原因的成本是外生给定(exogenous and given),无法借由原所有人改变行为、习惯而变化。若肯认原所有人防范动产遗失的成本高,则应该在遗失物善意取得时,特别保护原所有人。因为一旦加强保护原所有人,原所有人就不会付出高额之防范成本。反之,而原所有人不能取回非遗失物,就会付出一定防范成本以避免其物被无权处分,但此处成本较低。若只在部分情况中保护原所有人,应该选择在遗失物情境为之,因为如此可以降低原所有人的总防范成本。
2)善意买受人辨识系争物为遗失物的成本低,而辨识系争物乃因其他原因被无权处分的成本高
此处之逻辑必须是:买受人可以较轻易地辨识系争物是遗失物或非遗失物,但要在系争物为非遗失物时,不太知道如何分辨有权处分或无权处分。若只能在部分情境中保护善意买受人,应该选择在非遗失物为标的时为之,因为如此可免除买受人做无谓的征信、调查。
本文认为,这两项陈述都不会成立,因为其背后的逻辑在大多数人身上都不适用。当然,这两项陈述都是可能证伪的理论假说,但确实难以获得精确数据检验之。不过,吾人仍可以尝试进一步做理论推衍,挑战这两项命题。关于第一点宣称,防范遗失之成本有人际差异,有人容易丢三落四,有人从不掉东西。再者,防范遗失物与非遗失物遭受无权处分的相对成本,可能有正相关(但似乎并没有坚实的实证证据)——容易丢三落四的人,在生活其他层面也比较迷糊,例如比较容易识人不明,从而容易掉东西的人,也容易被诈欺、被侵占、被他人将东西为无权处分。若然,宣称1)不成立。至于善意买受人之辨识成本,本文难以想象,遗失物会比较容易区辨为无权处分标的,道理何在。若宣称2)也同样不成立,则多保护遗失物之原所有人,无法找到降低防范成本与确权成本方面的论理基础。
至于搜寻成本,如果目标是降低(极小化)搜寻成本,则在多数国家采用的善意取得二分法框架(有时保护、有时不保护受让人)下,应该诱使原所有人在搜寻成本低时行动、搜寻成本高时放弃。在标的物为遗失物时,原所有人因为不知道无权处分人的身份,搜寻成本高;在标的物为德国、台湾地区法上所谓“基于己意而丧失占有”时,原所有人知道无权处分人之谁,搜寻成本低。因此,在此种思路之下,搜寻成本的论据会导出和现行中国大陆、德国、台湾地区法下相反的结论。亦即,原所有人丢失物品时,应该放弃追索受让人[注]绝大部分国家中,原所有人仍会将失窃一事报知警察单位,因为仍有在处分前寻回的机会。失窃后搜寻虽然从事后观点只是资源重分配,无关效率,但可以事前吓阻窃盗此种无效率的行为。;但所托非人而致物品被无权处分时,应该循线查获。请注意,本文并不主张此种相反的结论,因为此仅为考虑单一效率考量的结果,并非综合考虑所有效率考量的结果。此处所论者仅是:无法从搜寻成本及其他生产效率考量,证立现行中国物权法的动产善意取得规定。
(三)盗赃物
盗赃物在《物权法》中没有正面处理。学说有主张盗赃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注]参见高富平:《物权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55页。,也有认为盗赃物若在公开市场或拍卖购得,仍适用善意取得[注]参见前注〔8〕,王利民书,第456页。。对某些论者而言,《物权法》未如德国法或台湾地区法一般,正面处理盗赃物,或许是立法缺憾。但对本文而言,这是一大幸事,因为本文不认为盗赃物有必要成为特殊处理的标准。
为何要在无权处分标的物为盗赃物时,特别保护原所有人?上一节质疑给遗失物原所有人的较多保护的理由,在此亦同样适用。此外,如果是以减少盗赃物买受人保护为手段,以降低窃盗率,此种推论面临下述挑战:
1) 盗赃物较难适用善意取得之规则,就算为全民所知,买受人如何能获取资讯以分辨盗赃物与非盗赃物?若买受人无从分辨,此种规则只是整体而言降低了交易安全而已,并没有引导买受人改变行为。
2)若要借由此种规则,使无权处分人更常向买受人负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从而降低其无权处分之诱因,是舍近求远。刑法和侵权法本来就已经有处罚故意无权处分赃物者的刑事与民事责任[注]参见陈华彬:《民法物权》,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8页(公安、检察机关对盗赃物采取“一追到底”做法)。,且此种责任是无论有无善意取得都存在。以物权法作为吓阻犯罪的手段,且以“不许善意买受人取得所有权”作为代价,一定会降低交易安全乃至增加交易成本,但此种瑕疵担保责任是否有任何边际上的吓阻效果,本文高度怀疑。
3)是否要采用盗赃物规则,与中国的窃盗率高低、失窃后(处分前或处分后)寻回率高低有关系。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没有必要为了极少发生的窃盗,制订一个增加制度费用的制度。无论窃盗率高低,若失窃后一律可以即时寻回,就不需要盗赃物规则;如果大多无法寻回,则盗赃物规则也只是纸老虎。笔者对中国各地的窃盗率、寻回率没有深度掌握,也不知道官方数据是否可信,因此无法进一步申论。
(四)拍卖
《物权法》第107条规定,若买受人是以拍卖或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买,则受到额外保护。《物权法》上的拍卖,一定公开为之?笔者翻阅许多本权威教科书,似乎只有尹田教授引申了该条的文义。根据尹田教授之解释,拍卖是指有资质的拍卖机构依照法定程式而进行的公开拍卖[注]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根据此种解释,并不是任何以拍卖竞价方式选定买受人的交易,都符合该条文义;而必须是特定拍卖机构的“公开”拍卖方符合文义。这是非常重要的限缩解释,如下节所论,买卖场所公开与否,与经济效率有重大关联。
四、中国民法典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建议[注]本节部分内容改写自前注〔7〕,张永健文。
以经济分析探讨《物权法》问题,本文并非首开先河,学者对此问题运用经济观念者,不在少数[注]参见前注〔49〕,高富平书,第18~27页;申卫星:《物权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5~116页。。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各种动产交易之量,早居全球之冠。大胆地说,民法必然要透过善意取得制度维护交易安全[注]参见前注〔8〕,王利民书,第434页。类似主张(保障交易安全是市场经济的《物权法》的核心使用),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而且,相较于“静的安全”,更要保护“动的安全”[注]类似见解,参见杨立新:《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笔者关于此论点的详细论证,参见前注〔7〕,张永健文。。在此理解下,本部分将建构一套符合效率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一)以公开市场规则区别买受人之保护程度
法院难以个案判断两造孰为较能利用资源者。以促进配置效率作为设计善意取得制度之纲领,较佳的判断标准是“买受人是否支付市价”。买价低于市价,表示买受人之愿付价格可能低于市价,又因为原所有人的愿受价格(或言其经济价值)大于或等于市价,则让原所有人保有所有权,较可能提升配置效率。买价等于市价,则难以判断原所有人或善意买受人谁的价值高。至少,立法者知道,若要以配置效率之论理为基础,对善意买受人区别保护,应以是否支付市价为准,如此至少可以区隔出不值得保护之买受人。
有几种立法设计方式,可以落实此种观点。第一,直接以“买受人是否支付市价”作为善意取得要件,现行《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受让人必须支付合理价格,看似可以直接解释为市价。然而,2016年开始实施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规定“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称‘合理的价格’,应当根据转让标的物的性质、数量以及付款方式等具体情况,参考转让时交易地市场价格以及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认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并不支持以市场价格作为合理价格的唯一界定方式。
第二,结合《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和第2款,在买价低于市价,推定买受人为恶意。此种类型下,买受人比较容易善意取得,因为即使买价低于市价,在此种设计下,仍有机会举反证推翻其恶意,证明其善意。
第三,采用公开市场规则(market overt rule),即在公开市场销售或拍卖之物,善意买受人取得所有权[注]参见前注〔6〕,Schwartz & Scott文,第1334页。德国《民法》第935条、荷兰《民法》第3编第86条即为适例。。“公开市场规则”还有一个变体“公开市场补偿规则”,亦即在公开市场销售或拍卖之物,原所有人必须补偿善意买受人后方能取回所有权[注]法国《民法典》第2277条、日本《民法典》第194条、台湾地区“民法”第950条、瑞士《民法》第641条即为适例。《物权法》第107条则对“遗失物”之无权处分采取“公开市场补偿规则”。另据学者研究指出,这是从中世纪即发展出之规则。参见前注〔6〕,Salomons书,第1071页。。采用公开市场规则背后假设为,在公开交易场所购买者,买受人大多必须支付市价。
要降低善意取得制度之制度费用,必须买卖双方能以清楚明确的规则,预测交易之可能效力。换言之,要让(尤其是)买方能在合理查证仍无法确知标的物是否为无权处分时,确定能取得所有权,方不至于促使买方付出额外的查证成本,或放弃交易。但买受人所支付之价格是否为市价,并不总是容易在交易时查证;如果要判断《物权法》第106条之“合理价格”,更为困难,因为价格合理与否,带有法官主观、事后判断的因素,而不像市场价格是可以客观、事前确知。相对地,是否为公开市场,买受人多半可凭常识判断,制度费用较低。
是故,中国民法典若要制订善意取得制度,较佳的方式是以公开市场规则取代现行《物权法》第106条以遗失物为界定的规范模式[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规定“受让人受让动产时,交易的对象、场所或者时机等不符合交易习惯的,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已经为本文见解铺路——因为以公开市场为标准,就是因为应该考量交易对象、场所等因素。;以公开市场规则异其保护程度,也优于任何其他以原所有人之物遭无权处分的原因事实为界分的可能规范模式[注]同见解,参见王泽鉴:“盗赃物之牙保、故买与共同侵权行为”,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自版,1979年版,第229页[“动产能否善意取得,不宜就标的物设其区别,应依交易过程之性质而定。申言之,凡由拍卖或公共市场或由商人以善意取得者,不论其为盗赃(或遗失物)与否,均能取得所有权;反之,非依上述交易过程而取得者,纵其非属盗赃或遗失物,亦不能取得其所有权”];张永健:“论动产善意取得之若干问题”,《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1年第27期,第117~120页。。换言之,善意买受人若符合公开市场规则,可以取得所有权。若不符合公开市场规则,或买受人为恶意,则买卖效力未定;无重大过失之原所有人,得向买受人请求返还,无须偿还支出之价金。此外,为免公开市场交易价格低于市价,让配置效率之判断失去准头,可以再加上:买受人未支付市价者,推定为恶意。
公开市场规则有两层经济道理。第一,减少资讯成本与交易成本:无权处分者,无论处分目标是否为盗赃物,会尽量避免拿到公开交易场所贩售,否则可能暴露行踪而被查获。而无权交易者若找上“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注]根据尹田教授的解释,经营者是指“对与遗失物相同种类的物品具有合法经销资格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商人”。参见前注〔52〕,尹田书,第211页。”以求脱手,例如把偷来的汽车卖给二手车商,也可能因为专业经营者具备判断真假与权利归属的专业知识,而事迹败露。在公开交易场所出卖之物,与专业经营者所卖之物,通常都伴随处分权。准此,一律让买受人取得所有权,是因为多数情形是有权处分;在少数无权处分情形,选择保护(与原所有人同样值得保护之)买受人,让全体买受人都可以无须担心无法获得物权,因而节省征信成本。而且,买受人判断交易场所是否为公开市场,比判断标的物是否为盗赃物或遗失物更为容易。第二,配置效率:专业商人与公开交易场所中的卖家,在市场竞争下,其报价通常趋近于市价。买受人愿意支付市价,才代表其愿付价格可能不低于原所有人,因而构成保护善意受让人之经济理由。
不过,提倡公开市场规则而非迳用买受人是否支付市价为准,是为了节约买受人资讯成本。中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或许会认为,此两种规则的资讯成本差异有限,但《物权法》第106条用“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作为界定是否保护买受人之标准,已经运行约十年,为法官、律师等专业社群所熟悉。为节省制度转轨带来的混淆,本文也能接受全部保留现行《物权法》第106条之规定(但应该将“合理的价格”解释为市价[注]如前所论,物权法司法解释中定义合理价格之方式,必须予以限缩,而以市场价格作为最主要判断标准。其他司法解释中所提到的考虑要素,则是在市场价格范围很大时,用于限缩、特定。),但删除第107条之规定。如此,可以维持配置效率的判断标准,而相对于本文提倡之制度,略略降低生产效率。
但请注意此两种规则的生产效率落差何在:因为市价是区间,以市价支付与否作为善意取得标准,买受人所支付之价格是否落于法院认定之市价区间,较为不确定;此种不确定性会引发较多诉讼。而在市价(在本文提案下)只是推定是否过失之标准时,原所有人必须有信心能举证说服法院售价低于市价,且买受人无法以其他证据反证自己已尽合理查证义务时,才会有诱因提出诉讼。较多诉讼耗费较多生产成本。此即为何本文提倡之制度,生产效率较高。
(二)保留价格的自我揭露
即令认为《物权法》第107条之公开市场补偿规则,仍然有用,其用途也非保护盗赃物或遗失物之所有人,而是应该用来作“保留价格的自我揭露”(self-revelation of reservation prices)机制。详言之,公开市场规则已经用于作为善意取得与否之标准,公开市场补偿规则应该用于原所有人比善意买受人保留价格更高时。但法官如何知道原所有人比善意买受人保留价格更高?答案是:法官不用知道,因为原所有人会用行动告诉法官。公开市场补偿规则可以适用在(1)标的物是替代物,买受人从贩卖同种类物、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处购得,且(2)原所有人能说明标的物对其有特殊意义。例如:买受人从二手珠宝商处购得一只翡翠手镯,若原所有人能证明这是传家之宝,且愿意支付买受人其买价,则很可能原所有人比买受人更珍视此物,且买受人可以用受补偿之价金另外购买一只翡翠手镯。由于系争物对一般人是替代物,而且买受人又必须已经支付市价,如果系争物对原所有人并没有特殊意义,原所有人根本没有诱因要出价赎回,可以另外购买一只翡翠手镯,或将钱用于其他用途。原所有人愿意出价赎回一事,就已经告诉法官:他的保留价格必定大于或等于市价。要求说明标的物对原所有人有特殊意义,只是要进一步确保原所有人之保留价格会高于买受人;相对于原所有人愿意支付市价的行动,说明并没有这么重要。至于制度设计上只限于替代物可以适用公开市场补偿规则,是因为非替代物(例如梵高的向日葵画作)根据定义没有替代品,每个人都有其主观价值,难以被第三人观察。买受人之保留价格可能是9 999,但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么为梵高神魂颠倒,他只支付5 000就获得画作。如果容许原所有人出价5 000就赎回,并无法保证原所有人之保留价格会高于9 999,而买受人拿5 000所能购买的其他画作,并不一定对其有这么高的价值。
(三)以拍卖分配产权
再进一步申论,或许前述两要件(替代物、说明特殊意义)可以完全摒弃,而使用原所有人和善意买受人彼此竞价拍卖的程序。价高者得物,价低者获得金钱补偿。实际操作的结果,可能等同于公开市场补偿规则,也可能是反向由受让人付钱给原所有人。美国学者Ian Ayres & Jack Balkin多年前提出的higher-order liability rule(高阶补偿规则)[注]See Ian Ayres & J.M.Balkin,Legal Entitlements as Auctions:Property Rules,Liability Rules,and Beyond,106 Yale L.J.,1996,pp.703,711~717.,和本文此处所提出的想法相通:两者都不像一般拍卖,由确定有所有权之人主持拍卖,并获得拍卖金;而是竞争产权的人彼此竞价,竞价的其中一人会获得金钱,一人获得产权。Ayres & Balkin称之为“内部拍卖”(internal auction)[注]同上,第707页。。本文提出的想法,相较于高价补偿规则(容许任一方在一段时间经过后,再以更高价格取回系争物),则是更直接地运用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Vickrey教授[注]See William Vickrey,Counterspeculation,Auctions,and Competitive Sealed Tenders,16 J.Fin.,1961,p.8.(等人)发展出的“次价密封投标拍卖”(Second-price sealed-bid auction)。
当法律规则无法适切判断应保护原所有人或善意买受人时(例如无法系统性判断依据配置效率,系争物对哪一造价值较高;依据生产效率也得不出结论),即可运用本文提倡之机制[注]以下论述之数学证明从略;有意者可向作者索取。。此机制的第一个步骤是决定原所有人和善意买受人各拥有多少比率的产权,可以是0:100、50:50、100:0或任何比率。此比率可以是乱数决定,甚至可以不用告知双方其比率各为何。只要比率的决定和拍卖的结果无关,而且出价最高者要依据另一方之出价(因为另一方的出价必然是次高价)而付出代价,Vickrey教授的理论证明了,双方都会诚实地以心中的保留价格出价。如此,拍卖的结果就会符合配置效率。不过,得标者实际拿出来的标金,并非对方之投标金额本身,而是对方投标金额乘以对方的产权比率。假设原所有人出价120,买受人出价100。当产权是各半时,原所有人实际支付的价格是100×50%=50。当产权是受让人有九成时,原所有人实际支付的价格是100×90%=90。
无论此处的产权比率为何,都不会影响拍卖本身的配置效率性。因此,法律(或法律授权法院事后决定)正可以依据公平、正义、分配等非效率的理论,决定产权比率。
以次价密封投标拍卖处理善意取得问题,可以不限于现行法律与学说中最困难的价值判断情境。所谓最困难的价值判断情境,是指法律并未规定所有权当然无(时效以外)条件归属于原所有人或善意受让人,而以受让人在特定条件下受让作为保护前提,或者要求原所有人补偿受让人方得取回物之占有(与所有权)。无论是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善意取得规定,无论在困难或不困难的价值判断情境,其实不脱使用0:100或100:0的产权分配比率。换言之,不是全部由原所有人拥有、取回,就是由善意受让人即时取得。由一方单独所有,相对于共有,有效率好处[注]所有权共有可能导致共决问题(anti-commons),并产生效率损失。参见前注〔4〕,张永健书,第58~59页。,因此有一定道理。但在本文提倡的机制下,无论产权在拍卖前如何配置,在拍卖之后都由一方单独所有,所以使用0:100或100:0以外的产权分配比率,不会带来效率损失。而一旦非极端的产权分配比率成为可能,立法者就可以更细致地依照各种分配面的规范理论,以及经济分析理论,调整不同行为表现的两方的产权分配比率。例如:法律可以规定从0:100,即善意受让人取得全部产权的基准开始;若受让人善意有重大过失,则善意受让人损失50%产权;若受让人未在公开市场购买,损失40%产权;若为盗赃物,损失60%产权等等。当然,最极端也只能调整为100:0。若立法者认为制订此种比率调整太过困难,也可以直接授权法官在个案中斟酌双方行为表现,定下产权比率,再让双方进行拍卖。
本节探讨的立法可能性,是以前沿的法经济学博弈模型,设计出现实可行的法律制度。笔者明白此种倡议距离现在的立法方式过远,或许无法立即为人接受。但如同Ayres教授另一本书的标题所问:Why not?[注]See Barry Nalebuff & Ian Ayres,Why Not? How to Use Everyday Ingenuity to Solve Problems Big and Small,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中国迟至2020年方制定民法典,应该享有“后发者优势”(late-comer advantage),而不是坚持要背负着罗马法以来2 000多年的法学枷锁。要建立中国特色,此其时也!
(四)建立“原所有人重大过失”的失权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向来都只关注买受人之善意,也有学者特别强调善意与否和让与人无关[注]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但由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的考量出发,没有道理只关注其中一方是否有付出最适努力获取资讯,却完全不在乎另一方是否付出适当努力避免其物被无权处分。尤其是无权处分后,若原所有人追究此事,许多制度成本(像是公安、法院)都外部化由其他纳税人负担,使得原所有人本来就没有最适诱因防范,如果无权处分的规范再度忽略原所有人的作为,只会让原所有人的诱因雪上加霜。本节将提倡:善意买受人在非公开市场上购得系争物,但原所有人对无权处分一事有重大过失时,例外使原所有人不得请求买受人返还[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5条,如同德国和台湾地区,将买受人之善意限于无重大过失者。在区分买受人的善意是否值得保护后,进一步区分原所有人的丢失是否值得保护,解释阻力应该较小。。
原所有人未善尽防范之责,导致其物被他人无权处分,不应赋予其返还请求权[注]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是欧洲学者整合私法规范的重要文件,其VIII-3:101之Comment D说明,遗失物与盗赃物区别处理,是因为遗失物被无权处分,导因于原所有人之过失。由此可知,DCFR之撰写者,也隐然将原所有人之过失纳入考量。但是,东西被偷,有时也是原所有人过失所致。DCFR之撰写者并未考量此点。。原因是:原所有人若能付出合理成本,离家锁门、疑人不用、行事谨慎,就不会掉东西。没有无权处分事件,就不用动用公安、检察官、法院等纳税人大幅补贴的公共权力。直白地说,原所有人自己疏忽把一个行李箱的Rolex放在酒吧,导致全部名表被无权处分;在《物权法》第107条的构成要件下,这样的原所有人仍比善意买受人更受保护,有道理吗?所以,从事前观点[注]关于事前观点与事后观点的区分,参见前注〔4〕,张永健书,第24~29页。,若不论原所有人是小心谨慎还是粗枝大叶,都一律可以动用宝贵的法律体系资源,进而干扰善意买受人对系争物之所有与利用,并非最佳诱因机制。但必须注意,规定原所有人要无重大过失地保护自己的所有物,从事前观点,不会改变许多人的行为;因为多数人多数时候,都已经用更强的注意程度,保护自己的财产。准此,剥夺重大过失原所有人的返还请求权,仅能小幅改善物之所有人之行为。
从事后观点设想,不保护有重大过失的所有人,有额外的经济意义。第一种切入角度是,如果规定有重大过失的所有人,一律不得请求返还,则此种原所有人遇上无权处分,就自认倒霉,免除后续利用法院等制度成本。但是,有重大过失的原所有人不可能因为此种规定就当然放弃追索,因为无权处分人可能尚未完成处分,买受人也可能并非善意,而警察的调查成本不用原所有人负担。是故,有重大过失的原所有人还是会做一定的追索。所以,此种切入角度,无法完全证立排除有重大过失之原所有人请求返还。
第二种切入角度是,事后比较个案当事人之保留价格。在天平上被比较的两造,一个是有重大过失原所有人,一个是可以证明自己善意,但未在公开市场购买系争物的买受人,两者都(至少曾经)有高于市价的保留价格。但或许原所有人以重大过失方式防范自己的动产,显示了他的保留价格或许已经降低。因此,买受人比较有可能是较能利用资源的一方。
综上所论,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做如下设计:买受人“善意+非公开市场购买”,可以在原所有人有重大过失时,使买受人保有系争物;而买受人恶意时,原所有人纵有重大过失,仍不丧失返还请求权。换言之,对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而言,其善意比“在公开市场进行交易”更为重要。原因在于,公开市场只是辅助判断买受人是否支付市价的“代理变数”(proxy)。在本文制度下,买受人如果可以举证成功自己善意且支付市价,公开市场要件不备,仅有次要意义,因为此时买受人的愿付价格是大于或等于市价。至于买受人若为恶意,则由买受人停止购买无权处分物之行动,最能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制度设计上,自然应该让恶意买受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获得动产所有权。
五、结论
本文铺陈了效率观点的民法立法方法论,并展现如何由抽象至具体应用此套方法论于善意取得问题。效率观点挑战了传统物权法学说、比较法制中的既存规范,主张“以原所有人因何缘故遭遇无权处分(遗失、盗赃……)作为改变买受人保护方式之规范”,并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可以支持。若要在乎物尽其用,重点是买受人或原所有人谁的保留价格较高。若要在乎节省社会资源、引导交易者行为,则善意取得之规范必须奠基在交易者在买卖成交前就能判断的标准(例如是否在公开市场交易),而非以交易者几乎不可能查证的资讯(是否为盗赃遗失物)作为判断标准。后者的规模模式,无法让交易者避免购买盗赃遗失物(因为交易者通常无法辨识标的物是否为盗赃遗失物),只是让交易安全水平整体下降。若要在乎善意取得制度造成的整体社会成本,也应该关注原所有人的防范水准。如果原所有人无论如何离谱行事,都仍因为系争物遗失了或被偷了而获得较多之保护,原所有人就不当然会付出最适防范。
本文并没有主张中国民法典的立法只应该考虑效率。本文的主张是,中国民法典的制订,一定要考虑效率。而如果要考虑效率,就必须用严谨的经济方法论,一以贯之地考虑。当各民法问题的效率考量铺陈出来后,再与其他理论架构一以贯之推导出来的立法建议,一起参照比较。如各观点的见解一致,立法者可以信心满满;如果各观点立场不同,则立法者必须取舍。学者、实务工作者固然方法论各有不同,但都应明了自己只摸到大象的一条腿。当社会资源不足时,我们只能刻画大象的一部分,但我们必须谨记在心,失去的是哪一部分。
——兼论《民法总则》第171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