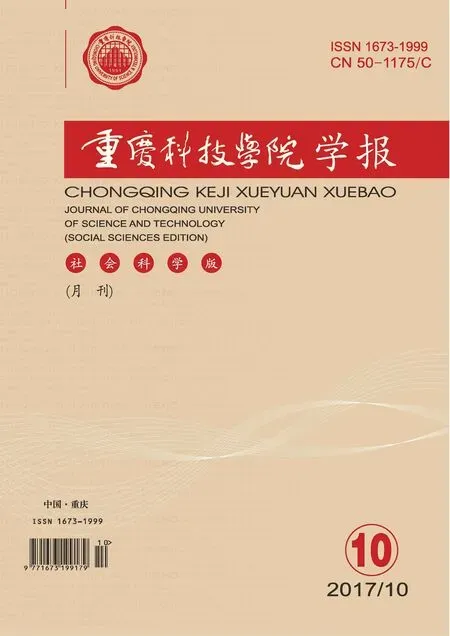论迈克尔·坎宁安《试验年代》中的创伤体验
傅婵妮
论迈克尔·坎宁安《试验年代》中的创伤体验
傅婵妮
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在小说《试验年代》中叙述了3个人物在19世纪工业革命中丧失家园、21世纪 “9·11”袭击后寻找家园、150年后在遗失的家园中渴求家园的创伤经历。作者借小说谱写出一首哀婉动人的家园恋曲,表达了作者对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忧思,对美好家园强烈的渴求以及向传统价值观念回归的倾向。
迈克尔·卡宁安;《试验年代》;创伤体验;家园
痛苦和创伤是人类情感体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源泉。“创伤”(trauma)一词,原指“身体遭受的伤害”[1]3。 但在弗洛伊德看来,“创伤”更指向“对精神的伤害——精神在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经历中的破坏(breach)”[1]4。 弗洛伊德将“创伤”拓展到了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创伤的理论性研究逐渐升温,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文化等领域,创伤的伦理、文化、社会意义被更多地挖掘。进入21世纪,“9·11”恐怖袭击再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时至今日,恐怖袭击接连不断,给遭受灾难的国家和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因而对“创伤”的思考、研究和书写具有了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验年代》(Specimen Days)是美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普利策”最佳小说奖得主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1952—)的作品。 他设纽约为故事发生地,展现了西蒙(Simon)、凯瑟琳(Catherine)和卢卡斯 (Lucas)3位主要人物在19世纪工业革命中丧失家园、21世纪纽约遭遇“9·11”袭击后寻求家园以及150年后渴求家园的创伤经历,用美国民族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串联起这3位主要人物的宿命,将人物的故事杂糅进宏大的时代背景中,复调式地凸显了作品对创伤的书写,表达了他对家园的眷恋与渴望。
一、机器离散家庭的创伤
小说的第1节“在机器中”,以19世纪下半页的纽约为时空背景,叙述了机器致人于死地而导致家庭离散的创伤故事。当时的纽约已进入到了机器大生产时代。西蒙年方20,迫于生计而工作,却不幸被机器夺走性命,化为幽灵躲在机器里表达对家人与家园的思念。他的未婚妻纺织工凯瑟琳以泪洗面。他的弟弟卢卡斯年幼而善良,为减轻家庭重负,怀着丧亲之痛顶替哥哥工作。本将组成的家庭,好端端的家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创伤事件而瞬间丧失了。
机器对家庭的离散是由机器对人的禁锢与异化引起的。卢卡斯在厂房里就觉得“这里好像不是工厂,而是马厩或农场,机器就如表情平和的牲畜一般”[2]30,他感受到了机器的冷酷无情。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长期单一重复的动作,卢卡斯深感到:“在工厂里,时间是那么漫长,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不断反复,就是一个小世界,住在里头的人,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偶尔会到另个世界吃饭休息,然后再回到这里。这里的人都放弃了原来的身份,移民到了工厂……”[2]64。
机器使人异化,人变成了机器。工厂的监工“说话时只有嘴巴在动,好像就是个钢铁做的人”[2]28。机器的噪音让卢卡斯最终知道原来哥哥“走入了机器世界……他通过机器的嘴巴对活人唱歌”[2]97。人归西后不像惠特曼说的会变成草,而成了机器。弗洛伊德认为“事件性的创伤,是由离开的行为所承载的……不仅对离开的人……也与那些因事件而遭受创伤并试图弄明白事件的人有关”[1]4。 “自由地离开”不是“生的自由,而是死的自由:在离世时向他人传递自己的声音”[1]4。 西蒙的离去仿佛获得了“死的自由”,但依然没有离开机器。机器扭曲了卢卡斯的心灵。他十分害怕凯瑟琳也被机器掠走,不惜自残来阻止凯瑟琳回到机器旁边,从而使凯瑟琳躲过了工厂的火灾。这一切努力就是卢卡斯想要战胜机器神,延长凯瑟琳的生命,带给她未来。西蒙用生命,卢卡斯用决心与肉体战胜了无情的机器,保护了家人。在死亡与保全,牺牲与奉献间,坎宁安似乎暗暗为创伤的抚平寻找良方:以爱的名义、用爱的行为与决心抚慰创伤的心灵。
二、恐怖袭击破坏家园的创伤
小说第2节“孩子的圣战”发生在遭受“9·11”袭击后不久的纽约。黑人女警凯特(即凯瑟琳)负责寻找和破获一起炸弹恐袭案件。而制造恐袭的人是 “圣战组织”中的一个孩子。孩子利用凯特对自己已故孩子的思念获得凯特的信任,唤起她无处寄托的母爱,最终使凯特落入他的陷阱。
作者将现实中恐怖袭击对社会家园地破坏与小家庭的丧子之痛连结起来。凯特的创伤融入到了“9·11”空袭后悲伤气息弥漫的纽约,虽然在小说的第1节中失去爱人的凯瑟琳在本节中与男友西蒙相爱并团聚了,但却遭受了丧子之痛。她经常沉浸在对逝去孩子的回忆中,“如果卢克还活着,今年应该12岁了……他一定还在某个地方……不在天堂,也没变成幽灵,但他就在某个地方……在这个危险重重的世界,她只相信此以及正义得到伸张”[2]295。 凯特强烈的母性和善心战胜了她的职责感,当她看到制造恐袭的孩子时,她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就独自带着孩子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情节安排更加烘托出丧子之痛带给凯特的精神创伤,也折射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文化思潮急剧地向传统价值观念回归的趋势:人们对家园及家园所代表的价值表现出更加热切的渴望[3]119。
孩子对成人善与爱的利用更让人感到了恐袭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破坏与造成的精神创伤。孩子在得知凯特故去的孩子名为卢克(即卢卡斯)时,故意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叫卢克。但我也可以叫卢克,难道你不觉得吗?”[2]433在思子心切与爱的善意中,凯特以为她获得了孩子的信任,却未料到这不过是孩子设置的陷阱。孩子说:“你现在也是家人了”[2]436。 所谓“家人”是指凯特也成为了恐怖分子大家族中的一员。凯特才意识到“他是杀手……她突然明白,她已经掉进去了”[2]437。恐怖组织早已使孩子丧失了应有的纯良,不相信除“圣战家人”外的一切善与爱,唯有毁灭目标的念头,这便是精神家园沦丧的深深悲哀。可当凯特意识到这点时,却已回不去了,“她还是想当他的母亲……他已经杀死她了,不是么?”[2]438作者透过本节的故事仿佛在诉说光凭爱是无法抚慰创伤的,仅靠爱与善也无法拯救创伤的世界与灵魂。
人们对恐怖袭击破坏家园的悲痛被作者巧妙地通过一个不论气质还是外形都很像19世纪的美国民族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妇人之口道出,她仿佛是诗人惠特曼的轮回转世。她认为惠特曼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预言幻想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到:“冲动、冲动、冲动,世界不停繁衍的冲动……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重新来过。重新来过什么?世界。受伤的世界”[2]371。当凯特问妇人,世界会如何重新来过时,妇人只能摇头地感叹“孩子已经死了”[2]372。 这句双关语既指其他制造恐袭的其他孩子已经随着人肉炸弹而毁灭,也指孩子的纯真已经丧失,他们已不再是人类印象中的孩子。丧失孩子的家园是残缺和没有希望的家园,这样的精神创伤是永远无法愈合的。这里作者再次严厉声讨了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他们对人类家园的破坏是惨痛的。
三、核辐射摧毁家园的创伤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类似于美”围绕对美的感知和渴望展开。作者将故事推进到了150年后的纽约,悬浮车、机器人等高科技在那时已经变得普遍,但核泄漏事件让整片地区了无生机,满目苍夷,基本没有人类的踪迹。核辐射对地球家园的摧毁与人物对美与家园的渴求形成了强烈的比照。来自“纳迪亚”星球,外形酷似蜥蜴的凯瑟琳遇见了生物机器人西蒙,为了弥补自己身体的“欠缺感”,西蒙决意去寻找制造自己的科学家。善良又富于正义感的凯瑟琳决定帮助西蒙,找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人类小孩卢克,3个人结伴而行。最后,奄奄一息的凯瑟琳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爱上凯瑟琳的西蒙错过了前往另个星球的飞船,独自向西进发,卢克搭上了飞船,去向了一个好坏不得而知的星球。分离的结局寓意在地球家园毁灭的情况下想要拥有个人的家园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
本节中,凯瑟琳与西蒙都无法感知美。西蒙说“我有种欠缺感……我知道何为美,也可以理解它……但是我却感受不到”[2]514。 虽然西蒙体内被插入了“读诗芯片”,以除掉机器人可能的极端和暴力,变得更有道德感,西蒙却觉得他没有与世界产生连接感。凯瑟琳的“纳迪亚”星球意思是“空无”的星球,因为她知道星球的富庶和智慧始终无法形成,既然无法形成智慧,也就无法感知到美,这也就是她在西蒙说出“美”这个词时,感到十分诧异惊愕的原因。
在此,作者以小见大,借两人的感受批判以核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对地球与人类的毁灭。在一个美已不在的星球渴望感受美,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也是人类心灵创伤的写照。而这种反讽的效果通过西蒙对旅途中所遇事物不断地赞美得以强化。在西蒙看到蜥蜴凯瑟琳时,他暗自赞美她;当他们在遭受核辐射的水中游泳时,他赞美到“多美啊,动物!多美好,我的灵魂!多美啊,地球和地球上细小的生物!”[2]587,即使上岸后他们马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呼出的气都具有放射性。无法感知美,表面上是制造西蒙技术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美已不复存在,无法感知美就是自然的逻辑。小说中,核辐射过后纽约及其美国他处荒芜的模样与西蒙对所见事物与景象的赞美交织并叙,在不断地表现科技之破坏性的同时又不断唤起人们对美的渴望与回忆,营造出一种更深沉的幻灭感和对科技更掷地有声的批判,渲染出了一种厚浓重的悲观情绪。
四、结语
《试验年代》中的3个主人公实际代表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间的关系与组合象征着千千万万的普通家庭。作者将故事从小家到社会之家再到地球家园层层推进,从身体的创伤升华到精神家园缺失的创伤,通过书写机器离散家庭的创伤、失去孩子的母亲寻求孩子与精神家园的创伤以及人类在荒芜的家园对新的家园的渴求,表达出对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忧思,抒发出对美好家园的眷恋与渴望之情,表现出向传统价值观念回归的倾向。但这一创伤难以愈合,因为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困境正是人类自酿的后果,而作者只能借书写家园毁灭丧失的创伤表达对家园的眷恋与渴望,谱写出一首哀婉动人的家园恋曲。
[1]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2]CUNNINGHAM M.Specimen days[M].New York: Farrar,Straus&Giroux,2005.
[3]江宁康.文学想象与民族认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9.
I106
A
1673-1999(2017)10-0069-02
傅婵妮(1980—),女,硕士,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7-06-20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美国当代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小说研究”(15C0564);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英语专业教育中的文化批评精神与文化信仰培育研究”(XJK016BGD026)。
(编辑:王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