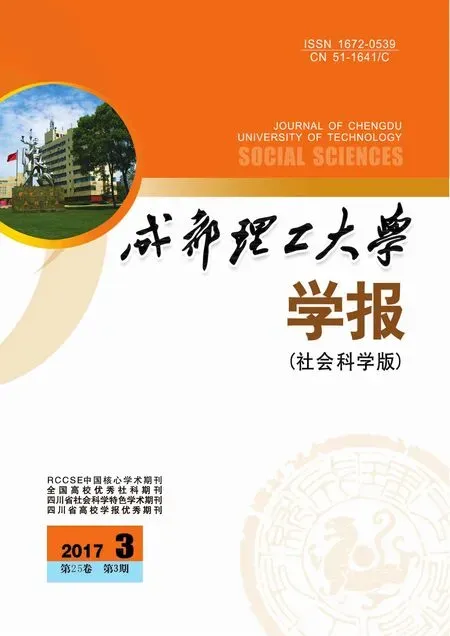迷人的疼痛
——论《小城之恋》的虐恋书写
王晓芳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迷人的疼痛
——论《小城之恋》的虐恋书写
王晓芳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在人类复杂的精神图景中,虐恋作为性欲的特殊形态引人侧目,出现于1986年的《小城之恋》以其纯粹浓烈的性爱描写展示出欲望强大、不可抑制的原始力量。小说的生存环境虽然抽空了政治成分,但虐恋以癫狂的姿态暗示着特殊时代对人性禁锢,及其可见不可说的微妙与残忍。身体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相互倾轧,欲望在人性的角逐场上艰难求生,虐恋成为饮鸩止渴的选择,而真正的救赎来自生育冲动,在神秘的自然力量面前她注定会超越他。
《小城之恋》;性欲;虐恋;超越
在社会风气初现开化的征兆里,《小城之恋》犹如晴天惊雷,让人们看到了王安忆不同于以往温情柔和的一面,她以锋锐不可挡的姿态,在文学的禁域攻城略地,在对性欲的描写尺度和研究深度上都令时人不禁咋舌,所以当时甚至有人将“三恋”归入性爱小说一脉。但时至今日再侧身反观,与当下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相比,其笔触的含蓄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独特性在于将性欲以虐恋的方式打开。
虐恋是一个英译词,由潘光旦先生首次译介过来,“sadomasochism”由“sadism”(施虐倾向)和“masochism”(受虐倾向)合成而来,施虐与受虐的角色定位并不绝对,它既可共存于一人,也可随时在双方间自由切换。关于虐恋的理论研究在国外已经十分充分,而在中国李银河是虐恋研究的集大成者,在博览国外的相关专著后,她将虐恋定义为:“它是一种将痛感与快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1]6抛开这种狭隘的定义,一些研究者认为虐恋不仅仅是一种性活动,凡是能产生快感和满足的非性活动也可归属于虐恋范畴,比如语言虐待、肢体虐待等。由于虐恋表现形式的极端性,它一度被人视为某种精神疾病,比如弗洛伊德就这样断定“所谓虐待症,实则是性本能中侵略成分的独立及强化。”[2]这种看法沾染着其职业习惯,不免武断。在心理学家的一些后继研究中,发现一定程度上的虐恋是人类的正常心理机制,具有自我疏导和治疗的功能,它在生理和心理之间衡量调配着外界的压力,从而实现身体和心灵的动态和谐。但超过安全范畴,表现出暴力倾向并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虐恋则是一种心理疾病。
一、朦胧的欲望
人类的欲望具有丰富的层次性,食、色为自然属性的欲望,名、利为社会属性的欲望,当食欲随着婴儿的呱呱降生而出现时,性欲则沉睡在它柔软的肉体里,随着身体的逐渐成长,性欲在朦胧中识别出自身的存在,开始蠢蠢欲动,而此时文明社会里的道德规约已然内化为个体的心理自抑机制。
(一)被展览的身体
“虐恋倾向主要来源于焦虑感和恐惧感,其一是焦虑与惩罚,其二是快乐与宣泄。”[1]174《小城之恋》中主人公的虐恋情结来源于身体初醒时所受到的心理伤害,由于受教育少,加之年少缺乏世俗经验,他们的心理防御机制非常脆弱。从省艺校舞蹈系来的老师“还特特地将她拉到练功房中央,翻过来侧过去的让大家参观她,尤其是典型的腿,臀,胳膊。”[3]116将她的身体作为一个训练失败的典型,在众人面前进行展览的行为无疑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精神惩罚,这是中国古老的示众文化的文革版,在以仁善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中,人们通过“看”的行为无声地宣泄着内心积郁的暴力,而被看者即为受虐者,十二岁的“她”虽然颟顸混沌,但在内化于心的耻辱文化中,她朦朦胧胧地从众人的目光中感受到了羞耻。示众带来的巨大心理伤害激活着她自我保护的本能机制,“为了克服这羞耻,便做出满不在乎的傲慢样子,更高的昂首挺胸撅腚”[3]116,性格粗犷头脑简单的她选择以逃避的方式面对窘境,事实上内心的伤害并未因此消弭,它们只是暂时潜伏起来,等待着宣泄的机会。在满是阴阳头、高帽子、大字报、游街示众的年代里,由于女性身体有着几千年被“观赏”的传统,似乎更容易成为被展览的对象。
与此同时,他似乎要幸运很多,虽然十八岁的他长着一副小孩的身形和一张老成脸,但却逃过了示众的厄运,然而他始终逃不过自我的内省,在与常人的比较中,畸形的身体带来的自卑在心里悄悄酝酿,等待着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释放。
(二)被遣返的痛苦
他们身体的畸变虽然正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似乎有着相同的缘由——错误的练功方式,练功房里的朝夕相处,同病相怜的痛苦把这两个正处于身心萌动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她畸形的身体、浓重的体味让她的女伴避之不及,被孤立的自卑的情绪被深深压抑,她以物以稀为贵为由,为自己被同伴指认的所谓“狐臭”辩护,然而这种阿Q式的自欺方式始终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即便她能用这种倨傲的态度来掩饰伤痛,但也改变不了疼痛的事实,与她高调的反抗方式相反,他选择在沉默隐忍里孤独地消化着自己的苦闷。当纯粹的心理机制无法治愈受伤的心灵时,因身体造成的心理伤害将再次被遣返回身体。“当她做着日常生活绝不需要举手投足的舞蹈动作,良好的自我感觉便逐渐上升……当他耍着难度极大的工夫时,心中的感情竟是壮阔的。”[3]120内心里被压抑的痛苦和焦虑随着淋漓的汗水宣泄而下,欲望遵循着唯乐原则,在身体和灵魂的立体空间里驱逐着来自外界的痛苦。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将源于畸形身体的精神痛苦遣返回高强度的肢体训练所产生的疼痛中,并在肉体的疼痛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是超越性满足的广义上的虐恋表现,“受虐倾向是自我对来自各种方向的内外威胁的自我保护反应,既有回避危险的性质,又具有寻求满足的性质。”[1]181外在的伤害不可预测,而虐恋中的痛苦具有自我选择的确定性,对于忐忑的心灵有着显著的安抚作用。
二、裸奔的性欲
文明建立在对人性的规约上,学校、军队、监狱等社会机构在权力的运作下,批量生产着合乎规则的社会成员,然而人们的欲望可以在惩罚的威胁中被遮蔽,却不可能被消除。《小城之恋》的故事虽然发生在文革期间,然而王安忆似乎有意抽离时代背景,以性自然的方式讽刺着时代的荒谬性并揭示出政治对人性的残酷镇压。在1986年作家们以笔为刀、以高扬性欲的方式呼吁并解放人的热浪中,王安忆的冷静深刻之处在于她既看到了性欲给灰色的人群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看到了性欲的洪流泛滥后灵魂的满目疮痍。
(一)初尝禁果的快乐
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提到因夏娃亚当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故而产生了带着原罪的人类,性欲就像成熟的禁果,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即便冒着被惩戒的危险,他们也阻挡不了彼此身体的吸引。然而身体苏醒还需要成熟的心灵来牵引,实验表明同龄的男孩和女孩不仅在身体发育上存在差异,而且在心理层面上也存在距离,相同年纪的男孩较之于女孩心理上更为稚弱,《小城之恋》中他比她大四岁,虽然他们的身体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在心理状态几乎是对等的,甚至他更为成熟一些,这为他们彼此身体的接近提供了精神平台。同为异群者的他们,同病相怜且彼此间朝夕相对,下腰开跨踢腿等练功的动作也是在彼此的帮助下完成的,然而在日日的身体接触中,他心中那种欲望从萌发到澎湃,似乎越来越难以抑制。“他再也克制不了内心的骚乱了。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止,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背上,肩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当他为她开跨的时候,他心里生出一股凶恶的念头,他想要弄疼她。”[3]125这段并不暴露的文字极具性意味,身体里倾泻下来的何止是汗,还暗指男性身体里代表着欲望的液体,而此时的他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所有的举动都朦胧地听从身体和心灵的指引,模糊里他感知到似乎她身体的疼痛能够让他感觉到满足,而这种行为正是对性爱中女性肉体疼痛的模拟,也是溢出狭隘的性器官享乐的性爱模式。性欲在他们各自的身体里慢慢苏醒,而当他们还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它被他们以怒火的形式莫名地释放,或假借练功的名目在彼此的肢体接触中暂缓各自身体的饥渴与焦灼。在几经或真或假的交战与和解后,在他二十一岁,她十七岁的这年,她身体里无穷的渴念不停地折磨使她倍感痛苦和寂寞,因求助于食物对口腔的慰藉而使本就夸张的身体更加肆无忌惮地膨胀;此时的他已然清楚自己痛苦的根源,性欲的不能满足导致了他的食欲不振,因而形容消瘦而憔悴。此时的他们因为无法得到直接的性欲满足,便将由此而来的焦虑诉诸于语言虐待,它“是指一些对人具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语言,是一种心理暴力行为。”[4]小说中他们的关系几经曲折,尤其在彼此怨怼不愿意有肢体惩戒时,常以语言暴力的形式发泄性欲不得偿的焦灼,“我恨你,我要杀你。”“再嚷,就掐死你。”[3]150,等等,这些语言对心理的伤害也是虐恋的一种精神表现形式。
直到舞蹈《艰苦岁月》上演的时候,激昂的音乐使他们回想起那次排练时身体的亲密接触,欲望终于酝酿到顶峰,一泻而下的快感让他们忽然变得容光焕发,“她面色姣好得令人原谅了她硕大笨重的体态,眸子从未有过的黑亮,嘴唇从未有过的鲜润,气色从未有过的清朗,头发则是浓黑浓密……他,则是平复了满脸满身的疙瘩,褐色的疤痕不知不觉地浅了颜色,毛孔也停止分泌那种黄腻腻的油汗,脸色清爽的多了,便显出了本来就十分端正的五官。”[3]144-145这是性欲在得到满足之后,年轻的生命力的自然展露,此时王安忆对自然性欲的积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男女主人公刚从混沌里走出,对身体欲望的思考还来不及达到精神的高度,所以撇开爱情不谈,即便是纯粹的身体渴念和满足在王安忆看来也是合乎自然人性的,即便这种身体的渴念以虐恋的形式展现也不妨碍其合理性的存在,做爱时他们彼此间撕、咬、扯等粗暴而疯狂的动作反而更加彰显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也暗讽了环境压抑的残酷性。
(二)狂欢后的空虚
有西方的性学家甚至将性欲满足认为是治疗一切心理疾病的有效手段,虽然这样的论断不尽妥善,但性欲的满足对身体与心灵健康的重要性是可见的;然而欲壑难填也是性欲必须面对的困境,欲求无度的结果是以自救的名义走向自戕。“使自己沉浸在‘一场折磨的狂欢宴会’中,寻求痛苦的狂喜经验,受折磨是痛苦的,但是让自己沉浸在极度的折磨之中,反而可以冲淡痛苦。”[1]194虐恋带来的预期中的痛苦和快乐,让他们像温水煮着的青蛙渐渐沉浸其中,由于缺乏健全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他们发现时已然不能自拔,纵欲后莫名的空虚与失落,内心对性道德模糊的认知,因性欲失控而产生的羞愧与自责都成为这场虐恋所负载的消极后果。
传统的性道德以生育为标准,弃绝一切淫荡的肉体享乐,而他们却享受着这场道德和性欲激烈交锋的战争,在恐惧中迎受着莫大的快感,精神的鞭笞似乎加剧了身体对受虐的渴望,他们的做爱就像一场场搏斗,撕扯着纠缠着抵抗着,直到筋疲力尽。这种对身体惩罚式的做爱方式“源于对性行为本身的负罪感”[1]181,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承受一定的折磨就是逾越规则的代价,以便得到等价交换的安全感,并且心甘情愿地领罚以减缓他们内心的罪恶感和羞耻感。此外他们不知收敛拼命尽情地厮打做爱,似乎越疼痛就越快乐,哪怕鲜血淋漓也在所不惜。这种疯狂的需求使彼此既成为施虐者又是受虐者,角色的动态双向转换只因为“受虐的冲动来自对爱的需求。”[1]194对爱的疯狂索求源自对孤独的焦虑,他们两人自十几岁时便生活在剧团里,虽然过着集体生活,但他们怪异的体貌和性情使他们很难融入人群,孤独成为不可避免的精神常态。现代科学证明,焦虑会造成血管收缩,产生冷的感觉,而一定程度的击打疼痛能加快血液流通,使身体产生温暖的感觉,他们甚至无需借助对方:“粗糙的树皮摩擦着她的手心,微微地擦痛了却十分的快意……沁凉的柳条勒进了脖子,越勒越深,那沁凉陷进了肉里,他几乎要窒息,却觉得很快乐。”[3]159这两个都有受虐倾向的孤独者有着相互吸引的心理基础,他们虐恋就是一种彼此取暖的行为,越渴望温暖就越渴望受虐,就越加疯狂地做爱,在这种恶性循环里,他们就像鸦片吸食者,越吸越多,作用却越来越小,身体和精神则越来越虚弱。“这时才感觉到悲哀与悔恨,可是,一切早已晚了。”[3]149因为他们自觉性欲的肮脏不堪,而又无法自控,不管是有头脑的他还是没有头脑的她,都被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神秘的力量驱使着,停不下来。
三、他被她超越了
在这段无休无止的虐恋中,肉体的折磨是肮脏的,在经历了一场场肉搏似的性爱之后,由于对彼此身体的稔熟,他们越加麻木,很难在从彼此的身体里找到刺激和战栗的快感,每次筋疲力尽之后是狼狈不堪的失落,特别是一次连日水泻、身体虚弱时仍被惯性推着做爱,而忘了连夜赶回,在翌日清晨才赶回剧团大院,他们在晨光里看到别人清洁和平的幸福后,内心一直以性为耻为罪的道德感忽然膨胀起来,头脑简单的她无法处理这样的局面,于是她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死亡。然而也正是因为她生性简单纯良,在她可能还不明白什么是“死”的时候,并不惧死,但生活中点点滴滴任何细微的事物也都很容易唤起她对生活的热爱,那么既然死亡无望,他们各自又该如何选择?
叔本华认为“女人本身像个小孩,既愚蠢又浅见”[5],即便这种极端的偏见存在,但女人较之于男人,身体中隐藏着更巨大的力量,头脑简单如她,面对虐恋的困境虽无法自主脱身,但“‘人体结构决定的命运’对于男女截然不同,”她体内的原始本能给了她自我救赎的力量。“女性通过做母亲来实现她的生理命运,是自然赋予她的‘使命’,她的全部生理机体都为物种延续做准备。”[6]195作为社会的第二性,女人只能用孩子证明了其自身存在的正当性,证明性爱存在的价值。波伏娃认为,女人作为第二性的社会地位是被文化、社会、历史和权力等构建起来的,所以母亲的身份也是一种话语虚构,而且她所描述的母亲形象区别于我国传统的慈母形象,在希腊神话里美狄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以报复背叛自己的丈夫,可见西方文化里从来不掩饰母性中残忍的一面,但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选择用母性来救赎沉沦在性欲中无法自拔的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相吻合的,这里将母性提纯,然后预设为天性。
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只知其母还不知其父,孩子在母亲的身体里长大,在未分娩之前他们是一体的,因此孩子和母亲具有天然的亲厚联系,在分娩之后男人才开始意识到父亲角色的真实性,而在此前女人已经做了九个月的母亲,但对他而言,“他尚需要间隔着肉体去探索,生命给予的教育便浅显了。”[3]191所以他无法感受到自己与这个小生命的紧密联系,也无法对他们产生爱与责任,反而害怕这个小东西占有着女人的身体,而使自己的性欲无处发泄,“作为内在的和外在的剥夺结果,指向客体的力比多的目标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偏转、限制或禁止。在大多数情况下,新的目标都是与性满足截然不同的,或者与它只有很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都是一种无性欲的或非性欲的目标。”[7]他将力比多转移到赌桌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沉沦,而她由于“性冲动和生育冲动由受虐的桥梁连接在一起。”[1]213力比多在她的身体里被转移到了成为母亲、孕育孩子的辛苦与喜乐中去了。在虐恋里他只需要享受性的快乐,她却要承受全部,包括性受虐和精神受虐的痛苦,在小说假设的背景时间里,未婚而孕的社会道德指责是不可避免的,但王安忆更为关注的是她内心的自我超脱,而非外在规则的宽恕,凭借着自然的力量,她以孕育新生命的方式超越了他,妊娠的折磨和分娩的剧痛净化着自己的灵魂,在母性的光辉里得到了内心的平静。
[1]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49.
[3]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4][美]伊文斯.语言虐待:如何认识、如何应对[M].宋云伟,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98.
[5]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生命哲学的启蒙者[M].陈晓南,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48.
[6][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195.
[7][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141-142.
编辑:鲁彦琪
Charming Pain:On the “TownofLove” Sadomasochistic Writing
WANG Xiao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In human complex mental picture of, as a special form of sexual sadomasochism strikingly, appeared in 1986, “Love in a Small Town” with its pure intense erotic depiction strong desire to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the original can not be suppressed. Although the novel living environment evacuated political component, but SM to madness attitude implies that special era for humanity imprisonment, visible and can not be said of subtle and cruel. Social attributes and natural attributes of the body of mutual strife, lust in the human race to survive a difficult field, sadomasochism as its harm than good choice, but the real salvation from birth impulsive, mysterious force in the face of nature she is destined to surpass him.
LoveinaSmallTown; sexuality; sadomasochistic; beyond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3.020
2016-08-30
王晓芳(1991-),女,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家及文学作品研究。
I106.4
A
1672-0539(2017)03-01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