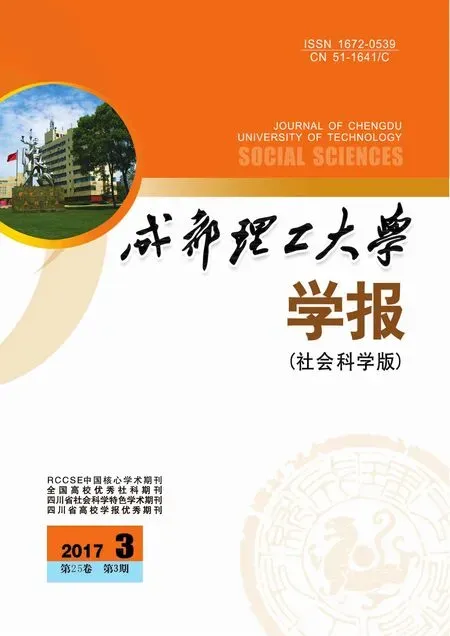《福》的互文性解读:现代性建构与后现代解构
孙雨竹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福》的互文性解读:现代性建构与后现代解构
孙雨竹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福》是对《鲁滨孙漂流记》的改写,因而两部小说也建立了历时性的联系。文章从复调和对话性两方面对文本进行内部研究,进而从广义的互文性角度进行宽泛的文化研究。四个不相融合的声音构成的复调性强调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复调基础上构成的对话以开放的自由言说创建着意义。两部小说都与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互文性,《鲁滨孙漂流记》的荒岛故事体现了现代性建构的因素,而《福》反映了资本主义后工业阶段对中心权威的解构。
《福》;《鲁滨孙漂流记》;互文性;现代性;解构
库切创作的《福》是对笛福《鲁滨孙漂流记》的改写,两部作品之间也产生历时性的联系。对于《福》这部小说,中外学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点:第一,从后殖民的话语权利、他者、身份和边缘化等角度对小说进行探究;第二,将小说置于南非的文化背景下,南非的殖民地、种族隔离历史在小说创作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第三,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鲁滨孙漂流记》中女性声音的缺失和《福》中苏珊·巴顿的叙述主体地位,批判父权话语体系中对女性的压迫;第四,研究小说中的叙事声音和叙事策略。然而,作为后现代时期对原著解构的小说,鲜有论文探究《福》中的复调和对话性,进而从互文性角度进行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
巴赫金首先提出复调理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1]4-5复调理论赋予了文本以生命,不相融合的声音使文本有更多的言说能力。以此为基础的对话理论进一步思考了不同声音之间的互动关系,即通过“他者”来实现自身价值,“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340克里斯特娃发展了对话理论:在文本即书面语中不可能有主体的在场,因此主体间的对话关系不可能是直接的,只可能表现为话语与话语之间的联系,她提出互文性来阐释文本间的客观联系。由此可以看出,互文性是对对话性的丰富和发展,从强调文本中各主体的声音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甚至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
一、《福》中的复调性
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以及由特定时空决定的不可重复不可取代的意识和话语。如果意识和话语失去其独立性,个人的主体性也被剥夺。在《福》中,文中并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叙述声音。虽然主人公苏珊·巴顿是事件的绝对叙述者,但读者在阅读中能够明显地感知不相融合的声音、意识所形成的多种频调。
文中的女性叙述者是绝对的叙述主体。她寻找女儿,与克鲁索和星期五在荒岛求生以及寻求反抗男性话语,福先生叙述她自己故事的经历都充满探险精神。苏珊·巴顿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不受他人干扰。因为自身的写作能力,她将自己的海岛故事口述给福并请求他真实地表达。但当她意识到福将她口述故事的重点改为她到荒岛以前及寻找女儿的经历以吸引读者的注意时,她拒绝福来写作,并尝试自己的女性书写。因此,她的女性书写就构成对传统男性话语和书写的挑战。
对比《鲁滨孙漂流记》,《福》中克鲁索的主体地位已经被剥夺,成为苏珊·巴顿口中颓废、安于现状、没有书写自己历史和控制他人欲望的“小岛主”,由此产生的强烈反差赋予了克鲁索丰富的言说空间。克鲁索不用强制的态度要求星期五学习西方的语言以期赋予他“文明人”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观念中,荒岛是他自给自足的天堂,外面所谓文明世界的巴西到处都是食人族。他也不愿意构建自己的历史,他相信“所有忘记的事情都是不值得被记忆的”[2]37。克鲁索对法律制度有自己的理解,认为法律是用来节制欲望,而没有欲望的小岛不需要法律,这些观点也体现了克鲁索对现代国家契约精神和国家暴力的解构。
表面上看,星期五像是被控制和言说的人物,但实际上他却用无声的方式抵抗着权威。他的言说是组成苏珊·巴顿故事真实性的重要部分。“星期五的舌头可以言说很多故事,但真实的故事却被埋藏在星期五中。我们将听不到真实的故事,直到我们发现一种艺术的方式赋予星期五言说的能力”。[2]118而且,为了抵抗苏珊·巴顿对他所谓的启蒙,星期五用沉默、肢体语言和吹奏长笛的方式进行言说。然而这种神秘、原始的表达方式与被资本主义启蒙观念赋予的文明相悖。
《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笛福从故事的权威叙述者变为故事的参与者。福先生不是荒岛故事的直接参与者,却因与星期五和苏珊·巴顿的二元对立中白人男性的身份而拥有叙述权利。事实上,库切似乎在暗示苏珊·巴顿的叙述与笛福的创作存在着强烈的互文性,笛福似乎从苏珊·巴顿的叙述中汲取材料完成了他称之为史实的小说,克鲁索是他笔下的鲁滨孙·克鲁索,而苏珊·巴顿则是他故事中的罗克珊娜。
相对于《鲁滨孙漂流记》中只有一个权威的声音控制着人物,上述四种不相融合的声音构成了《福》的复调性,每种声音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复调性是《福》的一个显著特征,构成进一步探讨对话性和互文性的基础。
二、《福》和《鲁滨孙漂流记》中的对话性
对话性发生在“地位平等、价值相当的不同意识之间,是它们互相作用的特殊形式。”[1]374《福》的复调性已经为对话性提供了多个不相融合的声音,构成对话的基础。在语义层面上,不同主体之间会产生对话,更进一步,巴赫金将对话理论渗透到句法层面,“对话语中任何一部分有意义的片段,甚至任何一个单词,都可以对之采取对话的态度,只要不把它当成是语言里没有主体的单词而是把它看成表现别人思想立场的符号,看成是代表别人话语的标志。”[1]243对话也不限于主体话语和他者话语之间,巴赫金指出主体话语内部的对话性。“我们同自己说出的话,不论是整篇话语还是它的某些部分,以至其中个别的词语,也都能够发生对话关系。”[1]244对于《福》的读者来说,鲁滨孙·克鲁索的故事已耳熟能详,这就形成了一种前语境。
不同主体的不同声音会产生对话。作为白人男性,克鲁索的存在与苏珊·巴顿代表的女性和星期五代表的黑人构成了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对话中,传统的鲁滨孙式的权威话语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几个相互交织的平等声音。《福》中的第二种对话出现在苏珊·巴顿和小说家福之间,并占据着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两人之间的对话实则是一场争夺写作话语权的斗争。正是因为对话中二者的矛盾与相互依赖,对话性为个体的言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如果将两部小说对同一人物的刻画看作内心两种矛盾想法的冲突,那么人物自身就形成一种主体话语内部的对话。最大的不同莫过于两个文本中对鲁滨孙的描述: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他具有资产阶级颂扬的品质:冒险精神、勤劳刻苦、野心十足、追求财富。而《福》中,他拒绝离开小岛,仅对小岛进行简单的改造,把荒岛当作自给自足的终身王国。第二处体现于星期五,在《鲁滨孙漂流记》中,他无意识地被殖民被驯化。而《福》中,他虽然被割去舌头失去话语权,但却用歌声、身体、笛声作抵抗,构成自我主体。对话性的文本并不追求终极的答案,在争论过程中,差异与复调早已形成了足够的理解、演绎空间。
话语的任何一部分都可能代表不同的思想、立场,个别的单词就可能反映对话关系。苏珊·巴顿不断地向星期五教授的词汇是主人(master),这一具有浓郁殖民色彩的词汇似乎象征着她对星期五主体身份的界定。克鲁索在与星期五的交流中并未出现有任何殖民色彩的话语,仅仅是简单的生活交流用语。这种句法层面的词语使用也构成了不同思想间的对话。
在巴赫金看来,所有的社会交往活动都是无限的、连续性的。在对话性中,不存在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因为话语向过去和未来延伸。“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涵义,但在对话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它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的面貌(在新语境中)获得重生。”[1]391苏珊·巴顿和福对于文本话语权的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所有的意义都被后来者再叙述。《福》中最后一章描述了一个神秘的我发现了苏珊·巴顿的尸体,而福和克鲁索可能也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的涵义,正如巴赫金所说任何意义都不会被时间冲走,它们只是在等待复活。
文本内部的对话性仅是狭义互文性的特征表现。作为后现代、后结构的标志术语,互文性“已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偏重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3]641因此,考虑小说创作的社会文化语境,更多文本将参与构建意义。
三、互文性:现代性建构与后现代解构
以互文性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一切都文本化了,任何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学、历史或神学文本都变成了互文本。由此,文本的研究从封闭的文学内部延伸向更为宽泛的文化研究层面。
《鲁滨孙漂流记》歌颂自由和启蒙,对理性的强调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形成强烈反差。鲁滨孙生活在笛福的年代,所以小说的背景与笛福生活的十七、十八世纪形成了互文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海外殖民的扩张和人文精神、清教主义的传播,鲁滨孙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积极地探索财富。鲁滨孙的故事虽然发生在荒岛,但小说却包含现代性裂变的因素。现代性主体意味着与中世纪的全面决裂,成为与传统社会隔离的孤独个体。鲁滨孙被搁置在与世隔绝的荒岛,这象征着个体在现代化过程中感受到的与传统的疏离和孤独感,海难的风暴也正是传统的力量,它将个体卷携,迫使他面临新的环境来重新构建自我。现代国家注重法制、秩序,鲁滨孙在荒岛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空间的定位和选择,划分出居住区、种植区、狩猎区和危险区域。空间规划和整合正是现代国家的标志性行为,通过规划赋予混乱以秩序。鲍曼指出:“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是由资源充裕的(即占有知识、技能和技术)主权和机构所监管,它便具有了现代性”。[4]12鲁滨孙从沉没的船只上取出的种子、火药、猎枪、简单的工具成为他建立、控制现代性机构的基础,他也成为海岛机构的主人和绝对权威。
同时,现代性的经济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市场。鲁滨孙的大种植园在巴西,发达的海上贸易使非洲和南美洲的商品出现在英国的商店,这打破封闭民族的闭关自守,使落后的东方从属于现代性的西方。理性和启蒙使现代人摆脱了自然和上帝的双重阴影,自然变成能为人的意志和能力改变的材料。鲁滨孙依靠自己的双手改造着自然:搭建住所,种植庄稼,制作面包和工具,打猎捕鱼,驯养动物。清教主义相信财富可以被合理的获取和积累。鲁滨孙勤恳地在巴西开拓种植园,在荒岛建造自己的王国,同时将钱寄回英国的委托人保管,这样走向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到了现代性的成熟阶段,它逐渐积累起来的形象就是疆域固定的民族国家、自由民主政制、机器化的工业主义、市场化的资本主义、主体—中心的理性哲学、权利和理性巧妙配置的社会组织,以及所有这些之间的功能关系,等等”[5]6。
然而,现代性的深层危机不断突显。“可在300年的扩张中,资本主义无时不在背离其许诺。与现代性的美好理想严重相悖,资本主义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铜臭和血腥。它张狂进取,索求无度,每到一处都带来旷世未有的冲击震撼,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污染、异化和沉沦”。[3]641库切站在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现代性。然而现代性中早已包含了后现代性因素,只是那些边缘的走向了中心,中心的走向了边缘。
《福》与库切所处的后工业时代构成了一种广义的互文。互文性作为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戏仿其他文本以达到颠覆、解构历史文本的目的。首先在于对笛福的解构,笛福本名就为福(Foe),为了使自己的姓氏更加贵族化加上De,而De同时也为解构的意思。笛福在自身创作中不断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而福先生对苏珊故事的随意篡改和拼贴暗示着小说的虚构性。这也体现了后现代作品对小说的真实观和历史观的颠覆。在后现代语境中,解构中心,关心边缘。克鲁索不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开拓者,而是消极、堕落的保守形象。相反,原本被现代性男权隐没的女性和被殖民者出现并参与叙事。创造意义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解构意义才是后现代艺术的重点。
走出了现代性中人定胜天的思想,从人对自然改造的理性到人与自然的互动。鲁滨孙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曾标志着人类面对自然的祛昧,然而自大和面对自然的强权却值得反思。被解构的克鲁索已不再是“造物主”,他的房屋在自然的基础上做简单的改造,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他不过多地开垦荒地,种植的作物只有苦莴苣,这种人与自然的健康互动也体现了后现代生态观。在现代性的构建中,男性被当作现代性的主体,而女性则被想象为未开化的自然。丽塔·菲尔斯基提出:“如果我们在考察现代性时, 不把男性体验作为范式,而是将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体验置于分析现代性的中心,那么现代性会呈现怎样的图景?”[6]10《福》中将苏珊·巴顿这一女性形象作为叙述者本身就解构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现代性。在大航海开启的时代,女性似乎还被拘束为家中的天使,甚少踏足公共空间,很难想象库切将苏珊塑造为跨洋远航的殖民者。库切这一将女性置于现代性中心的思考也体现对男权中心的现代性的解构。
四、结语
小说的叙说形式作为内容的一部分也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建构。《鲁滨孙漂流记》描写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中心权威的强调,所以全文由一个中心的叙述声音来统领。而《福》中的解构叙事给予每一个人物言说的权利,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后工业阶段解构中心权威的精神特质。
在《福》中,四个不相融合的声音构成的复调性,强调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在复调基础上构成的对话以开放的自由言说创建着意义。同时,在此基础上广义的互文将文本带出了封闭的文学内部研究,转向更为宽泛的跨文本文化研究。从现代性启蒙到后现代的解构,文本跨越了三百年,体现了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学、历史或神学文本的广义的互文性的思考。《鲁滨孙漂流记》留下的褶皱,等待《福》去填写,这种改写揭开了历史的褶皱。通过文本与时代的互文性,读者可以通过文本去触摸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不必再去追求故事的终极答案,书写与阐释才是文本生命的起源与延伸。
[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Coetzee, J.M. Foe[M]. New York: Viking Penguin.1987.
[3]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4]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M].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Felski, Rita. Gender of Modernity[M]. Massachu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笛福.鲁滨孙漂流记[M].郭建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编辑:鲁彦琪
Intertextuality Interpretation of Foe: Modernity Construction and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SUN Yuzh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Coetzee’s Foe is the rewriting of classic novel Robinson Crusoe,so the two novels are connected diachronically . This thesis makes research based on the text through polyphony and dialogicality, and further make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through broad sense intertextuality perspective. Polyphony consisted of four independent voices emphasizes each individual’s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dialogicality based on polyphony makes sense in open debate. Those two novels are intertextual with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respectively. Robinson Crusoe’s island story embodies the elements of modernity construction, while Foe reflects deconstruct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 age.
Foe; Robinson Crusoe; intertextuality; modernity; deconstruction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3.019
2016-06-30
孙雨竹(1992-),女,黑龙江绥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诗歌翻译。
I106.4
A
1672-0539(2017)03-0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