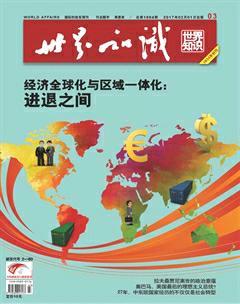在“特朗普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周鑫宇
在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到来,似乎使得世界充满了不确定的危机感。然而对于中国的公共外交来说,则迎来了同样不那么确定、一定程度上却很明显的新机遇。“特朗普时代”所代表的,是西方普遍进入一个不满意、不自信、不确定的政治躁动时期。在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出现了反精英、反建制和反全球化思潮,金融危机之后民众抗议此起彼伏,政治激化、社会撕裂,2016年西方世界“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
在政治躁动背后,是西方多年未见的精神危机。这首先表现在西方的制度自信快速下滑。新自由主义作为冷战后西方“胜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如今成为了西方民众批判和怀疑的对象。早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的时候,美国媒体的民调就显示,多数美国人把经济危机归因为体制。接近3/4的受访者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修补美国经济。接近80%的人对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不满,其中45%的人表示“极为不满”。这样的情绪到2016年美国选举的时候,演变为选民对体制的绝望。当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强大”宛如一只悲哀的号角在落日黄昏中吹响时,投票者中有一半把票投给特朗普是因为他誓言要“革旧世界的命”的。正如《明镜》周刊在题为《西方往事》的文章说,“西方”这个词曾经代表着民主的尊严,比专制和暴政国家更加正义。但现在,一切看上去成了“往事”,“西方”已经不复存在了。
制度自信的下滑,导致了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迷茫。“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信条在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光环的褪色,使得部分西方民众的价值认同开始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而这种利己和排外的思潮,在西方内部导致了更加尖锐的价值观撕裂。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意大利,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乡村和低教育阶层出现的逆反情绪痛心疾首,但对于底层暴露的问题却又束手无措。当美国大学教授在特朗普获选之后在课堂上留下泪水之时,内心深处恐怕不只是对政治选举失败的沮丧,而是面对年轻一代美国学生疑惑的眼神,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这样的西方,自然给中国外交的舆论环境带来新的变化。西方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压力出现明显的缓解。特朗普说到中国问题,谈的都是安全和利益,却很少提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所谓的“人权”等问题,这在之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中是非常罕见的。而英国在卡梅伦政府时期则明显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传统上和中国“只谈钱不谈感情”的政治正确性被超越,形成了中英关系所谓“黄金时代”。仅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中国和西方关系开始出现以前不具备的条件和基础。
对中国来说,在话语权问题上不但相对被动的局面得到了缓解,更迎来主动的机遇。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下,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关注不多,而今天,西方在自身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反思中,对于中国的模式和道路有了更开放的态度和兴趣,“中国故事”有了更多的听众。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反思浪潮,也伴随着对中国——这个现如今热情、昂扬、自信的东方大国的持续聚焦。在“特朗普、卡梅伦们”用不同的方式把“中国”挂在嘴边时,西方对中国的心态已经悄然变化。不管他们如何认识中国上升的力量,他们都更理性地面对中国的发展奇迹,想了解中国发展背后的原因。
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有强烈的偏见。在当前局面下,中国有机会更好地讲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全球充滿不确定的时代,显然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恶性对抗和社会撕裂,更能坚持做正确的事,在政策层面上也能够更好地协商、平衡和坚持。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共外交中,讲“优势”不是讲“优于”,不必搞比较、对抗,而应求补充、互鉴。要讲中国也在认识和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治理的先进经验,在加强民主监督、防止腐败、简政放权等方面,和西方互学互鉴。
中国还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习近平主席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展现了中国的领袖气质和担当精神,在不确定的时代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是非常好的公共外交。
当前,对于困扰西方的“文明冲突”,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融合史可资借鉴。跟欧洲不一样,中国在政治上从来是崇尚“合”而不是“分”,民族和宗教是文化层面的因素,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因素。在西方社会撕裂的剧痛中,一贯被西方视为天经地义的“民族国家”观念,可以从中国的政治哲学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