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之重,沉著痛快
廖伟棠
成为中年是不幸的,你要承担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都是如此庞大,稍一不慎就沉下去了,谈何沉著痛快?稍一不慎又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而被万千链条困顿,又谈何优游不迫?我们唯一的机遇,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赋予的,一种反思的可能,一种从自己身上革“中年”的命的可能。
“在人生的中途,我在一座幽暗的森林里迷了路。”但丁写下《神曲》这著名的开头时,他才35岁,看来,依他那个世纪人的定义,35岁就可称中年了。
我早闻此道,却心有不甘,当我30岁的时候,我从一本《香港后青年散文选》学到“后青年”一词以自喻,又自创“前中年”一词自嘲,近年又在友人脸书偷得“微中年”一词,聊以自慰——其实,就是不肯承认中年二字。
是啊,在我年少轻狂的年纪,“中年”二字就等于陈腐、保守、迟钝,就像Bob Dylan《瘦子歌谣》中讽刺的那位琼斯先生:“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你对此一无所知/是不是,琼斯先生?”这迟钝于时代之烈风的颟顸先生,和敝国之中年唯一的不同是在于他是瘦子。那时我们还信奉一句话:“永远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但是,我们很快自己就三十岁了,从此活在矛盾中。
第一次意识到这矛盾,是前几年在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演出台下,环顾左右,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是年纪最大的叔叔。慨然又慨然,我当时许下豪言:“我未来将成为万能中年。”实际上万能青年旅店的成员和我年纪差不了多少,同为七零后八零后,书写的都是一个时代走向尾声的苍莽心象。这样一个时代成就的中年,理应饱含青年之锐气和老年之睿智。
可惜,中国诗人多在中年折戟,要么提前进入中年。新时期花样百出的诗歌写作中有所谓“中年写作”一说,是一群在1990年代只有三十多岁的老气横秋的诗人提出的,虽然与年纪不符,却很有他们的意义——他们针对的是中国新诗一直以来的青春期荷尔蒙式写作,尤其是朦胧诗与海子的诗,中国新诗的确需要更成熟更胸有成竹。
但诗歌中的中年写作不是音乐里的“晚期风格”,就像那些青春期写作中也缺乏真正青春的自由,徒有热血与孤绝。大多数的中年写作是对热血、孤绝和自由的抹杀,以求建立一个想象中风雨不动的集大成者,以便指点江山时百毒不侵,只有少数人依靠自身的才情颖异而例外。我寫诗二十多年,几乎就是伴随着对这些师长的景仰、学习与洞察而成长,佩服他们中流砥柱的野心,但觉得这并非我所意愿的中年。
今年我41岁,无论怎么说,也算是站在中年的入口处了。简单说来,我对“中年风格”的期许是四个字:沉著痛快。沉著痛快者,据《法书要录》引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是一种书法的境界;而据严羽《沧浪诗话·诗辩》:“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著痛快。”是一种诗的境界,陶明濬《诗说杂记》演义为:“至于沉著痛快,则倾囷倒廪,脱口而出,……为此体也,要使驱驾气势……必使读吾诗者心为之所感,情为之所动,击节高歌,不能自已。杜少陵之诗,沉郁顿挫,极千古未有之奇,问其何以能此,不外沉著痛快四字而已。”
沉著源自对自身才能的自信,也因为对自身局限的全面了解,故能按兵不动,亦能大开大阖;痛快源自对自身初心未改的确信,故无顾虑、无拖累,畅言其志,不躲躲闪闪、畏畏缩缩。能做到这两点,中年无论写作不写作,都是敞亮无邪的。

沉著相对的是轻浮,少年轻狂可以,中年轻浮则恶心。写作需情恳意切,为人亦如是,詹幼馨先生析司空图诗品之“沉著”一分为二:“要沉于思,着于情;沉于辞,着于意。一句话:要深沉而有着落。”深得我心,我41岁生日前写《生日诗》明志,中间有一句:
“十岁以后我常剖腹与冬雨,三十年来将心比心
而不顾身在江上海上还是高原之巅,一样风干。”
也是这个意思,司空图说:“所思不远,若为平生。”三十年来一路踌躇眺望,要在世上寻一个着落处,以安身立命。身与命安立之处,就是“诗言志”那个志之所存。四十不惑,于我,也就是明白了“志”,在这个坐标系前面,许多世俗羁绊都可以迎刃而解。
事实上,在世俗意义里做好一个中年是如此困难,甚于文学中的纸上谈兵。最近几年,中年二字意味着在所有的媒体时评都可以嘲笑的大叔,在输入法里输入“猥琐”就能联想组词的“大叔”,再高端状态,也不过是《洛丽塔》里的亨伯特·亨伯特。这种状态,一个不惑之人可以避免,而“不惑”与“无欲”密切相关,无欲则刚,我们都挂在口边,但是四十岁仍是壮年,纵可把食色之欲等闲视之,却难以破除“成功”之欲,那样仍然不能不惑。
于是我们在中国各个领域都看到中年人的国师情结,国师者,欲为祭酒至尊也,欲被人称为“牛逼”也。不是只有张艺谋这个级别才可以问鼎,多少以孤独英雄自况的人也逃不过这种幻象。比如说姜文,从《让子弹飞》到《一步之遥》,他的孤傲明显是中年成功的亢奋所致,而不是少年气血。要面子讲派头,是中年膨胀的结果,与少年的耿介刚烈并非一回事,中国许多在中年陷入固步自封的艺术家,都自以为遭到世人误会而更骄横,在电影界、摇滚界、思想界比比皆是,这样的国师范儿中年比世俗处处的猥琐大叔更显得可怕。
如何面对自己的成就与短板,面对前行者的不可逾越与年轻人咄咄逼人的挑战,在中国,如果不寻找宗教支持,如何不陷入逍遥逃逸或者是进入狂暴出击模式?这两分法之间,很难奢谈清醒的第三条道路,除非真能跳出举国的名利交织之网,秉持古人所谓士的坦荡从容,才能做到前述沉著痛快的同义:优游不迫。
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成为中年是不幸的,你要承担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都是如此庞大,稍一不慎就沉下去了,谈何沉著痛快?稍一不慎又成为了既得利益者而被万千链条困顿,又谈何优游不迫?我们唯一的机遇,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赋予的,一种反思的可能,一种从自己身上革“中年”的命的可能。
“访旧半为鬼”,成为中年,意味着无论在我们的前辈中还是当年的同行者中,都已经渐渐越来越多逝者。如此,他们将不再成为我们的扶持、我们的慰安,中年意味着和逝者告别,真正直面生之难——我们必须告别的还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里尔克所谓“何有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常常被我国的文青滥用,也被不少文学中年用来自我感动一番。这句诗出自里尔克33岁所写《为沃尔夫伯爵冯·卡尔克罗伊而作》,按德语应该译作“有谁在谈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绿原译本)或者“谁还会说起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陈宁译本)——冯·卡尔克罗伊是里尔克素未谋面的一位早夭的青年诗人,里尔克在33岁、中年的门槛之前写这首挽歌给他,包含着对另一个自己:天才青年诗人里尔克的告别,以及对未来那个中年里尔克的期许。
真正熟习中年写作的英语大诗人奥登,用自己的方式解读了里尔克这句话以及里尔克本人。奥登在其著名的《战时十四行诗》中写到里尔克:
“……当我们悔不该生于此世的时分:
且记起一切似已被遗弃的孤灵。
今夜在中国,让我来追念一个人,
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谬佐显出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堡,像一个庞然大物。”(卞之琳译)
何谓“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里尔克从1912年到1922年,陷入一个表面沉寂的状态,从杜伊诺古堡到谬佐古堡的长期隐居,最后写成他的巅峰之作《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浦斯的十四行诗》两部。37岁到47岁,他也是这样真正进入了自己的中年,“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个交代”。四年后,1926年12月29日因白血病去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诗是:“来吧你,你最后一个,我所认识的,肉体的无药可救的痛楚。”他不但直面了中年向老年的步伐,也直面了加繆所说的必须清醒进入的死亡。
“忍耐意味着一切”,德语原文为“Wer spricht von Siegen? überstehn ist alles”,据译者陈宁在豆瓣的一篇小文所辨,关键字überstehn 有“忍耐、隐忍”。译作“忍耐”之意固然比“挺住”更中正,免除了后者想象被打压而反抗的自我感动和自我打气之滥调。但窃以为如果译作“沉著”又何如?这样更为矫健,预知了十年之后中年里尔克在谬佐古堡的魄力所来源的积累。
像里尔克51岁逝世,却仍保有少年般宝贵的气魄的中年诗人,在当代中国很难寻到。除了游离于诗坛外的木心,假如顾城不死,也许近焉,假如穆旦1953年不回国,亦能存也。少年洁净是理直气壮的,中年能洁净则几乎是神话,即便能洁净于声色利欲,儒家阴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不能免于权力的诱惑、“匡国”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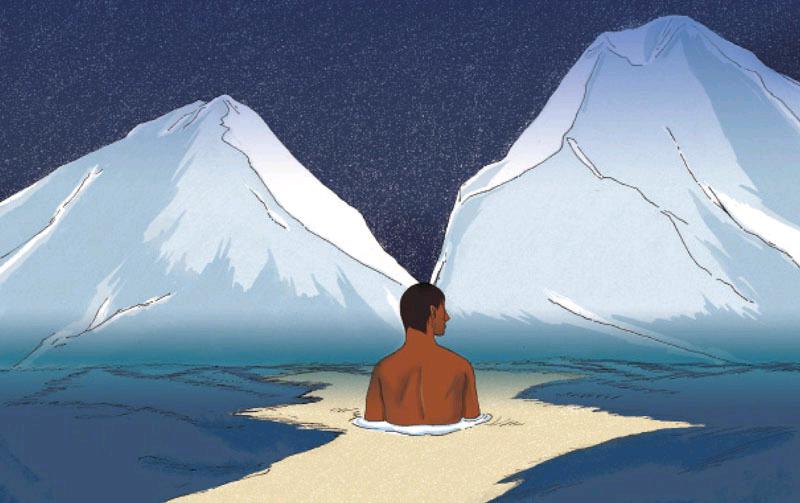
能做到“终身不仕”的诗人,我所热爱的有现代的废名、古代的姜夔。废名有孤介不遇的因素,姜夔在较开明的南宋而不出仕,乃是一种自觉。年轻时我耽读姜夔白石词,深被其绵延二十余年的合肥情事感动,后来更钦佩他40岁之后的豁达、豁达又始终情深不悔,中年而赤子,宋以后罕见如此了。
“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姜夔的《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一读一断肠,所谓幽恨难语,所谓寂寞流年,中年滋味。其时姜夔42岁,距永别其合肥情人已五年,之后一年的元夕,他更连作五首怀人词,几成绝唱。
如果终于此,姜夔只是一个优秀的情诗人,但一个朋友的到来使他的境界再次提升。那是南宋与他齐名的辛弃疾,姜夔49岁后写有多首词作唱和辛弃疾,既是惺惺相惜,也是在相同精神高度上难得知音的和鸣,竟融入了辛弃疾的遒劲豪放。《汉宫春·一顾倾吴》把对世事的感叹扩展到一个高广的角度:“大夫仙去,笑人间千古须臾”,又从这俯瞰中落至一个人身上:“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而这个人明显就是诗人自己,他不仅从世事抽脱,还从自身也抽脱了出来,但他又没有就此转身逍遥离去,而是返观之,珍重之。
对于姜夔这样一个深诣中年情怀的诗人来说,人生并无逍遥可言,拯救与逍遥实则一体,都是对由人生之不完全所致的痛苦的较量──在这紧密相拥又猛烈抛掷的较量中,诗人得以深味痛苦。如果说面对的中年之重、中年之难将能带来什么收获给我们,这种经验才是我们需要珍重的。
归根到底,中年是为了进入老年的准备,为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就先得不惑、知天命和耳顺,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我想起青年时代很喜欢叶芝这首《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翻译:沈睿)
希望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发觉中年之重本身,既是承担起负重的过程,也是抖掉心中挂累的过程,将如此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