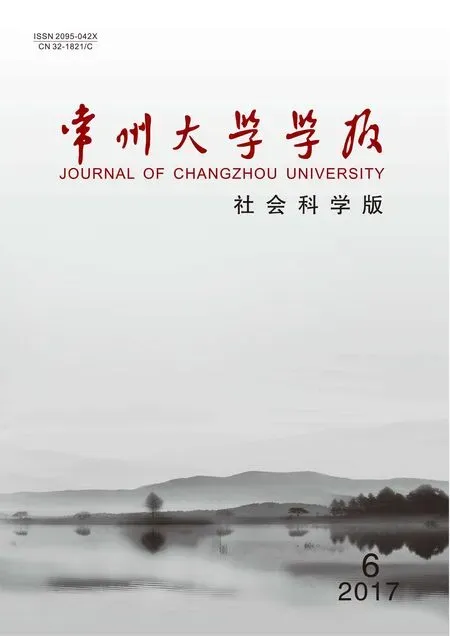商标混淆可能性标准的客观化路径及其反思
宋 颂
商标混淆可能性标准的客观化路径及其反思
宋 颂
混淆可能性标准具有主观性,需要通过客观化路径实现具体解释适用。但现有路径在商标权人话语体系下不能真实反映消费者实际消费情形,异化了商标功能、夸大了知名度的影响,简化混淆认定的过程,司法机关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也难以真正实现角色转换。因此,司法机关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在认定商标混淆时应当更加注重客观因素考量,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势提升认定准确性。
混淆可能性标准;商标话语;司法及行政修辞;混淆可能性标准客观化;大数据分析
混淆可能性标准*混淆标准实际就是混淆可能性标准,二者在本文中同义。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不同,参见张体锐:《商标法商混淆可能性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版。在商标侵权认定中处于基准地位*李雨峰教授提出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应当以商标权作为考虑的基点,“商标显著性受到损害之虞”可以统合商标法上既有的“混淆可能性标准”与“淡化标准”,矫正了既有商标权认定标准的不足,有其自身的优势。但该标准仍需要配套制度措施来实现具体司法适用。参见李雨峰:《重塑侵害商标权的认定标准》,《现代法学》2010年第6期。,混淆认定中需要结合多种因素进行个案考量。我国法律法规对如何认定混淆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似乎理顺了商标混淆认定要件间的逻辑关系,为混淆认定制定了明确的标准。但在司法及商标行政管理实践中仍经常出现对于同一案件混淆与否的不同认定以及认定结果与公众认知偏离的情况,这就需要对混淆可能性标准进行反思。
一、混淆可能性标准及其现有客观化路径
(一)混淆概念
商标的基本功能是识别来源,其彰显了特定商标与特定商品之间的特定的联系。无论是注册商标还是未注册商标,其受法律保护的基础最终都体现在其所具有的识别性上[1]。混淆是一种认知状态,商标法上的混淆可以分为直接混淆和间接混淆。直接混淆是指相关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来源发生了混淆。间接混淆是指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不存在混淆,只是认为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如赞助、合伙、许可使用等[2]。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不同生产者有着明确的认识,只是因为误认为两个生产者存在特殊关系进而认为该种产品与商标产品在品质上一致因而购买。
(二)混淆可能性标准的现有客观化路径
法律术语的一致性使得裁判标准能够适用于大量形同或者极为相似的情形,这样就可以保持制度及结果的一致性、连贯性[3]。但社会生活样态丰富,具体到特定案例情形时,需要通过对抽象性、普遍性法律的客观化、特定化阐述、解释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商标混淆认定的法律表达具有抽象性,商业活动中可能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情形具有多样性。商标侵权认定遵循“使用行为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商标商品近似及其他因素”—“相关公众混淆可能性”—“商标侵权”的逻辑路径。其中,在混淆可能性的判定环节中,认定混淆的主体是相关公众*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相关解释》第8条的规定。,包括对商标和产品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对商品来源作出基本的判断的消费者、经营者。所谓一般注意力是指相关公众在选择商品或服务时所施加的普通注意力而非高度的特别的注意力[4]。司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需要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身临其境地自觉站在相关公众立场上,模拟相关公众的一般认知水平来进行商标混淆的认定。
认定的客体主要是商品和商标。商品和商标的近似性强弱是混淆认定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着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商标混淆与否认定。对于商品近似而言,多采用“关联性”标准*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定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1条。,也即从产品的生产流通、主要消费者群体、提供服务和商品内容等因素是否存在特定关联来认定商品近似。对于商标近似的认定采用整体对比、主要部分对比相结合,隔离审查的方式,并充分考虑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此外还需要参考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商标实际使用情况以及实际混淆等其他因素。
(三)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
现代科学试图打破我们根据自身感觉所呈现的事物,通过不断细化分析,试图呈现对于事物的完整描述,进而实现对唯一“客观事实”的准确认知[5]。唯一客观事实的深入影响也体现在司法裁判领域。我们已经习惯于每一个案件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到[6]。但社会生活是丰富的,司法成本以及行政管理成本是高昂的,法律不可能事事都回归于社会现实的调查、追溯中去。除此之外,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其难以从事实认定行为中获得足够激励;对于行政管理及执法机关而言,虽可以从行政执法行为中获得激励,但对于具体事实的认定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因此需要一种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标准来协助司法机关以及行政管理机关完成对于客观事实的认定。混淆可能性标准恰恰充当了高效的认定工具,它预设了相关公众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制度设计在精确性和成本之间的兼顾[7],彰显了法定标准下侵权认定的科学性、公正性。
任何混淆认定都是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基于双方证据所作出的盖然性的自由心证,混淆可能性标准最终由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解释适用。但混淆可能性标准的现有客观化路径并不能帮助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准确把握公众认知,做出与客观事实、消费者认知一致的认定。
二、商标混淆客观化路径的反思
按照已有混淆认定路径,我们似乎可以明确得出混淆与否的确定结果,但此种制度设计并不能避免在司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常见的“近似”“混淆”循环论证现象,也不能解决“混淆可能性标准”简单化适用的问题。
(一)混淆可能性标准的话语与现实
1.“相关公众”的面纱
商人将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被描述或者假想成为仅凭商标即做取舍的头脑简单之人,他们在购物时常常粗心大意或不作分析[8]。一是混淆可能性标准通过“相关公众”的假设,认为消费者出现的混淆给其带来损失[9]。这一表达将保护商标权人利益与保护消费者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为商人进行整个商标权利话语的构建奠定公众接受的道德基础。二是将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和相关公众作为完全可对等互换的主体,表明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的认定就是相关公众的认定。这提升了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认定的科学性、公信力,削减了社会公众对于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代替自己所作认定客观性、准确性的质疑。实践中,普通商品的相关公众范围极广,而特定的技术领域或者特定品牌的相关公众则数量相对较少且地域分散,相关公众的范围难以确定。我国也并未引入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度来减少因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原因产生的失误,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不可能到每一件商标侵权案件中去寻找一定数量的不特定相关公众来协助其认定混淆。此外相关公众群体本身存在年龄、文化差异,特定地区的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难以捕捉把握这部分相关公众的认知特征。最终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仅能凭借自身的生活经验、双方证据、对法律法规的理解来进行自由心证。以“相关公众”作为认定主体的混淆理论出现了话语与现实的分离。
相关公众的话语表达无法遮盖司法及商标行政管理人员才是混淆认定主体的实际,实践中“相关公众”的范围难以确定,“相关公众”的特征也难以准确把握。
2.“一般注意力”的游离
社会科学中,用“概念”(或理论)代替“事实”的危险并不是不存在的[6]34,“准确”的概念、严谨的逻辑看似可以解释概念间的内在联系但不一定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一般注意力水平”的概念看似科学、客观,但其拉平了个体间的差异、忽略了特定的消费背景,难以准确地反映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不同的购物消费环境下进行商标商品选择的注意力水平,也就难以通过该注意力去认定消费者是否会产生混淆。
传统环境下个体性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有限,消费者的注意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选择的准确与否。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单个的消费者已经逐渐置身于消费者群体中,许多人在共享经济中与他人分享已经购买的商品,接受在线社交媒体网站“朋友圈”中交流的建议、评论、口碑、个人喜好等的影响。总体上消费者对于商标、商品的信息搜集能力,商品识别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社会环境的变化给消费者“一般注意力”水平带来了影响,一般注意力却难以及时反映这种变化。此外,消费者通过重复消费等对商标商品进行渐进的反复的认知,但“一般注意力”预设的适用情形多是一次性购物或者初次购物情形,这忽视了商标认知的过程性和丰富性。
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标准虽然有较强的话语说服力但实际操作困难极大。甚至有的法院或者商标行政执法机关在商标侵权认定中,会先判断消费者混淆存在与否,再确定消费者的注意程度以自圆其说[10],在混淆可能性的认定逻辑上已经陷入了循环。
(二)商标功能的异化
1.商标作用被夸大
商标诱使权利人通过广告宣传,花钱来创造一个疑似高品质的形象,使消费者从相同品质或者更高品质但价格较低的替代品上转向,从而获得垄断租[11]。商标已演化为捕捉、黏合、固化消费者注意力的工具。我们也已习惯商人们所构建的商标话语,认为商标可以减少搜索成本、获得质量保证、彰显身份地位,过于强调商标在消费者整个购买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从传播媒介来看,商标是一种由简单色彩、文字、图形构成的符号,本身属于一种冷媒介*冷媒介是低清晰度媒介,本身并不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要求公众高度参与、自觉地补充缺失信息,完成认知。热媒介则与之相反,本身含有充分信息,不需要公众再自行补充。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本身所含的信息极少,消费者并不能够单纯的从商标本身解读出有关商品质量、产品生产者的信息。作为一个外部刺激,商标刺激消费者充分调用经验中形成的有关该商品、该商标的认知,决定是否选择该商品。需要注意的是同为商誉载体的商品广告、包装装潢能够传递给消费者更多的产品信息,塑造商品商标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对于消费者的购物决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品广告、商品包装装潢的近似也成为引发消费者混淆的重要原因*加多宝与王老吉红罐包装装潢之争即体现了包装装潢在商品营销中的重要作用,相同或近似的包装装潢也容易引起消费者的混淆。。但在混淆认定的司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却对之参考甚少。
此外,商标、商品品质间关系也出现了错位。商标的作用在于彰显产品或服务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并借此捕捉、黏合市场中的消费者。商标要让消费者产生信赖,消费者凭此信赖决定是否购买特定产品[12]。商标对于消费者的捕捉、黏合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商标所代表的产品或服务的品质的高低。知名商标象征着持续、稳定的品质,消费者对于商标的认可实际上是消费者对于商品品质的认可。当一个品牌的品质并非持续稳定时,消费者就知道该商标并不能使他们将其过去和将来的消费经验联结起来,他们也就不愿意付出更多的钱去购买该品牌商品[11]217。特定商标市场份额的减少,消费者对于某一品牌的逐渐冷淡抛弃,根本原因仍在于商品品质的式微。
消费者对于商标的理解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商标决定论。对于商标商品具体细节要素近似结论,并不代表这相关消费者就会产生混淆。
2.商品知名度影响混淆认定
商标财产权化业已成为现实趋势,商标持有人主张要像保护私有财产权一样保护自己的商标。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对于知名度高的引证商标更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两个商品之间有关联,因而其排斥的商品范围也越大[13]。从内心情感、道德倾向上也就越容易认定被控侵权人有搭便车的主观恶意。
商品的知名度本质是消费者内心的认可度,这种认可度有其生命周期,知名度与消费者混淆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商标商品的知名度越高,恰恰表明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了充分的商标商品信息,消费者对于该商品的质量、包装、商标、生产商有着较高的认知度,能够在消费者内心形成明显的商标确认。即使由于消费者因为混淆购买了其他品牌的近似商品,对模仿品牌的消极体验实际上可以增强消费者对于被模仿品牌的正面评价[14],形成更为明确的品牌印象也就更难以造成混淆。
商标财产权的观点已经深刻地影响我们对于商标商品判断思维,商标的知名度业已成为消费者混淆认定的重要考量因素。这直接导致我们对于商标商品近似、消费者混淆认定的主观化。
3.忽视商标持有人自身的不当使用
科学的商标运营可以保持商标的显著性,实现商誉的持久性累积。但商标显著性也会因商标持有人自身的不当使用而产生异化,直接促成消费者的混淆。在注册过程中,企业往往注册大量的防御商标和联合商标,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注册在不存在联系的商品上。在实际使用中,企业又会将原来自身拥有的较为知名的商标用在多类别的商品上,让自己不知名的其他商品搭自主拥有的知名商品的便车,借以降低开拓市场的成本。但这种行为会降低特定商标与特定商品的联系,同时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假象,该商标持有人在进行多种类别不相关产品的生产,再次面对贴有该商标的他人生产的其他种类的商品时就会减少质疑,理所当然认为这也是该商标持有人生产的产品*例如,我们所熟知的百事集团(PEPSI)不仅生产饮料也生产百事牌内衣,这给初次消费者认知造成冲击,消费者内心认知会进行相应的修正。当消费者再度看到百事公司并不授权生产的“百事牌PEPSI”或类似商标的床上用品时,便会较为容易地认为这也是百事公司的产品。消费者的此种混淆客观上还是由于商标权人不当使用所造成的。。消费者由此产生的混淆更应归因于商标持有人的对于商标的不当使用而不是他人的模仿。
(三)司法及行政管理过程的修辞
1.先验因素的影响
理想状态下我们对于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的印象是丝毫不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完全独立客观地适用法律认定案件事实。但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也是社会中的人,生活在社会关系编织的网中,而不是超然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居中认定者。先验因素无所不在且无法排除,在作出决定之际,没有谁可以忽略自己的一切先验因素[15]。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在整个的认定中会无意识地加入自己生活经验、主观态度、爱好习惯,对于特定物品的偏好等诸多因素,这也才真正符合我们的司法实际、生活实际。自觉身份互换,置身相关公众位置以一般注意力来进行认定,已经明确表明允许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依赖自身在生活中的经验来进行认定,这已经使得相关公众混淆的第三方混淆流于形式,成为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主观化现象。
2.难以实现的身份互换
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促使商标认定业务的专业化,工商联动、信息共享提升了商标行政管理机关的认定能力和执法水平,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本身在专业化的过程中更加倾向于成为一名理论与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的认定并不是一个被动认定而是分析运用各种因素积极构建新认知的过程。以往案件认定所积累摸索出的或明或隐的认定规则也无时无刻不充当着认定的规则。同时特定地域和生活环境下的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其对于商标商品的认知也受制于特定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能够互换的也只是与自身存在一定共同点或者近似生活经验的公众。对于与自身消费水平、生活环境经验、教育背景、年龄差距较大的公众,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是难以仅仅通过修正、调整自身主观认知来模拟其他主体实现身份互换。消费者有时并没有对商品发生混淆,但法院认定产生了混淆[16]。
由此可见,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与相关公众并不同质 ,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替代相关公众进行混淆性近似的判断是不合理的,其忽视了公众在商标识别功能的塑造,剥夺了公众在混淆认定中的“话语权”。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自觉将自己置换成相关公众从一般消费者角度进行判断仅仅是一种修辞。
3.诉讼包装
认定所依赖的“事实”并非本体论上的客观事实,而是带有主体主观烙印的认识论意义上事实[17]。由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认定的案件通常经过修辞装饰,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商标情况的认知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对于各自所谓事实的描述上。利益总是与话语紧密相伴,各方基于各自的利益对于事实进行了相应的取舍、加工甚至夸大,形成足以代表自身立场的话语,以影响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的自由心证,获得有利的认定。基于双方利益诉求进行取舍后的话语已经与相应的事实发生了较大分离。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原告往往对于某一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产品间的质量差异、可能对消费者造成欺诈、被告的主观恶意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进行夸大性描述,塑造自己在诉讼中的道德优势,进而获得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对于自身权利的内心认可。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虽然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举证对于相应的诉求进行甄别,但是在法庭认定过程中,总会受到双方当事话语的影响而不能彻底地置身事外。
4.混淆认定标准的简单化适用倾向
美国和我国均明确规定了在混淆认定中要进行多因素的综合考量,但就条文内容而言,我国对如何认定商标、商品近似制定了详细说明,对于其他考量因素如商标实际使用情况、市场格局等因素的内容及其具体解释适用则阐述较少。司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也都没有严格贯彻多种因素原则,而是逐渐地将商标商品近似成为认定混淆的决定性因素,只要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商标商品近似形成了内心确认,就会不断地从原被告的话语表述、证据中寻找验证。其他较为客观的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消费者的明确区分和已经形成的市场格局等因素,由于被认为取证难、证明力低,始终未能纳入到混淆认定参考体系的核心部分,沦为混淆认定中不起眼的点缀。
三、混淆可能性标准客观化路径的完善
正如前文所言,现有的客观化路径存在部分瑕疵,司法机关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过多地受到商标权人商标话语的影响,错置了商标定位,高估了商标功能,夸大了商标知名度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客观化路径的完善来弱化商标话语体系的裹胁,通过更为丰富的客观化路径体系帮助司法机关及行政管理机关更好地认知市场中的相关公众是否因为行为人的搭便车行为产生了混淆。总体而言,对于现有路径的完善应当以更为准确的认知相关公众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为目标,以理性看待商标定位及其知名度为前提,将商标、商品以及市场客观因素的考量作为路径完善的重要方式,将市场作为混淆可能性认定证据的主要来源。强化当事人对于混淆可能性的证明责任,从而为司法机关既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混淆可能性的认定提供更为充足的证据。
(一)理性看待商标知名度
理性看待商标知名度是合理准确认定相关公众混淆可能性的前提。虽然显著性越强的商标,市场中竞争者搭便车的可能性更大,但这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更加侧重考量的因素,与相关公众是否产生混淆是两码事。相反知名度越高的商标越高的商标相关公众赋予的注意力越高,产生混淆的可能性可能越低。对于知名商标的强保护更多应当在商标注册、打击侵权行为和赔偿商标持有人损失的环节,不应当错位地放置于相关公众混淆可能性认定的过程中。只有如此,司法机关以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更为理性地审视商标商品的相似度、主张相关公众产生混淆的各类证据,进而更为客观地认定是否确是行为人的假冒或仿冒行为造成了相关公众的混淆。
(二)注重客观因素*有学者提出客观因素主要是指商标的音形意,商品的性质、功能。参见刘庆辉:《我国商标近似、商品类似的认定:标准、问题及出路》,《知识产权》2013年第4期。笔者对此并不赞同,这其实与传统路径无异。的考量
认定法律事实的制度设计必须以能够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实现客观真实为目标,衡量认定法律事实的制度设计是否完善也以其是否能够最佳地发现客观真实为标杆[18]。在适用商标侵权认定的混淆性近似标准时,认定市场混淆采取足以产生混淆的主观判断标准,但有客观因素支撑主观判断时,通常应当更加重视客观因素[1]119。这些客观因素主要有商标的使用情况,商品的实际覆盖地域,已经形成的较为明确的市场格局区分等。商标使用是商标混淆认定的前提,如果被控侵权人的行为不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就根本与混淆侵权无关。在构成商标使用的前提下,再对其它客观因素进行考量。对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商品、服务而言,实际使用地域、商品服务同一市场竞争的可能性等客观情况是认定混淆的关键。此时,虽然商标、商品较为近似,在初始阶段消费者可能会产生混淆,但结合双方实际使用情况、经营地域、已经形成的明确市场区分,则应当尊重事实认定相关公众未产生混淆。侧重对于客观因素的考量能够较为有效地弱化商标知名度以及商标权人话语体系、诉讼包装的影响,使得司法机关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更多地从市场现实考量相关公众产生混淆的可能性。在我国的司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产生了系列侧重强调客观因素的案件*参见:“诸葛亮”酒诉“诸葛酿”酒案,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监字第37-1号民事裁定书;“红河红”案,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提字第52号民事认定书;“鳄鱼案”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认定书;武汉“湘巴佬”诉深圳“湘巴佬”案,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9)深福法知产初字第113号民事认定书等。。
(三)市场调查
商标的印象和好感价值,是一个集合性概念,体现了相关公众的群体意识和共同价值,司法认定中法律尺度的把握,在很大意义上是在寻求一种民意测试和公共论证[19]。调查实验旨在将分散的消费者不确定的心理状态转化成一种可计算的形式进行科学界定,真实地对消费者主观认知进行模拟,为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判案提供必要的依据[20]。市场调查可以直接从市场中获得有关消费者消费以及是否产生混淆的第一手资料,针对性强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对于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能够直观地展现被调查者产生混淆的比例,为司法机关及行政管理机关的推断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以美国为例,其法院乐于依靠调查证据并视之为“科学”证据,来修正在认定混淆可能性问题上的主观倾向[21]。例如,在商标侵权案件中,针对消费者混淆问题的社会调查而言,一方当事人如果没有进行社会调查,法院往往会认定其败诉。尤其当未能进行社会调查的一方是一家大公司时,法院会声明:“你说消费者会产生混淆,但你竟然没有做测试?你肯定是做了测试,而你只是不想告诉法院结果而已。”[22]但在实际操作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司法及行政管理实践中也并未广泛采用。就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想化的方法无法形成专门的技术或者无法在技术上得到保证[23],调查结果难以成为法院认可的强有力证据。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完善社会调查的深度广度,建立正规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培育社会参与社会公众客观参与调查的热情。
(四)司法鉴定
商标混淆认定究竟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目前仍有争议*具体论述参见彭学龙:《论“混淆可能性”——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改草稿》(征求意见稿)》,《法律科学》2008年第1期。。有学者认为商标混淆认定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商标混淆案件中之所以出现商标商品相同或近似、以及是否混淆有不一致的结论,是因为未对此进行区分。对于案情简单的案件,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对较为复杂的商标混淆案件应当将是否相同或近似导致混淆的事实认定与是否构成侵权的法律适用分离开来。将对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导致混淆的事实的认定,提交司法鉴定,将会有助于法院对案件的公正认定[24]。
商标从符号学意义而言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志图案,加之详细地对比指导,对于商标近似的认定一般相对一致。商品近似认定则存在一定困难,对于与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生活、认定相隔较远的特定科学技术如化学、电学领域的商品而言,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单纯凭借商品名称、说明介绍难以准确认定商品近似。这就需要借助包括专家意见在内的司法鉴定来进行判断。商品近似的司法鉴定可以从商品本身、生产生活实践出发,借助特定技术领域专业知识,对商品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进而对商品近似与否提供鉴定意见。商品的司法鉴定弥补了法官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认知上的缺陷,全面对比了商品间的异同,所提出的鉴定意见也更具技术性、专业性和说服力。
(五)注重广告、包装装潢的相似度
广告与商品的包装装潢同商标一样也是商誉的重要载体。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不仅仅依靠商标也凭借广告和商品的包装装潢。商品包装装潢的近似也成为可能产生混淆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对于商品包装装潢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野下,混淆可能性标准本身并未对商品广告、商品包装装潢在混淆认定中的应用进行相应的规定和阐述。在关注消费者是否产生混淆时,可以将包装装潢的相同或者近似纳入考量。一方面,这是对包装装潢长期以来脱离混淆认定考量因素的纠正;另一方面,商标以及商品的包装装潢在商品宣传销售时往往是统一整体,将包装装潢纳入对于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可能性的判断,更符合商品营销以及消费者选择、采购商品时的真实情景,更有利于作出更为客观的与现实相符合的判断。
(六)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
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混淆的相关证据时,应当对其中诉讼包装进行自觉地识别剥离。各地区所认定的地方知名商品一般地域狭窄且具有浓厚的地域保护色彩。对于商品的知名度应当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知名度也是时刻变化的,在认定是否混淆时不能因为原告商标知名度高就径直认为被控侵权商标恶意搭便车、攀附原告商标、欺诈消费者造成消费者混淆。
法院应当提高对于原被告双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如果原告能够提交证明相关公众产生实际混淆的证据,法院就相对容易做出判断。这些实际混淆的证据包括直接提供消费者混淆的证据,或将订单、申诉信件、保修单或者维修信件错误地寄给另外一方。在美国,消费者实际混淆的证言也已纳入到实际混淆的证据中来[25]。另外在商标案件中还要注意对于既有认定内容效力的认定,原告在案件认定中会经常将彼案中已经生效认定中认定事实作为证据证明存在混淆可能性。案情基本相同但不同认定的案件在商标侵权领域屡见不鲜,同案不同判需要辩证地看待。已经生效的认定也只有认定的主文具有既判力,认定中的认定理由、事实认定原则上并不具有相应的既判力。即使对于认定主文,也必须赋予当事人就有关事实提出反证的权利[26]。此外还要充分考虑两个认定的时间间隔,两个原本容易产生混淆的商标,在经过一段各自宣传使用或者诉讼推广后,消费者反而会产生较为明确的区分。
(七)前瞻性思考:大数据分析的应用
大数据分析发现了以往样本分析难以发现的相关关系。虽然相关关系不能通过严谨逻辑清晰地阐述为什么两个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可以帮助我们对消费者是否混淆进行预测。目前,无论是各个网上店铺还是实体店都积攒了大量的用户的购物痕迹以及对于购物活动的评价,这些信息较为客观地记录了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品牌认知和购物的评价。大数据提供了海量的关于商标、商品的信息以及相关公众对于该商标商品的评价,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行为人以及商标商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司法机关以及行政管理机关都可以从海量的数据中获取有关商标商品、市场占有率变化以及公众评价的各类信息作为混淆可能性认定的依据。大数据的全数据分析模式恰恰弥补了小样本的市场调查本身的局限性,消费者市场调查与大数据分析相互印证。司法机关以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加强与市场主体尤其是电子商务服务提供者的合同,构建起层次多样的信息共享平台。司法机关以及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商标商品信息资源汇聚优势、大数据分析的模式优势,更加准确全面地把握相关公众混淆与否的实际情况。
四、结语
混淆可能性标准客观化新路径解构了商人塑造的商标混淆话语体系,是对已有的路径的修正。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商标行政管理机关在商标混淆认定中应更加注重统计学对于确定公众认知的作用,冷静对待商品知名度影响,更加强调客观因素考量,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势使得法律推定与客观事实更加一致。
[1]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63.
[2]祝建军.判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标准及考量因素——“满汉楼”与“湘巴佬”两件商标案之矛盾判定引发的思考[J].知识产权,2010(4):46-51.
[3]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2.
[4]胡继先,杨成国.商标近似中的比对方法及混淆可能性认定[J].人民司法,2010(16):41-45.
[5]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修订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3-16.
[6]约翰·莫纳什,劳伦斯·沃克.法律中的社会科学[M].何美欢,樊志斌,黄博,译.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
[7]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0.
[8]黄海峰.知识产权的话语与现实——版权、专利与商标史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230.
[9]孙红优,马千里.反思“混淆”[J].科技与法律,2013,103(3):63-68.
[10]姚鹤徽.论商标侵权判定中的消费者注意程度[J].知识产权,2014(4):47-53.
[11]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的经济结构[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3.
[12]杨延超.知识产权资本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5-47.
[13]蔡崇山.再论商品类似判断标准——兼评新商标法的有关修订[J].电子知识产权,2014(6):83-89.
[14]迈克尔·所罗门,卢泰宏,杨晓燕.消费者行为学[M].杨晓燕,郝佳,胡晓红,等译.10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6-57.
[15]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M].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4.
[16]张朋.商标侵权标准“两立”的矛盾解析[J].知识产权,2013(10):61-64.
[17]王立争.民法推定性规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5.
[18]孔祥俊.论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J].政法论坛,2002,20(5):86-99.
[19]谢晓尧.用数字说话:商标主观认知的科学度量[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10):35-43.
[20]谢晓尧,陈贤凯.商标混淆的科学测度——调查实验方法在司法中的运用[J].中山大学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3(5):159-171.
[21]周家贵.商标问卷调查在英美法院商标侵权案件中的运用[J].知识产权,2006(6):82-85.
[22]约翰·莫纳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美国法院中的应用[J].魏奎楠,白麟,赵军,等译.清华法律评论,2008,3(1):164-173.
[23]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M].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1.
[24]曾德国.商标的司法鉴定标准及指标体系建设初探[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2013(6):26-29.
[25]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M].2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106.
[26]陈晓艳,程春华.商标侵权民事责任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要求——以新商标法的规定为考察范围[J].知识产权,2014(10):57-61.
TheObjectificationPathofCriterionsforTrademarkConfusionPossibilityandItsReflections
Song Song
Due to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onfusion possibility criterions, the objectification path is required to achieve specific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 However,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trademark oblige, the current path cannot truly reflect the real consumption situations of consumers, which alienates the function of trademark, exaggerates the influence of fame, and simplifies the judicial adjudication of confusion.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for judiciary and trademark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to switch roles. Therefore, when they certify the trademark confusion, judiciary and trademark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bjective factors, strengthen the burden of proof of parti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big data analysis to promote the accuracy.
confusion possibility criterions;trademark discourse;judicial and administrative rhetoric;objectification of confusion possibility criterions;big data analysis
2017-06-28;责任编辑:晏小敏)
宋颂,法学硕士,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经理。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制改革研究”(16BFK139)。
D923.43
A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6.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