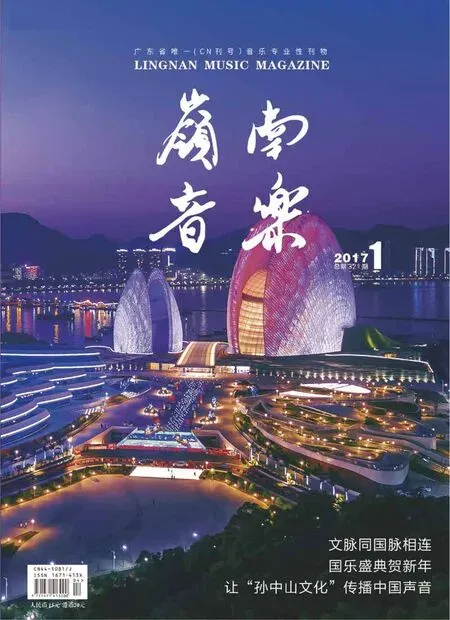她依然在创作
—— 朱婕新作出版
文|邓希路
她依然在创作
—— 朱婕新作出版
文|邓希路

如果说,希望通过别人的言说去寻觅好听的音乐作品的话,我宁可相信纯粹的爱乐者,而不是专业乐评人。因为,前者所依托的,仅仅是审美直觉;而后者所依托的,往往是技术分析。前者着眼于意境,后者着眼于手段创新。然而,美感不是分析的结果,而新手段也未必一定能营构出诱人的音响意境。对于爱乐者而言,诱人的音响意境,这种诉诸直感的物化形态,才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尺度。至于营构这种音响意境所调遣的技术手段新旧与否,他们从来都是不在乎的。因为,他们没有把作曲家当作发明家。当然,他们也期待有新意的音乐,而这种新意,指的是别无雷同的意象,虽然,它也得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使之外化,然其本源还在于心灵。
就艺术而言,所谓技术,就是得心应手,得心在前,应手于后。而所谓应手,作为技术手段,其取向终亦在乎应心,其新其旧,似乎无碍宏旨。将技术创新当作首要的审美尺度,实际上是把作曲家当作发明家,而非艺术家。
月前一位朋友来寒舍造访,见我桌面放着一本打开的总谱,或许是出于职业本能吧,他随口问道:“这作品有新意吗?”我说:“你指的是哪方面?”他回应道:“当然是作曲技法!”。他似乎很仔细地翻着总谱,我想,他一定在琢磨其中的织体、节奏、和声与配器。我说:“不妨听听”,他欣然接受。随即,我给他播放了高胡与乐队《自梳女》。一段沉默之后,他对我说:“真没想到,可以写成这样诱人!”。我说:“你对一道好茶有赏心之感,难道是你分析了它的化学方程结构吗;对一处风景有悦目之感,也绝非通过分析其各种组合因素之间的比例”。对于艺术,我还是相信直感。一首曲子诱人与否,听感是最可靠的,无须计较其技法之新旧。正是,这一际遇引发了我前面的一段思考。
朱婕老师与我可谓是忘年之交,20年间不时听到她有新作问世,她多部作品在国内外获选上演并有专辑出版。近年来,每有新作她也总会寄一份总谱给我,有可能的话,还附上音响制品。对她的作品,我向来不从技法新旧与否这一工艺层面去把握的,尽管她也孜孜以求,也尽管我在阅读与分析其总谱时略有所感——如《自梳女》中那些音簇;非三度叠置和弦;利用五声性音阶中那些模糊音调建构异调或多调复合;还有在《粤春》中所显露的多声部间的复合节拍;色彩性转调,以及其他作品所运用的局部无调手法等等,但我更看重的是她那种独特的心灵体验,以及由此而外化为音响实体的那种优美而又质朴的风貌。她的音乐显然不是写给学者或评论家们看的,她也从不像时下那些急于向社会索取回报的功利艺人那样,借助媒体以图自售,因而,人们难得在媒体中见到有关她的铺张报道。她似乎也无须为评职称而写点什么,也无须通过媒体博取名望,而所有这些,她似乎也早已拥有。但她依然在创作,甚至不在乎这些作品能否上演。在我看来,创作是她的一种本能,一种生活方式,因而,她也无须迎合时尚,也正因为此,她才能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并由此变得很纯粹。
记得辛丰年先生曾说过:有两种作曲家,一种称为“老作曲家”,一种称为“作曲老家”。前者是以前曾作过曲,现在不作了;后者是一直在作曲,从没间歇。在我心目中,朱婕属于后者。之所以成为后者,是她将创作看作是一种精神信靠。
欣闻朱婕老师的新作总谱即将出版,并嘱我为之写序,这颇让我有惶恐之感。作为晚辈与学生,虽喜欢她的音乐,写点感想,倒属分内之事,岂敢言序。谨以此表达我对她为人处事那种纯粹姿态的敬重,以及对其近年不懈创作所获得的成就表达一种欣喜之情。
——旅美作曲家梁雷音乐作品学术研讨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