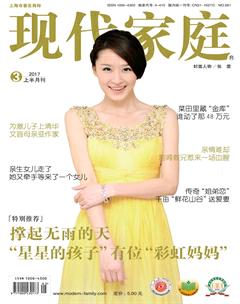撑起无雨的天,“星星的孩子”有位 “彩虹妈妈”
陈洁瑾
天冷了,别人都在加衣服,张灿红却给儿子嘉伟脱了一件衣服,为的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冷热变化,让他感觉冷后自己能主动加一件衣服。热了脱一件衣服,冷了加一件衣服,这么简单的道理张灿红却给嘉伟灌输了好多年。嘉伟今年已经26岁了,张灿红还是有很多生活常识需要事无巨细地反复教他,只因儿子是一个“孤独症”患者……
儿子2岁半时被诊断为“孤独症”
日历翻到了2017年,张灿红的生活还是如同过去一样。每天除了照顾、陪伴患有“孤独症”的儿子,就是在“彩虹妈妈工作室”里接待其他患儿和家长。她不是医生,她不会治疗“孤独症”,“孤独症”也无法治愈,她只是一个有着照顾“孤独症”儿子20多年经验的母亲,她想把她的经验分享给那些茫然无措的父母。
经常,张灿红要向其他家长说起自己的故事。那些过往的记忆早已深刻进张灿红的心里,20多年的人生路上,有欢笑、有泪水、有心酸、有无奈……
1956年出生的张灿红和比她大4岁的丈夫周胜方原来是一家玩具厂的同事。周胜方是知青,27岁才回上海顶替母亲的工作,进了玩具厂。张灿红是个性格外向、十分能干的人,周胜方的性格跟她恰恰相反,内向、老实。但是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爱学习,要上进。两人一起读高中、读大学。恋爱8年后,他们才结了婚,这时两人都已經取得了大学文凭。张灿红调到另一家厂当了总务科长,周胜方辞职去了外企,当起了工程师。夫妻俩可谓事业有成,连婚房也是单位分配的。
张灿红以为只要自己努力,生活就会一直这么灿烂下去,然而有时命运由不得自己选择。1990年,儿子嘉伟出生了,出生的时候,连医生都夸赞这个孩子长得漂亮,身体也很健康,可以打满分10分。张灿红抱着儿子,想象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的模样,甜到了心里。
没想到的是,嘉伟出了月子后就变得很难带,他哭闹不停,睡眠也比同龄孩子少。张灿红的母亲和婆婆年纪都大了,帮不了多少忙,张灿红只能自己照顾儿子。可是,随着儿子的长大,他表现出越来越多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7个月不会坐,9个月不会爬,18个月不会走……最关键的是,儿子跟自己没有眼神交流,这让张灿红的心里有了隐隐的不安。
嘉伟18个月时,张灿红把他送去了里弄里的托儿所。她休了一年半的产假,不得不回去上班了。嘉伟各方面的异常并没有因为慢慢长大而正常起来,他不会讲话,只会大喊大叫,显得十分亢奋。连托儿所老师都说,嘉伟不太对劲。
2岁半时,嘉伟还是不会讲话。张灿红就带着他去了儿童医院。结果医生诊断结果是——孤独症。这是张灿红第一次听说孤独症,她不懂这是什么病,她顾名思义地以为只是孩子的心理问题,或许多陪陪孩子就好了。她至今清楚记得当时问了医生三个问题:“患了孤独症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医生说不知道。“大了会讲话吗?”张灿红最担心这点。医生说,大了总会说话的。“哪里可以治这病?”张灿红心想,知道是什么病就好了,总会有希望。结果医生说,没地方可以看。
其实孤独症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听说过的“自闭症”。在当时,对于孤独症,医生也只是刚刚有所知晓,并不十分了解。
从医院出来,张灿红的心理还算平静,并没有觉得天塌下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无知者无畏”吧,因为她根本还不了解什么是孤独症,她并不知道孤独症的可怕。
经医生确诊后,张灿红开始当起了有心人,到处打听或是寻找关于“孤独症”的资料。单位同事的亲戚在美国,张灿红就让同事帮忙打听一下。几天后,同事神情凝重地对她说:“说给你听,你别难过,这个孤独症也叫自闭症,是终身的残疾,无法治愈,你要作好准备。”那一刻,张灿红觉得整个人瘫了下来。
放弃事业,当全职妈妈20多年
从那一刻开始,张灿红意识到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儿子既然注定是个特别的孩子,那么作为母亲,她义不容辞有帮助他、照顾他、培养他的责任。这是命运给儿子的考验,也是给她和老公的考验,既然改变不了,唯有面对。张灿红很快就振作起来。
语言障碍、刻板行为、智力落后是孤独症患者伴有的核心问题。对于普通孩子来说叫爸爸妈妈是很自然很简单的,对于患有孤独症的孩子来说却是难上加难。难在哪里?难在不知道怎么教。对于孤独症,当时并没有资料可以查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况且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即使都是孤独症孩子,各种表现、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等都是不同的。张灿红唯有自己去观察、摸索儿子的行为、学习习惯,自己寻找儿子的“规律”。
张灿红发现,儿子的记忆力没有问题,她重复说的话,他可以跟着复述。她尝试着教他背唐诗。嘉伟居然可以背下来。这一点让她惊喜又困惑,既然能背下唐诗,为什么就“记不住”那么简单的爸爸妈妈呢?嘉伟有时会无意识地念叨妈妈或爸爸,但他不是对着张灿红和周胜方叫的。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张灿红切身体会到,儿子真的跟别的孩子不同,别的孩子几天就能学会的东西,儿子一年半载也未必能学会。可是,不能因为他难以学会,就不教他啊。张灿红心里着急、担心,自己和丈夫总会老去,无论如何也要教会儿子基本的自理生活的能力。
人有时不是因为看到希望而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1994年,张灿红再三衡量之下,决定放弃自己好不容易打拼回来的事业,全天候陪伴儿子,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教导儿子,更多地了解儿子的特点。渐渐,张灿红发现儿子就像没有软件的电脑,带着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操作系统,一切行为出于本能。社会的规则要靠家长事无巨细地重复输入。在儿子的思维里,任何东西只能对应单一的名称。所以,张灿红告诉他自己是他的妈妈,但是他又听到周胜方叫张灿红的名字,并不是叫“妈妈”,于是他的认知就混乱了,就不会开口叫张灿红妈妈。这是张灿红观察了很久,才发现的“奥秘”。
于是,张灿红和周胜方约定,从此以后称对方为爸爸和妈妈,这样就能让儿子统一称呼了。果不其然,日子久了,嘉伟就知道张灿红是妈妈,周胜方是爸爸。终于,在嘉伟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对着张灿红叫了声妈妈。张灿红得开心与激动瞬间化作了眼中的热泪。儿子这声妈妈的背后,有她多少心血,只有她自己知道。
患孤独症的孩子脑子好像只有一根筋,不会转弯,不会融会贯通,你告诉是他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他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张灿红教嘉伟挂毛巾,教的时候,张灿红总说要挂整齐些。没想到的是,一段时间后嘉伟的确是学会了挂毛巾,但同时他像患上强迫症一样,每次都要把毛巾挂得整整齐齐,不能有一点没对齐或不平整。最夸张的一次,嘉伟站在毛巾架前挂了一刻钟,才觉得“挂整齐”了。从此以后,张灿红不敢再给嘉伟提这么具体的要求,毛巾挂上去就行,皱着也没问题。这般的小事,听着觉得无奈又有些好笑,但是对于孤独症孩子的家长,都是煎熬。
尤其是教导嘉伟的最初几年,绝望和崩溃成了张灿红习以为常的状态。甚至每一天都有些时刻,她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但是看着儿子静静发呆的样子,她的心里一阵酸软,如果现在不好好教导,儿子将来可怎么办?凭着这份一切为了儿子将来的信念,她坚持了那么多年。
孤独症的孩子不仅行为认知有困难,还时常会有些怪异的举动,并且乐此不疲。春天来临孩子显得异常兴奋,5岁时嘉伟将家里眼光所及的东西全部朝窗外扔,包括玻璃牛奶瓶、BB机等,无论是否贵重或危险,张灿红越禁止他越起劲。张灿红一度崩溃,可又不能把他绑起来,后来只能藏起重要物品,买来箩筐专门给他发泄。嘉伟7岁时,他又突然“爱”上剪床单和毛衣。张灿红几乎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每天24小时的生活,会有各种无法预知的事情,张灿红真可谓心力憔悴,可她一直坚持着。她总是相信,儿子只要有一点点的进步,她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教会嘉伟过马路、看红绿灯、坐公交车、买票刷卡……张灿红和丈夫花了足足8年。嘉伟在里弄里的托儿所一直待到7岁,张灿红知道儿子是不可能进普通學校学习了,只好把他送去了特殊学校。从那时起,张灿红就教嘉伟过马路,乘公交车。
操练过马路时,张灿红和周胜方各自把守斑马线两头,一遍遍引导嘉伟等绿灯过马路。偶尔碰到街边的车锅时,张灿红会把嘉伟带到现场,告诉他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就可能遭遇这样的后果。上下车注意事项、公交车站名、突发情况如何处理,所有细节张灿红都反复跟他讲。终于,在嘉伟15岁的时候,张灿红放心让嘉伟独自乘车去学校了,但他也只能独自走这条固定的路线。
健康的孩子会随年龄增长自己习得生活技能,但孤独症的孩子事事处处都要关照。这就是张灿红作为家长,辛苦的地方。
“彩虹妈妈”给更多“星儿”希望
有人把孤独症患者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不是智障,他们不是没有情感,只是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与他们交流。国外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雨人》。影片中患孤独症的主人公雷曼咬字不清,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叫成“瑞曼”,英文 “RAINMAN”,意译过来,就是“雨人”。从此,“雨人”便也成了孤独症患者的代称。不管是“来自星星的孩子”或是“雨人”,都意味着孤独症患者需要更多的爱和陪伴。张灿红的名字用上海话念,跟“彩虹”同音,她希望成为儿子生命中的彩虹。
1995年左右,张灿红从报纸上看到有专门的门诊可以看孤独症,她抱着希望带着嘉伟去了。结果,医生配的药只是让儿子变得安静些,并没有实质的效果。失望之余,张灿红却庆幸因此认识了好几位孤独症患儿的家长。张灿红终于有了可以听她倾诉,真正明白她内心痛苦的人。从此以后,张灿红时常约一些孤独症患儿和家长到自己家里聚聚,大家说说各自的成功经验,说说自己的困难。每一次交流都是经验的汲取,压力的释放。既然孤独症是伴随患者一生的顽疾,是根本不可能治愈的,那么作为家长唯有耐心陪伴引导,希望孩子多一点点进步。
这样的聚会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012年,丈夫周胜方退休了。张灿红原本以为,丈夫退休了,可以多个人帮自己多分担一些,白天也可以有两个人陪着儿子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又发生了。周胜方刚离开工作岗位,生活状态一下子改变了,多少有些不习惯。更不习惯的是,每天要24小时对着儿子了。他不是不知道儿子的情况,以前每天下班回家和休息日他也会和张灿红一起教导儿子。可是原来每天几个小时的面对和每天24小时的面对是完全不同的。全天候对着儿子,让他觉得没有透气的时间,儿子不时会有各种突发情况。与此同时,儿子嘉伟也不习惯了,孤独症最害怕的就是“意外”情况,他们无法适应固有的习惯被打乱。对嘉伟来说,周胜方每天白天也在家里了,打乱了他原本的生活规律。他时常在家发脾气。张灿红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尽力安抚、疏导儿子的情绪,告诉儿子以后爸爸每天都在家了。
老实内向的周胜方情绪无法发泄出来,居然“闷”出了病,整夜失眠。张灿红陪着周胜方去了医院,诊断结果居然是抑郁症,而且很严重。张灿红理解丈夫,丈夫不喜言辞,什么苦闷都放心里,才会憋出病来。家里住房条件有限,仅有一居室,父子俩避无可避,只有靠时间让大家习惯新的状态了。周胜方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张灿红尽量看着儿子,不让儿子再去烦丈夫。自然,在这样的状态下,张灿红不可能再约患儿家长们到自己家里来聚会了。
2013年11月,周胜方的病情稳定了。张灿红又惦记着那些患儿和家长了。张灿红想把自己20多年跟“来自星星”的儿子沟通的经验传授给更多年轻的“星儿”父母,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张灿红走过了20多年,她清楚这一路如果自己不够坚强,可能早就垮了,放弃了。所以,她想让命运相同的大家可以抱团取暖,彼此安慰,彼此鼓励。
张灿红跟周胜方商量后,拿出家里三分之一的收入在小区里租了一间房,开办了“彩虹妈妈工作室”。张灿红45岁就退休了,所以退休工资很低,丈夫是企业退休,工资也只是普通水平。儿子每月有800元补助。张灿红家的经济条件很一般,但是她心里一直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心愿,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孤独症患儿的家庭聚到一起,大家彼此鼓励,一起望着彩虹坚持下去。
现在,嘉伟的情况逐渐稳定好转,每天早晨跟妈妈买菜,然后听上2个小时的古典音乐,下午和爸妈一起去工作室跟其他孤独症的孩子一起做游戏、学习,他喜欢固定的生活。可以说,张灿红对嘉伟的教育是成功的。
如今,在工作室登记的家庭已经有400多户了。工作室每周会有固定的各种活动。大家都非常感谢张灿红的付出,这两年自愿分摊了工作室的房租。张灿红的经济压力少了,可她的干劲一点没少。她让自己一直保持着活力,她说孩子还没长大,她不敢老去。孤独症患儿的家长不怕日夜陪伴照顾自己的孩子,最怕的是自己将来不在了,孩子怎么办?他们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只会通过自残、暴力等方式发泄。
死亡对于大多数孤独症患儿来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课题。亲人朋友病重时,张灿红会带嘉伟一起去探望,张灿红要让他知道什么是死亡。外婆过世时,嘉伟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是他吃的炸猪排掉在地上,他会哭。这就是孤独症患儿。
张灿红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能活到90岁以上,这样嘉伟已经60岁了,可以进养老院了,她才能放心。她说,每个“星儿”父母都跟她有着相同的想法。
如果说,患有孤独症的患儿是“来自星星的孩子”,那么这些“星儿”的父母们都是最可爱的“天使”,就像张灿红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