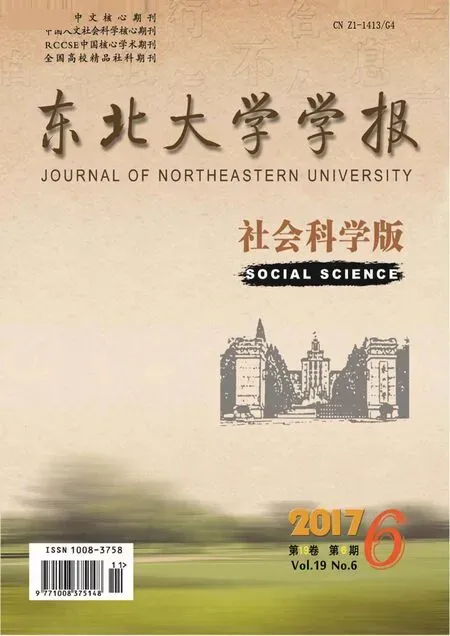从赤裸生命到世界公民
——从《日光》看难民的身份重建
吴 轶 群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从赤裸生命到世界公民——从《日光》看难民的身份重建
吴 轶 群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英国当代作家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作品大多探讨人在面对极大心理危机时的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日光》中的难民个体因为民族国家政治身份的丧失和心理秩序的坍塌,而成为被排除在一切法律和人类共同体之外的赤裸生命。面对存在的绝境,生存的本能使她想象性自欺地将避难国优秀的他者形象当做自己生命的本质加以复制,以重建自己瓦解的主体性。而心理机能恢复的难民个体摆脱了他者的侵凌性占据,重生为兼具原在国和避难国特质的具有国际化身份和全人类视野的世界公民,重建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心理身份。
《日光》; 难民; 赤裸生命; 他者; 公民
从20世纪初至今,世界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和无数局部战争,而战争引发了难民潮,“难民作为群体现象的首次出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1]42,从此以后无数无家可归的难民就成了困扰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政治难题。对于难民问题,学界大多从法律、政治和哲学的角度探索安置难民的妥善方法,而少于关心难民在避难国生活中心理上的身份重建和自我认同,而文学则能真切展现难民实际的生存境遇和内心情感经历。《日光》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1996年布克奖得主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第七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妻子杀死出轨的丈夫的犯罪事件。在国内外的很多研究中,研究者的着眼点大多放在杀夫的妻子莎拉和她雇佣的私家侦探乔治在爱中获得的灵魂救赎上,而往往遗忘了这起刑事案件的重要关系人、莎拉的丈夫鲍勃出轨的对象、来自因战争的失利而失去主权的克罗地亚的年轻女人克里斯蒂娜,一个没有国籍的难民,在避难国的生活境遇和心路历程。本文从克里斯蒂娜没有政治身份的生命切入,分析她作为难民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其原在国语言文化的陌生国度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和心理身份的经历,试用文学的思考和心理分析的关怀为解决世界难民问题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希冀。
一、 赤裸生命
1990年克罗地亚战争爆发,克罗地亚战争指的是1990年到1995年之间,克罗地亚从前南斯拉夫独立出来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因民族对立引发的战争,由于战乱“大量民众渴望在邻邦寻求避难所,继‘二战’后难民问题又一次成为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和危机”[2]。1993年,克里斯蒂娜这个18岁的克罗地亚女孩在国内局势还未完全失控时获得了一个来英国伦敦学习的机会,从而离开了战争中的祖国,而“她离开后的那个世界的一切都破碎殆尽”[3]44,战争愈演愈烈,她的哥哥和父母先后都在战争中被杀害,当她走进莎拉面对国外学生开设的英语课程的教室时,“她看起来只有一半的灵魂存在”[3]45,“丧失了生命的绝大部分,是一个被损毁的灵魂”[3]46。到了1994年夏天,克里斯蒂娜在英国的学生身份和签证全部到期,国内紧迫的战争局势让她无法回国,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英国登记成为寻求政治避难的难民。
依照1951年《难民公约》和1967年《难民议定书》的共同规定,难民即指 “因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由于政见观点等确实原因遭受迫害,现居住于原国籍所在国或通常居住国之外的地方,不能或者因为畏惧被迫害而不愿接受原在国的保护,或返回到那里”[4]的人。克里斯蒂娜离开克罗地亚到达了英国,因为当时国内已由塞尔维亚人当政,具有克罗地亚民族身份的克里斯蒂娜回国后就是国内当权民族的异族他者,势必会面临巨大的人身危险,也许会遭到像她家人般的毁灭性侵害,所以她完全符合难民的定义,也被英国政府确认了难民的临时避难资格。克里斯蒂娜在陌生的国度远离了被原在国的他族武装伤害的危险,英国成了她暂时可以安全栖身的避难所,但她原本所具有的克罗地亚国籍也因为克罗地亚政府对国家统治权的丧失而失去了法律效力,而掌控克罗地亚领土的塞尔维亚政府是连克罗地亚人民生命权利都无法保障的敌方政权,更无法为她提供法律的身份。克里斯蒂娜在这个为她提供安全的避难之国“既没有与英国的历史渊源,又非被授予合法地位的当地居民,她在英国的存在也只是暂时的”[2],她成为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只被法律容许一半存在的人”[3]78。
没有国籍的人是普遍意义下异于常态的人,是不包含在一般法律界限内的没有身份、不被法律保护的“无权利者”[5]385。无权利首先体现在他们丧失了享有安身立命家园的权利,而丧失家园代表丧失了整个支撑他们物质存在和心理存在的社会结构,丧失了他们建立的让自己能够生存发展的独有个人领域。克里斯蒂娜因为原在国纷乱的战争局势而孤身前往完全陌生的国度,到达英国不久就获知了至亲纷纷离世的噩耗,而随着克罗地亚民族武装的失利,她不仅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可以回归的祖国,只能留在他者的世界,成为一个没有国籍没有家园的避难者。另外,拉康说:“在人类经验中唯一不堪承受的方面,不是一个人自己的死亡经验——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而是对另一个人死亡的经验”[6],他人的死亡对生者而言是最难以承受的创伤,而作为主体的人在遭到残酷的创伤事件的侵害和打击后,强烈的创伤体验会毁灭性地抹去人存在的所有实质性心理内容,人的主体存在中,就只剩下主体性的纯粹形式,“主体被还原为一个不具实体的空洞主体性形式”[7]。在经历了战争侵袭和亲人死亡的巨大心理创伤后,克里斯蒂娜的身体看似完整无损,可她的精神却处于极度的混乱和惊骇中,原有的稳定的内心机制和心理秩序彻底坍塌,原本安稳的内里灵魂支离破碎、濒临瓦解。作为难民的克里斯蒂娜丧失了家园和亲人,丧失了作为主体的全部实质内容,丧失了全部的个人物理领域和心理领域,成为了一个空洞而纯粹的存在。
无权利者还丧失了拥有政治身份的权利,这代表他们不再作为原在国的公民受国家的承认和保护,丧失了在原在国的合法地位,而且也丧失了在所有国家的合法地位。这是因为,虽然长久以来,人类这个名词是被人们以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的意义来认识的,但人类在现实范围内更是在现有法律和秩序下集合起来的严密封闭的组织,一旦不被已有的法律和规范所囊括,一旦当前的人类规则解释不了个体的存在形式与身份意义,那么个体生命就会被人类共同体抛弃,所以,当前国际上对个体身份以其所在国的国籍和公民身份为界定的原则,无国籍无公民权利的人就被抛弃在人类共同体之外,无权利者“不再属于任何人群社会。他们的困境并非在法律面前不平等,而是对他们不存在任何法律”[5]388。“在民族国家系统中,人的所谓神圣且不可剥夺的权利表明,当它们无法再以属于一国公民之权利的形式出现的那一刻,它们自身就立即丧失所有的保护和现实性”[8]173,而难民就是被排除在人类共同体之外,不受任何法律的保护,存在本身丧失了现实意义的“赤裸生命”[8]12。
赤裸生命是“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8]117。可以被杀死意味着非赤裸生命可以在不受法律责罚的情况下完成对赤裸生命的屠戮,从而悬置了世间法律对杀人惩处的基本职能,说明赤裸生命是不受法律的制约和保护的生命实体;不能被祭祀则指在宗教的秩序中赤裸生命也没有存在的地位,不能作为宗教的献祭也不能在死后被宗教性的祭奠和铭记。赤裸生命就是这样“既被排除在人间法之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既被排除在俗世之领域,又被排除在宗教之领域外”[8]116的生命样式,“是被城邦禁止在外的人”[8]147-148,他们的“生命无法挽回地被暴露在弃置面前”[8]118,不受任何形式的保护,不在任何秩序中拥有自己的合法身份,而无国籍、无公民权利的难民就是如此的赤裸生命,被排除在民族国家的法律界限之外,被弃置于人类政治共同体范畴之外。赤裸生命不是政治生命,也不是单纯的自然生命,而是处于无区分地带,“是动物与人之间,自然与约法之间的无区分界槛”[8]148,他们是人但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个人领域和社会关系,他们是人却不被任何法律承认存在意义。克里斯蒂娜就完全处于不能被不复存在的克罗地亚政府保护,无法取得塞尔维亚政权的认可,在英国的学生身份终结但无法取得英国公民身份,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的认可和保护,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和精神支持,完全丧失主体内在领域、外在政治身份和公民权利的赤裸生命的纯粹而空洞位置。
二、 成为他者
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里没有属于赤裸生命的存在空间,难民在他国避难的地位从本质上是临时的,难民的出路只能是被避难国同化或是被遣送回国。但根据国际难民法规中的难民“不推回”原则,除非难民本人自愿,否则“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遣返(推回)使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所在的种族或所具有的国籍参加某一社会团体或坚持某种政治见解而遭受威胁的国家领土边界”[4]。然而克里斯蒂娜她并没有一个祖国、一个和平的故土可以回归,所以她暂时不能主动返回原在国,而且英国政府既然接受了她的难民身份,也不能贸然遣送她回国。另外,一个国家的立法是以其国民的权益为原则建立的,而国民是拥有此国国籍的人,因此对无国籍的难民的同化不是立法的必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制定归化法案。而且英国1993年才将1951年的国际难民法律置于其移民法规之下,所以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难民并没有健全的保护机制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无法获得来自避难国实际的生活扶助。因此,克里斯蒂娅这个19岁的女孩,一个失去了家园、亲人、身份和灵魂的赤裸生命,归化于他者世界的唯一出路对她来说也几乎无所期盼,她的生命一片荒芜。
然而克里斯蒂娜也是幸运的,当她如游魂般的赤裸生命第一次走进莎拉授课的教室,莎拉就情不自禁地将这个破碎的灵魂护卫到自己的羽翼之下,而当克里斯蒂娜失去学生身份,正式成为难民之后,莎拉和鲍勃就将她接进了他们的房子,将她接纳入英国本土家庭中。克里斯蒂娜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亲人离世的巨大人生变故后在陌生的他者国度找到了一处远离战火和死亡,能保障她生存需求的容身之所,在陌生的他者家庭中找到了暂时的避难之所。但是,尽管克里斯蒂娜已经处于安全的庇护之下,可她在英国社会仍没有受法律保护的政治身份,她的内心仍因为创伤的侵袭而支离破碎,她内里的存在困境和外在的身份处境还停留在成为难民的最初。而对生之渴望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即使在最险恶最艰苦的环境中,人类永远拼搏求生。所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悲伤沉溺后,克里斯蒂娜的生命意志逐渐复苏,她开始寻求心理秩序的自我重建和社会身份的重新获得,既然她的人生只剩下了归化为英国人这一条出路,她就必须接受避难国对自己的全面同化,完全归化于他者世界,成为与英国公民看似无异的人。
克里斯蒂娜要重组内心秩序,她不能寄希望于沿袭从前的自我,因为已经不复存在,她只能挪用他人的特质。莎拉生于英国,天然是英国公民,她的职业是大学英文教授和高级翻译,是英国语言文化的高级人才和有力传播者,她住在郊区的花园别墅里,丈夫鲍勃是医生,独生子在美国工作,莎拉即是典型的英国本土中产阶级的代表,具有明确的政治身份和优越的社会地位,是被英国社会和英国人承认和赞赏的完美英国公民。这样的莎拉是克里斯蒂娜这个赤裸生命在英国的保护者,是这个异国难民的老师,是这个寻求政治避难者的避难所提供者,是距离克里斯蒂娜最近的英国人,莎拉拥有的学识、职业和家庭都让克里斯蒂娜这个一无所有的赤裸生命无限向往。所以,强烈的求生意识使克里斯蒂娜在内心秩序几近崩溃的境况中彻底认同了莎拉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本质,将莎拉视为完美的理想自我模板,莎拉这个他者成为支撑她全部生存的内心法则和全力追求的人生目标,“主体在他自己的情感中认同于他人的形象”[9],“莎拉就是克里斯蒂娜想成为的人”[3]145,她要成为莎拉。
拉康认为“每个人都存在于他者的存在”[10],为了存在,我们必须获得来自他者的承认,为了获得承认我们必须用他者的特质建构自己的生存秩序,于是,成为他者成了我们自身的理想,就像审视镜中的自己时,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面容,而是心中渴望成为的他者的形象,这个以他人的形象为主体生存基础的心理特征被拉康称为想象界。而在我是他者的想象中,一无所有的赤裸生命,为自己坍塌的内心秩序和丧失的政治生命找到了重新建立的可能,因为“那个形象给予主体以强烈的向心力和肯定感”[11],使他们在出离其自身的位置上重新获得对自己生命的承认和掌控。所以,在求生意志统辖下的赤裸生命为了重建自我身份,陷入了一种心理误认性想象执念中,任由他者生存形态侵凌性地占据自己的整个意识,将他者体验为自我,在他者形象的理想自我中获得生存的根基,生活在“我是他人”的想象性自我欺骗中,自足于假面具下。所以,克里斯蒂娜这个破碎生命的全部内心支撑就是:我是莎拉,我是完美的英国公民。
克里斯蒂娜实现“我是莎拉,我是英国公民”的第一步就是获得莎拉的语言能力和社会身份,“模仿她的外在真实”[12]。为了复制莎拉的事业轨迹,克里斯蒂娜进修口译课程,学习英国文化,努力将英语运用到与英国公民无异,努力成为能够在原在国语言与英国语言间自如转换的高级口译人员,努力用避难国的语言和文化填充自身赤裸无依的政治生命和社会身份,将自己打造成如莎拉一样被英国社会和英国人认可的优秀社会共同体成员。“而一切都成真了。她的英语十分完美,她获得了学位。一位优秀的翻译人才。”[3]145克里斯蒂娜复制了莎拉的事业,并在“我是英国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中,自欺性地感觉自己完全被接纳入英国本土的社会生活,误认性地感觉自己已经彻底融入了避难国的他者世界,在他者的世界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
克里斯蒂娜实现“我是莎拉”的第二步是拥有莎拉的感情和家庭,她与莎拉的丈夫鲍勃相爱了,鲍勃支付她的一切生活和学习开支,并在别处建立了他们两人的家。克里斯蒂娜于是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赤裸生命、一个受莎拉慈善帮扶的难民成为了一个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英国男人真心关爱照顾的女人。克里斯蒂娜之所以爱上鲍勃是由于她“我是莎拉”的自我身份认知对她内心情感的侵凌性占据,鲍勃因是莎拉的丈夫而自然成为她爱情的欲望对象,她因爱莎拉之所爱而迷恋鲍勃,“她甚至分享了莎拉的丈夫”[3]190,并且通过与鲍勃建立起的亲密关系,通过鲍勃对她感情的回馈和爱人身份的认可,她的想象性自我认同也得到了更确实的肯定。而且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是莎拉”的自我欺骗中,她失去亲人、丧失身份的巨大创伤得到了抚慰和缓解,因创伤侵袭而破碎的内心秩序也在想象性身份建构中重归一个有序整体。克里斯蒂娜这个无所依凭的赤裸生命,在成为他者的想象界中得以继续存活,并在我是他人的自我设定中重建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心理身份,重获了内心的安稳。“自我从一个位置观看和建构自己的存在,通过对这个位置的先行认同来构想自己与世界的关系”[13],通过自欺性地建构自我身份,作为难民的克里斯蒂娜在他者世界为自己找到了自圆其说的存在意义,与他者世界建立了想象性的合法关系——我是莎拉,我是拥有理想事业和美好家庭的完美英国公民。
三、 世界公民
原本破碎的自我存在因为他者形象的注入而恢复了继续生存的力量,赤裸的生命因为“我是他人”的想象性自我倾入而获得了来自被自身和社会认可的能量,难民的边缘性存在因为复制了他者的妆容而被幻想性地稳固化,克里斯蒂娜在“我是莎拉”的心理建构中获得了临时的自我身份和暂时的内心安宁。然而,想象终究只是幻觉,他者的形象再完美也不是自己的真实属性。当人们在他者的相貌中寄生求生,潜在的自我就被强行压制在他人的虚假装扮之下不得展现,所以“我们既依赖于他者作为我们自身存在的保证人,同时又是对这个他者充满仇恨的竞争者”[14],他者与自我在潜意识中互相争斗,每一方都试图消灭对方的存在,从而赢得自我的实现,而这既彼此需要又彼此斗争的矛盾共存中产生的冲突,只有当一方彻底消失时才能得到解决。
所以,当克罗地亚民族武装赢得了内战重新获得了国家主权,当克里斯蒂娜恢复了民族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不再是必须仰仗他者世界收留、依赖他者形象生存的赤裸生命时,她的自我也赢得了与他者的战争,夺回了被他者侵凌占据的主体性,她不再是莎拉的仿冒品和膜拜者,她重生成为了被他者世界的精华文化滋养过而又清除了他人致命烙印的全新生命。在克里斯蒂娜得知将被遣返回国时,她的内心是坚定和充满希望的,因为她“重新统一了自己,深入身体骨血的东西”[3]190在灵魂中回归。所以,在与鲍勃最后的相处中克里斯蒂娜一直是更冷静坚强的一个,“她是在这场危机中引领方向的一个”[3]199,她坚定地踏上前往永久中立国瑞士的著名城市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签署地——的飞机,并将在日内瓦通过身份认证后回归克罗地亚,“整个异国大都市的灯光都在她的下方,随着飞机下降而逐渐放大,准备好了与她相见。高品质的生活,好的生活。一个训练有素的口译者,一个翻译,一个世界公民”[3]285。
“公民”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公民的通常含义是参与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公民,但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15]。公民从产生之初就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也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范围内界定的,“民族国家指的是把本土或出生(也就是土著人的生命)作为主权基础的一个国家”[1]43。1789年发表的《人权与公民宣言》“把出生地置于任何政治组织的核心,从而牢固地把主权的原则维系在民族之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出生即刻作为民族出现”[1]43,自然生命在这里成为权利的直接载体,出生的本土人即刻成为民族国家的合法公民,两者之间无任何分隔间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类是政治的动物,从出生就被建构了政治身份。而赤裸生命是民族国家体制中的例外状态,既不属于单纯的自然生命也没有合法的政治身份,作为难民的赤裸生命,因为非本土血缘身份,被排除在国家公民内涵之外,被排除在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国家权利享有人之外,但又作为人类个体真实存在,以难民这个无身份的身份被接纳入避难国,由此“生命将自己呈现为一种通过排除而被接纳的东西”[8]11。因此,难民这个不被法律接受又现实性存在的生命样式,在民族国家秩序中成为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他破坏了人与公民、出生地与国籍的天然性和同一性,把国家-民族-地域原有秩序的三位一体分裂开了。所以,难民的概念与难民的存在是对民族国家的根本性界定原则的质疑和冲击,也许人类应该创造出另一种涵盖更广的政治秩序,在该政治中,赤裸生命不再被排除在社会法律和人类共同体之外并能获得本该有的权利。
“世界公民”即是这种政治,民族国家虽然是现代国际政治的秩序基础,但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派就提出人是城邦的动物,也是世界国家的动物,是世界公民的思想。18世纪康德提出了世界公民主义的概念,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使他们具有到任何一块土地上居住的资籍,并且能够与那里的居民友好相处。一个自由和理性的公民,不仅属于某个民族国家,而且也属于全世界,是世界公民,他所必须遵从的理性的普遍法则,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公民共同体之间互相的尊重和承认”[16]。随着20世纪全球化国际形势的推进,哈贝马斯提出了世界公民社会的理论,认为未来的人类世界必定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限制、所有个体、民族和种族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世界公民社会,每个人类个体将作为权利界定的直接载体,个体在具有某一国家的公民身份的同时也拥有国际共同体的合法公民地位,世界每一个体生命都具有平等自由的权利并受法律保护,成为世界公民。“世界公民社会”的美好设想应该算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政治乌托邦,在依然战火不断的世界环境中,并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深入探讨过难民生存困境和出路的阿伦特也认为“这种想法超越了目前的国际法范围;再者,这种两难状况也根本不会由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消除”[5]391,但是“世界公民”作为一种理想和希冀,并不是完全没有变相实施和部分成真的可能。“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就曾推出过一种针对没有国籍的难民的国际身份证——南森护照。1942年,有大约42万难民接受了这一护照,有52个国家承认了该护照的合法性,而这些拥有南森护照的战争难民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批被很多国家承认的世界公民,并通过南森护照的身份认证在其他民族国家获得了正式的公民资格。而当今国际社会难民救助的主要机构——联合国难民署,在成立之初仅是一个拥有34名工作人员,30万美元经费的国际组织,并且直到现在该组织的性质一直是人道主义的、社会的和非政治的,它以外交中间人的身份出现,将原属各民族国家的难民作为实在的人类个体对待,将这些无政治身份的赤裸生命当成世界公民看待,积极实施各项援助,安置他们一无所有的生命。
然而对于在英国本土家庭中长期生活过, 在纯英语的环境中学习并取得学位、成为了训练有素的克罗地亚语与英语的高级口译人员, 经历了内在世界和外在身份全面瓦解、以他者形象建构自己存在的迷惘并最终被遣返回国的克里斯蒂娜来说, 她的身份已经很难明确界定。 政治身份上她恢复了克罗地亚国籍, 但她曾切实地以难民的赤裸生命样式避难于英国多年, 并曾迷失于避难国的他者世界,以为自己就是真正的英国公民, 一度遗忘了自己的本源和自我身份; 语言文化上,她已经能说流利的英语,与英国的本土公民无异, 并可以自如地在母语与英语间切换而毫无瑕疵, 而且因为在英国生活多年和刻意地融入, 英国的文化已融入她生命的机理, 与原在国的文化一样是构成她心理秩序的重要部分; 感情上,她当然怀念故土, 虽然在克罗地亚已经没有至亲可以重聚,但祖国依然是她情之所系, 然而在英国她与英国男人鲍勃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乎拥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克里斯蒂娜从一个处在动物与公民之间的赤裸生命成为了一个将原在国与避难国的特质都刻写进自己外在真实和内在本质的融合体,拥有了世界性的开阔视野和极具国际包容性的心理结构,她的自我身份已经无法用单纯的国籍进行界定,或者就可以叫做理想中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的理想在克里斯蒂娜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成长历程中得到了完美地体现,“她就像世界的传输管道,同时传递关联性与差异性的信号”[2]。克里斯蒂娜“一个克罗地亚难民,她的家人全部遇难,她自己在英国作为一个寻求避难者存活了下来”[17],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内心创伤和生存迷惘后最终重生为一个全新的自我,她穿越了岁月的风霜最终成为一个更全面和完善的美好自我,成为一个具有世界视野和多元心理广度的世界公民。《日光》中并未叙述克里斯蒂娜步入机场安检口之后的人生经历,但作为故事叙事主人公的侦探乔治表达了他对这个曾经的赤裸生命的希冀和祝福,“我看见她依然在日内瓦。我看见她在联合国任职。我看见她回到新的祖国,作为某官方团队的一员。一位联合国翻译官,一位观察员”[3]285,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公民。
1993年,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世界难民状况报告》指出,1960年全球只有140万难民,1976年之后难民数量开始加速增长,1980年达到820万,到1992年底则达到了1 820万的高峰。而根据《 2009年全球难民趋势报告》的数据,截至2009年全世界有4 330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机构负责的全球难民已达到1 520万人,国内难民2 710万人,申请政治避难者98.3万人,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大难题。报告公布的难民分布地区显示,非洲、中东、中亚及西南亚地区难民人数最为庞大,而欧洲相对来说成为全球难民分布最不密集的地区,也成为国际难民安置问题压力相对较小的经济发达地区。欧盟各国共同制定了《都柏林公约》,规定了难民安置的基本措施和最低收容标准,但仍有如希腊和奥地利等民族国家因为自身经济与管理现状无法实行对难民最低标准的安置,或者如匈牙利和英国等国因为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保护而对难民安置采取不合作态度,难民在世界上最可能被妥善保护的人类生存区域内仍得不到应有的妥善照料,仍被排除在民族国家人类共同体之外,维持着赤裸生命的存在特征。所以,蜕变成为世界公民的克里斯蒂娜是全球难民总体中的最幸运个体,她的人生际遇几乎代表了当今国际社会能够为难民提供的最高生活标准,她虽一路艰辛但最后顽强重生的生命轨迹成就了世界公民的政治乌托邦理想。我们是否也可以希冀,从经济发达、难民人数最少的欧洲地区最先开始以全球化的眼光,以全人类共同体的视角看待每一个因战争和宗教等原因被迫远离家园、一无所有的赤裸生命,保护他们生存的尊严与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用经济的照顾和教育的滋养为难民贫瘠的生命注入生存的意志和活力,让更多的赤裸生命个体成长为完善的世界公民?
四、 结 语
难民安置和难民保护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作为失去政治身份的难民成为被排除在所有民族国家法律保护之外的赤裸生命,没有基本的生存和生活保障。有一些被避难国承认难民资格并幸运地受到慈善资助不至于流离失所的难民个体,因无法返回原在国,只能寻求在避难国归化成为当地的居民,而心理极度匮乏的赤裸生命很容易将身边的本土公民当成自己需要复制的对象和想象性自我认同对象,期望通过成为他人而被他者世界接受。而更幸运的难民个体在心理机能逐渐恢复后,就会慢慢从自欺的自我身份中回归现实,在从前的自我身份基底上将避难国语言文化融入内心秩序并整合出全新的自我,重生成为具备国际化身份和世界性视野的世界公民。《日光》用一个难民个体的完美身份重建经历为难民问题提供了一种世界公民的美好理想,对难民问题的解决给予了一份来自文学的真诚祝福。
[ 1 ] 吉奥乔·阿甘本. 在人权之外[M]∥斯波斯托,汪民安,郭晓彦. 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斯托. 陈永国,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2 ] Agnes W. Something Blurred in Her?: Imagining Hospitality in Graham Swift’s The Light of Day[J]. Textual Practice, 2012,26(3):450-454.
[ 3 ] Swift G. The Light of Da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 4 ]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9,63(2):390-401.
[ 5 ]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M]. 林骧华,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6 ] 雅克·拉康. 欲望及对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J]. 陈越,译. 世界电影, 1996(3):169-170.
[ 7 ] 斯拉沃热·齐泽克. 事件[M]. 王师,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113.
[ 8 ] 吉奥乔·阿甘本. 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M]. 吴冠军,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
[ 9 ] 雅克·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187.
[10] Lacan J. Homeostasis and Insistence[M]∥Lacan J, Miller J A.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Ⅱ: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Tomaselli S,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72.
[11] 福原泰平. 拉康:镜像阶段[M]. 王小峰,李濯凡,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45.
[12] Lea D. Graham Swift[M].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199.
[13] 吴琼.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409.
[14] 肖恩·霍默. 导读拉康[M]. 李新雨,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38.
[15]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颜一,秦典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99-100.
[16] 周俊. 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D]. 杭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07:67.
[17] Malcolm D. Understanding Graham Swift[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3:199-200.
From a Naked Life to a Citizen of the World——Based on the Refugee’s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TheLightofDay
WUYi-qun
(Faculty of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The works of Graham Swift, a British contemporary writer, mostly explore peopl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 and behavior in the face of a great psychological crisis. The refugee inTheLightofDaybecomes a naked life who is excluded from all the laws and human communities because of the loss of the nation’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sychological order. Faced with the hopeless situation of existence, the instinct for survival makes her copy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s excellent others as her own for reconstructing her disintegrating subjectivity with the imaginary self-deception. However, when the refugee’s mental mechanism is restored, she gets rid of the aggression of the others, and is reborn a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with qualities allied by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her original country an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human vision, so that she rebuilds he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psychological identity.
TheLightofDay; refugee; naked life; the other; citizen
10.15936/j.cnki.1008-3758.2017.06.015
2017-02-20
吴轶群(1983- ),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外国文学、西方文论研究。
I 06
A
1008-3758(2017)06-0650-07
(责任编辑: 李新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