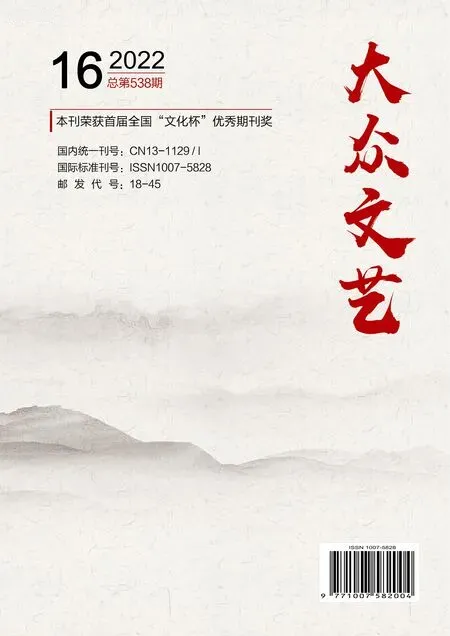浅谈动画电影《大护法》的反乌托邦主题
徐 露 (四川大学 610207)
浅谈动画电影《大护法》的反乌托邦主题
徐 露 (四川大学 610207)
《大护法》是今年国产电影的最新力作。导演以明亮的中国传统山水画为背景,以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为电影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极权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本文将细读电影文本,分析这部引起很多观众讨论的电影中的反乌托邦主题。
《大护法》;国产动画电影;反乌托邦
近期一部片方自主分级成PG-13,宣称是献给成人的动画电影《大护法》正在热映中。该电影在电影评分网站豆瓣网上已有65139人评分,得到8.1分的好口碑,可谓是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中的良心之作。正如《大护法》制作方的标语是“献给时代高墙下的自由灵魂”一样,《大护法》更是一部献给产业高墙下的中国动画电影。面对国内不成熟的动画产业链,《大护法》勇于创造新题材和新世界观,避免陷入无谓的情感纠纷漩涡。 “反极权”和“反乌托邦”是这部国产动画电影最独特的标签。
“乌托邦”最早是由十六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摩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指代不存在的地方。后来乌托邦被用来指美好但无法企及的理想社会,“反乌托邦”则是一种压抑的社会状态,打破了乌托邦梦境的不切实际和空想未来。
一、意识形态下的批判
从经典的《v字仇杀队》到近年的《饥饿游戏》、《雪国列车》、《龙虾》等大热电影,乌托邦虽然从未存在过,但反乌托邦却一直受到创作者们的青睐。反乌托邦是国外电影题材的常客,但国内电影的反乌托邦题材却是很少,尤其是动画电影中。《大护法》无疑是一个极为亮眼而特殊的存在。
电影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批判有两种渊源。一是阿尔都塞在他划时代的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明确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种意识形态是花生人每晚都要接受的洗脑工程和固定集会时的群体心理暗示。国家机器则是被吉安统治作为暴力执法的花生人。执法者的武器——束棒斧头更是明显的法西斯时代产物,这个特殊符号向我们揭示了极权状态下国家机器的极端暴力。这种暴力统治是吉安对花生人主体身份的摧残。
二则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文化实践并不随身携带它的政治内涵,日日夜夜写在额头上面,相反,它的政治功能有赖于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其间文化被描述为一种结果,体现出它贯通连接其他实践的特定方式”,统治阶级/统治者只有在确立了文化霸权之后,才能成功地运行国家机器。建立假想社会和构建虚假关系是吉安真正掌控花生人的手段。花生人的群体关系由吉安掌控和断定。吉安赋予他们生存的理由和合法性。
二、非人化的世界观和话语权利
在同为反乌托邦的经典小说《1984》中,老大哥选择推行新话以规范和简化思想。到了《大护法》里的集权者——吉安则更加激进,他告诉花生人说话是一种从口腔开始溃烂至全身的疾病。当有人试图挑战时,他向花生人宣告“这疯婆子竟然敢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会害死所有人的,杀了她”。缄默的花生人像鲁迅笔下吃着人肉馒头,面无表情的麻木看客,一面打开窗户围观同伴被追捕;一面又紧闭口耳不与同伴交流。吉安剥夺了他们说话的权利,他们剥夺了自己思想的权利。这种非人化的世界观设定就是反乌托邦主题中常常出现的“异化”。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表现,其中第四重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当花生人被压迫时,他们没有团结反抗,反而是互相举报,残杀同类。
异化不仅存在于花生人与花生人之间,也存在于花生人和疱卯之间。一直坚信自己是在解剖牲畜的疱卯是在听到花生人开口说话后才第一次对“花生人是牲畜”这一观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此前,疱卯坚定不移地认为吉安大人说的就是真理。为了体现疱卯的狂热无理智,制作组为疱卯设计了行纳粹礼的动作,与之前的束棒斧头符号相呼应。
“说话”变成了标记人和非人的工具。就连一直散乱无组织的花生人也是在隐婆站出来振臂高呼后才开始觉醒反抗。他们依托话语翻身,开始相互交流联系。但他们也因为话语再次陷入地狱。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思想破坏语言,语言也能破坏思想”。觉醒的花生人因为重新掌握了话语,掌握了权利,一场新的权利分配开始,他们将枪口对准了“旧花生人”—— “现下花生人都要摘掉假眼睛,你不摘掉就死吧”。
三、极权下的个体
疱卯为了继承发扬祖先庖丁的大名,一直通过解剖花生人尸体练习刀法。当外来人大护法说花生人是人时,他立刻下意识反驳这不过都是牲畜。这刻画在潜意识中的反驳就是吉安的洗脑成果,“意识形态提供一份整体的想象性图景,其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的、或者称为‘宿命’的位置,并接受关于自己现处位置的合法性叙述”。在吉安宣称的花生人就是被宰杀的畜生的观点熏陶下,疱卯也将花生人定位于非人的位置。所以被分尸是花生人的宿命,而他的职责也是命运的安排。
这种想象性关系也对花生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电影前半段花生人相互揭发残杀,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接受了这种关系阐释——长了黑蘑菇的花生人的“宿命”就是死亡。在吉安的话语权驱动下,他们严格地按照吉安的指令活着。面对强大的权利,在服从与被清理之间,花生人选择了从“我”变成“我们”。从此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想象性图景一直没有被打破。即使后来吉安被夺走话语权,广场上的宣传画被砸毁,代替“极端之恶”的却是“平庸之恶”——花生人中的起义者开始抓捕枪毙不愿摘掉假眼睛的花生人。电影多着墨刻画吉安个人的极端之恶,只通过部分画面传达了对平庸之恶的不安。但这已经向观众抛出了警示:千千万万个的“平庸之恶”并不比一个人的“极端之恶”好。
四、小结:产业高墙下的动画电影
反极权和反乌托邦无疑是这部电影内容的最大卖点。大家争先恐后地讨论着其中的对话,解读背后的隐喻。但讨论的背后隐藏着导演掌控能力的不足。《大护法》导演不思凡对自己的评价是“没学过动画,更没学过电影”,“只是一腔热忱,这个梦才得以活到今天”。体现在电影中就是画面叙述问题十分严重,导演借用角色的口大段大段地说着 “这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所有人都活在被恐惧建设起的幻想里”的台词。但对电影而言,主题的揭示,人物心理的刻画,是通过画面语言的耳濡目染而非角色台词的强行灌溉。
这背后当然有着国产动画电影产业链不成熟的因素。《大护法》的启动资金20000多美元来源于众筹网站。但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国内一个动画作品制作成本约五万元一分钟,动画电影成本更高,一部3000万元投资,要破亿票房才能收回,这在目前的国产动画电影中寥寥无几”。
虽然《大护法》有诸多不足,但一部电影的灵魂是剧本。它“大声说话”“大胆做人”的口号稳稳地打在了新时期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每一位中国观众的心中,而《大护法》将有限的资源最大化地投入剧情之中无疑是国产动画电影的一个好兆头。期待未来的国产动画电影题材和内容能够更加丰富多元。
[1]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林清.中国动画电影[M].江苏: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