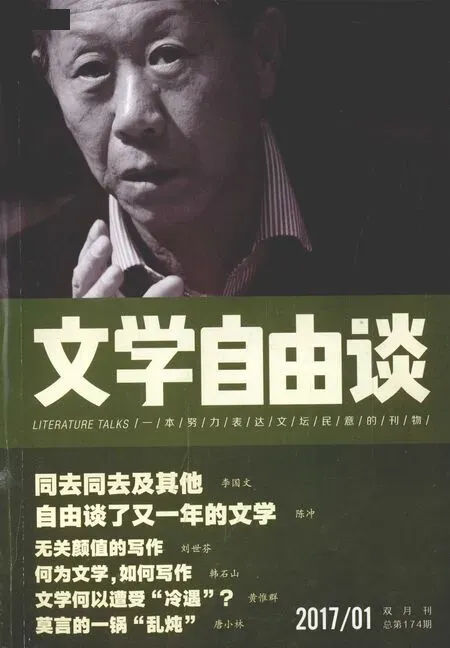边缘的力量
曾纪鑫
边缘的力量
曾纪鑫
如果没有 2003 年的举家南迁移民厦门,自然就没有书稿《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 11 个人》(九州出版社,2016 年8月第 1版)的形成与问世。
古时的厦门,是一个位于东南沿海、偏远蛮荒的岛屿。尽管三千年前就有原始居民在此生活,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始于唐朝的薛、陈两个家族迁居岛内。据最新考古资料表明,唐时厦门称嘉禾屿,又名嘉禾里。 宋、元沿袭此名,《鹭江志》载:“宋太平兴国时产嘉禾,一茎数穗,故名。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抗击倭寇加强海防,命江夏侯周德兴前来福建增设卫所,筑城十六座,构建沿海防御体系。 厦门城作为其中之一,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开始兴建,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建成,称“中左所”。 “厦门”之名,则因该岛位于九龙江口外侧,与内侧的海门岛相比,位居下方出海口,故称“下门”,后雅化为 “厦门”(谐音)。 明末清初,嘉禾屿、中左所、厦门三名并用,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 年),才以“厦门”之名统称全岛。
厦门东南,越过浩瀚的大海,是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诸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得厦门成为“八闽门户,海防重镇”,而且也是中国的大厦之门。
闽南人的生活区域,主要为福建南部的厦门、泉州、漳州三地,以及莆田市、三明大田县和龙岩的新罗区、漳平市等地的部分区域。 生活在这块中华版图边缘地带的闽南人,却从国中之国的河南等地迁徙而来,至今仍保留着古中原地带的部分语言、习俗、文化与信仰。
随着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生活区域又相应地扩展至台湾及东南亚地区。 据有关资料统计,台湾居民约百分之八十为闽南人后裔,海外祖籍闽南的华侨、华裔约两千万;闽南话属全国八大方言之一,海内外操闽南方言的人口将近六千万,被誉为海外华人第一方言母语。
闽南人虽属汉族,却如客家人一样,是汉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闽南民系。作为移民,千百年来,他们在与原住民闽越族的不断磨合,与西方海洋文化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闽南文化。
闽南民系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及三国时期的孙吴时代,如晋江、惠安一带的黄氏家族先祖,便于东汉末“弃官入闽隐居”,迁于惠安锦田。晋时的“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就有相当一部分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 隋唐时期,北方汉人大规模迁入闽南地区。 唐总章二年(669 年),闽粤交界处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矛盾激化,爆发了所谓的“蛮獠啸乱”,唐高宗派遣河南光州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三千六百人入闽平叛。 当地土著激烈反抗,陈政寡不敌众,“退保九龙山”。唐高宗又命陈政的两位兄弟陈敏、陈敷再率府兵三千驰援,其子陈元光一同随军南下。陈敏、陈敷在增援途中战死。 两军汇合后奋勇反击,这才打退“蛮獠”,进军云霄,建寨屯田。出征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靖边平叛战争进行得异常艰难而漫长。“蛮獠”实力强大,作战勇猛,唐军伤亡惨重。陈政苦战八年,终因“备极劳瘁”病逝军中。陈元光继承父职,“剿抚结合,恩威并重”,又经三年,这才消灭“蛮獠”主力,基本肃清动乱。此后,陈元光采取长期戍边政策,鼓励部属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在此落籍繁衍,推行中原制度文化,安抚蛮民,和集百越,以夏变夷。 永淳元年(682 年)八月,陈元光以《请建州县表》上疏朝廷,“其本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请求在泉州、潮州之间的漳江流域新建一州,以江命名,是为“漳州”。 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准奏,并任陈元光为首任漳州刺史,他也因此而被当地民众奉为“开漳圣王”。
唐朝末年,黄巢农民起义爆发,中原战乱频仍。河南光州固始县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乘机起兵,率五千兵士及其家属渡江南下,转战于江西、广东。 唐僖宗光启元年(885 年),王氏兄弟进入福建,由闽西攻取漳州,第二年占领泉州。 他们以漳州、泉州为根据地,休养兵马,安顿百姓,实力大增。 景福二年(893 年),王氏兄弟率军攻占福州,福建各地纷纷降服,王潮被唐昭宗任命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 王潮去世,王审知继任,唐亡后又被梁太祖封为闽王。因此之故,王审知被后世尊为“开闽王”。王氏兄弟虽统领福建,但其大本营却在闽南,这里是他们的发迹之地。此次中原移民大开发,对闽南民系的形成,对闽南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厦门同安区北辰山便有王审知衣冠冢,立有王审知塑像,建有王审知庙——广利庙(又名王公庙、忠惠尊王庙),每年阴历二月十二日,这里要举办广利庙会。
中原汉人与本地土著之间的争斗之激烈,对峙时间之长久,融合之艰难,仅从泉州辖下的南安县、惠安县、安溪县、同安县,漳州治下的长泰县、南靖县(元代设立时名南胜县)、平和县、诏安县、华安县等寄寓长治久安的县名,即可窥见一斑。
历经数百年的孕育,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终于在五代末年、宋代初期得以同步形成,逐渐发展,走向成熟与辉煌。
随着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的形成,闽南这块长期被人忽略的边缘“蛮荒之地”,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开始缓慢而执着地发挥它的作用与影响——除外向南洋、台湾等地播迁外,并朝内地与中原回向“发力”。
因时局的演变,这种回向“发力”于明清之际达到前所未有的峰值,闽南在中国历史所占据的地位日趋重要。 对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自飞黄(郑芝龙号)、大木(郑成功别名)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
从宋元时期全国的最大港口泉州港,到街市繁华、商贾云集的漳州月港,再到厦门港的兴起,闽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海外贸易,一直位居全国前列。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厦门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于 1843 年 11 月 2 日正式开埠。 闽南地区在整个世界发展大格局中不再偏远闭塞,闽南民系成为汉人中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闽南文化在闽越土著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外来西方文化的融汇中更加丰富深厚,传统性与现代性、一体化与多元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地域性与世界性兼备。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厦门作为五个经济特区之一,闽南文化作为联结海峡两岸同胞的桥梁与纽带,仍以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闽南,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处人文环境——一个肉眼无法洞见,只能心灵感知的文化“气场”。 在厦门工作、生活,一不留神,就“越界”进入了同属闽南区域的泉州与漳州。其实,就行政区划而言,古时的厦门,即泉州府同安县嘉禾里。 在我眼里,厦、漳、泉历来就是一个整体,闽南文化已将它们凝聚在一起,如今的厦、漳、泉同城化建设,又以有形的方式将三地紧密相连。
从湖北移居厦门时,我年届不惑,身上携带的主要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的因子。地域文化间的差异之大,唯有“当事人”的感受最为深刻。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说说容易,实则相当艰难。尽管我努力融入闽南文化之中,可十多年过去,仍不会说闽南话,连猜带蒙,也只听得懂一半。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与本地人的深入交流,除极个别的老阿婆外,厦门人都能讲一口略带“地瓜腔”的普通话;也不影响我欣赏闽南语歌曲,那种温温绵绵的有点嗲气的旋律,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婉转与妩媚。不过呢,作为全国八大方言之一的闽南话,不同地方也有差异。一次,厦门同安区莲花镇小坪道地村举办莲花褒歌比赛,歌曲质朴,演唱以情歌为主,但歌词却是半点也听不懂。 便问土生土长的本地同事,没想到他们也没听懂,说不上一句完整的歌词。
闽南人不事张扬,不温不火,有一种见惯不惊的从容、含蕴与内敛。 闽南人居于边缘,对中心、正统多有不服,骨子里透着一股反叛精神,有时便显得另类而胡闹,正是这一特点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而作为一个整体,闽南人之间的差异又是那么明显。比如泉州历史深厚,有点排外,而厦门则具有广纳百川的包容,但这包容又有一定的限度,如厦门人就听不得别人说半点厦门不好; 再如唱红全国乃至全球华人地区的闽南语歌曲 《爱拼才会赢》,这种拼搏,多为泉州特别是晋江、石狮一带的写照,厦门人则温温的,缓缓的,“小岛意识”浓厚,安于享受生活,缺少打拼精神。正如其他地区一样,闽南人的文化性格,既统一又充满了差异与悖论,如保守与开放、怠惰与进取、叛逆与忠诚、边缘与中心、单纯与复杂、排斥与包容等,同存并行。
闽南对历史的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这种强大的作用力,自然通过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主体——闽南人得以体现。
自古以来,闽南著名的历史人物众多,稍稍列举,开疆拓土者就有开漳王陈元光、开闽王王审知、开台第一人颜思齐,其他如民族英雄郑成功、陈化成,政治家李光地、曾公亮、吕惠卿,革命家杨衢云、林祖密,军事家俞大猷、施琅、蓝廷珍,思想家、学者、作家朱熹、李贽、黄道周、辜鸿铭、林语堂、许地山,科学家苏颂、卢嘉锡,教育家陈嘉庚、马约翰、林文庆,经济学家王亚南,海商蒲寿庚,语言学家卢戆章,艺术家蔡襄、张瑞图,名医吴夲、吴瑞甫、林巧稚,史学家赵汝适、何乔远、张燮、连横,等等等等,不胜枚举。
《历史的砝码》的创作,即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闽南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其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以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的描述,展现闽南人的群体特征与历史贡献,以及闽南文化的丰富内涵及深远影响。
限于篇幅,对闽南著名人物的选择,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产生过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当时,还得延续至今,仍被人们提及或发挥作用。如开漳王陈元光、开闽王王审知,其影响主要是地域性的,便不予纳入。 二是生长于闽南,属地地道道的闽南人。非本土出生者如朱熹、李叔同,以及籍贯闽南而非本地出生者如辜鸿铭、杨衢云等,便没有选入。 于是,本书选取的十一位影响中国历史的闽南人,他们是苏颂、俞大猷、李贽、洪承畴、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李光地、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以出生先后为序)。
这十一位闽南人物,我写得最早的是李贽,因其与我故乡有着较深的渊源。 他在湖北麻城隐居十多年,一生中的主要著述也在那儿完成,并与晚明文学流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亦师亦友,过从甚密。 刚来厦门不久,我便前往泉州探访李贽故居,写下《另类思想家李贽》一文。 不久又写了郑成功、陈嘉庚、林语堂,然后就搁下了。直到 2012 年,才重续前缘,断续写下其他七人,边写边在相关报刊发表,终于了却一桩心愿。
每一人物,所写篇幅虽只一二万字,但所花工夫甚多。首先是资料的占有,通过不同的渠道与方式,尽可能地将所写对象的著述、评论、传记等相关资料收入囊中;然后是阅读与消化。苏颂、李贽、黄道周、李光地、林语堂可谓著作等身,除林语堂的作品外,其余皆为文言文,仅全部通读一遍,就得花费大量时间;俞大猷、洪承畴、郑成功、施琅、陈化成、陈嘉庚等人的著述倒不是很多,以奏章、书札等为主,但研究资料不计其数。 后人反复不断的分析解读,有着宝贵的借鉴参考价值,半点也不能忽略。资料匮乏自然无法研究,但多了又不免芜杂歧义,有的甚至相互矛盾。 因此,利用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加以考订甄别,对于必要的引文,尽量不转引,而以原著为准,避免以讹传讹。与此同时,每写一人,都得进行一番田野调查,探寻相关名胜遗迹,还原现场,澄清事实,增强感悟。 实在无法亲临,也要通过一定渠道解疑除惑。 比如创作《大明孤臣黄道周》时,黄道周在南京的行刑地址,便有西华门与东华门两说。 其实,只要弄清哪一处古迹离明孝陵近就是。 一时难以前往,查地图也不甚明了,便打电话询问南京朋友戴珩兄。他也不太清楚,第二天请教当地专家后,给我发来短信:“明孝陵在东面,还是东华门离明孝陵近些。 ”如此这般,我就可以在文章中“放心大胆”地写明黄道周的行刑地点为南京东华门了。
来厦门之前,我与闽南无甚渊源瓜葛,也就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冷静、客观、公正为旨归,不以一面之词为准,不受某种观点左右,不掺杂个人意气,不拔高、不偏袒、不护短。 既重视叙写对象的本人著作及正面评说,也参照敌对阵营的不同论述与看法,而日本、朝鲜、荷兰、英国等外人的资料则尤显珍贵。在综合比较、合乎情理的基础上加以阐述,力争超越偏见与陈说,还原事实与真相。
当然,这并不等于我没有自己的认识、观点与好恶。个体有生死,力量有强弱,时局有迁移,朝代有更替,民族有兴衰,但天地之间,自有一股千年不变的浩然正气充塞其间,彪炳日月。 苏颂、俞大猷、李贽、黄道周、郑成功、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等人,是我内心敬佩、笔底赞颂的对象;而洪承畴、施琅、李光地三人,即使在闽南人眼里,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
于李光地,我通过各种资料加以分析,基本予以正面评说。除显赫的政绩外,他不仅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集大成者,还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著述《榕村语录·榕村续语录》,该书是他与门人学子探讨学问、论述时事的记录,也是研究清初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全书明白晓畅,谈学问,解惑释疑,深入浅出;叙事实,生动亲切,质朴动人;记游历,风景风情,娓娓道来,宛在目前……不仅口语化,且不避闽南方言,有一种“原生态”的味道,读来饶有趣味。 作为文言读本,却有我早年阅读冯梦龙《三言》、凌濛初《二拍》之类古代白话小说的愉悦与快感。于是便想,他日得闲,还得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地好生阅读。
黄道周、陈嘉庚堪称古今完人,而洪承畴则走向了另一极端——属大节有亏之人,说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汉奸,一点也不为过。无论怎样洗刷,洪承畴于汉民族的污点实难洗清;不论怎么褒扬,“千古贰臣”这一铁的事实无法篡改!
就个人情感而言,我不喜欢施琅甚于洪承畴,但他无疑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闽南地区影响中国的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本想撇开不写,却又无法绕开。施琅是一个突破底线的人物,洪承畴叛一而终,施琅则一叛上司、同乡、友人郑成功,两次背叛南明。 施琅平定台湾的历史功绩是一回事,而双重背叛的个人品性是另一码事,二者须区别对待。
遗憾的是,我叙写的十一个闽南人物全是男性。其实,闽南历史上也产生过林巧稚等著名的优秀女性。 作为一个整体,她们甘居幕后,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美丽与青春。 传统文化的承载,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程朱理学对她们束缚甚多,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