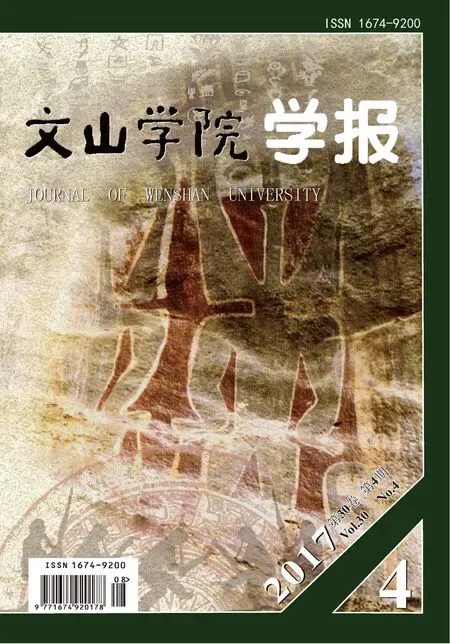主粮结构的优化:当代生态建设的又一关键环节
杨庭硕,耿中耀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
主粮结构的优化:当代生态建设的又一关键环节
杨庭硕,耿中耀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
农业生产是人类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制衡运行的纽带,优化“主粮”结构直接关系到人类与生态系统和谐程度的提升。在时下的生态建设中,社会各界总是习惯性地聚焦于凭借工程技术手段,或创立和扩大自然保护区去推动生态恢复。这样的努力当然无可厚非,但却远远不够。原因在于,“主粮”结构不合理对生态系统构成的冲击和损害,更其直接和影响深远。在生态建设中忽视“主粮”结构优化能够发挥的关键作用,显然是一种建设思路上的失误和偏颇。这样的思路若不及时调整,势必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灾难。
“主粮”结构;生态建设;关键环节
一、“主粮”结构的内涵
一提到“主粮”结构,习惯性的看法总是将其内涵锁定在禾本科作物内。但这是一种十足的偏见。综观古今中外的“主粮”物种构成,除了禾本科作物外,往往还包括众多科属的粮食作物,如豆科、藜科、苋科、旋花科、唇形花科等等。此外,很多非禾本科粮食作物,在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中都充当过“主粮”,有的还一直沿用到今天。比如,属于豆科的扁豆,仍然在土耳其充当“主粮”;属于棕榈科的桄榔木,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群岛的十几个国家中也依然充当“主粮”;芭蕉科的芭蕉籽实,在中美洲和几内亚湾沿岸各国民族中,至今还将其作为“主粮”种植。
因此,仅仅把“主粮”锁定在禾本科作物中,不仅无法满足人类生活的多样化需求,还会在无意中导致相关生态系统遭受损害。生态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多一种“主粮”作物,就会在该作物规模种植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庞大的食物链,也就能够支撑起更多生物物种的延续,从而能够在不经意中发挥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能。此外,同一物种不同品种的“主粮”并行种植,也能发挥同样的功效,同时还能起到防治病虫害和防灾减灾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的“主粮”结构所涉及到的生物物种越丰富越好,同一物种的不同品种和地方栽培品种越丰富越好。
“主粮”结构的定型,涉及到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一是自然与生态结构,二是与此相关的民族文化,三是农业生产的历史演化过程。因而,评估“主粮”结构的优劣,显然需要兼顾到上述三大要素的实情和发展趋势,才能做到在确保全国人民基本生活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也能为当下的生态建设发挥作用。
众所周知,任何意义上的“主粮”生产,都必须与所处地区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相适应。如果适应水平较高,那么相关民族的“主粮”生产,不但成本投入低,成效大,而且还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病虫害的防治等发挥重大作用。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类型丰富而多样,如果“主粮”产品的物种构成过于单一,就会对相关生态系统构成重大的压力;若“主粮”生产不能与当地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相适应,就会直接干扰到该区域生态建设的成效,甚至还可能抵消已经取得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主粮”结构的物种构成越丰富,其生态维护价值就越大。
我国民族构成复杂多样,民族文化多样性极为复杂。因而,我国“主粮”种植的农耕体制,以及生态管护体制,也会表现得互有区别。这样的区别,又会导致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益的迥异。由此而产出的“主粮”产品,即使是同一农作物物种,其产品都会表现得千姿百态。
在这些多样化的传统农产品中,必然包含着众多名特优农林牧精品。这不仅对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和管护,可以发挥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丰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生物物种基因多样化,也会具有重要价值。
在历史上,我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还是世界上“农业文化遗产”拥有量最多的国度之一。由于这些“农业文化遗产”,都是定型于工业文明之前,因而它们本身就具有生态维护的禀赋。当下,发掘利用好这样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为“主粮”结构的优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还能支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具有提供生态食品,确保粮食安全的功效。就这一意义上说,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和创新利用,也是当下从事生态建设必须加以有效利用的手段与方法。
“主粮”结构的定型是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演化的产物。这样的历史过程,又必然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区和特定技术水平,相互制衡和协同演化的过程,而且还与不同时代的国内外形势直接关联。以至于由此而形成并定型延续下来的“主粮”结构,无不打上了时代和地域的烙印。这对于当前中国的生态建设来说,所表现出的作用必然会优劣参半,其间的精华,必须发扬光大;其间的偏颇和失当,也需要及时加以消除。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满足当前中国生态建设的需要。
立足于上述,若评估现行“主粮”结构的优劣,显然得取准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建设的具体要求,去具体分析、论证两者之间的契合程度,以及能否及时消除和化解历史留下的不利因素,并在这一过程中放大和提升有利因素。
二、“主粮”结构的评估
我国当下的“主粮”结构,仅重点关注稻米、小麦和玉米三种。近年来,我国农业部才致力于推动马铃薯的“主粮”化。而大豆在我国民众的实际生活中,本身就具有“主粮”属性,在国家规划的“主粮”种植中,甚至没有把大豆列为粮食作物。还有一些作物,在历史上曾经是国家法定的“主粮”,但在当代却被归为“杂粮”,根本不纳入国家管理的框架之内。如藏族所种植的青稞,蒙古族培养的糜子和沙米。这只能理解为,时下我国的“主粮”结构严重缺乏包容性,不但物种构成较为单一,而且在大力推广种植这些“主粮”作物后,还会在无意中损害我国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水平。
随着杂交稻的推广,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培养成功的数以千计的水稻品种,其种植规模和利用范围都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很多名特优产品也随之销声匿迹。正如朱有勇所指出的,随着品种的锐减,水稻的病虫害日趋猖獗,进而由此还会引发农药的滥用,其生态受损所付出的代价,比杂交水稻种植所增加的产量还要大。[1]这同样是“主粮”结构不合理而酿成的悲剧。
此外,另一个带有国际意义的重大生态问题还需要高度关注。时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主粮”结构,同样也极为单一,仅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和马铃薯等有限几个物种。世界上最大的四家粮食跨国公司,均是按这样的模式去主导了国际“主粮”贸易。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鉴于中国大豆消费量巨大,才致力于在该国扩大转基因大豆的种植,产品专门销往中国。其后,又将转基因大豆的专利转让给巴西,在巴西种植后向中国倾销。结果,中国和巴西的生态结构都因此而引发了重大的损失。中国的传统大豆品种,也由此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这一事件最值得注意之处还在于,如果我国的“主粮”结构依然单一,国际粮食贸易就会轻而易举地左右中国的粮食市场。如此一来,不仅中国的经济会遭受严重的冲击,生态结构也会因此而蒙受难以预测的损失。但如果“主粮”构成尽可能多样化,那么国际粮食贸易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中国的生态损害都可以降到最低。同时,中国大量的非转基因粮食,在国际粮食贸易中,还会因其符合“生态食品”的标准而获取巨额报偿。时至今日,欧洲各国依然抵制转基因农产品,在这种背景下强化我国传统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本身就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今后中国“主粮”结构的优化,看来需要更多地向欧洲各国学习,才能摆脱美国粮食垄断以及对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造成的双重压力。
除了物种品种构成外,“主粮”作物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也是评估“主粮”结构是否合理的必备内涵。我们必须牢记,每一种粮食作物,其生物属性都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在不合适的生态背景下种植特定的粮食作物,不仅生产成本高、产量低,而且还会威胁到生态的安全。我国是一个山地环境构成比例极大的国度,在山区坡面推广种植玉米,不仅会酿成严重的林粮争地的尖锐矛盾,还会引发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等严重的自然灾害。[2]我国乌蒙山区之所以会成为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即是历史上无原则地大面积推广玉米种植酿下的生态隐患。但时下乌蒙山区的各族民众,依然大面积种植玉米作牲畜饲料。这样的经营范式纯属多此一举,在“主粮”结构调整优化中,对这种做法也必须高度关注,尽可能消除其负作用。事实上,乌蒙山区各族民众,根本不需要大费周折地种植玉米作饲料,因为当地本来就具有众多的优质牧草。这其间仅是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而如今要处理这样的问题,难度不大,但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因而在今后的“主粮”结构评估指标设计中,必须把这样的问题包容在内。
在我国,水稻最佳的种植范围极为有限,但时下的水稻种植区域,不仅推广到东北,还推广到内蒙古的阿拉善腹地,甚至有研究者还致力于将水稻推广至雅鲁藏布江河谷。这样做的结果,水稻的总产量虽然可以提高,但由此而引发的生态问题,同样会抵消其生态效益,还会诱发无穷的生态后患。
有鉴于此,“主粮”结构的优化,不仅需要体现为提高物种和品种构成的多样化,还必须针对我国的生态结构特点,严格控制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和产量比例。以此确保不同的“主粮”,都能够种植到它最理想的生态环境之中。而不能凭借习惯或者主观的判断,去追求“主粮”产品的短期市场价值,更不应当把心目中的“主粮”,推广到它不适宜种植的生态系统之中,而最终在无意中制造生态灾变。因此,今后制定“主粮”结构优化的指标时,必须将“主粮”物种和品种的最佳适应范围、最佳种植背景纳入其中;也需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不适宜种植的地带明令禁止种植。时下,没有将这一问题纳入评估指标,本身就是一种失误,应当及时启动新的评估办法,对此前的失误加以匡正,并以此推动我国“主粮”种植的全国性协调。
生产“主粮”作物的农耕体制对生态建设而言,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一物种,甚至是同一个品种的粮食作物,在完全相同的生态背景下种植,由于耕作体制不同,其产量和质量也完全不同,其生态影响更会各不相同,有的对生态建设极为有利,有的则会带来始料未及的生态负效应。因而,“主粮”结构的优化,还必须关注耕作体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早就明确指出,西方的集约农业耕作体制,主要是针对温带草原建构起来的合理制度,这样的制度并不适应于其他的生态系统,也不值得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去抄袭和模仿。[3]时下,美国正在大力推广“免耕法”,而我国的粮食种植,却在致力于推广机械化操作和大规模集约经营,其间的走向恰好相反。而值得反省的教训又非止一端。
在历史上,沙米曾是我国内陆干旱地带的“主粮”作物。这种作物可以在半流动山丘上规模性种植,产出的沙米价值极高,其杆蒿还是牲畜的饲料。更具价值的是,这种作物还能防风固沙,极具治理草地退化和土地沙化的生态功效。唐代河西四郡的税赋粮种,就包含有沙米在内,[4]并被其后的各个王朝沿用。清代康熙皇帝御驾亲征讨伐葛尔丹时,漠南蒙古各部提供的军粮,主要就包括沙米。[5]近年来,环保部门鉴于沙米具有防风固沙的生态效益,并为此投入了巨资,耗费了多年的精力,希望推广沙米的种植,以便收到治理土地沙化灾变的成效。但研究的取向和采用的种植体制,却抄袭自禾本科粮食的种植办法。结果,沙米的萌发率和成活率极低,根本无法达到生态治理的目标。而我国蒙古族和其他好几个游牧民族,使用他们种植沙米的传统农耕体制,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大面积种活沙米。这应当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其失误仅仅是来自对农耕体制的误用,而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因而其失败,是从研究起步时就种下的祸根。如果仿效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业遗产,将其发扬光大,或者设计同等功效的耕作体制,那么不仅沙米可以升格为“主粮”,沙地灾变的治理,也可以步入一个新的台阶。
“架田”是我国南方利用固定水域实施农业耕作的“农业文化遗产”。类似的农耕体制,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中目前还在使用。[6]但中国自宋代以后,各朝政府为了行政的需要,明令禁止这种农耕体制的实施。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下中国水资源的维护,水体质量的保障,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而架田种植在这方面的功效,至今没有找到替代的办法。我国大型水库修建的数量日趋增多,相关部门又把这些水库的水面租赁给企业或个人,供作网箱养鱼之用,并因此酿成水体的严重污染和水资源的无效蒸发。但如果重新启用“架田”种植,不仅可以维护我国的耕地红线,还能坐收水环境优化的成效。当前没有将这样的农耕体制,纳入“主粮”结构的评估框架,同样是一种无意中犯下的失误。同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我国沅江流域的各族乡民,长期执行“林粮兼作”体制,“主粮”种植不会干扰到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维护。我国岭南地区的各民族,在历史上早就拥有一整套在森林环境中种植粮食作物的成熟农耕体制,比如在森林中配种木本粮食作物,如桄榔木、木薯等;还在林下种植天蓝星科的芋属作物等。这样的农耕体制,不但不会引发林粮争地的矛盾,还可以做到“主粮”种植与森林维护的和谐兼容。我国凉山地区的彝族,利用牧场的间隙配种圆根和燕麦,也是能够兼顾到“主粮”种植和生态维护的农耕体制。
为此,评估“主粮”结构的优劣,必须将农耕体制纳入其中。但凡农耕体制与种植的粮种相互适应,又能兼顾到所利用的生态系统,就应当视为“主粮”结构优良。反之,就应当视为“主粮”结构的不合理。有了这样的评估指标,才能推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建设的两全其美。然而,“主粮”结构的优化,由于涉及到历史的积淀和生态的适应等一系列问题。以至于要完成这样的使命,必然要耗费较大的投资,需要经历相对漫长的历史岁月。为此,“主粮”结构的优化,还必须兼顾到“主粮”生产的当代创新空间这一棘手问题。
就总而论,我国确实是“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度。但这些遗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因各式各样的社会原因而失传,即令能够活态传承至今,其生产规模也无法达到优化“主粮”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可是出于我国生态建设的考虑,只要这些传统的“农业文化遗产”能够为我国当前生态建设所需要,都具有发掘和创新利用的必要;只要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创新,就有必要纳入“主粮”规划当中去组织推广和发展。
小米本来是远古华夏居民的“主粮”。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仅仅是因为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步向南、向东迁徙,原来的小米主产区逐步被边缘化,其“主粮”地位也就随之而丧失。但这种作物非常适应于在干旱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中大面积推广种植,并都能对这样的生态空间发挥生态维护的效能,其潜在的空间又几乎可以覆盖我国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因而,发掘创新利用小米,其生态价值极大。据文献记载,我国汉代推行的“代田法”,就是专为这种作物而设计。[7]“代田法”的技术操作,只需创新设计农业机械化的设备,完全可以实施机械化操作,只要能够做到这一步,将小米一类的作物确立为“主粮”,完全可以实现。
我国历史上的某些“主粮”作物,特别是块根类,如桄榔木那样难以加工和保鲜的粮食作物对我国异质性较大的生态背景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对喀斯特山区、水土流失地区和石漠化灾变区等特殊的生态环境维护而言,几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历史上却受运输条件、加工条件和国家行政管理条件的限制,而不能成为国家“主粮”。当下的运输、保鲜和加工基本不成问题,而耕作体制的现代化,却又成了亟待解决的创新领域。鉴于当代农业机械主要是针对禾本科粮食作物而设计,要创新利用块根类的粮食作物,确实存在着诸多技术和科研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并非不能改变,而是此前的研究取向没有关注到这一紧迫需要而已,只要科研取向做出有效的调整,这些粮食作物的机械化生产同样可以做到。
举例说,我国凉山地区的彝族,是采用“粪种法”种植圆根和马铃薯,其单位面积产量并不比高产的杂交水稻低。[8]但“粪种法”却要受到牲畜拥有量的限制,否则就难以提供足够的脱水厩肥。实施这一耕作体制的核心技术原理,仅仅是为了规避地温偏低的自然缺环。在当代技术和材料装备的基础上,要规避这样的自然缺环,其实并不存在问题,只需要脱离地表,建构悬空的高标准耕地,也能收到同样的生态适应实效。而且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完全可以抵消较高的成本投入。作出这样的创新应对,完全可以使我国此前无法实行农耕的高海拔地带,也能拥有稳定的耕地。
从创新的视角去规划我国的“主粮”结构,就可以使很多历史上失传或者濒危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并兼收生态维护的成效。为此,对传统的农业遗产全面分析和应对其创新空间的大小,也应当纳入“主粮”结构优化的评估框架内去评估考量,才有助于“主粮”结构的优化,也才能够在生态建设中发挥其关键性的作用。
三、亟待应对的几大挑战
当前我国按照惯例运行的“主粮”结构,主要是顾及到行政管理的方便和考虑到粮食安全的维护。但这种做法,却与我国长期粮食生产的实情相左。查阅清代的地方典籍就不难发现,在国家规定的“主粮”框架内,当时的各府州县,还包括当时所称的“蕃部”,无一不拥有琳琅满目的“主粮”作物。当时朝廷虽明文规定有税收“主粮”粮种,但同时也极大地宽容,甚至是支持适合地方的粮食作物种植。这些粮种,也始终占据着当地的“主粮”消费地位。这显然是一种既关系到粮食安全,又兼顾到生态维护的“主粮”结构优化。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仅仅将稻米、小麦和玉米确立为“主粮”。近年来,国家才将马铃薯作为“主粮”作物去加以规划和种植。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开头,但显然还远远不够。为了兼顾到生态建设的需要,“主粮”的物种构成还需要进一步多样化。原则上,在二十世纪初,曾经处于“主粮”地位的作物,都理应纳入“主粮”结构去加以发展和稳定种植。如此一来,就可以做到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同时收到生态维护的实效。
正因为时下我国的“主粮”结构过度单一化,其结果导致了粮食作物的压库,生产能力的悬置,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盈利空间越来越小。而市场紧缺的粮种,特别是那些名特优粮食产品却供不应求,形成了市场供给的“短板”。这样的现实都一再警示我们,“主粮”结构的物种构成和品种构成亟待优化。而阻碍这一优化的关键制约因素,不在于生态环境,也不在于技术条件,而在于观念上抱残守缺。
当前,我国生态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我国政府先后提出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和“退耕还湖”的正确决策,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暴露出了一些新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就有很多粮食作物的生产,不仅不会与还林、还湖、还草等措施相互冲突,反而还具有提高生态建设成效的积极作用。
桄榔木、木薯,还有芋属块根粮食作物,都可以在“还林”后的森林中正常种植。历史上作“主粮”用过的葛根、山药、版脚薯等,不仅可以与森林相互兼容,还可以作为“还林”的先锋作物去加以利用,对提高“还林”的成效具有重要作用。沙米和粟类作物,完全可以在“退耕还草”后实施规模种植。这些作物不仅与当地的草原能够相互兼容,还能与当地各族乡民从事的畜牧业相合拍,从而更有利于当地受损草原生态系统的快速恢复。实施“架田”种植也与“退耕还湖”不相矛盾,不但能够净化水质,防治水污染,在干旱地区还能抑制水资源的无效蒸发。
就这个意义上说,从事生态建设就不一定单靠行政和工程技术手段去完成,创新利用“重要传统农业文化遗产”,推动“主粮”结构的优化,反而可以降低生态建设成本,提高建设的实效。应该做到,在我国的国土范围内,只要粮食作物的最佳适应面积超过一万平方公里,就有必要纳入“主粮”结构中去加以规划种植,以期稳定其用地面积和产量。这样去优化“主粮”结构,才能确保我国当前的生态建设,既能够得到高效的利用,又能得到较好的维护,生态建设也就能降低成本,提高成效。
为了确保“主粮”结构的优化能兼顾到生态建设的需要,其间必然存在着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问题。而当前我国对“主粮”作物的研究,却一直按社会习惯去加以规划,主要是对有限的几种粮食作物展开深入研究,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主粮”作物,以及相关的“农业文化遗产”和耕作体制,却长期处于科学研究的闲置状况。相关的科学研究,根本没有将这些内容纳入科研范畴,即令有零星的涉及,也需要亟待深入和完善。而这已经成了我国“主粮”结构优化的关键制约因素,若不调整这样的科研取向,“主粮”结构的优化同样会寸步难行。
就终极意义上说,任何科研活动,都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动。以至于具体的农业科研活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受到传统“主粮”观念的规约和左右,从而导致研究取向和研究思路的偏颇。比如,西汉晚期推行的“代田法”,不管是农业史专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会做出充分的肯定,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先进的发明。但受到当代“主粮”结构的习惯性干扰后,对此展开的科学研究都很少关注到,“代田法”对我国西北干旱地带的疏树草地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适应能力,对规模化的农事耕作也不缺乏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发扬光大这样的传统农业遗产,本来不该成为问题,但却因为受到习惯性的思维干扰,导致相应的科学研究长期缺位。同样,对我国南部山区的农业研究,也会在无意中出现了研究取向上的偏颇。研究者总是过分地关注农业机械的小型化,以及拆装搬运的便利化,而从不考虑另建适合山区作物种植的机耕体制,更不考虑换种能够与特殊山区环境相适应的作物,并创新利用与此相关的传统耕作体制。这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举例说,在我国西南严重石漠化的喀斯特山区,在历史上当地各民族是通过农林牧副的复合经营,凭借“免耕法”去种植特种“主粮”,如桄榔木、葛藤等等。其后,仅仅是因为不能与国家赋税制度相接轨,这份农业遗产才在无意中被窒息。时下的研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反而是大动干戈去规划设计超小型的农业器具,却不会考虑创新利用传统的“免耕法”。而近年来美国农业部门正在大力推广的“免耕法”,正与我国西部山区的“免耕法”具有内在的同质性。
事实上,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山区,强行推广禾本科粮食作物种植不是办不到,而是会引发诸多的生态问题。但如果改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粮食作物,如上文提及的桄榔木、葛根、芋头、木薯,却可以收到生态建设的实效。而改种这样的粮食作物,并确立为“主粮”去加以规模性发展,那么以禾本科粮食作物为对象而设计的农业机械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但如果改用索道运输,情况则会大不一样。因为这些适合于山区发展的粮食作物,通常都不需要全面翻地,也不需要频繁地除虫、施肥和除草,基本上都是实行“半野化”种植,为此付出的主要劳力投入,都集中在收割环节。而就收割环节而言,山区采用索道运输,可以做到投资少,操作便利,而且对生态环境的冲击还可以降到最低限度。因而,要优化我国的“主粮”结构,确实需要作出科学研究取向的调整。但这样的调整,必然要受到现存“主粮”结构造成的干扰,两者之间互为因果,相互牵制。最终会使得,没有观念上的更新,就不会有科学研究取向的调整,没有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也无法支撑“主粮”结构的优化。这反倒成了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难题,如果不及时加以化解,相关制约因素将难以排除。
“主粮”结构的定型,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会制约其后的历史发展。其中,消费习惯的调整和与时俱进就不容忽视。现有的“主粮”结构均习惯于将小麦、稻米和玉米以外的粮食作物,不加区别地视为“杂粮”,甚而加以贬低。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生活的日趋富裕,三大“主粮”的人均消费水平,特别是城市人口所表现出来的消费水平,比之于改革开放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主粮”消费在食物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降到不足四分之一的水平。[9]与此同时,对所谓“杂粮”的需求,却出现了难以置信的反弹。而国家的粮食管理,却依然在不计成本地大规模储粮避荒,储集的粮食依然定位于“三大主粮”和大豆,由此而耗费了大量的粮食保管支出。这不仅是经济上的不合理,也与生态建设的实际需要背道而驰。此外,还会进一步诱导人们消费心理的变态,富裕起来的人们不再看中中国土产的“主粮”,而是更看中进口的粮食产品。如此一来,势必加剧中国生态建设的难度,还会增加生态安全的风险。在“主粮”结构优化的目标下,主动消费中国产出的琳琅满目的“杂粮”,特别是那些与生态环境直接关联的“杂粮”,本身就为中国的生态建设做贡献。上文提及的沙米、桄榔木、葛藤等,都可以体现这一客观价值。
由此看来,“主粮”结构的优化,不仅要对付科研问题、技术问题、生态问题,还得对付消费心态和社会价值观所带来的习惯性障碍。相关的决策应责无旁贷地发挥关键作用,引导我国民众树立理性消费多物种粮食的正确观念。中国民众在粮食消费中,必须做到需要为中国的生态建设承担,而且很容易承担起的责任来。
上述几个必须应对的挑战,若作出有效地应对,我国“主粮”结构的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对策,才能一并落到实处。理由全在于,“主粮”结构的优化,不是单纯的农业问题,而是与生态建设休戚相关的关键问题,只有将“主粮”结构的优化与生态建设捆绑起来,协调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建设才能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互为支持,和谐共荣。
四、结论与讨论
长期以来的惯例,我们都是将“主粮”结构与生态建设,作为相互独立的问题去对待,而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至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主粮”结构的调整与生态建设总是难以相互兼容,甚至还会出现针锋相对的矛盾和摩擦。尽管这是历史和习惯延伸的结果,但对生态建设极为不利。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农业是广义上的大农业,理应包括农、林、牧、副、渔,以及狩猎采集在内的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这里受篇幅所限,仅就其关键性和典型性,对“主粮”结构的优化展开探讨。以便让社会各界注意到,农业生产并不仅仅是一个确保生存的基础产业,而应该是生态建设中必须加以兼顾和创新利用的关键环节。“主粮”结构的优化,不仅对农业本身至关重要,对生态建设也同样至关重要。“主粮”结构得以优化,不仅可以坐收生态建设的实效,而且可以支持生态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行,及建设成效的提升;“主粮”结构不合理,不仅会给农业本身造成损害,同时还可能压低,甚至抵消生态建设的实效。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本身就应该成为生态建设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决不允许农业生产部门和生态建设部门各自为阵,甚至相互摩擦和对立。
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面对的困难却非止一端。思想观念的转型,基础装备的完善,科研取向的调整,一项也不容疏忽。原因在于,“主粮”机构的优化,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改变的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技术问题,或者是政策调整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相互配合,协同推进,才能收到成效。因而,社会各界能够注意到“主粮”结构优化与生态建设的内在关联性,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突破。这足以表明,符合时代的价值观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和认同。接下来,虽然还会有诸多的困难,但只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那么历史积淀下来的各种障碍因素,具体创新利用的科学探讨,科学研究取向的调整和具体技术的完善,是可以次第落实的。
[1]朱有勇.利用水稻品种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2003(5):521-527.
[2]张振兴.论清代在西南山区推广玉米种植的生态后果[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3):40-47.
[3][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2.
[5]《清高宗实录》卷14[Z].雍正十三年.
[6]伍磊,吴合显.漂浮农业在当今中国的实用价值初探[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3):8-13.
[7]邵侃.“代田法”新解——汉族农业遗产的个案研究[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2):9-15.
[8]杨庭硕,等.彝族文化对高寒山区生态系统的适应——四川省盐源县羊圈村彝族生计方式的个案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7-33.
[9]汪希成,吴昊.我国粮食供求结构新变化与改革方向[J].社会科学研究,2016(4):130-135.
(责任编辑 王光斌 )
Optimization of Staple Crop Structure: Another Key Link for Moder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YANG Tingshuo, GENG Zhongyao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a connection link for balancing oper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s. Optimization of staple crop structure is closely concerned with the promotion in harmonious degre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al ecological systems. During moder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eople are mostly used to relying and focusing on engineering techniques, or establish and expand natural conservation areas to drive the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Such endeavor is originally undisputable but far from enough. If the staple crop structure is not reasonable, it will bring more direc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and damage for ecological structure. Therefore, it is a mistake and bias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nking without paying high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staple crop structure, which needs promptl adjust to avoid suffering great losses and disasters.
staple crop structur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key link
S181
A
1674-9200(2017)04-0001-07
2017-06-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辑、研究与利用”(16ZDA157)阶段性研究成果。
杨庭硕,男,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终身教授,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耿中耀,男,贵州威宁人,吉首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