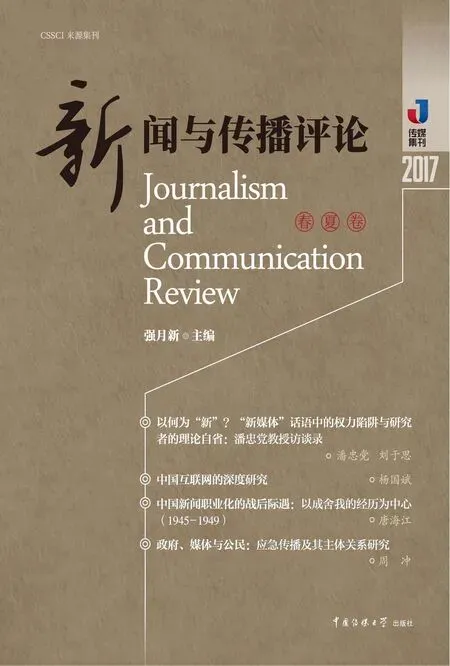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
◎ 杨国斌
特稿
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
◎ 杨国斌*
本文通过对《争锋互联网》一书的讨论,探讨中国互联网和数码文化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深度互联网研究”的可能性。“深度互联网研究”强调人的经验、历史性,以及对理论与描述、深描与浅描的平衡。文章讨论了人类学者针对“深描”而提出的“浅描”概念,介绍了近年来美国文学批评学者提出的“描述的转向”,指出“互联网深度研究”与这些新的理论动向的契合之处。
互联网,深度研究,社会理论,深描,浅描,细读,浅读
中国互联网的研究可谓日新月异,海内外文献十分丰富。本文从笔者在2015年编辑出版的英文论文集《争锋中国互联网》(China’sContestedInternet)的内容谈起,探讨如何使中国互联网(包括手机等新媒体)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笔者将这种努力称作“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Yang,2015)。
“深度研究”这个提法,借用了一本人类学著作的书名,即《深度中国》(DeepChina)(Kleinman et al,2011)。该书的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假如说政府政策、社会机构和市场活动构成变动中的中国的表层,那么,亿万中国人民的感知的、情感的和道德的经验,则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深层中国。”(Kleinman et al,2011:3) 换句话说,《深度中国》一书的宗旨,是关注普通人的状况。该书的八个章节,分别研究了卖血、自杀、抑郁症、性的革命、对社区和家园的记忆、艾滋感染者和心理疾病患者受到的歧视等问题。该书启发我们去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诸多层面的人的经验与社会实践,以及人对自我的塑造和再造。具体到互联网和新媒体来说,它启发我们如何深入研究与互联网等新媒体相关的普通人的经验与社会实践。
《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中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深度研究”的精神。本文首先介绍此书的内容。之后,笔者将分三个方面,对“互联网深度研究”做初步探讨。这三个方面是:(1)人的经验;(2)历史深度;(3)“深”与“浅”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现象描述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下面先从《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的内容说起。为便于讨论,笔者把全书的目录翻译成中文作为附录列于参考书目后。
一、“前微博”与“微博”:互联网的两个时代?
1995年,在中国接入全球互联网仅一年后,张树新创办了首家民用互联网服务公司“瀛海威”,并以巨大的街头海报宣告其诞生:“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前1500米!”这幅海报下,一条1500米的短路通向她的办公室,但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历程”却要长得多。1995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中国近14亿人口中已有半数接入互联网,使用互联网。这一进程也改变了互联网的意义,使互联网在中国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在互联网研究中充分认识互联网的中国特色,是重要的课题,也是“互联网深度研究”的重要内容。
使互联网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方法之一,是把时间和变化纳入分析的框架,也就是说需要使互联网研究有历史纵深感。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可以通过历史分期的策略,将连绵不断的历史分解为较小的时间段进行分析。通过划分历史时期,研究者可以识别普遍性和特殊性,凸显每个时间段与其前后时段的延续和变化。
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分期,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也不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但是《争锋中国互联网》所收的十篇文章,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力图传达一种历史感。前五章主要关注的是前微博时代的议题或事件,后五章关注的是微博。因此,仅就该书的内容来看,可以把中国互联网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前微博时代和后微博时代。这样划分不是因为真有泾渭分明的这么两个时代,也不是说微博的出现在互联网的历史上有多么重要的划时代意义。从早期的BBS、个人网页、QQ聊天、博客到微博和微信,每一种新功能的出现都给互联网生态带来冲击。以微博的出现来划分互联网历史,有一定的随意性,是一种分析策略。使用这样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可以提出一系列历史性的问题,如:两个时代在网络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技术诸方面,有哪些变化?变化的原因何在?过程如何?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否使貌似中性的技术形态,具备了威廉姆斯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特征(Williams,1974),并在使用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某种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历史分期策略,跟线性的历史观没有必然的联系。学界对时间概念与线性历史观的批判由来已久。传播学者中近年对该问题做过深入探讨的有美国学者斯蒂芬·田中(Stefan Tanaka,2015)。田中(2015)写道,钟表时间、线性时间等概念,都是西方工业化与现代性的产物,这些现代性的时间和历史概念,包含着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时间从过去向未来的线性展开,代表了社会的进步。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表明,世界没有变得更美好,进步与其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如说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一种意识形态。基于这样的分析,田中进而提出了“没有编年史的历史”的命题,以求摆脱目的论的历史观,从而洞察历史的重复性、偶然性、不确定和多样性。
我们可以想象“没有编年史的历史”,但是难以想象没有时间的历史。田中在提出“没有编年史的历史”命题之后,阐述了如何把时间纳入“没有编年史的历史”研究之中。他提出的办法,是承认历史存在的多种时间尺度。他说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 ,1992:341-342) 曾经提出,人类生存需要6个社会—时间尺度:对个体来说是以年岁为尺度;对家庭来说十年、二十年是尺度;对国家和部落来说,尺度为世纪;对文化来说,尺度是千年;对人类、物种来说,尺度是万年;而对地球生命来说,尺度则是亿万年以上。从这个多时间尺度的历史观来看,互联网发展历史的时间尺度,应该大大短于早先媒介的时间尺度。互联网学者也早就意识到,研究互联网需要有“互联网时间”观,“十年的时间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时间段上只是一瞬间,但在互联网时间上堪比万年”(Loader & Dutton,2012:609)。
二、互联网信息审查与创客空间
互联网信息审查在海外备受关注,但是很多研究都落入“控制—抵抗”或“审查—异议”的二元思维框架。最近几年,学界的视野和分析角度有所拓宽,对网络信息审查的研究有所深入(如Han,2015;Taneja & Wu,2014;Yang,2014)。《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中,任教于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中国文学学者陈晨(Thomas Chen)对小说《如焉》的审查过程的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首先,陈晨将网络文学审查看作是一种另类创作(alter-production)的过程。他使用另类创作的概念,一是为了避免将网络审查和抵制简化为二元对立的斗争,二是强调对审查的各种回应之间的异质性。他认为创作和另类创作的过程都是一种“工作”,做这个工作的空间则可叫作“工作室”。工作室是一个“以相互启发并形成另类公众(alternative publics)为特征”的空间。经由这种途径,网络文学审查实践及其引发的回应,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再创作活动。2004年,《如焉》的作者胡发云完成小说写作后,本来计划出版印刷版,计划落空后开始在网上以电子文本的方式流传,直到2006年在《江南》杂志上发表,半年之后再出书。2009年,博客写手“食砚无田”在网上发文说:“花了两天多时间,对《如焉》两个版本对照浏览,把《如焉》中被删部分的文字全部‘捉’了出来,供博友一读。《如焉》删节本共删除约八千字(含标点符号数)。”由此催生了网上对《如焉》的不同文本的对照、分析。一位叫“老礁”的网友写道:“从删掉的部分能读出的,和与允许出版的版本的比较能分析出的,要远远多于字面本身。一些年之后,或许会有叫作‘版本比较学’的新学科诞生呢,届时人们就会记起无田兄的发轫之作。”(Chen,2015:26)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如焉》不仅没有因为被审查而销声匿迹,反而经网友的“另类创作”而得以扩散。
林云雅(Silvia Lindtner) 对创客空间的研究,同样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她认为“网民”这个广泛使用的名称,虽然意义很丰富,但它强调的是作为用户的网民,所以仍不足以表达网民创造性的一面。因此,她提出“创客主体”(making subjectivities)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创客。
讨论创客,不能不谈中国的“山寨”技术文化。当“山寨”文化常常作为中国缺少创造性的互联网产业的反面样本的时候,林云雅却提出,“山寨”文化就是创意文化。她采访的创客甚至告诉她,山寨文化就是中国的开源(open source)文化,因为山寨也看重共享、开放,通过杂糅实现创新。林云雅在她的民族志研究中还发现,创客文化既是个体赋权的过程,也是对创新、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重新想象和界定。与中国IT行业缺乏创造力的传统观点相反,林云雅为中国技术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感到自豪。她说,他们只是缺乏使想法得以实施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因此,他们愿意与政府合作。这导致了貌似对立的两种行动主体之间的结盟,也引起了系统内部的变化。最终,林云雅发现,中国的山寨文化既不是彻底的反文化,也不是制度的歌颂者,而是试图利用国际风险资本和国内官方的新经济思想来实现其创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客精心谋划了多种主体性。
三、作为目的和手段的互联网治理
2010年,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白皮书》,通过提出“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构想,表明一种全面的互联网控制模式诞生了。白皮书的发表主要针对国际舆论,系统阐明中国政府在互联网发展和治理方面的立场,是中国政府首次正面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网络审查的批评。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文明治网、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网络正能量等等,成为新的治理策略和公共话语。鉴于此,对中国互联网的分析也必须更多地关注国家权力的新的、更巧妙的表现形式。
美国政治学者白君竹(Steven Balla)研究的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网络咨询和协商,分析的是微博出现之前的案例。他的研究说明,互联网治理既是管理的目标,也是改进政府治理的手段。利用互联网,征求公民对法规草案的反馈意见,正是借助网络实施和改进治理的手段。白君竹具体研究的是在卫生系统改革这一政策领域的网络议政。鉴于“数字空间的复杂性、多面性”,他没有对互联网的作用进行一般性评估,不去谈论互联网是维护还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那类空泛的问题。相反,他聚焦于一个具体的制度机制(institutional mechanism)及其在具体政策领域的应用。卫生系统改革提案发布上网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网上征求意见。在此期间,网民对卫生系统的改革方案发表了3万多条评论,其中有6,000多名发表反馈意见的网民,甚至提供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白君竹通过对这些网络协商参与者的调查发现,内心相信绩效、有民主倾向的人,相比不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来说,评论的语气更积极,所提出的问题更有实质性。他认为,这一发现说明卫生系统改革中使用的在线协商机制,使公民接触到了民主原则,体验了利益表达的过程。这是一种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变革,但白君竹同时告诫说,这种变化发生在一个特定的体制框架内,而不是在整个国家层面。
政务微博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推动政务微博的发展,鼓励政府部门和官员使用微博发布信息,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影响力和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施雷格(Jesper Schlager)和蒋敏(Min Jiang)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政府”这个概念过于笼统,不能反映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对社交媒体可能做出的不同反应。例如,市政府由多个职能部门组成,负责公共安全的部门与负责商业或城市规划的部门职责有所不同。因此,当社会问题在社交媒体上曝光时,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即使在政府内部,也并不总是很清楚。两位作者认为,尽管许多地方政府看上去热情地投入了微博政务建设,但政府微博主要还是一种“测试机构”(beta-institutions)。他们将“测试机构”定义为“供临时使用或试验的一般原则和组织行为”。这一观点抓住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即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改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之外,这种测试机构使得政府部门能够尝试与公民互动的新方式,建立地方政府与商业ISP之间的新关系。例如,当政府部门在新浪微博注册账号时,它们须得到互联网公司的认证和批准,而不是反过来;它们的帖子被储存在新浪微博的服务器上,而不是存在政府的档案馆里。因此,仅就网络发帖而言,档案存储这一重要职能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网络公司。此外,施雷格和蒋敏所调研的市政府,在商业微博平台上对用户数据没有特殊的访问权限,也不存在任何正式的法律途径可以让他们随意获得用户数据。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中国政府形象。的确,施雷格和蒋敏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不同层级上的多种官僚机构不做区分,只是泛泛地谈论政府,必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四、族群认同及休闲与欲望的阶层政治
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许多研究都承认,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的群体借助网络获得了新的发声机会。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公民努力通过网络开展网络公共参与和在线抗议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些研究专门讨论新浪微博的网络行动。然而,瑞典隆德大学的史雯(Marina Svensson)的研究发现,新浪微博上的个人言论是不平等的,有的人能发声,但很多人被边缘化,不能发声。名人和网络舆论领袖利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赢得大量粉丝,能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外来务工人员和劳工民间组织则极少活跃于微博,他们更多地使用QQ。
能否发声关涉到社会承认和认同的问题,压制声音就是拒绝承认。南加州大学的弗雷泽(Frazier)和张琳对关于娄婧身份的网络论争的研究,分析的就是网上关于边缘群体的身份政治的论争问题。娄婧是混血儿,母亲是华人,父亲是非裔美国人。2009年末,当她在上海某个颇受欢迎的电视音乐比赛节目中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时,引发了网上激烈的辩论。Frazier和张琳发现,这些争论中既存在普遍的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也有能够包容多元性和差异性价值观的反思话语。除了娄婧的母亲与非裔美国人的关系之外,争论还延伸到了身为中国人的意义、女性与外国人的种族关系,以及中国混血儿童的身份等问题。最后,娄婧之争演变为围绕中国民族身份和中国如何看待异族的全国性辩论。网络上既有对娄婧及其母亲的诋毁,也有来自网民对娄婧母女的支持。两位作者从中梳理出一个复杂的种族和民族认同故事。这些关于娄婧的争论,特别是种族主义言论,折射出中国长期存在但很少公开讨论的种族意识形态和行为。此外,两位作者还发现,对娄婧的某些批评来自特定的全球化思想,因为在全球舞台上,对现代化的态度依赖于一套种族话语,其中“非白种人,特别是非洲裔群体,除了被扣上经济、政治落后的帽子之外,还被划分为种族和文化落后的群体”。最后,弗雷泽和张琳将娄婧事件归因于大众和网络文化。娄婧通过在电视上的强大表现来保护自己及其中国身份,成为举国关注的对象,成为全国名人。她的故事也因此成为草根名人养成的新潮流。这种趋势与网络参与文化的兴起相并行,同时也搭上了“美国偶像”类电视节目(如“超级女声”)的浪潮。这些大众形态,标志着从官方大一统的高傲宣传型媒介,向多声音、多元化的媒介和娱乐场的转变。网络热词或流行语是当代网络文化的独特景观,是全球性的现象。然而,网络热词的内容和意义以及它们的生产与流通手段,却因文化和社会背景而不同。
中国网站上出现的大量网络热词通常是因有趣的网络互动而生,尽管十分盛行,但我们对它们出现的社会背景知之甚少。美国传播学者斯懋熙(Marcella Szablewicz)对“屌丝”一词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屌丝”是2012年兴起的网络热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用来嘲笑社会下层青年的流行语,却作为一种自我嘲弄和自我肯定的形式受到热捧。斯懋熙认为“屌丝”是“一种新的情感认同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人们可以想象和实现替代性的欲望(alternative desires)和社会流动形态”。为了理解他们的替代性欲望是什么,可以先看看“屌丝”的反义词“高富帅”。“高富帅”表达了当代中国关于财富、地位和高尚生活方式的价值观。而“屌丝”则是对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嘲讽。斯懋熙认为,“屌丝一词所针砭的对象,是这些正统的、被社会认可的成功模式,它尤其质疑这种模式在当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然而,在肯定“屌丝”所包含的批判性的同时,斯懋熙也看到了它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既挑战又强化传统价值规范”,因为“这一热词对物质财富、人的外貌和性别成见的强调,最终可能会强化它本来要嘲弄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
斯懋熙对欲望政治的分析与人类学者张宁(Ning Zhang)关于驴友社区的网络行动主义的研究相映成趣。虽然张宁没有从阶层和财富角度搭建分析框架,但她指出,驴友社区出现的背景不是互联网,而是日益增长的城市繁荣和休闲娱乐的新生活方式。这些社区的“驴友”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品位和基本的物质财富才能从事这类休闲活动。张宁认为,在活动中,他们发展了一种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意识,帮助和支持穷人的道德情感。当然,他们的目标只是温和的改变,而不是激进的批评或变革。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类行动主义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背包旅行是休闲性质的,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网络社区,并因他们在网上经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而改变”。因此,如同斯懋熙的文章所揭示的那些自我嘲弄的失败者一样,张宁的民族志研究对背包族的刻画也关涉到政治参与,只不过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
五、在线与离线行动主义的边界
张宁对网络背包社区的研究模糊了在线与离线、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她认为国家和社会是在动态的社会领域中,不断地进行角力和协商。在这一社会领域中,新兴的背包客通过网络社区同时参与线上和线下活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持续挑战、反抗和质疑权威体系”。在张宁的分析中,网络社区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与表面上更真实的“线下世界”之间的区别,而是这些社区的人们如何斡旋于在线和离线空间之间。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区生活和公民行动主义,旨在通过同行分享、志愿者工作以及在线和离线慈善来实现社会变革。
澳洲学者许建(Jian Xu)的文章研究的是网络围观。这种新形式的网络活动兴起于新浪微博,引起了传播学者的广泛兴趣,但在英语文献中这类研究并不多。许建将“围观”定义为“一种由网络促成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有助于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公众舆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他认为,网络围观为普通老百姓创造了一种政治参与形式,用以表达社会不公和监督政治权力。他的文章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对网络围观行为的历史溯源。对历史的追溯,他以鲁迅1919年的小说《药》开篇。鲁迅这篇作品中对漠然围观革命者斩首的人群的描绘,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对于鲁迅来说,这种公共观看文化代表了普通中国人在传统社会中的无知和被动。许建认为,作为网络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网络围观的出现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长期的文化、政治实践再创造的结果。
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许建说明了网络围观作为一种“积极观众”(active spectatorship)和话语政治的意义和重要性。来自英国的传播学者陈小瑾(Sally Xiaojin Chen)的文章则研究了2013年1月某媒体抗议事件,分析了线上和线下的抗议及其互动。如果说许建是从文明衰落和革命历史的维度分析网络围观,陈小瑾则把网络行动看作是一种有身体在场的行动(embodied action)。她认为这种网上行动,与街头现场的行动一样真实。基于对有关技术和身体(body)的文献的分析,她认为网络身体(online body)也是身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即使只是简单地操作鼠标和键盘加入网络行动,也是身体的动作”。尤为难得的是,她通过对这一抗议事件的分析,深入探讨了线上和线下抗议活动之间的关系。她通过大量访谈和开展网络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发现虽然该媒体的编辑和记者积极参与了在线行动,但他们没有将行动扩展到街头,因为很多记者和编辑愿意在体制内谋求变革,不愿采取激进行动。大多数街头抗议者是年轻人,他们是忠实受众但不是工作人员,没有参加街头抗议的经验。然而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经验,再加上对于事件过程中微博删帖现象的义愤,才减少了他们的恐惧感,促使他们加入了街头抗议行动。
六、人的经验
《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中的十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研究中国互联网的视野,分析的触角深入到研究现象的里层,如“屌丝”现象背后的社会情感结构,政务微博背后的政府部门的实际运作与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它们都呈现出现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甚至是内在的矛盾性,体现了“中国互联网深度研究”的一些特点。
“互联网深度研究”注重研究互联网与普通人的经验和社会实践。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播学研究,对这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互联网、新媒体与社交媒体等的问题,不仅是技术和媒介的问题,更是人的生存状况的问题。因此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尤其是在主流文化、媒体和政治生活中难以发声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边缘人群,他们的故事就更需要讲述和传播。这里笔者想介绍一篇给我们带来人的故事的文章,文章内容是云南大学孙信茹教授对云南少数民族普米族青年微信群使用情况的研究。孙信茹(2016)通过线下和线上民族志的观察,在文章中展示的,与其说是微信对普米族村民的影响,不如说是普米族村民如何通过微信进行群里群外的互动与交流,把一种新的社交媒介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同时又能够借助媒介化的渠道,表达他们在面对面的情景之下,不太习惯说出来的内心话语,包括个人理想和对社群的认同与想象。
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的故事少,这种倾向本不是什么问题,毕竟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多样性。但是有一种趋势值得注意,即在人的故事减少的同时,物(objects,things)的故事却在大量增加。现代社会商品化和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倾向,不断冲击和侵蚀人的内心的、精神的、情感的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单一化、扁平化。因此,强调“互联网深度研究”,是通过对人的经验和社会实践的研究,加深对人的主观和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发掘。讲人的故事,是为人的主体回归所作出的一种努力。
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经深入剖析物的文化(objective culture)对精神文化的侵蚀,说“当代文化的发展,其特点是我们可称之为客体精神的东西统治了主体的精神”(Simmel,1903/1971:337)。齐美尔所说的客体文化,包括各种外在的形态,比如商品和熙熙攘攘的都市空间,同时也包括了各种社会机构、组织和制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齐美尔所分析的客体文化对作为主体的人的统治,在互联网和新媒体领域呈现出什么样的状况,是格外值得重视的课题。
七、互联网的历史性
“深度研究”还有一个层面,即历史深度。有了历史深度,可以更好地把握现象的复杂性。历史深度又可分两方面来探讨。一是历史性(historicity),二是历史叙事(history)。对互联网自身历史的研究,属于历史叙事。历史性则指历史对于社会现实的构建作用,包括对理论和概念的建构。
关于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性的重要性,学界多有论述。例如,李金铨(2017:215)教授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中,就对历史视野的重要性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论述。文章写道:“社会科学及传播研究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要能见树又见林,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故必须捕捉时间(历史)与空间(全球)如何影响事物的‘常与变’及其变化的‘同与异’。”
笔者在这里借用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强调说明历史性对于互联网研究的重要性。艾布拉姆斯在《历史社会学》中提出,历史社会学的任务,是要弄懂“人的能动性这个谜”,并且通过对“社会结构化的过程”的分析来阐释人的能动性。他又说:“能动性的问题,就是要找到这样一种阐述人的经验的方法,这种方法同时地、对等地承认,历史与社会的创造,来源于永不停息的、有目的的个体行动,而个体行动不论如何有其目的性,又都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Abrams,1982:XIII)他所说的问题,是个体与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的老问题。重要的是,认识这个关系的方法,不是将两者分开,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中纠缠在一起的两个方面。不管分析的是阶级还是革命,是个人英雄还是罪犯,对历史社会学来说,它们都“不是存在的状态而是变化中的过程”(Abrams,1982:267)。艾布拉姆斯以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思的著作《文明的进程》为例,说明个体与社会在历史进程中如何被重新形构(figuration)。人的日常举止的文明的过程,既是个体行为演变的过程,也是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训形成的过程。“文明个人的诞生,就是分层社会的诞生。分层社会的诞生,就是文明个人的诞生。社会学分析的对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舞蹈,千变万化的舞蹈形态不是舞动中的演员还能是什么?”(Elias,1939/2000:223)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中,人是核心,社会、结构、制度的产生与人的行为不可分割。
互联网研究具有历史性,包括相关的理论与概念也同样具有历史性。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学者威廉姆斯的名作《关键词》,正是因其对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做了历史性分析,才揭示出词语背后的社会情感结构。在当代互联网研究中,新概念频频出现,如果在使用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辨析,不考察概念的历史性,就容易导致概念混乱不清,甚至是混淆视听的情况。胡泳与陈秋心(2017:33)对“舆论”和“舆情”两个概念的研究,以对历史性的分析,为互联网研究如何批判地分析概念,提供了范例。他们写道:“舆论”与“舆情”两词当下在中国被广泛混用,其实它们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现实意义。源于西方的“舆论”一词自近代传入中国,内涵几经演绎,成为一种治理工具,而“舆情”则是这种中国式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控制性变种”。胡泳和陈秋心认为,舆情的出现,是社会监测与控制的需要。
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研究,国际传播学对互联网和数字文化关键词的关注有更长的历史。2008年,《软件研究:词语集》(SoftwareStudies:ALexicon)出版,对与软件相关的关键词做了研究(Fuller,2008)。2016年出版的《数字关键词:信息社会与文化关键词》(DigitalKeywords:AVocabularyofInformationSocietyandCulture)一书(Peters,2016),秉承威廉姆斯对关键词的分析方法,由25位作者对各自选择的一个关键词做了历史性的分析,是互联网和数码文化研究者对本领域的关键概念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中颇有精彩的章节。例如,尼古拉斯·约翰(Nicholas John,2016) 对于英文“分享”(sharing)一词的分析,就是通过对该词的历史溯源,揭示它不断变化的意义。他说“分享”是当代网络社会的关键词,不仅因为“分享”来源于数码和网络文化的核心——计算机语言(如“文件分享”),也因为“分享”作为当代网络和手机文化的核心观念,常常被赋予深刻的社会含义 ——“分享”意味着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他通过对1999年到2010年间44个社交网站上“分享”一词的分析,发现社交网站上“分享”一词的意义在不断发生变化。总体趋势是,早期的“分享”意思更为具体,但逐渐地,“分享”的意思变得越来越宽泛。如2000年左右,社交网站上说到分享,一般会提到具体分享的东西是什么——社交网站可以邀请用户分享照片或分享链接,诸如此类。等到2007年,社交网站开始敦促用户分享“模糊的东西”,比如分享“你的人生”“你的世界”,分享“真正的你”。什么是“真正的你”?这是很模糊的东西。当要你分享的东西偏模糊的时候,网上分享的行为就更为宽泛。再稍往后,连模糊的东西都没有了,很多社交网站在自我描述里,就直接说“在这个网站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甚至只说“请分享”,具体要分享什么,好像已经不言自明。换句话说,到2010年左右,“分享”几乎已经成为社交网站的代名词,要办社交网站,必然竖起分享的大旗。对“分享”一词意义变化的分析,揭示了互联网时代价值观的变化如何通过一个词语的变化而表现出来。
八、互联网历史学
深化互联网的研究,还应当关注互联网本身的历史,包括互联网发展史、网站史、网页史、互联网使用的社会史、互联网文化形态的变迁,等等。
“互联网历史学”(Internet historiography)和“网络历史学”(Web historiography) 是国际传播学界方兴未艾的话题。丹麦学者尼尔斯·布鲁格(Niels Brugger,2012、2013)一直致力于互联网历史和网页历史的研究。他在一篇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在互联网研究领域,应该加强对“网络历史学”的重视,因为不论从什么理论角度研究互联网,互联网历史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先决条件。2017年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来说是格外有意义的一年。先是《洛特里奇互联网历史手册》(RoutledgeHandbookofInternetHistories,Goggin & McLelland,2017) 出版,继而是英文国际期刊《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InternetHistories:DigitalTechnology,CultureandSociety)创刊。《互联网历史》杂志主编和《洛特里奇互联网历史手册》主编分别在他们的导言里提出,对于互联网历史的书写要重视互联网历史的多样性(histories)和全球性(global)。《互联网历史》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在哪里?重新定义互联网历史》提出,对互联网历史进行研究,首先需要重新定义互联网(Abbate,2017)。所谓重新定义,是因为现有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大多侧重互联网的技术层面,如硬件、软件,而这个层面的互联网历史叙事,则一向以美国为中心。互联网的发展史,往往被叙述为从美国向世界各地扩散的历史。文章作者阿巴特(Abbate,2017)认为,互联网的历史还可以定义为“内容和社会实践”(content and social practice) 的历史,也可以定义为“本地经验”(locally situated experience)的历史。如果这样来定义互联网历史,那么互联网的历史将是多样性的、地方性的,因使用者经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书写,理应体现中国的历史性和社会、文化、政治等特征,这在从事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应该说有一定的共识。前面提到的胡泳、陈秋心对“舆情”概念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好的例证。王洪喆(2015)对媒介技术的历史,尤其是计算机在内地发展历史的研究,也是互联网历史书写的重要成果。他的分析说明,中国电子信息工业和计算机的发展,在冷战语境下和改革初期,如何表达了乌托邦自动化的美好愿景,同时互联网又是生产的工具和阶级政治的中介。2016年,意大利学者加布利尔·巴比(Gabriele Balbi)与中国学者陈昌凤、吴静为《互动:传播与文化的研究》(Interactions:StudiesinCommunication&Culture)杂志编辑了一期“中国媒体历史”的专辑。三位编者在专辑导言里提出“召唤(新的)中国媒介历史”,其中“新的”部分,即包括对计算机、互联网和手机历史的研究(Balbi,Chen,& Wu,2016)。该专辑中主要谈互联网的文章是意大利学者巴劳恩(Bahroun)的《重写中国计算机媒介的历史,1990年至今》。巴劳恩(2016)认为,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大多只关注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忽视了用户,因此应该强调用户层面的历史,用户才是互联网信息交流与传播的核心。他认为人们习惯称之为网络空间的互联网,实际上乃是一种新的写作和阅读,网民在网上的行动并非真正的走动,而是读、写、发帖,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从符号学角度书写中国互联网历史的可能性。
在当代历史写作中,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普通人的记忆,是一种下层历史书写的形式,可以弥补官方“正史”的空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还有其独特的记忆方式:网站上的发帖,一经发出便成为网络历史的一部分,成为天然的网络历史“档案”。大量消失和关闭的网站,也同样留下许多可追寻的痕迹,比如散落在论坛里的网民对网站的个人回忆等等。这些材料成为网络历史研究的“档案”。杨国斌和吴世文(2017)即将发表于《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的英文论文《追忆消逝的网站》,在这方面做了初步探索。中国的互联网空间不断有网站关闭或消失,对于其中一些网站,网友常常会在网上描述自己深刻的记忆,表达怀念之情。文章发现,通过对这类怀念文章的分析,讲述消逝的网站故事,亦是挖掘互联网历史的一种可取的渠道。
九、以深为浅,以浅为深
以上从人的经验和历史深度两个方面,讨论了“互联网深度研究”的意义。“深度研究”之“深”,不是对普遍理论的追求。相反,它建立在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局限性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有了这样的反省,我们才可以看到,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互联网研究,应该做到虽深亦浅、虽浅亦深。或者说以深为浅、以浅为深。
对人文和社会科学局限性的反省,涉及理论、方法、认识论等诸多方面,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做过系统的探讨。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E.P.汤姆逊在1978年出版的《理论的贫乏及其他论文》一书中,对阿尔杜塞的结构主义理论予以尖锐的抨击,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譬喻,被潘忠党教授归纳翻译为“理论分析犹如蝗虫,侵蚀生命,袒露毫无生命活力的骷髅”。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在1991年出版的《否思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出要抛弃19世纪以来一直控制我们思维的社会科学核心概念,如“发展”。他认为“社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方法论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分析过程中删除了时空的概念”(沃勒斯坦,1991:3)。他因此提出重新在长时段的历史中,认识21世纪的世界体系。
本文无法总结这方面大量的文献,仅就与“深度研究”直接相关的“深”与“浅”的关系,做简单探讨。这个问题也可分两方面,一是理论与描述的关系问题,二是深描与浅描的关系问题。
“互联网深度研究”的“深”,其对立面不是“浅”。甚至可以说,“深”包含了“浅”的一面,这个“浅”可以指“显”,也可以指“表”“表层”。这是笔者所说的“深度研究”与人类学家格尔茨著名的“深描”概念的一个差别。格尔茨的“深描”对“浅描”持排斥态度,而我们的“深度研究”并不排斥“浅描”。“浅描”也可以成为“深度研究”的一种方法。要说明“浅描”在“深度研究”中的意义,需要考察相关领域的学者对“深”与“浅”和“理论”与“描述”的相关论述。
先说“描述”(description)。在人文和社科研究领域,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研究被奉为正统。谁要是说你的文章“纯粹是描述”,那一定不是恭维。“描述”为浅,理论的解释才是深。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2005) 在《重组社会》一书中,彻底否定了这一社会科学的正统,提出抛弃理论,认真描述。他说:“‘纯粹的描述’有什么不好?”他认为描述从来就不是简单直接的描写,如同画家从来不是直接把看到的景物搬到画布上。描述包含了观察、分析、选择等多个步骤,描述的过程跟科学家在实验室做研究没有什么差别。“哪位学者也不必因为执着于描述而觉得丢人。相反,描述才是最高的、最少见的成就。但是,我们却仍然担心执着于描述也许会失去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贡献出那个常常被叫作‘解释’的东西。然而,实际上描述与解释的对立,只不过是那些本该早已寿终正寝的二元对立的一个样本。如果描述后还需要再解释,那只能说描述得不好。就像‘安全性交’一样,坚持描述可以防止传染上解释的病症。”(Latour,2005:137)
拉图尔对理论和解释的厌恶以及对描述的倡导,源于他独特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个理论简称ANT,与英文的蚂蚁一词相同,这并非巧合。ANT理论的目的,就是描述各类行动者之间的网状关联,而行动者不仅包括人,还包括物体、机器等。把非人的物件作为行动者的理论,自然不能去挖掘行动者的动机,人可以有动机,物的动机何来?因此,在他的ANT理论里,反对解释,提倡描述,也算是符合理论的要求。
但是最近几年,在美国文学研究界和人类学界,却也有学者专门著述批判理论和解释,大力倡导“描述”和“浅描”。文学研究领域向来崇尚“深解”(depth hermeneutics)。“深解”的核心是通过对文本的细读(close reading),来充分挖掘文本的多义性,从而揭示人的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一点上,本文所谈的“互联网深度研究”与文学分析中的“深解”有相通之处,因为“互联网深度研究”和“深解”一样,也重视对人的经验的丰富性的挖掘。近年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对“深解”传统的挑战,其核心是倡导在研究与写作中从解释(interpretation)向描述的转向。
先是2009年两位英语系和比较文学系的学者史蒂芬·贝斯特(Stephen Best)和莎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在《表述》(Representations)杂志上组织了一个关于“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的专辑,倡导“表层阅读”。专辑的两位编者在导言里讨论了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倡“表层阅读”。他们认为传统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假设文本的真正含义隐藏在文本深处,因此要通过细读,将意义发掘出来,加以阐发。然而在当代社会,很多事情都在表面展露无遗,不需要谁来解释,最需要的是记录、见证、行动。比如美军在伊拉克战争期间采取的酷刑、卡特琳娜飓风期间新奥尔良的非洲裔贫民被抛弃不管的惨况等图像在网上广泛流传,甚至对于政客的种种承诺,人们也都能一眼看穿其谎言的实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如果不是政治行动的代名词,那它还有什么意义?”(Best& Marcus,2009:3)
稍后,201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的希瑟·拉芙(Heather Love,2010)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细而不深:文学伦理与描述的转向》(ClosebutnotDeep:LiteraryEthicsandtheDescriptiveTurn)的文章,把讨论的问题扩展到对“深解”传统的批评和对“描述”的进一步肯定。她不赞成抛弃“细读”的传统,但认为可以“细而不深”,意思是对现象的描述要细,但不必“深”,即不需要致力于对现象背后的动机、深层意识及社会根源的挖掘,因为对现象背后隐性因素的执着,反而会导致对现象本身看不清楚,看不全面。希瑟·拉芙认为“细而不深”的文学分析方法,蕴含着一种新的文学价值观,即文学的作用不是做阐释、批评和道德评判,而只是记录和描述(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她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小的反响,所以到2016年,她又与马库斯和贝斯特联手,编辑发表了《建立更好的描述》(BuildingaBetterDescription) 的论文,进一步论述“描述”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Marcus,Love & Best,2016)。
人类学界关于对“深描”的批判和对“浅描”的倡导,有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即出版于2013年的《浅描:民族志与耶路撒冷的非洲希伯来犹太人》(ThinDescription:EthnographyandtheAfricanHebrewIsraelitesofJerusalem)。该书作者恰好是笔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教授。作者在书的导言里说:“《浅描》一书是对人类学里某种过分的自信的回应。这种过分的自信无异于傲慢,傲慢来自‘深描’所赋予其信奉者的权力。‘深描’犹如一个有神奇效用的比喻和方法论的护身符,它代表了想获得丰富、严谨甚至是全能的社会认知的努力,或者说是野心。”作者又写道:“在某种意义上,深描一向都很浅。它把自己伪装在玄乎其玄的外表之下,假装什么都看得见,其实常常看不见那么多。”(Jackson,2013:14)
由此可见,近年人类学家对“深描”的批判和文学家对“深解”传统的批判,有一个核心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全知全能精神”(totalizing ethos)(Jackson,2013)的批判。这种“全知全能精神”反映在“深描”的实践中,是对现象的貌似全面、透彻的描写;反映在“深解”的实践中,是对理论的崇拜和对“描述”的鄙视。因此,对“描述”和“浅描”的肯定,不仅是对“深描”和“深解”的抵制,也是倡导一种新的对待“他者”和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开放的、谦逊的,是承认差别,承认科学的局限性,是反对对理论的盲目崇拜和对那种自恃“全知全能”、唯我独尊的研究的怀疑。
这种对“浅描”的肯定和对“深描”的怀疑,对本文所说的“互联网深度研究”有两点启发。一是它使我们看到,“深度研究”虽然力求向纵深挖掘人的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但它必须对自身的局限有所反省。深度挖掘,即使再深,也有其浅的一面,不可能做到全面和彻底,因此研究者必须能够容纳新的解释、新的故事,要能够以深为浅。另外一个启发,涉及对理论的态度。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理论和概念,但是对理论的局限性反省不足,甚至导致对理论和概念的盲目崇拜,走向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后果,对理论来说,是走向自身的封闭;对社会和政治实践来说,则有可能导致灾难。“互联网深度研究”重视理论但不盲目崇拜,不摈弃好的“描述”。当某一理论被奉若神明,用来压制异己、封闭对话的时候,就真不如认认真真的描述来得更有意义了。
【感谢李金铨教授、潘忠党教授、夏倩芳教授、吴世文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纰漏之处,文责自负。】
胡泳,陈秋心.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40):33-74.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J].开放时代,2017(3):215-231.
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0):6-24.
王洪喆.从“赤脚电工”到“电子包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与劳动政治[J].开放时代,2015(3):34-4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M].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ABBATE,J.What and where is the Internet? (re)defining Internet histories[J].Internet histories,2017(1-2):8-14.
ABRAMS,P.Historical sociology[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BAHROUN,A.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omputerized media in China,1990s—today[J].Interactions: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2016,7(3):327-343.
BALBI,G,CHEN,C & WU,J.Plea for a (new) Chinese media history[J].Interactions: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16,7(3):239-246.
BEST,STEPHEN & MARCUS,S.Surface reading:an introduction[J].Representations,2009,108(1):1-21.
BRÜGGER,N.When the present Web is later the past:Web historiography,digital history,and Internet studies[J].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2012,37(4):102-117.
BRUGGER,N.Web historiography and Internet studies:challenges and perspectives[J].New media & society,2013,15(5):752-764.
BRÜGGER,N.& SCHROEDER,R.The Web as history: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M].London:UCL Press,2017.
DYSON,FREEMAN.The face of gaia[M]∥Eros to Gaia.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2:338-345.
ELIAS,N.The civilizing process: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M].Oxford Malden Mass:Blackwell Publishing,1939/2000.
FULLER,MATTHEW.Software studies:a lexicon[M].MIT Press,2008.
GOGGING & McLELLAND,M.Introduction:global coordinates of Internet histories[M]∥GOGGIN G.& McLELLAND M.Routledge handbook of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London:Routledge,2017:1-20.
HAN,R.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China’s “voluntary fifty cent army”[J].The China quarterly,2015,224:1006-1025.
JACKSON Jr.,JOHN L.Thin description:ethnography and the African Hebrew Israelites of Jerusalem[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JOHN,NICHOLAS A.Sharing[M]∥PETERS,BENJAMIN.Digital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269-277.
KLEINMAN,ARTHUR et al.Deep China: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LATOUR,BRUNO.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LOADER,BRIAN D.& DUTTON,WILLIAM H.A decade in Internet time[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2,15(5):609-615.
LOVE,HEATHER.Close but not deep:literary ethics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J],New literary history,2010,41(2):371-391.
MARCUS,S.,LOVE,H.& BEST,S.Building a better description[J].Representations,2016,135(1):1-21.
PETERS,BENJAMIN.Digital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
SIMMEL,GEORG.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3/1971.
TANAKA,STEFAN.History without chronology[J].Public culture,2016,28(1):161-186.
TANEJA,H.& WU,A.X.Does the great firewall really isolate the Chinese? integrating access blockage with cultural factors to explain Web user behavior[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4,30(5):297-309.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M].London:Routledge,1974.
YANG,F.Rethinking China’s Internet censorship:the practice of recoding and the politics of visibility[J].New media & society,2014,18(7):1364-1381.
YANG,G.China’s contested Internet[M].Copenhagen:NIAS Press,2015.
DeepStudiesforChineseInternet
Yang Guobi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hapters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volumeChina’sContestedInternet,this article discusses issues of theory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in China.It proposes a “deep Internet studies” approach that foregrounds people’s lived experiences,historicity,as well as a balanced and reflexive approach to theory and description.Recent works on “thin description” in anthropology and “surface reading” and “the descriptive turn” in literary theory are reviewed to shed light on the reflexivity of a “deep Internet studies” approach.
Internet,deep studies,Social Theory,thick description,thin description,close reading,surface reading
*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Grace Lee Boggs传播学与社会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媒介与社会理论、社会运动、在线抗争、全球传播、文化社会学、中国的媒介与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