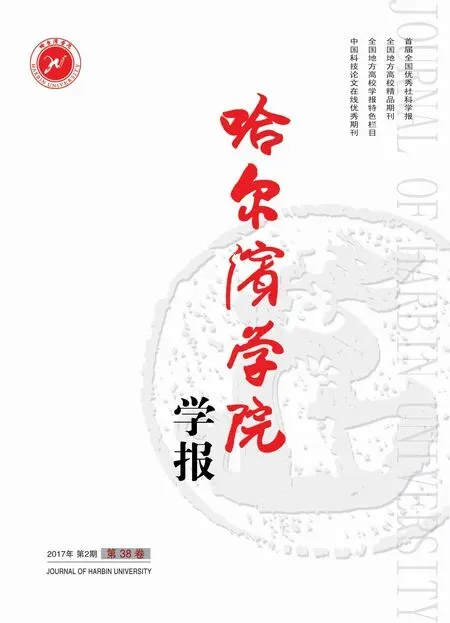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影响
刘 琪
(唐山学院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000)
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影响
刘 琪
(唐山学院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000)
辩证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古代先人们常用的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先秦辩学角度看,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先秦辩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谈说论辩的过程中,先秦诸子根据谈辩对方的具体情况、所处环境等因素而选择相应的谈辩方法或技巧,以期取得良好的谈辩效果。探讨先秦时期辩证思维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展现先秦时期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对先秦时期逻辑思想的拓展和深化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发展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促进本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与完善。
辩证思维;先秦;辩学
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辩证思维成为古代先贤用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李约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人是高深的。”[1](P337)冯契也曾指出:“原子论思想和形式逻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但是中国人却比较早地发展了朴素的辩证逻辑和朴素的辩证法自然观(气一元论)……这却是一个优点。”[2](P49)彭漪涟称冯契的上述观点为:“实际上这是对中国传统逻辑思维特点的最简明的概括。”[3](P316)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辩证思维方式应该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它对先贤的逻辑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辩证思维已经具备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较成熟、较完备的典型形态,因此,分析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展现先贤们对辩证思维的理解和运用。本文重在探讨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先秦辩学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辩证思维释义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中众多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它是思维依据辩证法的观念基础和事物存在的辩证本性对事物的一种整体把握。具体而言,辩证思维建基于辩证法基础上,将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从事物的辩证本性即对立统一性和由它所导致的运动、变化、发展出发灵活变通的对待事物,其最终目的是完成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转变,进而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客观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对辩证思维的理解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上的。先秦时期辩证思维与此种意义上的辩证思维有诸多共同点,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同。因此,对先秦时期辩证思维的研究不能仅仅进行“据西释中”的比较研究,也要用“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方法来推进研究。将先秦时期的辩证思维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背景中,站在历史化的角度考察它,挖掘其内在特征,应该可以避免用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辩证法来解释甚至重构先秦时期的辩证思维。
先秦时期的辩证思维是先秦诸子认识世界、把握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整个自然界中的万物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有机整体,旨在从运动变化的角度认识、考察万物。先秦典籍中最为典型的体现辩证思维的莫过于《周易》和《老子》了。
《周易》认为,阴阳间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进而据此提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以及对立面及其转化的规律。此外,《周易》还认为,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矛盾对立双方,并不能总是保持着“阴阳相抱”的平衡状态,它必然会受到“物极必反”这一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老子》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进行论说。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内含阴阳两种对立的因素,正是这两种因素的相互斗争、相互作用促进了事物的变化发展,即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同时,《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这一表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命题,这是辩证思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受先秦文化的影响,先秦时期辩证思维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服务生存的实用性
中国古代哲学及一切学术研究的任务和职能,就是为解决人事问题、维持社会秩序和君主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中国哲人,因思想理论以生活实践为依归,所以特别注重人生实相之探求,生活准则之论究。”[4](P10)西方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传统,以及高度抽象化、概念化、形式化的认知理念和论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几乎是不存在的。
首先,先秦诸子承认事物中存在着矛盾对立的双方,但他们对矛盾对立项的选择都来源于日常生活经验,没有上升到纯逻辑的形式抽象。孔子对具有对立性质的概念和范畴的表述,“过”与“不及”、“智”与“愚”、“教”与“学”、“多”与“寡”、“生”与“死”;荀子所论说的“阴”与“阳”、“寒”与“暑”、“损”与“益”、“存”与“亡”、“知”与“行”之间的对立统一;老子所肯定的“美”与“丑”、“善”与“恶”、“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等对立面的存在;庄子所强调的“成”与“毁”、“大”与“小”、“长寿”与“短命”;以及墨子所谓的“治”与“乱”、“贫”与“富”、“贵”与“贱”,等等,这些对立概念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没有超出人事的范围。即使在《老子》《周易》这样高度抽象的哲学里,也都具有这一特征,二者的共同点就在于将辩证思维的运用与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秩序、规范结合起来,并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普遍性规律。只不过相比较于《老子》在矛盾双方注重“柔”的一面,《易传》强调“刚”的一面。
其次,先秦诸子对概念的解释,并不是西方那种纯理论形态,即首先明确概念的基本特征——内涵和外延,然后从基本概念出发,经过一步步严密的推理论证而最终得出结论,灵活地解释概念,即注重结合具体情况、具体事例解释具体情境下概念的含义,没有将概念的含义固定化、凝固化,因人而异、因时制宜是其最大的特点。孔子关于“仁”“孝”等道德概念的解释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
综上,孔子对同一道德范畴的界定是因人而异的。虽然这种道德范畴的本质是不变的,但具体落实到不同的认知主体上却可以根据认知主体的具体情况给予最为适宜的解释。以问仁为例,“克己复礼”是孔子倡教儒学的根本目的,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孔子便用最切要领的“克己复礼”揭示“仁”的内涵;仲弓出身“贱人”,在尊重他人方面有所欠缺,孔子针对他的不足,以“如见大宾”告诫他。因此,孔子主张结合日常生活场景去理解概念,真正将概念贯彻到自己的生活中去,而不是脱离日常生活将概念进行纯形式的抽象。
(二)重和尚同的和谐性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先秦诸子对矛盾的认识中。先秦诸子虽然承认事物中普遍存在着矛盾双方,但在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上却偏重于二者统一和谐的一面,忽视了二者对立斗争的一面,即重“和”甚于重“分”。
孔子提出了“执两用中”的思想方法,强调事物存在的理想状态就是事物内部对立面间的和谐统一。继而,他又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并将其内涵解释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子思在孔子“中庸”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本体论的高度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他认为事物只有达到“致中和”的状态才是最为理想的存在状态。他追求事物绝对的和谐统一,追求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将重“和”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孟子处理天人关系的态度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也,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此外,当他提出“万物皆备于我”这一命题时,就已完全把天地万物融合在人之中,二者间对立的一面就不复存在了。
老庄处理矛盾的方式体现了其辩证思维中重和尚同的一面。老子认为,如果任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斗争,那么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走向衰亡。为了长久的维持事物的存在,就应该防止矛盾的转化。因此,他认为“无为”“不争”“贵柔”“守雌”才是人类存在的最为理想的状态,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毫无矛盾的“玄同”境界,维持矛盾统一体的和谐。
庄子则从更加极端的角度来否认矛盾的对立面。庄子认为矛盾双方间的对立和差别都是有限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齐物论》)
从绝对无限的“道”的角度看,万物是无所谓差别和对立的,任何差别和对立都能够在“道”中消解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绝对同一境界。
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思想简单直接地表现了他期望建立一个无矛盾、无纷争、无差别的和谐社会,追求“和”“同”的思想不言而喻。
总之,先秦诸子辩证思维中重和尚同的倾向是较为明显的,这也使得其辩证思维长期处于素朴形态。只注重矛盾间的统一性,忽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就限制了矛盾双方间的转化,最终取消了矛盾。这种错误的矛盾观就像黑格尔在批判康德矛盾观的不彻底性时所指出的,“他似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应具有矛盾的污点的”,[5](P131)认为事物有了矛盾是难以容忍的大事,从而不敢正视矛盾,想尽一切办法取消矛盾。殊不知矛盾间的对立性是不可能随人的主观意志而随意取消的,“学天地者不妨矛盾”(方以智:《一贯问答》),不承认这一点反而使自己的理论陷入尴尬的境地。
(三)直观体悟的模糊性
先秦诸子由于其生产、生活条件的要求,对事物本身的矛盾性质、宇宙的变易的考察往往带有直观的性质。他们在运用辩证思维分析事物、思考问题时也是如此,他们重在对事物进行整体、直观的把握,而不太关注对事物的质的规定性进行细致的分析。他们常常给出一些结论性的命题,但也常常没有对结论的得出给出相关的推理论证。
道家的辩证思维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老子的“道”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绝对本体,既不能用经验感知,也不能用语言描述,更不能用概念去定义。总之,不能用任何常规的方法去认识。要把握“道”,必须“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涤除玄览”(《老子·十章》),在摒弃世俗观念后,用一种虔诚体悟的方式去参悟、体会“道”的真谛。这就是所谓的“知常曰明”。“明”就是通过直观体悟所达到的认识的最高境界。老子的诸多命题,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等都是直观的产物。
正因为老子没有对“道”进行明确界定,后继者庄子则可以在此基础上对“道”进行极端化的解读。从“道通为一”(《庄子·天下》)的角度出发,庄子完全否定了事物间的差别、人的认识的差别,进而否定了人们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实则,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内是确定的,是可以被认识的。此外,是非也应该有一个可供衡量的标准,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一定的方法、依据一定的准则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庄子从事物绝对运动的角度主观随意的认识,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诡辩论。
邓析子提出的“两可之论”虽然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由于他否定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所具有的相对确定性,以及是非判断存在着的标准的客观尺度,因此最终还是被视为诡辩而遭到后人的批评。
在惠施的“历物之意”中,“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南方无穷而有穷”“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今日适越而昔来”这几个命题包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但是初看起来似诡辩无疑。原因就在于,这些命题并没有明确南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具体的所指,万物有一存在的过程以及“今”就是“今”、“昔”就是“昔”等确定性的认识,而是直接从绝对运动的角度提出上述命题,难免会受人诟病。
总之,先秦诸子的辩证思维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但由于他们没有从理论形态上更好地把握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没有在对认识客体给予明确界定的基础上进行辩证思维,因此,其辩证思维多少带有直观意会性、模糊性等特点。这种缺乏明确的概念规定和逻辑构造的辩证思维,只能提供种种笼统的、模糊的、似乎是万能的认识方法。这显然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朴素性的重要原因。
综上,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由于自身产生条件的特殊性,具有实用性、和谐性、直观模糊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中固然有些是需要加以改正的,但有些却是当今时代发展所需要的,应该去粗取精、加以继承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历史进入了新时期,欧式辩证法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这就要求从东方辩证法中汲取智慧,来充实完善自己。具体而言,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三论”式的辩证法,即质量论、矛盾论、否定论。今天这“三论”虽然不过时,但已经不够用了,这就需要与中式辩证法的“平衡论”“和谐论”相结合,相互补充和完善。“平衡论”与“和谐论”是紧密相连,彼此互通的,都旨在强调“和为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之一。[6]欧式辩证法的成果只有与中式辩证法的相关成果相结合才能拥有持久不断的生命力,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
二、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先秦辩学的影响
先秦时期虽有“辩者”的称谓,但却没有“辩学”的称谓,“辩学”是后人提出来的。根据先秦思想家的表述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7](P23-25)我们认为辩学以谈说与论辩为对象;辩学的基本问题是谈说论辩的性质界定与功用分析;辩学的内容主要包括:谈辩的种类、原则、方法或技巧等。先秦时期的辩学主要是指先秦时代关于在辨别、辩论的思维过程中,以怎样的思维方法和准则以明同异、定是非、审治乱、决胜负的学说。由于谈说论辩本身就是一种听说双方就某一问题相互交流、争辩的交际活动。因此,谈说的顺利进行以及取得论辩的胜利都需要考虑到对方的实际情况,根据对方的知识背景、言语习惯、理解水平等情况而采用相应的谈说或论辩的策略。这些都与谈辩双方的辩证思维密切相关。
孔子一生教学、游说,非常重视言语谈说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言语谈说中要坚持灵活性、恰当性的原则。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所谓“无可无不可”即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它并不是一种不辨是非、模棱两可的思维方法和说话技巧,而是一种强调一切分析要从具体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的思维方法。孔子强调自己的灵活性更大,不拘泥于某一种特定的形态。孟子评价孔子的这种思维方法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此处提到的“时”,正是“无可无不可”的特点,即所谓“道中于时而已”(清焦循《论语补疏》),即中国人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曾问“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虽然未明确提出“知言”的方法,但他在论说“说诗”和“读书”时提出的两条原则,可看做是对“知言”方法的描述:
第一条: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第二条: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就第一条原则而言,“文”即文字,“辞”即语句,“志”即语义。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即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单个文字、语句的含义,而是要把它们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就第二条原则而言,所谓“知人论世”,即根据说话者成长的环境以及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去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思。二者都是强调在言语谈说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谈话语境来理解说话者的意思,否则就可能会出现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的错误,影响双方的正常交流。
荀子则提出“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谈说方法:“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于是闲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举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嬴绌,府然若渠匽、隐栝之于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荀子·非相》)
荀子认为,谈说的困难在于所用的谈说方法不恰当。人们在谈说时应根据谈说对象的具体情况与谈说的内容,选择一种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交谈,只有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这种论说方法的特点在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曲尽其理,而又不挫伤别人。“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荀子·劝学》)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荀子在论述“圣人之辩”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方法:“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成文而类,居错迁徙,应变不穷,是圣人之辩者也。”(《荀子·非相》)
荀子理想中的“圣人之辩”的描述显然过于美化了。但其中所说的“居错迁徙”“应变不穷”与”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大同小异,都旨在强调一种灵活的论辩方法。这是他极其看重的,也是圣人应该具备的。
墨子在论辩中最为熟悉且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是比喻式类推论辩方法。这种方法通过两类事物的相似点来论证或反驳一种思想的是非曲直。这一方法又可分为比喻式的类推谕证方法和比喻式的类推归谬方法。前者用于证明,后者用于反驳。
按此,比喻式类推论辩方法的运用都必然涉及到一个用来做比的“他物”。由于这些“他物”都是论说的前提或依据,因此对“他物”的选择至关重要。墨子对这些“他物”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毫无根据的,而是结合着谈辩对象的具体情况做出的可以被对方所理解、接受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比喻式类推方法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谈辩方法,也是一种体现着谈辩者辩证思维的谈辩方法。
墨家在充分继承并发展墨子比喻式类推论辩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止”“效”“辟”“侔”“援”“推”六种论辩方法。这六种方法或是给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标准,或是以对方所同意抑或反对的事例为同类事例进行证明或反驳。这一标准或事例的选择与墨子的比喻式类推论辩方法中用于做比的“他物”的选择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一种易于对方认可或接受的有针对性的选择。后期墨家对这些论辩方法的灵活并广泛的运用体现了其较为成熟的辩证思维。
名家邓析子将“辩”分为两类:“大辩”和“小辩”。所谓大辩者,别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故浅知也。(《邓析子·无厚》)
所谓“时措其宜”,《中庸》二十五章云:“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强调适时施行才是合宜的。在这里,邓析子认为“大辩”者能够做到“时措其宜”,就是说真正的辩者在论辩过程中能够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恰如其分的论辩,达到明同异、定是非、别善恶、分清浊的目的。而“小辩”只是在玩弄言辞,互相攻击,缺少深入探究客观真理的精神。据此,邓析子主张“大辩”,反对“小辩”,强调了“时措其宜”在论辩过程中的重要性。
至于如何具体做到“时措其宜”,邓析子认为,应该按照辩论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辩论策略,亦即辩论的对策要灵活多样。“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此言之术也。”(《邓析子·转辞篇》)
他把谈辩对象分为八种类型:“智者”“博者”“辩者”“贵者”“富者”“贫者”“勇者”“愚者”,并根据不同的对象,提出了八种谈话方式,体现了灵活变通的谈辩技巧,是“时措其宜”论辩原则的突出体现。
惠施在谈辩中善用“譬”式推论方法。所谓“譬”式推论也称比喻式类推。惠施将“譬”界定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说苑·善说》)这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第一次对“譬”给出定义。这一定义将“他物”明确表述为“其所知”,即辩说一方以对方所熟悉的事物为譬,进而使对方明白其原先所不知道的事物。这种对辩说语境的关注充分体现了“譬”式推论的语用性特征。惠施能够根据辩说对象实际情况的不同,选择对方熟知的、可以接受的例子作譬,这本身就是其朴素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
名家学者在论辩中十分注重根据论辩对象选择论据,这些论据多为对方所认可接受的,或出于自身情况而不得不承认、或不得不认可的。他们综合运用这些论据,以多种巧妙的方式,来证明或反驳自己或对方的观点。前文表述的惠施所擅长的譬式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孙龙子和尹文子也善于针对特定的论辩对象选择不同的论据。如:
龙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请去此术,则穿请为弟子。”
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与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迹府》)
孔穿说如果公孙龙子放弃“白马非马”的理论,就拜他为师。在公孙龙子对孔穿的反驳中,有一层是专门针对孔穿这个辩说对象,公孙龙选择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言论,以孔子的观点(异“楚人”于所谓“人”)与自己的观点(异“白马”于所谓“马”)为同一类进行论证孔穿的自相矛盾。当然,对孔穿来说,这一层的反驳更具说服性,从中可以看出公孙龙子独到的论辩技巧。
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齐王曰:“善!此真吾所谓士也。”……尹文曰:“唯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也。然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齐王无以应。(《公孙龙子·迹府》)
尹文子给“士”下定义的前提是“是时齐王好勇”,也就是说,找到辩说对方的爱好,进行有针对性的论辩。因此,他在给“四行”下定义时,故意缺少了“见侵侮而终不敢斗”这一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尹文子所给出的这一定义只对齐宣王有效,如果换成另一个有其他爱好的君主,那么这样的定义就可能不会产生良好的论辩效果。
总之,先秦诸子在进行论辩时非常具有针对性,能够具体分析谈辩对象的实际情况,从而选择适合特定对象的论辩内容与论辩方法。这种做法收到了良好的论辩效果。应该说,在谈说论辩过程中不存在最好的谈辩方法,只有最合适的谈辩方法。他们将一个个谈辩对象视为特殊的存在,分析不同谈辩对象间的差异,就可以选择出最适合此谈辩对象的方法。这不仅是先秦诸子惯常运用的灵活多变思维的体现,更是其朴素辩证思维在辩学中的具体体现。
三、探讨先秦逻辑思想中的辩证思维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启示
如上所述,先秦时期辩证思维对诸子谈说论辩方法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在于,先秦诸子所热烈争辩和探讨的名实、同异、坚白、言意、是非等问题,以及先秦诸子在推理过程中,对推理前提的选择等问题,无不具有辩证思维的色彩。又之,中国古代主导推理类型——推类的有效运用需要对“类”概念进行辩证分析。推类是在整体思维的框架下进行的,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思维,主要包含两点,一是整体观点,或曰整体思维;二是对待观点,或曰对待思维”,[8](P9)因此,整体思维亦是辩证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辩证思维对概念、判断、推理的运用,主要是从它们的辩证本性出发,注重展现其灵活变动性的一面,因此,辩证思维对于保障全面认识问题,避免思维片面性、僵化性有重要意义。
鉴于此,全面探讨中国古代辩证思维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影响,符合“文化逻辑观”的研究理念。因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实质和意义,它构成一个文化体系的最深层、最关键的因素。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前逻辑或原逻辑,体现着一个民族的逻辑思想。辩证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必然会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的实质是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一种研究自然、社会、历史和思维的哲学方法,是以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视角看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9]先秦时期辩证思维从运动变化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世界,自有它的优越性所在。但先秦时期的辩证思维尚处于朴素萌芽阶段,仍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主要缺点是分析方法不足,这在先秦哲学即已显出了。西方古希腊哲学中,形式逻辑体系完整,哲学著作论证详密,在这些方面都表现了突出的优长。到了近代,分析的研究方法导致实证科学的突飞猛进。中国传统哲学中,亦非完全没有分析思维,但只是初步的、简略的。”[8](P16)“中国人老是满足朴素的辩证法,而对形式逻辑缺乏兴趣,因而使得这种辩证的观念容易流于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可以以辩证法的语言为外衣,搞居阴为阳的权术,掩盖乡愿的处世哲学。”[10](P52)这一缺陷势必影响先人对逻辑问题的思考,使得先人的逻辑思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思维方式固然在某一民族思维中长久稳定地发挥作用。但人们完全有能力自觉地对自己的思维活动进行调整,校正传统思维模式的不利倾向。
为了克服这种逻辑模糊性,我们就要大力变革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就需要对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思维中的过分注重和谐性及直观模糊性的特征加以改进,同时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注重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的有机结合。
具体而言,一方面,正确认识矛盾对立双方间既同一又斗争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又相成的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与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过分注重矛盾双方间的同一性,而刻意忽视矛盾双方间的斗争性,对于事物的发展、创新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整体上直观地把握事物,而是要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深入到事物内部,对组成事物的要素进行细致分析,如此,才能够由最初对事物的直观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指导实践,加深我们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学习西方的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一方面,致力于辩证思维的条理化,另一方面,致力于分析思维的精密化。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的改造,应是进一步实现辩证思维与分析思维的统一。”[8]“我们所主张的是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联手,并不认为辩证理性‘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主张它应当也是可分析的,应当去除不必要的神秘感。我愿意牢记分析哲学学者张志林的警句:辩证法不应该成为思想懒汉或空谈家的避风港!我引申道:辩证法应当经受得起分析哲学家的批判性分析。我又赞成逻辑学者张建军的理念:精致的语义分析与逻辑分析并不排斥辩证理性。我最想说的是: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立。在进行语义分析与逻辑分析的过程中,知性分析与辩证分析二者应当有机结合起来。”[11]
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不仅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且具有历史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在充分发挥本民族辩证思维优越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进和提高,以期促进本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完善,为人们提供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思维方式。
上述两点都是今后的研究方向,如若能够把这一研究进行下去,不仅会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从新的角度展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而且对促进本民族思维方式的变革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我们从中国逻辑史的角度探讨先人辩证思维对其逻辑思想的影响,挖掘中国古代时期辩证思维的朴素性所在,进而改进完善它,就是期望在现代社会充分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越性,从而为整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2]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余雄.中国哲学概论[M].高雄:复文出版社,1991.
[5]〔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彭燕韩.国学精华与辩证法之“和谐对立交替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7]崔清田.名学与辩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8]张岱年,成中英.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9]闫顺利,赵雅薇.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思想论析[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9).
[10]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桂起权.“辩证二十一事”之解读:分析理性要与辩证理性相结合[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12,(2).
责任编辑:魏乐娇
The Influence of Pre-Qin Period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Pre-Qin Logics
LIU Qi
(Tangshan College,Tangshan 063000,China)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one of significant features in ancient Chinese thinking modes,which is a usual way of thinking that ancient Chinese use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e-Qin forensics,the influenc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on forensics can be seen in the process of debates. The scholars at Pre-Qin period chose debating methods or skills per the counterpart’s situation,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to achieve good effect. The study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mode,on the one hand,is good to show the full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extend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on the other hand,it is good to change people’s thinking mod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s logic thinking.
dialectical thinking;Pre-Qin period;forensics
2016-04-14
刘 琪(1987-),男,河北唐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逻辑史研究。
1004—5856(2017)02—0017—07
B2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