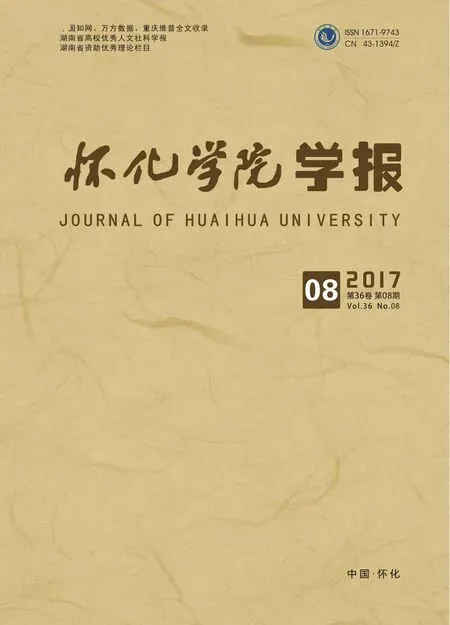先秦儒家“止”思想及其内在矛盾
杨学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先秦儒家“止”思想及其内在矛盾
杨学建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止”是儒家哲学体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见于《大学》、《周易》、《论语》等儒家经典文本之中。“止”大致有“停止”和“至于某处而不迁”两种含义,前者反映了儒家适时而动的处事原则,后者体现了儒者对于“止于至善”的追求,此外“止”概念所包含的规定性与儒家的“礼”相通。“止”的两重含义能够打通“中庸”、“仁”、“至善”等儒家核心概念,但“止”概念所内含的知与行、礼制的可行性、止于至善的追求和止于经典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不可忽视。
止; 中庸之道; 礼; 至善: 内在矛盾
一、“止”的文字学及哲学内涵
“止”在古代典籍中出现和使用甚早。许慎《说文解字》释义:“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许曰:出生根干也。”[1]523可见,“止”的本义为“根基”;宋代编纂的《广韵》释“止”为“停也,足也”,与今义大致相同,都有动作停止的意思,尤其强调与“足”的动作有关,与“行”相对。此外,根据《康熙字典》的释义,“止”还有以下含义:1.静,如“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1]523。2.已也、息也,即停止,如“止吾止也”[1]523。3.心之所安为止,如“安汝止”[1]523。4.留也,如“止子路宿”、“不可止而止”[1]523。可见,“止”字虽因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使用而含义稍有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有“到达,止步”的含义。
据统计“止”字在《十三经注疏》中共出现571次,其中《论语》8次,《周易》24次,《诗经》122次。可以说“止”在儒家思想体系中虽然不能同“仁”、“礼”等核心概念相提并论,但依然具有特殊地位。后世儒家对“止”的阐发可分为以下几个路径:(1) 历代注家对儒家经典中“止”的注解,这些注解往往结合具体的章句,侧重于字义训诂,是对整体文本的辅助;(2)宋代理学家对“止”概念的阐释和发挥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范仲淹以及周敦颐、张载,他们以《周易》为研究对象,高度重视六十四卦中艮卦的“止”的内涵,也即“艮止”思想。范仲淹在其《易义》中认为“艮止之道,必因时而存之。时不可进,斯止矣”,强调“止”与“时”之间的密切关系[2]137;周敦颐的修养工夫主静,他说:“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也。其道也深乎!”[2]494发掘“艮止”内涵为其主静工夫提供理论依据;张载则另有切入点,他十分注重研究“艮止”所含的“光明”之意,有“艮一阳为主于两阴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势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则名之义也”之说,从象数的角度分析艮卦与“止”之关系[2]734;(3)以明代学者李材为代表,着眼于《礼记·大学》文本中的“止”概念,提出“止修”的观点,而所谓“止修”便是通过修养工夫止于本体之至善;(4) 以明代学者黄绾为代表,将《大学》之“止”与《周易》的艮卦之“止”相结合,把“止”看作自然和人世运行所体现的理则,世间万物纷繁复杂,运行不已而各得其所的根本原因是万物有所止,对于学者而言为学之道就在于“知止”[3]143。笔者认为以上各家均有独到见解,但是多阐释了“止”之一面而未作全面分析,例如周敦颐认为止、静同义,这未免有失偏颇;另外各家以“止”为切入点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难免偏离“止”概念在早期儒家文本中的内涵。笔者认为儒家典籍中,除了《诗经》中作为句尾语气词的用法比较明显之外,“止”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为“停止”,强调“停止正在做的事情”;二为“止于某处而不移”,含有“固守”之意。本文意在探讨“止”的双重含义以及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沟通其他核心概念的纽带作用。
二、“止”思想在儒家哲学体系中的体现
对儒家“止”思想的理解不能仅从其文字层面着眼,事实上在先秦儒家文本中“止”极少单独出现,儒家学者也极少对“止”作专门的论述,这是因为“止”常与“中庸”、“礼”、“至善”等儒家核心概念相呼应从而体现儒家的哲学思想。
(一)“止”与“中庸之道”
“止”作为“停止”之意,与行动相对,但两者又紧密相关,有行必有止,有止必有行,这本是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但是儒家敏锐地察觉到了“何时当止,何时当行”的问题。《易·艮卦》有“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4]281;《周易注疏》将其解释为“凡物之动息,自各有时运。用止之法,不可为常,必须应时行止,然后其道乃得光明也”[4]281。这一注解道出了行、止之间分水岭,以行为先、为常态,迫不得已,无法行时,才能止。可以说,止是行的一种辅助形式。那么这道分水岭究竟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就在于“时中”。
“中”的观念由来已久,《尚书》中即有帝尧传授帝舜“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心诀的记载,而“中”与“庸”的结合,则是孔子的创造,“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5]18,足以体现“中”作为方法论的普适性。而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中”可以被理解为普遍的标准,但是它并非来源于思想家的凭空想象,更不是哲学家运用概念构筑的理论教条。“中”的内涵很难被准确概括,因为对它的把握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情形之中,在各种选项之间确定一种最合适的方式。对“中”的体认和把握被儒家看作是君子得一种品格和能力,也是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之一。求“中”要求根据一时一地的情形作出适应,因事而动、因时而变,所以求“中”必须要对时空有所关切。
“时中”不仅仅具有时间上的恰当性,更指向限度,它不仅表示外在事物的尺度、限度等规律性的特征,更重要的是道德主体对于自身使命的自觉和践行。所以“时止时行”不仅仅在于对外界环境有敏锐的洞察和预见性,更要关切主体本然的行为风格,而行为风格则是内在心性的显露。儒家法天道,“与时偕行”这一方向本身就蕴含着向前发展的刚健动力。所以“时止时行”明显以“行”为前提,直到难以前行的时候才选择止步,当然必要时也有例外,那便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行、止关系与曾子所谓“死而后已”有相同之处,它们的实现均需要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无疑可以追溯到孔子所言的“天”。在孔子看来,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的终极来源,亦是人之行为的根本保障,人之生命历程的意义便是将“天之所予我者”在人世间努力地发挥,最终到达修养的至高境界,这即是“事天”。由于君子的求道任重道远,所以将求仁、行仁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恢弘刚健的意志力便是士君子所应葆有的诸多品质中的重要成分。何时该止、何时该行,这一合理性问题全在于行为主体自身的把握,非有充分的道德自觉而难以实现。所以在儒家方法论层面,相对于“行”这一常态化的方式,“止”似乎有些迫不得已,它可以被看作“行”的过程中受外界限制而采取的暂时妥协的形式。这种外界限制儒家称之为“时命”,它是一种外在于行为主体并对主体行为有很大影响的客观因素,主体对其难以把握也不能避免。唯有这种情况出现,采取“止”的态度和方式,暂时收手以等待时机不失为一种明智而正当的选择,除此之外的“止”的情形便有可能是主体自身的故意堕落,即孔子所谓的“自画”,也就是自己画地为牢,不愿有所作为。
由此可见,中庸的处事方式虽然于各种情形之间灵活变化,但其中却不乏严格的规定性。失去了对于天所赋予的道德使命感的自觉,主体便有可能完全顺遂一时一事而不知所归,缺乏了“行”这一前提的“止”是没有意义的,必然陷于静止以至于消亡;缺乏了“止”这一调和形式的“行”也难免因为过分刚强而鲜有恒久、普遍的适应性。唯有对自身道德感有真切的体认,明确道德使命意义上的“当止之时”并能使之作用于实际的选择之中,既遵循内在的道德尺度又能对主体所处的真实情境有所洞见,才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要求。
(二)“止”与“礼”的关系
礼制视野下的“止”首先与儒家的人性论有关。儒家承认人性向善但同时并不否认外在环境对于人之心性、好恶的影响。儒家尊重人的正当的物质需求,认为人们关于“饮食男女”的欲望是非常自然、不该苛责的,然而对于过度或不正当的欲求儒家则予以批判和摒除,所谓“克己复礼为仁”正是明确礼与非礼之间的界限,自觉回复到礼所规定的正当范围内,它的具体条目即体现在对于学者视、听、言、动等诸多日常行为的要求中。心体不得其正,由其所生发出的种种情绪都难以恰当,这种不合宜情绪的外化便是各种不当的行为,也就是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的原因。所以《中庸》要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5]18,从内在心性的发动处即作出某种防范,为了使心性发用“得其正”,君子必须“慎其独”,因此这是一种强烈的道德自律性。
而对于心性的外在表现,儒家倡导以“礼”来约束,所以“礼”是引导人们向善的外在规范,从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理解为指导人们的行为该“止于何处”。《诗经·相鼠》中有“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一句,将止、礼、仪三概念并举以说明“止”与“礼”的相通之处;另有《周易注疏》中将《节》卦训为“止,明礼有制度之名”则说明节、止二字在《周易》中均有“节制”之意,这种节制便是礼的特征。礼乐被作为社会治理手段是周代统治者的创造,对周代乃至后世的社会管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朝的礼制等级明确,不同阶层的人应该遵守相应的规范,不同等级的人各就其位并安于其位,在各自的本职上尽心尽力。但春秋时期周王朝衰微,整个社会陷入礼崩乐坏的无制度状态,处于当时社会大环境并向往周代政治制度的孔子在思考挽救社会颓唐的出路时自然生发出恢复周朝礼制的愿望。“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正名”而“兴礼乐”,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条理化、制度化,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和施政策略。因而对“礼”的理解和把握就成为了儒家学者重要的学习内容,遵循礼制便成为儒者行为处事的重要规范。荀子认为学者的学习目标在于对“礼”有深刻的认知并能自觉遵守,而“明礼”也是道德修养达到极限的体现,这种观点正是着眼于“礼”对于个人修为和社会治理重大意义。
《论语》中有齐景公问政,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答,作为作为君臣、父子就应该按照各自应有的行为规范来行事,那么应该遵循何种规范呢?《大学》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朱子注解: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5]5。“君臣父子国人”五种角色是一个人处于家庭、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要承担的不同责任,五种根本的角色一旦确立,人伦关系便有了规范。“正名”被孔子看得极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5]143。名实不存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因而要积极防治名实错乱的情况发生。《大学》所阐述的五种主要社会角色之“止”可以说为维护名实关系提供了一个维度。这里的“止”有两种意味,一为“行而止”,即处在社会生活中的成员应该努力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一系列的修养功夫,使自己的品德行为等方面与自身角色相适应,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就积极的一面而言;二为“止而勿过”,在认清个人角色之后就应在本角色之内努力完善自身,实现自身在本角色范围内的“至善”,而不应该有某些超出该角色规范的不良企图。儒家不反对人的积极进取,但是更强调个人行为与所处地位的符合。所以《诗经·文王》有“穆穆文王,於辑煕敬止”,所谓“敬止”即“言其无不敬而安所止也”,便是要心安于所处之位而无所僭越,文王虽然具有推翻商王朝的道德优势和实力,但是仍然固守作为臣子的本分[5]5。《易·艮卦》中所谓“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要求把个人注意力止于其位,同《论语·泰伯》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看,在其位则要谋其政,足可以看出儒家对止于其位、尽其位的重视。
儒家对于“止于其位”的关切一方面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建设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和儒家的修养观念有着很大关系。儒学是“为己之学”:学的主体是学者自身,学的过程要自己经历,学的目标是自身境界的提升,所以学者自身在求学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指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无论在何种境遇,君子都能够坚定不移地落实对“道”的追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5]24。儒家注重“治国平天下”的事功和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但是儒家最根本的超越理想却并不完全唯政治等级标准是瞻,而更倾向于通过政治事务的处理来完善自身的境界提升,这种超越更多的是德行的完善。
(三)“止于至善”
“至善”是儒家哲学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也是儒家修养的根本指向。然而“至善”的根本内涵古今学者却则难以形成共识。朱子《大学章句集注》认为“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5]3,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至善”并非某种实体,它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待于修道者努力去获取的东西,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与其说外在于人需要人的修炼才能得到,不如说它正发生、内含于人的行为方式之中。从横向上来讲,至善兼顾“明德”与“亲民”两个方面,其中前者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终达到通晓天地之道的圣人境界。从修养工夫层面上看它偏向于内省、主静,而“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可以说是这一循序渐进的路径的具体展开[5]3。
而从纵向上看,以“至善”为目标,则“止”倾向于工夫,此时之“止”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止”意为“知”,有理解并选择之义,“止于至善”首先要确信有“善”的存在,进而以求善为己任。《大学》以“止于至善”为“三纲领”之一,而“三纲领”着重强调境界论,具体的修养工夫则在于“止、定、静、安、虑”这一过程的展开和作用。“知止”即是知“以止于至善”为终点;其二、“止”还关涉“善”之完成后的持守,这一层面的止便是“固执”之意。固执意味着对善的恒久的涵养而不至于丧失,使善真正内化为学者的自身原则和品质。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来看,“止于至善”实际上包含了境界与工夫两个方面,关涉“求善”和“守善”两个阶段,也就是“择善固执”。“择善”表明人对于“善”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儒家虽确信人有“善之端’,但“善之成”却需要在经验生活中通过后天努力加以扩充;“固执”则是对“善”有真切体认后的态度。根据傅佩荣先生的理解,“固执”有三大要点:择善之后应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践行,不懈怠也不后悔;随时斟酌权变问题,因为“善”根本就不是只凭主体单方面就能够实现的,它要求内在原则和外在情况的和谐一致;必要时“固执”不惜牺牲个人生命[6]73。“固执”本身即非易事,它需要学者具备坚韧不拔、安贫乐道的有恒精神。孔子曾感慨“固执”之难——“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5]69,在道德追求和现实诱惑之间仁者能够始终保有求道的热情而不动摇。与这种态度相一致,孔子对得意门生颜回的看中,正是因为他“其心三月不违仁”的有恒精神。“固执”最重要的是遵循内心的原则,也就是“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5]70。唯有这种自觉才能产生巨大的道德信心。然而仅仅做到有恒只是“固执”之一面,它体现着对于理想信念和修养目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但是在具体的实现路径和方法上,则依然要注重权变。孔子曾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5]99。有恒者固守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而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此便接近善人,两者之间细微的差别便在于是否能够考虑权宜问题。善人(或君子)有意识地同环境和谐势必要对某种情势作出选择,因为他实在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这不仅由于君子所承担的社会职责(教导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等),更在于君子对自己道德使命和所选道路的认同。
“止”所承担的双重内涵并不矛盾,因为双重内涵是儒家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反映。“止”作为“固守”之意讲,强调儒家在道德方面的追求,具体地说是就是决不放弃不断修德的理想,持之以恒地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儒家讲求内在超越,所以修德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在这一层面上儒者任重道远,所以止于此事业、坚守此事业是题中应有之义;就儒学所关涉的另一个方面即社会和政治领域而言,“止”的内涵更侧重于“停止、止步”,但这并不代表懈怠和消极。行、止之间“度”的把握是儒家极其重视的内容,这个“度”既是自然社会的规律性以及客观具体的实际情况,更是儒家在义利之间所更注重的“义”。义即宜也,强调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唯有合理的事情才是君子应当放手去做的事情。正是这两层内涵的两相关涉和统一才使得先秦儒者能够既有坚定的求道信念同时能够在具体的行政和处理人际问题方面张弛有度。
三、先秦儒家“止”思想的内在紧张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由“止”这一概念连接的儒家思想不外乎修德和行事两个方面,修德要求止于至善,择善固执;行事要求时止时行,讲求中庸之道。两个领域并行不悖,足以为儒者提供境界和工夫上的指引。但是也不难看出,对“止”概念所内涵的限度性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并非易事。一方面,修德的固执精神如果运用于行事,则难免不合时宜,但行事如果没有内在道德感作为规范,往往流于虚妄;另一方面,行事的“时中”原则不适合作为修德这一漫长事业的方法,但修德并非只是对心性的主静涵养,亦需要在时时事事中得到体证。所以目标与路径、知与行之间的内在紧张便展现开来。
(一)“知其所止”与“行其所止”
“知其所止”与“行其所止”本是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其所止”的道德约束和“时行时止”的行事原则为道德主体的行为提供原则和合理限度,儒者在遵守大的道德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较为从容地进退,因此“止”和“知”的目的是更好地“行”,荀子所谓“学至乎行而止矣”将“行”作为“知”的归宿和目的,两者是不应支离开来的统一整体。但是后儒往往将两方相割裂,或者只是盲目地做事,而未首先树立内在的道德尺度和内省机制,使行为肆意荒诞;或者只是专注于理论研究、着力于心性修养而不肯着实躬行,即使着手实干也往往拘泥于陈规而不合时宜。在这种情况下先秦儒家所倡导和致力的“内圣外王”的修养理想便难以实现。这一割裂被陆九渊、王阳明等心学家察觉并在理论上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可是阳明后学以“本心”作为德性标准而自作主宰,极易导致人性中天然、本能的一面的过分膨胀,从而突破理欲之大防。正是洞察到这一威胁,李材等明代学者重新倡导儒家修身为本、止于至善的传统。从止、行之间这样一种反复博弈的过程来看,如何把握两者的关系,真正实现儒家的理想状态“中”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原则问题,更关系到儒家的学术风格和走向。
(二)追求至善与止于经典
儒家以“至善”作为修养目标,但“至善”的内涵和维度却不易被学者理解和把握。由于“至善”或“道”绝不能用某种具体的学说和概念加以定义,也不可能指出一条明确的途径,世间所有求道者都能够沿着这一路径、遵循这一法门修炼成君子。但现实问题是,修道这一事业本身不可能盲目,它需要一定的指引和路径,所以儒家不得不把“至善”境界具象化,这一方面是以三代君王和孔子为代表的圣人,一方面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圣人的特征可用“仁且智”来概括,既具有完满的道德,又具有极高的知性。在儒家学者看来,圣人已经对宇宙人生的所有领域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精微的答案,后来者只要遵其道而行。中国古代尤其是儒家的学术发展就是在“发前圣之所未发”的范式中进行的。在学术研究方面,“我注六经”以儒家经典为蓝本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形成“经-传-注-疏”的诠释体系;“六经注我”虽有学术创见,但仍要引经据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有时不惜断章取义,最终演化为“代圣人立言”的表达形式;在学术传承方面,儒家学派道统意识十分强烈,从先秦时代的孟、荀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到唐代韩愈正式提出“道统论”,以至于宋明理学内部的学派之争,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便是是否合乎先儒纯正的哲学观点,否则便有异端之嫌,无怪乎古文学家皮锡瑞曾言:“盖凡学皆贵求新,唯经学必专求守旧……世世递嬗,毋得改易。”[7]139求道和治学以圣人和经典为所止之至善,虽与后儒未能洞察先儒思想精义所致,但也不得不归咎于以“止”为表征的儒家修养论和方法论之间界限的模糊。更有甚者,若将尧舜等圣人之道作为完满、至善的学说,则难免产生一种偏执心态,从而拒绝了抵制其他一切意见中相左的观点。这种倾向在先秦荀子便已有端倪,“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8]394一旦道德理想与具体的人格特征甚至个人相比附,便极容易导致狭隘的“卫道”观念,甚至导致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人的崇拜。而到了汉初倡导“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更是认为“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9]35汉代以降,圣、君结合为最高统治者一人,儒家之“道”屈从于政治权力之“势”并为其服务,在这种封闭的求道环境下很难说会有更具创新性的理论创建,而在此观念支配下的修道者亦不过是圣人盲目的拥趸。
(三)礼治与道德自觉的矛盾
以“礼”作为社会规范的德治模式区别于以刑、法为治理手段的法治模式,这种社会模式良好运行的条件不是民众因畏惧刑罚、暴力的服从而是他们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觉。“安于其位”的态度并非受外界政治压力而采取的被动措施,而是主体的自愿行为。君子能够“止于其位”无非是因为他的道德修养和价值理性已经使其达到了适应诸多外部环境并将对逆境的体验转化为精神愉悦的满足感,这便是后世学者所谓的“内在超越”。但是社会的运行不仅仅只有君子得参与,更重要的还是要着眼于占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存在方式。修己、安人、安天下的治理之道不仅仅需要在位者端正自己的德行,更重要的是民众能够自发响应,“草上之风必偃”这一政治构想的先决条件是民众道德水准的提高。儒家虽坚信人心向善,但也隐隐察觉到诸如“未见好德如好色”的人性的消极方面。教育能在一定水平上促进民众的道德自觉,但是往往只能实现民众对于政令的了解和遵守,而期望达到所谓“自得”的理想状态,确实并非易事。
结语
综合以上诸多方面来看,以“止”概念作为节点能够联通起儒家思想中诸如礼、中庸之道和追求至善等重要方面。而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决定了“止”绝非被动地接受外在压力的束缚,“止”的动力来源于人理解、选择、坚守“天”所受之于人的使命感,“止”的分寸以内在的道德自律和外在环境的双重作用为依据。唯有主体对其自身以及所处的周遭情形有深刻的认识,才能自愿地在当止之地止,在当行之时行。“时中”的实现及其灵活性必须要靠以“守死善道”的自律和以“礼乐”为代表的外在他律为边界和尺度。这正是儒家哲学最精微的内容之一,但同时也是发展史上反复博弈、儒家学者难以拿捏好恰当火候之处,当然也是我们应该给予极大重视和警醒的地方。
[1]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2]黄宗羲,等.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张学智.明代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郑玄注,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7]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王先谦,撰.荀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9]董仲舒.春秋繁露[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
Confucian Idea of“Zhi”and its Inherent Contrac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YANG Xue-jian
(School of Philosoph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Zhi”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system,which scattered in The Great Learning,Book of Change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other Confucian classic texts.“Zhi”roughly has two kinds ofmeaning,namely“stop”and“for somewhere notmove”.The former reflects the Confucian timely and moving principle of doing things;the latter embodies the Confucian pursuit to“strive for perfection”.Besides,“Zhi”contained in the concept of rule and the Confucian“Rites”connected.Doublemeaning on“Zhi”to open zhongyong,benevolence,perfection and other core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But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pursuit of etiquette feasibility,striving for perfection and sticking to the classics can notbe ignored.
Zhi;Zhongyong;ritual;the supreme good;inherent contraction
B22
A
1671-9743(2017)08-0042-05
2017-07-09
杨学建,1993年生,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儒家哲学、中国管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