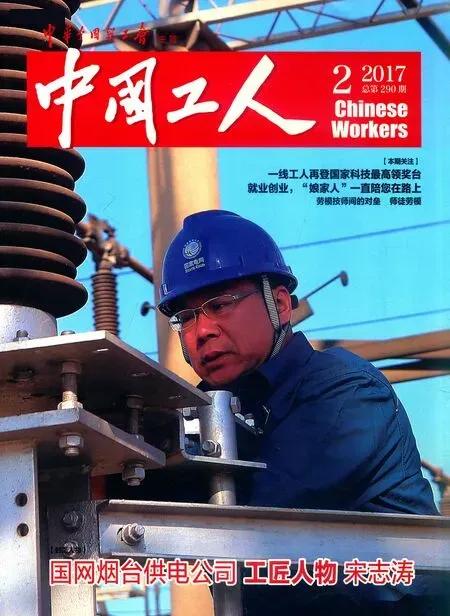深圳城中村镜像:那城那村那人“来了就是农民工,买房才是深圳人”
■粤人
深圳城中村镜像:那城那村那人“来了就是农民工,买房才是深圳人”
■粤人
2016年8月26日,是深圳建立经济特区的第36周年。过去三十多年,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曾聚集此地,用青春、智慧、勇气和汗水缔造了“深圳速度”和“财富神话”。距离深圳“世界之窗”——一个知名的微缩景区不过一两公里,城中村白石洲是另一个世界。密密麻麻的巷子里是密密麻麻的楼。不少楼间距只够一个人通过,从楼里伸出的电线和网线在楼外缠绕交错,纠结成半空中的一片蜘蛛网。这里有深圳规模最大的“农民房”。
根据2015年的调研数据,白石洲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下了2527栋出租房,有约14万人在此生活居住,其中外来流动人口为12万人。如今,深圳的高房价令外来工头疼,这座曾以“包容”著称的城市,是否仍向他们敞开大门?
房东吴子仪:支持城中村改造
“大量和集中建房就是90年代末和2000年左右,五湖四海的人来了,外地人口增容有住房需求嘛。农民也没有地了,要依靠出租来生活。”吴子仪说。
吴子仪是本地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白石洲。如今,他在白石洲村拥有一个小庭院,里面四栋楼,几十家租户,他每月房租收起来有六位数。
1997年,土地出让、转让市场化和住房商品化同时进入加速轨道。白石洲仿佛城市中的一个岛屿。商业综合体、高层写字楼、高尔夫球场、花园小区公寓……城市在扩张中挤压了村民的生存空间,却也让他们看到了致富的新出路——建房。
1999年, 深圳 启动了大规模违法建筑拆除活动,白石洲“抢建农民房”的高潮期到来了。“大家都觉得只要建了都能租出去。家家户户都在抢建,实际上是不好管。”吴子仪说。他形容当时的情景“也是很艰难,像打游击一样”:总有人来查,但管了东边管不到西边。停水停电的举措也常有,还是挡不住大家先把新楼地基打起来的热情 。新建的楼大多在七层以上。为节省土地,建筑间距被牺牲,“握手楼”因此形成。平面设计上,两室或三室的房型也不再适用,单户或一室一厅更多,一层可分好几间单独出租。
深圳市规土委资料显示,白石洲自2014年就已列入城中村旧城改造范围。从实地情况来看,已有两个工业区被拆除,但大部分的民居还未动工。
吴子仪是赞成白石洲改造的,觉得这里脏乱差、没有规划。他说:“租户没有这种条件就去别的城市啊。”
司机柳庆:20年的深圳梦
其实他的“正职”是网约车司机。每天早晨7点起床后,他送孩子上学,然后就去跑车,一直忙到晚上9点。柳庆在白石洲住了近二十年。这里楼挨着楼,室内光线昏暗,加上室外密如蛛网的电线网线,显得加倍压抑。
柳庆1998年搬到白石洲,两年内从石棉瓦房住进了“握手楼”,起初因为没有暂住证,总要东躲西藏,开的旧货买卖铺也总被警察查。“收容所我进去过三次。”他说。
在来到深圳后的第19年,柳庆凭借计算机高级职称申请到本地户口,他希望接下来申请到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一套保障性住房:“来了就是农民工,买房才是深圳人”。但是,他很犯愁:“我有个朋友,申请了三次保障性住房,都没申请到,系统里怎么个算法也不知道。他都交了十多年的社保,我社保才交了六七年,希望不大吧!”
“这些年,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最难过的就是还窝在这儿,也没混出多少出息。”回顾来深圳的二十多年,柳庆感叹道。他的老家在湖北农村,1994年经老乡介绍,来到深圳打工:“老乡们经常说嘛,都说深圳特别好。”
房产中介杨善庆:买不起现在的房子
杨善庆来自安徽,是一名房产中介,已经在深圳买了房。2005年,他一头扎进了房产中介行业。2009年,他在距深圳90多公里的惠州买了一套房,每平米两三千元;2011年他又在深圳买了一套,时价一万出头。如今两套房价格都已翻了四五倍,“跟我一样做房地产的,谁身上都有两套房”,他说起来却是云淡风轻。
杨善庆以6500元每月的价格出租在南山区的房子。他自己则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在白石洲租了套两房一厅的小区房,月租4000元。差额刚好用来还贷。
其实他已经年薪百万。近两年深圳房价暴涨,他手上去年卖出近40套房,佣金就赚了好几十万。
杨善庆初来深圳的那几年,房价还没有涨起来,生活成本也不算太高。而现在他觉得深圳房价快到顶了:“一套房子就凭你那工资……一句话,绝对买不起!从零几年到现在,从几千到几万,翻了十几倍了。”

清洁工李阿姨:最后还是要回家去的
早上九点之前,李阿姨就要完成科技园写字楼里的清洁工作。
六年前,李阿姨经老乡介绍从四川老家来到这里,除了清洁工作,还负责为附近一家美发店做午饭和晚饭,顺带洗毛巾。两份工作加起来,每个月有四千元左右收入。她很满足。
比起十年前在家里务农,她说如今的工作还算轻松,每天下午和晚饭后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前几年,她和丈夫靠打工赚的钱在老家盖了房,每年春节都回家过年。她挺喜欢深圳,但落户、买房这些事她从不敢想,那是“城里人担心的事儿”:她说: “打工最后还是要回去的。怎么可能不回去呢?”
白领傅俊:从不后悔来深圳
早晨八点半,209路公交车缓缓驶入白石洲站。等待的人骚动起来,距离远的以百米速度赛跑,车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傅俊举起手机默默拍了一张照,附上评论:“又没挤上去。”
在傅俊看来,白石洲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他和两个朋友合租两室一厅的农民房,分摊2800元的月租金。他现在拿五六千的月薪,打算等薪水再高一点,就搬去环境好一点的小区房。
两年内傅俊换了三份工作,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一度全身上下只剩两百块钱。偏巧遇上发高烧,医生说要打吊针,医药费要256元。傅俊问医生∶“我先付一针的钱,打一针行不行?”一针140元,当天高烧退下去了,他就没去打第二针。
即便是这样,他也没后悔来深圳,更没想过要回去:“如果我没有来,混好混坏就那样得了。但是我来了,混不出个样子我不会回去。”傅俊说,他接触了不少相对年长和有本事的人:“要是还在老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他的计划是,月薪达到三万的时候,就在深圳买房;但如果35岁之前还买不起,大概就只能回老家。他认为,拥有一段青春奋斗的日子,总是值得。
晨曦
每个周六的早晨,傅俊都会去楼下的肠粉店叫一份五块钱的肉蛋肠粉。老板是一对潮汕小夫妻,见他来,熟络地打个招呼,端一份上桌。“汤不够,太少啦。”傅俊理直气壮地抱怨。老板不声不响地抄起勺子,多浇满满一勺。
“你可真不客气。”
“熟嘛。我都可以在这边赊账吃一周。”傅俊笑笑,有点小得意。
此时,餐厅夜宵生意结束后的小白可能刚睡下不久;周末不用去写字楼打扫卫生的李阿姨也可以睡个懒觉;吴子仪多半在和妻子女儿以及好不容易周末回家的儿子共进早餐;曾峰正匆匆赶往公司和老板开周末高层会议;杨善庆大约已走在带人看房的路上。
许许多多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又开始了新的一天。他们沐浴着晨曦,期望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