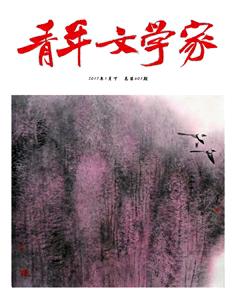唐华清宫词与骊山温汤里的爱恨情愁
郭苗苗
课题项目: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011)。
摘 要:在唐华清宫词及同题材诗中,以骊山温汤为诗题者约有30首,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侧重于歌功颂德,书写皇家大气风范;后期则可大致分为情诗、讽刺诗、祸水与反祸水诗三大类,主要因唐王朝由盛转衰而引起,表达诗人或感慨追忆,或讽刺批判之意。
关键词:唐诗;华清宫词;骊山温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02
唐开元初,玄宗励精图治、选拔贤才,且天下太平,出现“开元盛世”的光景。开创盛世之后,玄宗自得其乐,逐渐沉溺于享乐之中,这一时期的骊山温汤诗在文风上集大气富贵于一体,诗作类别主要以“美诗”为主,情感则侧重于歌功颂德,书写皇家风范。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势陵夷,生活于中唐前期的诗人,大多身经从安定繁荣到灾难迭生的沧桑巨变,这一时期的诗作在形式内容、情感态度、意象使用、写作技巧等方面较前期都有了重大转变,而骊山温汤则是所有事件的缩影,现根据主旨及情感基调将乱后的“骊山温汤诗”大致分为情诗、讽刺诗、祸水与反祸水诗类。中晚唐诗作中,有不少歌颂李杨爱情的佳作,且将其归为情诗类;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诗人在发追怀盛世繁华之音的同时,也不乏批判李杨二人之作,且将其归为讽刺诗类;而文坛上历来对杨贵妃的评价褒贬不一,且将其归为祸水与反祸水诗类。
一、且吟盛世之歌
骊山温汤诗中的“美诗”以彰显皇室风范的“应制诗”和再现大唐盛世的“乐舞诗”为主,前者以歌功颂德为主要感情,少数也述及对皇帝的期望。如钱起《温泉宫礼见》有云:“新丰佳气满,圣主在温泉。云暖龙行处,山明日驭前。顺风求至道,侧席问遗贤。灵雪瑶握降,晨霞彩仗悬。沧溟不让水,疵贱也朝天。”以玄宗在温汤的悠闲之象衬托出大唐的安闲稳定,而韦应物的《骊山行》“开元至化垂衣裳,厌坐明堂朝万方”,以及杜甫《忆昔二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等诗句,则是在乱后对开元盛世进行追忆以及赞颂。诸如此类的诗都以写景或事为表,而抒颂德之情,该类型的诗还有李乂《登骊山寓目应制》、张九龄《奉和圣制温泉歌》、李白《清平调三首》等。
“乐舞诗”则表欢愉之象,再现盛世光景。如杨贵妃有诗《赠张云容舞》:“罗袖功香香不己,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和阶也边初拂水。”写云容舞“霓裳羽衣”似仙子,而张祜《春莺啭》“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己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写贵妃舞《春莺啭》时的婀娜多姿、轻歌曼舞,最惹人注目的“乐舞诗”当与玄宗梦游广寒宫所作《霓裳羽衣》相关,比如王建《霓裳辞十首》、鲍溶《霓裳羽衣歌》、李太玄《玉女舞霓裳》等,而李商隐在《华清宫》中更云:“朝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曾在元和年间观赏宫中乐伎表演此舞的白居易于宝历元年作《霓裳羽衣歌》,生动地描述了霓裳羽衣舞由服饰、乐器伴奏到具体表演细节,玄宗在众多舞曲里尤其钟情于“霓裳羽衣”,以致日后重返长安仍对此曲念念不忘,如《长恨歌》云“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二、静听缱绻之情
唐骊山温汤诗中,情诗占其大部分。骊山温汤凭借其独特的优势成“宠儿”,“甲子,幸郿县之凤泉汤。十一月己卯,至自凤泉汤。乙酉幸新丰之温汤……甲午,至自温汤。”[1]而白居易《骊宫高》在盛赞骊山风景秀丽时有言:“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迟迟兮春日,玉甃暖兮温泉溢。”而唐众温汤中,唯有华清为第一,华清池水是从骊山中流出来的温泉水,常年温度保持在43度,极适于沐浴且具有保健疗效,如李隆基在《幸凤泉汤》中提及“阴谷含神爨,汤泉养圣功。益龄仙井合,愈疾醴源通”,而张说《奉和圣制温泉言志应制》也云:“起疾逾仙药,无私合圣功。始知尧舜德,心与万人同。”
位于骊山脚下的华清宫是唐帝王游幸的别宫,“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式的爱情更为其增添一份缱绻。如张祜《太真香囊子》“蹙金妃子小花囊,销耗胸前结旧香。谁为君主重解得,一生遗恨系心肠”,写玄宗佩戴杨妃所遗香囊,以表现二人的一往情深及脉脉温情,其《雨霖铃》“夜却归秦,犹见张徽一曲新。长说上皇和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写尽杨妃死后,玄宗的相思之感,而“龙脑移香凤辇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台若使香魂在,应作烟花出陇头”(黄滔《马嵬二首》其二),用假设法写用情至深、香消玉殒后的杨妃仍情系玄宗,于此《长恨歌》则写得更明白:“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夕诗是情诗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如权德舆《七夕》“家人竞喜开妆镜,月下穿针拜九霄”与林杰《乞巧》“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都记述唐代民间七夕之盛况。论七夕,宫廷自比民间富贵豪华,如王建《宫词》“画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镊采桥头。每年宫里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与此类似,和凝《宫词》云:“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嫔乞巧忙。总上穿针楼上去,竞看银汉洒琼浆。”而关于李杨的七夕,王建《温泉宫行》有云“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和李商隐《马嵬驿》“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都讲述二人于七夕时共看星河、山盟海誓的情形,《开元天宝遗事》载:“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2]
三、轻呢讽刺之篇
相较于氛围轻松的“美诗”,刺诗的情感基调则以沉重深思见长,此类诗作大都作于乱后,诗人历经开元之安定而转悲泣之乱世,面对而今衰败的昔日繁华胜地,缘事而发,有感而作。如张继《华清宫》“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叙写安史之乱前,玄宗劳民伤财、沉醉“温柔乡”,以致战乱爆发,如今所有悲恸都寄予这流不尽的温泉水,许浑《途经骊山》又云“闻说先皇醉碧桃,日华浮动郁金袍。风随玉辇笙歌迥,云卷珠帘剑佩高。凤驾北归山寂寂,龙旟西幸水滔滔。贵妃没后巡游少,瓦落宫墙见野蒿”,追忆前时而借机讽刺玄宗歌舞升平的生活,与张继《华清宫》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批判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则如韦应物于前追忆盛唐而后暗含讽意的《骊山行》:“干戈一起文武乖,欢娱已极人事变。圣皇弓剑坠幽泉, 古木苍山闭宫殿。缵承鸿业圣明君,威震六合驱妖氛。 太平游幸今可待,汤泉岚岭还氛氲。” 而《明皇杂录》记载玄宗幸华清池时的盛况:“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因复上闻,请各乘马。”[3]王建《温泉宫行》亦云:“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朝元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龙暖水。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鸡昼鸣宫中树。温泉决决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楼。禁兵去尽无射猎,日西麋鹿登城头。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讽刺诗,一方面,皆因对现实生活的失望,而批判当朝统治者,另一方面更侧重于对后世的警戒,如杜牧《过骊山作》“始皇东游出周鼎,刘项纵观皆引颈。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傍穷百姓。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直接明了地告诫统治者切勿胡作非为,否则只有“烧作灰时犹未枯”的下场。
诸如此类主题的讽刺诗还有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二“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早梅悲蜀道,高树隔昭丘。朱阁重霄近,苍崖万古愁。至今汤殿水,呜咽县前流”,又李商隐《华清宫》云:“朝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当日不来高处舞,可能天下有胡尘。”此外,吴融有《华清宫》同题组诗,各二首、四首。
唐骊山温汤诗中的“刺诗”除了批判指责玄宗骄奢享乐的生活之外,还有对其夺媳之行苛责。如李商隐《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揭露玄宗夺儿媳之事,对其违背纲常伦理之行表示愤懑,相比《骊山有感》的委婉含蓄,他的另一首《龙池》:“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则直接了当地交代了这种违背伦理之行,同时也批判了玄宗安逸奢靡的生活。
四、曲论祸水之章
“祸水论”题材在唐骊山温汤诗中比比皆是,“祸水论”指责玄宗因过度宠爱杨妃而误国误政。《明皇杂录》载“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李约《过华清宫》“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辇升天人已尽,故宫犹有树长生”,描述玄宗重生活淫逸、轻国计民生的下场,此外,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全诗以“荔枝”为题眼,表达对玄宗不惜耗费民力财力以博贵妃愉悦的不满与荒唐,又李商隐《华清宫》“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尖刻地将贵妃堪比褒姒。而薛能诗《过骊山》“丹雘苍苍簇背山,路尘应满旧帘间。玄宗不是偏行乐,只为当时四海闲”,点明并非玄宗偏爱行乐,只是因天下过于太平,而为玄宗的罪行开脱。《新唐书》载:“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4]则把女祸论批判得淋漓尽致。
唐骊山温汤诗中也有对贵妃深表同情、惋惜的诗,即所谓“反祸水论”诗。如温庭筠《龙尾驿妇人图》“慢笑开元有幸臣,直教天子到蒙尘。今来看画犹如此,何况亲逢绝世人”,赞美贵妃倾国倾城之貌,而非祸水。罗隐《帝幸蜀》云:“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时。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讽刺僖宗为避黄巢祸乱而奔蜀地,同时也借“阿蛮应有语”为杨妃“翻案”。此类诗还有韦庄《立春之作》“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關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徐夤《开元即事》“曲江真宰国中讹,寻奏渔阳忽荷戈。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尘惊骑透潼关锁,云护龙游渭水波。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等。
总而言之,蕴含在骊山温汤里的爱恨情愁,既是唐华清宫词情感主题演进的一个侧面,也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在诗坛上的一个聚焦点,它的情感起伏变化与大唐命运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64。
[2](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86。
[3](唐)郑处诲撰,(唐)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29。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