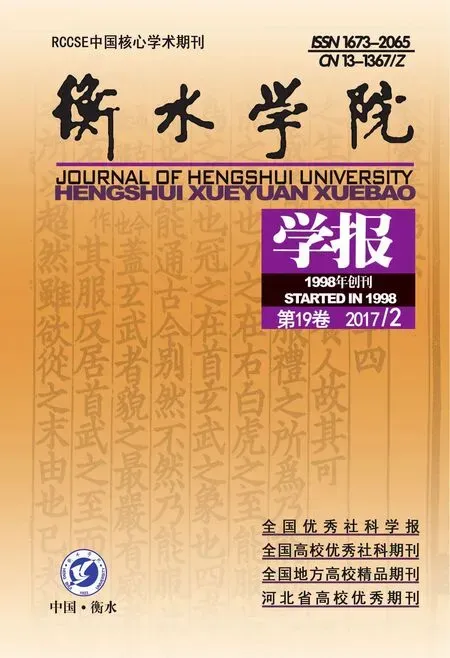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思想启蒙
刘建华
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思想启蒙
刘建华
(北京慧士德咨询中心,北京 100012)
如何以当代语境言说孔子,如何以孔子文本讲述世界,这是21世纪中国的学者和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要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笔者将这种不同于朱熹之前天下孔子的时代命题称之为“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并将这一命题归结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与思想启蒙,汇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宏大叙事,且视为当代学者的一项具有宿命意味的孔子式使命。
孔子;世界;文化复兴;思想启蒙
人类文明所有学问及其教育,无非就是为了复兴而启蒙;世界大学所有学者的使命,无非就是复兴和启蒙。问题只是:什么样的复兴?什么样的启蒙?
当今中国文化复兴与启蒙的宏大叙事,注定离不开孔子和世界这两个基本范畴,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复兴与启蒙的传统源头,不能不追溯到孔子;中国文化复兴与启蒙的当代环境,不得不面对世界。如此宏大叙事,犹如一部复调音乐,其中包含有两组并行、交叉且对应的主题:一是孔子的世界与21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一是世界的孔子与当代中国的新启蒙。这样一种多主题变奏,注定了要纵贯古今,融汇中西,要在短短一篇文章内讲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请允许我在本文的论述中,尽可能省略严谨的学术论文所必须交代清楚的一些论据,而将有限的篇幅更多地用于举要阐发我的思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短章,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论文,不如说是一份思想碰撞的邀约。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并不缺乏思想,而是缺少在一个志同道合的思想平台上有建构意义的对话与碰撞。
下面,先交代一下,以“孔子的世界”说“21世纪新启蒙”何以必要?何以可能?算作解题。这里,请允许我先拉来两位著名汉学家的大旗,为我作虎皮,为我壮壮胆。
先说“孔子的世界,世界的孔子”。这句话一开始就错,因为,在孔子的字典里,没有世界,只有天下。孔子的天下如何能够转述为孔子的世界,当今世界又为什么需要一个世界的孔子?这对于孔子和世界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困境。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用《儒家的困境》()这个书名,试图回答“儒学对于今日世界有何意义”这样一个“东亚文化之困”,这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只是当代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问,当代韩国、日本、新加坡也都在问。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儒学?
他指出:“如果答案是《论语》中孔子的教导,那么,今天几乎所有关系到儒学的言论都不是针对它。实际上,就连本世纪(20世纪)初那些指责儒学的言论都很少触及孔子本人的观点,他们只是在批驳后世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这也就是说,至少在绝大多数西方汉学家和东亚学者的文化视域中,孔子不同于儒家,反之亦然。
将儒学与今日世界联系起来是一种困境,那么,将孔子与儒学的联系做一个切分,然后越过儒学,而将孔子与今日世界直接联系起来,是不是就可以解脱困境了呢?还是用狄百瑞的话说:关键看你怎样理解这种困境。他说:“我希望用‘困境’的说法,覆盖儒学陷入的各种困境、儒学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的各种困境。在我看来,就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仍在继续的言说,儒学从一开始便问题丛生。”
狄百瑞认为:“如果把‘困境’当成儒家本身的问题或者当成后来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应当‘依据什么尺度’进行判断。我的答案是,应当首先以儒家摆在他自己面前的标准和目标评判他的失败。”
狄百瑞面对儒家困境的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孔子及其困境。
那么,孔子给自己的学术理想提出过什么样的标准和目标呢?这个目标与当今世界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我的答案是:“复兴”和“启蒙”。孔子终其一生志在“克己复礼”,而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一言以蔽之,就是“启蒙”。由此而论,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不只是一个西方的老概念,也不只是一个时尚的新概念,同时也是早在孔子那里就开始了的,迄今为止远没完成的老标准、老目标、老课题。
当今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同样不是一个新课题,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百年老课题的新话题。百年以来,人们不止一次地言说复兴和启蒙,以至于当代中国没有一位学者可以不说复兴和启蒙而能够成为当代学者,由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百年思想史,是一部无人不说复兴和启蒙的梦想学说史。
无论怎样,只要孔子的困境还在,只要孔子的标准和目标还没有达到,复兴和启蒙,就会有人不倦地说,反复地说,在主流语境下独立地说,在喧嚣与寂寞中执着地说,在困境中不为所困地说,这样的言说,本身就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至少可说是孔子式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
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维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在为自己的专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中文版序言中最后写道:“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无论代价是多么的高昂。”与几乎所有言及启蒙的西方学者一样,舒衡哲在这本论及中国启蒙的汉学著作的开头同样引用了康德关于启蒙的定义——“要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就让康德的这句话,同样成为我这篇文章的题解和开头。在中国,理智难,勇气更难,知难不难。
本文旨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几个相关概念作出正本清源的简要界定,以期回归本来的常识。
一、两大文明源头:人类文明源头和中国文明源头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21世纪的中国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论从什么样的立场出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首先是对人的重新发现,都首先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21世纪的中国,首先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重新发现并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此本体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重塑自己的文化精神,惟其如此,才能够产生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用中国当今最标准的话语来说,在当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文化精神的重塑,只有通过对两个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当代重构才能够实现,这两个古代世界是:中国古代的孔子的世界和西方古代的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所谓西方古代的这“两希世界”,其自身的源头也都主要在东方,其历史的影响也都不只在西方,其归属很难划定为西方或者东方,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两希文明”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源头之一,尽管它们过去更多地被指称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为什么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需要重新发现本来只是所谓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这个问题如同西方人的反问一样:为什么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对本来只是中国文化源头的孔子的世界重新发现?
这两个相对方向的问题,共同的答案只有一个:21世纪的世界,既不是西方的世界,也不是中国或者东方的世界,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是人类责任共同体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中国是一个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负责任的新的大国。中国要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责任,首先必须具有人类文明共识的世界意识,而孔子的世界和古希腊及古希伯来这两个人类文明的古代世界,就是当今人类文明最具普遍共识的世界意识基础。这句话也表明:这两个古代世界,只是当今人类文明最具普遍共识的基础,并不是人类古代世界的全部,更不是当今人类文明共识的全部。人类文明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在当今世界,都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尤其需要构建一个具有普遍共识的人类文明基本框架,实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这个普遍共识的基本框架,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
二、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当今世界的这一“共同体”属性,决定了人类各种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不是文明间的冲突和竞争,甚至不是对话与交流,不是相对的互鉴,而是协同一致的共构。所谓协同一致的共构,绝非世界博览会式的文化大观园,一盘散沙式的,在一个“盘子”内的各自表演,而是以全人类共同命运和责任的名义,世界各种文明对各自文明边界的生态化超越,在此前提下,实现人类文明及其生态的有机整合。
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的这种空前自觉的有机整合称为“人类文明重构”,这一重构注定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其间少不了会有曲折,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暂时的夭折或局部的倒退,而21世纪只是这个注定了艰难重重的“人类文明重构”的开始,这是因为,21世纪的世界,由于科技超空间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已经到了不进行人类文明的整体重构,人类各种文明都难以可持续生存下去的危机关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并非出于理想主义的梦呓,而是现实人类文明生态危机倒逼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的世界,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需要一场世界范围的新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不只是中国,而是世界各国,都需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的时代需要,共同重新发现孔子的世界和古希腊及古希伯来世界,以此为新的参照,重新发现各自文明的古代世界,重新构建各自文明的新世界,由此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的全球大世界的共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行标志的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人类重新发现自己的古代世界并以此为根基重构人类文明、共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人类责任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使命、任务和意义,不只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为了人类文明伟大复兴。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喜是忧,都会直接影响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代新人在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候,就不能不具有世界责任意识,这在实质上要求一代中国新人同时也要是世界公民。所谓世界公民,主要是指相信并认同人类具有真善美理想的共识,非如此,即便其经济实力可以撼动世界、可以主宰人类,也无以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美善力量。
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重新发现中国自己的古代世界,为其当代复兴找到再出发的历史高地和文明原点,也需要像欧洲当年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那样,自觉地探索和重新发现西方的古代世界,还需要与当代国际思想界一样,对欧洲当年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利弊得失进行再反思,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复兴、再启蒙,否则根本就无法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构,更不用说主导这个新世界的共构了。
三、两个古代世界:超越儒家与回归孔子
21世纪的中国,由于过去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原因,对西方的古代世界并不陌生,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尤其熟知,近几年间,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世界各国的时候,每每对世界文化名家和文学名著如数家珍就是明证。
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由于过去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原因,反倒是对自己的古代世界缺乏令人信服的基准认知,以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缺乏应有的文化底气和文化共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误将汉代以来逐步形成和流变的儒家文化当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原点,当成了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所要重新发现的古代世界,当成了21世纪中国新启蒙所要重新阐发的思想元典。
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实际上针对两个古代世界:
一个是要挣脱和超越的古代世界,这就是与中国秦汉以降的中华帝国(前221-1912年)在思想文化垄断方面可以相类比的中世纪(Middle Ages,476-1453年)。
一个是要重新发现和“复兴”的古代世界,这就是与中国的孔子(前551-前479年)的世界(西周,前1046-前771年;东周,前770-前221年)几乎同时产生、同样辉煌的古希腊(前800-前146年)世界及古希伯来(特指《圣经·旧约》形成时期,约前1500-前300年)世界。
我们还知道,欧洲的中世纪,同样是源于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只不过主导这个中世纪的教会将古代世界的文化遗产为我所用,变成经院哲学,变成教会垄断的神学,变成只有僧侣才能解读的经典,由此成为古代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中介,这在实际上阻断了人们与古代世界的直接联系,阻断了人类对其文明源头的渴望,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过,尽管如此,欧洲的中世纪也并非像我们过去被人们告知的那样黑暗蒙昧,那样死寂沉闷。产生于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就是最好的例证,既黑暗也辉煌;更不用说城市的兴起、大学的诞生,既保守也开明。同样,我们自己的中华帝国,在漫长的思想专制时期,也曾经为人类贡献了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同样既伟大也悲哀;更不用说农业技术的发明和中医药的智慧,既封闭又先进。
的确,同欧洲的中世纪一样,中国自汉代以降,与中华帝国相伴而生、相随而行、相依而成、相对而立的儒家,或许还应该加上道家和中国化的禅宗佛教,扮演了如同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角色,其儒家道统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繁琐神学,其儒家学人自命为孔子传人而类似于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僧侣。这样的儒家及其所诠释的古代世界,正是21世纪中国之所以需要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对象性原因,当然也正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要超越的文化障碍。
四、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
人类为什么要重新发现古代世界?这有两个前提性原因:
第一,古代世界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代世界与其说是一个曾经的历史世界,不如说是一个永恒的理想世界,由此而言,所谓重新发现古代世界,其实是重新找回人类的理想。
第二,这个古代世界中,的确有人类所需要的而又为现实社会的人类所失落的某种终极价值,这种终极价值之所以称之为终极价值,就是它超越任何个人、集团、国家和种族的功利需求,是人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即基本人权。
我们知道,源于意大利的欧洲文艺复兴,是为了重新发现人本来就有的尊严、神圣和崇高,人从此自觉自己不同于动物而是万物的灵长,这是因为人有人性,人有灵魂,人有精神。
我们又知道,接下来对文艺复兴的反思,是要重新发现人本来就有德性和天赋权利,而不依赖任何他人以上帝的名义的恩赐,这样的发现,让人知道自己是自主的人,是以自己的行为对自己也对人类负责的人。
我们也知道,源于法国的欧洲思想启蒙,是为了重新发现人本来就有的理性,用康徳的话说,还要重新找回运用理性的勇气,这种勇气让人成为自由的人。
我们还知道,接下来对思想启蒙的反思,是要重新发现理性的局性,人类从此得知:反抗专制的理性,也可成为非理性专制的罪恶之源。这样一种理性成为自己对立面的“启蒙辩证法”,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两次疯狂的世界大战,专制极权的肆无忌惮,民族主义的革命狂热,爱国主义的群众暴力,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仇恨,乃至生态环境的科学破坏,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几乎都是人类理性被极度工具化、功利化的文明恶果。
由此可见,人类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是一个不断重新发现的过程,甚至是一个不断否定和修正发现的反发现的痛苦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所谓进步,就是不断地发现和反发现,不断地文艺复兴和新启蒙。
以中国为例,自从孔子以降2 500多年间,汉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复兴原儒;唐代的韩愈,以古文运动复兴道统;南宋的朱熹,以义理之学复兴元典;明代的王阳明,以心学复兴孟子;五四时期的胡适,从白话文重返国学,以“整理国故”重振文艺复兴。
这些大学问家,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且绝不拘泥于一家之见,不能简单归为儒家。尽管时代背景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以治学为复兴,且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从孔子的世界,即秦汉以前的古代世界,重新找回失落的中国文明和失落的中国人自己。
正是这样“不断”的失落与找回,随着历史的长河一以贯之,构成了孟子、韩愈和朱子所谓的“道统”。
这个道统,绝非只是儒家一脉,其实就是中国特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基本传统,用北宋关中大学问家张载的话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总之,中国文明的历史,即便是在思想专制的中华帝国之下,即便是在文化垄断的儒家道统之中,从来都不乏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恰恰就植根于孔子的世界。孔子本人及其时代,就是一个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伟大时代。
不断地失落,不断地远离,不断地重返,不断地重新发现。人类文明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特定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失落是人的天生缺陷,西方视为堕落的原罪,中国叫做蒙垢和蒙羞。心地蒙垢,所以需要启蒙;灵魂堕落,所以需要救赎。无论是心灵启蒙,还是灵魂救赎,都是人自己的自我启蒙和自我救赎,前提都是相信或者预设人本来有纯洁的灵魂,人本来有智慧的良知,人本来有运用理性的勇气,总之,人对自己重返自己有信心。这样的启蒙和救赎,其实质是人类的浴火重生,这也就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源于拉丁语及法语的复合词的本来涵义,这也就是孔子整理的《周易》中的《蒙卦》和《复卦》之于启蒙和复兴的人类命运象征和世界光明隐喻。
五、失落的假说和发现的预设
现在的问题是:人的这些终极价值——人性、人的尊严、人的德性、人的理性、人的天赋权利、人的自我反思、人的良知、人的勇气、人对自己的信心及由此对整个人类的同情心,所有这些,在中国的古代世界即孔子的世界,一如在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也都同样存在而同样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受到礼赞吗?所有这些,在21世纪的中国,一如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一如在欧洲及世界各国的文明进程中,也有所失落吗?
如果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在孔子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我们无以言说重新发现孔子的世界;如果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在21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失落,我们不需要所谓文艺复兴和新启蒙。
除非我们失落了自己的古代世界,而这个古代世界又的确有我们失落的家园,我们才需要、才可能有21世纪的文艺复兴和新启蒙。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还必须知道:究竟什么是孔子的世界——它的文本、它的语言、它的图像、它的精髓,所有这些,都是否一如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能够被文艺复兴的艺术创造所转换、所表达、所重构,都是否能够被新启蒙的当代语境所转述、所阐发、所激活。
这样一来,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问题,就从历史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思想领域,转到了技术层面,转到了艺术教育,转到了艺术创作,甚至转到了创意产业上来。一如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赞助和罗马教廷对艺术家的委约,一如德国宗教改革德语版平民圣经洛阳纸贵,一如启蒙时期《百科全书》的畅销让狄德罗名利双收,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顾名思义,同样注定了只能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且受到市场欢迎的“经典新潮”和“艺术时尚”,否则,只不过文化精英的自娱自乐和学术宗派的圈子游戏。
六、孔子的世界与中国元典
下面,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孔子的世界。这是一个如同古希腊世界及古希伯来世界一样丰富多彩且美轮美奂的艺术世界,充满了理想,也充满了想象。
孔子诞生的时代,是中国开始有系统地整理、记录、保存、阐释、传播中国三代(夏、商、周)文明和现实社会“观念形态”的时代,可称为“中国经典的自觉时代”。以孔子名义整理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及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是中国具有“元典”性质的“集大成”,其中记录和保存的内容,既不是所谓蒙昧时期的天真想象,也不是所谓童年时期的浪漫史诗,更不只是所谓“六经皆史”的客观历史记录,而是中国文明高度成熟的“思想观念世界”,且自成体系。
《孔子家语·本性解》记载说:“孔子生于衰周(周代的衰败时期),先王典籍,错乱无纪(散落错乱);而乃论(论述)百家之遗记,考正(考据订正)其义(义理),祖述(遵循)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删(编订)《诗》述(阐述)《书》,定(确定)《礼》理(整理)《乐》,制作(写作)《春秋》,赞明(阐明)《易》道,垂训后嗣(后代),以为法式(准则),其文德(礼乐仁德)着(彰明)矣。然凡所教诲,束修(十条干肉)已(以)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将欲与素王(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有天下之使命)之乎?夫何其盛也(如此多的弟子)。”
《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节也记载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遵守)天时,下袭(沿袭、遵循)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覆盖),辟如四时之错行(交错运行),如日月之代明(更替照耀)。万物并育(共生)而不相害(妨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违背),小德川流(细流而浸润),大德敦化(敦厚而化育万物),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所有这些记载,都与孟子说的一样:孔子是他此前2 500多年中国文明典籍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悠久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
《孟子·卷十·万章下》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
这里所谓“圣之时者”,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孔子作为时代的导师,应运而生,顺时而动;二是指孔子作为时代的批判者,与现实格格不入,与时代潮流逆向而行;三是孔子作为超越时代的圣人,注定生不逢时,却为万世师表。这样一种“圣之时者”,其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
这里所谓“集大成者”,也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孔子作为此前上古2 500多年文明的保护者,其观天下的方式是“向后的”,这必然与向前变革的时代产生冲突;二是指孔子作为历代文明各种文献典籍的编订者,其对待天下的方式是“多元的”,这必然与争霸天下的一元化要求产生矛盾;三是指孔子作为先圣、先王、先贤的追随者,其理想境界是“尽善尽美”的,这必然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这样一种批判性“集大成者”,其命运也必然是悲剧性的。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对孟子的说法做了进一步阐发,他以“四时循环”的“始终圆满”,来比附“金声玉振”的“始终大成”,二者都以“有始有终”或者说“善始善终”来阐明孔子为什么是最具神通的“时之圣”。孟子和朱熹以四时(四季)礼赞孔圣,是有道理的。
中国古代的存在哲学,究其根本,是一种时间哲学。在孔子的世界,世界不是一个空间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由时间构成的变易围合。在这个变易围合中,时间不是一条朝一个方向无限延伸的直线,而是如阳光一样,由一个不断变动自身方位的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弥漫;时间不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流逝,而是如月光一样以圆缺变化交替流转的斗转星移,更是以四季变换往复循环的生命轮回。
孟子和朱熹深谙此道,不约而同地以时间即存在的哲学观,以存在即始终的道德观,以始终即完美的审美观,从学理上而不只是从人格上,将孔子提升到了真正圣人的思想高地和精神高度。
由此我们得知:孔子作为圣人,是一种四季始终意义上的时间性存在:每一循环,有始有终;往复循环,无始无终。圣人孔子因为如四季始终而永恒,而在孔子而言,每一个真正的人,即所谓正人君子,也都莫不如此。
将天地大道的万世经典归于一人,这样一种近乎神话和圣化的历史阐释,在人类几乎所有文明的古代世界中都一样地发生过。一如古希腊经典悉归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少数几位著名思想家,一如流传了千余年的《圣经·旧约》统统归于耶稣名下,一如传唱了千年的希腊神话以《荷马史诗》归于荷马之口,一如千僧结集的印度佛教经典归于佛陀拈花,中国上古2 500多年文明的经典结集,神奇地归于“孔子的世界”,可谓顺理成章,不足为怪。
或许正因为如此神奇,孔子世界的“六经”,与古希伯来世界的“旧约圣经”,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第一,二者都不是一个既定时期的个人著作;第二,二者都是历经千年无名者传录的集大成;第三,二者都是超越杂多史实的思想观念体系;第四,二者都是为了教化天下、惠及万民而记录、而整理、而结集;第五,二者都因为超越现实和历史的表象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永恒的生命,如此永恒和不朽,西方称之为“普世价值”,中国称之为“周易”——周遍之道。
《旧约圣经》也称希伯来手稿,通常分为律书、历史书、诗歌和先知书,其中包含了神话、传说、寓言、散文、诗歌、谚语、格言、箴言、启示录等多种形式。无独有偶,孔子的世界的“六经”,在内容、题材、体裁、语体、文本结构、故事情节、戏剧场景等诸多方面,与《旧约圣经》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关于“六经”的这些特色,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过极为精辟的评说,至今没人能出其右,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由此观之,孔子与“中国元典六经”的“集大成”关系,决定了孔子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只是一个姓氏的孔子,一个鲁国的孔子,一个春秋时代的孔子,一个文化个体的孔子,一个哲人或者圣人的孔子,而是中国古代文明之源的一大集成性标志:既是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类型之一的地理空间地标,更是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且“逝者如斯”的历史时间座标——此前2 500年或许更长时期的神话、传说和记忆,在此集成为“六经”和《论语》;此后2 500年乃至永续之年的复兴、光大以及衰败或者消融,以此“元典”为参照。
“六经”及《论语》作为“中国元典”集大成,作为“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库”,具有多元共构、多家共源的显著特质,这是后世任何所谓诸子百家,所谓儒、释、道三家都无法比拟的,由此,“孔子的世界”大致可以在我们面前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显然,它既不同于儒学,也不同于国学,甚至也不等同于所谓优秀传统文化。
第一,在时间上,“孔子的世界”局限于春秋战国之际,还没有受到秦汉以降专制帝国的政治污染。
第二,在空间上,“孔子的世界”局限于狭义中国地理核心,还没有受到“泛中国化”的地理变异。
第三,在思想上,“孔子的世界”局限于孔子、老子或者还可以加上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知先觉”的个人说话和讲述,还没有沦落为后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的宗派极端。
第四,在语言上,“孔子的世界”局限于文学的优雅和诗意的音韵,还没有被繁琐考据、官样文章和八股文所束缚而失去活力。
第五,在人格上,“孔子的世界”局限于君子道义、天命责任和智慧良知,学者的自由,还没有被君主赎买、被暴君扼杀、被恐惧泯灭、被穷困窒息,人的灵魂,还没有离开人的性命。
这样一个“孔子的世界”,当然不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全部,但却是当代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基点。
这样一个“孔子的世界”,如果用当今人类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标准,当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甚至还是一个相当“反动”的世界。其实,即便在孔子时代,这个世界也都是被视为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有缺陷的古代世界,仍然不失为当代中国的一个古代理想。
这样一个“孔子的世界”,如果与欧洲文艺复兴所重新发现的古希腊世界和古希伯来世界这“两希世界”相比较,其文明的成熟性,其文化的丰富性,其艺术的多样性,其理想的完美性,其思想的深刻性,其自由想象的广阔性,其政治社会的宽容性和可塑性,其人格精神的崇高性和神圣性,可以说毫不逊色。
的确,这样的比较,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这是因为,每一种人类文明都有属于自己的基因密码,这些独有的基因密码之间,没有任何优劣或者先后的可比性。
但是,尽管如此,这样的比较,依然还是有必要的,作为一种参照,它至少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古代世界不那么不自信,或者不那么过于自信。
这样的比较,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必要性,这就是即便是欧洲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两希世界”,相对于西方现代和当代而言,也同样是不完美的,甚至是“反动”的,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像是专制极权王国,而不是自由民主世界,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妨害柏拉图的世界成为西方文明源头的理想的古代世界。
这样一个“孔子的世界”,当然不同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如果是,那也是通过孔子的思想视域所折射、所过滤、所重构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因此可以说包括三个世界:一个是孔子不想要看见又不得不看见的批判的世界;一个是孔子想要看到而又看不到的理想的世界;一个是孔子内心想要表达而又没有人想要听他表达的孤独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既属于孔子之前的历史,也属于孔子生活的现实,更属于孔子之后的未来。
综上所述,关于“孔子的世界”与当今热词儒家、国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划分界限,见出区别:
第一,从“六经”及《论语》的形成时代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儒家、道家以及诸子百家尚未产生,所以,这些古代元典并非为后世任何一家学说量身定制。
第二,从此后儒家、道家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而言,百家无一不是取之于“六经”这“一家”,也无一不是受制于“六经”这“一家”。儒家、道家,诸子百家,以及后来中国化了的禅宗,在思想资源上,大体上可以说是同源于“六经”。但是,思想资源同源,并不等于思想大一统,更不能成为思想大一统的依据;恰恰相反,同源而异道,才是人类思想之花之所以灿烂的美的本质。同源,人类不同文明及其思想因此可以互通;异道,人类不同文明及其思想因此可以共存。
第三,从“六经”及《论语》的具体内容而言,老子和孔子在两个基本点上没有根本分别:首先,二者的思想基础,都同源于“六经”;其次,二者的最终社会理想,都殊途同归于“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一直被认为只是老子的世界,其实是老子身在其中的“孔子的世界”。
七、结论
如前所述,本文旨在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几个相关概念作出正本清源的简要界定,以期回归本来的常识。
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复兴。人性的复归,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基本权利意识的觉醒,一句话,人的自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前提。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进程上说,首先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这是因为,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作用,就是唤醒和启迪人成为自由的人,由此成为能够自主承担责任的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工作及其途径,是两个重新发现:重新发现古代世界,重新发现人自己,准确地说,是通过重新发现古代世界而重新发现当下的人自己。
第三,立足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中国,要重新发现的古代世界,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古代世界:一个是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人类文明共同源头之一的古代世界,一个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中华文明共同源头或者主要源头的古代世界。所谓重新发现,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如何看待这两个古代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如何重构这两个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关系问题。这样的重新发现,让我们看见了三个世界,如何在这三个世界中可持续生存和相安共存,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课题,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这也是21世纪全球振兴的全新课题。
第四,立足21世纪人类责任共同体时代的中国,要重新发现的人,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人:一个是具有人类责任意识的世界公民,一个是具有中国文化自信的中国人民。所谓人的重新发现,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如何看待这两种人的关系问题,准确地说,是如何在重新发现的两个古代世界与当今世界的重构中,同时成为世界公民和中国人民这两种人的问题。如前所述,从根本意义上说,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回答和解决这两种人的问题,非如此,便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五,对人类文明共源和中华文明共源这两种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和对世界公民和中国人民这两种人的重新发现,不是庸俗意义上的复古,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而是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重构。这其中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前提性预设: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当今时代的人类社会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上述两个古代世界中,的确可以找到人类共有和中国特有的精神家园,的确可以重新找回同时作为世界公民和中国人民的人自己。
第六,关于上述两个预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探索和实际进程中,具有诸多分歧。正视这些分歧,尊重这些分歧,保护这些分歧,在此语境下讨论这些分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常现象,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一种常态。在各种分歧中,有一种分歧最为要害,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点在哪里?我们知道,这样的问题对于西方不是问题,甚至对于东方很多国家和地区也不是问题,因为古希腊世界和古希伯来世界,本来就是东西方共源的结果,本来就是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诸多宗教文明的共源或者源流之一。
第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点,既不是历史概念,也不是地理概念;既不是国家概念,也不是民族概念;既不是政治概念,也不是经济和军事概念,而是思想的超时空视域和精神的自由境界,这样的视域和境界,有人主张在儒家传统中寻找,或者在儒释道三教合流中提取其精华,而本文指出:只在孔子的世界。正如当年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原点,不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在古希腊世界和古希伯来世界;中国自汉代以降的儒家文化主流及其所赖以存续的中华帝国,和欧洲中世纪及其经院哲学一样,都是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重返古代世界所要摆脱的精神桎梏,所要超越的文化障碍。这些神似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中国儒释道传统,自身都需要借助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从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中重获生机,从对人的重新发现中重返人间,如同当年罗马教廷需要文艺复兴艺术家的雕塑与绘画一样:让神圣重新为人而降临。由此而言,儒释道传统,可以既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负面对象,也可以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同行者,但绝不是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之所以立足的原点,更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源头和文化目标。
第八,什么是孔子的世界?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原点是在、只在、只能在孔子的世界?这个孔子的世界,能否也像古希腊世界和古希伯来世界为当年欧洲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艺术灵感和思想源泉一样,为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乃至为全球振兴的世界艺术家和思想家提供独具中国特色且具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艺术想象时空,让思想自由翱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有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球振兴的志士仁人一道来重新阅读孔子时代的中国元典,需要有志于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一道走进孔子的世界,艺术地感受元典文本的艺术魅力,艺术地捕捉元典文本中的艺术灵魂,否则,任何所谓肯定或者否定的思辨性答案,在充满生命活力的艺术创造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而毫无意义。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的这篇拙文,其实更像是一份阅读邀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借着“21世纪中国文艺复兴和新启蒙”名义,向中国和世界的艺术家、思想家,特别是向代表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年轻一代,发出的一种呼吁:让我们共同阅读孔子的世界,共同走进孔子的世界,共同重构孔子的世界,由此共同构建未来理想的世界。
我相信,任何一个真正阅读过中国元典的人,都会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发现“孔子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世界的孔子”。你会发现——
在孔子的世界中,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走,自由地选择,自由地办学,自由地传道,自由地合作或者不合作,自由地爱一个国家或者不爱一个国家。这个自由的世界,不是虚幻的理想,而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真实生活的天下。
在这个孔子哀叹“礼崩乐坏”的天下,人放言无忌如老子,人崇高神圣如孔子,人有德性和良知如君子,人有自我反省精神如先贤,人有理性和智慧如先哲,人有使命和责任如先王,人有至善榜样如尧舜,人有治世作为如子产和晏子,人有尊严和人格如伯夷、叔齐,人有道义和正气如孟子。
这样一个孔子的世界,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在孔子的世界,我们穿越,所以我们存在。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Confucius' World and the World's Confucius: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Revial and Thought Enlightenment
LIU Jianhua
(Beijing Wisdom Consulting Firm, Beijing 100012, China)
How to tell about Confucius in modern world and how to tell about the world based on Confucius’ texts are the common topic of the times that faces both the 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scholars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ho make studies on China. The author calls “Confucius’ world and the world’s Confucius” this kind of topic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onfucius before Zhu Xi, classifies it as Chinese cultural revival and thought enlightenment, merges it into grand narrative in the era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considers it as a fatalist Confucius-styl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Confucius; world; cultural revival; thought enlightenment
10.3969/j.issn.1673-2065.2017.02.010
刘建华(1954-),男,湖北仙桃人,独立学者。
B222
A
1673-2065(2017)02-0072-10
2016-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