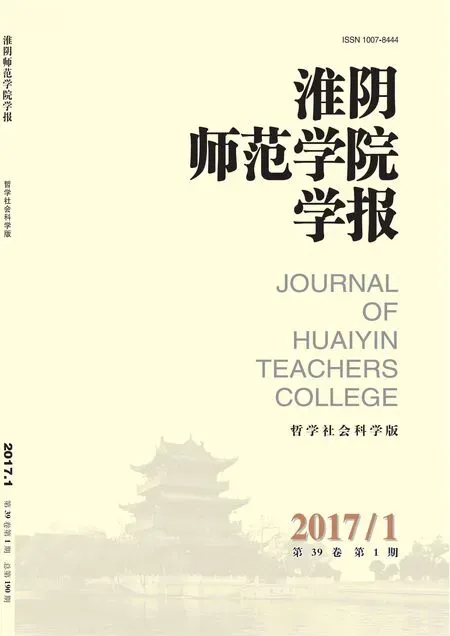振叶寻根 观澜索源
廖名春, 陈 瑶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振叶寻根 观澜索源
廖名春, 陈 瑶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华文明作为亘古常新的古老东方文明,中国文学无疑具有一段可供追溯的悠久历史。对照新近出版的剑桥版文学史系列,其中两卷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的起讫年代(公元1400年)与早前出版的欧洲诸国文学史(包括意大利、德国和俄国)的发端年代,恰好重合一致,这正是编者的真实意图所在,附带声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文学史的源远流长及其书写长度,世界上其他民族罕有能够与之相匹敌。
文学发生史与文学史的书写相倚而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也可追溯至中国文学的发生源头。如果早期正史系统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与《儒林传》《文苑传》可以认定为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述的话,那么,章学诚先生评价为“体大而虑周”而堪称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集大成者的《文心雕龙》,对刘勰所处南朝时期之前的文学体裁进行考镜源流,对文学作品、作者进行臧否褒贬,对文学理念进行囿别区分,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视为我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式的论著。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写道: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1]
刘勰在此一一枚举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挚虞《文章流别论》和陆机《文赋》等重要文论著述,并指出这些论述的不足,最后标举自己论文叙笔的理想,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同样,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念统摄下的一种文学史书写理想,其根本方式便是寻根究底、探本求源,具有典型的中国气质,恰与悠悠漫长的中国文学史符节相合、精神相契,其重要意义与价值是建构了书写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传统。方铭先生主编此部《中国文学史》,力图并最终实现了这一文学史书写理想。
文学史须注重自我个性这一要论,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对此进行过充分的论述:“这明显是个性和价值的问题,甚至在研究一个时期、一个文学运动或特定的一个国家的文学时,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也只是它们有别于同类其他事物的个性以及它们的特异的面貌和性质”[2]4,“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2]6,并进一步地宣称:“文学是一元,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文学史才有前途”。[2]45那么,融入全球化的语境,要编著一部卓然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国别体中国文学史,应该如何体现其独特的个性与气质呢?针对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独特发展规律的中国文学,方铭先生所主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开篇即标举其鲜明的立场即“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要求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与中国方法。
首先,文学史书写对象体现出中国文学本位的“广义文学”观念。何谓“文学”?这是困扰文学史书写者的普遍问题。文学一词,作为一门学科专用术语,在西方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20世纪中叶,新批评学派所持的“狭义文学”观,视文学作品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文本系统而进行单纯的语义分析,相较而言,追溯中国的固有文学观念,则无疑是一种“广义文学”观。从字源来看,文,东汉许慎《说文·彡部》:“错画也。凡文之属,皆从文。”段玉裁注:“画者,文之本义。……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3]《易·贲·彖传》:“物相杂,故曰文。”[4]中国古人界定“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具有丰富性与广义性。
方铭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序言》中,通过纵向历史的全面梳理,认为“中国文学学科的诞生,其最初历史可以上推至春秋时代”。首先,先秦时期的“文学”,自“孔门四科”始,即明习人文经典,以及泛指文学之士一切以“谋道”为目的的人文活动。其次,由汉降清,“文学”因学术与文章的逐渐分野而进入“狭义化”的进程,以清朝康熙年间陈梦雷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所列文学典而仅仅囊括文体、诗赋、文学家列传等。由此强调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学科范畴。[5]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编孙康宜教授,撰文《新的文学史可能吗?》指出:
现在的欧美汉学界,只有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戏剧史的观念,但缺乏一个全面的中国文学史的观念,所以,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观念都是比较片面和残缺的。比方说,我们会说某某汉学家是搞唐诗的、搞宋词的、搞明清小说的、搞元明戏曲的,但是,很少人会说这个人是搞先秦文学,或者是搞唐代文学、宋代文学,或明清文学的专家,所以,一般说来,美国的汉学家习惯于专攻某个时代的某种文体,忽视了同一时代的其他文体(genres)。我一直以为很有必要改正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剑桥文学史》这种格式是很有挑战性的。[6]
孙教授观察到海外汉学界目前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狭义化书写,主张矫正此种“片面和残缺”的趋向。这正与方铭先生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书写立场遥相呼应、殊旨同趣,即中国文学史不应是西方文学观念影响下的单一的文体史或纯文学史,而应表现横向与纵向交错的多元化文学发展脉络与态势,借此亦强调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广义性。这种文学史书写的理论自觉,可视为向中国文学本位的一种趋近与回归。
其次,文学史书写方法采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体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传统。按照文学四要素来论,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是一个息息相关而相互依存的系统。中国“轴心时代”以来的儒家文学批评方法,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孟子所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源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以及《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谓以作者的身世背景去推求作品的内涵,以己之意去度作者之志。这部《中国文学史》在编撰过程中,运用颇多笔墨,厘清各时代的“社会蜕变与文人构成”“文人世家的构成”等人文背景,由“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路径切入,叙写作者与世界等文学要素之间的关联,典型的例子,如“司马迁的经历及《史记》的成书”等相关文学史内容。
这部《中国文学史》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运用传统方法研究新材料,许多章节关涉出土文献,如“现存传世与出土战国叙事体文献”,“现存传世与出土战国诸子体文献”,“《郭店楚简》与《礼记》”,“敦煌文献的发现与价值”。编著者采用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与材料,来补阙传世经典的疏漏与讹误,比如,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1993年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1994年的上博简等。这里运用了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院时代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7]“二重证据法”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彼此印证。中国文学史上的典籍,包括“四书五经”“十三经”等,历经两千余年的经典化进程中,难免遗留聚讼千年不息的学案。采用“二重证据法”,地下新出土的材料保留原始的历史风貌而可能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尤其对于书写漫长历史的中国文学史显得更为重要。
最后,这部《中国文学史》还体现出中华各民族文学的大融合,呈现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独特面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第三编“辽宋夏金元”,一改过去文学史编写只有宋、元,而无辽、夏、金的旧面目。正如编著者在《中国文学史·序言》中所论:“我们对现今中国版图中曾经存在过的区域政权或少数民族的文学也给予关注,如西夏文学、大理文学、吐蕃文学等,过去很少在文学史体现,我们填补了这部分空白。”[5]7
纵观整部《中国文学史》,从中国文学本位出发而试图“寻根振叶”“观澜索源”,本身就是对这种延绵、传承不断的中国传统文学史书写理想的积极回应与蹈行。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54.
[2]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5.
[4] 楼宇烈.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256.
[5] 方铭.中国文学史[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6] 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J].清华大学学报,2005(4):39.
[7]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