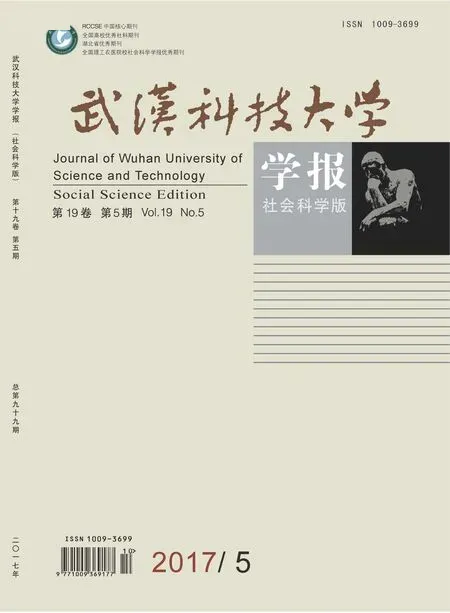控制及其扬弃: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逻辑新探
熊治东
控制及其扬弃: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逻辑新探
熊治东1,2
(1.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4)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理论命题。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结构中,人受物质、资本和符号的多重控制,人的自由和发展受到限制,人格和精神饱受摧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得冷漠无情,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必须扬弃人受社会权力关系控制这一基本事实,将人从权力控制中解放出来。首先,要扬弃物质对人的控制,解放人的自然生命;其次,要扬弃资本对人的控制,解放人的社会生命;再次,要扬弃符号对人的控制,解放人的精神生命。
马克思;控制;扬弃;人的解放;符号;理论逻辑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哲学关注的终极性问题,也是研究人及其相关论题不可忽略的视阈。在马克思理论中,究竟人的解放是如何实现的?其中又蕴含怎样的逻辑理路?目前,关于马克思人的解放逻辑理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马克思实践观为基本线索来探讨人的解放及其实现,强调社会实践是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途径;其二,从异化劳动及其扬弃的视角出发,剖析了人在异化处境中的受操控的事实,解放人首先应对异化劳动进行扬弃,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其三,立足于社会生产关系视角,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的私有制,建立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公有制。也有部分论者从依赖力量、物质基础和现实路径等维度对人的解放进行了探讨。上述研究虽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大多停留在外部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层面,缺乏对阻碍人解放的内部权力机制的探究。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从控制及其扬弃的角度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逻辑进行剖析。
一、控制的根源及其表现
与以往思想家们侧重于人的意志自由和思想解放不同,马克思独辟蹊径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人的解放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运行机理分析,揭示了阻碍人的解放的社会权力控制根源。在异化劳动境遇中,人被物质、资本和符号等因素全方位控制,人的生产活动及其生活行为都成为控制的对象,人失去了自由,变为“受控者”,成为被操控的存在。
(一)控制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根源上来看,控制即为控制主体对被控制者的操控过程,其实质在于社会内部权力的交换与互动。被控制者按控制主体的意图和目的行事是控制的基本模式。“马克思所理解的是,这样一个行为者被迫把他自己的行为看成截然不同于他所操纵的那些人的行为。因为被操纵者的行为是按照他的意向、目标和理由而被设计的,他把这些意向、目标和理由看作是摆脱了那些控制着被操纵者的行为的规律,至少当他从事这类操纵时是这样”[1]。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拥有财富意味着掌握权力,资本家受贪欲刺激,情感变得扭曲,疯狂追逐资本。“贪欲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2]50-51。资本家为了增加自己的财富,相互之间进行激烈竞争,一方面不断侵蚀竞争对象的既有财富,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力度,以“计件”和“计时”的方式压榨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仅提供维持他们生命活动和种的繁衍所需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使得劳动者完全成为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对象,而劳动者在资本所有者的控制下又无力摆脱这一处境,这样他们就在这种财富占有不均衡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沦为受控者。人与生俱来的嫉妒心和平均主义欲望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的竞争激烈程度。“这种嫉妒心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2]79。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者为了生存必然陷进资本主义循环往复的恶性竞争怪圈之中,将自身降格为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摆布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商品/金钱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倒,它们充当着一种社会权力结构控制的手段,属于劳动者的本质权力显得苍白无力。资本所有者对劳动者的这种控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形压在人们头上的磐石。
(二)控制产生的具体表现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基本手段,也是促使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要途径。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但阻碍了人的解放进程,而且还加速了人陷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泥沼。因此,在人类还未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桎梏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人注定是受控制的对象,并且人受控制的程度与私有制对人的压迫剥削程度和人自身异化的程度呈正相关。
首先,物质对人的控制。作为鲜活的生命体,人的存在首先是自然的生命存在。“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67。个体有机生命的活动需提供一定的物质资料,这既是人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最初动力,同时也隐含着人受物质控制的基本事实。人为了生存必须依赖于物,在这里,物不仅是满足人生存之物,而且还是权力之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中,人的对象化和外化的结果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的存在,表面上人生产的物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实际上这都与他们自身无关。人与物品之间的主客关系被颠倒,人让位于物,成为受物控制的对象。物质间的社会关系取代了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质的丰富性取代了个人的丰富性。个人在商品交换中,被化约为商品的消费奴隶,受商品拜物教的操纵,自觉不自觉地受商品摆布。人的活动首先表现为劳动生产,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产品越多,自身就越贫穷,受产品控制的程度就越深。物对人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其次,资本对人的控制。资本为何?它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魔力?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2]21。资本所有者是资本的掌控者,他们拥有的不是资本本身,而是资本体现出来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市场购买力。掌握资本的购买力就意味着能够对物质资料进行使用和调配,也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能够对劳动者进行使唤。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一方面为了维持生计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不得不服从资本的召唤,听从资本的指挥;另一方面又使他自身沦为受资本所有者操纵的商品,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过程就是劳动者商品化的过程,劳动者从人变为商品,受资本所有者任意调遣。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仅生产了物质产品,而且也生产了控制与被控制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社会权力结构关系中,劳动者往往自觉自愿地跟随和服从资本所有者的控制步伐,对资本所有者产生依赖,变得麻木不仁,这就是资本逻辑对人进行控制的内部秘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3]287。资本对人的控制超越了物质对人的控制,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捉摸。
再次,符号对人的控制。马克思指出“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4]110。在商品的交换流通过程中,物及其货币形式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当人们普遍追逐金钱的时候,并不是在向往物本身,而是在追求物所表征出来的象征符号。相比物质和资本,符号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嵌入人的内部结构中,影响人对物的认知与判断,成为控制人的又一重要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可替代和可选择的商品与日俱增。让·鲍德里亚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已经终结了,劳动被机器取代,价值的结构规律摧毁了价值的商品规律,商品实现了由功能向结构的转化,“符号形式征服了劳动”[5]。这使得权力结构形式发生了极大变化,由原来的生产控制和资本控制变为符号控制。符号权力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进行控制的新模式,人成了符号的奴隶。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转变为符号拜物教,人沉沦于符号控制中迷失自我,权力对人的操纵形式也发生了变种,控制的程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控制带来的现实困境
资本家通过物质控制、资本控制和符号控制等形式对劳动者进行操控,使得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疏离,成为与之对立的力量,他们从生产活动的“主人”变为资本所有者的附庸。物质、资本和符号的多重控制导致劳动者失去自由和发展的可能,人格出现异化,精神发生分裂,社会结构也随之剧变。
(一)自由与发展的交互迷离
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体,自由意志是人猿相揖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6],自由具有属人的特性,尽管动植物界也有“自由生长”“自由活动”之说,但这种“自由”只是自然界赋予的基本能力,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自由。人不光具备自然界赋予的基本自由能力,而且还能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及其行为,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他们只有进行生产的自由,没有可以支配自己产品的自由,更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自由对他们来说不是解脱,也不是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折磨。自由本来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囿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它对人来说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奢侈品。马克思继承了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自由观,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他十分强调自由的实践维度,指出只有经过实践充分发展和检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在实践活动中,人的自由不仅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而且人的活动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延展。然而这一切都在私有制生产中化为泡影,人的实践活动并不是他自身生命力的自然表征,而是受社会内部权力机制的控制,他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他们的自由在压迫和剥削中残缺不全。
自由的缺失对人的最大影响是制约了人的发展。自由是发展的前提,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之间是相互交织、互相促进的关系。人的自由受到限制,人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相反,人的全面发展,会带来人的解放,推动人的自由的实现,从而不断丰富自由的内容。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受物质、资本和符号等因素的控制,因而是片面的发展。物对人的控制及人屈服于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实写照。资本所有者利用手中的物权力控制着劳动者,同时也对社会秩序进行操纵。资本所有者通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和要求对其他人进行限制,使整个社会秩序表现出“利己”而不是“利他”格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是单向度的发展,与他们相对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不断地将自身的生命对象转化到控制他们的物化秩序中,自然而然地处于社会关系链的末端,受物化秩序的统治成为受控制的“奴隶”。这种扭曲的社会关系使得社会本身的发展也更加不健全,不是以更好地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目标,而是为了满足资本所有者对物的无限贪欲,过度强调物而忽视人,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资本主义世界是物的世界,而不是人的世界。
(二)人格与精神的双重缺失
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中,人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受到控制,而且在精神世界也被物的结构秩序表象控制。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不仅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且还发生在交换过程中。前资本主义阶段,物品较为稀缺,只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时期,物质资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商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替代,人们在商品交易中购买的是商品所代表的符号象征价值,崇拜物的符号价值。符号意味着所有者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符号内化到人的社会意识之中,使人产生一种符号信仰,符号的价值在这时前所未有地展现。恩斯特·卡西尔指出“我们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而不是理性的动物”[7]。受符号逻辑的影响,人自觉不自觉地服从符号秩序,对符号表现出痴迷和狂热,普遍以拥有符号为荣。实际上,符号只不过是物的外显形式,它表征的是与物相区分的代码,根本而言,符号的存在要以物为依托。在符号的操控秩序中,个体人格出现异化,他们将自身的价值和信仰建立在符号之上,视符号为“上帝”,以符号为追求。价值和信仰体系紊乱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人格缺失,人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符号而活。人不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人格在符号秩序之中逐步消解。
人受物和符号的控制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人的精神分裂。单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受到压迫和操控,其又很难摆脱这种处境,使他们对现实感到压抑,对生活产生绝望。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属于他自身,直接导致他们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甚至还会出现焦虑、苦恼、烦闷和不安等情绪。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处于控制之中,因而他们的自我价值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也缺乏价值实现和表达渠道,这对他们的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长久的人性压抑加速了他们的精神分裂。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54。人在异化劳动中感受到的不是劳动的快乐和幸福,而是被劳动折磨的痛苦和摧残。劳动不仅没有给人带来智慧,而且还给人带来了愚昧。人的物质生活的匮乏必然导致精神生活的缺失,加上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操纵,人的精神变得麻木和空虚。在马克思看来,除了夜以继日的劳作之外,工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更不用说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充实,他们被资本所有者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和手段进行压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失去的不仅是剩余价值,而且还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三)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变迁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取代。社会关系的主体不是人,而是冷冰冰的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4]89这种转换使得物与物的关系成为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支配性力量,也就是说,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意识,并且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支配。马克思认为这种以物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将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随着物对人的控制程度的加深,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淡漠。与人际关系冷淡相伴随的是人情味的消失,人们只在意物,而不在乎物之外的人。人彻底成为了受物控制的对象,而不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社会性情感逐渐消解,变成彼此隔离的原子式存在,物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的中介,离开了物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以人为主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系取代,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3]278。无产阶级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生产中产生的,在历史上他们与资产阶级几乎同时诞生。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阶级对立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资本所有者为了攫取更多的资本和利润,对无产阶级进行多种控制。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日益觉醒,他们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阻碍人的解放的最大障碍、是控制他们的现实根源,这势必会引起无产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并逐步走向联合。社会结构在这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由原来的资产阶级的单向度控制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斗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不仅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更要从私有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打破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成为不受资产阶级剥削和控制的社会存在。
三、控制扬弃与人的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操控是阻碍和影响人的解放的真正根源。实现人的解放,必须将人从这种操控中解脱出来,祛除私有制对人的种种限制和束缚。私有制对人的控制是多方面的,摆脱私有制的控制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扬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
(一)扬弃物质控制实现人的自然生命解放
物质是维系人的生存的必要前提,是人的有机生命运转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从未否认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生产带来的丰厚物质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而是对此大加赞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77与生产力进步相伴随的是社会的发展和提升,然而,生产力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合理、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结构的良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考察,发现隐藏其中的对人进行剥削和控制的秘密。资本家借助人对物的自然依赖特性,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质资料对人进行控制,影响人的行为和选择,实现操控人服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马克思强调的扬弃物质对人的控制,并不是扬弃物质本身,而是扬弃物质背后的不合理的所有制形式及其社会生产关系。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生存。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8]在个体与外界双向互动过程中,人很难甚至不可能不与外界进行交换,这样就很容易陷进资本主义物权力体系中,成为物控制的对象。人要摆脱这种物化的生活处境,就必须打破物的统治秩序和物对人的控制,将人从物的操控中解放出来。
扬弃物质对人的控制,使人成为自由自在和自由自觉的生命体,是人的解放的最初阶段。人不再受物的支配,人与物之间颠倒的关系被倒转过来,回归人与物的正常关系,人在与物的交换中占据主导地位。摆脱物质对人的控制,首先需要打破物背后隐藏的不合理的社会秩序,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摒弃物的社会权力属性,向物的自然属性皈依。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2]78。扬弃私有财产意味着对私有制的超越,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对人的控制。人从物质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活动主体,按照自身的意愿和需要从事社会生产活动,劳动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不是受控制的被迫行为。扬弃物质对人的控制,也不意味着人可以完全从物质中脱身出来,不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而是主动地投身到生产实践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对象性存在,在劳动中实现人的本质。劳动对人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像私有制中劳动者对劳动“趋之若鹜”。人在劳动中的舒畅心情能够激发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物质生产的不断进步,将人从物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真正的物的所有者,使人的自然生命超越物质控制的窠臼。
(二)扬弃资本控制实现人的社会生命解放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从物中抽离出来的以货币符号为表征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最初以货币的形式出现在商品流通中,货币极大地方便了商品的交换,实现了人们之间互通有无共享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看,资本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以“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摧残,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871。资本对人的控制比物质对人的控制更加不易察觉。马克思肯定了资本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批判了私有制社会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自身的私利罔顾劳动者的死活。资本主义社会依托资本增殖的逻辑建立起了以资本为核心参照的社会结构关系,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被消解,社会关系围绕着资本的流通展开。在资本的控制下,社会关系的主客体发生颠倒,人丧失了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变为受资本控制和奴役的对象。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受资本的控制,固而呈现畸形的片面发展。
扬弃资本对人的控制实质就是扬弃资本所体现的社会结构关系,将人从资本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6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异化的存在,人的本质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中日益扭曲,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关系的反常。恢复人正常的社会关系状态,必须扬弃资本对人的控制,实现人的社会生命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而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是不同关系主体之间的交织与互动,因此人的解放与社会关系的扬弃密不可分。人的解放和发展是在实践中逐渐生成的,追逐人的自我价值实现需要不断扬弃社会关系。良好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扬弃资本对人的控制,发挥资本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不仅是社会关系走向健康的表现,而且还是人的解放得以实现的基础。实现对资本控制的僭越,摆脱资本无处不在的控制,摒除资本的消极作用,使资本成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助推器,促进人的社会生命健康发展。
(三)扬弃符号控制实现人的精神生命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符号的流通和盛行需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要以全社会的承认为前提。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以货币为代表的符号扮演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为符号的竞争,各种商品为了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借助各种渠道进行符号宣传。符号的泛滥迷惑了人们的理性消费观,对符号产生了宗教式的崇拜,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对符号的过度痴迷势必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扭曲,精神生活变得空虚,盲目地崇拜充斥于社会交换中的各种符号。不可否认,符号在商品流通中具有积极的一面,但超越某种限度的符号崇拜则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人的生活世界被符号世界取代,人被符号的迷雾笼罩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世界中的非符号景象,人的精神生活让位于符号的统治秩序,随之而来的是普遍的浮躁情绪和人文意蕴的失落,人的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宁静,符号冲突、符号歧视时有发生。在符号世界里,人并没有从物的极大丰盛中解放出来,而是又陷入到对符号的无限期待之中,从一种控制转变为另一种控制,人的解放仍是未知数。马克思强调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必须将人从符号控制中解放出来,摆脱符号对人的操控。
扬弃符号对人的控制需要重建人的精神生活,重塑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的解放是人的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中,精神解放是人的解放的终极归宿,精神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资本主义符号控制中,人的精神生命不受自身掌控,属于受操控对象。人的精神生活的缺失、精神生命的失落是阻碍人解放的真正根源。精神障碍不除,人的彻底解放就会沦为空谈。人成为符号的奴隶,根源在于精神世界的空虚,不能在纷繁杂乱的物质世界中追寻自我的价值和尊严,不能真正认清符号的本质,结果只能跟随符号世界的统治而狂欢。只有重塑人的精神世界,复归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跟随物的泛滥迷失自我,才能真正扬弃符号对人的控制。马克思认为,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带来的危害和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秩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解放被操控的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到这时,“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3]85。人的精神得到了高度发展,活动内容和承担的社会角色更加丰富。“人的素质和个性随着人的活动的多样化、社会关系的丰富化形成、发展起来”[9]每个个体最大程度上发展了自身的才能,实现了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1]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M].宋继杰,刘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07.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让·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7.
[7]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李化梅,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36.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5.
[9] 吴向东.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1):29-37.
[责任编辑 周 莉]
B0-0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5.012
2017-06-1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编号:142D002).
熊治东,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