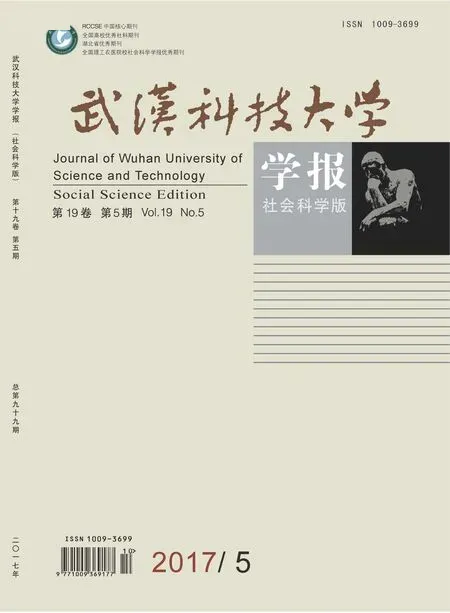我国舆论治理: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邹千江
我国舆论治理:历史与现实的分析
邹千江
(中国传媒大学 经管学部,北京100024)
舆论是民众对事件、问题的公共言论,对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分析舆论的发出人群及我国舆论的基本特征和应对措施,以此为基础提出治理舆论的途径和方法。舆论本身因其海量多元难以控制,但对于舆论起中介过滤的媒体机关、学界学者和意见精英可以依法依章约制,这是舆论治理的不二法门,由此可促进舆论发展的健全与合理。
舆论引导;舆论治理;现代媒介;意见精英;约制
舆论是社会的提示器和风向标,反映出特定时期和阶段的某些社会常态和人心所向。经过民众热议后的舆论会产生较大影响力,有些舆论能够起到革旧维新、移风易俗的作用,进而改变政治社会制度。舆论以多数公众的名义将公共事件的理解和意见通过媒介的渠道公布或发表出来,无疑给相关组织和当事者造成压力,可起到约束监督作用。梁启超说:“盖地方自治诸机关以及谘议局,资政院,乃至将来完全独立之国会,凡其所讨论设施,无一非舆论之返照。”[1]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舆论披露的问题大部分上升为国家的讨论议程,舆论反映于上,足以为天下之重。舆论和政治密切相关,大多针对公共机关。“舆论的最高价值无疑是在政治方面,舆论能够纠正政府错误,发扬民主,修改法律制度。政府之得民意,最方便之法,就是观察民众之舆论”[2]。综而言之,舆论是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
社会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事件发生,吸引为数不少的人参与讨论,舆论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那么何谓舆论,舆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这是我们分析舆论的出发点。一般而言,舆论是对国家政治、经济、民生、教育、宗教、国防、国际等公共问题的看法与评论。“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3],“舆论为在社会上占多数之关于公共问题之自由的意见”[4]。也就是说,舆论讨论和争辩的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公共论题,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社会发展,这是舆论的本质。相形之下,那些庸俗的或仅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公众人物的逸闻趣事不能称之为舆论。公众人物不等于公共论题,而公共论题面对整体大众,是大部分民众普遍面对的问题。
舆论的论题类型多样,良莠不齐,其中反映了公众的一些真实想法,同时掺杂了偏见和狂热的情绪。“近儒之研究群众心理者,谓其所积之分量愈大,则其热狂之度愈增。百犬吠声,聚蚊成雷,其涌起也若潮,其飙散也若雾。而当其热度最高之际,则其所演之幻象噩梦,往往出于提倡者意计之外,甚或与之相反。此舆论之病征也。而所以致病之由,则实由提倡者职其咎。盖不导之以真理,而惟务拨之以感情,迎合佻浅之性,故作偏至之论。作始虽简,将毕乃巨。其发之而不能收,固其所也”[1]。变化、偏至是舆论的固有属性,好的舆论适应环境为各界接受,不良舆论导致社会冲突动荡。本文拟梳理评述我国历代舆论治理的方法,以供借鉴。
一、我国古代舆论传播治理
舆论是公众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和言论,舆论的背后归根到底是人在起作用,物不平则鸣,舆论治理转至分析舆论的发起者是谁,他们属于何种阶层。舆论固然出自于公众,但不是指所有的公众,对于同一影响力事件,不同的阶层持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以我国古代而论,通常分为君主及其官僚集团、士林、民间三大类或四大类。舆论显然不是指所有这些人群的共有意见,其中君主和臣子的议论不能作为舆论,他们所说的是朝议。朝议对政策法律进行发布和解释,通常是不同官僚集团之间相互斗争,以意识形态为铺垫同时表达一定民意的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之间的论战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士林中也有一部分替君主造势并依附在君主和官员队伍当中为朝廷出谋划策的,朝议的文字主要由他们书写、加工。士林作为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本身就阶层来说并不独立,这些在朝知识分子的言论严格来说不能认作舆论,他们和朝议基本一致。与此对照,士林中的另外一部分“在野书生”的言论可以认作舆论,这类人群脱离了事件本身的直接利益而纯属履行“士”的公共职责,他们面向民众,是舆论的筛选者和符号修饰者。
上述与我们论题有关的是区分朝议和舆论,朝议是朝廷政策决策的核心部分,不能与舆论混同。朝议自古以来是各种言论最主要的集中场域,背后是各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表明所属阶层的观点态度。朝议一旦确定,各方遵守而行,声动全国,牵一发动全身。舆论的地位不可与朝议相提并论,舆论只是辅助朝议影响国家社会演化的微弱言论。我国古代舆论指民间舆论,古代文籍的记载明示了朝议与舆论的区别,如“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旧唐书·本纪第十八下·宣宗》)说明舆论出自民间万众,不是指士本身所言。又“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明史·本纪第十八·世宗二》)即朝议如果不寄望于民间,反之朝议决者,就未必再向民间咨询,朝议和舆论的主与次泾渭分明。
民间舆论的代表为公众,公众是数量最广大的群体,舆论的大量构成还是出自民间百姓街头巷尾的日常议论。现代社会民为贵,民的地位崇高,但在古代王权社会,民众的看法并不显得十分重要,他们的观点不系统,带有情绪渲染,难以传播开。在印刷术、报纸没有发明之前,依靠口耳相传,在熟人圈传播,而平时人们出行范围不过百里,所论很难形成舆论氛围。古代人大多不识字,不能将想法完整地书写下来,只是口头表达,只有当民众的观点汇聚成诸如预言这种类似歌谣的简单、琅琅上口的形式才能迅速传送,产生影响。这些预言歌谣通常直指朝廷更替,即谁当皇帝掌握权力,现实性和震撼力很强。但总的说来,古代舆论并不受特别重视,公众舆论的作用在现代民主制度后才显现出来。
如果舆论主体是民间言论,那么舆论内容就很难管理,因为民众散布在各处,活动时间模糊,难以做到精细管理。但从管理角度而言,主要仍是判断舆论出自何种人及其阶层之手,找到发声的主要群体,对其进行必要约束。读书人的言论最可能为多数人接受而形成舆论,他们总结表达出公众心里所想但是说不清楚的话,因此对读书人应当重视。读书人的言论可以管理,体制内的读书人吸纳进来,以鼓励惩罚并行的方式达到目标,少数人例外,一般在朝的士人对君主和官僚的批评再激烈,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统治的长治久安。谏议大夫的监察也是如此,是君主用来约束官员的手段,不可能对统治构成根本威胁。御史、谏议官职不高,而且向来是个摆设,作用不大,元明后因其无用而取消。谏议的无非是官员贪腐、道德不当等,“只论是非,不讲厉害”或半公开讨论,不能涉及根本政治制度变革。即便如此,封建朝廷对于那些敢于公开批评君主和激烈讽刺朝政的儒生都实行严酷制裁,如秦朝的焚书坑儒、清朝的文字狱等,不惜制造思想恐怖,不让著书,汉代清议尚且不可,只能发展为魏晋时期的清谈,玄学家们未敢臧否人物。如果对君主议论过分,则被廷仗羞辱或投入监狱、禁言、流放迁徙,历史上制造“不当”舆论者大多以悲剧收场。
士人中的“在野”读书人与在朝书生不一样,这部分知识人的言论难以捕捉,大部分与朝廷不同的论调就是他们在私底下发出的倡导,他们在民间引领百工,为民之首,是创设对抗朝廷的言论发源地,典型的如明代东林党人运动。在野书生在民间做巫医、算命郎中,教私塾,做师爷、管家等,这些职业不足以实现其抱负。始于隋朝的科举考试,让在野的书生凭借考试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巨变,使其发生向上的流动,平复胸中块垒,但只有少数幸运儿改变了命运,整体看这种制度对于大多数知识者来说是理想而不是现实。科举制度满足了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愿望,冲击了既有利益集团,利于安抚下层知识分子,触动中上层知识分子继续上进。但科举途径以外,还有大量的知识拥有者汇聚民间,他们若结党在书院学院,发出文字声音号召民众,其力量却不可小觑,历代王朝都是这些中下层士大夫在判断时势后运用谋略并连同一些秘密结社组织起义而被削弱甚至推翻的。
下层知识分子生活在民间,了解民众所想,他们的舆论针对具体事件,有时起到教化的作用。民间舆论的导引或线索通常源自突发事件,但根源还在于民众对事件判断的主体价值观念。民众思维和言论与其平时积累起来的教育有关,这些教育往往是中下层知识者通过潜移默化的传播而起,小说、报纸容易煽动民情,这是民意起势的根源。小说、戏曲等基本上是失意知识人创造出来安慰自己和时代的作品,而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如蒲松龄的小说就不仅仅是小说,亦具有社会政治的功效,移风易俗、讽刺时弊,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以及根据通俗小说改编的戏曲歌谣等,教人辨别忠奸美丑,都起到教导训化作用。
正如严复与夏曾佑在《国闻报》所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所说:“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5]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舆论为之一变,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近代以来,传播媒介一改旧式传统,报纸期刊盛行,着力于描摹民众思想变化,民众意见上升到政治舞台,舆论的引导力量由此发生了剧烈改变。
二、民国期间对于舆论的分析与控制
如上所述,“舆论是关于整个或一部分社会的福利以共同关心为中心依相互作用所组织之公众意见”[6]。意见围绕公众关注的问题展开,这些问题要上升为舆论,还要经过讨论环节。讨论有不同级别,其传播范围可至国际、全国,或仅限于地区等,不同范围的舆论,由其对应的公共机构日常处理。对于社会反应至为强烈的舆论应特别处理,舆论的激起是从策动、触发至渲染而蜕变的系列过程,有的越来越锐利,势如潮洪,有的逐渐趋于平静,无庸抗争[7]。而舆论的激烈之处,正在于和官议相违背。朝议或官议有时与舆论重合或大致吻合,这些讨论激不起多少舆论浪花,只有那些相互对立的不同观点才能够激起舆论浪潮。“舆论起自于何,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8]。征求民众意见,多少都会和官方有所不同,要认识舆论的这种特点,将舆论和朝议综合起来看。
近代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知识者职业出路增多,学校、研究院和报纸期刊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一些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直接参政的机会,但找到了更多安身立命之处。清末时期的记者、主笔、访员尚属于体制外或知识群中的边缘人,189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就有如左宗棠所说“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的说法,只有少数的《申报》《新闻报》等报,投身报业为未能中举的读书人的权宜之计。1895年后报馆逐渐汇成一股大能量,这时报纸不能专视为民间舆论,组办者为“声光炳然的魁儒硕士”所代替[9]。报纸数量激增,教育水平的提高使阅读报纸的人随之增加,新闻人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精英。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联系在一起,书报、学会、学校、政治、政党关联一处,很多报纸为政党机关报或市场报,对上传播民众诉求,对下传递上层信息,“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①参见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转引自倪琳博士论文:《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演迁》(上海大学,2010年)。,报刊实现了引导民众和批评时政的功能,报业报馆作为代表民众和政府的中介桥梁,监督政府,汇聚“第三种力量”。现代报纸不像封建王朝时期的邸报,其仅用于传递诏令等。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而已,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邸报登载的非舆论,而是朝议向下传播的一种载体。现代的报纸耳目一新,是为新报,为农工商贾们喜爱,“邸报之作成于上,而新报之作成于下”[10]。现代报纸,人人可阅,上下之交,既无隔阂,报馆由此“有助耳目、喉舌之用”[11],有名的“耳目喉舌论”于焉诞生。
为便于向民众传达传播,民国一些报刊标明是独立法人,保持言论自由,不做党争团体的附庸。储安平在《观察》创刊词强调说,《观察》是一个“发表政论”而非“政治斗争”的刊物,“大体上代表一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更无任何组织”[12]。《大公报》更是打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些报馆倾向于收集民间意见,报馆的主笔变为“舆论之母”,主编和编辑们转为民间智慧担当。“报馆在舆论已成之国则负代表之责,在舆论未成之国则负造作之责”[13]。报纸直陈利弊得失,言及如何兴利革弊,献积极之言。民国有“没有报纸杂志,就没有民国”之说,有名的报刊如《申报》《大公报》《新青年》《独立评论》《观察周刊》《东方杂志》等,都在引导舆论、转移时势方面树立功绩。这些报纸杂志制造的舆论演化为一种左右局势的势力。“此种势力,可以左右人类之倾向,决定政治之种类,转移人类之心理,改良社会之腐败,增进人类共同之幸福。其势力维何?舆论是已。其势力之宏大,实无以比拟,社会上一切变动,改革诸事绩,均因此而实现焉”[14]。报刊舆论革新旧式思想观念,演化为新的行动。
民国对于舆论的管理张弛不定。以国民政府为例,国民党政府初期的控制能力较弱,杂志报纸对于政府和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比较自由。在国民党政府取得了巩固地位,国民政府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和“训政”统治,力图统一全国的思想和言论后,对报纸杂志的检查就很严格了,一些报纸被勒令停刊。国民党先后制定了《出版法》(1930)、《宣传品审查标准》(1932)和《图书杂志审查办法》(1934),由宣传部专门成立审查处,审查各地新闻报刊。新闻文章未经审查一律不得出版,所出图书须冠以审查证字号,如果出现言论不当,动辄封报馆、扣报纸,甚至迫害记者。抗战前期舆论全部实行统制和检查,报纸不敢随意发表言论,而为党国需要甚至炮制假舆论,可见政治机构对舆论的控制程度。
民国学者主张发展健全的舆论,他们用“健全”一词形容舆论治理的结果。胡政之提出塑造健全舆论的必要条件:“如果另有一部分少数识者,别具见地,也尽可以公开研讨,不客气地交换意见,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数人在这许多不同的观点之间,根据他们对于事实之认识和理解,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选择一种他们所认为比较合理的议论,一致起来赞成它,拥护它,主张它,经过如此阶段,这便可以成为所谓‘健全而合理的舆论’。”[15]健全舆论的前提包括自由讨论、公开交换意见和各界理性选择。吴景超将健全的舆论分为批评、建议、讨论、舆论的法律化这四个实质,呈先后关系的过程。他分析舆论不发达的原因:①批评不能自由,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②缺乏真正的专家学者,缺乏真知灼见。大部分所谓的舆论都是“一些呼号,一些谩骂,夹着一些讥笑”,都是感情的发泄,而不是以理智为基础。不是言论不自由,而是没有人才,没有智识的领袖来充分利用这种自由。③缺乏讨论的态度。讨论的态度是虚心领略别人的理论及其主张,从别人的批评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并立即矫正。不可遇到赞成自己观点的便高兴,听到批评的声音便气愤,甚至不尊重人格,没有礼貌,相互攻讦。这种态度,没有价值,没有结果,不能生成成熟的舆论。④舆论缺乏发挥威权的工具。舆论要发挥作用在于能影响政治,违背舆论的政府要受到制裁。如果舆论只是纸上谈兵,政治不对舆论负责,甚至对舆论置若罔闻,那说话写文章都是白费力气,于是大部分人都面对问题将闭嘴不说话,说话起到作用,舆论才能发达[16]。胡政之、吴景超他们对于舆论的探讨,从舆论的实践和目标出发,说明了舆论控制的核心内容,概括了舆论的特点,对现在的舆论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三、现代媒体约制法:历史借鉴和现实
现代媒介越来越发达,有报纸、电视、电影、杂志、网络等,报纸、电视都变成传统媒介了,网络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舆论传播途径。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从BBS、博客到微博、微信,发布信息已不仅仅是信息公共部门独有的权力,每个个体都能够随时随地发布,媒体变成自媒体。发布的文字越来越短,传播速度加快,微博甚至达到了“秒传播”的“快闪”境界。网络社群中的QQ、SNS、Facebook以及开心网、人人网等,瞬间将成千上亿的人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科技的发展叹为观止。就舆论而言,传媒技术发展到今天,但凡遇到略微能激起社会反应的事件,就如同一块小石子投进池塘,即刻形成舆论传播的介质,舆论的刺激点勃然增加。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符号的提取组合成为简单的技术,舆论的构成不能缺少刺激符号及其渲染,这种符号要足够强烈,全面点燃人的感官神经,化作一种独有的象征[17]。“唤起社会的舆论,必须予以强烈之刺激,宣传的之重要性即在于此,特别是在人们感情昂进时候的刺激最为有效”[6]。现代媒体在掌握刺激要素技巧方面轻而易举,文字、声音、图像立体冲击,若是着力推出某种“声音”,即刻就会成为全民“围观”的论题,面对这种趋势民众只能是一群“沉默的螺旋”,无暇反思也难以抗拒。当前公共媒体和自媒体竞相辉映,信息资讯海量,不同的媒体发出不同声音,公众阶层更加分化,新新群体不断涌现,加上商业驱动下的网络公关和网络营销雇佣“水军”“打手”有意识地推波助澜,舆论体现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碎片化和分歧多变。
现代社会对于舆论实际难以规制,技术上可以做到关闭一些舆论的来源渠道,但总体上控制会遇到极大困难,大量跨国际的流动信息衍生,不能预料舆论从何处冒出来。这个时候宽容实际比禁止更为可行,宽容赢得良好形象,舆论的本质应是建立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以宽容和接受批评的姿态出现,利于推行社会民主获得好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保持信息的开放透明和自由流动,避免各种冲突的手段,让言论自由作为认识达成真理的微量要素而保存保鲜。但宽容不等于放任自流,不是对舆论不加治理,舆论本身具有弊端,“意见通常是不成熟的未加认真考虑的情绪表达,就性质而言,舆论破坏之能力大,建设之能力小”[4]。舆论本身都不是万能有效的,对待一些错误、含混的舆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将其辨明并扭转过来。
目前在舆论治理方面,需要对出现的各方观点进行比较、鉴别和引导,形成主流舆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舆论管理的永恒主题,通过导向、辩论增强舆论认识的合理性,将对事件评论的传播纳入正确的轨道。一方面国家媒体要发出主流声音,让主流声音压倒杂音,满足人们探悉事情真相的权利期待。另一方面培养体制外的“意见精英”,引导粉丝群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在事件发生之初,情绪和偏见占有很大的成分[18],先行引导舆论,积极领导舆论,避免舆论被少数人捏造操纵,是舆论管理的主要程序。对于明显违法的言论以及恶意诽谤和炮制的虚假舆论,毅然予以惩戒。“盖同人始终抱一理想焉,以为舆论之养成,非偶然也,必也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依此舆论而行之政治及社会事业,始能不误轻重缓急,不入迷途”①参见张季鸾:本报一万号纪念辞(天津大公报,1931-05-22),转引自倪琳博士论文:《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演迁》(上海大学,2010年)。。舆论的最终作用在于解决公共问题,建构友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当前的舆论环境,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言论治理,同样需要抓住纲领,关注舆论发出者,而不是将着力点置于那些不可胜数的舆论内容本身,主要约制报纸、电视、网络的主管以及学院知识人、民间有影响的意见精英等。拉扎斯菲尔德早就证明多数人是舆论追随者,他们倾向于越过媒介,从信得过的同一阶层中活跃交际分子的舆论精英那里接收信息和观点[19]。因此就舆论治理而言,对于意见精英设法招抚纳入是不二的选择。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行政吸纳政治,同样可以考虑学术吸纳政治的路径。当前的媒介环境,公众有大量发表意见的机会,但这种意见能不能传播出去具有影响,关键在于选择、过滤舆论的意见精英的把关人之手。对意见精英们的立场态度及如何引导处理,是历史沿袭下来的问题,也是现在舆论治理的关键,不妨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1]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J].广益丛报,1910(1):1-6.
[2] 朱显庄.舆论之分析研究[J].清华周刊,1934(7):12-21.
[3] 喻国明,刘夏阳.中国民意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77.
[4] 徐宝璜.舆论之研究[J].北京大学月刊,1920(7):105-108.
[5] 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M]∥舒芜,陈迩冬,周绍,等.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0.
[6] 陈固廷.“舆论”究竟是什么[J].留东学报,1936(4):1-7.
[7] 蒋绍炎.什么是舆论?[J].建国月刊(上海),1934(4):11-18.
[8] 论湖南官报之腐败[N].苏报,1903-5-26.
[9]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43.
[10]邸报别于新报论[N].申报,1872-07-13.
[11]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3.
[12]谢泳.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113.
[13]金其堡.舆论正义[J].北洋政学旬报,1911(33):1-22.
[14]刘国桢.舆论与社会[J].社会学杂志,1925(5/6):1-10.
[15]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J].国闻周报,1934(2):1.
[16]吴景超.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J].独立评论,1934(87):1-4.
[17]Erving Goffman.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M].New York:Anchor Books,1959.
[18]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1.
[19]Katz Elihu,Paul F Lazarsfeld.Personal influence: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55.
[责任编辑 勇 慧]
C912.63
A
10.3969/j.issn.1009-3699.2017.05.003
2017-08-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SH001).
邹千江,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媒体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