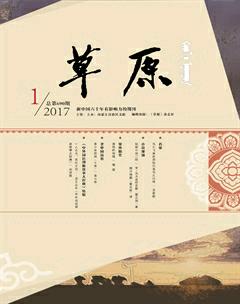夜行汽船
郭仲白
大学在新校区,校址位于一个江南县城偏僻的郊外。学校的宿舍楼紧邻一条京杭大运河的分支,站在宿舍的阳台能看到过往汽船上,船家养的白狗跑来跑去。宿舍楼前面是一大片荒地,每每晨起,薄雾弥漫,睁着惺忪睡眼站在阳台伸懒腰时,总能看到三两农妇在荒地上开垦。短短几月每日感受天气,顺便见证了一块荒地是如何被农妇的巧手料理得井井有条。
来这里终于到了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年头,很多不适都被慢慢淡化,但依然不能习惯潮湿的气候,这大概和乡音难改是一个道理。深夜,躺在床上,白日嘈杂慢慢消去,便能听到不远处过路汽船低沉的轰鸣。此时,是游子思乡的好时候,我总会想到我的姥爷。
记得上小学时,父母上班忙,姥姥姥爷来我家照顾我。一大早,姥爷会叫我起床,和我一起吃早饭,帮我梳小辫儿,骑车载我去上学。记得姥爷第一次给我梳头的时候,我很不信任他。因为按常理来说,姥爷是不会扎小辫儿的。我拿着皮套和梳子,披头散发地歪着头问姥爷:“姥爷你会梳吗?”姥爷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对我说:“会啊,当然会,你妈、你小姨她们小时候的小辫儿都是我梳的!”一听这话我兴高采烈地把头发交给姥爷梳,梳完一看效果真不错,甚至超过了从小就给我扎头发的妈妈。于是,给我扎小辫儿的重任就由姥爷全权负责。
过了一段时间,妈妈问我:“每天早上都是姥爷给你扎头发的?”我理所当然地回答说:“对呀。”妈妈听后便笑了:“你姥爷可真是有进步呀,都会梳头发了。”小时候的我认为和姥爷是最好的朋友,任何时候都维护姥爷。这时我觉得妈妈是在笑话姥爷,于是便气鼓鼓地说:“姥爷梳的可好了,比你扎的都好,你和小姨小时候的头发都是我姥爷扎的呢!”我沾沾自喜地以为这一席话已经让妈妈心服口服,可万万没想到一听这话,妈妈笑得更厉害了。妈妈说:“你就听你姥爷瞎说吧,小时候他从来没给我們俩梳过头发!”我一听急了,有人敢质疑姥爷梳头的手艺那还得了,于是赶忙辩解道:“怎么可能,这是姥爷跟我说的,而且姥爷还梳得这么好!”妈妈总算不笑了,慢慢解释说:“那是他想让你放心才这么说的吧,我们小时候你姥爷很忙的,基本不着家。”
当时年龄尚小,一直无法理解为何姥爷会和妈妈说法不一,于是便觉得妈妈是嫉妒姥爷的好手艺才不承认。直到几年前,我在姥爷家翻到一张相片,姥爷穿着及膝的呢子大衣,带着黑色绒帽,踩着铮亮的皮鞋,站在北京的一条马路上,笑盈盈地看着镜头外,那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事情了。我被姥爷帅气的外表迷倒的同时,终于解开了十几年前的那个问题。听妈妈讲,姥爷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妈妈小时候家里从不缺粮食。姥爷还开过汽水厂,小时候别人喝一口分五次咽下去的美味,妈妈他们都当水喝。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还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想而知姥爷得有多忙。一年到头家都很少回,更何况每天早上能给女儿们扎头发了。其实姥爷完全没必要为安慰我而说好话,毕竟我只是个小屁孩儿。梳完头发,吃完早饭,姥爷还要拖着他年轻时因打狍子而受伤的腿,一拐一拐地骑自行车送我上学。
时间就这样过去,我从一个头发都要姥爷给扎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能在异乡生活的成年人。我走过了很多路,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却无比怀念和姥爷玩捉迷藏藏在洗衣机里的时光。今年暑假,妈妈回家看望姥姥姥爷,我以路途遥远为借口没有同行。与到达姥姥家的妈妈视频通话时,姥爷在一旁说:“孙女你怎么不回来啊,你快回来呀,你想去哪玩姥爷陪你去,就咱们两个人,不带别人……”当时的我欲语凝噎,我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回答我为什么不回去。现在我也想问自己,为什么不回去?后来听妈妈说,姥爷的伤腿越来越严重了,脚肿得跟个馒头似的,都不能穿袜子。前些日子,他自己出门遛弯儿,家门口有个小斜坡,坡上有些小石子儿,别人一脚能踢老远的石子儿却把姥爷绊倒了,因为他的伤腿挪不开步。
钱塘自古繁华,每每去西湖总能听到《鸿雁》这首歌,江南的人们只把它当成一首旋律悠长的舞曲。可对于一个草原的孩子来说,其中蕴含的感情可想而知。鸿雁,向南方,心中是北方家乡。天苍茫,秋水长,你听,又一条汽船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