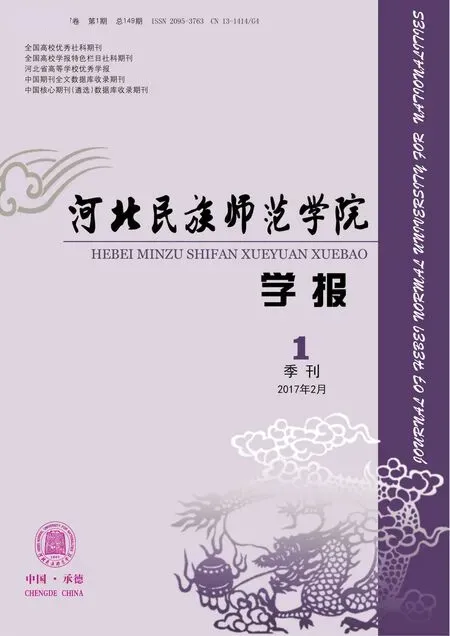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王杏芳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
试析荻生徂徕的人性论
王杏芳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2)
文章围绕荻生徂徕的人性思想进行分析,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徂徕对人性的基本认识取向,从人的“性者,生之质也”本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气质不可变化”,以这两点上来明确徂徕对人性的基本态度。之后再论述人虽然有本性,但又不限于本性,它在后天的过程中还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这便是第二部分要讨论的“习性”。习性与性善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与性、德、材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讨论的重点。另外,习性在受到诸种条件的影响时,应当如何去规范它使它合于正当性呢?以这个问题为线索,从而进入到第三部分人性善移而“养性”的话题。最后为本文结论部分。
荻生徂徕;人性;习性;人性善移
一、“性者,生之质也”之本性
人性论是徂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徂徕在这个问题是怎样论述的?它有何特点?与传统的人性论点又有何区别?关于这些问题,先来进行简单的分析。
徂徕从“生之质”的角度来解释人性,他认为“性者,生之质也。宋儒所谓气质者是也”(《辨名》)以及“性者,性质也。人之性质,上天所畁,故曰天命之谓性。”(《中庸解》)。①以“生之质”来解释人性,在《尚书》以及《诗经》等书中也曾出现。《今文尚书》中出现过两次:“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食康,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西伯勘黎》)以及“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召诰》)这里的“性”具有“生之质”的含义。
首先“性者,生之质也”(《辨名》)与“性者,性质也” (《中庸解》)这两句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人的气质之性。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徂徕在第二句中机上了“天”的概念来解释,“上天所懶”之“畁”是给予之意,也即“人之性质”是“上天”所给予的。②徂徕笔下的“天”具有自然和人格宗教性两方面的含义,不是内在道德意义之“天”。
从徂徕对“性者,生之质”(《辨名》)的第一个命题到明确人性之来源的“人之性质,上天所畀”(《中庸解》)这一个命题来看,可以发现徂徕是在强调人之自然而然的事实层面之“性”。实际上,徂徕的这一论点是针对程朱理学的“天命之性”及“气质之性”二元人性论而提出的。
“天命之性”一说首先来自于张载(天地之性)③“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天命之性”的说法最初是来源于张载的“天地之性”。,之后被二程及朱熹等所继承。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天命之性”指从天而来的性,“天即理也”、“天命之性”就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人天生具有的本然之性;而通过借助于“性即理也”(《二程集》)、“斯理也,成之在人则为性”(《二程集》)等论述,为理在人身上找到呈现之处,也为“性”找到形而上的本体依据,使性具有超越性,又具有内在性。而且作为人的本然之性的“天命之性”是纯善的,这是人的先天善性。“生之谓性”是指人生下来后所禀受的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人的现实状态,而作为现实状态呈现出来的“气质之性”则是有善有恶的。但实际上“天命之性”是“性之本”,“生之谓性”①“生之谓性”是二程在解释与“天命之性”相区别时所使用的一种说法,如二程所言“生之谓性。性即气,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后朱熹弃“生之谓性”的说法,而直接采用张载的“气质之性”,至此形成学界普遍使用的“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是“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二程集》)。因此从根本上说,人性先天是善的,恶是人生而后有的。但是两者之间又是不离的关系,“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程集》),如果只是讨论“天命之性”,不议“生之谓性”则不完备,因为人总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不可脱离其一,相反如果只讨论“生之谓性”而弃“天命之性”,那么就会使得人之为人之性不得昭示出来。
徂徕对宋儒的二元人性论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在只承认“生之谓性”的基础上,反对“天命之性”的说法,从事实层面重新定义人性,这是徂徕去道德价值化的第一步。宋儒的二元人性论实质上圆满的解决了先天性善和后天性恶的问题,但是徂徕直接以“生之质”来解释人性,从其根源性的设定上就否定了人性的道德价值。人性是“生之质”,单纯从“生之质”这一点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这里所说的“一样”不是在性善或性恶或性三品基础上的相近,而是停留在“生之质”这一基础上的相近。徂徕与宋儒截然不同的人性取向决定了他对人性的第二步解读也将与此有所差异。
他否定了宋儒的二元人性论理论,因此宋儒所建立的以“天命之性”为本然纯善之性,以“气质之性”为后天恶的来源,并通过修养后天气质之性以回归清澈澄明的天命之性的说法,即“变化气质”一说,他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直接认为“气质不可变化”。
徂徕认为 “及变化气质,学为圣人类,皆非先王孔子之教之旧矣。”(《辨道》)也即,在他看来,变化气质先王孔子之教中不是本有的教义,而是宋儒根据《中庸》所臆造出来的,他说道:
变化气质,宋儒所造,渊源乎中庸,先王孔子之道所无也。……且气质者天之性也,欲以人力胜天而反之,必不能焉,强人以人之所不能,其究必至于怨天尤其父母矣,圣人之道必不尔矣。孔门之教弟子,各因其材以成之,可以见已。……据于德,依于仁,各随其性所近,以成其德,苟能得其大者,皆足以为仁人焉。(《辨道》)
徂徕首先明确了“变化气质”在先王之道中本就是没有的,而其之所以产生在于宋儒臆度孔子之意,依乎《中庸》从而造出“变化气质”之理论。在明确先王之道没有“变化气质”这一说的基础上,他从“气质之性”的角度对气质不可变化这一论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论证之一在于,他认为“气质者天之性”,也即如上文所分析的,人之性质是由“上天”所赋予的,因此想要通过人力来反抗上天所赋予我们的“性”,其结果是“必不能焉”,就像是强人之所不能,最终只能是“怨天尤其父母”。其二,他以孔门为例,徂徕认为孔子教育他的学生,都是“各因其材以成之”、“皆各以其材成焉”,也就是说孔子教人从没有要求他的学生变化各自的气质,而是根据学生本身的气质“据于德,依于仁,各随其性所近,以成其德”(《辨道》),比如“由之勇,赐之达,求之艺,皆能成一材,足以为仁人之徒,共诸安天下之用焉。”(《辨道》)由、赐、求都是按照他们自身的气质“得道”其中一端从而成一材,“皆不必变其性”(《辨道》)。
徂徕在完成上面的具体分析后,又对问题进行了更为追根寻底式的深入性探讨。毕竟“变化气质”一说在宋盛行一时,那这在先秦本无的“变化气质”之说到宋代为什么会成为主流?其缘由又何在?他抓住了怎样的关键证据从根底上否定“变化气质”而肯定“气质不可变化”呢?
徂徕以礼乐为支点,找到了攻击宋儒“变化气质”的所在。他认为宋儒之所以认为气质可变在于他们不知礼乐,“礼乐得诸身,谓之德,古之君子,皆礼乐以成其德,岂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气质为说,不知礼乐者也。”(《论语征·述而》)在徂徕看来道不离礼乐刑政,离礼乐刑政就没有所谓的道,“道者统名也。举礼乐刑政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言之,非离礼乐刑政别有所谓道者也。”(《辨道》)而道与礼乐又是不分的关系,而他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论语徵》中也多有所见,现简单列举如下:
(1)学之道,在默而知之。何者?先王之道礼乐是已。礼乐不言,欲识其意,岂言之所能尽哉。学之久则自然有喻焉,故子欲无言。(《论语征·丁》)
(2)二子皆不识先王之教全在礼乐故而。(同上)
(3)且古所谓学者,诗书礼乐而已。其在孔门,不言而可知矣,故谓诗书礼乐为孔子常言者。(同上)
(4)先王之教,诗书礼乐。(同上)徂徠反复强调先王之道存于礼乐刑政之中,离开礼乐刑政便没有先王之道了,因此在这一点上他改变了宋儒认为道存在于人伦日用之中①如《四书章句集注》:“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之者,则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盖天命之性,仁、义、礼、知而已。循其仁之性,则自父子之亲以至于仁民爱物,皆道也;循其义之性,则自父子之亲以至于仁民爱物,皆道也;循其礼之性,则恭敬辞让之节文,皆道也;循其知之性,则是非邪正之分别,亦道也。”认为道存于父子君臣仁民爱物等人伦日用之中。的看法。以道存于六经的礼乐之中,而非存在于人伦日用之中为起点,批判了宋儒不知“古之君子,皆礼乐以成其德”(《论语征·述而》)而落入“变化气质”之说,进而主张“殊不知古之成于道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岂必变化气质哉。”(《论语征·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而得存在于礼乐之中的多端之道的一端从而“大者大成,小者小成”。
外在礼乐是一种得之于身的问题,而“得”是践行问题,因此对礼乐,尤其是对礼乐被得之于人的重视,使得徂徕把视点从内在的心性转向外在的身得,从而对决定此趋向的人性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大转变,实现了从二元人性论所注重复归的“天命之性”到开启强调“先天所畀”且去掉了善恶价值评判的“气质之性”。
“性者,生之质也”徂徕对人性的第一层基本认识,它认同区别于二元人性论的“气质之性”,并以此为基础,倡导“气质不可变化”之说。“气质之性”是“上天”所予,但人是要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总会受到诸种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受到社会性因子影响的人性,又该如何称呼呢?
二、“习与性成”之习性
上文曾在论述宋儒之所以认为气质可变在于他们不知礼乐时,简单地提到过礼乐的问题,而徂徕在强调礼乐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人性结论是:“人之性万品,刚柔轻重,迟疾动静,不可得而变矣。……习善则善,习恶则恶。”《辨名》人之性是“生之质”,是“上天所畀”,这一点是相同的,但各人禀赋不同,从而产生“刚柔轻重,迟疾动静”(《辨名》)的人性万品。然而人性万品都是不可得而变的,排除了注重内在心性视角的“天命之性”存在的可能性,及“变化气质”复归“天命之性”的必要性,强调外在礼乐的身之“得”而主张“气质之性”。但礼乐毕竟是一种外在之物,外在礼乐得之于身,不是静坐修养便可得,而是需要践行的功夫,践行用徂徕自己的话说便是“习”。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学习养德成才,其目的不是为了“扩天理而遏人欲”(《孟子集注》),而是为了“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诸安民之职已”(《辨名》)。因此以礼乐基点对宋儒变化气质的批判,到使礼乐得之于身的“习”之手段,出现了人性论的第二个命题,“习与性成”。
“习与性成”最早出现在《尚书·太甲上》中,它所强调的是后天环境以及个人内心变动对人性的变化能够产生影响。①太甲是商汤的嫡长孙,太丁之子,商朝第四位君主。太甲在继位之初,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但是太甲不守成汤法典,失去为君之道,于是伊尹对其进行劝诫,“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尚书·太甲上》)蔡沈传:“狎,习也。弗顺者,不顺义理之人也。桐,成汤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为乃不义之事,习恶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习不顺义理之人,于是营宫于桐,使亲近成汤之墓,朝夕哀思,兴起其善,以是训之,无使终身迷惑而不悟也。”由于太甲不遵守成汤的法典,于是伊尹把他放置到桐官(桐官是成汤的墓陵之地),使太甲亲近商汤的墓陵之地,朝夕哀思,使太甲兴起善性。王充也有相似的说法,如“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不善不恶,须教成者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论衡·本性》)但区别在于,王充是将人性定为三品,只有中人之性是“在所习焉,习善则为善,习恶则为恶”,而上品与下品的“极善极恶”之人,则“非复在习”。
到明末王夫之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把“习”放在人道的基础上。强调人在环境中的学习和实践,王夫之认为人性的善恶,就好像是古代善射的后羿,而其善射并不是来自于天生,即“性自生”,而是来源于习巧,是出于“内正外直审几发虑之功”的结果。因此“性为最初之生理,而善与不善皆后之分途也”(《四书训义》卷三十五)。善恶是习之而成的,“人之皆可以为善者,性也;其必有不可使为善者,习也,习之于人大矣”(《尚书引义》卷三),又“性无定质,而足以任人之运用。以之为善可也,无不足也;以之为不善亦可也,不必善也。是故随习相而远。”(《船山全书》第八册)他认为性没有定质,会随着“习相而远”,从而使得“以之为善可也”、同时“以之为不善亦可”,突出了人性的形成离不开人的自觉意识与活动。
徂徕认为“性与习不可得而别者也”,因此他在对“性相近也,习相远”(《论语·阳货》)进行解释时,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者,性质也。人之性质,初不甚相远,及所习殊,而后贤不肖之相去,遂致辽远也已。”(《论语征·壬》)他是在“气质之性”的本性基础上谈论人性问题。徂徕认为人性的相近是指从上天“所畀”的角度来看,而不是指每个人的性都是一样的,“及所习殊”即在后天的“习”的过程中由于所习不同而产生了贤与不肖相距甚远的现象。
从肯定人人性相近(对此相近性的追问不是回到被中国主流传统所肯定的天理本然之性),而转向生之谓性,即都来源于“天之所畀”的刨除了善恶价值评判的气质之性。但是他没有把问题停留于此,对“生之谓性”的人性本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引向了“习”的问题的讨论,即习性。
“习”的引入,是徂徕人性论的一大特色,那“习”在其人性论理论中又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
对“习”的讨论离不开“移”,人性善“移”是理解“习性”的前提。“气质之性”不可变化,及人性善移,这两句话从表面上来看可能会产生误解。既然气质之性是不可变化的,那人性善移这种说法是否欠,可能会产生类似的疑问,而对这个表面看似矛盾的地方,徂徕通过“移”字的使用解决了两者之间的逻辑悖论。
“善移”不是指向善移的性的向善倾向,而是指人性容易发生变动,但它本身又是“不动”的建立在人人所具有的本性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后不同于前的一种“成就”状态。“移”这个概念在徂徕的文本中随处可见,如:
盖移云者,非移性之谓矣。移亦性也。不移亦性也。故曰上知与下愚不移,言其性殊也。中人可上可下,亦言其性殊也。不知者则谓性可得而移焉,夫性岂可移乎?学以养之,养而后其材成,成则有殊于前,是谓之移。又谓之变。其才之成也,性之成也,故书(太甲)曰:“习与性成”,非性之移也,学者察诸。(《辨名》)
“移”,不是指“移性”,因为“不移”也是性。因此《论语》中有“上知与下愚不移”,性是不可移的,只是从学而养、养而成材、成材而与前不同的角度来讨论“移”。“材成”是习之暂时完成,而“习成”便是性成的过程。
“性”与“习”之间的关系,中间还涉及到“材”的问题。移是人之性,不移也是人之性,性的特点在于殊,每个人在先天“所畀”这一点上是相近的,但是表现在每个个体身上,它又是“万殊”的。因此“移”只是说明在与之前相比的不同,即成材的不同。性是不移的,不可变化的,能“移”的只是根据每个个体的性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材,从人的“成就”上所说的“移”,也就是说性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人的成材结果。从每个人的前后成就角度上来把握的话,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其不断的变化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不断“移”的过程。但是在这不断的一步一步发生“移”的过程中,有一东西是永恒不移的,即人之性。徂徕在肯定人性不变的基础上,即人性唯一不变的基础上来解释人性成材之成就上的“移”。
又如,“人之性万品,刚柔轻重,迟疾动静,不可得而变矣,然皆以善移为其性。”(《辨名》)人之性各不相同,刚柔轻重,迟疾动静,这些人的性都是不可变的,人先天有其固定不变之性,而这固定不变之本性是决定他今后成材不同的根据所在。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人性,但根据各自不变的人性特点会成为不同的“材”。
如上所述,性“移”涉及到了性、德、才三者,那么作为习性前提的“移”,其中的性、德、材三者之间的逻辑顺序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先王之道的最高目标就是仁,仁是儒家学说中关于政治的最高境界,徂徕认为仁就是统治者像父母抚育子女一样抚育百姓,让百姓安居乐越,繁衍生息,所以他更加注重仁的客观效果。因此只有主观动机上的安民而没有安民的客观效果的仁只是与佛老一样的空虚之论。如朱子强调的心,仁斋讲的慈爱,都是只强调主观动机,不问有没有实际的安民之效果,所以都是“不学无术”之谈。与仁的内在性相比,他更为强调仁的实际功用性,其次他认为仁和道一样都是包括性的,所以在仁的要求或者规范之下,需要各种人才,同时为了实现“仁”,需要各种人才的合作。
但是人材的实现又离不开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先王之道,因为先王之道是社会的全体性。人通过先王之道及其所教实现自身的社会性,也即当人纳入到先王之道的范围内的时候才具有了自身的社会性,在先王之道形成之前,人的社会性是不成立的或者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问题。在圣人“造”了先王之道之后才有了关于人的社会性问题,他所关注的是在圣人制作道之后的人的社会存在形态,关注人在先王之道范围内的社会性。
然而人参与先王之道的社会性的具体表现在于成材,才的基础在于性,而性又将通过每个人的德表现出来,所以性之“移”所表现出来的逻辑是:性——德——材。当然人材的形成在此还有标准问题,这个标准被徂徕设定为一系列的德目,如仁、智、圣、孝悌、忠信、恕、诚、谦逊不让、勇武刚强毅等等。
可以看出人性“善移”之“移”是通过性——德——材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具体表现出来的,而德和材实际上又是一件事,德是得于身之德,材是得于身之德的具体外化。因此,可以进一步选取人内在的“性”和将性具体外在化的“材”为中心,即甚至可以说“善移”是通过性——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实现“移”本身的运转。
“善移”之“移”不是人性之移,而是根据性之不同而有不同之材的形成,而在依性成才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习”的参与而使得性最终以得完成。通过习,而使得性“成”,这里的“成”是指实现之意,“性”本身是具足的,但是它在初始时是一潜存的时期,而从潜存的未实现状态到现实的实现状态,中间所依借的是“习”。
从性到材的过程,中间所凭借的“习”是一种外在环境的习染,同时还有表现在行为上的“习行”,也即它不简单是一个外在环境的问题,而是在环境之中关涉到主体作为的行为,而其主体行为方面主要是指身体部分。恰如徂徕对“德”的解释一样,他从“得于身”的角度来解释德,如:
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僅有得乎心,岂足为德乎?古曰:礼乐得于身,谓之德,得于身者,能诚也,能诚则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论语徴·丁》)
从得于身谓之德的解释角度否定了宋学以心为落脚点来解释“德”的解释传统。但是以心或身为出发点的两种解释,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思,徂徕的身体论,并不排斥心的作用。按照子安宣邦的说法,与其说徂徕是身体一元论,还不如说是身心一元论,但需要注意的是,徂徕重身,同时也重心,但是他对心的重视并没有把它放在一个明确的地位上,他把心直接纳入到身体之中,因为讲身则自不能离开心而谈。但是若一定要分出个前后和根本的话,他是企图通过谈身来进入到心。先王之道本就是一外在的社会行为标准和规范,因此对于如何纳入到这种行为标准之中,他所找到的答案是践行,也即是习行。通过行为主体的这一主体作为,并且这是一个不停息的过程,在这个渐行渐深的过程中把外在的行为规范纳入到主体的内在反思之中,从而通过“习”这一过程实现外在规范和内在理念相融合,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即是徂徕所强调的移性、成材之过程。
因此,徂徕通过对性、材、习(性、地、材、习)的运用,以三个亦或是四个概念为基础解释了“移性”这个思想。在这一点上,徂徕抛开了关于性的价值判断,人性如何的价值评判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同时对“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也不作区分。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他的思想中不存在“天命之性”,而一定要用“天命之性”这一词时,其意义与宋儒也大不相同。在徂徕的语境中“天命之性”只是带有自然性和人格性的“上天”所“给与”的性,是人先天所有的,但是这个先天所有之性,本身并没有道德上善恶的区分,只有是否符合先王之道并在其先王之道的范围内是否能够根据其性以得德而成材的善和恶。在先王之道的多端之内得德而实现其中一端并成材便是善的,“性移”是获得“德”的前提,也是“材成”的前提,而“习”则是其中的条件。
人性“善移”的基础是“习与性成”,而“善移”最终要通过具体的外在化而得以显现,即在“习”的引导下,将性——德——材(亦或性——材)之间的结构使“移”外在化的逻辑顺序得以具体展开,使其完成了系统的习性论阐述。
习性的讨论是通过性、德、材之间的逻辑关系完成的,但再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深思发现还存在一个问题急需解决。即人根据自己的第一本性而得德进而成材,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呢?还是一个人为的过程?针对这些问题,徂徕提出了“养”这一话题,他说“学以养之,养而后其材成。成则有殊于前,是谓之移,又谓之不变。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辨名》),因此习性之“移”需要人为之“养”,而得德,最后以成材。
三、人性“善移”之养性
人性善移,通过“习”来完成它自身的“移”,但是“习”本身不是无目的无规则之“习”,而是要通过“习”来导向徂徕思想中的最高目标,即先王之道。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放之不理,而是要“养”,“学以养之,养而后其材成。成则有殊于前,是谓之移,又谓之不变。其材之成也,性之成也”(《辨名》),然而“养”又不是没有任何规定或是依据的“养”,而是按照每个个体各自所禀受的性而“养”之。
所谓“养”,是指养材、养德。但是“养”的基础是建立在每个个体自己的性的基础之上的。也即“养”不是一种毫无规则性的随意之养,而是在认识到自己的“性”的基础上,按照个人“性”的特性而加以培养,因此是“各随其性所近而养之”(《辨名》)。但是建立在近于个人的“性”的基础之上的“养”,其“养”的目的还是“移性”,而“移性”说到底又是为个人参与先王之道,实现先王之道的一端而服务的。
也就是说,在以“移性”为目的而实现先王之道的这个最高目标上,中间是通过“养”来实现的。“养”本身是建立在先王之道这个最高的目标上的,徂徕说道,“大氐先王孔子之道,皆有所运用营为,而其要在养以成焉”(《辨名》),“养”是先王之道的内在要求。先王之道是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规则而存在的,在这种人为参与的非自然的社会性规范之下,所有的运用营为都具有一定的目的。因此都有要为了达到目的有所“成”,而其“成”的实现关键在于“养”,如徂徕所言:
大氐人,物得其养则长,不得其养则死,不啻身已,才知德行皆尔。故圣人之道,在养以成之矣。天地之道,往来不已,感应如神,为于此而验于彼,施于今而成于后,故圣人之道,皆有施设之方,不求备于目前,而期成于他日。日计不足,岁计有余,岁记不足,世计有余。使其君子有以自然开知养材以成其德。小人有以自然迁善远恶以成其俗,是其道与天地相流通,与人物相生长,能极广大而无穷已者也。(《辨名》)
就正如物得其所养则能正常生长,但不得其养则只能走向死亡一样,圣人“造”先王之道就是为了养人,从而让人在先王之道的浸润之中得以移性成材。先王之道从其政治的表现形式上来说是一种规范,但是这种规范不同于一般的规范,因为它是以礼乐为手段,“礼乐不言,能养人之德性,能易人之心思,心思一易,所见自别,故致知之道,莫善于礼乐焉。”(《辨名》)又,“故乐者生之道也,鼓舞天下,养其德以长之,莫善于乐,故礼乐之教,如天地之生成焉,君子以成其德,小人以成其俗,天下由是平治。”(《辨名》)在这种礼乐的氛围之中自然浸染以被“养”,从而自然以成其德,自然开知养材,最后再自然迁善远恶成其俗。
因此我们看到,“善移”以人性为前提,以礼乐为手段,实现“养”人得德成材的目的。“善移”的基础是“习与性成”的理论前提;“善移”的展开是各随其性所近而“养”之;而“善移”的展开所实现的结果便是成材。
习、移、养三者之间互相循环的结果,从根本目的上来说是为了先王之道的现实化和社会化,而从直接目的上来说则是为了成材。但是先王之道和成材毕竟不能分开,成材也是为了先王之道的展开,而先王之道的展开只能通过具体个人的成材来完成它自身所提出的社会性建构,“善移”所实现的便是在多端之道中得道之一端以成材。
四、结 论
徂徕以“上天”所畀的人性、“性者,生之质”为基础,同时在各自所禀受的不变的人性的基础上,加入“移”的概念,而解释人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气质变化之变化,而只是依据在气质不变的基础上的人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的变化。人性相殊,每个人各自禀受的性是不同的,且与此同时人性都不可变化,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不可变化之中,不可变化是绝对性的前提,但是在此绝对性的前提之中,为了缓和和解释人性得以成材的问题,引入了“移”的概念,即人性“善移”。然而人性善移之“移”,不是指人性之移,而是人性通过“移”的作用实现了它的外在化显现,而展现为具体的有德、有材,也就是从性到德或者材的形成的“移”,但是实现“移”这一结果,是在“习”的认识的引导之下完成的。从根本上来说,“习”是践行的问题,即人所禀得的不变之性,要通过践行的中介,而实现它自身的外在显现。因此徂徕的人性理论,是以性近论为基础,以性善移为展开,以习性为中介条件,以养性为规范,从而完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性论叙述。
徂徕批判了宋明传统的人性论,从性殊经过中间的性“善移”,最后达到习性的结论,三者之间缺一不可,是徂徕完成其人性论建构的基础,同时也是圣人“造道”的前提。自古关于人性的讨论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但是在此基础上如何完成自身的建构,并将之与传统主流的人性论区别开来,而同时又为其先王之道的形成服务,就是徂徕需要思考的问题。他通过现实的人性相殊为人性论的理论基点,加入“移”的人性特征,同时以“移”为分析对象,进而引申到实现“移”的“习”之功夫,通过层层嵌套的关系,完成了从人性相殊经人性善移,进而到完成习性论的理论建构。以此人性论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一套人性与先王之道之间的关系。圣人“率性”以“造道”,“造道”的前提之一在于“性”。但“造道”本身具有其自身特色,它是区别于天地自然的一种人为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然与人为的分界,虽然圣人所造之道有“天”的前提性保证,但他笔下意义上的“天”区别于义理上的天,此“性”也区别于宋明的二元人性论,作为先王之道之前提基础的“天”和“性”,都是在先王之道的范围内而展开的,也即都是为先王之道而服务的。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 [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董灏智.儒学经典结构的形成及其在近世日本的变迁 ——以“四书体系”和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中心[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
[5]今中宽司,奈良本辰也编集.荻生徂徠全集[M].東京:河出書店新社,1975.
[6]宋红兵.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J].求是学刊,2005(5).
[7]平石直昭.荻生徂徠年谱考[M].東京:平凡社,1984.
[8]子安宣邦.徂徠学講義「弁名」を読む[M].東京:岩波書店,2008.
[9]小岛康敬.徂徠学と反徂徠学[M].東京:ぺりかん社,1994.
[11]小岛康敬.「礼」と「楽」による統治——荻生徂徠の統治理念[A].儒家思想与理想之治论文集[C].北京:国际儒学论坛,2013.
An Analysis of Ogyu Soral '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ANG Xing-f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Ogyu Soral 's human nature,and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o analyze Sorai's basical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Human nature is what be bornd. And he thought ‘temperament cannot be changed’. These two points reflect Sorai's basic attitudes towards human nature. Following this, he further argues that although people have human nature, they are not limited to such nature, since the nature can be affected by various posteriori condition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re crucial in this part of discussion: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xing’ and the variation of human natur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nature, virtue and material? In addition, if ‘xixing’ is affected by various conditions, how can it be subject to norms so as to satisfy justifiability? This leads to the third part of human nature.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Ogyu Soral;human nature;xixing;human nature’s transformation
B313
:A
2095-3763(2017)-0057-08
10.16729/j.cnki.jhnun.2017.01.010
2016-12-13
王杏芳(1990- ),女,江西修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日思想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