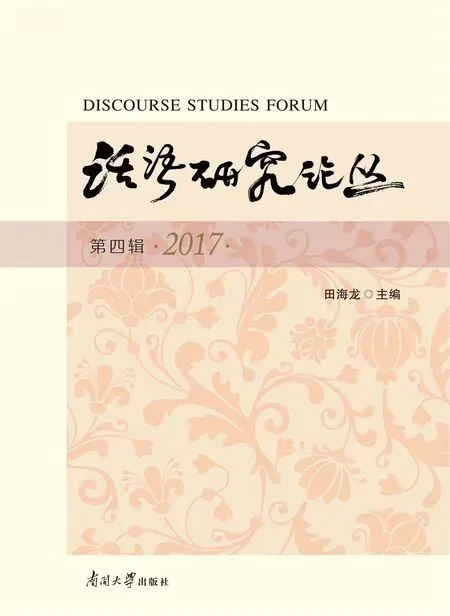从“治疗疾病”到“照顾生命”的职业认同定位变化——关于病人临终和死亡的医生叙事分析*
◎王景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从“治疗疾病”到“照顾生命”的职业认同定位变化——关于病人临终和死亡的医生叙事分析*
◎王景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研究采用叙事定位方法分析了一名肿瘤科医生关于病人临终和死亡的叙事话语,探究了其中的职业认同变化。研究结果发现该医生的职业认同经历了从“规避死亡的医生”到“走近死亡的医生”、从“与临终病人隔离的医生”到“去牵临终病人手的医生”、从“治疗疾病的医生”到“照顾生命的医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通过死亡、临终病人和职业三大主题叙事中的不同定位呈现,在这个过程中,叙事者也逐渐认识到这些照顾临终病人的经历是巨大的“礼物”。
叙事;临终;死亡;定位;职业认同
1. 引言
本研究聚焦肿瘤科医生有关病人临终和死亡的叙事,探究其中的叙事定位和职业认同建构,分析语料是笔者学位论文项目的一部分。研究的大背景基于整个社会开始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如好的死亡(good death)、尊严死(death with dignity)以及临终关怀等引起的广泛讨论。另一方面,不论在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中,临终和死亡仍旧是禁忌话题,谈论死亡会让人们感到不舒服或沮丧,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达成共识:不论对于临终病人,还是对于与死亡近距离接触的人们,坦诚和公开地讨论临终和死亡对于挖掘死亡的正面意义和积极体验都是非常重要的(Semino, 2014)。
医院是见证死亡的机构化场所,处理临终和死亡也是重症科室医护人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相对于普通科室的医护人员,经常与临终和死亡病人打交道的肿瘤科医护群体是一类比较特殊的群体,从第一次面对死亡病人的紧张,到后来可以独立和冷静处理,以及在随后的工作中见证更多的死亡场面,这些与临终和死亡接触的经历成为他们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影响着他们的自我建构和认同变化。本文是对一名肿瘤科医生工作经历的叙事分析,基于定位理论(Bamberg, 1997)的分析框架,追踪叙事实践中的不同定位,呈现叙述者有关病人临终和死亡叙事过程中的职业认同变化。
1.1 职业认同与叙事定位
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学界对认同的认识也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传统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认同是属于个人的、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不依赖情境的自我特征,并且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而后现代理论持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认为认同具有关系性,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依赖一定的情境,与话语和交际过程紧密联系,并且是流动和不断变化的(Giddens, 1991; Bauman, 2005; De Fina & Georgakopoulou, 2008)。作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形式,叙事呈现了“建构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群体与特定情境和事件相关的形象,也为叙事者提供了重新想象生活和建构(重构)认同的方式”(Harvey & Koteyko, 2013: 91);同时故事的建构方式也反映了叙事者希望得到怎样的理解,以及所指向的自我意识。Riessman(2008)认为叙事的核心功能是建构认同;叙事者通过叙事可以凸显其中的某个特定方面或方向(Anderson, 1997; Cohler, 1982)。
本研究考察的是认同的一个特定方面,即职业认同。职业认同是指基于信念、价值观、动机和经历的职业自我概念(Ibarra, 1999; Schein, 1978)。本研究聚焦的职业认同与叙事者的工作场所和其中的角色相关,即在医院工作的经常接触临终和死亡的肿瘤科医生群体的职业认同。死亡叙事与医护群体职业认同研究的主要对象为重症科室和临终机构的医护群体,分析该类群体对死亡和自身工作的解读,并探究叙事中的职业认同建构。如Osterlind等(2011)对瑞典4家养老院的护理人员的叙事研究发现,护理人员谈论死亡时的话语结构表现为规避死亡和面对死亡之间的移动,其主要表现在规避死亡;Candrian(2014)采用“驾驭/驯服”(taming)来形容临终关怀和急诊科医护人员对死亡的描述,并且发现医护人员对死亡和工作的定位会影响其临终护理决定;Semino等(2014)对13位英国的临终关怀机构管理者的死亡干预叙事研究发现,叙事者的话语具有鲜明的形式和功能特点,这些特点在建构该群体的职业观点、挑战和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Davies 和 Harré(1990)最早将定位(positioning)引入叙事研究领域,将其定义为“多重自我的话语建构”(p.47),定位是动态和不断变化的,并且在叙事过程中呈现的,区别于静态和相对稳定的“角色”概念。定位这一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Hollway(1984)性别研究中所采用的定位(position)概念。Bamberg(1997)继承并发展了Davies和 Harré(1990)的理论,认为叙事所有的表现特征都服务于话语意图和认同建构,人们在谈话中不断定位自我和他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情景化的社会人。Bamberg区分了三个层面的叙事定位:1)故事世界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2)叙事者如何定位与听众的关系;3)叙事者如何定位“我是谁”(1997: 337)。研究者在阐释说明部分引述了对一段叙事的分析:
“我们当时在酒店打电话聊天……给这个孩子约翰……打了三个小时,一个晚上的电话账单高达15美元,我妈妈非常生气,像个女巫一样。”(p.338)
故事中的主角“我们”和反面人物“我妈妈”形成了青少年之间同盟关系与成年人世界的对抗(第一层定位),并且呈现了一定的道德立场和认同主张,即青少年与成年人有关电话账单和责任的冲突,叙事者向访谈者(听众)呈现的是对现有道德秩序的质疑和挑战,这些认同冲突在叙事者对访谈者的提问进行应答时呈现出来(第二层定位)。Bamberg在最初的研究中没有对第三层定位进行细致分析,在后期研究中进一步解释了叙事的第三层定位,将其阐释为“叙述者如何在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或宏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中定位自我意识和认同”(Bamberg & Georgakopoulou, 2008: 385),上述材料中的第三层定位即“我们”挑战有关现有道德秩序的叙事,对抗成年人世界,建构青少年群体具有反抗意识的认同。定位是一个基于实践的概念和一种情境化实现,与社会行为相联系,话语中的定位可以实现不同的认同。定位理论提供了认同在不同层面呈现的动态模型:认同来自故事层面的人物定位,即被讲述的自我(the narrated self);互动层面的叙事者定位,即讲述故事的自我(the narrating self);社会层面的叙事者定位(the social self)。因此,叙事定位理论将话语呈现和话语互动层面的认同结合起来,并实现了认同建构的宏观过程考察,定位理论也成为探究叙事中认同建构和协商的重要方法。
医护人员的工作经历叙事研究能够帮助医护人员梳理其接触重症患者或濒死病人的工作经历,分析其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反思未来工作实践,并且能够使其更好地理解自我和职业。基于此,本文将聚焦经常接触临终和死亡的肿瘤科医生,希望能够从医护群体的职业视角透视死亡,解读临终和死亡的体验经历,深入对医患关系中的医生角色的理解。本研究是一名肿瘤科医生关于临终和死亡病人的叙事分析,将通过叙事定位的三个层面——叙事者如何定位故事中的“我”和其他人物、叙事者如何定位讲述故事的“我”和听众(即研究者),以及叙事者如何定位医疗情境主流死亡叙事中的“我”,来分析该名医生工作经历叙事中的不同定位,并且通过定位探究职业认同的建构。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考察肿瘤科医生关于病人临终和死亡叙事中的职业认同构建。其职业认同建构是在医生的叙事过程中不断建构的,叙事的过程也是不断定位话语情境中的自我的过程。本文的研究围绕一名肿瘤科医生关于病人死亡和临终经历中的职业认同建构,研究问题如下:
1. 叙事者在叙述过程中呈现了哪些不同的定位?
2. 这些定位呈现了什么样的职业认同变化?
2. 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肿瘤科齐医生(化名)工作中经历的临终病人的故事展开。齐医生是北京市某二级甲等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女性,50岁左右,拥有近20年的肿瘤科从医经历。齐医生在接受访谈时分享了其经历的临终和死亡病人的故事、对临终和死亡的思考,以及对近20年工作经历的反思。研究者是社会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女性,与齐医生在生前预嘱协会志愿者培训活动中相识,并且通过齐医生的介绍,于2015年3至4月份以“调研者”的身份进入其所在的肿瘤科,体验肿瘤科医生的日常,并接触了病人和病人家属。随后,齐医生作为参与者之一接受了访谈。研究得到了参与者的同意,签订了知情同意书。本文的语料源于2015年5月的一次深度访谈,访谈持续65分钟。
本研究采用叙事定位理论(Bamberg, 1997)框架,对访谈录音的转写文本进行了叙事定位三个层面的分析,考察叙事定位和职业认同的变化。本研究中叙事定位的三个层面为:1)故事世界人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故事中“我”与临终病人、病人家属以及其他人的定位;2)说话者如何定位与听众的关系:故事讲述层面的“我”与作为听众的访谈者的定位;3)叙事者如何定位自我:叙事者如何在有关临终和死亡叙事的主流话语中定位“我是谁”。
3. 研究结果
分析呈现了死亡叙事中齐医生的职业认同变化,表现为对死亡、临终病人和肿瘤科医生职业的理解三方面。死亡、病人和医生职业三者是整个叙事中的三大主题,这三大主题与职业认同定位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死亡充斥在肿瘤科日常工作之中,病人是每天需要面对的群体,肿瘤科医生的职业成为其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通过分析叙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定位,研究结果显示了叙事中的职业认同的变化:从“规避死亡的医生”到“走近死亡的医生”、从“与临终病人隔离的医生”到“去牵临终病人手的医生”、从“治疗疾病的医生”到“照顾生命的医生”。这些变化通过根据时间历时变化的不同的定位表现出来,发生在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的变化)之间,也是在进行之中的变化。齐医生的经历也是一个“自我疗愈”“自救”的过程,她最终从癌症和死亡带来的职业创伤中走出来,发现工作带给她的是一件“礼物”,并逐渐尝试成为一个“照顾生命”的大夫。下面的分析中将分别呈现这种变化。
3.1 从“规避死亡的医生”到“走近死亡的医生”
齐医生的第一个职业认同的变化是从“规避死亡的医生”到“走近死亡的医生”,对死亡的态度经历了“切断”“远远地躲着”到“走近”“有勇气面对”的变化,而这些也正是因为看待死亡的视角不同。因为经历很多的病人临终和死亡,齐医生受到很多冲击,因此会“躲得远远的”,将自己保护起来。在这里,齐医生用“活在罩子里”和“行尸走肉”两个隐喻来描述自己用一种“切断”的方式与死亡和病人隔离,与悲伤和痛苦隔离。而规避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恐惧”死亡,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对死亡本能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下意识的救世主”情节、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无法挽救病人生命的无力感,如下面的故事中所展现的“无奈”。然而死亡是确实存在的,作为医生需要接受有限,接受死亡。在这里,齐医生讲了一个发生在两三年前的故事。病人是一个患胶质瘤的女孩儿,大约19岁,刚刚上大学,因为手术后的复发,生命走到了尽头,完全丧失了运动功能,无法讲话。于是,她就把手机键盘上的数码背下来,通过眨眼睛,让妈妈摁手机上的相应按键,形成相应的文字信息,成为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片段1)。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齐医生数次沉默、停顿,似乎很难找到合适语言描述女孩患病时的状况。
访谈片段1
20 但是我感觉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21 随着肿瘤的症状,她整个人……
22 就越来越差,她最后就完全卧床。
23 随着后来病情的发展,虽然后来她的神志是清醒的,
24 但是她的运动功能完全丧失,
25 到最后的时候……
26 她完全不能说话,
(……)
31 我,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的。
32 在她快要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33 就把手机键盘上的那个数码背下来,
34 眨几下眼睛,她的妈妈就知道按几号键。
(……)
59 (我的)想法就是人在自然界相对于疾病的手段太有限,
60 太多的无奈。
61 对于命运不得不臣服吧,我们还是要接受。
在这段故事中,第一层定位是故事中的人物定位,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包括患癌的19岁女孩、齐医生和女孩的父母。叙事者齐医生在一开始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拯救女孩于死亡的医生”,对女孩的病情进行了较多描述,展示了临终的痛苦画面,如对女孩患病状态的描述中的否定表达“越来越差”“完全丧失”“完全不能说话”等,女孩父母“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他们想到的一切办法”,以及齐医生自己“只能做这些(减轻疼痛)”“太多的无奈”。随后又将自己定位为“受到震撼的医生”,女孩是一个失去运动能力、饱受疾病折磨,但仍旧坚强乐观的病人。齐医生两次重复使用“让我印象最深刻”,并且在评价部分使用绝对否定形式“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都呈现了死亡所激发的生命力以及女孩顽强的行为使齐医生感受到的震撼。
第二个层面的定位是互动层面,发生在齐医生(受访者)和研究者之间的访谈互动中。在互动层面,齐医生向研究者展现了一个能够从病人身上感受到生命力和收获震撼的医生,她希望被研究者理解为与病人拥有更多共情的医生,整个访谈过程也是医生通过与研究者的互动梳理自身职业认同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对于故事的进展也起到推动作用,如叙事的承接问题(如“她走后,她的父母?”)和对情感评价的追问(如“您还有其他感受吗?”)。在这个过程中,齐医生也向研究者展现了“痛苦的死亡”与“强大的生命力”的对比。
第三个层面的定位和医疗情境中死亡叙事的主流话语有关,与当前的医学模式相联系。目前医学领域死亡叙事的主流话语更多强调的是专业技术的提升和医疗经验的积累,更多关注疾病的治疗,把医学当成一门科学,客观和理性地分析疾病和死亡。齐医生的故事是10名肿瘤科医生关于临终和死亡病人叙事中一部分。研究者所收集数据中临终和死亡叙事的主导部分是从专业角度对各种癌症晚期疾病的解释和对具体医疗措施的描述,而本研究中的叙事者更多关注临终病人以及死亡所激发的巨大生命力和能量,以及病人末期使其受到震撼的举动,而非具体医疗措施的描述,患病的女孩成为其中的主角,而“我”成为背景,突出更多感情的表达,收获了临终病人面对死亡时强大的生命力带来的感动。同时,相对于其他故事对于医疗技术改进的反思,上面的故事更关注情感的表达。因此,这一层面也反映出齐医生的叙事展示的是一名和病人有更多情感共鸣和链接的医生。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医生“对于疾病的手段还是太有限,不得不接受(死亡)”。
正是因为从死亡中看到强大的生命力的震撼,认识到“死亡不再是负能量”,于是齐医生尝试去“自我疗愈”,尝试去改变,走近死亡,因为在自我疗愈的过程中,齐医生逐渐发现了内心的力量,“有勇气去面对死亡”。走近和面对死亡需要接受有限,也需要和病人建立各方面的链接。在回忆过去的经历时,齐医生谈到的是切断、恐惧、伤害,所以她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受害者”“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而死亡是恐怖的,是让人产生“恐惧”的,对于后来经过自我疗愈后发生的逐渐改变,她又将自己定位为“内心力量强大的人”“有勇气面对死亡的人”。所以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对自我的定位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是与从病人身上感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3.2 从“与临终病人隔离的医生”到“去牵临终病人手的医生”
齐医生第二个职业认同变化与临终病人有关,从“与临终病人隔离的医生”到“去牵临终病人手的医生”。作为肿瘤科医生,齐医生在工作中会面对很多临终和死亡病人,这些病人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齐医生在临终病人身上看到了一个病人在生命后期所表现出的乐观和豁达,让齐医生去反思死亡和生命:“死亡到底可以给活着的人带来什么?”病人和医生的定位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病人让他们看到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经历死亡事件,获得教育。齐医生对临终病人的认识和定位发生了变化,从认为“经常接触死亡病人是负能量”到“生命的末期会绽放异样的光彩”。在这里,齐医生讲到两个临终末期病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来自齐医生的心理咨询师朋友,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性骨髓癌病人的故事,病人过去是一名非常成功的保险师,在五十多岁时患病,骨髓癌末期,瘫痪在床。尽管如此,病人仍旧非常快乐,并且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片段2)。此外,齐医生还讲到了一个卵巢癌病人的故事,病人身体忍受巨大的疼痛,但是身上散发着非常温暖的东西,内心充满喜悦,因为她感觉自己除了身体之外,生命中的其他东西都“心想事成,非常顺利”。她发现这个病人身上有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东西,虽然身患重病,但是精神获得了升华。限于篇幅问题,本研究只对骨髓癌病人的故事进行分析。
访谈片段2
191 那个人也大概五十多岁,他曾经是台湾顶级的保险师,
192 他有几年完全就是一部工作机器,他带着三部手机,
193 除了吃饭睡觉,这生理生存要求之外,其他……,所以……
194 当时为什么这么努力,为什么这么玩命?
195 他认为他生命的价值就是工作。
195 然后,去看到他的时候,病人已经完全瘫痪在床上躺着。
(……)
223 他说生命是生病的方式强迫他停下来,
224 就看在他以前生命历程中完全被漠视掉的东西,
225 他说后来才知道这世界多美,亲情多可贵。
226 他在完全卧病在床情况下,
227 可以指导他的父母去做生活中的其他事情,
228 他觉得可以帮助他人。
这个故事是一个间接体验叙事(vicarious narrative)。其中第一个层面的定位是故事中的人物:骨髓癌患者,而齐医生是一个故事讲述者,不是故事中的直接人物,作为故事的接受者转述这个故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患骨髓癌的病人,病人是一个积极乐观、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尽管身体失去控制,但是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而齐医生的朋友对病人在患癌末期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感到震惊,受到震撼。定位的第二个层面发生在叙事者和作为听众的研究者之间。这个故事发生在齐医生反思自己“过去远远躲避死亡,是否错过了什么”之后,这是她的朋友亲眼见到的病人,在讲述的过程中她给出了自己从专业角度的解读“我自己是学医科出身,我知道骨髓瘤到末期是非常痛苦的”。这也是叙事者向研究者强调这名病人所经历的疾病折磨,但是这些对于病人“完全瘫痪在床”、活动受限的描述也和后期叙事中病人“带着病床出去旅游”形成对比。同时,病人生病前的认识“人生的意义在于工作”也与生病后的感悟“停下来去发现和感悟”形成对比。这个故事也是叙事者讲到“病人是我们的老师,用生命的苦难去教会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之后的例证。在这个故事中,临终病人的积极力量具有强大的穿透力,齐医生作为一名间接体验者也强烈地感受和学习到。这是叙事者呈现给研究者的故事,同时也是呈现给齐医生自己的故事,建构了一名从“把病人当成需要被照顾的群体”到“可以从临终病人身上学习”的医生形象。第三个层面的定位和上面小节的故事类似,齐医生将自己定位成“发现病人带来的感动、与病人有情感共鸣和链接”的医生。
因为与病人的情感共鸣以及从病人身上获得的教育,她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把病人定位成“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到“我们是共同面对死亡的队友”,她给予了病人和病人家属支持,反过来,也得到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支持。而走近病人,去“牵病人的手去”需要很大的勇气。这些力量和勇气不仅仅来自自身的疗愈,也来自临终病人带给医生的感动。去牵病人的手,让病人感受到支持,这个过程也是相互的,她逐渐从病人身上获得了力量和支持。
3.3 从“治疗疾病的医生”到“照顾生命的医生”
第三个层面的职业认同变化是从“治疗疾病的医生”到“照顾生命的医生”。上面一个小节主要呈现了认知自我的变化,强调医生可以从临终病人身上获得教育;本小节主要强调行动自我的改变,即齐医生与行为相联系的职业认同变化。对于医生职业来讲,不论是远古朴素的“仁爱助人救人”“普同一等,同仁博爱”,还是现在“治病防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医学理念,广大医护群体一直肩负着光荣而神圣的职责。在我国,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也被称为“白衣天使”,整个社会对医护群体拥有根深蒂固的“救死”“救命”的期待。另一方面,医护群体通常也有某种“救世”情结,承认病人濒临死亡通常也意味着治疗的失败,会对“治病救人”的职业认同产生冲击。然而,医生群体也需要接受医学的有限性,学会接受可能的死亡。
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自18世纪以来一直是医学界的主导,医学也被定义为“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与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20世纪以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人文医学模式也相继被提出。然而当今医疗卫生界和社会公众对医学模式的认识仍旧停留在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过分相信科学的魔力,甚至对人体实施过度诊疗。医疗情境中死亡叙事的主流话语是“治病救人”,而无法治愈疾病和挽救病人生命就意味着医疗的失败。因此,目前的医学在很多程度上也过多关注疾病,强调治疗,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病人的生命。可是,住在ICU、浑身插满管子、靠机器维持的生命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吗?
这也是齐医生在讲述中对现代医学的反问,也是对当前医学模式的反思。引述台湾某位教授的话,齐医生对现在的职业定位是“用生命去照顾生命”,这也是她所讲到的今后工作的目标和方向,将医生的职业定位从“关注病人的病情”转变为“病人的身心社灵”全面照顾(即身体、心理、社会以及灵性/心灵上的全面护理照顾)。医生除了需要治病救人外,也需要给予病人整体的人文关怀。当走近死亡和病人的时候,工作不再是“一件事情,一项任务”,而是一个能够给自身带来支持的过程,医生和病人相互支持,共同面对死亡。在陪伴病人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齐医生会去牵病人的手,让他感受到支持和力量,让病人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他的亲人,还有为他治病的医生。
这个层面的认同变化是通过习惯性叙事(habitual narrative, Riessman, 1993)呈现的,即描述习惯性和重复性行为的叙事,主要表现为问诊方式和死亡告知两个方面。问诊方式由“打断废话”到“开放式谈话”的转变叙事中呈现了“关注病情的医生”到“关注病人的医生”的变化,让病人讲述自己的感受,同时充分了解病人家属的看法。这里涉及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病人是否应该被告知病情或是即将面临的死亡。因为“病人的身体不会撒谎”,齐医生也谈到告知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时候她也会提出自己的建议,比如去尝试和患者沟通(片段3),但是在沟通的时候也需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区别对待,如果是病人不想知道自己的病情,也要尊重病人的选择。
访谈片段3
395 她(病人家属)说:“我不知道怎么劝。”
396 那我就告诉她:
397 “没关系啊,如果你同意的话,
398 我会当着你的面,去试着和他谈一下。”
399 现在就是我们需要最新提出的,
400 就是我怎么样去尝试性地去交流。
401 然后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既不伤害到病人,
402 然后真的是让他逐渐地接受现实,
403 让他知道,意识到这个疾病实际上终归是不好的。
在互动层面,齐医生反思了自己过去的工作中的问题,也表达了对病人临终过程中医生角色的反思,认为过去“仅仅关注病情”应该转变为“关注病人的身心社灵”。同时研究者也在访谈过程中追问了叙事者有关未来工作实践的思考,受访者认为未来中国的医护人员在病人临终和死亡方面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且将自己有关病人临终和死亡的叙事定位于中国和世界缓和医疗以及临终关怀的大情境中。因此,在叙事定位的第三个层面,叙事者对自身的定位是一名“缓和医疗的实践者”,正在努力做一名“照顾生命的医生”。齐医生的叙事反映了来自缓和医疗和临终关怀的声音,呼吁关注临终病人的生活质量,并且积极挖掘死亡的正面效应和积极能量,这也是对医疗情境死亡叙事主流话语的挑战。
最后总结其从医经历,齐医生说她的经历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礼物”。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在作为“人的一生的最终解释”的死亡面前,她看到了生命的价值和光彩,对人生有更深的思考。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她也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4. 小结
本文是对一名肿瘤科医生死亡叙事中职业认同建构的分析,探究其在叙事呈现方面的职业认同改变,主要从叙事定位的三个层面呈现职业认同的建构,研究结果呈现了从“规避死亡的医生”到“走近死亡的医生”、从“与临终病人隔离的医生”到“去牵临终病人手的医生”、从“治疗疾病的医生”到“照顾生命的医生”的职业认同变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本研究中参与者的叙事是有选择性的,叙事内容是参与者对工作经历提取的结果,是叙事者通过叙事话语实践的过程建构和呈现的。
齐医生的职业就是与死亡和临终病人打交道。对病人临终和死亡的不同情境化定义和解读:是消极被动处理死亡,还是积极主动去面对死亡?是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biomedicine),还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人文医学(humanistic medicine)?这些都导致了职业认同的差异和变化。其中,齐医生叙事中的职业认同的转变还反映了认同导向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去挖掘死亡的积极意义,看到生命末期的光彩。齐医生死亡叙事中的认同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更积极的职业认同建构,叙事话语实践呈现和建构了这些职业认同的变化。另一方面,医生在面对死亡时也存在无奈和无力感,也要“学会接受有限”。
本研究是对一名肿瘤科医生死亡叙事中的职业认同建构分析,具有一定的个案性和局限性,但是齐医生的经历和转变也代表了一批正在反思和建构自身职业认同的群体。中国的医疗行业目前也在发生转型,如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到人文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生群体的认同也或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齐医生对死亡意义的正面解读和积极建构也为我们解读死亡提供了启示:透过死亡去关注生命,向死而生,实现更大的生命价值。同时,笔者也期待国内出现更多有关死亡话语的研究,从更多视角探索死亡话语。
致谢: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高一虹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Anderson, H. 1997.New York: Basic Books.
Bamberg, M. 1997. Positioning between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7: 335-342.
Bauman, Z. 2005.. Cambridge: Polity.
Candrian, C. 2014. Taming death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iscourse., 1: 53-69.
Cohler, B. J. 1982. Personal narrative and life course., 4: 205-241.
Davies, B. & R. Harré. 1990. Positioning: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selves., 20(1): 43-63.
De Fina, A. & A. Georgakopoulou. 2008. Analysing narratives as practices., 8(3): 379-387.
Giddens, A. 199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K. & N. Koteyko. 2013.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Hollway, W. 1984. Gender differen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In J. Henriques, W. Hollway, C. Venn, and V. Walkerdine (eds.).London: Methuen, 227-263.
Ibarra, H. 1999. Provisional selves: Experimenting with image and identity in professional adaptation, 44(4): 764-791.
Osterlind, J., G. Hansebo, J. Anderson, et al. 2011. A discourse of silence: Professional carers reasoning about death and dying in nursing homes., 31: 529-544.
Riessman, C. K. 1993.. Thousand Oaks: Sage.
Riessman, C. K. 2008.. Thousand Oaks: Sage.
Schein, E. H. 1978..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Semino, E., Z. Demjen & V. Koller. 2014. “Good” and “bad” deaths: Narrativ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interviews with hospice managers., 5: 667-685.
Professional Identity Change: From “Illness Treatment” to “End-of-Life Care”:A Physician’s Narrative of Patients’ Dying and Death
Wang Jingyun, Peking University
Drawing for the framework of narrative positioning,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d the change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an oncologist’s narrative discourse of patients’ dying and death.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ncologist’s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changes: from “avoiding death” to “confronting death”, from “emotional isolation with dying patients” to “holding the dying patients’ hands”, from “treating illness” to “end-of-life care”. These changes were represented in and emergent from different narrative positionings in narratives about death, dying patients and her profession, and she finally realized her experiences with dying patients were a “big gift”.
narrative, dying, death, position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王景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100871)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
电子邮件:wangjingyun@pku.edu.cn
王景云,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叙事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