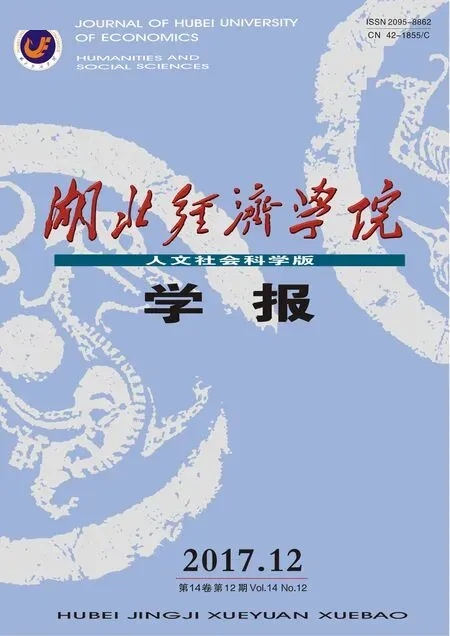“小说家”应该从诸子略中除名吗?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小说家”应该从诸子略中除名吗?
杨叶青青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共收十家,“小说家”以街谈巷议之内容、稗官小吏之传播、丛残琐屑之意义忝列其中,其地位甚至遭到作者本人的否定,本文试图通过厘清“小说家”这一概念在阐释学层面和目录学层面的双重定位问题,为“小说家”的存在提供合理的出口。
《汉书·艺文志》;杂家;小说家;小说概念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根据其序文可知,其作者班固对当世流传书目的收集工作,应从刘歆所著《七略》溯源而上直至刘向《别录》,每一略所列书籍之后,班固给出的的评论也是在参考了刘向、刘歆父子旧文的基础上,略加批注的①。
《汉书·艺文志·总序》有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直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②也就是说秦以前的诸子文章都被付之一炬了。直至汉代,“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这里,我们从“下及”之语便可不难看出,辑录者在收选书籍时,首选仍是经学一类,诸子之言并不在重点关注之列。
来到“诸子”一略之中,其又有“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姚明辉《汉志注解》对此句惟“去小说家”之解读。诸子本就不在关切之列,而“小说家”又被排除在“诸子略”可取的九家之外,“小说家”在《汉书·艺文志》中的不重要性便可不言自明了。
然而,《汉书·艺文志》中对于“小说家”和“小说”的这寥寥数笔描述: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在后世却成为了定义“小说”概念的先声。这其中,后人阐释与前人草创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值得玩味的依违现象:从班固著史的角度出发,“小说家”无论如何都是拿不上台面的,但若从文体学角度考量其历史意义,“小说家”的成立却又是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二者间的巨大落差让我们不禁想问:“小说家”是否可从诸子之说中剔除呢?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试请论之。
一、“小说家”考辨
“小说”这一语汇确切真实的出现,要上溯到《庄子·外物篇》中,其文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难矣”③之语,但学者普遍认为,当时的“小说”只是和后文的“大达”相照应,“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④,不仅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不同,甚至与《汉志》所载之“小说”也并不一致。王庆华《“小说”与“杂家”》一文认为,“小说”一词产生于先秦诸子争论之中,最初只是一个“社会普通用语”,“泛指与智者所论高深之理相对应的浅薄之论”⑤,《荀子》中有“小家珍说”⑥,盖亦出于此。到了汉代,才有桓谭首次在《新论》中指出“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⑦——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小说家”内容、体式、作用的具体说明,但也仅是一个模糊的概况,真正将其纳入文学规范的仍要到《汉书·艺文志》。
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讲稿中有“文章的体类”一节,他总结道:“中国有真正的文学当自建安时期开始。至宋元代才有西洋文学之体裁风格。在先秦诸子时代,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等各家,各家思想不同,故其文章亦不同”⑧,由于思想的不同,造成了语言上的区别、文体上的差异,如果要对各家体式进行明晰的分别,则应清理“言”、“人”、“文”之间的关系:“言”是针对作者说的,创作者试图表达的话语就是“言”;而作者之“言”的输出主体,也就是读者或听众,指“人”;最后,“文”指的就是那些,如何将作者的描述精准度最大化的技巧。因此当我们讨论某种文体时,我们最终要解决的无出于“言”、“人”和“文”这三个方面。
让我们从“言”开始。首先,“言”从何处来?“诸子略”十家之体例,以各家由谁人所著为始,《汉志》为每一家之思想都归纳了一定的官职,从各官员的职分和地位便可以推测出各家思想所侧重的方面,由此更可体现《总序》之所言“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的特点。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司徒之官为《周礼》之中负责教导君主礼仪教化的官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其职责就是要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福祸古今之道”,然后方知如何保持本心,“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其余诸子,如阴阳家出于义和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之出于礼官、墨家之出于清庙之守⑨,纵横家、杂家、农家又分别出于行人之官、议官和农稷之官,而“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汉书·艺文志》紧接着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即这些“小说”是在坊间的街头巷尾被拿来议论的,因为其传播媒介是每个人的口耳相传,又因其发生地点在民间,故这些言论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这也正是孔子将之称为“小道”的原因。然而根据儒家一贯重视民间声音的传统,孔子继续说:尽管这些是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于谈论的内容,但仍有它的可取之处,如果圣贤之人离这些声音太远,恐怕就难以获得兼听则明的品德,从而成为贤者了。
余嘉锡先生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⑩一文中详细考证了“稗官”的概念,他指出,就现存可考之古籍而言,先秦时期,对类似“街谈巷议”的言论进行传达的,有这样几种情况: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春秋》襄十四年传)
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过书而宰收其膳,宰之义,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进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贾谊新书·保傅篇》)
《春秋》之云“士传言”,传的当是庶人的“谤”言,即庶人负责谤讥于野,士则负责将这些议刺的话传达给上级,从而完成底层环节的信息交换[11]。《贾子新书》则又向前迈了一步,“大夫进谋”是向管理者提供更适用于统治的策略,一个“进”字,实际上道出了大夫工作的两个面向,“谋”首先由大夫输出,而输入者显然就是他们效忠的君主,同样的,“士传民语”也能体现出士所沟通的上、下两个渠道,《国语》“周语篇”中所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12]正是双向渠道的最佳证明,这里的“庶人传语”,韦昭注曰: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士也。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谈到“士”的地位问题,认为“士”是存在于“庶人”与“大夫”之间的阶级,阶级之划分对于当时的邦国而言,是其成立之根本,是以《左传》有:“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下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13]
孟子《万章章句》先有,“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的等级制度,又有“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14]这样更森严的阶级设立。也就是说,首先周朝之“士”分三层,但就地位而言,整体低于大夫,而又略高于庶人。又因为“下士”和做官的庶人获得的经济收入是相等的,并且这样的一份收入足以使其无需参与耕种劳动,这让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尽管已经脱离了最底层民众的范畴,但仍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稳定的第一个分野。《晋语》又有:
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於民,於是乎,使工诵谏於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15]。
这也是在告诫君主听取意见于民间:需要在市朝之间采集底层的声音,通过辨别个中之真伪善恶来对管理工作进行相应的修补和纠正。先秦时期,谏言的传统已经被普遍接受,而根据严格的等级制度,庶人之语由士来转达应当是不应有疑的,因此稗官出于士之阶层也是可信的了。
训诂学的研究成果亦可作为以上推测的理论支撑,《九章》有“细米为稗”的说法,而街谈巷议,闾里风传的又无非是一些琐碎的言论,故收集民风之官员的选派,也应任用贴近庶民的阶层,一方面这是人力资源的最合理支配,同时也是对封锁阶层间流动的必然要求。
二、“小说家”研究的尴尬局面
本文开头引入宾四先生“言”与“人”的理论,在前文论述中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文”,即“小说家”的创作规范究竟如何,我们无法从班固的评语中获得答案,这也正是学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源头时绕不开的话题。毕竟当我们将历史的拼图一片片聚合在一起,以求还原出小说最早的样貌时,我们都会感到疑惑,它似乎与魏晋南北朝开始往后的“小说”很不一样。陈文新师在《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的开篇便有“‘小说’首先是故事吗?”一问,因为班固在诸子总论中称各家“曰‘术’(学术),曰‘说’(学说),曰‘股肱之材’,曰‘万方之略’,都意在突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诸子以立论为宗。”[16]尽管小说不在“可观”者之列,但“既附于骥尾”,应当也不离议论之法,然自魏晋以来之小说,都以叙述为宗,通过虚构、非虚构的情节来传情达意,实与《汉志》之小说大相径庭。
更有甚者,如明胡应麟就发现,《汉志》中所称之小说,“虽曰‘街谈巷语’,实于后世博物、志怪等书迥别,盖亦杂家者流,稍错以事尔”[17],他认为“小说家”和“杂家”是大体相同的,只不过“杂家”所言仍围绕国体王治生发,而“小说家”议论的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罢了。
当然,我们所谈到小说家之“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创作内容,也只能是一种理想情况下的抽象概括,《汉志》收录的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究竟记载了怎样的内容,由于它们早在唐代以前便全部亡佚,今已不得而知,故我们也只能根据其题名和班固简短的批注,以及其他文献中保留下来的短小片段中进行推测,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略》中作了一些考证工作,华中师范大学的王齐洲教授为之专著一书,名为《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18],其史料之详备,内容之完整,堪为学界小说源流研究的厚重之作。
从汉《艺文志》所列小说家书目之题名便可发现,其中诸如“伊尹”、“鬻子”等,本应分属先秦诸子,其内容估计或多或少都代表了诸子的部分思想,但从“其语浅薄”的点评可看出,对于这些思想的描述,小说可能只提供最简单的呈现,缺乏观点的凝练;有的尽管兼有多家思想,但内容似乎不太严谨,风格倾向民间俚俗的普及,故被划为闾里巷议之谈也未可知。另有一些诸如《封禅方说》、《虞初周说》,题中有“说”字的书籍,前者或描述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器物、方法等方面的礼仪;而后者之“虞初”,据《汉书·艺文志》注:“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史记》也曾载其为张衡《西京赋》中“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之虞初,所以此类小说由方士所作,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其一,“待诏臣”本是汉代地位极其低下的官员,被汉武帝视为“俳优”的东方朔就曾“待诏金马门”,我们甚至可以从“待诏”二字猜测他们连正式编制都未见得拥有,因此这些人员的身份之复杂程度就可窥见一二了;其次,题中有“术”字,说明它讲的就是一些方式方法,“饶心术”、“未央术”大概就是一些身体保健的民间验方[19],它们或者与时令节气相关,或者同星象水土有关,因此容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这些书籍只能短暂流传而不能被长久保存,也出于这部分的原因。
如此杂乱无章的目录分布,也令很多人产生混淆,即“小说家”与“杂家”是否可以相等同,从而放弃“小说家”类的划分,而将名下诸书归入“杂家”一类呢?比如,我们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看到对于杂家《淮南子》一篇是这样描述的:“《淮南子》吸收了不同流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其宇宙秩序整合了古代神话、作为理想的天地主宰的完美“真人”形象、以及五行相生相克思想等若干因素。与《吕氏春秋》一样、《淮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杂家”类。 ”[20]“小说家”里有关仪典、方术、延年益寿的内容与《淮南子》何其相似,甚至在这些诸子散文中,叙述的笔法也已经日趋老道。
郑樵《通志》有“古之编书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21]的评价。韩进廉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中直言,诸子散文中的寓言对情节描写的掌握,和情感表达的升华“已经符合了小说的创作原则”[22],只因这些故事已经寓于散文之中,并非独立的问题,故而无法成为小说的直接传承者。
综上所述,我们至少能总结出两点汉志中“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尴尬局面,首先,该“小说”与近代意义上的“小说”近乎于两种文体,汉代小说不重虚构、没有情节发展、甚至没有一定的篇幅,更遑论叙事手法,人称视角的运用;其次,在分类上,“议官”与“稗官”同为谏言之官职,且“稗官”的位阶离庶民只有一线之隔,“小说家”和“杂家”又实在不容易区分,“小说家”在汉代的地位确实当得起“不可观”三个字。当历代学者抱着追寻中国小说之渊薮的伟大希冀翻开《汉书·艺文志》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便足以使他们垂头丧气了。
三、浅议文学史研究的“恋母”情结
近代以来,无数的文献被发现,无数的假想被验证、被推翻,新文化运动以来,记叙文学的蓬勃发展,让中国的俗文学异军突起,而那些在本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寻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突然就得到了答案:
敦煌变文的出现,为宋元叙事文学起源的研究撕开了一道口子,为此,郑振铎激动地振臂高喊着:“这个谜团解开了!”和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古兰经》这类带有宗教色彩的经典不同,他说:“我们的‘宝卷’、‘弹词’,绝不可能是“从天上凭空落下来的。”[23]于是关于西域文明、敦煌文献的研究便开始了。
但想要这个拥有三千年文明的文化国度,承认吾国之文学是抒情的文学,不是记叙的文学,并且记叙的传统只怕还是从遥远的中南半岛,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从神秘的印度教、佛教、梵剧当中移栽过来,恐怕即便是受到了当时如梁启超、郑振铎,现在如季羡林、饶宗颐这样的大家的支持,也还是令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罢。因此我们更要在更古老的文献里挖掘更古老的材料,用我们的史传传统,散文传统充当故事情节的演绎,以证明我们的各体兼备。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一书中谈到了小说文体与史传、诸子散文的关系[24],事实却是,他讨论的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并非中国最古老的小说家之语,也就是说,天平的至少一端被人为地放错了砝码。《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入“诸子略”中实乃首创,且在《庄子·外物篇》里“小”和“说”二字偶然巧遇之后,为学者追溯小说文体之源流提供了完美的目录学史料,但是在狂喜过后,附加的过分期待便随之到来,人们始终努力地想要为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明清的章回小说找寻一粒属于本民族的种子[25],中华民族的“恋母”情绪在文学史研究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或许也是儒家文化传统下,群体自身体会到“危机感”的一种表现。
现代人之阅读记叙文学所为何事?朱东润先生的见解颇具启发性。《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中有《传叙文学与人格》一篇,其中引述狄士莱里[26]的话:“用不到读史,止要读传叙,因为这是不带理论的生活。”尽管朱先生区分了小说与传叙文学的概念[27],为虚构和真实定义了清晰的边界,“传叙文学底价值,全靠它底真实。……真实是传叙文学底生命”[28],但对有关“记叙”这一文学手法的见解,是可以烛照到小说文学上去的,所谓“不带理论”的生活,是否是要求我们抛开形而上的一切构筑,回归到对生命本真的忠实表达,单纯地享受不同情节中不同的人生体验呢?
民国六年,钱玄同在寄予胡适的书信中提到:“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多用白话之故,用典之病尚少。”[29]此语也意在认可近代小说在解放人类个体意识上所作出的贡献。然而当我们回到公元一世纪的东汉,这个模棱两可、含混不明的“小说家”应该被排除于“诸子”之外吗?请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有一个房间,内有许多可供归置的书柜和抽屉,然而各色不同的杂物被屋主凌乱地抛却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到了这一天,有人提出要将它们收纳起来,于是他先构思好,要将贵重的物品摆在架上以供客人观赏,要让实用的小件放于最顺手的地方随时取用,然而还有一些零碎的小物,它既不似其他事关日常生活的用品一般富于实用价值,又不具备赏玩功用,于是整理者为它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抽屉,它不华丽,却也安全无虞,这似乎是它最好的归属。
对于汉代小说而言,“小说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抽屉,在现有的文学理论无法解释其存在的当下,有一个可供其栖居的空间让它等待,等待下一个人将其发现,这也许是两千年前的文学家对于知识和文学所给予的最大善意罢。
注 释:
① 《汉书·艺文志·总序》记载了,经刘向、刘歆直至班固,《汉志》成书的过程,即: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② 本文征引《汉书·艺文志》及其后世评注之诸文字,均出于(汉)班固,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后文不再赘述。
③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07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⑤ 王庆华:《“小说”与“杂家”》,载自《浙江学刊》,2008 年 2 月。
⑥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
⑦ [汉]桓谭撰:《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页。
⑧ 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成都: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
⑨ 此处“守”据考也应为“官”字,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守字者官字之误,志叙诸子十家,皆出于某官,不应墨家独作守。
⑩ 余嘉锡:《古代小说丛考》,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11]底层的信息交换曾一度被忽视,台湾籍学者试图诠释中国社会的“底边文化”概念。该文化所涉及的人物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下九流”者,这类所谓的庶民在法理和个体支配上,长久以来都没有完整的权利和自由,但他们无疑是全体社会生活中不可抹杀的环节之一,他们也有自己的思维逻辑、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如果说《水浒传》的伟大反映在对底层游民义上梁山的豪侠情义的推重上,那么“民间的声音”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显然也应获得我们的关注。乔健.底边社会:一个对中国社会研究的新概念[J].西北民族研究,2002-01.
[12]曹建国,张玖青注说:《国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1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4][战国]孟轲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75页。
[15]曹建国,张玖青注说:《国语》,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16]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17][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
[18]王齐洲:《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
[19]参考李零:《中国方术考》,上海: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20]宇文所安:《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41页。
[21][宋]郑樵著,吴怀祺校,吴怀祺编著:《郑樵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2]韩进廉:《中国小说美学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2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3-81页。
[25]我们找到了,但它显然并非全部。
[26]英国政治家、文学家,今译为迪斯雷利,该句出自小说《康塔利尼·弗莱明》,见蒋承勇等著,英国小说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03月第1版,第182页。
[27]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中国传叙文学,是比较后起的文学《穆天子传》、《燕丹子》是小说,不是传叙。”
[28]朱东润:《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八代传叙文学述论》,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29]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杨叶青青(1992-),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