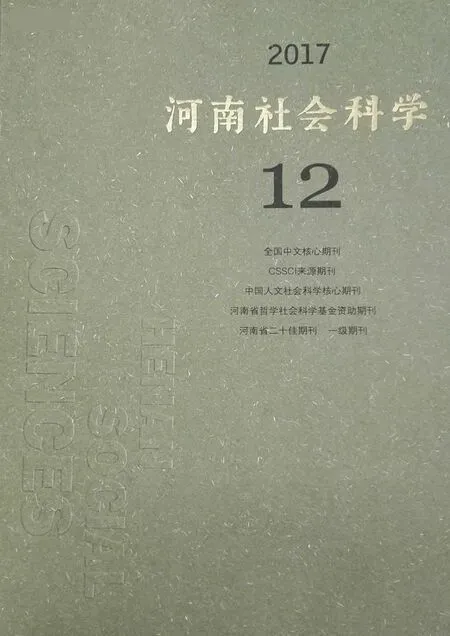明清浚县古庙会:权力主体与场域构建
——基于浚县浮丘山明清碑刻的研究
邢 涵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1100)
浚县正月庙会,是全国著名古庙会。因庙会的主要活动在大伾山、浮丘山上进行,所以浚县正月庙会又称浚县山会。浚县正月古庙会与山东省的泰山庙会、山西省的白云山庙会、北京市的妙峰山庙会,被公认为华北地区四大庙会。由于浚县正月庙会起会早、时间长、规模盛大、民俗味浓,又被公认为“华北第一古庙会”。庙会的主体是庙宇本身,庙宇和人的行为共同构成了庙会,人们在庙会活动中会产生选择性的行为,这种选择性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和时代性所决定的。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主要指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产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指单一的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他人行为相关联的许多因素。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进一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皮埃尔·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提出了资本、场域、习性这三个概念,“场域”(field)是皮埃尔·布迪厄从事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也是皮埃尔·布迪厄艺术场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场域的定义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殊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上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相关的专门利润(profit)的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①。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非单纯的地理空间,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由于资本和权力的运作,会有无休止的斗争,因此这个空间是一个动态的空间。基于这一理论,可以清晰地分析明清时期古庙会的发展方式和过程,为当今古庙会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一、庙观修筑:政府与官僚政治资本的攫取
在庙会活动中,我们可以将一切与庙会有关的活动看作一个独立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占有资本和权力的显然是政府和当地官员,以明代为例,明代中后期皇帝崇尚道教,尤其是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对于道教的尊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了这样的信仰基础,自然会产生出与之相匹配的空间主体,即庙宇和道观。官员们也是上行下效,在全国各地建起了道观。浚县也不例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浚县知县蒋虹泉主持修建碧霞宫,历时21年才建成,建成之后又历经数次翻修扩建,终成现在的规模,而蒋虹泉也马上就得到了提拔,由知县升为河南布政使,紧接着又当上了云南都御史。碧霞宫的建成对于浚县当地来说意义深远,时至今日,每年正月前来上香朝拜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有趣的是,华北地区的四大古庙会所祭祀的主神都是碧霞元君,可见在政府和官员的引导之下碧霞元君信仰的兴盛程度。
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修碧霞元君行宫记》②“明兴敬神恤民,神道设教,世加崇奉,歆动灵贶,赫赫奕奕。历圣天子封神为‘天仙玉女广灵慈惠恭顺普济护国庇民碧霞元君’,敕赐庙额,岁命中贵捧香以进,上祝圣寿,下祈国泰。而天下民士无不敬礼,应显尤多,山东西,河南北,岁时道路不绝于行。如不及走登,则建为行宫,遍郡邑闾里矣!……嘉靖庚子,普安进士蒋虹泉来尹于浚……蒋始神之,复具衣冠往谢。因其祠卑隘,大捐俸资,迁之浮丘山椒。浚人淳厚者欢然助之……工讫,蒋方为河南布政使,已而升云南都御史,万里驰书属记于思……”这段碑文明确记载了明代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推崇和浚县碧霞宫的建成过程,并且说明了碧霞元君祠是有官方背景的,碧霞元君也是被“官方认证”的神祇。这块碑记是由“乡进士龙川孟思撰文,邑庠生它山陈瑶书篆”的,也说明在碧霞元君信仰的宣传上来说,文人、知识分子及神祇的官方身份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道释儒化:乡绅、文士与地方文化的重构
之后清朝的宗教政策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政策,但清朝的皇帝并不像明朝皇帝那么崇尚道教,因此对于民间信仰的道教神祇进行了一部分的改造,模糊了碧霞元君的身份,淡化了民间佛教和道教的界限,碧霞元君作为道教的神祇,在清代的碑刻之中则被称为观音的化身,如清顺治年间的《浮顶进驾万善碑记》③云:“尝闻释教以无我为宗,儒道以同人称大……考诸传记,圣母元君乃观音大士之化身也。大士驾慈航而渡苦海……”而参与立碑的人也并非普通香众,其中包括“林文郎知浚县事江东王誉命县丞张有孚,典史陶尔锦,儒学教谕冷然善,训导王珹,四川道监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马大士,钦差陕西榆林道今转江南淮海道布政司参政兼按察司副使佟国桢,原任河南按察司驿传道兵备佥事李子和,钦差河南清军驿传、盐法兵备道按察司佥事程淓,大同山阴县知县张施大,工部观政进士侯梦卜,礼部观政进士黎焕然,举人刘芳誉,举人邹镕,原任宣大督标旗鼓游击赵景云”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立碑之时,犯下佛道不分的错误,显然是有意为之,而碧霞元君与观音大士这两个神祇对于普通香众来说在功能上并没有太大分别,都是用来求子和祈求平安的,模糊道家和佛家的界限会使碧霞元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信众更多。时至今日,当地一些群众还认为浮丘山是佛家圣地。除了这块《浮顶进驾万善碑记》之外,还有很多进香的碑记中也会用到很多佛经教义中的词语。清代对于神祇的改造不仅仅限于模糊佛教与道教的界限,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创建纯阳吕帝君洞阁碑记》④云:“堪舆形胜之论,儒者每讳引之。虽然,勿过执……客曰:‘邑夹伾浮两山间,东伾西浮,东西文武所分署位也。按天文志,东方木星曰“岁”,岁主文章;西方金星,曰“太白”太白主甲兵。伾浮既划然列东西,地与天应,则文武之各有攸司,不甚明耶?今浮之巅有岱之玉女离宫在焉,雕甍画栋,金碧灿然,而香火倾大河南北。乃伾,则青坛故迹,已翳荆榛,虽有佛阁龙洞,名在实亡,几于寂寂空山矣。龙精为虎气所夺,缝掖之劣于韬钤也,或职是故?’予曰:‘是说有似,然则补救之道何出?’客曰:‘是宜增胜于左,以与右敌,俾龙虎各得其所而已。’予因思增胜之说,非仍以神道设教不可,而求其神之英灵盻蚃,可埒于岱之玉女者,一则于佛,取观音大士焉,一则于仙,取纯阳吕祖焉。即而思之,大士以浮屠之道道天下,释与儒不相为谋。而纯阳,唐之进士,终归于道,始则为儒,且好为篇章……此文章神仙也。此祠于伾而拟于浮,庶几纯阳太阴之两不相绌乎?……”此碑为文林郎知浚县事开原刘德新所书。从这块碑能够看出,作者看到浮丘山香火过于旺盛,而大伾山人迹寥寥,觉得阴阳不能协调,因此要在大伾山建造吕祖祠,吸引香众,来遏制浮丘山的碧霞元君信仰的发展。而作者本身是儒生出身,对于鬼神之说并不笃信,在选择供奉的神仙上就能看出,选择了和儒家有密切关系的吕洞宾,并指出吕洞宾是唐代的进士,在成仙之前也是儒生,较为隐晦地宣传和抬高了儒家的地位,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吸引香客到大伾山祭祀,而这一行为被动地使得浚县庙会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从吕祖祠内的很多香客朝山的碑刻就能看出,这座道观落成之后,确实香火旺盛,甚至延续至今,县令刘德新也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大伾山,大伾山上现存的刘德新的题字遍布各个角落。时至今日,浚县庙会的朝山活动还是正月初九上大伾山,正月十六上浮丘山。而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仁育万物碑》⑤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对庙会活动加以改造和解释:“……德思以善鼓一方之人,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几几乎聚居而成邑矣。思先王以神道设教,约乡人虔奉三仙圣母,会朝浚邑浮丘山进香焉……会始于康熙肆拾肆年,唱者数人,和者百余人。善男信女不介自孚,如候鸟之依于长,如葛藟之依于木。于今三年矣……众归功于会首,曰:‘众善始于一人也。’而玉侯王君愕然曰:‘人性皆善,启众者予,启予者谁耶?非神耶?是不可不有以志神之功、彰神之灵以明人之诚焉。’因乞吉于予,予曰:‘人耶,神耶?知之者人也,不知者神也,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人之至,神之至也。’是诚不可不志之以为后来者劝。”这块《仁育万物碑》更多地赞扬了香会中会首的教化作用,认为人宣扬教化、组织香会的过程本身也是功德无量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会社会首的分量,并赋予了会首更多的义务,使得香会中会员关于会首的竞争更加激烈,会首的当选条件也更为苛刻。从朝山进香的碑刻中可以看出,自顺治年间之后,几乎没有女性会首,会首多为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或官员家属。
三、经济促动:寺观与乡民的利益诉求
在庙会这一场域中,拥有资本和权力的一方不仅会引导和把控,也需要对既得利益进行保护。《清康熙五十二年告示》⑥中明确说如果有人前来捣乱,允许到官府说明,官府将“立拿重处,决不宽宥”,用行政手段保证寺庙和香众利益。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严禁作践庙宇告示牌也明确说,在庙会活动期间,禁止商贩在庙宇内强搭铺面,如有违反,严惩不贷。在庙会活动中不仅有罚还会有赏,用一定的奖励制度来鼓励这种民间的庙会活动。在浚县,民间的香会会以自然村或家族为单位参加庙会活动,并自发排演祭祀时用来娱神的歌舞活动。清朝当地政府为鼓励这样的民间文艺活动,还会制作并颁发银牌给表现优秀的会社,使得各个会社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从而使民间参与庙会活动的热情更加高涨。如现在浚县卫溪社区顺河街道张和平一家就珍藏有清代县令陶珙赏赐给顺河街道花船圣会的葫芦形银质奖牌三面,奖牌上“正堂陶”和“赏”字可清晰看到。在庙会这一场域中,存在着多方资本的斗争,宗教之间的斗争、儒生与宗教的斗争、商人与政府的斗争等。各方都希望能够把控庙会这一资本,这种资本斗争被动地促进了庙会的繁荣与发展。而对于普通乡民来说,则是希望在庙会活动中,通过向神祇祈祷,获得诸如平安、求子等心愿的满足。这种行为本身是符合普通群众的需要的,因此庙会香火的繁盛程度对于普通香众来说更容易获得认同感和满足感,同时也会让大家觉得寺庙中的神仙确实很灵验。
对于寺庙本身来说,庙会活动也会扩大寺庙的影响力,香火的多寡直接影响到的是寺庙的利益,因此寺庙本身也会维持一定的秩序,比如禁止一些影响到进香安全的活动出现,禁止一些商业活动影响到进香的秩序,更不允许捣乱的人前来破坏。其中有些并不是寺庙本身可以执行的,需要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因此康熙和嘉庆年间的告示通知碑刻就出现了这样的官府行为,这一行为本身也是在宣示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作用,对场域中的既得利益方进行维护。同时庙会行为也需要对事物或活动进行选择,即优胜劣汰,这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摒弃一些不符合社会主流思想或者资本需求的活动,庙会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化,最终形成如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庙会活动。
四、习俗传衍:香会与会首的信仰传达
浚县古庙会在浚县当地传承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具体出现时间尚无定论),若仅仅将其归类为信仰的强大体现则未免过于牵强。在庙会的传承中,习性和习俗的传衍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将场域这一概念看作一个游戏的话,资本无疑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一方,而习性则是这个游戏能够进行下去的重要保障。人们会在得到游戏体验后获得参与的能力,其对于游戏的理解和对规则的遵守就形成了习性。习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使其更加符合自身行为逻辑,而民间庙会活动繁荣兴盛并活跃至今,习性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庙会形式的活动。《礼记·杂记下》就有记载:“子贡观于蜡,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其中的“腊”就是指腊祭,是古代的一种祭祀活动,从对话中就能看出,这种祭祀活动具有很强的全民娱乐属性,而子贡本身就是卫国(今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时至西汉,《盐铁论》中就有了关于“朝山”的记载:“古者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忘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而《通俗编》中,直接指出“俗于远处进香谓之朝山,据文,则此俗之兴,由于西汉”。之后的数千年中,这种活动都不曾消失,只是在不断地变化。
明清时期的民间香社空前壮大,是民间参与庙会活动的主要力量,浚县众多庙宇中的碑刻也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民众参与庙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是以线性方式存在的,更多的是通过时间线来反映习性的产生。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常香会善信题名碑记》⑦云:“浚县南关内韩应龙母姓林氏者,性秉懿微,乐蠲好善,约闺阃淑媛二百余众,于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神庙点常香会,继十余年而未有已也……”由碑文内容就可以看出,有能力的庙会参与者会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庙会活动中来,如“韩应龙母林氏”这样一个德行兼备的信众就能够带领自己的朋友闺蜜二百余人参与到庙会活动中。这种“榜样”的力量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惯性。时至今日,笔者在浚县的采访过程中,依然看到有很多周边县市的群众和香会参与庙会活动,最远的甚至是从北京专程赶来上香的,更多的则是游客来参观这一民间盛会。当地很多参与庙会活动的人认为这样的活动已经在当地延续了上百年,到现在不应该丢弃,并且参与庙会活动已经和当地的过年风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年内必须做的一项活动,这种习惯深入当地人的骨髓。在浚县当地,不仅是庙会活动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各个大大小小的香会组织也都延续了下来,其内部的组织构成及文艺表演内容也都延续了明清时期的样式。这一惯性“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过程(ontogenesis),在身体上体现,而社会结构本身,又来源于一代代人的历史努力,即系统生成(phylogenesis)”⑧。清代乾隆二年(1737年)的《十王圣会四年完满碑记》⑨更是体现了这一理论观点:“……而邑东张耀祖一会,父子相承,祖孙相继,已历七十余载,其间苾芬歆香以飨以祠,其诚敬可谓至矣。前已立碑者二,今至周士儒、至张耀祖又四年完满。会众议立碑刻名以垂不朽,属余作文以纪其事……”这说明这个香会是以宗族家族为单位的会社。在家族的传承中,庙会活动也作为其重要一环传承了下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形成了这样的习性。
习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使其更加符合行为主体自身的逻辑性或自身的利益。法国社会学家菲利普·柯尔库夫认为:“禀性,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感觉、行动和思考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每个个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观条件和社会经历而通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在化并纳入自身的。持久的,这是因为即使这些享性在我们的经历中可以改变,那它们也深深扎根在我们身上,并倾向于抗拒变化,这样就在人的生命中显示某种连续性。可转移的,这是因为在某种经验的过程中获得的享性(例如家庭的经验)在经验的其他领域(例如职业)也会产生效果;这是人作为统一体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统,这是因为这些享性倾向于在它们之间形成一致性。”⑩一个群体的习性的产生一定是和当时的社会情况、群体受教育程度、历史文化的传承密不可分,习性代表着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我们将考察某一习性的时间线拉长就不难看出,习性在浚县的庙会活动中一直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并最终由量变的积累引发质变。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原因,另一方面是资本对抗。庙会活动起源于早期祭祀活动,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很多宗教祭祀的活动。在中国,宗教祭祀与民间祭祀是并存和共生的关系,到了唐代商业活动加入到祭祀活动中;而宋代则形成了相对发达和固定的庙市体系,祭祀活动与商业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庙会这一场域并非突然出现的,其本身就是习性的延续。依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庙会是由于资本的介入而形成的场域,而资本之所以会介入也是习性作用的结果。而在民间祭祀活动中一直不断地有新的资本介入,资本与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的关系,这种对抗也使得习性在其中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明清时期香客朝山进香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立碑,浚县浮丘、大伾两山留存朝山进香的碑刻就有80余块。最早记录朝山进香的碑刻是明代嘉靖年间的《浮丘山岳神灵应记》,立碑人为“浚司训谢载”。到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子孙祠碑记》,捐资和立碑人都是平民。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泰山圣母碧霞行宫供会四年圆满记言碑》,立碑人为“会首王思艾妻李氏”。顺治十三年《善信进香题名碑记》立碑人为“总领会首申养德母郭氏、会首邓守信母杨氏、会首刘天就母王氏、会首李一成妻卢氏、会首李三秋母屠氏、会首李从云母毛氏”。从这些立碑人就可以看出,顺治十三年以前的会首和立碑的人基本都是女性;时至顺治十六年《碧霞元君行宫碑记》,立碑人为“驾主李尚春,妻张氏;男李兰芳,妻李氏;次男李桂芳,妻孙氏;孙李进国,李进贤,李进忠”,此外还有部分捐资的官员名单,这块碑的立碑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但基本是以男性为主;清顺治十七年《浮顶进驾万善碑记》则是几家共同立碑,立碑人除一些官员外,还有上文提到的“驾主李尚春”,但这块碑记中已经没有女性出现了;之后的碧霞宫朝山进香的碑刻中仅4块中出现了女性。从这些立碑人的身份及性别变化就可以看出习性的变化,浚县早期的庙会活动很可能是由官员主导的,随后参与的人员以女性为主,毕竟从神祇的职能上来说,碧霞元君主要是负责送子和保平安的。康熙年间之后则是以男性为主导,神的功能也愈加强大,上文中提到的清康熙四十七年《仁育万物碑》也为男性知识分子参与庙会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使得能够参与庙会活动的人群范围更为广泛。时至今日,庙会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或观念的传达,甚至脱离了信仰传承的范畴,更多的是在惯性的作用下在当地形成了一种风俗习惯,这种风俗习惯将进一步与市场和新的观念相融合并不断延续下去。
五、结语
在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资本、习性和场的概念是要联系起来分析的,在分析庙会这一独立场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庙会活动中的场,不仅仅指的是空间和地理的场所,更多的是指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所谓习性正是由民间信仰和文化创造出来的,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印记,外部的资本介入才使得这一习性形成相对独立的一个场域,而资本在介入的过程中本身也会经过习性的改造。可以说,资本本身就是习性的产物,资本的介入使得场域中充满斗争性,让这一场域本身充满力量,并在斗争中不断优化和改良,使这个场域更加符合一定的内在逻辑性,这样才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被破坏并延续至今。用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庙会这一场域,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浚县古庙会是如何在历史发展中一直得以延续的,在了解之后我们也更加容易得知现在应该如何去保护古庙会这一优秀的民间文化内容。
注释:
①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康、李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171页。
②《重修碧霞元君行宫记》,此碑位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前院东侧,雕龙碑首,赑屃碑座,高380厘米,厚21厘米,楷书。
③《浮顶进驾万善碑记》,此碑位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前院西侧,高266厘米,宽88厘米,厚84厘米,楷书。
④《创建纯阳吕帝君洞阁碑记》,此碑位于浚县大伾山吕祖祠乾元殿前,雕龙首,赑屃碑座,高207厘米,宽79厘米,厚22厘米,楷书。
⑤《仁育万物碑》,此碑位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前,高235厘米,宽86.5厘米,厚23.5厘米,楷书。
⑥《清康熙五十二年告示》,此碑位于浚县浮丘山寝宫楼前西配楼内,高122厘米,宽73厘米,楷书。
⑦《常香会善信题名碑记》,此碑位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前,高214厘米,宽71.5厘米,厚24厘米,楷书。
⑧皮埃尔·布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桂裕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84页。
⑨《十王圣会四年完满碑记》,此碑位于浚县浮丘山碧霞宫中院东廊前,高97厘米,宽127厘米,厚19厘米,楷书。
⑩菲利普·柯尔库夫:《新社会学》,钱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