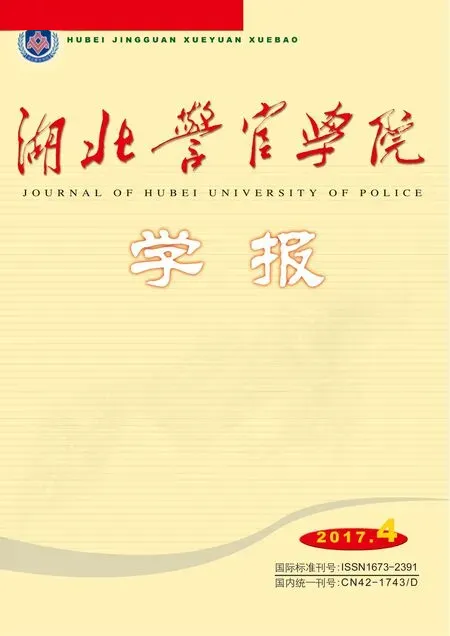家暴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中警察权的权限及行使
赵 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38)
家暴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中警察权的权限及行使
赵 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38)
随着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实践开展,关于警察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中的角色与责任、权限等问题引发一系列讨论。警察在家暴案件人身保护令执行中负有告知、协助申请保护令、收集资料与保留证据、执行保护令、及时教育及制裁加害人等职权与义务。警察权行使要以受害人、儿童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为优先考量;要有准确的立法授权,使警察职责明确,执法规范,干预积极;要实现社会联动,加强多机构合作;要适时培训与训练,开展专业干预。
人身安全保护令;家庭暴力;警察权;即时强制;告诫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关于妇女议题的讨论,特别是大会达成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强调了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的政府责任,也开启了中国对“家庭暴力”的研究及其立法进程。经过20多年的推动,我国在防治家庭暴力工作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16年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强调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明确了各政府机关、各职能部门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等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的职责及义务。《反家暴法》第四章专门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予以规定,民众对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充满期待。其中,与警察权行使相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警察在人身保护令实施中的角色与责任是什么?其权限设定如何?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中,警察权行使应坚持哪些原则?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一、家暴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中涉警问题
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为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在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常被称为紧急保护令(对受害人的保护)、暂时禁制令(对施暴人的禁止与限制)、不接触令(对受害人及其他相关人的保护)或保护令。它诞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美法系国家,是国外反家暴的成功经验。其设计意图在于:改变传统的事后处罚的干预方式,加强事前预防和事中合理干预,进行有针对性的司法法律救济。这种做法在国内外都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探索,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最有效的措施。
我国的人身保护令制度经历了长时间的司法实践。2008年,《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制,以下简称《审理指南》)开始试用。最高人民法院选择9个基层法院开展试点,2010年增至72个。由于效果明显,江苏、广东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学习试点省份经验的基础上,在本省自行开展试点工作。这一研究虽然不具有法的强制效力,但它开拓性地探索了法官审理与处置家暴案件的措施。《审理指南》专章规定人身安全保护措施,也是各地试点着重研究的问题。从实际效果看,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上百起案件中,被申请人能够自觉遵守裁定,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非常明显。①有关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参见杨跃、蔡仲维:《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反家庭暴力中的应用与完善》,《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139页。家暴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中的涉警问题主要集中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人身安全保护令警察执行限度和执行范围、公安机关与法院的配合等。
(一)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主体
《反家暴法》第32条明确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应当协助执行。《审理指南》第36条和2010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家庭暴力婚姻案件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程序规定(试行)》(以下简称《重庆规定》)同样把公安机关设定为执行主体的协助机关。②《审理指南》第36条规定:“人民法院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抄送辖区公安机关的同时,函告辖区的公安机关保持警觉,履行保护义务。公安机关拒不履行必要的保护义务,造成申请人伤害后果的,受害人可以以公安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追究相关责任。”《重庆规定》第15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由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执行本条规定第九条第(一)至(五)项时,可以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审理指南》第36条还规定,公安机关不履行保护义务,造成申请人伤害后果的,应追究责任。从实际意义上看,该规定将公安机关设定为执行主体。这一表述显示出该项工作模式仍处于探索之中,将哪个机构设为执行主体更适合,更有效还不明晰。
有的地方则把公安机关设定为主要执行主体。2010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依法处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家庭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江苏意见》)第8条至第12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作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执行主体的主要职责及具体措施。如第8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同时抄送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局(分局)、妇联组织。”第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由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局(分局)监督执行,妇联组织予以配合。”很明显,这里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设定为执行主体。
另有学者认为,民事保护令以公安机关为执行主体存在很大问题。该观点认为,警察权的设置与行使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必要。只要公民的行为没有危害国家利益,没有影响社会公共秩序,没有超越“私领域”,国家公共权力便不宜干预。同时,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基于警察权的强制性,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确保行政权力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行使而不被滥用。据此,警察权介入权限应被明确限定于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如依法及时取证,依法行使即时强制权、治安调解和处罚权。而在民事保护令执行方面,由于缺乏基本法的明确授权,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的适格性遭到了严重质疑。基于此,有学者提出,民事保护令须由人民法院执行,司法警察是民事保护令执行的应然主体。而公安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权力行使具有法定限度,公安机关不适合作为家暴案件民事保护令的执行主体。坚持此观点的学者还强调:“对于以民事请求方式出现的保护令,注重的是对受害人个体民事权利的维护,将属于司法权定位及司法强制权性质的民事执行权交由公安行政机关行使,缺乏理论上的支撑。”[1]
(二)警察执行范围
人身安全保护令包括对受害人的保护令和对施暴方的禁止令。《反家暴法》第29条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的四项措施。①《反家暴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审理指南》第三章对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种类、管辖、申请时间与条件、有效期、申请审查、送达、生效、执行、复议、听证、撤回审查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第27条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七项主要内容,其中四项为对被申请人的禁止措施,第4款和第6款为必要时责令被申请人必须做的内容,第7款则为对申请人的保护内容。②《审理指南》第27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内容:1.禁止被申请人殴打、威胁申请人或者申请人的亲友;2.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申请人,或者与申请人可能受到伤害的未成年子女进行不受欢迎的接触;3.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一方不得擅自处理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4.有必要的并且具备条件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暂时搬出双方共同的住处;5.禁止被申请人在距离下列场所200米内活动:申请人的住处、学校、工作单位或者其他申请人经常出入的场所;6.必要时,责令被申请人自费接受心理治疗;7.为保护申请人及其特定亲属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可见,禁止措施、责令要求和保护条款非常丰富。
根据工作需要,有些试点基层法院对裁定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和补充。例如,《重庆规定》第9条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内容扩大为九项,包括四项禁止条款、三项责令条款、一项中止条款和一项其他措施。除了《审理指南》七项内容外,其还增加了两项:在审查基础上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的生活费、医疗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教育费等款项。③《重庆规定》第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可以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内容:(一)禁止被申请人对受害人继续实施暴力行为;(二)禁止被申请人利用电话、信件、网络等方式骚扰受害人,或对受害人实施跟踪、窥视等行为;(三)中止被申请人对其未成年受害子女行使监护权或探视权;(四)有必要且具备条件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暂时迁出双方共同的住所或受害人的其他住所;(五)禁止被申请人进入受害人的住所或其他活动场所;(六)禁止被申请人擅自处分受害人居住的房屋及其他价值较大的夫妻共同财产;(七)申请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或者生活确有困难的,经申请人申请并经审查确有必要,可以责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在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生效期间的生活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费、教育费;(八)经申请人申请并经审查确有必要,可以责令被申请人给付受害人因被申请人的暴力行为而支付的医疗费及其他必要费用;(九)为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所必须的其他措施。
《江苏意见》则作出了更为细致的程序性规定。第9条规定:法院作出裁决,由当事人所在辖区的公安机关监督执行。第10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法院的裁定后,找双方当事人谈话,告知民事裁定书的具体内容和法律责任等。第11条规定:民警需将所有工作记录在案;依法处理家暴案件需规范化;公安机关要及时回应家庭暴力报警求助,及时出警,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公安机关可依照有关规定对行为人进行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常州市公安局《家庭暴力警情处置规范》强调,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由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局(分局)监督执行,并重申了时限、告知义务和准确记录的要求。
随着该项工作的深入,保护令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与我国法律对公安机关的赋权存在很大出入。特别是涉及金钱给付、监护权与探视权的中止以及房屋等共同财产的处分等内容的保护令,公安机关并无管辖权和执行权。
(三)公安机关与法院的配合
从目前的执法实践来看,各地公安机关能够配合人民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法律没有明文赋予公安机关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职权,对公安机关协助执行范围也没有进行明确规制,许多人仍然认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的协助执行并不属于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范围。这样一来,裁定的执行效果取决于当地法院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公安机关在人身保护令工作中的角色与责任、权限设定等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常态机制,无疑是裁定执行过程中的软肋。
《江苏意见》第8条规定,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后,除送给申请人和实施家暴的加害人外,还要送至当地警方和妇联。第9条、第10条规定:“公安局应在12小时内将民事裁定书转递至申请人、被申请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派出所应当在收到民事裁定书后12小时内指派社区民警与申请人、被申请人谈话。”“如遇申请人、被申请人外出等特殊情形导致无法在前款规定的12小时内进行谈话的,社区民警应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在上述情形消失后立即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第11条至第13条规定,警方及时回应报警,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同时收集固定证据并反馈给法院,法院则依法予以处理。如果当事人行为涉及犯罪,将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而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书但无权管辖的行为,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人民法院。很显然,公安机关与法院的配合与沟通贯穿于整个人身保护令的执行过程之中。
二、家暴案件人身保护令执行中警察的权限与义务
在我国,有关家庭暴力防治的规定是逐渐出现的。2001年《婚姻法》首次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并设专章规定了各机构的责任和救济措施。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要求公安、民政等机构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反家暴法》则总结近年来家庭暴力干预实践,对各机构的主要工作责任与工作原则进行了规定。我们需要明确警察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中和具体的家暴案件人身保护令执行中的权限范围。
(一)家庭暴力防治中的警察权限
世界各地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经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美国、加拿大、英国为代表的积极干预模式。这些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致力于防治家庭暴力问题,并在社区警务的框架下探索针对家庭暴力的“强制性逮捕”“强制性起诉”政策,授权警察在有正当理由认定某人实施家庭暴力时必须立即出面制止,强力干预,强制逮捕。二是以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为代表的法定介入。香港地区《家庭暴力条例》(1986年制定,1998年修订)和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1998年通过)明确对警察防治家庭暴力进行授权。台湾地区还专门制定了“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1999年),要求警方依法介入。①参见赵颖:《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2006年,第400-423页,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警察对家庭暴力干预的内容。三是以韩国为代表的有限介入模式。警察在制止暴力后,展开调查,并尊重受害人意见的酌情处理。警察权作为公权力,其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正当性基础是由国家赋予的。各国家及地区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稍有不同,但都经历过从不管到管的过程,也都对警察的干预权限进行了法律规定,并与社会各机构合力,以达到防治家庭暴力的效果。
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权主要包括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公安执法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必须在合理的限度内依法进行,有效处置。我国在家庭暴力干预实践中,综合考虑过以上模式,试图在法律上根据警察权的性质明确其权限行使的范围。我国《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刑事诉讼法》和《人民警察法》规定了公安机关的执法权界限,是指导公安机关依法行政的主要依据。而《反家暴法》则根据家庭暴力的特点,在出警、制止暴力、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协助民政部门对受害人进行临时庇护安置与救助、伤情鉴定、告诫、协助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等方面都涉及公安机关,进一步明确了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的责任义务。
家庭暴力干预中,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权主要是刑事立案、刑事侦查、刑事强制和刑罚执行权。根据《刑法》,家庭暴力涉及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强奸、猥亵、侮辱、诽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重婚、虐待、遗弃等。其中,除了故意杀人和造成严重后果的故意伤害罪外,其他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需要告诉才处理。针对这一现状,《反家暴法》第14条和第35条设置了强制报告制度,使警察获得介入自诉案件的合法途径。同时,为积极预防和有效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加强对家庭暴力被害人的刑事司法保护,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法发〔2015〕4号)(以下简称《2015意见》,要求依法及时、有效干预;迅速审查、立案和转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也就是说,警察面对家庭暴力中的各种犯罪行为,必须及时立案、侦查,及时收集证据,及时告知受害人自诉权利,及时实施刑事强制等,以有效行使刑事司法权。
家庭暴力干预中,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执法权的问题较多。长久以来,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进行分界,限制警察权的扩张,是规范公安行政执法的重要思路。公安行政执法既要尊重人们正常的私人生活,又要干预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警察处置家庭暴力的困难所在。对此,以妇联为代表的各机构通常以《人民警察法》第21条规定的公安机关的社会服务职能为依据,要求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对家庭暴力积极介入。②《人民警察法》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
综合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结合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执法实践可知,在反家庭暴力工作中,警察权的权限范围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防权。预防胜于打击,加强前期预防,可以有效加强社会建设,减少受害者痛苦。公安机关预防权的行使既包括《反家暴法》规定的各种普法宣传,也包括防止家庭暴力行为升级为犯罪行为的各种措施。
第二,即时强制权。警察的即时强制权包括警察及时出警、控制局面,制止正在发生的危险或者违法行为。2008年中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全国妇联七部委《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2008意见》)强调,要将家庭暴力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并及时有效处警。①《2008意见》第8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设立家庭暴力案件投诉点,将家庭暴力报警纳入“110”出警工作范围,并按照《“110”接处警规则》的有关规定对家庭暴力求助投诉及时进行处理。公安机关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构成刑事犯罪的,应当依法受理或立案,及时查处。
第三,收集证据权。国家对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的禁止态度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制裁来体现,而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都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证据基础上。《2015意见》第11条专门强调:“公安机关在办理家庭暴力案件时,要充分、全面地收集、固定证据,除了收集现场的物证、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外,还应当注意及时向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妇联、共青团、残联、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单位、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被害人的亲属、邻居等收集涉及家庭暴力的处理记录、病历、照片、视频等证据。”警察出警过程中的及时调查取证和准确记录,对于后续的其他法律救援工作极为重要。
第四,告诫权。公安告诫制度是《反家暴法》的一大亮点。《反家暴法》第16条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制作书面告诫书制度强化了轻微家暴行为的执法规范。
第五,行政处罚权。《反家暴法》第33条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警察依据法律规定,及时对施暴者实施行政制裁,表现出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绝对不容忍的态度。
第六,行政调解权。这主要针对情节轻微的家庭暴力。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行使行政调解权,并不是单纯追求双方和解,而应该尊重受害者的意愿,表明其保护受害者权利的态度。《2008意见》特别强调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对于可以调解的情况,“应当遵循既要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家庭团结,坚持调解的原则,对施暴者予以批评、训诫,告知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相应的后果,防范和制止事态扩大”。
规范人民警察干预和处置家庭暴力行为是警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面临的法律问题。公安机关反家暴的明确态度和及时处理的现实做法可以有效警示加害人,妥善救治、安置被害人,预防和减少犯罪。
(二)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执行中警察的义务
结合警察在家庭暴力防治中的权限范围,借鉴国内外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警察在家庭暴力人身保护令实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警察出警后,会第一时间接触受害人与加害人,警察如何作为,如何行使职权非常重要。它表明了公权力的态度,也会对受害人与加害人造成切实的干预效果。
第一,告知。警察负有对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告知义务,需要通过谈话,明确告知裁定书的具体内容和法律责任。特别是对申请人的告知要清晰明白,告知申请人的权利、可获得的帮助以及公安机关和其他机构可协助其获得这些帮助。警察的告知可以起到预防家庭暴力的作用。各地公安机关在制定家庭暴力处置操作规范时,都在送达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书时特别强调了告知义务。
第二,协助申请保护令。申请保护令的一般程序是由受害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特殊情况下,公安机关也可以代为申请。《反家暴法》第23条对此进行了明确规定。②《反家暴法》第23条规定: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其他遭受强制、威吓等无法申请的,公安机关也可以代为申请。按照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警察机关可以为被害人申请暂时保护令;在特别紧急情况下,甚至可以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替被害人向法院加急申请。而警察在紧急情况下提出暂时保护令申请的,法院通常会根据警察所陈述的事实,在4小时内就以书面方式核发(除非有正当理由)。这一紧急(暂时)保护令是在对家庭暴力进行适时的危险评估的基础上的决定,可以适时保护受害人、限制加害人。
第三,收集资料与保留证据。警察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时,应及时收集资料并注意保留相关证据,制作书面记录。依据《反家暴法》第2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出警资料、告诫书和其他证据也为受害者进一步申请人身保护令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执行保护令。虽然《反家暴法》确定公安机关为保护令的协助执行单位,但各地在实践中皆将公安机关作为最重要的执行单位。特别是我国“110”报警热线的24小时制和公安派出所和巡警部门的网格式勤务制度,使人们对于警方及时出警、制止暴力、执行保护令心存期待。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和《美国示范法典》都强调警察机关要执行保护令,并根据警察机关与法院的不同权限,明文严格区分警察机关、法院执行保护令的不同职责,具有可操作性。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主要集中于及时充分地告知受害人所享有的权利、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人身安全、协助受害人和孩子及时就医、协助受害人随身带走个人生活必需品,协助将受害人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或救助管理机构等。
第五,及时教育及制裁加害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只是一种临时性救济措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送达、执行和监督旨在教育、限制及制裁加害人,引导其改变其行为,调整好家庭关系。能否达到目的,送达人和执行人的威慑力和强制力极为关键。①参见陈敏:《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现状、挑战及其解决》,《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6年第3期,第36-42页。文中作者统计了《反家暴法》实施后1个月里全国3117个基层法院共发出的33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效果,发现有4名被申请人挑战了司法权威,其中两位明显只服从于公安警察的行政执法。诸多经验使部分人开始致力于修改《反家暴法》,试图重新规定公安机关为执行义务机关。各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强调公安机关接到法院的裁定后,要找双方当事人谈话,告知裁定书的具体内容和法律责任。②如《江苏意见》第10条。警察在送达、执行和监督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干预家暴工作中必须兼顾制裁与教育原则,对于家庭暴力加害人进行及时教育,告知禁止事项,及时提醒其对法律的遵守,明确再犯责任,加强对加害人的控制与管理。
三、家暴案件人身保护令执行中警察权行使的建议
2016年《反家暴法》颁布实施后,各地积极出台配套措施,健全并落实强制报告、公安告诫、家暴庇护、人身安全保护令等系列制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11月底,已有17个省区市出台了贯彻实施《反家暴法》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文件共计110份。[2]在人身保护令签发与执行方面,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特别是试点地区积极出台政策,规范相关工作。警察机关在执行家暴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时还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以受害人、儿童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为优先考量
公安机关与人民警察不论是初次接警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还是接到法院有关保护令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面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和加害人时,必须以受害人、儿童和执法人员自身的安全为优先考量。
2009年董珊珊被丈夫王光宇殴打致死案表明,公安机关必须重视家庭暴力问题。③陈虹伟、莫静清:《董珊珊,一个家庭暴力下的冤魂》,《爱情婚姻家庭(特别观察)》2010年第4期。2010年兰州市公安局特警窦勇处置家庭暴力案件时遇害案则表明警察面临的现实危险。处置家庭暴力必须对家庭暴力的危险性进行准确评估。两个典型案例均表明面对家庭暴力,警察缺乏足够的敏感,未能准确评估其危险性,故不但不能有效保护受害者的安全,还会使警察自身陷入危险境地。
及时而准确的危险评估是警察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关键环节。英国West Yorkshire市通过逐渐加强的三阶段介入措施防止被害者的重复被害:一方面保护被害人,另一方面消除加害者再次施暴的动力。他们研制了三阶段危险评估程序,按照执法的一般流程,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评估由现场警察负责,是现场的初次危险评估。警察接案后及时到达现场,处置时要判明是否有违法情节,还会观察环境和询问被害人是否存在高危险因素。在此基础上,警方现场搜集有关信息,对加害人施加给被害人之危险层级分析,判断其是普通(Standard)、中度(Medium)还是高度(High),并依层级进行记录。第二阶段评估由家暴专员(DomesticViolenceCo-ordinator)负责。家暴专员会检查警察在案发现场所作的初次评估,还会尽快安排被害者作更深入的危险评估,根据危险的不同等级和相关政策规定,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采取相关措施。第三阶段是起诉或释放前的危险评估,这一评估由看守所评估员(Custody Officer)及家暴专员共同作出。当加害人因家庭暴力罪被逮捕后,看守所评估员对加害人进行访谈,并将其判断和评估交给家暴专员加以判断。实践证明,相互衔接的评估减低了案件再次发生的机率。[3]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明杰设计了DA量表(DangerAssess-ment),对家庭暴力进行危险性评估。这一设计增加了干预的操作性。不论是警察还是社工,接案后就可以先评估,再依据致命危险程度制定干预策略。这既可以有效地保护受害人,也可以对施暴人进行必要的治疗辅导。[4]
(二)准确的立法授权,使警察职责明确,执法规范,积极干预
没有准确清晰的立法授权,警察在处置家庭暴力时就会责任不清、程序不明。《婚姻法》第43条和第45条规定了警察制止家庭暴力的义务,强调公安机关要及时制止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并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分别规定了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但相当笼统。《反家暴法》第三章要求公安机关及时出警,并特别强调了调查取证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警察职责,还规定了公安机关的协助救助义务,如协助就医、伤情鉴定和安置,针对最多数量的“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家庭暴力特别加设了公安告诫制度,但仍然相当原则。如果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没有关于具体措施、程序和执法责任的规定,警察遇到家暴案件时可能会不作为,或未能及时提取证据、制作笔录,造成事后的定性难、取证难。
对此,我们需要借鉴域外的良好经验。警察是治理家庭暴力的积极的执法者。美国《反家庭暴力模范法典》第204条、第205条、第206条、第207条、第209条分别规定了警察防治家庭暴力的各项职责,如对涉及家庭暴力犯罪人、对某些违反保护令的人的强制性现场逮捕,警察扣押武器的权力以及对违反释放所附条件的强制逮捕。警察职责的清晰化使美国警方必须严格执法,调查搜证,严肃处理嫌犯,执行保护令,协助受害人。[5]
警察机关如何配合法院做好家庭暴力人身保护裁定的相关工作,可以采用哪些具体方式,同样缺乏足够的法律授权,使相关工作的开展缺乏依据。我国台湾地区警察处理家庭暴力的权责包括申请及执行保护令、协助受害人取得紧急保护令、搜捕施暴者、保护受害者、通报及协助义务等。为克服轻视家庭暴力的现象,规范警察处理家暴案件的办案程序,促使警察严格执法,台湾地区还进一步制定了“警察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流程图”“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流程图”,①具体流程可参见赵颖:《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理论与实践》,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第422页。也为处理家庭暴力制作了专门的调查记录表和现场报告表。这些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公安机关要在法治框架内实施积极干预,亟须制定相关政策与法律,准确进行立法授权,界定警察的执行保护令的职权界限与执行程序。应制定有关实施《反家暴法》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和办法,特别要细化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除了细化保护令申请书的格式、执行保护令的具体措施和保护令的举证责任及审理程序外,还需要对具体的执行程序,特别是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会如何协助执行作出明确规定,以确保保护令能够执行到位。
(三)实现社会联动,加强多机构合作
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利于及时保护家暴受害人,防止家庭暴力升级。《反家暴法》第四章共10条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形式、管辖、条件、种类、措施、期限、送达、执行进行了规定,还在法律责任中设专条规定违反保护令的法律责任,全面完整地规定了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各项制度。这些制度涉及许多机构。
多机构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除当事人可以申请保护令外,为了保护那些受到家暴却没有能力或无法申请保护令的的受害者,法律赋予其近亲属和相关机构代为申请的权利。《反家暴法》第23条规定:“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不能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这些可能与家暴受害人直接接触或了解家暴情况的机构的及时介入、代为申请可以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安全,使他们有机会及早脱离家暴环境,避免继续受暴。
多机构协助执行保护令。《反家暴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多机构合作的目标是有效干预家庭暴力,减少家庭暴力犯罪,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各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都能积极参与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就能减小警察的压力,有力遏制家庭暴力案件,提高干预家庭暴力的正面效果。多机构合作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模式。正如欧盟会议文件(1999年)第8条和第11条所指出的:“警方不可能孤军奋战,面对伤害妇女的暴力问题,必须加强与其他团体和组织的合作,特别是例如家庭犯罪法庭、儿童青少年保护协会、妇女团体、预治暴力犯罪的团体。为了有效减少针对妇女的暴力,一个多方面、多层次的相互合作是十分必要的。警方应有效地与地方、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建造一个有效打击家庭犯罪的网络。”“所有的政府部门必需共同承担家庭暴力的责任,共同合作。”
家庭暴力人身保护措施实施中,警察权行使更应在多机构合作的框架下进行。防治家庭暴力和受害人的救助是一项系统工程。应通过社会联动,实现防治结合。一是通过宣传发动,在群众中逐渐形成反家暴的社会共识。二是通过预防和遏制家庭暴力,有效化解因家庭纠纷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面对复杂的家庭暴力现象,家庭暴力干预主体和干预手段必须多元化。社会联动的多机构合作是一种战略考虑,涉及从观念到行动的系统工程。为了发挥多机构合作的作用,应建立多机构合作机制,使各机构在预防与处理家庭暴力工作中各司其职,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推诿;必须强调从观念到行动的综合改变,开展对相关机构的培训与教育,在各机构建立共同的、不容忍家庭暴力并认真处理家庭暴力的价值观和工作规范。
(四)适时培训与训练,开展专业干预
基于家庭暴力的复杂性及其破坏性影响,警察对家庭暴力报警给予积极响应十分重要。有些公安机关和警察虽然重视,但由于不了解家庭暴力的规律和特点,视家庭暴力为一般案件,缺乏专业对待的意识和能力。探讨警察预防与制止家庭暴力的执法规范,设置专人进行专业干预非常重要。目前各省市出台了大量文件,探索防治家庭暴力的有效办法。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创建“零家庭暴力社区”,公安机关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站”;辽宁省为提高公安民警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敏感度及处理家庭暴力的能力,举办公安民警社会性别意识与反家暴培训班;河北省迁西县则推行“白丝带运动”,公安、司法与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各乡的工作小组,设立家庭暴力投诉站,进行共同干预。这些探索意义重大。
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都有家庭暴力的专门规定,当地警察也针对家庭暴力展开干预探索,制定了相应的干预流程。台湾地区还专门制定了“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办法”和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现场报告表、调查纪录表等;在警察机关处理家庭暴力案件流程中,专门规定了对受害人的保护与安置。如“发现伤患,即呼叫救护车送医,并做适当之急救”“保护被害人及子女至庇护或医疗处所”,还强调及时与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联系,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和法律扶助等。[6]这些规定通过参与式培训方式传达给当地警方,以提高警察机关执行保护令及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能力。
在英国WestYorkshire市,各警察部门都配备了家暴专员。当家暴发生后,这些受过特别训练的专员会以高度敏感性参与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置,对其进行危险评估,并与被害人一同制定安全计划,还会以警告信函(WarningLetters)的方式教育加害人。此外,他们还提供相关救助信息和救助机构名录,以方便被害人及其家属求助。WestYorkshire警察局要求每位警察都要重视家庭暴力问题,为被害人提供支持,教育并控制加害人;特别注意评估危险等级;特别重视证据的收集,并强调只要查实证据即移送起诉。[7]
[1]姜虹.民事保护令执行主体的立法考量——以公安机关作为民事保护令执行主体是否适格为切入点[J].公安研究,2013(7):37.
[2]宋秀岩.在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交流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妇运,2016(12):39.
[3][7]林明杰.台湾家庭暴力危险分级方案之成效:一个分类整合模式[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1):23-24.
[4]林明杰.婚姻暴力加害人再犯危险评估量表之建立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06(3):117.
[5]赵颖.美国警察针对家庭暴力的逮捕政策及干预模式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1):154-155.
[6]涂秀蕊.家庭暴力法律救援[M].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67.
【责任编校:王 欢】
The Author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Police Power in the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 of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Zhao Ying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38,China)
Along with the practice of personal safety measures,and caused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on the role,responsibili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poli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The function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olice in domestic violence cases according to the personal protection order,such as inform and assist in applying for protection order,collect information and preserve evidence,implement the protection order,conduct timely education and penalize injuring persons and so on.In the execution of the domestic violence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the police power shouldbe taken toguaranteethe safetyofinjured persons,children andlaw enforcementofficers aspriorityconsideration.We should have accurate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and defin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olice clearly,standardization of law enforcement,and positive intervention.In order to achieve social linkage,strengthen cooperation of various agencies,timely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d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Personal Safety Protection Order;Domestic Violence;Police Power;Immediate Coercion;Caution Against
D923.9
A
1673―2391(2017)04―0033―08
2016-12-21
赵颖(1968—),女,辽宁锦州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安思政与文化。
本文得到北京市马克思主义与全面依法治国协同创新中心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