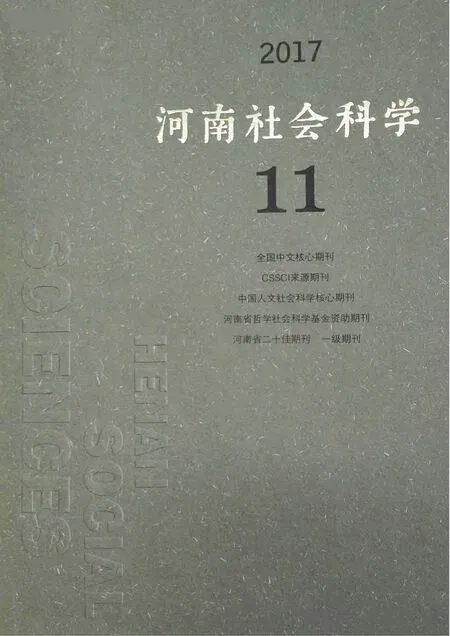左翼文学批评的裂隙:1932年《地泉》批判再解读
张 剑
(1.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左翼文学批评的裂隙:1932年《地泉》批判再解读
张 剑1,2
(1.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2.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1932年的《地泉》批判在一致的表象下潜藏着诸多裂隙。由于批评者身份与学识上的差异,更由于其写序时的心态与关注点的不同,几篇序言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充满了批评与反批评。华汉的自序使得那些潜藏在表面的一致之下的诸多差异得以显现。这种差异、错位与裂隙,揭示出左翼文学批评的深层逻辑,即重内容轻形式与浓厚的政治焦虑,而对革命文学作品的“浪漫谛克”的形式的关注,不过是一个虚幻的聚焦点。
左翼文学批评;《地泉》;内容侧重;政治焦虑
1932年,在湖风书局重版《地泉》三部曲之际,瞿秋白、茅盾、钱杏邨等“五大批评家”联手“作序”对《地泉》进行批判,在左翼文学发展史乃至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史上,这都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大事件”。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地泉》批判被描述为左翼批评界一次空前的统一,彻底肃清了革命文学时期的“浪漫谛克”倾向。然而,一个时段的文学批评可能会由于时代因素与时代的审美趣味具备某些共性特征,但批评家的个性又总是使其或隐或显地修正、突破“共识”,从而使原先看似铁板一块的文学批评逐渐松动,造成差异化。对于研究界已经高度熟悉化、阐释定型的《地泉》批判,至少有几个问题需要追问:一是在批评对象上,《地泉》具备了怎样的典型意义?二是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五大批评家能否真正保持一致?三是这种裂隙丛生而又追求“一致”的左翼文学批评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一、《地泉》:非典型左翼文学批评样本
关于《地泉》三部曲的批判虽然发生于1932年,但《地泉》几个中篇的写作时间却在“左联”成立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其中《深入》原名《暗夜》,出版于1928年8月间;《转换》原名《寒梅》,写于1929年夏间;而《复兴》写于1930年的7月。除《复兴》外,另外两个中篇小说均单独出版发行过。至于将作品改名并以“地泉”之名将这三个中篇小说合在一起出版的原因,作者曾指出是应对当时审查制度的需要:“为了逃避书报检查,我们也想了很多对策。例如我的一个长篇《地泉》,其中是三个互不联系的中篇——《深入》《转换》《复兴》,因为这三个中篇都被禁,无法再出。后来湖风书店想出了办法,把三个中篇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长篇,用了个《地泉》名字(其中又把《暗夜》改成《深入》,《寒梅》改成《转换》)来出版。这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检查。”①实际上,以“三部曲”的方式将这三个中篇连缀出版,并不是始自1932年湖风书局的那个版本,而是始自1930年10月间。据回忆,“阳翰笙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完成《复兴》后,同年十月将前此创作的《深入》和《转换》连同这部作品一起连缀成长篇小说《地泉》交上海平凡书局出版”②。这次出版之后文艺界的反应,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我们已无从得知,据华汉自己所言,是“得到了相当的成功”的。
为什么这样的“得到了相当的成功”的作品,到了1932年却戏剧性地成为左翼文学批评的对象,招来大张旗鼓地批判呢?这彰显出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在创作与批评上的巨大分歧。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在概念上很大程度是重合的,革命文学是左翼文学的准备与“预演”,而左翼文学则是革命文学的成熟形态。因此,由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完全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自然发展,当然也很难发现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种种困惑、尴尬与悖论。实际上,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在产生语境、作家队伍、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左联”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针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混乱成立的,“左联”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在文学批评上肃清革命文学的影响,建立新的文学秩序与文学规范。
“左联”成立之后,非常重视文学批评对于创作的规范与引导作用,“左联”的总纲领之一便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具体说来就是“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③。这里所说的“对过去艺术的批判”,不仅包括古代作品里的封建思想,也包括“五四文学”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革命文学作品中的革命加恋爱、“浪漫谛克”倾向。在左翼文学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理论与创作之间不合拍的现象,虽然“左联”力图通过理论上的规范去引导创作,但是一旦落实到作家的具体的创作过程,作品总是有意无意地“越界”,从而与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紧张关系。
《地泉》再版的1932年,左翼文学批评界就处于这样的“批评的焦虑”中。左翼批评家们想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写作与批评秩序,却总是苦于理论的枯涩无力。《地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五大批评家”的视野。作为主要完成于“左联”前的作品,对《地泉》的批判足以彰显出左翼文学批评的鲜明姿态,而联手作序的方式又颇具话题意味与冲击力。那么,左翼批评家眼中如此典型的《地泉》,究竟具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实际上,将《地泉》作为革命文学时期的代表作,委实有点冤。从作品的内容上看,《地泉》虽多少带有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作品的特征,但并不明显,给《地泉》加上个人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等称号并不准确。《深入》写的是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整个作品里面只有革命,没有恋爱。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注重群像的展示而不注重个性的刻画,这对文学形象的成功塑造自然会产生影响,但是在当时却是受到“左联”鼓励的创作方法。而《转换》《复兴》的确写了林怀秋这样一个“突变式的英雄”以及他与女革命者梦云之间源于革命也终于革命的爱情,虽然也涉及革命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加恋爱的题材问题,但并没有展开很多笔墨。作品叙述的重点,仍然是落在革命上面。相比较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洪灵菲的《流亡》三部曲,甚至是茅盾的《虹》《蚀》三部曲等作品而言,《地泉》的“浪漫谛克”倾向并不突出。因此,对《地泉》的批判,并不是针对这一作品的艺术成就本身,而是将其看作某个特定时期的标本进行解剖的,显示了“左联”文艺批评强烈的一体化需求。
1932年湖风书局重版《地泉》,给左翼文学批评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作者华汉“请了几个曾经读过我这部书而且在口头上也发表过一些意见的朋友,严厉无情地给这本书一个批评”④,这就是书前的几篇序的由来。在“左联”文艺批评家看来,华汉的邀序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当时重版《地泉》的湖风书局本就是中共控制下的书局,这就使得他们能够畅所欲言,无所顾忌。于是,并不“典型”的《地泉》也便成为革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批评范本。
二、批评与反批评:五大批评家的“对话”
文学批评是一件凝结着批评家学识阅历、审美品位、人格魅力的文学阐释与鉴赏活动,好的文学批评往往是高度个性化的。特定时期的文学批评囿于时代因素可能有同质化倾向,但批评家的个性特征又往往使文学批评呈现出差异性与内在的裂隙。这种裂隙,恰恰是解读文学史发展的关键线索。
所谓的五大批评家,指的是易嘉(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华汉(阳翰笙)。其中华汉就是该书的作者本人。这五人之中,瞿秋白在1931年时被王明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到上海后主要负责文艺宣传工作,其余四人则都是“左联”成员。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了大量的杂感和文学批评,有着很高的文学天赋,但是中共的领导者的身份显然对他的文学批评有所影响。五大批评家联手作序,显然要彰显左翼文学批评界的团结,展现批评家在文学立场与批评观念上的一致性。然而,他们在身份和学识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写序时的不同心境,造成了他们对《地泉》解读的不同方式。
在五人之中,最权威的、能够代表中共对《地泉》定性,同时也是批评最严厉的是瞿秋白。他在序言中首先引用了法捷耶夫的《打倒席勒》中的话,即“普洛的先进的艺术家不走浪漫谛克的路线”“不走庸俗的现实主义的路线”,要和过去的艺术家不同,不但要理解世界,还要自觉地为改变这个世界而服务。接着,他给定了《地泉》在中国新文学史的位置,认为《地泉》正是中国新文学“难产”时期的产物,还留着难产时期的斑点。瞿秋白在此所言的中国新文学,联系上下文来看,实际上指的就是新兴的左翼文学。把革命文学时期称为难产时期,本身就表明瞿秋白对那一阶段文学的判断。在瞿秋白看来,革命文学这一“难产期”的文学的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充满了“革命的浪漫谛克”,而《地泉》的路线正是“浪漫谛克”的路线⑤。对于瞿秋白来说,得出这一结论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他写作这篇序言的目的,他无意于对《地泉》进行审美判断与分析,即使他在后面大段引用《地泉》的原文,也只是作为批判的例证。可以说,瞿秋白的序言是一种政治家解读文学的方式,有宏观视野而无审美体验,有严厉批判而无同情理解。他的论断也奠定了此次《地泉》批判的调子。
瞿秋白的论断,给这次联手批判奠定了基调,其他几人在对《地泉》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文学定位并无本质上的异议。与瞿秋白的果断、严厉相比,郑伯奇的序言写得相当谦虚、委婉,他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瞿秋白的结论:“普洛革命文学的第一期,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时代;因之,第一期的作品,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⑥不过与瞿秋白不同的是,郑伯奇多少对于革命文学作品有着一定的理解与同情,毕竟,他也是亲身经历过那样的阶段的。因此,评价《地泉》也是在反省他自身:“我读你的作品的时候,我的心中却不住的和以前的自己算账。当然,你的许多长处——斗争的实践,伟大的时代相,矫健的文字,强烈的煽动性——都是我所企求而不能得的;但是你的短处,却不幸有许多和我相同。”⑦
从所涉及的问题来看,茅盾的序言最有价值。茅盾显然不能满足于对革命文学作品“浪漫谛克”倾向的单纯批判,他所感兴趣的是从艺术的角度探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是成功的。当然,对于“浪漫谛克”倾向的否定以及向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迈进这一方向性、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否定的,这也是茅盾发言的前提。他承认“一九二八到三○年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现在差不多公认是失败”⑧,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分析这些作品失败的原因。他归结为两点:“(一)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二)缺乏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⑨关于前者,茅盾举出了蒋光慈的例子,认为其正是因为缺乏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认识,导致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脸谱主义”和对现实的严重歪曲。而关于后者,《地泉》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文艺作品之所以异于标语传单者,即在文艺作品首要的职务是在用形象的言辞以感情的去影响普通一般人”⑩,才能使读者热情奋发,从而产生感人的力量。茅盾所总结的革命文学作品失败的两条原因,尤其是他对“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的重视,与他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对艺术性的坚持是一致的。可以说,在作序的几个人之中,茅盾对于革命文学作品体察得最为深入,也最能批评到点子上。然而,从华汉的序言看来,他最不能认同的、反驳得最厉害的就是茅盾的观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留在下文论及。
第四篇序言的执笔者是钱杏邨。这是当时左翼文坛上最为活跃的批评家之一,从文坛倾向到具体的创作月评、作家论,他都有涉及。“左联”成立前后,钱杏邨保持着很高的文艺批评产量,他对左翼文艺批评的那套术语运用得非常娴熟。钱杏邨的文艺批评的特点是能够准确地把握政策的需要,且善于总结与归类。在《地泉》序中,他指出了“初期中国普洛文学”的几种不正确的倾向: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倾向,浪漫主义的倾向,才子佳人英雄儿女的倾向,幻灭动摇的倾向。“左联”虽然早在1931年就已经对这些错误的倾向开始了斗争,但是一直到写序时还是没有肃清,已经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一道阻路的牢实的大墙”。至于解决的方法,钱杏邨提到了大众化问题,认为只有大众化问题的开展才能克服这些错误的倾向。总体说来,这篇序言显示了钱杏邨出色的总结能力,但是核心观点上只是将瞿秋白的“浪漫谛克”做了演绎而已,并没有什么深刻与突出之处。
如果没有作者华汉自己写的序言,这场对《地泉》的联手批评可能真的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批判运动了。但是有了华汉自己的序言,有了他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和对批评意见的辩解,那些潜藏在表面的一致之下的诸多差异才得以显现,这一场旨在求同的批判运动也因此充满了裂隙。华汉在序中首先回顾了《地泉》的创作历程,尤其强调了左倾思潮的影响:“那时有好多人都在这一‘复兴’时期中发了狂,说大话,放空炮,成了这一时期的时髦流行病。”⑪而他当时在上海,也自然受到了这一风气的影响。华汉对于自己写作历程的回忆,显然是有所侧重点的,也包含着为自己辩解的成分。瞿秋白对于他的作品的定位是不容否定的,他也承认瞿秋白对于《地泉》所存在的问题看得最明白、最透彻,但是他仍然感到几分委屈。他认为瞿文“只教我们应该怎样走,还没告诉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走得到”⑫,也就是说对于“为什么我们那时几乎无例外的大都去走浪漫谛克的路线,而不在创作方法上去走唯物辩证法的路线”⑬的原因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在华汉看来,革命文学作品中固然有着很多缺陷,那也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是必经的阶段。左倾的气氛,革命的狂欢化与“浪漫谛克”化,小资产阶级的游移与彷徨,都是革命文学产生语境的构成要素。作家实际上正是抱着一种虔诚的信念去进行革命与恋爱的书写的,这种写作也是他们坚守信仰的方式。至少在情感上,他对于瞿秋白将《地泉》以及那个时代完全否定还是难以接受的。然而,由于华汉急于告别过去的决绝姿态,也由于瞿秋白结论实际上的不容否定,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更多的论述。
华汉在序言中回应得最多的,是茅盾的批评。他虽然表示对茅盾所指摘的两大缺点“诚意接受”,但是读完序言会发现他不仅没有接受,反而全盘推翻了茅盾的观点,甚至变成了对于茅盾作品的反批评。在华汉看来,茅盾的观点“实际上只是一个注重作品的形式的基本观点”⑭。由于茅盾不具备瞿秋白的党的领导的身份,而且在革命文学中还是被批判的对象,所以华汉批评起茅盾来很是放得开手脚,甚至在字里行间还弥漫着一股怨气。他举茅盾的《蚀》为例说,《蚀》对于“社会现象有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也有“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虽然如郑振铎之流将“我们的茅盾的三部曲”推崇为“划时期的作品”,可是在他看来,“却与我们所需要的新兴文学没有原则上的相同点”⑮。至于茅盾用以举例的蒋光慈的作品的“脸谱主义”,华汉反驳说:“读过光慈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丽莎的哀怨》的人,大概总不会把那样一个悲惨动人的丽莎,看成是一张可以‘戴来戴去’的‘脸谱’的吧!”⑯而从茅盾所说的第二个条件即“感情的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来看,这恰恰是蒋光慈的强项。蒋光慈的作品不乏拜伦式的激情与张扬,也往往能够引起读者情感上的震动。但在华汉看来,这并不是件好事,因为必须追问这种“感情”是什么性质的,它对于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早先华汉曾专门撰文批评蒋光慈的小说:“《丽莎的哀怨》的效果,只能激起读者对于俄国贵族的没落的同情,只能挑拨起读者由此同情而生的对于‘十月革命’的愤感,就退一步来说吧:即使读者不发生愤感,也要产生人类因阶级斗争所带来的灾害的可怕之虚无主义的信念。”⑰因此,蒋光慈的作品虽然具备了茅盾所说的文学作品成功的两个条件,但仍是失败了,这就从论点到论据把茅盾的观点全盘否定了。
三、错位与裂隙:左翼文学批评的内容侧重与政治焦虑
当我们将序言的作者们的身份、学识以及他们写序时的心态与兴奋点做一番考察,尤其是考虑到其中存在的不同观点的碰撞以及华汉自身的反批评,这样一场批判运动实际所达到的效果便大打折扣了,这更像是一个充满不同意见的对话,而不是一场纯粹的、完全同一的批判。这次讨论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对待革命文学作品的“浪漫谛克”倾向的具体问题,还关涉自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如何取舍、左翼文学批评的政治焦虑等一些较为根本的问题。
贯穿于这几篇序言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给革命文学作品定位。瞿秋白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缺乏对革命文学必要的感受与理解,首先将革命文学时期称为“难产时期”。瞿的论断之后,其他的几人关于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发言的空间,只能在瞿秋白的结论下做一些引申或者细微的修正。郑伯奇对于“普洛革命文学的第一期”的划分,茅盾对于“一九二八到三○年这一时期”的作品“差不多公认是失败”的论断,都对革命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但是在情感上,他们仍然对于那一时期的作品有着一定的理解和同情,这与瞿秋白的决绝批判形成了一定的对照。华汉在自序中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委屈,他认为瞿秋白并没有考虑到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氛围,以及这些作品在当时情境下所具有的一定的合理性。遗憾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这几篇序言所表现出来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左翼文学批评的方式与特征问题。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类型,左翼文学批评区别于京派文学批评和海派文学批评的特征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几篇序言写作者的思想理路,以及不同观点的碰撞,就可以对左翼文学批评的内在逻辑有所揭示。从几篇序言的内容上看,几乎所有的写序者都涉及革命文学作品的“浪漫谛克”倾向的问题,并对之加以批判。然而,“浪漫谛克”究竟指的是一种内容和题材上的倾向,还是指在写作方式上的概念化与公式化?从内容上看,《地泉》除了些许“革命加恋爱”的倾向外,它所描写的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农民的愤怒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转向等,都是符合“左联”文艺批评界的要求的。因此,这场批判运动似乎是要纠正自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中一直存在的文学作品的形式问题。瞿秋白对于《地泉》的“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能够做到”的论断,郑伯奇的“革命故事的抽象描写”的批评,茅盾和钱杏邨对于革命文学作品失败原因的总结,从表面上看来,立足点都在作品的形式问题。然而,最为吊诡的是,华汉在自己的序言中恰恰指责茅盾“只是一个注重作品的形式的基本观点”。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技巧本身在左翼文学批评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
实际上,自革命文学运动以来,文学作品的形式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左翼文学批评有着一种显明的内容优先倾向和意识形态焦虑。正如钱杏邨所言:“普罗列搭利亚文艺批评家的态度,是不注重于形式的批评的,这是说对于初期的创作。所谓正确的批评必然的是从作品的力量方面,影响方面,意识方面——再说简明些吧,普罗列搭利亚文艺批评家在初期所注意的,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形式,是要从作品里面去观察‘社会意识的特殊的表现形式’。”⑱不论是在创作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都有一种突出内容、贬低艺术形式的倾向。在作家的观念中,文学的技巧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能否在文学之中展示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因素、让文学参与历史的进程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心态正如洪灵菲在《流亡》自序中所坦露的:“在描写的手段,叙述的技巧,修辞的功夫各方面批判起来,我自己承认,《流亡》这篇幼稚的产物,可说完全是失败的!但取材方面,和文章立场方面,总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和一种新的努力!”⑲与写作的技巧相比较,作者显然更看重这种“新的倾向”和“新的努力”。“左联”成立以后,似乎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比如说对于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方法的引进等,但实际上,每一次写作方法更新的背后都牵涉到作家的思想与世界观的改造问题,都不是单纯的文学审美问题。这些创作方法的引进与其说是为了解决文学作品的形式问题,倒不如说是更加指出了作家思想意识改造的必要性。对于《地泉》的“浪漫谛克”倾向的批判,表面上聚焦于作品的形式问题,实际上仍然是规范作家思想的一种方式,即肃清从革命文学以来一直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即使是序言的写作者所指出的克服“浪漫谛克”倾向的两个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写实主义和大众化,所要解决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也是作家的立场问题和思想改造问题。也就是说,左翼文艺批评从来没有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探讨文学的形式问题,即使在探讨文学形式时,也大都从时代背景与作家的阶级背景、政治立场着手,很少顾及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1932年的《地泉》批判,对其“浪漫谛克”的形式的否定也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目的是要解决文学家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即通过批判达到作家在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文学形式本身只是一个虚幻的聚焦点罢了。
这样看来,茅盾受到华汉的猛烈批判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写序的几个人中,始终将批判的重心放在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上的,只有茅盾。茅盾的被否定,固然有着他自己论述上的疏漏,比如他举蒋光慈作品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本身就有不恰当的地方。他只抓住蒋光慈作品的“脸谱主义”,而忽视了蒋光慈作品对于读者情感的强大冲击力,这就为华汉提供了反驳的可能。但这种论述上的疏漏和举例的不当并不是茅盾被攻击的主要原因,华汉最为不能认同的,是茅盾的观点背后的那种逻辑——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的过分关注。可以说,茅盾与其他诸人在关注点上存在着错位,也的确存在着如华汉所言的某些“原则上的分歧”。在对于艺术形式问题上,华汉要比茅盾走得远得多,他甚至已经抛弃了文学形式本身。他很希望把《地泉》批判的矛头引到作家的思想意识这一问题上来。早在1930年,他就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进程分析过“浪漫谛克”的成因以及克服的过程:“在这一运动(指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引者注)的初期,因为还未完全扫清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故反映在文艺运动的本身上来,于是便有革命的罗曼谛克和个人的感伤主义出现。然而,历史是在那里不断地流变,无产阶级的文艺家在实际斗争中渐渐地获得了无产阶级正确的阶级意识,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残余也就渐渐地被克服掉了。”⑳在华汉看来,“浪漫谛克”的形式问题说到底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于获得正确的无产阶级意识。因此,在对于自己创作经历的回忆中,他着力突出的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彷徨心境和社会的左倾氛围。他认为过去的文学批评“竟看轻了作品的内容,或竟抹杀了作品中的阶级的战斗任务而不加以严厉的检查,只片面的从作品的结构上,手法上,技巧上,即整个的形式上去着眼”㉑。针对茅盾从艺术形式角度提出的批评,他认为是“丝毫没有看见过去我们的作品中比什么还严重的在内容上的非无产阶级乃至反无产阶级的意识的活跃”㉒。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错位、批判者之间在关注点上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碰撞、对话、裂隙,批评与反批评,都是更为深远的也更有意味的话题。只有揭示出在虚幻的聚焦点——革命文学作品在形式上的“浪漫谛克”——之外的左翼文学批评的真正兴奋点,即文学批评的内容优先倾向与政治焦虑,才能抓住左翼文学批评的本质与内核。
注释:
①阳翰笙:《左翼文化阵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斗争》,见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6页。
②《国内外文坛消息》,《拓荒者》第3期10日。
③朱璟(茅盾):《关于“创作”》,《北斗》创刊号,1931年9月20日。
④华汉:《“地泉”重版自序》,《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31页。
⑤易嘉(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谛克》,《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3页。
⑥⑦郑伯奇:《地泉序》,《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9—11页。
⑧⑨⑩茅盾:《地泉读后感》,《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14页、第18页。
⑪⑫⑬⑭⑮⑯㉑㉒华汉:《“ 地泉 ”重版自序》,《地泉》,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第30页、第32—37页。
⑰华汉:《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
⑱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拓荒者》第1期(特大号),1930年1月10日。
⑲洪灵菲:《〈流亡〉自序》,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版。
⑳华汉:《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
The Conflict of Left-wing Literary Critic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Criticism of Underground Spring in 1932
ZhangJian
The criticism ofUnderground Springin 1932 contained many conflicts under the same image.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identity,knowledge,mentality and focus of the critics,there is a dia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faces which are full of criticism and anti-criticism.The preface written by Hua Han makes the difference under the same image appear.The difference,dislocation and fracture,reveals the deep logic of left-wing literary criticism,which demonstrates an obvious inclination of the emphasis on content rather than form and strong political anxiety.The attention on romantic form of revolutionary literary works,is just a fantastic focus.
Left-wing Literary Criticism;Underground Spring;Emphasis on Content;Political Anxiety
I2
A
1007-905X(2017)11-0093-06
2017-05-03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ZW046);201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科创新团队“20世纪文学转型与思想传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6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中国化视域中的左翼文学思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张剑,男,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编辑 张志强 张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