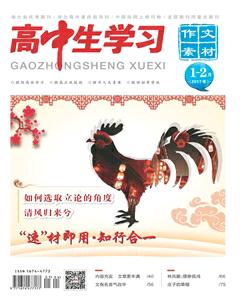“调和中西”的一代宗师
当林风眠从一个艺术运动的领袖回归到一个画家和教育家的时候,他的心态立即变得平和而冲融。应该说,在杭州艺专的十年,是林风眠一生中最优裕、最安逸的一段时间。
在这十年间,林风眠的艺术创作也收获颇丰。他开始亲手尝试“调和中西”的艺术设想,油画中融进中国元素,水墨中掺入西画构成。他还画出一批直接反映民间疾苦的大幅作品,如《人道》《民间》《痛苦》《斗争》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招致了一些非议和不满。
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把林风眠潜心艺术的梦想击碎了。1938年,教育当局下令,将杭州艺专与同样南下避难的北京艺专合并,成立抗战时期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这两所学校林风眠都担任过校长,然而,今非昔比,物是人非,多年来的矛盾纠结在一起,使两校合并成为一个摩擦与碰撞的爆发点。在经历了两次“倒林”风波之后,林风眠再也无法忍受这些烦人纠缠,他递交了辞呈,怅然地离开了国立艺专。
林风眠从国立艺专隐退后,跑到嘉陵江南岸的一个大佛殿附近租了一间旧泥房,离群索居,专事绘画。自重庆退隐之后,林风眠绘画题材主要转为风景、仕女、禽鸟、花卉、静物和舞台人物,对现实人世的描绘越来越少,对自然和虚幻人物情境的描绘日渐增多;作品的色调逐渐明朗,情绪转为平和;油画越来越少,水墨和彩墨成为主要形式;激越的呐喊和沉重的悲哀转换为宁静的遐思和丰富多彩的抒写。绘画艺术日益成为林风眠抒发和展现生命本体的手段,画家的情绪与大自然的生命日渐融合,两者共同编织着一个个真善美的梦境。
宣纸、毛笔、线条,这些中国画最重要的工具,标志着画家的文化执着;而色彩、造型、构成,却是显而易见的西方范式。林风眠在寻找一种新的绘画语言,来改造传统的中国画,抑或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画。“方纸布阵”,这本身就是自设的一个困局;不再留白,至少是不刻意留白,一举颠覆了中国传统美学里“计白当黑”的铁律;线条不再成为“笔墨”的载体,而纯化为造型的工具,这就从本质上动摇了线条在国画中的美学地位。林风眠在九十岁时曾有一段独特的“论线条”的谈话:“我是比较画中国的线条。”他说,“后来,我总是想法子把毛笔画得像铅笔一样的线条——用铅笔画线条画得很细,用毛笔来画就不一樣了。所以这东西练了很久,这种线条有点像唐代铁线描、游丝描,一条线下来,比较流利地,有点像西洋画稿子、速写,我是用毛笔来画的。”
在林风眠的作品中,黑色往往被当作一种色彩来运用,而不再被当作“墨分五色”来看待。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从外观上看确实不像传统中国画而更像西方画。但是,如果透过形式去分析一下作品的精神内涵,那种凝聚在尺幅中间的悲剧情怀,那种不必凭借题诗和书法就自然而然扑面而来的浓郁诗意,却使画面上的文化意蕴得到了升华,使之更为契合中国画作为“心画”和“诗画”的特性。
历史已经证明,林风眠在当代绘画史上开辟了一个迥异于任何人的新体系,他的中西融合的观点以及对诸如形式、材料等问题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绘画的创作面貌。如今,“方形布阵”的中国画早已司空见惯,而“风眠体”的后继者更是比肩接踵,绵延不绝,且名家辈出,风靡世界。
1991年8月12日,91岁的林风眠在香港溘然长逝。由此,中国现代美术史有了一个新的标识:在林风眠以后,中国绘画的整体格局已经与林风眠之前迥然不同了。
一生成就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一人开辟一条独特的美的历程。从早年弄潮于艺术运动的波峰浪谷,成为一位狂飙突进的先驱,到五十年面壁潜修,孤独求索,探寻出中西调和的绘画新径,直至秋霜红叶,实至名归,成为一代开宗立派的艺术宗师——林风眠,以自己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完成了一个现代艺术殉道者的使命,也使后人读到了一部凄婉而苦涩的人生传奇。
本栏目由李响的《孤鸿林风眠》和侯军的《林风眠:失驱·画陷·字师》综合编辑而成。
——早期北平艺专的国画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