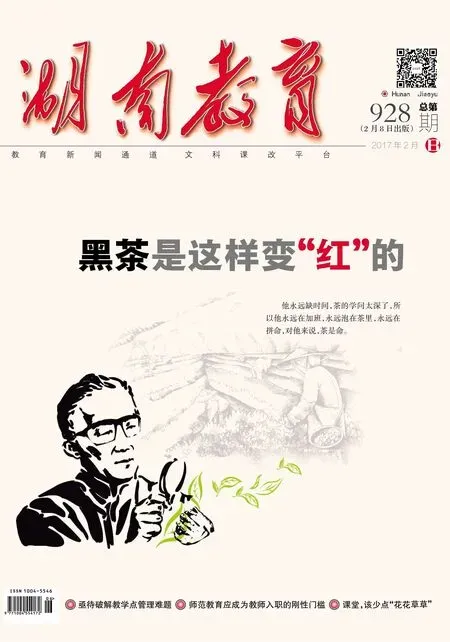大地上的语文
文︳
大地上的语文
文︳张宏祥

张宏祥,张家界人。曾用名,怡人,崆峒山狂人。当过农民,干过记者,写过文章,职业教肓。有《二公》《老码头》等文散见于报刊,发表作品近十万字。现就职于永定区解放小学,校刊《晨语》主编。
一
我的文学情结始于一场规模较大的运动。
是上个世纪的事,一本书稀里糊涂地就把我牵扯进去了,书的名字是《水浒传》①。估计是受批判的缘故,这本书出版了。封面是绿色,里面的字较小。
见到这本书,是一个偶然。我的同学姓龚,平时比较调皮,在老师眼里属于那种不听话、不受教的朽木,做不好作业,写的字与鸡爪子没有两样。也许,上天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想到的是缺陷,不是完美。大地有缺陷,就有高山与河流。生命有缺陷,就有生老病死。我家穷困,父亲是瞎子,母亲老实本分,在农村,属于乡民不待见的家庭。好歹,我在学校读书成绩好,填补了某些不足,增添了一丝优越。龚同学经不住老师的竹鞭,开始打起了歪主意,实行曲线救国。他想方设法讨好我,帮忙打扫卫生,像一个跟尾巴狗一样贴着我。看书,是我的爱好,于是一个霜冻的早晨,龚同学神秘地把我叫到学校的后山,掏出了一本很厚的书。那时学的字不是很多,有一个字认不得,另一个不知道是多音字,就当是“水许传”吧。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当时还不到八岁。
在夜晚的煤油灯下,一个孩子在那里埋头苦读,准确地说是在翻看“有字天书”。识字量太少,他只能囫囵吞枣。这半生不熟的阅读中,书本半古文半白话的语言让他惊诧而欲罢不能。搞不清究竟看懂了多少,但这本书却深深地扎入了他的生命里。很多年后,他在一篇小说中记叙了这样的情景,小孩一边翻着书,一边焦虑地思考,窗外的星星消隐了,太阳从后山爬到树梢,孩子的身影像一颗固执的钉子钉在门前的天塔中央。他不认识朱仝的仝,便把这个字读成工。三个不眠之夜,他算是把这本书翻了一遍。
二
读书的经历是苦涩的,为了看书,我穷尽办法,在大山上找可以换钱的药草。真正有属于自己的一本书大约是九岁那年。
一个好朋友告诉我,烂套鞋的胶可以换钱。母亲到队里出工去了,我就在家里找这些可以换钱的东西。家里贫穷积弱,实在找不到可换钱的东西,我很失望。徘徊了好久,看见婆婆家的门口放着几双烂了的套鞋,我想都没想,拿着就往街上跑,到生资公司换了一角二分钱。这是人生第一次有钱,特别狂喜,一路直奔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在十字街口,好在那时城市小,转了几圈就找到了。
书摆在柜子里面,用玻璃隔着,不像现在你可以先看内容提要,再确定购不购买。售书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不是很友善,不知是我在柜台前面站得太久让她有点怀疑,还是因为当时的我没有柜台高,看样子不会买书的缘故。
“你买不买书,不买就走。”在我看了约半个小时后,漂亮女孩子下了最后通牒。我就说,钱在这,你看能买几本?她数了数钱,三本。
我揣着三本书像揣着宝物一样,急匆匆往家里赶,到凉亭的时候,实在熬不住想先看一本。《035号图纸》,这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本书,在凉亭,很短的时间读完了。但意犹未尽,还想继续看一本,但天已经黑下,只好回家。还没等我进屋,迎接我的是母亲的一顿棍棒。在打断第三根棍子时,我已经哭不出声音了。母亲的确气急了,一个小孩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上街,胆也太大了;偷卖套鞋更是十恶不赦,小偷针,大偷金,农村这些朴素的道理不容辩驳。我跪了一夜,饿了一夜。
十三岁,我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好老师。他是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没有老婆,孤身一人,有几抽屉书。他愿意借书给我看,记得我看了《红旗谱》《艳阳天》,还有《铁道游击队》等。这个老右派语文功底深厚,填词写诗、小说散文都来得几手。我认真听他的课,课后请教他。他也夸赞我的作文好,并有一次对我说,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是什么?我是不理解的。但我觉得书上的人物的确让人敬佩,故事情节的精彩也让人浮想联翩。就在这一年,他带我见了当时本地区的一位作家,并把我写的文章交给了他。
三

寂寞生成文字。
一个人在贫穷的边缘苦苦挣扎,深知生活的艰难,只好疲于奔命。白天,用瘦弱的身躯丈量土地;夜晚空灵寂静,属于穷人,也属于孩子。孩子在数星星的空隙,乱七八糟的念头如蚯蚓在地底下,一寸寸挪移。蚯蚓的天空是黑暗的,孩子的天空或许有些光亮。书,就成了这一束微弱的光亮,在乡村的夜空驻足,或许它知道有一个遥远的去处,不再盛放一个安定的灵魂。乡政府办农校,没有老师,就给了我教乡土文学的机会。这一年,十六岁,嘴巴上刚刚长毛。
农校的学生大多是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的。这里培养的是未来的乡镇企业职工,还有乡镇干部。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做而十分乐意的事情,这是上苍的恩赐,是祖宗修福积德所致。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框定的时候,他的追求不再局限于给学生传授一点知识。知识也许可裹腹,能养家,但能力才是可以点亮前行路上的那盏灯火,如若开花亦会惊艳四座。面对这些比我大的学生,我第一次给他们谈了沈从文,谈了湘西。沈从文于茶峒走出湘西的大山,他的文字属于大山,属于河流,更属于岁月沉积的文化,一种精神图腾。他们认真听着,记着笔记。记不清楚究竟讲了多长的时间,或许是一个下午。
和学员们一起学习让我开启了一扇窗户,也让我的心灵日渐丰盈润泽。澧水,是我与学员们虔诚写作的源泉,在这里,流淌的是文化的乳汁,不再是一条普通河流。有个女学生姓陈,立志要做我的小跟班,在文学的路上看看红色的月亮。我告诉她,写作的先决条件是读书。读书可以走向远方,至少可以看见生命中的风景。这个时期,恰好迎来了文学的复苏,刘心武、韩少功、谭谈等各领风骚。我把当时所知道的作品按流派分类,用还不成熟的观点进行分析,同时告诉同学们,语言在民间。星期日,去民间采风成了我们一个不变的主题。听老农讲故事,到田头看农忙,于车间和工人交谈。有了一些散乱的作品后,便和同学们动手,编成小册子,美其名曰《澧水文学》。《澧水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多了一份期待,一种执念。同学们很爱自己的作品,三十年后,与学生相遇,谈到的依旧是《澧水文学》,还有陈姓女同学,她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
四
进入小学教语文,是两年后的事。农校是时代的衍生品,时代结束,其使命便结束了。
我到了一个叫代家湾的地方,这儿的鸟不生蛋,阳光呆上半天就猫到一旁打盹去了。四十多个孩子,三个班,三年时间,不离不弃。
三个班分别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第一堂课,给我的感觉不是失望,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四十四人中,三十五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但长芭茅的地方一定能长出庄稼。我开始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那时的家长很是理解老师,他们远远地待在一角,等着孩子。下课了,朴素的农人除了一声“多谢”找不出更多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情感。但这两个字里饱含了他们最朴实的情感,这是对知识的敬畏,对老师工作的肯定,对教育的顶礼膜拜。
学生有了简单的文字基础,关于文学的思绪又像蛇一样缠绕着我的心灵,让我窒息得吐不出一口气。如果不教会学生作文,学生不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老师是失职的。一种惶恐包裹着心智,终不能化去。我便在这惶恐的威逼下,不断突围。大地即语文,让学生融入自然,有可描摹的素材,应该会有新的东西长出来吧。春天,一个叫薄刀岭的地方,开放着一种叫映山红的花,艳满山岭。那时候的课没有条条框框,相对自由、任性,说走就走,无须打报告,连校长都不需告诉。孩子们上了薄刀岭,钻入花海,用喜欢的方式观察着花。观察的方式去之前有了一番交代,学生知道了基本的观察顺序。其实这种东西在现场指导最为实在,体验才是真正的生活,生活才是真正的作品。花鸟草虫的美源于观察后的思考,人的文化气息是大自然熏陶出来的。孩子们每天写日记,这是必修课。日记写多了,语言丰富了,开始寻找技巧。老师不要把所谓的经验讲给他们听,给学生提些建议倒是颇有实在价值。
仿写是小学作文的一条门径,让学生有一个参照物,老师不妨给他们介绍基本可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张天翼的、冰心的、叶圣陶的,学生从书本里找到可能属于自己的语言,然后就大功告成,先生就清闲了。
今后的岁月里,我希冀以何种方式教语文呢?我想,我肯定没有大家们提出的一二三条,若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的话,也是想就人生的经历做些说明。教学是没有方法的,无论你学识如何,仍需铭记:大地即语文,生活即作品。好的语文老师在思考着自身的文化体系,终身学习是最好的法宝。
注释
①1975年,全国掀起“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随后出版了《水浒传》的各类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