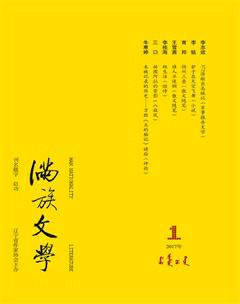未被记录的历史
牛寒婷
引 子
那一次与历史的“亲密”接触,让我记忆犹新。2011年10月,正值南方气候舒爽的季节,我在长沙与几个朋友一道去参观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曾震惊世界,我一直想一睹真容,仿佛只要被这个两千多岁的“长寿老人”检阅一下,我就拥有了那段历史。我至今记得,当我走进展厅,心情紧张地望向下方玻璃棺内那个叫辛追的女人时,我所看到的可怖画面在一瞬间给我带来的震撼:一股强烈的嫌恶感涌遍全身……我知道,这虽然是几近本能的生理反应,但是,想象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才是产生它的真正原因。
我没法即刻摆脱在展厅内感受到的恶心恐惧和失望沮丧兼而有之的复杂体验,我对付它的方式,是假装眼前这一幕未曾上演。我重新找回了去博物馆之前心中那个关于“历史”的世界,在那里,我拥有对辛追的美好想象,怀抱对往昔的浪漫憧憬——辛追夫人穿着薄如蝉翼的绢丝华服,漫步在花园中,作为轪侯利苍的爱妾,她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总会不时地长吁短叹;她尽兴地吃着自己喜欢的甜瓜,嘴馋得像个孩子,完全不顾过食生冷可能会要了她的命;虽年近五十,身体却似乎并未留下过多的岁月痕迹,她明艳鲜亮,如同少女……我的想象穿行于时光隧道,并执拗地在其中某处掘开一道口子,栩栩如生、充满细节的历史,一下子就从那里倾泻了出来。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历史的真实并不是皮肤僵硬、脸部扭曲、吐着舌头的辛追及其他出土物,不是看起来严丝合缝、没有破绽的史料文献,甚至不是“真实”的史实本身——已消逝在时间长河中的林林总总及是非曲直,真切鲜活地存在于一个人的畅想之中。
也许,正因为对历史做如此“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理解,我才与万胜结缘。他的长篇历史作品《王的胎记》,让分别属于我的和他的历史观,不期然地相逢了、投契了、暗合了。在《王的胎记》中,叙述人化身为“游客”,一路游走、探访努尔哈赤一生所攻打的二十一座城池,以此追怀努尔哈赤的戎马生涯。于是,“城”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线索。对努尔哈赤来说,攻城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他被命运推动着,几乎是机械地下意识地,攻破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直到生命终结。可以说,他的人生轨迹是由城串联起来的。另一条与“城”并行的线索,是游客的寻城之旅。摆脱了俗世喧嚣的他,孤独而执着地行走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他以“城”为触手,去追寻、亲近和想象已然消逝了的历史时空。如今,努尔哈赤攻破的这些城,大部分已烟尘般消散殆尽,偶尔能探访到一些断壁残垣那就算幸运。万胜附体叙述人“游客”所进行的行走,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寻访之旅,不如说是对“无处可寻”的历史的想象和杜撰之旅——而这,正合我胃口。
摇摆的文体
把《王的胎记》称作“长篇历史作品”,是权宜之计。在此书的文体选择与写作方法上,万胜大概情不自禁地借用了他笔下努尔哈赤所惯用的攻城伎俩——声东击西,这实在有点像恶作剧。在阅读过程中,它给我的感觉,有时是一部文化大散文(滥觞于余秋雨《文化苦旅》的一种流行文体),有时是一本历史小说,有时则是一本游记式随笔。书中既有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介绍,也有以小说笔法呈现的故事与人物,既有对实地考察的古城遗址风貌的描述,也有在穿越历史与现实时对生命感悟和脉脉情思的抒写。具体到书中的每一章节,写作上没有一定之规,无规律可循,读者只能跟着作者的思绪游走。也许,正是因为文体面貌的模糊不清,读者才能避开明确的文体所可能带来的阅读经验上的约束,更纯粹地投入到具体的文本中去直接地感受作品。如此,摇摆的文体,成为一种写作策略,一种规避非此即彼的文体选择和约定俗成的文本框架的写作方法,写作也因而趋向了一种可能的自由。就像阅读中,虽然我始终对万胜的文体选择有保留、有质疑、有不满,但我还是愿意尊重他的叙述方式,我对自己的要求只是:只管读好了,管它是小说、散文还是随笔。
写作历史题材作品,总要遵循尊重历史的原则,这样,就涉及到了如何面对和怎样处理大量史料文献的问题,当然,那些戏说和演绎历史的流行作品另当别论。《王的胎记》的前几章,详尽叙述了努尔哈赤的家族背景、女真族各部落之间如何互相制衡,以及关外女真等少数民族与明朝的复杂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史料叙述繁乱复杂,让作者颇为困扰,前几章的写作因而紧锣密鼓,匆促奔忙,读来难免枯燥乏味。直到第四章,杂乱的历史背景交代终于初见成效,作者好似松了口气,叙述才开始变得从容自如,笔触也得以深入人物的内心,那些在幽暗的历史中飘浮着的鲜活灵动的人物也渐渐从书中走了出来。直至第五章“扈伦四城”,历史真实与小说虚构、牢不可破或不堪一击的城与代表着四座城的不同气质的人物、战争的惨烈与悲悯的情怀、伤逝的历史与流淌的诗情……方更加紧密和恰当地交融在一起,读来惊心动魄,气势恢宏。这一全书篇幅最长的章节,成为女真族各部落自相残杀历史的一个缩影。
第六章是一个转折点。统一了建州女真并进一步巩固了政权的努尔哈赤,终于对大明朝宣战。接下来,他每攻下一城,距离他的子孙最终建立清王朝就又近了一步。作者彻底摆脱了与史料周旋的重负,写作变得轻松随意。他忽而把战场的残酷厮杀和惨烈情状写得震撼人心,忽而钻到小人物的内心里去呈现个体在极端状况下的生命选择,忽而在城郭和战争遗址处的繁盛草木中体恤生命、告慰亡灵,忽而在天寒地冻的游走和忍耐中反思战争、审视文明……气势磅礴、硝烟弥漫的历史画卷已然展现在面前,想象、虚构、杜撰之画笔尽可以上挂下连肆意挥洒。于是,那些被历史遗忘的人物,那些未被记錄的事件与细节,那些泯灭消散的情仇恩怨,那些遥远而又切近的场景与情境……一一被展示与呈现了出来。也便是在这样的展示与呈现中,历史的厚重,小说的滋味,散文的意境,得以有机地纵横交错并交相辉映。
消失的胎记
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了,阿玛在他身上发现了二十一块大大小小的胎记。野萨满也说不清楚这些胎记寓意着什么。在努尔哈赤的一生中,那二十一块胎记逐渐消失,直至公元1626年他离开人世,身上只剩下最后一块胎记。
《王的胎记》开篇的这段“引子”,写得有趣,值得玩味。
正如书中所写,努尔哈赤身上的胎记,寓意着他一生所攻打的二十一座城。他每攻破一座城,身上的胎记就消失一块。而在最终要了他命的宁远城之战中,由于败给袁崇焕,没拿下宁远城,所以他死时,身上还留有一块胎记。以“城”志“人”,以胎记喻成败,这颇有创意。写城,其实就意味着写战争,写努尔哈赤后知后觉的以大明朝为最终目标发动的一系列攻伐。可万胜却说,他不是要写一部帝王创业史,也无意为努尔哈赤再添新传。作为这些战争的发起者与核心人物,在历史上、在文献里、在传说中,努尔哈赤都披挂了太多被神化了的帝王光环和英雄铠甲,至于他的本真面目,却早已因弥漫的硝烟战火和纷飞的刀剑斧钺的笼罩修改,因后世历史口水的期待与诉说以及模式化和脸谱化的淹没覆盖,而模糊不清,而难以辨认。“我要把努尔哈赤拉回到泥土里”,万胜说,“他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被逼着走上了命运之路。”
不知餍足地消费历史,是中国人的一大癖好。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开始,当代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以一种细节的方式,走入了有着“恋史癖”的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尽管黄仁宇所说的那句“叙事不妨细致”,是针对像《万历十五年》那类严谨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言的,但从此,诉求亲和、讲究叙事的写作策略,还是引发了大众文化领域历史题材写作的汹涌潮流。余秋雨红极一时的文化大散文,当年明月横空出“网”的《明朝那些事儿》,二月河由小说而电视剧的“帝王系列”等等,无论是官史重述,还是野史戏说,都以让历史回到大众为噱头,以大众亲近历史为说辞。以至《琅琊榜》、《甄嬛传》、《芈月传》等国产历史剧的热播,能迅速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尽管,它们的历史依据极度有限,可凭借其漂亮的叙事、精彩的情节、上乘的制作,照样营造出了逼真的历史感,从而征服了广大观众。
与这些流行作品相同的是,《王的胎记》中的努尔哈赤,被诉求于亲近历史与个人想象的写作重新塑造,他身上作为普通人平凡的一面,得到了尽情展示。在第十四章“广宁城”中,努尔哈赤虽已接连攻下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等城,大明朝的关外情势岌岌可危,但接连的战事、不断扩大的地盘和日益增多的人口,让粮食短缺和国家管理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努尔哈赤觉得太累了,他给自己总结了一下,青年时打仗是为了仇恨,中年时打仗是为了理想,老年时打仗是为了生存。”作者把高高在上的努尔哈赤,从帝王的神坛上拽了下来,把他即将走到人生尽头时所感受到的无奈和悲凉,把他心中的痛苦与酸楚,把他已然老迈的身心,真实地展现了出来。
与其他历史作品相比,《王的胎记》自有它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努尔哈赤身上所特有的“文学的胎记”。把城与胎记作比,是一种暗喻。从表面上看,实实在在的城与杜撰的胎记之间毫无关联,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戏拟,才把它们连在了一起。但其实,胎记的消失,又意味着城的毁灭——从有到无的消亡,是它们无法逃离的共同命运。努尔哈赤每攻破一座城,或因愤恨,或因傲世,或因虚荣,都会将其焚毁,因此二十座城在经历了或惨烈或温和的战事后,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唯一算得上例外的是铁岭城。铁岭城之文士李如梃,想用自己的方式感化努尔哈赤,让他停止杀戮。在龙首山水朝寺的佛殿内,在香烟袅袅的佛堂前,李如梃与努尔哈赤两相对峙,一个是志在必得、野心昭昭,一个是祈求佛灵、心静如水。虽然李如梃的以诚相劝,如他预料的一样,最后以失败告终,他只能决绝地选择自杀;但转赴他地之前的努尔哈赤,却并没像以往那样下令焚城。遗憾的是,驻军离开时忘了熄灭烛火,这才让铁岭城终究陷身火海。这看似只是无心之过,可阴差阳错间,铁岭城却如同俄狄浦斯,未能逃过自己的宿命。
尊贵的王的身上,那渐次消失的二十个胎记是战争的胎记,它们喻示了二十座城的焚毁,可在二十座城消失的背后,又有多少有名的和无名的生命的夭折消亡呢?是无数亡灵,成就了王的至尊之位。虽然《王的胎记》写的是努尔哈赤的戎马生涯,写他的攻城与功成,写他以历史正义为借口的杀戮与荼毒,但在那文字中间,反战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吁求又贯穿了全书的始终。开篇那段惹人玩味的“引子”,其实绵里藏针地暗含着无数玄机,它的有趣和好玩,也隐藏着思考的沉重与生命的肃然。
回想阅读《王的胎记》的整个过程,扮演着叙述人角色的游客,在喋喋诉说的同时,似乎总在发出一声又一声长长的叹息。我想,那一定是他跟随历史的脚步时所情难自禁的有感而发吧,它们关乎一座座城曾经的繁盛与最终的消失,关乎人对城无限的眷恋与无情的践踏,关乎残酷的战争与殒灭的肉身,关乎理想、价值与人性的正邪美丑,关乎历史的选择与个人的信仰,关乎生存的尊严及其苟且……它们仿佛是一种在跋涉了久远的历史和穿越了古今的岁月后,却依然找不到答案的无处排遣的情愫,带着感伤与无奈,透着绝望与苦楚,它们终于郁结成一股股浓浓的诗情,从历史的深处流淌出来,让这历史,又无端地翻腾起文学的硝烟。
未被记录的历史
往返在枯燥的史料查阅和辛苦的舟车劳顿之间的“游客”,无论沉浸在故纸堆中还是做实地的探访考查,都渴望无限地接近历史。他喜欢“无限”一词的暗示,这让他感觉,自己正站在一个即刻便能抵达目标却又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中间点上,而仿佛正是这个为无限靠近与靠近不了居间分野的中间点,赋予了他杜撰的权力。他始终明白:“城是死物,守城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因而,他便无法控制自己不对寻访到的属于“城”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施行一种他驾轻就熟的魔法,动情地使它们变成了属于“人”的一颦一笑、一喜一悲。渐渐地,那些被历史所遗忘的生命,那些像嚼过的口香糖一样被弃置在记忆之外的情感,终于原汁原味地浮现了出来。
为花草而战的武尔古岱,是《王的胎记》中最打动我的一个人物。努爾哈赤攻打过那么多城,有数不尽的手下败将,可他却怎么也无法攻破武尔古岱所固守的哈达旧王城,无法击垮这个弱不禁风、身上一股子花粉味的男人。老天像是在与他开一个巨大的玩笑,这个不男不女、只会养花的懦夫,怎么就能让英勇的建州大军连连溃败、死伤无数呢?这大概是努尔哈赤一辈子也想不明白的事。对他来说,武尔古岱是个异类,是“天外来客”,他根本无法想象也无从体会,武尔古岱在面对满城无数争奇斗艳的花草时,面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幻境般的大花园时,内心所翻飞的种种兴奋和喜悦、快慰与满足。
武尔古岱的人生其实别无选择。不想称王、与世无争、只求伴花度日的他,为花草而战是他的信念所在,甚至那信念已升华为信仰。正是这种努尔哈赤所无法理解的信仰,使柔弱的花草芳香氤氲出了坚不可摧的抵抗的力量,让战无不胜的神话属于了哈达旧王城。“不要比谁的箭更尖锐,谁的刀更锋利,除了那一丝绕指之柔,一切都会消殒无迹。”在战争中逡巡的“游客”,透过岁月的影子,洞察到了历史和生命的真意。虽然,无论是历史还是花草,都阻挡不了王的脚步,被劝降的武尔古岱的命运只能如他的花草那般枯萎殆尽,但他的心魂,却自始至终都游荡在王城内外,不绝如缕地诉说着他无尽的眷恋。
沉醉在笔下人物百转千回、情难自已的生命境况中,“游客”好像多活了几世,那些由他赋予了生命的鲜活人物:为花草而战的武尔古岱、对城迷恋至深的拜音达理、为复仇而学会隐忍的布占泰、苟且一生却泰然赴死的尼堪外兰、美好得如同传说但却抑郁而终的东哥、内心坦荡的舒尔哈齐、狂妄自大的褚英、陷于爱情漩涡中却被命运不断推搡的阿巴亥、举手投足间典雅雍容的冷玉香……一个个从他手中飞离了出去,再落户安家于历史的角落。可他对他们,太恋恋难舍和无法忘怀啦,于是他利用了自己的叙述人特权,奋力冲破阻挠他倾泻情感抒发意绪的各种界限,在现实与历史间,在人与人或者人与物或者物与物间,在一切与一切间,自由地往来,尽兴地交流。
这样,那些遍布“游客”足迹和畅想的地方,便都成了心灵与心灵间沟通、对答和论辩的所在。沙济城与古勒城的彼此凝视和深入交谈,一支箭镞与一棵石榴树之间的争论,努尔哈赤对呼兰哈达山的问询,“游客”与叶赫城的促膝而谈,小清河与老树的彼此相依和耳语,功德牌坊与孙德功的对峙,明抚顺城与清抚顺城的隔空交流……这些处处禅意、语透机锋的对话,追问着生命的本质和个体的价值,蕴含着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与困惑,裹藏着对战争和文明的质疑与诘问,构成了“游客”寻访历史的另外一重精神风景线。在最后一章“宁远城”中,威名赫赫、荣耀一生的努尔哈赤,被命运的炮弹击中,在凝固了的时空中,他与击败他的袁崇焕“坦诚相见”。轻易就来到眼前的死亡,是一种错谬的偶然还是宿命的必然?即便如努尔哈赤般辉煌绚烂的人生,也终将消融泯灭在幽深的岁月长河里,就像对历史真实的无可拷问和追寻不得——真正可触可感可得的,唯有此在的生命与情怀,以及对思古之幽情的娓娓道来。
尾 声
好多年前,我很偶然地去了趟辽阳,在辽阳的街道上,远远地望见了浑圆的白塔。白塔应该算是挺古老了,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当时因为行程的缘故,我没能到塔下一游,可回家以后,对匆促间只是遥遥一望的苍老白塔我却无法忘怀。白塔属于砖塔,砖塔那特有的古朴、厚重和沧桑之感,仿佛一下子就能把人带入久远的历史,这大概是我向往它的原因。我常常想,若是站在塔下,那种不知此身何在的迷惑和畅想历史的快乐,肯定会愈加的强烈深刻。
就在上个月,为弥补心中的遗憾,我几乎算是专程地又去辽阳看了白塔。如今,白塔周围已经修建了漂亮的白塔公园,并和紧邻的广佑寺,组成了颇有规模、豪华气派的辽阳一景,从远处一望便可认出。我去的那天,游人不多,被一种特殊的幽静氛围所笼罩着的白塔和广佑寺,为辽阳这座小城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沿着广佑寺的外墙漫步,拐到與白塔相对的另一侧时,狭长的护城河突然映入眼帘,尽管河水几近干涸,但这个新发现,仍然让我兴奋了半天。
直到有朋友不解地问我,怎么突然对白塔如此钟情,我才觉出事情的“蹊跷”,也才记起,此番去辽阳前,我已开始阅读《王的胎记》。在这之前,我没意识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但如今想来,我的辽阳之行,恐怕跟书中“游客”寻访古迹的行为脱不了干系。尽管,当时,我还远未读到列为全书倒数第三章的“辽阳城”一章,自然也就无从想象,“游客”驻足护城河边吊慰无数亡灵、倾听亡灵呓语的一幕。
俯看护城河道时,虽然无法像“游客”那般对历史“有知”,但我的“无知”,也并非就空洞无物——相反,它是一种混沌复杂、捉摸不定的丰盈体验。在白塔下,在护城河岸,当那种不具名的空旷之感和几近神秘的静谧气氛将我裹挟时,我不由自主地心旌摇荡。后来我时常回味这种体验,想摸清它的来龙去脉,尽管我每每一无所得,但我的直觉又告诉我,它是某种更为深沉厚重的东西的投影。它有点像一个仪式,能激发人朴实无华的情感,能让人拥有面对信仰时的虔诚,能使人对无知的和不可控的事物心存敬畏;它特别地空灵广袤,能超越历史,超越生命的降生和殒灭;它有时会让人感觉到面对浩瀚大海和无边宇宙时的卑微,有时又会让人体验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无尽孤独与旷世悲凉;它还……我忽然意识到,我在《王的胎记》内外对于“辽阳城”的两度游历,其实是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共同赐予我的小小恩典,就像神一般的努尔哈赤身上,那终将消逝但毕竟曾经标志性地存在过的一枚枚胎记。我渐渐明白了,作为我的精神胎记,努尔哈赤也好,辽阳城也好,历史也好小说也好这篇文章也好,它们都是我无以替代的宿命,它们将于何时弃我而去我不得而知,但对于我的完成,它们却是不可或缺的滋养与塑造。
原来,除了王,凡夫俗子也有胎记,即使历史不屑于记录。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