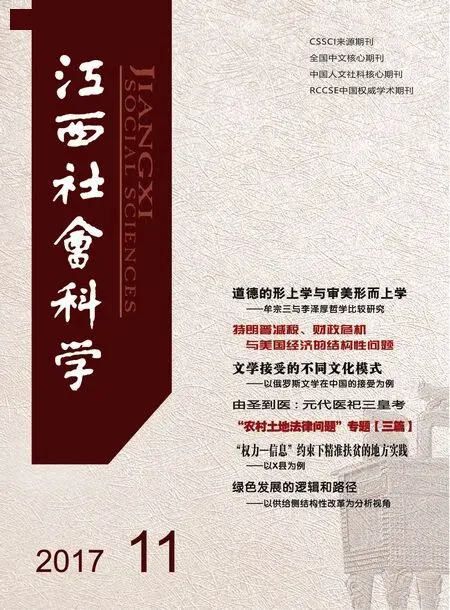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
——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汪介之
文学接受的不同文化模式
——以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汪介之
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和各语种文学之间的交流史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同一文学的接受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这一现象,在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纵观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史,不难看出这种接受主要显示为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三种不同的思路与取向。系统梳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深入考察这三种模式,对于我们总结接受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学接受;文化模式;俄罗斯文学
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史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同一文学的接受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模式。中国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中,这一点体现得特别明显。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来看,这种接受主要显示为三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三种不同的思路与取向。其一为新与旧、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等的二元对立模式;其二为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模式,但其内核仍然是“政治正确与否”的二元对立模式,与前一模式的区别仅仅在于“政治”价值取向的置换;其三为“求实—科学化”模式,它所遵循、实践与追求的是彻底摈弃从政治视角检视文学的思维定势,从活生生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文本自身出发,从文学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位的视角评价文学。系统梳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深入考察这三种模式,对于我们总结中国学界接受外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源于“两种文化观”的二元对立模式
中国文学接受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模式,其一为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盛行的新与旧、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等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接受模式,源于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入文化和文学评价的范畴,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中都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异质文化的“两种文化观”。按照这一文化和文学观,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可以被列入“苏联文学”的那一部分,曾经被描述成最进步、最健康、最有战斗精神、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苏联文学所遵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说成是最先进的艺术方法,并代表着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与此相对应,凡是不能被列入“苏联文学”的那一部分文学,则被认为是落后的、反动的、过时的、不健康的文学,其命运自然是反复遭遇批判,不入正史,以至渐渐被读者遗忘。具体而言,这后一部分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一直处于多种权威性文学史著作的论述范围之外,只是偶尔被作为反面例证提及。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明显地影响了我国学界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学者和作家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相关论述中,由于上述划分而导致的二元对立的接受模式,就已初现端倪。
1934年,前苏联领导人之一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说苏联文学是“最有思想、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文学”,“除去苏联文学之外,没有而且从来也未曾有一种文学”能够像苏联文学一样,为反对一切剥削制度而斗争,以工人农民“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作为自己作品选题的基础”。与苏联文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文学,则“无论题材和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是普遍地在堕落着”。日丹诺夫认为:“沉湎于神秘主义和僧侣主义,迷醉于色情文学和春宫画片——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颓废和腐朽的特征。资产阶级文学,把自己的笔出卖给了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文学,它的‘著名人物’现在是盗贼、侦探、娼妓和流氓了。”[1](P23-24)日丹诺夫对于苏联文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评判,成为把全部文学划分为泾渭分明、互不两立甚至你死我活的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学板块的标本,更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苏联文学的接受。1946年,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对这两家期刊的无情抨击,对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科的恶毒谩骂,以及1948年他对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米亚斯科夫斯基、哈恰图良等“音乐中形式主义倾向的主要领导人物”的点名批判,不仅提供了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学艺术的恶劣先例,还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接受中的二元对立模式。随着上述观点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50、60年代在外国文学的接受中,出现了严重的“一边倒”局面,全部艺术和文化领域,概莫能外,直到“反修”论战开始后出现更加极左化的格局。
从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学和文化接受模式,已经被中国学界逐渐抛弃。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化和文学(包括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摄取范围得到大大的扩展。但是,上述接受模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惰性尚未绝迹。因此,外来文化和文学接受领域内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就是要认清这种接受模式的根本弊端和不良后果,使我们的对外文学和文化交流走上更为科学的、健全的轨道。
二、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模式
中国文学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另一种接受模式,是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模式。这种模式形成的起点,是对极左文学思潮、极左文学政策的一种反拨。这一出发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极左政治的激烈否定情绪,投射到文学上来,便是对极左文艺路线的大力反驳。从对“阴谋文艺”的批判,对“三突出”的原则、“高大全”的形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声讨,逐渐涉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包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学为政治服务、写“重大题材”、塑造“正面典型”的怀疑与否定。这一切必然联系到对苏联文学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与此同时,中国当代作家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开始注意吸收包括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劳伦斯、伍尔夫、乔伊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在内的各国作家的艺术经验,建构起中国文学的崭新格局。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则渐渐淡出中国读者的接受视野。因此,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中俄文学关系降温,其实是抵制以往极左文学思潮的一种表征,也是对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流行的极左文学政策、对“独尊俄苏”路线的一种惩罚。
然而,这种合理性仅仅存在于旧有的接受模式逐渐被放弃、新的接受模式酝酿形成的开端期,再向前跨进一步,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误区。全部俄苏文学开始被一些评论者说成是始终为官方政治服务的样板,毫无艺术性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典范,“假大空”的集中展示,整个就是一批俄式或苏式的“革命样板戏”。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苏联文学、俄罗斯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似乎都是内涵和外延相同的概念。
在关于20世纪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评价中,这种“彻底解构、全面颠覆”模式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长期以来,这位作家被尊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其作品被认为是运用文学为革命服务的最佳典范。这种评价本来是苏联官方评论所设置的一种“权威话语”,并不符合高尔基的实际成就和本来面貌。因此,对高尔基和他的创作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重新评价,应当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某些评论者不是通过具体的作品文本解读对作为作家的高尔基做出令人信服的重新评价,也不是依据确凿的史实对他的思想和社会活动给予郑重的评判,而是以“政治鞭尸”式的语言,对这位作家进行全面抨击。《倒转“红轮”》(2012)一书的第二章“破解‘高尔基之谜’”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此文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无中生有和任意发挥。著者采用移花接木、捕风捉影等手法,把“流氓”、“看家犬”、“人格堕落”等一大堆污言秽语扣到高尔基头上,认定作家从1928年回国时起就“自投罗网,甘心地成为了‘斯大林的玩物’”[2](P103),成了“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个人崇拜的奠基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没有人性的御用作家”[2](P109)。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指责、抨击和谩骂,都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文学和社会史实。①值得注意的是,《倒转“红轮”》中的“破解‘高尔基之谜’”所习惯使用的抨击性语言,大都来自著者的基本词汇所形成的“文革”时代。
“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接受模式,和前述基于“两种文化观”的二元对立模式,尽管观点和结论不同,思维方式却显露出惊人的一致性。尽管这两种接受模式的观点往往是全面对立的,但是其思维方式却颇为相似,即双方事实上都把“政治正确与否”作为评价作家和文学的主要依据和标尺,把所有文学和文化现象都放到政治上的“左”和“右”这个天平上去检测。因此,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模式,但其内核仍然是“政治正确与否”的二元对立模式,与前一模式的区别仅仅在于“政治”价值取向的置换。只要国人不从根本上抛弃长期以来所习惯的非白即黑、河东河西的思维定势,“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接受模式就仍然会被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运用。
三、“求实—科学化”模式
在上述两种接受模式之外,中国学界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理解、接受和阐释,还存在第三种模式,即“求实—科学化”模式。它所遵循、实践与追求的,是彻底摈弃从政治视角检视文学的思维定势,从活生生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文本自身出发,从文学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品位的视角评价文学。
具体而言,这部分学者的努力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致力于呈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原貌和全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原本面貌、完整面貌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实,无论是奉行源于“两种文化观”的二元对立模式,还是热衷于彻底解构、全面颠覆的模式的人们,对俄罗斯文学特别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几乎完全不知晓绵延近30年的白银时代文学(1890—1917),从20世纪20年代起先后兴起的俄罗斯域外文学的三次浪潮,以及苏联时期受批判、遭查禁、被搁置的本土作家的作品。“白银时代”被杰出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称为俄罗斯的“文艺复兴”时代,“一个非凡的、具有创造天赋的时代”,“它为最有文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打开了新世界,为精神文化的创造解放了灵魂”。[3](P213-234)别尔嘉耶夫本人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西方学界称为“20世纪的黑格尔”。俄罗斯域外文学中先后涌现了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本土文学中则出现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什塔姆、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一些闪光的名字。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以罗赞诺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为代表的一代宗教文化批评家,对俄罗斯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象征主义理论家维·伊凡诺夫在20世纪初就开始的关于希腊酒神崇拜、民间狂欢活动的研究,使之成为巴赫金诗学思想的直接先驱;以罗曼·雅各布森、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则因其若干代表人物向西方的转移,带动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仅就文学批评这一领域而言,俄罗斯域外文学第一浪潮中就有三类学者和作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其一是专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或文学史家,如艾亨瓦尔德、德·米尔斯基、康·莫丘里斯基、格·阿达莫维奇、格列勃·司徒卢威、马克·斯洛尼姆等。他们一般具有鲜明的现代观念和为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现代文学史的意识,密切注视俄罗斯文学进入20世纪之后的复杂动向和新出现的问题,因此提供了关于俄罗斯现代文学的一批系统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把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史,致力于勾画出本民族文学的演变轨迹。第二类是第一代流亡作家和诗人们涉及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如伊万·布宁、弗·霍达谢维奇、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等。他们或对19世纪经典作家作品做出新的阐释,或为同时代人绘出文学肖像,或沉思某些根本的诗学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域外文学第一浪潮的几乎所有主要代表作家和诗人,均留下了各自的文学批评遗产。还有一类是论及文学现象与问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化史家等,这类学者中除了前文已提到的别尔嘉耶夫之外,还包括费·斯捷蓬、谢·弗兰克、伊万·伊里因等。他们当中有的在自己的思想史、文化史著作或宗教、哲学论著中评说文学,有的则直接发表作家作品专论,两者均以理论深度与视野的开阔见长。俄罗斯域外文学批评的成就和建树,是遵循“求实—科学化”路线的学者们致力于向汉语读者呈现并予以阐释的重要文学史现象。
其次,科学地区分相关基本概念,认清其内涵和外延。“彻底解构、全面颠覆”接受模式的信奉者们,对俄苏文论也同样只有肤浅的了解。由于20世纪30、40年代苏联的一些理论家们,在极左政治规范所允许的框架内,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断章取义地抽取了某些自以为对他们有用的内容,把臭名昭著的“庸俗社会学”作为其理论指导,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就使得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理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也导致一些人把俄苏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和极左文学理论等量齐观,也把现实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量齐观。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欧洲是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为源头的,中经文艺复兴时代以后诸多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的阐发,特别是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的深刻论述,及至泰纳、勃兰兑斯等已形成完备的体系,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俄国本土的现实主义理论则是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三大批评家的一系列著述中建立起来的,并同样对俄罗斯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实质和内涵,以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为其集中体现,与欧洲及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有根本区别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除了字面上有相似之处外,毫无共同之处。后者根本不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极左政治对作家的一种政治要求或限定,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摈弃了现实主义的怀疑品格、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内涵,消解了它的美学旨趣和艺术追求。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内容,使得苏联极左文学理论相形见绌。而全部俄罗斯—苏联文学理论,更不是仅仅包括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世纪的“西欧派”“斯拉夫派”和“纯艺术论”等,白银时代的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理论批评流派,宗教文化批评,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诗学理论与批评等等,都是构成俄苏文学理论的重要板块。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时期极左文学理论之间,就更有天壤之别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根据自己对于文艺作品的广泛了解和文艺规律的深刻洞察,紧密联系生动的文学现象,精辟地阐述过艺术感觉的历史发展问题,提出了“人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的”这一著名观点,准确地把握到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还曾论及审美感受与审美对象的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主张评价文艺作品应当坚持“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这一“最高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倾向性时,曾创造性地提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等经典的文学概念[4](P174),明确指出“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4](P186-189),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悲剧和喜剧创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包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等在内的诸多伟大作家的评价,都表明他们的深厚艺术修养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这一切都是苏联的极左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所不可能掌握的,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做出阐述的。
因此,遵循“求实—科学化”路线的学者们所进行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在区分现实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极左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揭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有意义、有价值的遗产,为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提供资源和参照。
最后,重新评价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作家,包括许多似乎早已盖棺定论的作家。遵循“求实—科学化”模式,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的作家研究中,着重关注的是他在文学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上贡献的大小,不在政治的天平上衡量作家,包括不苛求“被招安”、被收编、沉默乃至变节的任何作家个人,而是由此而探测政治权力干涉、规约、控制文学的力度、深度及其效果,呼唤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格局的形成。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对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一系列俄罗斯经典作家的研究。例如关于高尔基,只要认真研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代表作并不是以往的评论所确认的小说《母亲》和散文诗《海燕之歌》,而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1935年2月,也即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开过不到半年,高尔基就在致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亚·谢尔巴科夫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怀疑。[5](P381-383)他始终没有成为个人崇拜的吹鼓手,断然拒绝撰写官方授意他的《斯大林传》,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例证。
遵循“求实—科学化”的研究模式,进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难度很大。给人看起来,这似乎是在为一种已经消逝的辉煌唱挽歌,当然其实并非如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对我们似乎很熟悉、实际上一知半解的文学进行重新审视的郑重和庄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抵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横行霸道。这一研究的客观效果,可能不像研究者自己所估计的那样明显,那样迅速见效,但是我们相信,它将必然在学术史上留下不可忽视的篇章,并将对未来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详见汪介之《高尔基之谜:“破解”还是曲解?——〈倒转“红轮”〉第二章读后质疑》,《文学报》2013年7月11日、25日。
[1](前苏联)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A].苏联文学艺术问题[C].戈宝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2]金雁.倒转“红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Бердяев Н.Русская идея: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XIX 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Москва: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2000.
[4](德)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Горький М.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Т.30.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 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6.
【责任编辑:彭民权】
I106
A
1004-518X(2017)11-0082-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科学院《俄国文学史》翻译与研究”(16Z DA196)
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7)
- 江西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茶泡"工艺对传承民俗文化的艺术价值
——评《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 乐理下的民间音乐鉴赏
——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欣赏指南》 -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评《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及其应用》 - 论油画创作的写意精神
——评《油画写意性研究》 - 浅析苏联模式对新中国雕塑教学的影响
——评《苏联雕塑教育模式与新中国雕塑教育》 -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创新发展研究
——评《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